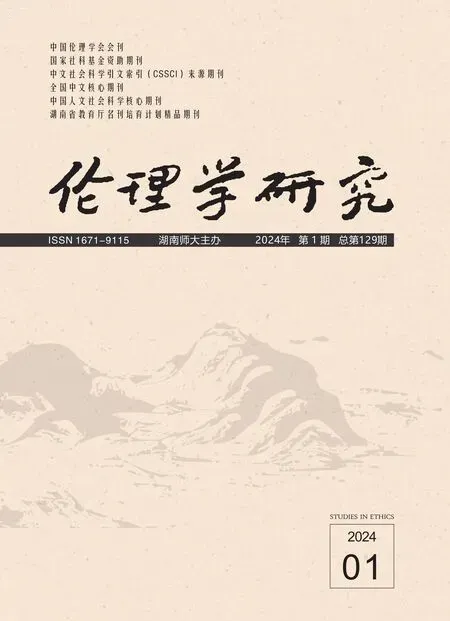家内关系的伦理辩证
2024-05-21胡盛澜
胡盛澜
伦理存在于关系之中,家庭的伦理本性体现于具体的家庭关系之中,对家庭的伦理理解要求对家内伦理关系进行阐释。以家庭关系为对象进行伦理理解,国内学界存在三条解释路径:一是儒家伦理思想的解释路径,即基于婚姻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所产生的夫妇有别、父子有亲、长幼有序等人伦秩序展开论说,围绕义顺、孝慈、友悌等伦理德性构建儒家伦理学视域下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解释框架①代表成果有陈林刚的《人伦之道及其内外和谐》(《江西社会科学》2006 年第6 期)、李祥俊的《儒学的人伦关系规范与自我认同》(《中国哲学史》2005 年第2 期)等。除了对家庭关系进行整体的儒家伦理的考察外,遵循此解释路径的成果还多散见于对具体家庭关系或具体伦理德性的研究。;二是吸纳西方哲学家们对家庭的法哲学演绎或现象学阐释形成家内关系的伦理解读路径,主要成果集中于黑格尔关于家庭的法哲学阐释和列维纳斯关于家的现象学阐释两个视角②孙向晨在其著作《论家:个体与亲亲》中就黑格尔与列维纳斯的家庭学说进行了分别解读。;三是将前两种路径相结合,发掘东西方理论对家庭关系理解的相通之处,此路径亦是对家内伦理关系进行创新理解的有益尝试③参见张再林:《作为“家际伦理”的中国式伦理》,《哲学分析》2021 年第4 期。张再林将儒家的家庭关系原理同列维纳斯的家庭关系学说进行对应性理解,寻找理论的相通性。参见邓晓芒:《黑格尔的家庭观和中国家庭观之比较——读<精神现象学>札记(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3 期。邓晓芒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家庭观同中国家庭观进行比较。。
事实上,聚焦于家庭关系进行伦理学解读的成果并不多见,原因可能在于家庭关系的伦理性从其直观上来看似乎是无需论证的命题,“家内关系是伦理的”正如“宗教信徒是有神论者”一样,属于经验确证的知识。故而,对家庭关系的伦理解读不在于证明其具有伦理性,而在于揭示家庭伦理性关系背后所涉及议题的逻辑同一性。在为数不多的对家庭关系进行伦理解读的理论成果中,学者们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关注自我与他者、特殊与普遍、个体原则与伦理原则能否同一、如何同一等家庭伦理精神发展的辩证环节。这是因为,作为家庭伦理精神的现实化,家庭伦理关系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个体与实体关系的辩证统一。在秉持“伦理地理解家庭”这一基本线索的基础上,本文将遵循家内关系伦理理解的第三条研究路径,结合黑格尔关于家庭的法哲学阐释与中国传统家庭的伦理实践来试图呈现家内伦理关系内在的辩证运动。
一、夫妻关系的伦理法内涵
《周易》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周易·序卦》)《颜氏家训》则言:“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也,不可不笃。”(《颜氏家训·兄弟篇》)围绕家内关系,最为关键的三重关系在于夫妇、父子、兄弟,而其中又以男女夫妇关系为家际关系的源始。
所谓“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孟子·万章上》),意指“人之伦类肇自男女夫妇”[1](174)。夫妇关系之于父子关系、兄弟关系而言具有源始性地位,根本上源于自然发生学层面的优先性——有婚姻关系继而产生家庭、孕育子女;同时又表现为社会规范层面的优先性——婚礼作为婚姻的定在是为“礼之本”。婚姻的本质特征呈现于传统婚礼之中:“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性,所以附远厚别也……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礼记·郊特牲》)其一,传统婚姻的重要规定在于“男女有别”,夫妻遵循不同的礼法规定;其二,自周代始,婚姻缔结讲究“同姓不婚”,是以“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其三,婚姻的重要目的在于“合二姓之好”,基于“取于异姓”的要求,婚姻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礼记·昏义》)。对于婚姻关系来说,这里出现了“别”与“合”这样一组既相互对立又彼此转化的范畴,既强调夫妻双方的男女之别、家族之间的“附远厚别”,又在婚姻关系的建立中实现夫妇同体、二姓之“合”。
所谓婚姻中的“别”,一方面体现在基于自然基础的“男女之别”,主要考虑男女性别的生理差异及父权制文化的影响:在“力”的层面上的强弱区分使家庭分工自然地走向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男性与女性在婚姻中所承担的“夫”“父”与“妻”“母”的不同角色决定了双方承担着不同的道德责任,两性的自然差异及父权社会的文化结构赋予了婚姻关系中的男女个体不同的道德期待。婚姻之“别”的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国传统婚姻制度中的“同姓不婚”与“附远厚别”,主要是出于乱伦禁忌和外婚制的需要及姻亲融合的社会期待:首先,在人类学研究中,可以看到古代社会普遍存在外婚制的传统,周代婚姻制度明确提出同姓不婚,《左传》中的“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或可见古人朴素的优生学考量;其次,“附远厚别”意在建立同异姓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伴随着两姓之家的男女个体缔结婚姻关系和生养后代,异性家族之间就建立了血缘层面的牢固关系。有学者指出,周人推行的“同姓不婚”的婚姻缔结原则同“男女有别”的社会伦理原则的结合在具体实践中为夫妇关系中女方的地位提供了思想和制度保证[2](45)。此处无意与现代男女平等理念进行内涵上的对比,但男女之“别”包含的朴素的平等性与个体性观念需要得到承认。不论是自然之“别”还是社会之“别”,可以看到婚姻的开始是两个个体的结合,婚姻的意志在结合初期就具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异质性”。
所谓婚姻中的“合”,是在男女之“分”与夫妇之“别”的基础上所期望达成的婚姻的伦理目的。一方面是夫妇关系维度的“合”。《礼记·昏义》有云,“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唯有遵守“男女之别”,而后才能实现“夫妇有义”,这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维,在充分尊重男女之别、各行其是的前提下,夫妇的结合才能达到“义”的要求。夫妇之“义”不是无差别性的,而恰恰基于这种有差别的亲密性,才能达至“夫妻一体”。另一方面是家族关系维度的“合”。古人重视婚姻有三个重要原因:一为合二姓之好,二为上事宗庙,三为下继后世。从家族关系的维度来看,“合二姓之好”是以姻亲关系将社会不同氏族、家族联系在一起,使单一、封闭的宗亲关系转化为全面、开放的宗亲—姻亲关系;“上事宗庙”“下继后世”则是在祭祀和生育的层面为维系和传递本家族(主要是男性家族)的香火以实现家族繁盛发展。婚姻之“合”是以个体为基础的两个人具有法的意义的结合,是以爱为基础的伦理性结合。通过婚姻,男女两性建立了家庭,于是家庭的一切人伦关系皆自夫妇关系而生,夫妇伦理之际构成人伦之始就在于由“别”而“合”的差异性同一。
中国传统婚姻的由“别”而“合”、“不同而一”的朴素辩证思维同黑格尔关于婚姻中“爱的辩证法”不谋而合,黑格尔指出,“爱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不欲成为独立的、孤单的人,我如果是这样的人,就会觉得自己残缺不全。至于第二个环节是,我在别一个人身上找到了自己,即获得了他人对自己的承认,而别一个人反过来对我亦同。因此,爱是一种最不可思议的矛盾,决非理智所能解决的……作为矛盾的解决,爱就是伦理性的统一”[3](199-200)。黑格尔以爱的情感为夫妻关系的“不同而一”找到了符合人的自然秉性的关键元素,在不强调“二姓之好”甚至“男女之别”的现代社会,爱的情感成为个体走向婚姻“共同人格”的重要驱动。婚姻关系的缔结使伦理家庭得以成立,在家庭中,夫妻双方克服了不同人格的对立与差异,形成完整、同一的家庭人格,婚姻因其伦理性而具有了不可离异的特性。
不论是传统社会缔结婚姻的“家族意志”,还是现代社会缔结婚姻的“个体意志”,婚姻关系就其本性来说是两个个体的伦理性结合,它的实体性存在表现为夫妻生活的伦理实践,包括家庭关系的再生,如生育和抚育子女、创造共同的家庭财富等。夫妻关系所体现的由个体性走向实体性的同一体现了婚姻关系的伦理法内涵。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婚姻是由两个个体的结合开始,就意味着伦理性结合存在分裂的潜在可能,尽管婚姻的伦理法内涵规定着自身的不可离异性,但不可回避的是伦理自身的裂解恰恰隐藏在它的产生阶段。现代社会婚姻关系所面对的“原子式个体”所形成的伦理危机或许正在造成“伦理的裂解”。
二、父母子女关系的伦理报施结构
夫妻的伦理性结合的现实定在之一是子女的生育和养育。在中国传统社会,“下以继后世”是婚姻缔结的重要目的,而随着儒家伦理对孝道的推崇,家族的子嗣传承成为家庭最为关键的环节,父子关系在社会价值层面甚至超越了夫妇关系在人伦关系中的地位。在黑格尔看来,子女是婚姻关于“爱的辩证法”的现实形态,是“爱的客观化”,“在夫妻之间爱的关系还不是客观的,因为他们的感觉虽然是他们的实体性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还没有客观性。这种客观性父母只有在他们的子女身上才能获得,他们在子女身上见到他们结合的整体”[3](213)。这种“实体性的爱”的客观性体现在精神中,即父母相互的爱及子女所得到的父母的爱。父母与子女关系的亲密性归根结底源自直接的血缘关系所产生的深刻情感羁绊,血缘使父母与子女之间产生天然的情感联系。
基于自然的血缘亲情而产生的伦理性的施报关系是父母子女关系的基本特征。人类由于直立行走的姿态限制了骨盆开口处的宽度,而骨盆开口的宽度又限制了产道,使得孕妇只能在婴儿还不成熟时就进行分娩,结果造成人类抚育子女极其漫长和艰难;此外,不同于动物只需要自然层面的养育,人类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父母还肩负道德培育、精神教养的职责,父母对子女在自然和文化层面的双重养育使子女对父母的付出更觉“恩重如山”。于父母而言,子女是爱的结晶和血脉的承继,对子女倾注心血与爱意是天然本能;于子女而言,父母生养的恩情催生“报本反始”的情感冲动。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施报关系之所以是伦理性的,是因为它基于自然血缘关系所产生的孝亲意识。张祥龙认为,正是养儿艰难的时间意识效应成为“孝”出现的契机,致使子女在父母年迈时仍然会事以尊重和照顾甚至逝去后依然会怀念和感恩,而孝道则是对这种孝行的自觉化、深刻化和信仰化[4](17)。孔子认为父母过世需守孝三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三年之丧”是有感于父母怀抱三年,更是孝的情感意识的流露和表达,在观念层面应予以重视和尊敬,在实践层面更应自觉恪守。孔子对学生宰我在父母丧期“安乎于食稻、衣锦”的态度表示不满与谴责,认为人应当合于自然情感(亲情)的流露,而不应与之背反。在自然情感的基础上,和谐理想的父母子女关系的现实化应当是形成父慈子孝的代际伦理关系与伦理行动。在传统父子人伦的孝慈结构中,相较于本源于父母养育子女过程中投入的自然情感催动的慈爱,子女对父母的孝亲意识则被赋予更多规定性,孝道内涵规定了子女应该在物质上奉养父母,在精神意志上做到无违与敬顺。《尚书引义》中王夫之有言:“所谓肖子者,安能父步亦步,父趋亦趋哉,父与子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志。”子对父的孝道实践关键在于对父母意志、经验的继承,而不是跟随着父母的意志亦步亦趋,因为父与子本质上“异形离质”,就“志”的承继而言,父与子是两个个体性的存在,具有朴素的平等观念。对父子关系“异形离质”而又亲密共生的认识是父慈子孝的代际伦理生动和谐发展的关键。
而在具体的伦理实践中,中国传统社会对孝道的规定伴随着以孝治国、移孝作忠的伦理政治化实践而变得越发严苛起来,进而造成孝道观念的结构化和纲常化。“父为子纲”成为“君为臣纲”的道德规范性来源,父子人伦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同构化最为直接的表现为父子关系延伸成上下尊卑关系。父子双向关系的非自然化应用一旦超过限度便存在着内在失衡的危险,对“异形离质”的忽视和对“恩养施报”的片面强调在思想层面催生反抗父权压迫、争求个体解放的观念意识,在社会制度层面则自然地走向父权制度衰落、契约社会兴起的历史命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父母子女关系作为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被运用于国家制度中,显化为公共关系的家庭化拟制,而问题在于,国家律法同伦理家庭的父权法之间在面临冲突时难免相互掣肘。“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伦理奥秘即在于此。国家律法下的个体身份同家庭中的父子角色所形成的冲突本质上是公共领域同私人领域的规则区分,也是理性法则与情感法则的内在对立,传统社会中家内的父慈子孝扩充到政治实践的君仁臣忠在现代社会必然失去合法性。
总而言之,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一方面呈现为基于血缘关系所形成的父慈子孝的和谐伦理关系;另一方面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又呈现出内在冲突,即父母子女关系在家庭中的伦理“不平等”和在社会交往中的个体“平等”的相遇,具体而言:一是父权至上的孝道优先性造成父母子女关系的不平等,二是家庭伦理法跃出适用范围产生社会应用的不适应。
对于父母子女关系所呈现的两面性,黑格尔对父母子女关系的表述认为,婚姻关系生育子女,世代传递本身就是家庭精神在有限自然界显现自己的一种方式,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在子女这样的他物身上看到了夫妻间的相互怜爱。“在子女身上这种统一本身才成为自为地存在的实存和对象;父母把这种对象即子女作为他们的爱、他们的实体性的定在而加以爱护。”[3](212)而子女这个他物作为“异己的现实”对父母的情感则是恰恰相反,“他们看到自己是在一个他物(父母)的消逝中成长起来,并且他们之所以能达到自为存在和他们自己的自我意识,完全由于他们与根源(父母)分离,而根源经此分离就趋于枯萎”[5](14)。父母子女之间“爱”的情感的相互过渡和时有侧重,恰恰表明了家庭伦理实体中父母子女间和谐共生的伦理关系,于中国传统伦理中的父子关系而言,就是摆脱了结构化、纲常化所天然呈现的孝慈关系。当然,黑格尔亦指出家庭成员尤其是男性成员最终将走向市民社会成为个体性的存在,而踏入市民社会这一特殊领域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法权意识的树立与伦理意识的消亡。对于家庭所代表的私人领域同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的交叉与冲突,黑格尔选择在兄弟姐妹之间“安静而平衡”的伦理关系中进行探讨。
三、兄弟姐妹关系的伦理平衡
第三种家庭内部的人伦关系——兄弟姐妹关系,被认为是一种“安静而又平衡”的伦理关系。黑格尔认为夫妻关系和父母子女关系总是处于相互过渡的不平衡状态中,而兄弟姐妹关系则是一种毫无混淆的纯粹伦理关系,同一血缘来源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安静与平衡”,因为兄弟姐妹之间既不像夫妻之间那样彼此欲求,又不像父母子女关系那样彼此牵制,他们彼此“各是一个自由的个体”[5](14),因而,兄弟姐妹关系被认为是纯粹伦理性的,这一关系扬弃了情感的任意性,纯粹地遵循着家庭的伦理精神。在兄弟姐妹关系的伦理平衡中,我们期待看到理性与情感的和解,以及公共领域的个体性原则同家庭领域的伦理原则之间的和解。
首先,兄弟姐妹关系具有最为直接的平等性,同辈血亲所带来的情感联系和长时间的相伴成长给兄弟姐妹关系带来天然的亲密性。兄弟姐妹间的关系概以兄弟关系进行表达。兄弟之间的伦理关系在儒家传统伦理规范中被规定为“兄友弟恭”,即以长幼为序、兄长应当友爱弟弟、弟弟应当恭敬兄长的伦理秩序。尽管存在着“幼”对“长”的恭敬、顺从的一面,但这种“恭敬”在同辈兄弟之间却不意味着兄长对弟弟的绝对权威,相反,它要求兄长对幼弟倾注更多的友爱与照拂。在五伦关系中,兄弟关系和朋友关系并没有被“纲常化”,这是由于兄友弟恭的伦常规定中不具备单向强制性的现实基础,长幼之“序”强调的是先后之分而非上下之别,兄友弟恭的和睦形成于同根同源的血缘情感和长期相处与共同成长所产生的深厚情谊。《诗经·小雅·常棣》歌颂兄弟间不可替代的情谊:“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遭遇死丧有兄弟相收,面临急难有兄弟相救,抵御外侮有兄弟相助,这种情感关系相较妻、子和朋友关系甚至更为珍贵。《颜氏家训》亦有言,“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颜氏家训·兄弟》),兄弟是“分形连气”的另一个“我”,既如手足,断无尊卑上下之分别,故而,团结友爱是兄弟伦理的核心主题。
其次,兄弟关系的亲密、平等特性使其遵循的伦理原则更容易推扩至社会交往层面。孔子言,“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对待乡党要克修悌德;《孝经》言,“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人为人兄弟者也”,因之“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正是伦理型社会中人际交往的理想形态。关于兄弟关系在社会层面的应用,西方哲学亦有相似的观点论述,兄弟关系(fraternity)这个词本身就有“博爱”的意思,即人类之爱,列维纳斯认为,“人类自我在兄弟关系中确立,人人皆兄弟这一点并不是像一种道德成就那样被添加到人身上,而是构成人的自我性”[6](274)。兄弟关系的推扩所面向的社会生活是合乎情理的伦理生活,人与人的交往在朴素的平等意识基础上遵循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的社会伦理秩序。
最后,兄弟姐妹关系所具有的自足、平等、有序等规范性特征致使这一伦理关系被期待塑造成为个体互惠、有序和谐的公共社会交往关系的理想范型。尽管我们承认兄弟姐妹关系具有相对自足性和情感互不欲求特性,但作为家内伦理关系的重要一环,必须看到的是,兄弟姐妹关系所达成的“和谐与平衡”仍然前提性地建基于血缘情感逻辑之上。一方面,兄弟友爱和长幼之序在儒家伦理规范中可以得到最广泛的应用和推扩,不同于夫妻关系的不可推扩性和父子关系的阶级性特征,维系兄弟姐妹关系的长幼之序及其原则具备向社会推扩的现实基础;但另一方面,作为家庭伦理关系的重要一环,兄弟姐妹关系在传统社会又具有相对有限的推扩半径,或局限于熟人社会,或止于圣贤君子的精神交往,它所调节的主要范围是熟人社会,而非现代公共社会所诉求着力调整的陌生人社会[7](99)。儒家伦理对社会规范的根本设计依赖于“亲亲”而“泛爱众”的情理逻辑,希求以“亲亲”原则达成“仁民”“爱物”乃至“民胞物与”的私人向公共空间的大跨越。现实却是,熟人社会所因循的情理逻辑遭遇现代公共社会的挑战,依赖血缘情感的“亲亲”原则与四海之内皆兄弟式的“博爱”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逻辑断裂。而这一断裂在黑格尔对兄弟姐妹关系的探讨中得以被明确揭示。
事实上,作为伦理性的关系,兄弟关系同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一样,无法回避以契约精神为底色的现代社会个体性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挑战。在黑格尔那里,民族原则同家庭原则的对立冲突借由兄弟姐妹关系的纯粹伦理性判定被直接地提出,借着安提戈涅不顾国王克瑞翁的禁令,将反叛城邦的兄长波吕尼刻斯安葬的选择,黑格尔阐明了家庭精神所代表的“神的规律”与民族精神所代表的“人的规律”之间的对立冲突。黑格尔对于安提戈涅的行为显然是赞赏的,因为“弟兄的丧亡,对于姐妹来说是无可弥补的损失,而姐妹对弟兄的义务乃是最高的义务”[5](15-16)。尽管黑格尔以兄弟姐妹中的男性与女性为代表呈现两种势力的冲突,但从根本上说,黑格尔是借由兄弟与姐妹所遵循的不同原则提出家庭伦理法与城邦公共法之间的冲突。对这一冲突的解决,显而易见的理想方向是实现理性法则与情理逻辑的合契,这恰恰是伦理不可回避却难以回答的持存话题。在跳出安提戈涅所面临的极端对立境况后,无法否认的是,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实践中,兄弟姐妹关系仍然是与现代社会中个体化交往融合度最高的伦理关系,其本质的伦理性的“安静和平衡”并不会因为外部冲突而轻易变更。事实上,真正可能扰乱这份“安静和平衡”的或许是存在于当下或未来的关系灭绝隐患,表现为少子化危机可能造成的兄弟姐妹关系的自然灭绝以及个体性对家庭的过度入侵所造成的家庭伦理精神的丧失。当然,后者是所有家内伦理关系共同面临的问题。
四、个体与实体关系的家庭精神演绎
从伦理的视角理解家庭关系是以家内成员之间的关系为表征的家内成员同家庭整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伦理关系是个体与伦理实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解家内关系的辩证运动的关键在于理解家庭成员同家庭伦理实体、家庭伦理精神之间的辩证内涵。基于此,透过对家庭内部伦理关系的分析,将家庭精神及其现实化的本质特征归纳为以下三点:(1)伦理性的家内关系呈现为个体与实体的同一关系;(2)达到“实体性的同一”的家庭关系自身存在裂解的可能,并且伴随着历史观念的更迭正在现实地发生着;(3)家内伦理关系的辩证运动内在地构成并呈现着家庭精神的历史演绎。
首先,“家庭精神”是在个体与实体的精神统一中实现的,因而家内关系呈现为个体与实体的同一关系。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之间相互的情感关系本质上是对家庭精神的普遍尊敬,“义”“顺”“孝”“慈”“友”“恭”等人伦规范本质上是基于自然情感的伦理表达和个体对实体性精神的伦理体悟。对于家内关系中的情感,黑格尔释以“伦理性的爱”,这种“爱”是伦理的,是对实体的虔敬,而不单单是个体之间的特殊情感[8](4)①贺麟与王玖兴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翻译中,将夫妻之间的爱称为“怜爱”,父母对子女的爱称为“慈爱”,子女对父母的爱则称为“敬爱”,这些家庭中的伦理性的爱都译自德文Pietat。邓晓芒认为对Pietat 的区分化翻译使它丧失了源本的词义,德文原意并不是自然的爱的情感,而更倾向于(对神的)虔敬、崇敬、尊敬之意,或可理解为一种对实体的伦理性的“尊敬”。当然,除了伦理性的“尊敬”,黑格尔还提到另一种自然的联系和情感,称为“感动”(Rührung,原意为拨动、搅动),正是在自然情感的激发下,伦理的尊敬形成,而尊敬中亦带有自然的情感。相关阐释参见邓晓芒:《黑格尔的家庭观和中国家庭观之比较——读〈精神现象学〉札记(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3 期。。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亦指出,“是家庭要求他们联合,是家庭使得他们爱与被爱、敬与互敬。家庭使所有这些关系带上了一种特殊的印记,提升到了那些个体之间的简单关系之上。直到今天……即使不再有家祠,不再有家神,人们对家庭也会始终不渝地充满了宗教之情;家庭是不容触动的一方圣土,其原因就在于家庭是学习尊敬的学校,而尊敬又是最重要的宗教情感。此外,它也是全部集体纪律的神经”[9](62)。作为自然的伦理实体的家庭,它所特有的精神对家庭成员具有统摄的力量,在这种伦理力量的统摄中,家庭成员成为伦理性的个体。对于伦理实体,黑格尔曾言:“伦理性的实体,它的法律和权力,一方面作为对象,对主体说来都是存在的,而且是独立地——从独立这一词的最高涵义来说——存在着,它们是绝对的权威和力量,要比自然界的存在无限巩固……另一方面,伦理性的实体,它的法律和权力,对主体说来,不是一种陌生的东西,相反地,主体的精神证明它们是它所特有的本质。”[3](189-190)家庭的力量在于,其自身的精神对家庭成员来说就是法律,就是权力,而家庭成员在其中既是伦理的参与者,又是维护者,是家庭实体性关系的构成主体亦是承载家庭伦理精神的客体。因而,家内关系的伦理理解就是看到家庭成员与家庭伦理共同体间的实体性关系而非单纯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
其次,尽管家内关系呈现为实体性同一,家内关系的伦理性仍然存在裂解的潜在因素。传统婚姻关系所体现的“男女之别”“两姓之合”“夫义妇顺”内在地隐藏着两性角色间的对立一面,父母子女关系的“父慈子孝”在代际伦理政治化后出现了尊卑上下的不平等地位,兄弟姐妹关系所达到的“安静与平衡”在现代社会则面临少子化(尤其是独生子女化)带来的自身关系灭绝的伦理危机。在中国传统的伦理社会,家庭精神具有统摄力量,它既体现为家庭伦理意志对家内关系、家庭成员的精神规定与意志统合,又在伦理政治化之后获得了社会政治层面的合法性,这使得家内关系的对立统一表现为“实体性的同一”是既合乎情理又合乎逻辑的。然而,在“实体性的同一”背后仍然存在着家庭成员作为个体对自身承担的伦理角色的自我认同和自我理解,这构成了家内关系“伦理性的裂解”的潜在因素。近代社会以来,传统伦理观念伴随社会变革发生了剧烈转向,中国近代的启蒙先驱们发出“逃离家庭”的呐喊,倡导新青年们成为独立个体而非遭受等级秩序压迫的家庭成员,性别平权运动和父权制批判成为击破传统家内等级秩序的直接表达。相较于传统社会注重整合家内成员的个体意识以实现同伦理型社会实体精神表达的嵌合,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大使发轫于“个体主义”观念的人格平等和权利契约意识逐渐浸入家庭领域,这构成了家内关系“伦理性的裂解”的外在因素。当家庭的实体性意识同家庭成员个体的自我实现之间出现价值抵牾时,家庭内部出现了诸如婚姻关系易碎、育儿及养老困难、丁克观念及少子化所带来的兄弟姐妹关系灭绝等现实状况,人伦关系面临原子化的现代性危机。
对于此,学者李祥俊就儒家人伦关系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见解:“儒学的人伦关系规范来源于人的生活实际,但一旦规范化、知识化、制度化以至本体化,它就既构成人的精神家园,同时又构成对真实生活的遮蔽,理想的精神家园就可能异化为创造性转化的自我的桎梏……反思儒学的人伦关系规范与自我认同,就需要我们时时透过儒学所建构的人的精神家园,去查看其背后的源初的地基——生活世界本身。”[10](66)就家内伦理关系的辩证运动而言,不论是“实体性的同一”还是“伦理性的裂解”,最终都要回到变化的生活世界即伦理生活中去寻找答案。希求自我价值实现的个体意识和维护家庭共同体团结的实体意识之间的精神统合需要回归到最为本真的情感生活和伦理实践中去。一方面,家内关系应当以“爱”的情感为前提,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维护,建立起彼此尊重、敬爱互助而富有韧性的情感连接,在日常的伦理生活中以“实体性的同一”的家庭精神实现对家庭成员的意识观念陶铸。另一方面,在自古以来重视人伦关系的中国社会,内外因素共同作用所造成的家内关系“伦理性的裂解”不应也不会走向家庭成员内部关系无差别的均等化。事实上,对家内角色的自觉体悟和家庭价值的感性实践未尝不是克服原子主义“现代性碎片”的重要出路。
最后,家内伦理关系的辩证运动内在地构成并呈现着家庭精神的历史演绎。家内伦理关系的辩证运动在近代社会外化为家庭观念的变革,这一变革离不开公私之分、古今之辩、中西之别的讨论。伴随市民社会的扩张和个体自由观念的传播,家内关系中个体性与特殊性的无意识在场在新领域、新观念中获得了自身发展的土壤。而所有这些思想观念的变化又动态地体现在家内伦理关系的历史变迁中,伦理的家庭正是在家庭成员个体性与实体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运动中呈现其不断更新的存在形态。家内伦理关系的辩证运动同社会层面的政治经济生活、思想观念运动息息相关。就理论领域而言,西方世界表现为启蒙运动后围绕自然家庭、市民社会、契约国家展开的论争①霍布斯、洛克对家庭的解读带有国家契约性;康德延续了自然法学家们的论述以市民社会的新概念来理解自然状态的家庭;黑格尔把握到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不同,指出正是伴随着市民社会转型,家庭观念发生变迁;亨利·梅因从法学层面指出社会进步促使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被用以代替源自“家族”各种权利义务上的那种互相关系,“个人”于是替代了“家族”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中国社会则表现为五四运动时期围绕“个体”与“家庭”展开的论争②《新青年》杂志最早提出“个体”与“家庭”之间的论争,由此,五四运动时期的学者们推崇个体主义并展开对家庭主义的激烈批判,传统社会“身—家—国—天下”的伦理观念受到挑战。。不论是以西方文明为镜像还是以现代文明为准绳,家庭精神就其根本而言是以家内伦理关系为内容的个体与实体关系的伦理精神呈现,其存在形态变迁是以家内关系中个体与实体的价值让渡为“经”,以历史向度内思想观念变化为“纬”而展开的历史与现实演绎。
总而言之,对于家内关系的辩证分析试图揭示儒家伦理框架下的家内关系所呈现的个体与实体关系的现实表达,这一关系同黑格尔法哲学所论述的家庭伦理实体内部关系所具有的辩证有机性特征内在相合。尽管家内关系作为自然情感关系在人类社会的普遍表达上具有相似性,作为一种描述性的理论相近似乎不足为奇,但是对家庭实体性及家内关系个体性与实体性辩证同一的伦理认知才是儒家伦理同黑格尔法哲学所共同切中的现实要义。进言之,对儒家伦理框架下所内生的个体性与实体性辩证同一的家内关系的认识路径将有助于我们以一种现代性的视角去理解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存在形态在近代化及现代化过程中所呈现的变迁状况,并旁击传统儒家伦理在现代性的理论转型中所面临的自身困境和应对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