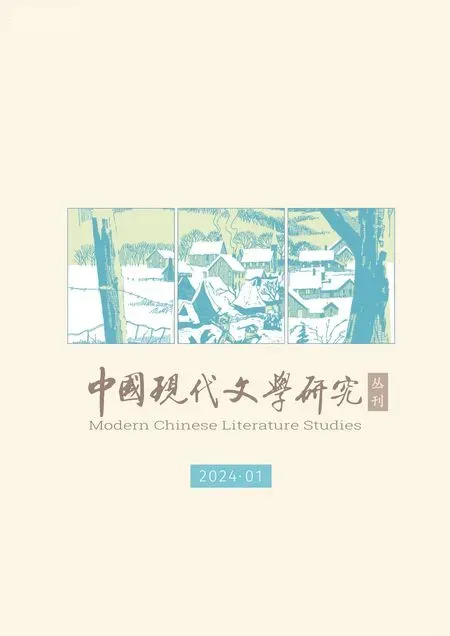“他者”的位置※
——关于1927年夏天鲁迅的一个文本群1
2024-05-18邢程
邢 程
内容提要:鲁迅1927年6月至8月间的著述中,存在这样一个文本群:《〈小约翰〉动植物译名小记》、《朝花夕拾·后记》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三个文本分别处理了非母语的、非文字的以及非现代的三个维度的“他者”。在广义的“翻译”的视野中重新阐释这样一个文本群,可以看到作为现代文学主体的鲁迅在“清党”后被动的沉默里,如何将诸种“他者”内化为自我确认与自我重建的可能性方案。
1927年国民党“清党”以后,鲁迅滞留广州,并在那里度过了整个夏天。2按,鲁迅于当年9月18日“整行李”,27日登船离粤。参见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年谱》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若以编年的办法盘点鲁迅这段时间的著述,在大量的译作之外,我们可以标记出这样一个文本群:6月的《〈小约翰〉动植物译名小记》,7月的《朝花夕拾·后记》,以及8月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这三个文本,无论体式还是内容,似乎都并无太大的相关性,放在1927年鲁迅驻留广州的语境里看,更像是他在被动的沉默里要刻意避开时事而做的几种零散的文本实践。但相比于1922年底《呐喊·自序》追述的“抄古碑”心境,即为了“麻醉自己的灵魂”而“沉入于国民中”与“回到古代去”,1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页。1927年暑期的这个文本群背后存在着一条质地完全不同的线索。概言之,《小约翰》的动植物译名问题、《朝花夕拾》的“后记”与重述“魏晋风度”,指向的都是某个意义上的“他者”:非母语的、非文字的(《后记》围绕《二十四孝图》与“无常”的图像考据展开),以及非现代的。但此时,鲁迅的姿态不再是“沉入”与“回到”,而是广义的“翻译”,2按照罗曼·雅克布森的区分,这三个文本分别指向三个层面的翻译实践:语言之间的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小约翰〉动植物译名小记》处理的是德文/英文被译为汉语的过程中产生的名实分离的问题;符号系统之间的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朝花夕拾·后记》处理的是图与文两种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问题;语言内部的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将古代资源转换为当下话语。参见Roman Jakobso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14。即在自我的、现代的、汉语白话的主体立场上,处理、再现并同化上述“他者”。
“他者”的位置由此构成我们重新解读这三个文本的视角。作为个案,跨语际的翻译、跨媒介的转换与历史讽喻各自要求不同的分析办法;而作为一个问题域,将三件阐释工作集于一处,则有助于提示鲁迅的文学主体姿态。在1927年左右,以及日后的上海时期,这种姿态或许是一种根柢性的东西,通向对另外一些“鲁迅难题”的解决。
克服“不可译”
《〈小约翰〉动植物译名小记》的起笔与写成,据鲁迅自叙,是出于翻译《小约翰》后的“意有未尽”。作为《小约翰》本文的一篇“附录”,这个在跨语际实践过程中衍生出的文本,标记出了翻译工作所要处理的一个具体的语言单位,即名物系统。基于《小约翰》自身的文本特质,译者需要不断面对他者语言内部的动物和植物名称,并将其一一译入汉语。也就是说,在翻译这个带有“成长小说”1张旭东指出:“……当代国际文学界……一般并不把它当作童话看待(尽管它有一个童话式的开篇),而是侧重于它作为‘成长小说’所包含的广泛的社会经验及其复杂的象征-寓言呈现。”参见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735页。性质的童话作品时,译者必须要为原作中那个物的世界(体现为德语与英语2关于鲁迅翻译《小约翰》所使用的底本问题,参见易彬《鲁迅译〈小约翰〉的若干文献问题论析》,《现代中文学刊》2022年第1期。)在目标语言内建立相应的命名系统。这之所以造成翻译的困难,是因为鲁迅发现白话文的名词系统不敷于用,换言之,外语世界中的名词(在《小约翰》里具体体现为自然界中的名词),在汉语白话里找不到明确的、至少是令鲁迅满意的对应。3这个问题周作人也指出过:“中国语文体的缺点是语汇太贫弱……辞汇中感到缺乏的,动作与疏状字似还在其次,最显著的是名物。”周作人提出的补救方法是在古语和外来语之外,要特重方言的引用,用方言词汇补之。见周作人1936年《〈绍兴儿歌述略〉序》,《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181页。
不难想象,造成这种翻译困境的一个原因,是汉语的经验世界与源语言的经验世界之间的不可通约。具体到动植物问题上,背后则是科学体系与科学方法论在有与无、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是文化、技术层面的而非语言本身的因素,使《小约翰》源语言的动植物世界相对于汉语白话而言成为一种“不可译”的对象。4熊鹰指出,鲁迅在翻译《小约翰》时遇到的困难与语言能力无关,“他所面对的是荷兰自成为海上霸主以来所积累的浩海无边的动植物知识”。参见熊鹰《从〈小约翰〉到〈药用植物〉:鲁迅反帝国主义植物学的一次翻译实践》,《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6期。本文认同这一观点,但本文并不意图在民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的框架之下理解鲁迅的名物翻译实践。
鲁迅的《小记》记录的就是对这种“不可译”的克服。他最初的解决方案是由《新独和辞书》(德日词典)查出所译对象的日本名,再到《辞林》中去索寻相应的中国字,5鲁迅:《〈小约翰〉引言》,《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但仍然有“二十余”动植物名无法通过这种操作获得着落。鲁迅于是请托周建人帮忙查阅德文的动物学与植物学材料,然后在中国名词系统中寻找德文学名的对应物,这个过程中周建人使用的汉语材料是“中国唯一的《植物学大辞典》”6鲁迅:《〈小约翰〉动植物译名小记》,《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247页。。此方法收效亦不佳,并且进一步暴露了汉语命名系统的问题。
一方面,“那大辞典上的名目,虽然都是中国字,有许多其实乃是日本名。日本的书上确也常用中国的旧名,而大多数还是他们的话,无非写成了汉字。倘若照样搬来,结果即等于没有”。这里鲁迅捕捉到并描述出的语言现象,正是约三十年后被高名凯、刘正埮1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鉴别出的三类汉语外来词之一,即“古汉语原有的词汇被日语借用来‘意译’西方词语,这些日语词后来又返回到汉语当中,但词义完全改变了”2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5、46页。。这一跨语际实践中“最具透明性的假象”3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5、46页。一旦被识别出来,外来词在追根究底的译者那里就无法成为翻译实践的最佳选项。
另一方面,《小约翰》文本中动植物意象的繁多,某种程度上正是其“童话”性质决定的;而这个特质使得《小约翰》在“跨语际实践”的过程中,较其他类型的被译文本而言,能够更为清晰地提示出语言现象的三个成分:首先,动植物意象的设置,分离出了词(符号)与其在自然世界中的指涉物;其次,在将这些符号转码至另一种语言系统中时,符号内部的能指与所指又进一步被离析了出来。在翻译的过程中,动植物这个物质实在界,成为鲁迅检验符号内部意指关系的一个环节:“只是中国的旧名也太难。有许多字我就不认识,连字音也读不清;要知道它的形状,去查书,又往往不得要领”4鲁迅:《〈小约翰〉动植物译名小记》,《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247页。,“即使查出了见于书上的名,也不知道实物是怎样”5鲁迅:《〈小约翰〉引言》,《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226、225~226页。。“要知道它的形状”“知道实物是怎样”即要求在实在界以经验的方式把握符号的有效性,这作为翻译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反过来揭露了中国旧名在指认新的经验世界时的僵死状态:“查书”的结果是“往往不得要领”。如此,日本名与中国旧名都成了“词的尸骸”(the carcass of words)6乔治·斯坦纳转引阿达莫夫,见乔治·斯坦纳《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孟醒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6页。,这就驱使译者不得不在句法结构的“务欲直译”而“反成骞涩”之外,7鲁迅:《〈小约翰〉引言》,《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226、225~226页。另要费神于汉语名词的辨析与再造。
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翻译《小约翰》的动植物,不仅仅是将名物系统在汉语白话里登记造册,更重要的是,他在此过程中探测了语言哲学的深度。相对于创作,翻译——尤其是名物系统的翻译——更能够为这种“探测”提供合适的场所和机会。通过外文名词而重新认识并整合一个物的经验世界,再将这个经验世界落座于白话汉语中,这是一个能指与所指不断穿梭和互相寻找的过程。当译者开始意识到,在情节内容和句法之外,名词(符号)这个单位内部也需要爆破和重建的时候,新文学的进步和“现代”就已经不仅仅在于博物学意义上的知识扩展,而是一种语言自觉;或者说,知识扩展相对于语言自觉,在新文学的实践中只能是第二位的,处于发生链的下游。相比于物质世界的建设、思想主张与意识形态的彰显,语言自觉是被编织在文本内部的、较为隐微的机制,对倾向和习惯于在文学那里追问观念的读者而言,语言自觉也是一个相对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假如我们可以暂时转换一下思维方式,从另一个方向来思考文学、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那么文学固然是对现实的摹仿和再现,但同时,语言的构型与演变也在形塑着文学主体的思维——特别是在中国新文学这个文学的初级阶段甚至草创阶段——从而影响着作为文学表现对象的现实。
一个可堪参照的对象是以周作人译笔为主的《域外小说集》。张丽华指出,在东京版(1909)中,周作人将英译底本的sparrows,swallows “一律译为‘黄雀’”,将nightingale “译为‘黄鹂’”,将pines,beeches,golden orioles译为“松柏鸣禽”。1张丽华:《文学革命与〈域外小说集〉的经典化》,《文艺争鸣》2019年第5期。而假如我们将之与《小约翰》关联起来,会发现这些名物正类属于后者的动植物学范畴,两相对照,可见1927年鲁迅在探测语言单位时所采用的更精确的度量衡。也就是说,周作人“向中国文化归化”以及“颇具林译风味”的译法,2张丽华:《文学革命与〈域外小说集〉的经典化》,《文艺争鸣》2019年第5期。关涉的不仅仅是文章风格或文化气质,它不只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尽管厘清一些历史叙事也是必要的工作),也在更深的意义上关涉着语言观——这不在于文言到白话的翻转,或“意译”与“直译”在概念上的区分,而在于有没有这样一种自觉和勇气:从词汇这个最小的翻译单位开始,胼手胝足地进行重建。相对于“松柏鸣禽”这种向中国文化附会的译法,《小约翰》的动植物翻译这项语言工程,势必会在汉语的名物系统中造成一种“陌生化”效果,而在另一个意义上,正是这种陌生化,才能真正克服不同生活世界之间的“不可译性”,即以活的语言把握那些尚未进入本土生活经验的意象和其背后的知识系统(同时通过名物再造而赋予并确认语言的活力),而不是削足适履地让后者在译入语既有的命名系统里强行落座。
在“松柏鸣禽”的林纾-周作人译法之外,鲁迅早年的老师章太炎也是一个可以参照的对象。关于后者的词源学思想及实践,学界已有相当的讨论。1参见孟琢、陈子昊《论章太炎的正名思想——从语文规范到语言哲学》,《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孟琢《论正名思想与中国训诂学的历史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如何处理名物系统,在章太炎的语言文字体系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实际上,鲁迅对《小约翰》动植物译名的计较,正是章太炎所关切的文字如何“孳乳”2参见王风《章太炎语言文字论说体系中的语言民族》,《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的问题,二者对语言文字的执念究其根本,不无相合之处。但在技术性的层面,鲁迅给出的答案并非章太炎思路的延续,二者间的对话以一种象征和隐喻的方式寄居在《小记》与《小约翰》本文的互文关系中。这里我们不妨对后者做一简短重访。《小约翰》这个“童话”故事正开始于主人公的一串“命名”行为:约翰在原生环境中的“花园”里“作长远的散步,凡他所发见的,他就给与一个名字。……为了房间,他所发明的名字是出于动物界的:……为了园,他从植物界里选出名字来,……”3F.望·蔼覃:《小约翰》,鲁迅译,《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108页。命名,特别是给物象命名,在这部“成长小说”之初成为主人公认识和把握生活世界的主要办法,也是故事本身象征的“求知欲”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在《小记》中所展示的对多种名物译法的探索,本身也与这个故事构成一种隐喻关系:约翰在漫游中不断遭遇这个世界,由认识各种“他者”而终于认识自己,正是翻译工作中译者主体的一种存在方式。而在这个“成长小说”中,随着约翰生命旅程的展开,各个表征着他“智识欲”与世界观的进化节点的标志性形象也逐一登场,这条“成长”线索在“号码博士”(Doctor Cijfer)这里达到一个极值。1鲁迅在《〈小约翰〉引言》中对这个“成长小说”的情节结构及其象征意旨做了如下概述:“人在稚齿,追随‘旋儿’,与造化为友。福乎祸乎,稍长而竟求知:怎么样,是什么,为什么?于是招来了智识欲之具象化:小鬼头‘将知’;逐渐还遇到科学研究的冷酷的精灵:‘穿凿’。童年的梦幻撕成粉碎了;科学的研究呢,‘所学的一切的开端,是很好的,——只是他钻研得越深,那一切也就越凄凉,越黯淡。’惟有‘号码博士’是幸福者,只要一切的结果,在纸张上变成数目字,他便满足,算是见了光明了。谁想更进,便得苦痛。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他知道若干,却未曾知道一切,遂终于是‘人类’之一,不能和自然合体,以天地之心为心。约翰正是寻求着这样一本一看便知一切的书,然而因此反得‘将知’,反遇‘穿凿’,终不过以‘号码博士’为师,增加更多的苦痛。直到他在自身中看见神,将径向‘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时,才明白这书不在人间,惟从两处可以觅得:一是‘旋儿’,已失的原与自然合体的混沌;一是‘永终’——死,未到的复与自然合体的混沌。而且分明看见,他们俩本是同舟……”见《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224页。据鲁迅的译笔,“号码博士”的特性在约翰与其初遇时被这样提示出来:
于是他们到了沉静的都市的一部分,那地方站着一所大房屋,有着大而素朴的窗门。这显得无情而且严厉。里面是静静的,约翰还觉到一种不熟悉的刺鼻的气味夹着钝浊的地窖气作为底子的混合。一间小屋,里面是奇异的家具,还坐着一个孤寂的人。他被许多书籍,玻璃杯和铜的器具围绕着,那些也都是约翰所不熟悉的。一道寂寞的日光从他头上照入屋中,并且在盛着美色液体的玻璃杯间闪烁。那人努力地在一个黄铜管里注视,也并不抬头。2F.望·蔼覃:《小约翰》,鲁迅译,《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179~180、194、198页。
号码博士认知并把握世界的办法是“用动物和植物,以及周围的一切来开手,如果观察得一长久,那便成为号码了。一切分散为号码,纸张充满着号码”(Everything resolved itself into figures - pages full of them),对号码博士来说,“号码”隔绝了象征世界与现实世界,在获取号码之后,现实世界就不再重要了:“号码一到,于他是光明。”而号码“在约翰却是昏暗”3F.望·蔼覃:《小约翰》,鲁迅译,《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179~180、194、198页。——作者借另外一个人物“穿凿”的声音指出,号码博士“看见一切,而仍然一无所见”4F.望·蔼覃:《小约翰》,鲁迅译,《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179~180、194、198页。。
《小约翰》本文中的“号码”,作为象征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中介,在鲁迅的《小记》末尾,被杂文式地召唤出来,而成为“语言文字”的类比物。1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在事物的代数化和自动化过程中感受力量得到最大的节约”,而艺术的存在正是为了从这种状况中拯救和恢复“对生活的体验”。形式主义者这个关于艺术本质的判断,或可用以理解《小约翰》中“号码博士”与约翰的不同的世界观。参见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在交代“蠼螋”(一种虫类,德文为Ohrwurm,英文译作Earwig)的译法时,鲁迅表示若“放出‘学者’的本领”,则这个名目在“古书”上的确有案可稽:“《玉篇》云:‘蛷螋,虫名;亦明蠼螋。’还有《博雅》云:‘蛷螋,蛷也。’”2鲁迅:《〈小约翰〉动植物译名小记》,《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250、250、247页。这里“学者”等语自然是杂文基因的显影,关联着1927年前后鲁迅的现实处境;另一方面,《玉篇》《博雅》的出现,也不难令人联想到章太炎的语言文字执念。鲁迅对“蠼螋”这种译法并不满意,自云“虽然明明译成了方块字,而且确是中国名,其实还是和Ohrwurm一样地不能懂,因为我终于不知道这究竟是怎样的东西”,而姑且采纳这个“不得要领”的译法,是“私淑号码博士”的结果:“看见中国式的号码便算满足了。”3鲁迅:《〈小约翰〉动植物译名小记》,《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250、250、247页。
在“蠼螋”这个译名上,“号码博士”(《小约翰》的本文)与《小记》中鲁迅本人的翻译工作,作为两条互相隐喻的线索,而忽然会合。鲁迅将“蠼螋”指认为“中国式的号码”,尽管携着杂文式的调侃,但仍然是强调在命名活动中,在将概念凝结为符号、为符号赋予意义的过程中,主体经验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整篇《小记》里,鲁迅不时要为所译对象附加一串性状、功能描述的原因。方块字形式的符号并非没有,它们可以被从日本语重新挪用回来,或通过求问“古书”而获得,如果只是在结构上拈来一个译入语内的名词,那么动植物的翻译不会如此棘手,译法也会相对统一。鲁迅拒绝这种简单翻译模式的原因在于,这些能指的意义已经丧失殆尽,因为它们无法落座于实在界。他不无讽刺地指出,对于典籍中的草木虫鱼,“学者”们“一向就终于注释不明白”4鲁迅:《〈小约翰〉动植物译名小记》,《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250、250、247页。,这种批评并不指向作为知识系统的文字与训诂,而是指向汉语相对于其所附着的生活世界的表意能力。一切语言的活性和有效性,都需要经受表意主体自身经验的检验,在此之外,各种各样的知识权威(古书典籍或域外资源)都无法让语言变得更加可信,而将翻译实践中的命名托付给古书与古字,满足于“中国式的号码”,显然是回避了这种主体经验的重要性,也就是“号码博士”的“看见一切,而仍然一无所见”。这同时也就意味着,“益以新制”对于维持语言活力而言是一项必要的(而非补充性的、退而求其次的)工作,因为主体的经验势必会随着生活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尤其是在中国新文学这个历史阶段。1鲁迅在《小记》开篇提出了整顿生物名目体系的办法:“采取可用的旧名”、选择“较通行而合用”的“俗名”,以及“益以新制”。尽管这也是章太炎语言文字方案的三种办法,但二者的主次序列有本质的不同,尤其是对待“废弃语”的态度。这背后的关切不仅在于对“普及”的要求,而且是一种更深刻的、基于自我与他者关系之上的对语言的思考:名物系统是否需要随着新的生活世界的展开而进行更新和再造?一种语言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开放的、不断接受异质元素带来的拓展和变革,还是应该封闭起来、努力维系某种“民族性”的纯粹?鲁迅给出的答案,显然不同于章太炎那种近乎悲剧的坚持;事实上,这种经由“他者”而再造自身的态度已经使鲁迅汇入了一个更有启发性的“世界文学”的传统。2参见安托瓦纳·贝尔曼《异域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章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
对于名词系统的翻译难题,鲁迅在《小约翰》这次实践中,并未给出一劳永逸的、方法论式的解决;相反,他在《小记》里对诸种译法的不厌其详的罗列,反倒暗示了(至少在1927年的汉语文化中、在以汉语确立关于动植物知识的现代科学系统之前)为名词翻译这项工作建立单一方法论的不可能。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件案头工作虽然繁难,但本身也具有实验性和游戏性,相对于经由《小约翰》的动植物世界为汉语的表意系统建立新辞典,毋宁说,《小记》经由对翻译过程的还原、通过铺排种种译法的勉为其难或差强人意,其意图更加在于展演翻译本身的困境,以及突破这种困境的不懈努力。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鲁迅拒绝将译名工作完全托付给现成的各类“辞典”,而不惜工本地另起炉灶,在名词这个语言单位内部进行几乎是造词式的努力,将外文对象一一亲手译出,但他自己最终择定的译法,也并非一经使用便可确立下来的权威典范,这不仅是后见立场上汉语词汇系统中的客观现实,也是鲁迅其时自己的译者意识——他没有在《小约翰》的译本里寄托这种将自身树立为权威的期待;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与章太炎在语言文字工作上的不同的抱负。这或许才是所谓“中间物”这一众所周知的“鲁迅思想形象”的具体表征:“中间物”的意义在于提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在于其指向自身的革命性意志而非一种客观的历史性,它“仅仅是作为自我否定、自我消解的形式和构造才获得其存在的理由”1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第662页。。而值得注意的是,“中间物”这个说法出现的原始语境,正是鲁迅围绕语言问题所展开的自叙。2参见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
考据解构考据
《朝花夕拾·后记》写毕于1927年7月11日,对于这篇文章,鲁迅自云“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两个月”3鲁迅:《朝花夕拾·后记》,《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页。。其过程所以断续拖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要多方搜集有关《二十四孝图》与“无常”的旧画像,与所托友人的信件往来耗费了时间。这一篇《后记》整体上并未延续《朝花夕拾》本文的笔法,而是专注于对两批图像的“考证”;“考证”之外,鲁迅特在《后记》的行文中插入四幅组图,呈现“曹娥投江”、“老莱娱亲”以及“无常”的诸种视觉形象,前两种对应《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的主题,后一种对应《朝花夕拾·无常》的主题。
作为《朝花夕拾》本文的一种视觉性补充,这篇《后记》乍看仿佛是对“自叙”文类的实证式的注脚:《二十四孝图》与“无常”形象的物质性存在,似乎是作者在有意加强回忆的“真实性”;而这种实证的姿态体现为细密的考据,从形式上结构了整篇《后记》,则更仿佛是在召唤着“过去”与“历史”。但在鲁迅对图像的兴趣以及在考据方面的功力背后,这篇《后记》在行文方式与所表述的主旨内容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反讽的张力,其中隐现的杂文风格,是这篇《后记》与《朝花夕拾》本文分享的共同的基因。排比图像,是将载诸文字的内容引入另一种媒介符号的领域,在这个“转码”与“翻译”的过程中,以文字为重要依凭的对于图像的考据,则导向一种检验。所检验的对象,是文字内容与图像内容共同指向和共同分享的整体意图,或曰“纯粹语言”(本雅明),体现在这篇《后记》里,这种整体意图便是作为文化产品的《二十四孝图》与“无常”本身的题旨。在下面的细读与阐释中,我们会看到,鲁迅表面上不厌其详的考据动作,在图像-文字的跨域实践中,如何解构了考据本身的意义。
先来看鲁迅对《二十四孝图》主题图像的处理。在《朝花夕拾》本文的语境中,《二十四孝图》是作者幼年并不愉快的阅览经历,它使嗜图爱画的作者在了解其本事之后,“接着就是扫兴”1鲁迅:《〈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2卷,第261、258页。,原因在于《二十四孝图》所主张的教化,以其伪诈的价值系统妨害了人的自然生命,也妨害了白话文的内在逻辑。这批文化产品作为白话(以白话为语言媒介和思维机制的真正的“新文化”)对立面的一个表征,使鲁迅在《朝花夕拾》的《〈二十四孝图〉》这篇文章里做出相当激烈的表态,“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2鲁迅:《〈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2卷,第261、258页。,以“诅咒”之。但是在《后记》中,鲁迅偏偏不吝工夫和篇幅地,对这个本应被诅咒的对象进行细致的罗列和查考:我们不难辨识出他在这里所调用的版本学的方法(排比“曹娥投江”“老莱娱亲”在不同年代不同作者笔下的图像中的分别)与训诂学的方法(考辨某一版本中“老莱娱亲”的“弄雏”之“雏”的具体意义),更无法否认,从文献学的立场看,鲁迅的这番考据是完全符合学理规范的操作。
考据的认真,与对所考据对象的憎恶,于是构成一种反讽。更重要的是,鲁迅对“曹娥投江”与“老莱娱亲”的图像分析,事实上提示了以图像形式存在的《二十四孝图》之败坏不堪的另一重原因,即当画者将叙事文本“译”为图像时,符号系统的转码会凸显或暴露所译对象在风格或逻辑上存在的问题。老莱子的作态,表述为文字时仿佛还可以成立,而一旦呈现为图像,某些在文字表述中可以回避的叙事性或描述性要素就不得不被处理。这种情况是各个符号系统内部的法则决定的,是“跨”界实践中最麻烦但也最有趣的问题。类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提到的,“I hired a worker”(我雇用了一名工人)这样一个英文句子被翻译到俄语中时,译者必须处理(选择)“worker”(工人)的性别属性,否则无法令其成句,这是俄语的语法系统要求的“补充性信息”(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3Roman Jakobso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New York:Routledge, 2000, p.116.回到鲁迅的《后记》对《二十四孝图》的查考,在“老莱娱亲”由文字系统转码到图像系统的过程中,后者也在“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这个文字表述之外,按照图像系统自身的规律要求着“补充性信息”。于是,图典中的呈现,或者是“一个高大的老头子”玩“摇咕咚”,或者是画师将老莱子的“身子竭力收缩,画成一个有胡子的小孩子了”1鲁迅:《朝花夕拾·后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338、338、340、341页。,其“不像样”之程度皆令人无法容忍。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考据”动作,实则指向图与文之间的翻译和转码,是一个通过对图像系统“补充性信息”的考察而检验《二十四孝图》这个“纯粹语言”的逻辑真实和情感真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考据本身携带的历史性价值,被鲁迅消解在了“不像样”2鲁迅:《朝花夕拾·后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338、338、340、341页。这个审美判断中。
本雅明认为对于重要的作品而言,译作是原作生命的延续,其背后的逻辑在于,译作与原作都是“一个更伟大的语言的可以辨认的碎片”3瓦尔特·本雅明:《译作者的任务》,参见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0页。,因此译作凭借另一种语言系统,与原作的语言一起,合力使作品本身更趋近于对“纯粹语言”的揭示。本雅明这里讨论的翻译问题被限定为跨语际翻译。在鲁迅对《二十四孝图》的考据中,我们不妨借用这个模型,将图和文视作同一个整体意图之下的两种符号系统,正如波德莱尔作品的法文形式与德文形式。在本雅明那里,原作与译作两种语言的互补关系,在《二十四孝图》的图文转译中,表现为一种不和谐:图像这个符号系统仿佛在有意揭露文字这个符号系统的隐疾。本雅明对译作的称许,前提是其所译的原作乃伟大作品;在相反的意义上,鲁迅在《后记》中有意展示的《二十四孝图》的转译的失败(“无怪谁也画不好”4鲁迅:《朝花夕拾·后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338、338、340、341页。),正合于《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本文的题旨,即《二十四孝图》作为一种“意义”是荒诞不经的。在这个意义上,《后记》实际上汇入并加强了《朝花夕拾》本文的题旨和主张。
鲁迅处理的另一批对象是“内有‘无常’的画像的书籍”。这里他同样在版本问题上做足功夫,不厌其详地陈列“北京龙光斋本,又鉴光斋本;天津思过斋本,又石印局本;南京李光明庄本。……杭州玛瑙经房本,绍兴许广记本,最近石印本;……广州宝经阁本,又翰元楼本”5鲁迅:《朝花夕拾·后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338、338、340、341页。等诸种《玉历》中无常的形象,并相互比对校勘。在《朝花夕拾》本文的语境中,无常这个意象寄托了鲁迅1920年代中期为自己确立的新的价值体系,它的意义并不在于“民间”或“过去”,而是在于鲁迅在“追忆”这个动作发生的微观现实语境里,如何将无常收编并转化为“当下”表意系统的象征性符号。1参见邢程《现实照进旧事:〈朝花夕拾〉中的“流言”与“自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期。这种意味,在《后记》的图-文转译实践中被再次强调,即鲁迅在考据了诸种典籍里的无常形象后,“还不能心服”,因此“自己动手,添画一个我所记得的目连戏或迎神赛会中的‘活无常’”。2鲁迅:《朝花夕拾·后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342、347、236页。
这个“添画”的动作颇值得注意。考据所得,尽管扎实,但在实证之外,并不能提供更多价值,因此实证本身也就丧失了价值。鲁迅于是亲自临摹无常的图像,但临摹所参照的对象,不是典籍中的文字性描述,亦非某个实存的物象,而是自己的“记忆”——“添画一个我所记得的……‘活无常’”,尽管其结果可能“大背经典,荒谬得很”。3鲁迅:《朝花夕拾·后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342、347、236页。以记忆为底本的无常与典籍中的无常被鲁迅拼贴在一起,并置于行文中,加以手写体的题名与落款,与典籍图像的铅印字体形成对照,由此,民间的、过去的、典籍材料中的无常被当下这一刻的鲁迅收为己有,考据被记忆消解,历史成为文学的对象。另外,在一个象征的意义上,将自己绘制的无常与典籍中的无常并置,也就是让自身进入到典籍式的知识谱系里,这并不是要将自身历史化、凝固为历史序列中的一环,如“学者”之流的追求不朽,而是以一种戏仿的方式,打破知识谱系的连续性和权威性:那一套看起来正襟危坐的、牢不可破的考据,随时可被文艺家凭借“记忆”而“添画”的东西所打断,正如阿Q也可以被作传一样。
与《二十四孝图》的“谁也画不好”相比,鲁迅自己绘制的无常显然是一次成功的转译,也是鲁迅为《朝花夕拾》本文提供的最有分量的图像形态。这一方面暗合了《朝花夕拾·小引》(1927年5月1日写毕)所谓“从记忆中抄出来”4鲁迅:《朝花夕拾·后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342、347、236页。的创作姿态,加强了追忆与自叙的文学立场;另一方面在《后记》本身的语境里,也是对考据的再次解构——在《二十四孝图》的问题上,考据被审美解构,在无常的问题上,考据则被作者的私人记忆解构;而后者更令作者顺势将《朝花夕拾》收束在一副杂文笔法中——在《后记》进入尾声的时候,鲁迅提出他对考据的态度:
研究这类三魂渺渺,七魄茫茫,“死无对证”的学问,是很新颖,也极占便宜的。假使征集材料,开始讨论,将各种往来的信件都编印起来,恐怕也可以出三四本颇厚的书,并且因此升为“学者”。……1鲁迅:《朝花夕拾·后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346页。
考据图像,“新颖”且可“升为‘学者’”,但这种指向实证的“趣味”,使鲁迅“不想干下去了”。多方搜集“书籍”与“经典”的结果,是鲁迅对它们更加不能信服,而尤其令他感到厌恶的是,这些东西很容易被转化为象征资本,以“三四本颇厚的书”的形态,成为“学者”们博识而有趣的凭据。但实际上,这种博识而有趣,是对“过去”的依附和对“历史”的服从,其代价是将自身沉没于对典籍的考据中,结果是主体被“知识”与“趣味”所占有。
从“公理”到“礼教”:语言的可信性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据鲁迅离开广州前的一次演讲整理而成的文本。在1927年夏天广州“只有‘而已’而已”2鲁迅1926年10月校讫《华盖集续编》时所作,见于《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页。此语后在鲁迅1928年10月校讫《而已集》时,被转用为《而已集》的题辞,《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被收于《而已集》。的语境里,这样的选题自然包含了历史讽喻的意味,曹操、司马懿的杀人与孔融、嵇康的被杀,很容易令人将之类比于“清党”的严酷政治;另一方面,坐而论古本身也是一次“文学史”叙事的演练,经后世学者的阐发,被表彰为一种合法的研究范式。
但鲁迅对魏晋美学的创造性解读,即将古事转译到当下,在上述两种倾向之外仍存阐释的余地。这里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鲁迅对时势的隐微表达,或鲁迅的治学方法论,即如何以“文学的外部要素”激活对文学内部问题的理解;而在于鲁迅借重述魏晋的机会,以“办事人”的“权力”区别并标记出了“老实人”的逻辑,后者关涉的并非现实世界里具体的政治立场,而是象征世界中名实关系的真实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的可信性问题。
鲁迅是以对嵇康和阮籍的推心置腹构建出“老实人”逻辑的。谈及他们对礼教的态度,鲁迅将“师心”“使气”的个性与“恣意妄为”的举止,在字面上化解为一种更为平常的表述:“老实人”的“迂执”。魏晋文士的特立独行,由此被“颠倒”为一种基本而普遍的价值和道德。文学史叙事往往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而鲁迅对嵇康与阮籍的重释,反倒是在一个去神圣化、去神秘化的层面展开,在鲁迅的转译里,嵇康、阮籍的另类和不俗,其表象上的“异”,本质是一种“常”: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第535页。
这里反复出现的“礼教”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符合特定社会语境中礼仪规范的具体行止;二是象征世界中的基本秩序,即名实关系的真实性。后者相对于前者,更能超越一时一地的规约,而具有某种普遍价值。鲁迅对嵇康、阮籍的重释,实则是对“礼教”这一字眼进行了上述两层意义的隐微置换。嵇康、阮籍的“毁坏礼教”,所违背的乃是前一种,而其“崇奉礼教”的“本心”,则在于对后一种礼教的维护。在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礼教中,语言的可信性是最重要的核心,礼教之名必须严格对应于礼教的实在,当这种对应关系被损毁时——在魏晋这里表现为权力以礼教之名行统治之实——“老实人”便选择连名带实一并放弃的姿态,即“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而这种激进姿态正是崇奉普遍价值即另一种礼教的表现。
所谓语言的可信性,是指语言的表意价值,即语言在流通过程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并不因为强制性的外在力量而遭到磨损。与之相对的情况是,“当相反的含义被加诸一个词上(奥威尔称之为‘新话’Newspeak),当词语概念的界限和估值被政令所改变时,语言就失去了可信性(credibility)”1乔治·斯坦纳:《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孟醒译,第38页。。权力对礼教的“偶然崇奉”,其败坏之处并不在权力自身,而在于这种“偶然崇奉”使语言的被使用变成了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当能指的出现每一次都无法有效抵达它本来的所指时,语言的可信性就丧失了,结果并不是仅仅淆乱了某几个概念或某几种表述,而是彻底取消了意指关系,使语言沦为空洞虚浮的能指符号。
因此在对魏晋风度的转译(雅克布森所谓“一种语言内部的翻译”)中,问题不在于鲁迅对权力的立场和态度,而在于“老实人”逻辑与“办事人”逻辑的相互区别,以及前者在这种区别中完成的主体确认。“文与武、笔与剑等等的对比,本身并没有什么新鲜的”,要讨论“实力与文章乃至语言的关系”,2木山英雄:《实力与文章的关系》,《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首先要离析出“实力”与“文章”两方面各自独立运行的机制。在1927年关于魏晋的历史讽喻里,实力与文章的二元关系假托“办事人”与“老实人”这两种人物谱系出现。“办事人”的言动,其目的在于现实政治的实现;而“老实人”的“迂执”则是指向象征世界的,关切的是语言的可信性,而非现实世界中的具体政治。在鲁迅对魏晋的重述里,对于“老实人”而言,礼教的名实不符在根本意义上带来的是语言的危机,而非生存危机,而当鲁迅将嵇康和阮籍指认为“老实人”、将特立独行解释为一种普遍价值时,他正是通过对“常”与“异”的颠倒揭示了那个独立于现实政治的语言象征世界的存在,以及维护语言可信性的必要。即使现实的权力或暴力会对历史的个人进行肉体消灭,这个象征世界仍然会在其内部保持着语言的主权,而语言本身也需要不断地建设表征自我的能力,以有效地把握能指通向所指的意指关系,进而维护象征世界的“可信性”。实际上这正是鲁迅在同年一系列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演讲中反复表达的看法,他并不是以否定权力和暴力的方式回护文学,或在权力与文学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决断与价值判定,而是在二者的张力关系中为双方的存在同时确立了各自的合理性;或者说,只有在二者同时获得各自合理性的前提之下,文学才能确立自身。竹内好所谓“把文学看作对政治是无力的”的“自觉态度”,1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35页。正是对这一点的深刻洞察。在这个意义上,进而言之,“老实人”逻辑就是“文学”逻辑在鲁迅的历史讽喻中的具体化与肉身化。
在另一个文本群里,魏晋“老实人”的礼教可以找到自己的同位语,即鲁迅前一年(1926)在《朝花夕拾》中以追忆往事的形式建构起的“下等人”的“公理”。在“旧事重提”的语境中,“下等人”对“无常”所代表的鬼世界的喜爱,并不是出于迷狂或对无序的向往,而恰恰是源于对现实生活世界中真正的“公理”的执恋,只是“公理”之名被“正人君子”之流把持,如同礼教成为“办事人”实施权力时的工具,“下等人”方才转向阴间,在象征世界里寄托真正的“公正的裁判”。在这个意义上,与“在广州之谈魏晋事”2鲁迅1928年12月30日致陈濬信中言:“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相同,鲁迅的追述无常,其意也并非指向纯粹的“过去”或被对象化的“民间”——实际上这也正是鲁迅的杂文特质,即不会正襟危坐地以客观的研究姿态处理一个被彻底对象化的“他者”。正如嵇康、阮籍及其所代表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不仅仅是(甚至根本不是)坐而论古的对象,“下等人”在《朝花夕拾》中也并非一个本质化的、包含阶级意味的指称,而是象征着一种价值取向,其实质与“魏晋风度”中“老实人”的“迂执”并无不同,背后的逻辑都在于维护语言本身的可信性。在“旧事重提”的语境里,阴间与阳间的互为镜像,正同构于魏晋风度中“常”与“异”的颠倒,“下等人”与嵇康、阮籍这类“名士”经鲁迅的演绎而站在了价值判断的同一边。私人回忆与古代经典,在这个文本群里成为彼此的注释与变体,一道揭示了鲁迅的主体位置和文学位置。
结 语
1927年对于现代文学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但本文无意引入社会历史与现实政治的材料,对鲁迅上述三种文本实践进行“语境化”的处理。我们当然可以在紧迫的现实环境与鲁迅的文本实践之间建立反映式的或解释性的关联,但本文的意图是在实证性的研究基础之外,在探问鲁迅的政治立场之外,补充这样一个视角,即在当时那样一个晦暗而复杂的环境中,鲁迅如何把握住了一个现代文学主体的时刻,这个时刻是通过在自我内部安置诸种“他者”而显明自身的。
现代文学所要面对的“他者”,除了忽然涌来的域外语言文化,也包括汉语自身漫长的文学传统,以及其他符号媒介的内容,这是“现代性”本身的全球化特质、时间观以及技术发展决定的。而当我们考察现代文学对自我-他者之关系的处理时,在追摹和抵抗之外,广义的“翻译”或许也不失为一种观照的思路。“翻译”提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主体姿态,一种在被动遭遇与主动触碰之间的调整和移动。本文所分析的三个个案,从语言内部的重建,到以审美消解实证,再到对历史经典的当下性征用,正是三个不同维度上的跨界转译;鲁迅在其中的实践,呈现了现代文学主体将诸种“他者”内化为自我重建与自我确认的可能性方案。在一个象征的意义上,也正是作为“他者”的现实环境的极端严酷,才使得文学主体能够在一种“例外状态”中确认自己的存在并显示自己的本质;而作为个案的文学实践,都在召唤具体的文本内部分析。将这个思路延伸下去,或许可以重新质询现代文学的本体性意义,从而为我们聚焦1927年搭建另一个具有生产性的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