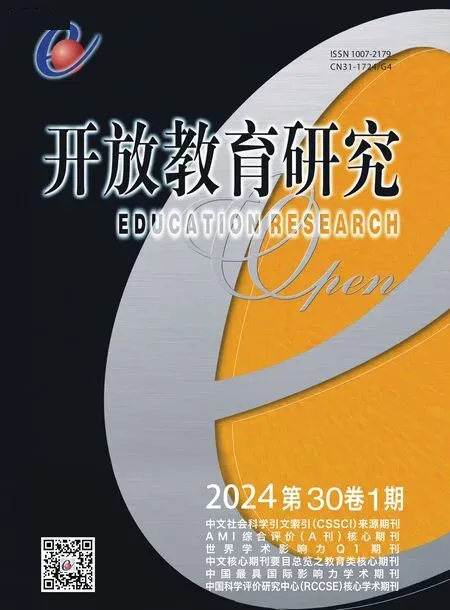技术与人类
2024-05-10米川
米 川
技术社会视角的现代性批判是今日理解“技术与人”关系的重要论域。有一天当我逡巡旧书架的时候,两卷本的《过时的人》抢入我眼前,这书德国哲学家京特·安德斯的大作,是批判技术哲学的经典著作。
“普罗米修斯的羞愧”是安德斯提出的一个划时代的科技哲学隐喻。其含义虽不至是“解码性加密”,却有其时代语境的“意义”:一是人不如自己创造的机器(指具有高度自主性进化能力的现代机器体系);二是“普罗米修斯的差异”(指自然人的演化不如机器的演进);三是现代机器体系的“自主性”日益强大,成为“类主体”,人很可能成为机器人的候选人或新的机器型号。简言之,“普罗米修斯的羞愧”在于人类的“过时性”。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有此等认识,安德斯果然有两把刷子,不愧为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弟子。说到安德斯所处的机械化社会,不由得想起我国上世纪七十年代一部驱迫性的流行京剧《海港》中一位老工人的唱段:“看码头,好气派,机械列队江边排。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
然而,从VUCA 到BANI,安德斯还是“过时了”。他如果看到今天OpenAI 的迭代和人形机器人所带来的“恐怖谷理论”和新卢德主义幽灵,他的“羞愧”度不仅会成指数级增加,更可能要变为“普罗米修斯的恐惧”或“技术的异化”:技术日益呈现为一种失控的独立力量,人类把创造历史的自主性托付给了技术,但是当技术成为社会的首要组织原则时,社会本身就会陷入技术逻辑的宰制。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已不可逆转地作用于人类,造成了人的异化。罗萨更是指出了现代技术社会人与“空间、物、行动、时间和自我”五种新的异化形式。无处不被量化分析的“数字人”的趋势,也使得教育的“数字异化”成为时代的宿命。
“羞愧”势必产生自卑,而自卑是要超越的。历史上技术哲学家提出了“技术的人文重构”之道。从芒福德的“自我反省”、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到哈贝马斯的让技术回归生活世界、伊德的在具体的生活世界中反思技术的意义,以及拉普、芬伯格等等,都从“人文”的角度寻求进路或方案,都包含了价值矫正、伦理制约、风险控制等内容。人是技术化了的人,技术是人化了的技术。
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人与技术镜像相生。人类不再是唯一的主体或智能体。今天,技术已成为当代最深刻的政治,技术与人的问题是当下最根本的问题,技术哲学应当是当代“第一哲学”。超越“普罗米修斯的羞愧”需要我们重新回到技术本体论,回到技术哲学的“人类对自然改造”的逻辑起点,遵循人与技术的内在关系,在实践活动中实现“人与技术的互构”。
身处时空折叠的场景,最尴尬的莫过于身体进入新时代,心理还在过去时。马斯克说,硅基数字人作为一种“后人类”进入人类社会势必带来系列社会问题,但马斯克还是肤浅了,殊不知,在技术社会的巨大“座架”下形塑出来的“碳基机器人(数字人)”才是人类最大的危险和悲哀。
斯蒂格勒说,技术既是解药,也是毒药。海德格尔指出“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马克思说“人的类特性恰恰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自由是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而实现的自我超越和自我进化。也唯如此,我们才可以避免经验的自恋、涂层的自负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也唯如此,我们才敢“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蔚蓝”,更深的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