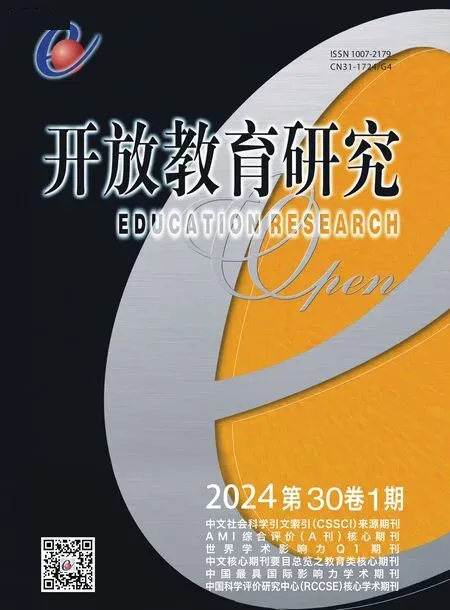人工智能时代的对话式教育技术理论
2024-05-10史圣朋鲁珀特韦格里夫
史圣朋 鲁珀特·韦格里夫 袁 莉
(1. 剑桥大学 教育学院,英国剑桥 CB12EW1;2. 北京师范大学 未来教育学院,广东珠海 519087)
一、引言
科学的理论应具有高度的实践应用价值(Greenwood & Levin, 1998)。本文根据劳里拉德(Laurillard, 2013)的观点,将教育定义为一门设计科学,其本质与工程学或建筑学相似,重在通过以设计为基础的研究方法(design-based research)进行实证数据的搜集与分析,探究和验证教育设计的原则,建立对话式教育技术的理论框架,推动教育技术设计原则的深入研究。
当前,教育技术设计领域的大多数研究着重于探讨教育理论本身,如应用行为主义指导设计,或在设计多元化学习环境时采用社会构建主义理论(Winograd et al., 1986)。然而,这些理论往往未能充分考虑技术在教育实践中的独特作用。笔者认为,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密不可分。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的认知结构和社会实践正处于转型之中,为教育研究带来新的课题。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给人类史和地质史的发展进程带来了空前挑战(Abdu et al.,2021)。互联网作为新兴的通信方式,不仅提供了实时双向对话交互机制,也对教育价值观、认知发展和社会化过程带来冲击和潜在的负面影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球文化开始从多元的印刷媒介向单一的网络文化转变,这不仅是一场文化的转型,也标志着人类活动已转变成影响地球环境变化的决定性力量(Wegerif & Major, 2024)。为了应对数字时代及人类活动给环境带来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创新教育技术理论,促进形成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为全球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二、教育技术理论
(一)对话理论视角下的教育内涵
“教育”这一概念具有多维性和复杂性,被广泛定义为通过教学、训练、探究等多元化方式传递知识、技能和价值观的综合过程。其核心目标在于全面发展个体认知能力、思维技巧和身份认同等。教育强调学习的全面性,不仅仅指知识和技能的简单传递,还指个体综合素质培养的关键路径,包括但不限于培养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以及形成社会和文化认同感。
从更广阔的时间维度审视教育可以发现,教育形态在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展现出显著的多样性。例如,依靠口头传输的文化对教育的理解与现代概念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原始社会,教育并不依赖于学校体系,也不单纯局限于知识传递、思维训练。原始社会通过师徒制度,即与“长者”建立对话关系,来对年轻一代进行文化熏陶。这种教育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生产技能的培养和文化身份的认同。人类学研究成果表明,在大多数真正的口头传输文化中,学习活动是通过与“长者”的对话展开的。这种教育模式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掌握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聆听和理解“长者”的话语,以及如何通过语言表达自身观点——与“长者”对话。
因此,教育可以被定义为引导个体接受文化熏陶的长期对话过程,而知识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知识不可能孤立于对话而存在,它是对话所提出问题的答案,并随着对话的发展而更新。教育具有两个主要且互相关联的功能:身份构建和文化实践的传承。引导性的文化对话使个体学会如何在文化和生物学上成为“完整”的人——这通常意味着学习如何与“长者”对话,并在社会体系中构建个体身份,即学习如何使用“长者”遗留的工具和技艺,并在文化熏陶中寻找自身的定位。因此,每代人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探索和学习,为文化传承和技术发展作出贡献,并把这些新的知识和理解传递给下一代。
这种对话视角强调知识的构建不仅发生在个体层面,而且在社会互动和沟通中形成,对话被视为促进学习和理解的关键机制。在这种框架下,教育被理解为一个动态的、互动的过程,知识不是被简单地传递,而是通过参与者之间的意义协商和批判性思考共同构建的。对话理论关注如何通过言语和非言语沟通拓展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如何通过对话实践支持个体的认知发展、思维进阶、文化熏陶与传承。
(二)何为“技术”?
对话理论 (Dialogic Theory) 为“技术”这一术语提供了深刻的诠释。源自希腊语的“dia”,意味着“跨越”,它揭示了“对话理论”与“逻辑理论”之间的界限。对话理论认为,理性的构建依赖于不同声音和视角之间的交流,并在特定语境中赋予关键事物以独特的差异化意义(Linell, 2009;Rommetveit, 1992)。
在教育领域,教育技术这一术语被广泛用于指代教学辅助工具。一般而言,现代教育技术特指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设备、软件及其支持系统,与笔、纸、黑板等传统教学媒介有别。然而,“techné”作为“技术”的词根,原本指手工艺和技能,涵盖陶艺、编织、音乐创作等,这表明教学方法和课程设计本质上也是教育技术的一部分。20 世纪50—60 年代,教育技术一词的广泛使用,实际上是对其本质含义的一种回归,强调学习科学在教室中的系统应用,而不是机械化运用(Skinner, 1968)。
从理论角度审视“技术”,它不仅仅是具体物件的代名词,亦是一种改变实践的功能或设计。例如,19 世纪初期黑板的引入,在教学实践引发了一场关于教学工具功能与设计的讨论。此项“技术”促成了教具使用方式的根本转变,即从专注于个体学习的工具向促进集体学习的工具转化(Russell,2006)。这一历史性变革不仅展现了教育技术的发展路径,而且强调教育工具设计的哲学和实践意义。在此背景下,新工具(如生成性人工智能)之所以是教育技术,不仅仅是因为其数字化、智能化特征,更因为它们能够实现教学目标。这反映了教育技术的本质不在于工具本身的先进性,而在于其如何被整合和应用于教育实践,以及如何促进教育目标的实现。这种观点强调教育技术的设计与应用中教育理论和教学目标的重要性,展现了理论、技术与实践之间的紧密联系。
(三)理论与技术的共生关系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将理论定义为对永恒真理的思考,这与技术(techné)的实践内涵相悖。技术关注一定时间内的创造过程(或创新性),而非不变的真理。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科学(Epistemé)界定为对恒定知识的探求,技术则被看作是随时间演变的事物(Aristotle, 公元前350/1925)。这种区分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持续演化,并对当代仍有影响——基础科学经常被认为是对自然界不变法则的探索,相对而言,工程与技术专注于这些法则的实践应用,通过时间的推移实现物质世界的演变。
笔者认同理论与技术之间存在区别。但这种区别在于技术专注于特定时间范围内的创造和创新过程,理论则是以更宏观的时间维度和全球性视角为参考点指导实践。二者本质上并非割裂关系。换言之,理论与技术的关系是互补且互融,特定时间范围内的技术创新不仅服务于即时的实践需求,同时也为更广泛、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发展奠定基石。这种相互作用表明,技术的发展能够为理论提供实证基础,而理论的深化又能指导和激发技术的创新,两者在时间体系的演进中相得益彰。
因此,理论与技术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对立或分离的两极,而应被视为在知识探索和实践创新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动态互动。以“笔记本电脑”为例,它在技术层面的含义体现在该设备的某种功能或特性(如便携性)对教育实践的有效促进。然而,教育技术理论的关注点在于如何精心设计和高效利用这些功能和特性,以及如何根据这些功能和特性设计相应的教学方法。这不仅涉及对现有教育技术的深入理解和应用,还包括对这些技术在教学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的预见和规划。由此可见,在教育领域,技术与理论构成融合的动态互动关系,共同推动教育实践的持续进步与创新。
因此,教育技术理论应当被界定为一种关注技术的设计与应用,以支持和增强学习过程的理论。教育技术理论不仅聚焦于技术工具本身,而且涉及如何将这些工具有效整合到教育环境中,以及如何理解技术对学习者、教师和教育系统的影响。简言之,教育技术理论是对“如何设计和应用技术以促进教育实践”这一核心问题的系统性回应,并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社会需求的变化不断地被重新定义、更新和发展。
三、对话的认识论与本体论内涵
对话理论强调,意义的构建并非是单一的、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互动的过程,其内涵依据词语在实际对话中发挥的功能和作用而变化。从更深层次的认识论角度看,一个词的含义不仅仅依附于说话者的主观意图,更重要的是它依赖于参与对话的其他各方的实际理解、反应和运用。在这个过程中,意义的确立成为集体协商的结果,体现了交流各方在共同语境下对话和互动的复杂性。这种观点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教学和学习的对话内涵。
(一)多元声音在对话中的根本作用
在对话过程中,意义(知识)的建构需要依靠多种声音的相互作用。只有当具备不同视角或观点的对话者互相阐释各自的理解时,真正的对话才得以实现。若这些多样化的声音趋于一致,对话便会停止,意义也会随之消失,知识亦不再发展。在对话理论中,“声音”象征着能表现世界多元视角的实体,它构成对话分析的基石。不论是个人、事物,还是抽象概念,都能在对话中“发声”,意义(知识)的构建离不开多元声音的交融。
(二)对话空间
对话空间指在富有创造性的张力氛围中,为各种不同视角提供的包容性场域。在这个空间里,“不确定性”是其核心特征,它强调对话中展现的多样视角不能被削减为单一且固定的参考框架。将其意义简化的行为,会阻止对话的多元性和流动性的发展。因此,这种充满活力的对话空间,必然超越任何单一的“客观”视角。对话的确受时空的约束,但对话的本质内核是开放的、无边界的,其蕴含的意义和价值不受物理界限的限制,能够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维度中流动和延伸。对话空间的“多元性”意味着它是一个交织着各种可能性的场域,每个参与者的声音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考量,从而在相互作用中产生新的意义(知识)。这样的空间鼓励参与者跨越传统界限,促进跨文化、跨学科甚至跨时代的知识交流与思想碰撞。
(三)对话关系的双向渗透性
对话过程呈现显著的双向渗透性,对话双方,即“受话者”与“发话者”,在言语交换的初始阶段就相互预判对方的反应(Rommetveit, 1992)。这种互渗性使我们认识到,对话中言语的发起不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递,而是一种双向的情感与知识交流。比如,回应一个玩乐高的孩子的问题,与回应上级对工作的询问,必然采用不同的语调、词汇和情感。在对话中,我们不只是与一个单纯的物理实体交流,实际是在与一个具有丰富情感和认知层面的关系网络进行互动,这其中的语言既是自我表达,也是对他者的回应。
这种对话中的双向渗透性映射了教育实践的深层可能性,它超越了简单的技能训练,就像巴赫金(Bakhtin,2010)所描述的内在说服性对话——一种发自内心的深度交流和思想碰撞。这种交流方式在教育领域尤为重要,它强调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价值观、思维模式和世界观的塑造。教育者通过对话的力量激发学习者思考,引导他们形成独立的见解和判断。在这一框架下,学习成为对话的回应,旨在深入探询知识、情感和文化价值观的内涵,教育过程因而成为一场涵盖认知、情感与社会维度的复杂对话。
(四)教育对话中个体与学科之声
在教育对话中,学习过程不仅仅是学习者通过主动探索构建对世界的理解,还涉及对外界声音的回应。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揭示,成熟的独立个体的认知是在对话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例如,婴儿的自我意识是在与母亲或其他照护者的互动中逐步建立起来的(Gallagher, 2020)。每个新的“自我定位”(Hermans, 2018)是在与他人的声音的持续互动中被引导和塑造的。
这些声音既包括个人之声,也包含文化之声。例如,数学教师不只是传递自己对数学的理解,更承载着整个数学学科丰富的历史对话和深层内涵。教师成为数学这一学科的使者,向学生发出学习和探索的邀请。当学生作出回应时,他们便成为这一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的学科对话的参与者。在教师引导下,学生不仅学习数学知识,更是被带入学科对话中,他们的理解和思考也因此扩展到数学学科。这种对话中个体与学科之声的交融体现了教育对话的独特性,它不仅包括知识的传递,更重要的是包含深刻的文化和学术传承。借用这样的教育对话,学生可以超越单一的知识点,接触到学科的生命力和发展脉络,从而在个人的学习旅程中能够不断发现、创新和贡献自己的声音。
(五)学习的过程:对话空间的扩展
对话式学习并非单一线性的过程。它如同多声部交响曲,每个新融入的声音都提供了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在这个过程中,新声音的加入并不意味着必须摒弃旧的声音,而是在不断扩充个人的声音库,拓展对话的边界。这种拓展并非单一的从A点直达B 点,而是一种从A 发展到A+B 的过程。即便是新视角在某些方面明显优于旧视角,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很多方面胜过拉马克的理论,旧声音依然在对话中占一席之地,作为思想演变与迭代的基础。
对话式学习作为对话空间拓展的一种实践,既体现在个人层面,也显现在集体层面。例如,在科学领域,每项新的发现都将之前被排除在外的内容纳入对话范围。无论是粘菌穿越迷宫的研究(Alexanderer et al.,2021),还是识字如何改变大脑结构的研究(Dehaene,2011),它们不仅仅是向已有的科学发现增添新的内容,更是引入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新视角,从而为该领域的对话空间引入新的声音。
对话并不意味着所有声音都会被平等对待。例如,在科学和伦理的发展过程中,新的声音往往试图压制旧的声音。然而,被压制的声音很少会完全消失,它们更像是随着新发现或新变化可能回归的备选声音,静待着时机。将学习视为对话空间的拓展,这一观点类似于生态系统的演化,旨在支持多样性,因为多样性已被证明是适应环境变化的有效策略。教育的目的在于引导学习者步入不断拓展的文化对话空间,学习知识,塑造自我。
四、当下主流教育技术理论的论述
对话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内涵强调理论创新应当建立在现有理论基础之上,并融合新的多元视角和观点。遵循这一框架,本节深入探讨当前两大主流教育技术理论——谈话理论(Conversational Theory)和联通主义(Connectivism),旨在寻求理论创新。
(一)谈话理论发展与应用
近代法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强调技术的自主进化动力。西蒙东的观点并非把技术视作与人类社会完全独立的实体,而是强调生物体与技术之间的互动性(Simondon,2011)。这种相互作用是理解技术能动性的关键。他阐述了人类个体与复杂机械之间的关系,认为这种关系不是外在的控制,而是基于深入理解和互动式探索的协同合作。这种互动催生了用于共同反思和共鸣的空间。例如,内燃机的发明展示了人类在整合机械的内部结构及其环境适应性方面的重要作用,不仅预见了机械的发展方向,还与之共同进化,促成技术与人类的共同进步。
教育技术领域的学者吸纳了西蒙东的观点,将教育视为发展中的社会技术系统,强调人类与技术的紧密联系。例如,智人的出现和火的使用、燧石工具等都与人类语言的发展密切相关(Stiegler, 1998)。技术的迭代与生物演化的步伐并不总是一致的。这种不一致导致多种紧张关系(Geary, 2008),教育可以被视为人类应对技术发展速度超越生物适应能力挑战的一种适应策略,其目的在于提升人类的技术能力,支撑社会技术系统的持续发展和繁荣。
担忧归担忧,李咏最终还是凭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小嘴儿把我们全家顺利“拿下”,1992年9月26日,星期六,我们俩在我的老家结婚了。
在西蒙东的理念中,技术——特别是主导的通信技术,被视为塑造人类本质的关键因素。基于这一理念,控制论专家戈登·帕斯克发展了谈话理论,将谈话视为学习的核心机制,认为在此过程中,不同的声音(不论来自人类还是机器)能够进行信息的交流和互动。他提出,为了构建有效的谈话,参与者需要精准描述自身行为,并持续探索和拓展这些描述。此外,他强调将这些共同构建的理解应用于实际活动中的重要性。简而言之,个体或系统要实现学习,必须就其所知与自己和他人进行有效的互动和交流。
麦克·夏普尔斯等(Sharples et al., 2010)将谈话理论用于解释通信技术支持下的学习过程,并据此发展了“移动学习理论”,即利用移动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其他便携式技术,开展教育和学习活动的理论。移动学习理论强调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任何设备进行个性化学习,并且能适应学习者的移动性。为了改善多样化环境的“无缝”学习体验,劳里拉德(Laurillard, 2002)强调必须建立有效的反馈循环和定义清晰的对话机制。这种方法旨在确保学习过程中的互动和沟通能够持续进行,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和环境条件。劳里拉德在其“谈话式学习框架”中进一步扩展了帕斯克的概念,突出了复杂学习过程中教师与学生间不断迭代的对话和互动的重要性。其谈话理论深刻反映了数字时代学习理论的核心要素,即教学互动的内容和形式应与相应的通信技术特性相协调(Laurillard, 2013)。例如,学习者可以通过观看视频材料获取基本信息,再通过网络平台对相关主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通过模拟实验加深知识理解。这种多维度、交互式的学习过程不仅促进了学习者对信息的深层次理解和吸收,也显著提升了学习的有效性和趣味性。
尽管谈话理论为捕捉对话的本质提供了框架,但其在揭示对话深层意义方面尚存在局限。真正的对话远远超越了机械式的表面互动,它触及参与者之间的互相启发和深层互动。这样的对话不只是信息的交换或简易的互动,还涉及参与者深层次思维、情感、价值观乃至文化背景的复杂而多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参与者不仅分享和接收信息,更在交流中相互塑造认知框架,扩展思维视野,通过相互作用实现知识与经验的共生与共进。从这个视角看,教育技术应更多关注拓展对话的社群和共享的内涵和意义,强调在教与学的互动中,深入理解和尊重多元观点,以及在共享的语境中寻求共鸣,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知识的深入理解与创新。互动不应仅限于表层的知识交流,而应深化至思维、情感与文化层面的交汇与融合。
(二)联通主义的兴起和影响
联通主义被誉为数字化时代涌现的新的教育技术理论,其理论基础来源于实践。乔治·西门斯(Gorge Siemens)2008 年在曼尼托巴大学开设的“联通主义与联通知识”课程,是这一理论的典范,该课程吸引了25 名注册付费学生和2000 多名在线免费学习者。课程采用多样化的技术手段,包括新闻订阅器(RSS feeds)、第二人生(Second Life)、Moodle 中的博客帖子和同步在线会议等,支持学习过程中资源的选择和内容创造、分享及应用(Siemens, 2005)。
科迈尔与西门斯(Cormier and Siemens, 2010)将该课程视为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的范例。随着MOOCs 的发展,基于传统讲授式教学的MOOCs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上述MOOC 则被追溯性地定义为联通主义MOOC(cMOOC),形成与麻省理工学院创立的EdX 和斯坦福大学发起的Coursera 上运行的xMOOCs(基于传统大学课程模式的扩展MOOC)的鲜明对比。cMOOCs 的特点在于基于唐斯提出的联通主义理论。该理论看重互联网对教育模式和方法的革新,将学习视为网络化的过程,强调跨网络整合以及分享知识的能力(Downes, 2012)。
联通主义理论认为,联通是自然发生的现象,它是一种基于网络互动的过程,而不是有意识的“社会构建”活动。这一理论观点挑战了传统学习理论中以认知主义为基础的观点,拓宽了学习的定义,强调学习过程不仅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物质世界和技术系统。例如,机器学习算法和某些基本生命形式,如粘菌,证实了非人类实体能够学习如何更有效地结合不同的知识源,以增强其功能(Alexander et al.,2021)。
联通主义理论倾向于将意义构建简化为由节点和连接组成的外在网络结构。这种网络连接的概念虽然能阐释计算机程序的学习模式和自然界生物演化的某些方面,但不能完全阐释人类之间的对话互动。在对话交流中,参与者不仅是网络中简单的节点,他们各自在互动中构建了对方的内在情感与知识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反思与行为调整,这仿佛是从第三方或对话见证者的视角进一步拓展对话。正是通过这种对话过程的自我意识扩展,个体能从新的视角审视问题,获得更深入的理解与认知。因此,教育中的对话不仅仅是简单的点与线的连接,它是一个涵盖认知发展、思维塑造和共情能力的复杂过程。
五、对话式教育技术理论
(一)教育技术与联通性
联通主义作为学习理论,劣势在于其本体论的简约性,即基于节点和链接构成体系。然而,教育的本质并非仅限于网络形成。教育发生在个体的意识层面(Stojanov, 2017)。对话式教育关注学习者如何通过汲取多种声音,不断完善个人认知。从根本上说,对话式教育旨在充分发挥联通网络促进知识分享与情感沟通的潜能,将联通网络转化为对话空间,利用教育技术拓展个体间以及个体与技术间的对话价值,创造一个“超个体”的人机共同体。
人工智能支持的在线辩论和决策系统(如Pol.is)通过绘制参与者在对话中的位置,展示不同观点。这种可视化地图让参与者看到观点的共识与分歧,促进认知层面的相互理解。当个体在Pol.is 中发表意见,他们不仅定位于网络的一个节点,而是从整体对话网络的角度观察。这种视角转变,既体现了个体向外界表达的声音,也反映了外部对个体的定义和定位。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不仅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还考量他人的、群体的观点,拓展自我意识,形成更具对话性的自我。这里的“自我”不是一个静态实体,而是一个动态的、持续对话的过程(Chang, 2021),同时它也促进了集体智慧的形成。
(二)教育技术与参与性
在探讨教育技术与参与性时,不可忽视的是帕斯克的谈话理论所强调的个体间外在的交互作用。然而,该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话过程中个体内在认知的转变与发展。这一观察提示我们,教育技术的设计与应用不应局限于对话的表面形式,而应深入地关注对话空间内的话语内容及其深层含义。这意味着教育技术的设计者和实践者不仅需要重视对话的形式结构,还要提升对话内容的质量,从而促进更全面的认知和理解发展。
开放对话空间通常由教育工作者建构,他们在与学生的互动中引入问题或挑战,激发深入讨论。开放的对话空间,尤其是结合互联网的广泛资源,可以大幅度地拓展、引入多样化的观点与声音。这一过程对个体在集体智慧构建和社会身份认同方面的发展尤为关键。例如,研究表明,通过互联网引导的不同文化背景青年之间的对话,能有效促进个体观念向开放式对话思维的转变。观点的差异不仅促使参与者审视支撑各自观点的论据,还有助于深化理解与促进知识的共同构建。
在技术层面,创建具体的对话平台(如维基、网络论坛或核心网站)可维持并加强这些对话。这些平台能够汇集不同观点的人员,促进交流与学习。具体来说,新一代生成性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根据这些多样化的观点,自动生成新的问题和话题,丰富和扩展对话内容。这种技术的应用,不仅体现了教育技术提升对话参与性的重要作用,还为多元文化交流与认知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三)教育技术与时间维度的扩展
传统教育倾向于将长期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观点作为不变的真理,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真理”更多的是特定时间节点下的共识或正确认知。教育的根本目标应当是激励学生积极投身于对这些共识的深入思考、质疑和发展。这一过程不仅涉及将共识或正确认知应用于验证具体事件(即降维过程),也包括从新实践中吸取经验发展这些共识或认知,以推动文化对话的不断继承与发展(即升维过程)。
兰克(Lemke,2000)提出,有效教育应当构建“异时性”(asynchronism)桥梁,以连接短暂的面对面对话和更为持久的文化对话的不同时间维度。韦格里夫等(Wertsch & Kazak,2011)将这一过程形象地比喻为教育中的“滑雪升降机”,象征从具体情境向抽象概念的过渡。因此,教育技术应被设计和应用于有效促进不同时间层面对话的交互与融合。例如,亨内西(Hennessy, 2011)关于电子白板使用的研究案例表明,学生可以在古老艺术作品上记录他们对伊丽莎白时代历史的初始理解,在接触到更多信息后,他们有机会回顾并反思自己的观点是如何随时间而变化的。学生不仅学习历史知识,更是主动参与历史解读的持续对话。教师的引导作用在于将学生的观点与当代学术史专家的辩论相联系,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于长期历史对话的参与和理解。
从短期到长期对话的转变贯穿于所有学科领域,例如,学生可能从在操场上直观讨论“力”,过渡到伽利略实验中对“力”的科学概念的理解,再进一步参与当代科学家对力学研究的辩论。技术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扩展时间维度,将短期实践与长期理论对话相互联系。这不仅提供了长期对话的渠道,而且在两者间建立了动态的互联,例如通过将课堂实验与在线科学辩论相结合,推动科学知识的深化和传播。
六、结语
在对话教育中,至关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对话中学会共同学习(learn to learn together),并激发他们积极参与跨越文化与时间的长期对话,拓展与丰富知识和观点。在这个过程中,通信技术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有效地连接了本地的短期对话与全球的长期对话,使得学习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时空环境。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与迭代,教育的模式也相应发生了变革:从依赖文字进行客观知识传递的传统方法,转变为互联网时代万物互联的方式。互联网技术在全球层面支持集体意识的形成,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知识分享与交流成为可能。
在数字时代和人类的挑战面前,对话式设计方法对教育和技术的发展尤为重要。在人类与技术的整合过程中,我们见证了全球人机协作的兴起。教育技术的应用并非单纯复制现有的教学方法,而是意味着在教育过程的设计中与技术对象进行互动对话,共同构建全球生物—社会—技术系统。这种融合不仅能促进教学方法的创新,而且为全球教育带来了深远的变革。我们提出的教育技术对话理论框架包括一系列设计原则:
1)设计链接:通过与不同层次的声音进行对话式接触,将其纳入网络,包括个体的声音和广义他者的文化声音;
2)设计参与:开放、扩大、深化、维护和保持对话空间;
3)设计时间维度的扩展:建立支持可持续的、双向的对话式互动,跨越从短期和局部到长期和全球的不同时空维度。
这一理论深入探讨了如何设计更具对话性的个体自我,并涉及技术支持的对话空间的广泛扩展。在有效的对话模式中,集体身份的构建不会抑制个体的声音。相反,它鼓励每位参与者感受并重视他人的贡献,同时促进自身的思想扩展与丰富。本理论的目标是推动克服人与人、人与技术之间的隔阂,共同构建更广泛的、对话式的集体意识。我们期望对话式教育技术理论能够促进人与技术的协同互动,不仅促进人类社会的繁荣,而且有助于实现全球性的生物—社会—技术系统的共同发展和兴盛。教育技术不仅是知识传递的工具,而且是促进全球性对话和理解的平台,有助于构建更加和谐、包容的全球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