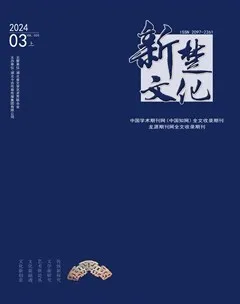刘姥姥形象新解
2024-05-10林玉峰
【摘要】汉语中“农民”的含义较为模糊,借助英文中有着明确区分的peasant和farmer,本文首先把这种模糊性澄清为两种“农民”类型。基于此,本文认为《红楼梦》中的刘姥姥是一种典型的peasant。根据相关文本,本文一方面分析了刘姥姥所代表的典型农民心理,另一方面考察了导致这种心理的外部现实条件。据此,本文认为现代化的关键任务之一是两种“农民”的转化,即不仅要取消等级隔阂,还要摆脱旧的农民心理。
【关键词】刘姥姥;农民;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2261(2024)07-0037-03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4.07.012
刘姥姥是《红楼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在一般的解读中,她通常被默认为是一个“农民”,但是现代汉语中的“农民”的含义却并不同于刘姥姥所代表的古代“农民”,因此这个解读策略上的预设带来了理解上的混淆,进而压缩了我们阐释“刘姥姥”的解读空间。
有鉴于此,本文借助英文中peasant和farmer的区分引出了“农民”的两种类型,然后以此作为考察的视角,首先对相关文本内容做出更为丰厚的解读,特别是从曹雪芹对刘姥姥的刻画中提取出典型的“农民心理”,然后在此基础上走出文本,进一步分析peasant意义上的“农民”等级,从而指出现代化的关键任务之一是两类“农民”在外部社会关系和内部心理活动两个方面之间的转换。下面首先辨析“农民”这个词的不同义项。
一、“农民”的含义
英语中指称“农民”的单词有两个:一是peasant,二是farmer。虽然这两个单词的汉译都是“农民”,但它们的具体含义却有着巨大的差别。peasant这个词在英语中和lord(主人)相关,它既指(为主人)做农活的一类人,也有身份等级之意,即依附于lord。与此相对,farmer指称的是一种职业,即在农业生产领域进行劳作的一类人,它与fisher、merchant等词是并列的[2]20-24。实际上,从词源学的角度看,farmer正是作为peasant的替代项而出现于16世纪晚期的,因此它的产生和流行与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化趋势紧密相关①。
英文peasant意义上的“农民”可以在古代汉语中找到对应项。
据学者们的考证,早在甲骨文、金文时代就已经有了“农”与“民”两个词,而“农民”这个词则是后来产生的,比如《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条中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据此可知,“农”与“士”“商”“工”所表示的是从事不同生产活动的人,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即一种“职业”,而“四民”之“民”则有“等级”的含义,即所谓“士农工商”。此外,“民”古同“甿”“氓”“萌”。《周禮·地官·遂人》中说“凡治野:以下剂致甿,以田里安甿,以乐昏扰甿,以土仪教甿。稼穑:以兴锄利甿,以时器劝甿,以强子任甿”。郑玄注“变民为甿,异外内也”。《说文解字》中说:“民,众萌也,言萌而无识也。”由此可以看出,“民”不仅指特定的“等级”,而且还有“卑贱”的意思。因此,古汉语中的“农民”不仅指一种较低等的“职业”,还有“卑贱的社会身份”的意思。
但是在现代汉语中,“农民”基本上与farmer同义,所指的是一种与商人、工人等群体相并列的职业。
在以上辨析的基础上,我们下面进入对《红楼梦》中的相关文本的解读,首先是从中提取出刘姥姥所代表的一种典型“农民心理”。
二、刘姥姥进大观园
我们先来看一个细节:“满屋里的东西都是耀眼争光,使人头晕目眩。刘姥姥此时只有咂嘴念佛而已。”[1]65“念佛”是净土宗传下来的方便法,本意是便于信徒修行,但是刘姥姥此时念佛显然不是为了“精进”,而是在镇定内心的惊惧:她惊的是屋里的摆设,惧的是屋主人的威严。她仿佛是要靠世尊的庄严法相才有继续走下去,以至于“不辱使命”的勇气。尽管佛教从魏晋以来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它最为基本的“众生平等”的信条却并未在现实层面留下有力的痕迹,反倒是转换为一种方便法,在贫苦农民的心中化作“阿弥陀佛”的咒语,成为这些劳苦百姓自我安慰的工具。刘姥姥“咂嘴念佛”何尝不是对上述反差的一种讽刺。
惊惧之后,刘姥姥第一次见到了凤姐:“犹未起身,满面春风地问好,又嗔着周瑞家的:怎么不早说?刘姥姥已在地下拜了两拜,问姑奶奶安。”[1]67曹雪芹在这里用的“已”字非常饱满,至少可以对其做出两种解读:要么是凤姐还没开口,刘姥姥已经拜下去了;要么是凤姐一边说一边下拜。但无论哪种情况,刘姥姥那种局促不安、诚惶诚恐的模样都跃然纸上。以传统礼仪作为参照项,这个场景表明“尊卑”的权力顺序压过了“长幼”的自然秩序,因此处在前一对关系中的刘姥姥纵使是比凤姐大几十岁的老人,也要向后者表示尊敬,并且还要承受心理上的压力。
的确,刘姥姥说的话和她的行动处处体现着她的卑微感。比如“论今日初次见,原不该说的;只是大老远的奔了你老这里来,少不得说了”,“刘姥姥才扭扭捏捏地在炕沿儿上侧身坐下”等。值得注意的是,刘姥姥的此类行为也被笼统地称之为“遵守礼数”,似乎她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且合乎礼仪的,但是如上所分析的,这种“遵守礼数”的行为其实是处在“尊卑”秩序中的刘姥姥所不得不做的。从刘姥姥自身的角度来看,她的“礼数”实际上是她对自己的自我贬低,因此与现代人表达尊敬的情况不同,刘姥姥的尊敬并不建立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的基础上,而是在恐慌心理中以牺牲自己的尊严、博得对方的欢心为前提。
不过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观察到其实仍有很多人采取刘姥姥式的打交道方式,这些人虽然憨厚可爱,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却几乎是本能般地以自我贬低的方式来博人一笑。就古代社会的情况而言,这种带有粗俗色彩的“质朴”的来源之一即前面所说的众生平等观的破产,而在现代语境中,这就是由于无法建立起人人平等的理念,所以刘姥姥们才需要而且也不得不博人一笑。对于这种“粗俗的质朴”,曹雪芹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写:
“我们也知道艰难的,但是俗语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呢。凭他怎样,你老拔一根毫毛,比我们的腰还壮哩……我的嫂子,我见了他,心眼儿里爱还爱不过来,那里还说的上话来?”[1]69-70
不得不赞叹曹雪芹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之能力的高超!刘姥姥这两段话简直是“老农民”最生动的写照。虽然刘姥姥这种不加掩饰地表达喜悦之情的方式确实直接、朴素,但是我们必须洞察到这背后所隐藏着的深意:这种质朴的感情建立在凤姐儿高她一等的预设之上,只不过前者给刘姥姥的二十两银子大大超出了她的预期,所以这种满足感就在前后不搭调的词句中突兀地表达了出来。毫不夸张地说,刘姥姥的话几乎是“谢主隆恩”的“歇后语”式表达。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粗俗的质朴”与孔夫子说的“质胜文则野”完全不同,因为后一种“质朴”的含义是在与“文”的对照中显现出来的,换言之,前一种“质朴”缺失的是“人人平等”,而后一种所缺失的则是“文”。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要问:刘姥姥“知礼”吗?回答是:当然不知,她只是在尊卑等级秩序中以一种恰当“得体”的方式表现出了她的局促不安和卑贱低下。那么她“质朴”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因为她那看似“天然”的、“自发”的感情流露只不过是一种不平等预设得到超额满足后的过激表达罢了。
三、农民(peasant)作为一种等级
刘姥姥二进贾府后直接见到了贾母,后者感叹自己的身体尚不如70多岁的人硬朗时,刘姥姥回道:“我们生来就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来就是享福的。我们要也这么着,那些庄稼活也没人做了。”[1]416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宿命论的观点,但是实际上,刘姥姥这番话其实表达的是一种无可奈何(她后面还说“我们想这么着也不能”)。这种“无可奈何”表明,像刘姥姥这样的农民虽然身份卑微,没有知识没有财富更没有社会地位,但是他们仍然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只不过如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的,身处尊卑等级中的刘姥姥们虽然想要过得更好,但是自己的心理却已被这个秩序所扭曲,习惯了遵照“礼数”在自我贬低中“享福”,因此他们缺乏改变自我的精神力量。而在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一种较低的等级当然也无力改变自身的现状。因此,除了前面结合《红楼梦》文本对刘姥姥的心理做出的分析外,我们还需要再深入到作为一种等级的“农民”受到了何种限制。
首先需要澄清一对相近的概念:阶级与等级。前者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或集团凭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无偿地占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团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甚至是一部分必要的劳动”[3]118,所以“阶级”产生的前提是有生产资料所有制,否则也就不存在“垄断”和“无偿的占有”。但“等级”却与此不同,它是基于权力所划分出的有继承性的不平等层级,因而是一个前现代的概念,如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所谓等级是指历史意义上的封建国家的等级,这些等级有一定的和有限的特权。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这些等级及其特权。”[5]655在这个意义上,“财产”在“等级”中反而居于次要位置,在传统的“士农工商”等级序列中,商人甚至包括富农从来都是被打压的对象,比如西汉的“三选七迁”,明初的“右贫抑富”等都是如此。因此,在一个等级社会里,财产不过是个人权力的物化形式而已,而且两者也并不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即并不是财产越多、权力就越大。因此,所谓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其实质“仍然是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上按权分配的等级分化,而不是在所有制关系基础上按资分配的阶级分化”[2]135。换言之,是在权力之强弱而不是在财富之多寡的基础上产生了“酒肉臭”与“冻死骨”的现象。
而这个“人身依附关系”其实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在那里(封建社会),我们不见独立的人,但发现每一个人都相互依赖——农奴和领主,家臣和封建诸侯,俗人和牧师”,他们和“所有同時代的人一样,本质上是共同体的成员”[4]53。也就是说“人身依附关系”是相互的,封建社会中并没有一个真正独立的人 ,所有人都依赖于整个共同体。反过来说,共同体既给个体施加了束缚,但也在同时提供了庇护,正是因为“束缚”与“庇护”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大多数的共同体成员不愿,也不能(或难以)走出去。
具体到“农民”这个等级,他们不仅没有财产,更重要的在于没有权力,尽管有来自权力更大者的压迫,但是因为这些人也能够为农民提供庇护,就像凤姐“大手一挥”送给刘姥姥的东西一样,所以农民实际上对于共同体的依附更强。而最致命的是,由于他们得到的庇护越多,实质上受到的束缚也就越强,因此其心理的扭曲程度也会随着这种恶性循环而加大,直到完全脱去仅存的质朴(尽管它是粗俗的)而成为溜须拍马的小人。
总之,封建社会的农民一方面背负着沉重的、卑贱的社会身份,没有社会地位的同时也没有所有权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又被压制在共同体当中,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个性。
刘姥姥虽然在大观园中畅快了几日,但也不过是“投了两个人的缘”而已。说到底,这种快活的日子终究是偶然的,不是她可以把握到的,回去了,就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然而必须指出,刘姥姥的不幸其实正来自她的“所幸”:她因是贾府的老亲戚(虽然是远房)所以得了贾母的喜欢(所谓“找个积古的老人家儿说话”),同时又因为来自乡下,有着许多新鲜事儿并扮得出很多滑稽相,所以博得了上自贾母下至诸丫鬟的(嘲)笑;然而,也正因为她得靠着“老亲戚”的身份和农民的粗野才能得到这一切,因而本质上她是在“售卖”了自己的人格与个性之后才“买到了”这一切(虽然刘姥姥自己不会认识到这一点)。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讲,她卖出的就是她自己的“自由”,而她所得到的,其实也不过是共同体中的“庇护”而已。
四、结语
前面的考察基于《红楼梦》中的相关文本,首先分析了刘姥姥身上折射出的农民心理:在权力秩序下,刘姥姥只得向内贬低自身以博得高位者的欢心,她能够做到“守礼数”,但是却因为出让了自己的尊严而不能践行“礼节”;她足够质朴,但由于生来的不平等让她不得不在这种质朴中添加奉承的因素,因此她并不淳朴。
在此基础上,前文进一步深入到形成这种心理的现实条件中,着重分析了作为一种等级的农民。借助马克思的理论,本文揭示出人身依附型的共同体社会所造成的“束缚”和“庇护”的矛盾循环:“农民”作为这种社会中的低等级受到强大的束缚,但是由于他们又必须为此寻求强权者的庇护,所以他们自己又主动地强化了对自身的束缚。
摆脱这种心理和社会关系上的扭曲的突破口之一,是把“权力秩序”换为“权利秩序”:不是事实上的权力的大小作为基石,而是“天赋人权(权利)”作为初始条件,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进而奠定每一个人的尊严。从历史上看,“天赋人权”观念的确认过程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以及启蒙运动的展开。工业革命打破了人身依附型共同体社会,个体因此成为自由市场中的自由劳动者,而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则为这些“自由人”提供了新的观念体系和道德价值。
就“农民”而言,上述转换意味着作为peasant的刘姥姥们转变为现代经济中的拥有独立人格和权利的farmer。在这个意义上,这两种农民类型之间的转变也正是现代化的要义之一。
注释:
①参考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https://www.etymonline.com/word/farmer#etymonline_v_33036.
参考文献:
[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裴效维,校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2]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
[3]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词典: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卷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林玉峰(1998-),男,汉族,山东泰安人,研究方向:德国哲学、现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