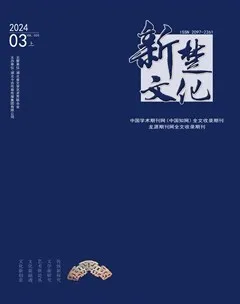记忆、共享与表征:基于奇石乡壮族传统婚礼的考察
2024-05-10陈鸣郭丽梅胡中全
陈鸣 郭丽梅 胡中全
【摘要】壮族传统婚礼仪式在具体流程、符号呈现、象征意义等方面有其民族特殊性,体现壮族人民的文化心理、精神思想和价值观念。本文以传播仪式观为理论支撑,选取奇石乡作为田野调查点,通过深描当地传统的婚礼仪式,分析其符号系统,揭示当地壮族人民共享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传统婚礼;仪式;符号;文化
【中图分类号】K8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2261(2024)07-0013-03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4.07.004
【基金项目】2021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传播仪式观视域下广西壮族传统婚礼研究”(项目编号:2021KY1533);2022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计算传播学范式下的广西非遗文化传播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2KY0749)。
仪式研究是一个巨大的话语系统,它活跃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宗教学和传播学等领域。传统的婚礼仪式被看作是人类生命进程中的神圣事件,承载着特定民族和地区的原始记忆和精神信仰,在各民族的文化历史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从神圣逐渐演变为世俗,不是私人性活動,而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场域,是家庭、家族关系往来的公共性事件。经历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后,我国各地的传统婚礼虽然在仪式内容上发生了较大变化,但仍保留了核心的象征符号,它们与特定流程、规范被基本确定下来,成为地区和族群内部的相对稳定的仪式形态。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由中国古代南方百越族群中的西瓯、骆越发展而来,有着悠久的民族历史与深厚的民族文化。作为古老的少数民族,壮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不断传承和保护着他们的精神文明,且又发展出新的独特文化。本文以广西贵港市奇石乡作为实地田野调查点,过去这里交通不便,奇石乡因此成为一个集“老、少、偏、山、穷、库”为一体的地区,多年来被人们称为港北的“西伯利亚”。2008年,奇石乡实现了村村通水泥路的目标,交通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贫穷落后的面貌。但因地理位置偏远,山路盘绕,村民出山进城仍然不便。这样的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使人们的生活形态极为独特,具有鲜明的壮族特色。他们的生产、生活、民族信仰和各种习俗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孕育而来。
一、呈现:仪式的过程描述
第一,婚前筹备。在壮族乡土社会,小孩满月、婚丧嫁娶、乔迁动土、老人过寿等都算得上是村里的大事,需要付出较多的精力和金钱。青年男女一般没有财力和物力筹办婚礼,主要还得依靠父母的能力和人际关系。壮族人民自古有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村民们平日忙于劳作,除了重要的传统节日之外,大家基本无暇聚在一起休闲娱乐,所以凡是村里有人办大事,尤其是婚礼这样的喜事,亲人和村民都会很热情地赶来帮忙,也会把自家家什拿来派上用场。村民们在后厨忙着备婚宴食材,巧妇壮汉们围坐在一起,一边忙碌一边闲聊,气氛十分热闹。
第二,祭社公。仪式当天是婚礼中最重要的一天,家族的重要成员早早就要备好香火蜡烛、红色纸钱、米酒、三牲(鲤鱼、全鸡、猪头肉)、糯米粽、水果(甘蔗、苹果、柑橘)、糖果等供品到社公庙祭拜,当地称之为“祭社公”。祭社公过程比较简单,在场成员依次给社公上香火和祭品,烧纸钱、燃放爆竹,最后行跪拜礼,再返回家中分配任务。然而,仪式虽过程简单,却是一个十分神圣的行为,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严肃对待,祭社公时新郎和其他晚辈须站在一旁,认真接受长辈的行为示范和家族道德观念的教育。
第三,接亲。祭社公结束后,父母和长辈们备好接亲的礼物,包括活鸡、活鸭、猪肉、米、面条、红包、茶叶、酒、香烟等。接亲的花车到达女方家后,新郎及伴郎们勤快地把满车礼品卸下交给女方父母,并向在场的女方亲人、邻里发香烟、糖果等小礼物以增进感情。按照当地壮族的婚俗,新娘出门前须携新郎祭拜女方祖先,答谢祖先养育之恩并祈求保佑。祭拜祖先也是神圣严肃的大事,其时辰很讲究,女方父母往往会提前请当地师公根据女方八字来选定祭祖和出门的良辰。祭祖结束后,新娘新郎再拜谢女方父母,最后拜谢女方的亲戚……所有仪式完成后新郎及接亲队会在女方家吃过酒宴,当日下午再把新娘接往男方家。
第四,点烛。新娘进门的时辰一般是师公合算的吉时。花车队返回男方家后,此时新娘不能出轿(过去是花轿,现在一般都指小轿车),而是坐在轿内等待新郎入堂拜祖先,意即告知有新人的到来。点烛是奇石乡壮族的婚俗特点之一,在新郎入堂拜祖先的仪式上,两位点烛人点上一对红蜡烛插在神龛上,寓意家族香火得以延续。点烛者原则上应为男方母系氏族的两位亲属,一般是新郎的舅爷(即新郎奶奶的兄长或胞弟)或舅舅(即新郎母亲的兄长或胞弟),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男方母亲族内其他德高望重的男性。两位点烛人各点燃一根蜡烛后合诵点烛词;然后舅爷为新郎佩戴红花,继续合诵贺婚词;新郎鞠躬,三拜祖先,点烛人合诵祝词;新郎再拜祖先。礼毕。
第五,进门。新郎随即引新娘入门拜堂,先递给新娘一个红包,伴娘在轿外为新娘撑开红伞,扶新娘的是新郎的姑婶,到厅堂门口后止步,待人用水浇熄一把被烧烫的犁头,新娘须跨过盛装犁头的火盆再入堂,伴娘收起红伞。据说撑红伞和跨火盆都各有含义:新婚当天新娘的地位最大,但不能与天相争,所以要撑伞避让;而跨火盆则是指驱除路途中新娘身上带来的阴气和邪恶,犁头作为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驱邪的吉祥物,在当地壮族也被认为具有驱邪的作用。
第六,拜堂。拜堂前,一位男方同族的女性长辈在地上铺一张席子,席子中间搭好“凤桥”。“凤桥”即一块方形红布,四边摆放六枚铜币。新郎和新娘分别站在“凤桥”的左右两边,另一只脚则共同踩在“凤桥”上。拜堂之前,其中一位点烛人抱起一只阉鸡(当地称“项鸡”),并用嘴咬住项鸡的红冠(据说过去要把鸡冠咬破,因为他们认为项鸡的血可以辟邪),另一位点烛人则念词主持新人拜堂,先三拜祖先,再背向堂外三拜天地,最后夫妻对拜。
第七,入洞房。当地没有闹洞房的习俗。新人拜堂结束后,新娘须独自在洞房内静坐片刻,在有些汉族地区也被称之为“坐帐”或“坐福”。洞房摆放的物件一般是固定几样——梳妆桌上摆放的油灯两盏,针线一盒,毛线一捆,牙刷一对,梳子一对,圆镜一面和床边放置的脸盆两只,水桶两只,桶里装有一些水果和糖果餅干等。稍坐片刻后,新娘则洗漱并更换一套新衣服,寓意洗去身上的邪恶之气。
第八,敬酒。壮族人民家族庞大,人情关系融洽,参加婚礼的宾客多,所以晚宴一般采用“流水席”的形式。新人敬酒十分讲究顺序——首先敬舅爷,其次敬舅舅,然后敬同族亲人,最后敬邻居朋友。敬酒环节的目的,除了表达对宾朋亲友们的感谢,更重要的是使在场的乡亲邻里和朋友们得以认识新娘,新娘的身份也从“外人”向“内人”转变。
二、表征:仪式的符号系统
仪式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由众多的符号组合而成,表征特殊的文化内涵。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指出,象征符号是仪式中保留着仪式行为独特属性的最小单位,它也是仪式语境中的独特结构的基本单元。当地壮族传统婚礼仪式的象征结构主要包括颜色、人物、物质、行为等。
第一,颜色符号。各民族对颜色的理解不尽相同,使得原本普通的颜色被赋予了符号象征功能。在仪式的符号系统中,壮族人民对颜色符号的表达最为明显、直观和活跃,对颜色的运用也颇为讲究,特别是红色的使用最为浓烈且广泛,无论是空间布置还是婚礼物品的选择都离不开红色,比如红色的“凤桥”,红色镜子,新娘入门时撑的红伞等,一些原本不是红色的物品也被张贴上小红纸。红色在婚礼上被广泛使用,不仅因为它能营造喜庆的氛围,而且也有驱恶辟邪的寓意。
第二,人物符号。人物符号是指通过人物个体在特定场域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表达一定隐喻信息的符号。按照符号学来理解,人物符号价值既不在于本体论本体和本身,而是一种高于本体的载体,并且也源于本体论本身来表达某些抽象的含义。人类生存的世界是一个符号化的世界,同时,把世界的一切进行符号化又是人类在创造自然和改造自然过程中的内在需求,包括把人作为符号化的对象。壮族传统婚礼仪式特别讲究人物角色的精心挑选。如在“点烛”环节中,点烛者由新郎的舅爷和舅舅担任,他们是整场仪式最受敬重的长辈,折射出当地壮族人民强烈的家族亲情观念。扶新娘出轿的人一般是育有一儿一女的姑婶,因为这样的角色寓意“好”,象征当地人向往幸福美好的愿景。
第三,物质符号。仪式中的物质符号是在仪式过程中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可感知的具象物质,壮族人民赋予这些物质以精神和信仰上的内涵,使共同体成员在看到这一物质时就能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传统婚礼对物质符号的运用一般来源于对物质用途与谐音的取义,有的甚至源于当地与该物质有关的神话传说。婚礼上随处用到的松枝、蕉叶等装饰品,既代表辟邪之意,也象征着夫妻感情长盛。糯米是壮族人民逢年过节或办大事时必不可少的食材和用具,但它在不同仪式上的象征功能有所不同,比如在某些法事中,做法的道公常常会有抛洒糯米的行为动作,因为糯米被认为是驱邪之物;而在传统的婚礼仪式上,也常常看到多处摆放的糯米粽,在这里,糯米则因具有较强黏附力的自然属性而象征着新郎新娘以及家庭感情的亲密无间。除此之外,婚礼中使用的红伞、红烛、“凤桥”、圆镜、针线等物品,都是仪式上特定的物质符号,有着各自的象征意义。
第四,行为符号。行为符号是指具有表意和象征意蕴的行为动作,它们往往有相对标准化的模式,被约定俗成地运用在特定场景之中。在表征意义上,行为符号通常比其他方式更加直观。传统仪式的行为符号颇为丰富,这些行为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相互联系,共同表达特殊的意义。其表征的主要方式是,人们在仪式的每个环节中借助该行为进行模拟表演。由此观之,壮族传统婚礼仪式的每一环都是模拟表演的过程,如新郎新娘在拜堂时共同踩在“凤桥”上,这一表演是借助“凤桥”作为“桥”所具有的联结功能,模拟夫妻渡桥,既表达了新娘通过“桥”过渡为新郎家人,同时也包含夫妻从此共渡难关之意。又如新娘入门时,由伴娘为其撑红伞,新娘跨火盆等行为动作,都是为新娘驱邪的行为象征。这些逐渐形成了一套固有的行为模式,成为当地传统婚礼仪式的标志。
三、共享:仪式的文化记忆
当地壮族传统的婚礼仪式通过以上符号的组合阐释着仪式的文化意义,使集体共享着古老壮族人民的文化历史和民间信仰。
第一,祖先崇拜观。壮族的祖先崇拜观念从氏族社会开始形成且深深烙印在壮族人民的心里。他们相信:祖先虽肉体死亡但灵魂永存,他们时刻关注后代的生存状态,并且通过意念保佑和决定子孙们的命运。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当地每家壮宅厅堂的正中央大多会摆放一张大约一米多的“神台”用以摆放祭祖的供品,正上方是一座写着“(姓氏)门堂上历代宗亲之神位”的神龛,左右往往张贴家族祈愿、戒规等性质的对联,如“积德乃能光祖业,善身方可扬家声”,横批“积善堂”等。这样的空间布局渗透着人们强烈的观念,即认为祖先是崇高神圣的,切忌亵渎,所以逢节日大事必供奉祖先。
第二,火神崇拜观。仪式有多个场景呈现出“火”的符号元素,如新娘入门时跨火盆,新郎祭拜祖先时舅爷和舅舅点烛火等。符号的象征意义通常是群体约定俗成的,“火”符号在很多民族或乡土社会都十分常见,其历史和文化意涵由来已久,具有“兴旺”“驱除邪魔”的含义及功能,成为很多民族和地区崇拜和敬畏的对象。在典籍里,传说中的人类祖先炎帝就是火神,因而火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神的化身。古籍中有“穷子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这一关于火的说法。取“薪火”之意,火则被衍生出人类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寓意。因此,在许多地方的传统婚礼仪式上都会运用火的符号,虽形式不同,但均用以象征家族子孙满堂,体现人们的火神崇拜观念。
第三,鬼神敬畏观。在原始社会,闭塞的自然生存环境易孕育出复杂的民间信仰。岭南地区流传着多神信仰,信奉着“万物皆有灵”的说法。虽然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鬼神,但对自然、神灵和祖宗的崇拜观念和敬畏意识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习俗文化的丰富内涵。“敬畏神灵”观念根植于壮族的婚俗文化中,在传统的仪式上留下深刻的印记。如在奇石乡壮族婚礼中通过“祭社公”仪式求得神灵对全家的保佑,祭祀活动必须由全家老少一起参加,而这样的仪式对年轻人无疑有教化作用,把鬼神敬畏的观念和信仰深深注入壮族人民的血脉里。
第四,舅权崇拜观。在母系氏族社会,孩子的舅舅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力,担负养家糊口的责任,因而具有强大的权威。受这一原始社会制度的深远影响,我国很多地区现在仍然尊崇舅舅在母系家族中的崇高地位,他们拥有很强的话语权,故而在民间也普遍流传着“天上雷公,地上舅公”的说法,体现了悠久且强烈的舅权崇拜观念,是母权制度的遗风。奶奶或母亲的长兄胞弟均属于母系亲属,他们在家族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与权威。因此,在壮族传统婚礼仪式中,新郎的舅爷和舅舅是婚礼的见证者和主持者,是整场仪式的核心人物,掌握比父母还重要的发言权,深受晚辈的尊敬。虽然人类步入父系社会,舅舅不再是家庭的掌权者,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关系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人们的交际生活和风俗文化。
综上,壮族的传统婚礼仪式有其民族特殊性,体现壮族人民的文化心理、精神思想和价值观念,是壮族传统文化的积淀和时代缩影。从根本上说,它是一场特殊的文化表演,它通过丰富的符号呈现和表征来为人们提供充分的对话场域,人们通过参与到这一场域里共享共通的文化意义,在时間上维系一个易逝的集体记忆。
参考文献:
[1]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7.
[2]Rothenbuhler E W.Ritual communication:From everyday conversation to mediated ceremony[M].CA:Sage,1998:53.
[3]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M].黄建波,柳博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6.
[5]符婷.民俗视野下中日崇火信仰的文化象征意义[J].文化学刊,2015(11):40-42.
[6]拉德克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M].丁田勇,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184.
[7]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理论与实践[M].陕西:陕西师范出版社,2019:25.
作者简介:
陈鸣(1993-),女,汉族,江西人,文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传播。
郭丽梅(1992-),女,汉族,广西人,教育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教学法、少数民族文化。
胡中全(1990-),通讯作者,男,汉族,安徽人,文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民族志影像、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