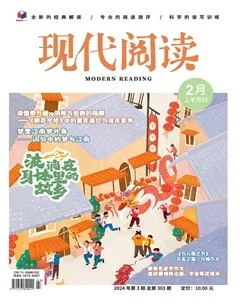天下有痴人,遗世而独立
2024-04-29梁开喜
明末张岱的《湖心亭看雪》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刘义庆《世说新语》中“雪夜访戴”的故事:王子猷居住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大雪纷飞的夜晚,他一觉醒来,放眼望去,银装素裹,好一个洁白晶莹的世界!他再也无法安睡了。忽然之间,他想到了远在剡县(今浙江嵊州市内)的朋友戴安道,于是连夜沿曹娥江(钱塘江支流)乘小船前去拜访。天亮时,他终于到达戴安道的家,可没有进门,又转身返回了。有人问王子猷为何这样,他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冰雪之气:象征高洁品格和忠贞心志
有人认为王子猷的行为疯癫怪诞,不可理喻。之所以如此,大抵是因为带着目的性和功利心去看待世界的缘故。我们的努力往往是为了求得一个结果,而“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王子猷在乎的却只是一个过程——那是一个享受孤独的过程,一个“妙处难与君说”的过程——那么,哪种选择更具意义呢?这是值得我们去探寻和思考的问题。不管怎样,“雪夜访戴”给我们展示了一种洒脱的生活态度和舒展的生命状态,具有穿越时空的恒久的诗意与魅力。
张岱的“独往湖心亭看雪”是放任旷达、元气沛然的魏晋风度的延续,与王子猷的“雪夜访戴”在精神气质上高度一致。
雪在这里不单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高洁品格和忠贞心志的象征。在古人看来,雪是至纯之物,所以有“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的说法。张岱在《一卷冰雪文序》中写道:“盖人生无不藉此冰雪之气以生……故知世间山川、云物、水火、草木、色声、香味,莫不有冰雪之气。”正所谓我见万物多清绝,料万物见我亦如是。或许,只有自己带有冰雪之气,才能在自然万物中真切地感受到冰雪之气吧。
大雪铺天盖地,大地纯然一色,这对任何有着孤怀逸情的人而言,都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召唤。但与一般人不同的是,张岱选择了一个特别的时间。这个时间是在“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之后,是在暮色四合的“更定”之后。雪势之大,本应诉诸视觉,作者这里却诉诸听觉,似乎世间所有的声音都被冻住了。“更定”出门,一方面是因为在特别的时间会有特别的景象;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作者既不欲人见,亦不欲见人的避世心理。
独往之行:表现超拔脱俗的高情雅意
在大雪封锁了“人鸟声”和“更定”的时候去赏雪,已经足够不同流俗了,更加耐人寻味的竟是乘舟“独往湖心亭看雪”。从后文的“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和“舟子”的悄声低语来看,作者肯定不是独自前往的,这里为何又说是“独往”呢?《教师教学用书》的说法是:“这个问题,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要去其形式,存其精神。这里不能单纯理解为作者目中无人。实际上,这表现了作者傲岸自持的情怀,是明末江南文人独立不羁精神的表现,其根源是魏晋风度。只有作者这样的雅士,才会夜赏西湖的雪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种解释抓住了“独”的本
质。但相比之下,我认为上海师范大学詹丹教授的见解更加切中肯綮:“就作者来说,他所谓的‘独往’,本来就不可能把雇佣的舟子包括进去。一方面,就如同我们打车出游,不会把出租车司机统计在游伴里。另一方面,也许在等级社会里,这种思维方式隐含着更深刻的含义,即主人们往往会把身边的奴仆等伺候者予以忽略。这使得舟子、奴仆等,根本不会影响到张岱是否写‘独往’中的‘独’。只不过,当作者进入具体画面描写时,……舟子等人又被重新统计进来。”说到底,这里的“独”是在审美旨趣与精神境界上将自己与舟子等人区隔开来,从而表现出作者超拔于世俗之上的高情雅意。
舟子的喃喃之语:“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既是俗人之惑,也是点睛之笔,那一个“痴”字,借旁人之口,表达了作者的清高脱俗和特立独行。而纵观《湖心亭看雪》,张岱之“痴”,不仅仅是行为之痴,更有寄寓在奇景与奇遇中的情怀之痴。
这里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作者虽在舟中,却用远观和俯瞰的视角来观察和描写景物,“痕”“点”“芥”
“粒”,愈来愈小。渐渐地,夜色朦胧,物我合
一,天地与人的关系,便成了“太仓”与“一
粟”的关系。在广大与渺小的强烈对比之中,个人似有若无,甚至变得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说“长堤一痕”是写实的,那么,“湖心亭一点”“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分明是在高远处才能看到的景致,所以这几处更多的是一种推想和感慨。
这种“情怀之痴”表现在凝练传神、字字珠玑的写景中,也表现在金陵客的话语里。“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有人先“我”而至,但不写“我”的惊诧而写客之“大喜”,将“我”的反应始终淡然地隐藏在“大喜”的背后。“问其姓氏,是金陵人”,金陵客的答非所问,是张岱含蓄地用故都代前朝,表达了如影随形的家国之痛与故园之思,与开篇“崇祯五年十二月”这样庄重的史家笔法一起,在简洁含蓄的文字之中,精巧地安放着自己对故国往事的一片痴情。
张岱与同样行迹不定而又旷达不羁的金陵客,属客中见客、痴中遇痴,“吾道不孤”的欣然,无处寄身的哀痛,自然尽在不言之中矣!
课堂指引
张岱之痴,到底痴在何处呢?我们完全可以从“痴行”与“痴情”这两个方面追问。而不论是“痴行”还是“痴情”,作者的意绪都始终被挥之不去的家国之痛和故园之思笼罩着。故此,张岱看的是雪,也是在回望和纪念故国往事。明亡以后,张岱避居山中,专心著述,《陶庵梦忆》和《西湖寻梦》便写于此时。实际上,他的遗世独立,无非是因为自己与现实世界已经格格不入。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是《陶庵梦忆·祁止祥癖》中为人所熟知的一句名言。当我们读《陶庵梦忆》的另一名篇《湖心亭看雪》,试图走进张岱的精神世界时,是否可以把这里的“癖”和“疵”理解为“痴”的另外一种表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