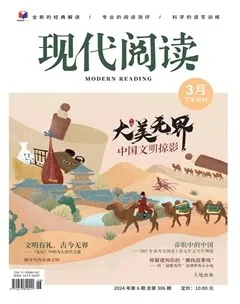孔子的理想世界
2024-04-29梁开喜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在《论语》中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它是《论语》中篇幅最长的对话,还因为它描绘了一幅集中而鲜活的学习场景,展示了一个完整而生动的教学过程。如果把它看作是现代教育的一堂课,那么,我们不妨用“问志—言志—评志”来概括其基本的课堂结构,勾画其轻松活泼的师生互动关系。
“言志”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而这里的“志”又可以分为两种:子路、冉有、公西华之“志”与曾皙之“志”。
解读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之“志”
孔子在教育弟子的过程中,子路总是第一个发言,并且常常是不假思索、冲口而出。“率尔”一词,恰如其分地凸显了子路的性格。在子路看来,他只要三年功夫,就能让一个兵连祸结、饥馑频仍、在大国的夹缝中艰难图存的国家走上正轨,也能让百姓敢于抵御外侮、懂得合乎礼仪的行事准则。孔子的反应是“哂之”,联系后文孔子对子路的评价“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哂”在这里应该带有否定的意味,当然,这里的否定是针对子路的态度而不是他的志向。冉有显然谨慎得多,他只敢说能在三年之内让一个小国的百姓丰衣足食,但要让他们懂得礼乐之道,就不是他能胜任的了。公西华则更谨慎,他期冀自己能够帮助国君做好祭祀与会盟之类的事。公西华是一个谦逊、有礼的人,身段自然也放得比较低。
尽管这三人的抱负或宏阔、或具体,口气或豪迈、或谦卑,但他们的志向都与治国平天下有关——即或是公西华用极其谦恭的态度所谈及的“宗庙之事”,实际上也是春秋时期的家国大事——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表现出了非凡的境界和雄伟的气魄。
但四人之中,孔子赞赏的人却是曾皙。这是为什么呢?在教学的过程中,这显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这里我们不妨先欣赏文中描写曾皙的两段文字。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在三人各言其志的时候,曾皙在弹瑟,但他显然并没有因此屏蔽孔子与其他三人的对话。这时孔子点名让他发表看法,他不是让瑟声戛然而止——“鼓瑟希”的意思是弹奏瑟的乐音渐渐稀疏,“铿尔”则是指“铿”的一声收束瑟音,“舍瑟而作”是将瑟稳稳放下,然后站起身来。由这一连串的动作我们不难看出,曾皙始终都是气定神闲、从容而优雅的,接下来他的回答也的确与前面三人大异其趣。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真是一幅和乐安详、岁月静好的画面:暮春时节,天气转暖,穿着新裁的衣服,与一群大人小孩到沂河里沐浴,洗去严冬的秽气,徜徉在习习春风里,唱着歌儿走回家去。
按一般的逻辑,曾皙的回答似乎已经完全跑题了,因为它无关乎志向,只关乎情境;无关乎为君之道,只关乎教化民风,但这正是孔子心中礼治社会的美好图景,也是最优雅、最体面、最高贵的生存姿态。于是,他情不自禁同时又直言不讳地说:“吾与点也!”
我们的教学常常止步于此,但这是不够的,因为并没有追问孔子的言外之意。如果没有在这种追问中去触摸并体会孔子礼乐治国的政治理想,就没有办法真正走进课文的内核。
探寻孔子之“志”的内核
《论语·公冶长》中,有一节内容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十分接近,我们可以在对比中一窥孔子的情感态度和政治理想。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这段文字同样涉及子路、冉有(即冉求)和公西华(即公西赤),孔子对这三人的了解,与这三人的自我评价是完全一致的。在肯定他们才华与风度的同时,孔子又诚恳地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到了仁”。众所周知,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清人程瑶田于《论学小记·进德篇》言:“夫仁,至重而至难者也。故曰仁以为己任,任之重也;死而后已,道之远也。如自以为及是,未死而先已,圣人之所不许也。……故有问人之仁于夫子者,则皆曰未知。盖曰吾未知其及焉否也。”意思是说,既然仁是需要毕生以求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在未死之时说达到了仁,因为那意味着还没有走到生命的终点,但对仁的探寻就宣告停止了。可见,对仁的追求是一件“永远在路上”的事情,不过,虽然仁不可知,但通往仁的路径是清楚的,“爱人”或者说“亲亲之爱”,便是通往仁的必由之路。由此,我们也就大致明白了,孔子对曾皙观点的赞同,实质上是其“仁学”终极追求的体现,是其礼治思想与大同和谐社会理想的体现,是其“内圣”而“外王”的人格锻造与所有才能和专长必须以礼制和仁德为前提和基础的主张的体现。
子路曾经问过孔子的志向,孔子直截了当地回答:“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这与曾皙在这里所描绘的充满了礼乐精神的融融泄泄的场景是完全一致的。在孔子看来,“政以体化,教以效化,民以风化”也是为政的一种方式,无怪乎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无怪乎当有人问他为何不去从政的时候,他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翻译过来就是,《尚书》说:“孝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把孝悌的道理推广到政治上去,这也是为政,为什么非要做官才算为政呢?
课 堂 指 引
毫无疑问,《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不仅仅是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动语录,还可以看作是一个鲜活的课例和一篇精彩的散文。曾皙鼓瑟,瑟音构成了教学的背景音乐,这一背景音乐一方面突出了人物的情致,另一方面也寄寓了美好的愿景。“唯求则非邦也与?” “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孔子的点评看似各说其是,实则隐藏着这样的深意:志向的大小其实无关宏旨,关键得看是否体现了礼乐治国的理念,是否将人生的意义安放在了追求百姓仁和、天下太平的过程之中。而在这方面,曾皙的回答比其他三人更为雅洁, 深得孔子的心。因此,孔子与弟子的问与答,无论是曾皙“异乎三子者之撰”也好,还是孔子因人而异的委婉表态也罢,跟是非对错没有关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中的这个大同世界,才是孔子心中的理想社会和盛世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