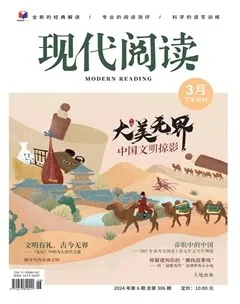盛唐:贵妃的红妆时代
2024-04-29李芽陈诗宇
瑰丽风华
审美与艺术
艺术是对客观世界的审美反映,它并非如展览品般束之高阁,而是浸透在日常吃穿住行的方方面面。独树一帜的中国式审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底蕴。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国式审美以海纳百川的平和与包容,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深远。
作为四大美人之一,杨贵妃与唐玄宗的浪漫传奇被反复传唱。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和百姓无不好奇贵妃的美貌和妆容。
贵妃时代真实的妆饰风尚如何?我们现在无法看到杨贵妃的“真实照片”,其具体的面貌难以还原,不过半个多世纪以来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尤其是数以百计的玄宗时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写实陶俑、壁画、绢画,已经让我们可以很科学地归纳出开元、天宝这几十年间,从长安京畿到西域、东北广大区域贵妇人的身材、妆发的审美倾向和变化。
这次我们就借杨玉环的一生,来看看盛唐开元、天宝时代几十年间,贵妇们从淡雅素净到红妆浓烈的妆饰变迁。
开元初:新君即位后的简朴收敛
开元(713—741)初期,刚当上皇帝的唐玄宗希望一改朝野追求奢靡华丽之旧弊,连下了几道诏敕,严厉禁止对奢靡的珠玉锦绣的追逐,亲自带头将皇家所藏金银熔铸为铤,将珠玉锦绣焚毁于殿前,令“宫掖之内后妃以下,皆服汗濯之衣,永除珠翠之饰”(《全唐文》),甚至下令妇女们要把之前的锦绣衣物染黑,不准织造华丽面料,各地官营织锦坊也停废。
在这种大风气的引导下,妇女妆饰也一改武周末期的华丽倾向,复杂的额黄花钿、斜红、假靥组合以及发髻上插戴的步摇簪钗、花钿至少在京城中被禁绝。杨玉环生于开元七年(719),幼年在蜀地度过,少女时的杨玉环所见女性妆饰,可能大体上还是简洁利落的模样。
入两京:精致“开元样”形成
开元十七年(729),十岁的杨玉环因父亲去世来到洛阳。
此时尚处于李隆基治下的第二个十年,长安、洛阳的流行风尚与妆饰,已经完全脱离了武周遗风和开元初年提倡的简朴感,往夸张和精致化发展。
首先是发型,当时最具符号性的改变,就是隆起的半圈鬓发越发蓬松,头顶小髻前移低垂,成为最流行的发型传遍全国。
妆面色调大体维持淡雅的风格,以白妆和浅淡的薄红胭脂为主。白妆即面施白粉,是素雅的淡妆,《中华古今注》说杨贵妃曾作“白妆黑眉”。从开元中期的壁画来看,可以看到面无朱色、描绘黛眉的贵妇形象。同时也有在脸颊施涂浅淡红晕的例子,这种浅淡红晕可能即“桃花妆”“飞霞妆”。唐宇文氏的《妆台记》中说:“美人妆面,既傅粉,复以胭脂调匀掌中,施之两颊,浓者为酒晕妆,浅者为桃花妆。薄薄施
朱,以粉罩之,为飞霞妆。”
与此同时,精致华丽的妆饰也逐渐再度流行,女性脸上的花饰增多,典型的斜红、额黄、假靥等全套妆面重现。
身在洛阳的杨玉环所见的贵妇们大约如此:隆起的鬓发、低垂的小髻、精致柔美的妆容、缀有花饰的衣裙以及她们日渐丰满的身材。
天宝初:步入浓烈的红妆时代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天宝(742—756)初年,登基已经二三十年,承平日久,天下安定,玄宗觉得功成治定,也早忘了当初躬亲节俭的信誓旦旦,逐渐奢侈无度,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与杨贵妃在宫中过着鲜花着锦的享乐生活。
当时的社会开始崇尚富丽奢靡,贵妇们的身材越发丰腴,审美越发浓烈夸张,逐步迈入“红妆时代”。此时宫廷贵妇的发髻更加宽松,脑后拖垂巨大的发包,收拢聚于顶束成前翘的小髻一二,形成了我们所说“天宝样”的标志性发型。贵妇们装饰花钿,衣着宽松,宽大的长裙束于胸上,下摆拖地,纹样花团锦簇。
妆饰上也有一些大胆的改变。最引人注目的是“红妆”,在脸颊大面积涂抹浓重的胭脂,范围甚至从眉下一直蔓延到耳蜗、嘴角,全脸只剩下额头、鼻梁和下巴露白,相当夸张。李白诗中有一句“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赪玉盘”即赤红圆玉盘,用其形容当时贵妇们涂抹了赤红胭脂的圆润脸庞,可以说是相当形象了。
不得不提的还有眉妆。开放浪漫、博采众长的盛世大唐,造型各异的眉形纷纷涌现,且各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时世妆,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眉妆造型最为丰富的时代。唐代眉妆的繁盛,与国力的强大和统治者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唯其国力强盛,广受尊重崇尚,才能展现出充分自信、自重、开放和包容各种外来文化的大家气度。
在唐朝,大量名贵化妆品的进口已成为可能,其中最为名贵的当属“螺子黛”,主要提取自栖息于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环带骨螺。古代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人、腓尼基人都把这种贝类染料当成名贵的染料。
(节选自湖南美术出版社《中国妆容之美》)
文明交流互鉴
纹样
中国丝绸纹样在魏晋南北朝以前主要是以几何纹(商周)、动物纹(春秋战国—秦汉)为其表现对象的。植物纹样虽然从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但始终处于附属和陪衬地位。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期间,西亚、罗马美术及佛教美术的传入,不仅给中国传统纹样加入了包括忍冬、莲花等植物纹样的新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丝绸纹样以此为契机,终于突破了传统的纹样樊篱,形成了以植物纹样为主体的纹样新格局。盛唐之后,在广泛吸收外来纹样营养基础上,涌现出众多纯熟的中国气派的崭新的植物纹样,如宝相花、唐草纹、写生折枝花、写生团花和散朵花等,其中尤以写生型花鸟纹最具代表性意义。它已经没有与外来纹样交杂的生硬痕迹,而是将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写实花卉,牡丹、海棠、秋菊……与众多飞禽,绶带、雁鹊、鹦鹉……自由组合,俨然是一幅花团锦簇、练雀翱翔的唐代自然生活图景的真实写照和大唐盛世生机勃勃的象征。
(节选自黑龙江美术出版社《中国丝绸纹样史》,作者:回顾,有改动)
壁画
唐代的敦煌石窟壁画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随着佛教思想与中国儒家、道家思想的互相濡染,佛教具有中国特色时,敦煌艺术形式也渐渐起了相应变化,反映在菩萨像上便是男女一体化、男相女身菩萨塑像的出现。敦煌艺术在处理菩萨像时,本来就有男相女身的根蒂,中国儒、道思想的濡染大大加强了这一趋向。儒教中庸伦理思想主张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中和常行,反映在艺术上则主张一种敦厚淳美的风格。道家崇尚自然,认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主张“知雄守雌”,讲自然无为,因而在艺术上常有一种融于自然、游弋无穷的空灵绝尘的自由气派……隋唐时期的菩萨像不论在哪个阶段,都极其微妙地反映了这几种思想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的文化内涵。
(节选自兰州大学出版社《敦煌壁画艺术论》,主编:李映洲,有改动)
瓷器
代尔夫特是荷兰的瓷都,类似中国的江西景德镇。荷兰在17世纪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最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中国进行贸易,把中国的大量瓷器运到欧洲,卖给欧洲各国,赚得盆满钵满。整个中国的瓷器贸易在17世纪的欧洲是由荷兰主导的。
中国瓷器给欧洲带来的冲击不仅是瓷器本身质地的精良,欧洲的瓷器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他们花了上百年的时间模仿……
更重要的是,欧洲人文学者还从中国瓷器中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瓷器上的图案所反映的内容与欧洲艺术不一样。欧洲艺术当时反映的主题主要还是宗教,而中国瓷器上的图案反映的几乎都是民生,如农夫耕作、老人垂钓、儿童嬉戏、多子多福,还有大自然的山水风光。用今天的话说,中国艺术的题材早就是非宗教的、接地气的、人间的。这一切给当时的欧洲带来了震撼,甚至可以这样说,是中国的世俗文化很大程度上把当时的欧洲从神学世界引向了人间世界。从神学世界到人间,这就是现代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要义。
(节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这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力量》,作者:张维为,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