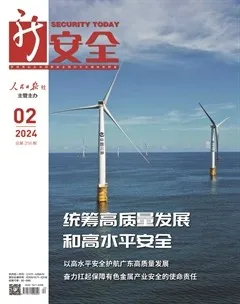熙宁变法提振北宋经济
2024-04-29柳青
柳青
当年仅20岁的少年赵顼成为北宋第六任皇帝的时候,他面临的是一个极具矛盾感和两面性的时局。
从表面看,这是一个花团锦簇的繁华盛世,是让后世不少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精神家园。都城汴梁,人口远超汉唐时代的长安、洛阳十倍以上,其行业之多、商业文化活动之发达,无不令后人称道。整座城市夜幕降临后便灯火辉煌,雕车盈路,如此繁华昌盛,可谓天上人间。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然而,汴梁的盛况并不具有普遍性,但凡走出都城,繁盛大宋的另外一面——积贫积弱的困境,便展露无遗。开国制度之弊形成的冗兵、冗官和冗费问题,仿佛一个沉重的镣铐,拖损着国家的实力,威胁着国家的安全。“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就是最真实的窘迫写照。冗官、冗兵造成了朝廷财政困难,但若为解决财政困难而扩大赋敛,又势必造成更大的财政困难。在这种怪圈下,无论赵顼或者其他北宋皇帝自己再怎么节省,朝廷再怎么俭约,终究也只能“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内忧重重,外敌猖獗,宋神宗在这种困境中,决意改弦更张,力图“富国强兵”。为此,他起用了朝野上下一致看好的名人——王安石。
提起王安石,许多人都会不假思索地想到“唐宋八大家”之一,想到他极高的文学造诣。其实,王安石从政数年任知鄞县、舒州通判、知常州、提点江南东路刑狱等职,政绩斐然,在地方官任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上调中央,次年出任负责财政系统的三司度支判官,针对“三冗”“二积”的局面,他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观点,这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关键理念,这一改革史称“熙宁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变法大刀阔斧推进。这是一次对北宋整体架构的重塑,旨在缓解当下危机,进而改变大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最终实现“富国、强兵、安民”的总体安全目标。因此,变法涉及范围从推动经济运行到保障国家安全无所不包,囊括了农业政策(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商业政策(均输法、市易法、各种政府专利制度),以及军备政策(保甲法、保马法)等。新法创举之多、领域之广,前所未有。
概括而言,新法的逻辑思路是利用政府干预或货币调控等措施,从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入手,达成“富国”目的,在“富国”基础上,进而“强兵”。至此,中央财政问题得到了极大缓解。时至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为北伐做准备,将新政中各项收入盈余“悉归朝廷”,一次性就装满32库。元丰五年(1082年)他又“取苗役羡财为元丰库”,再建20库。纵观神宗时期,政府岁入是6000多万缗钱,约为仁宗时期的1.6倍。北宋最后50多年的繁荣,或可谓神宗期间大变革的遗产。史学家漆侠在《王安石变法》中说:“如果说,宋代的社会生产,在整个封建时代居于两个马鞍形的最高峰,你就应当说,王安石变法时期的社会生产,则居于这个最高峰的最高点。”
变法期间,财政得到缓解的北宋进行了必要的军事改进,甚至有以资本比拼国力的形式取得对西夏战争的胜利。熙宁六年(1073),王韶率兵北拓二千余里,开边河湟,将宕(今甘肃宕昌县东南)、叠(今甘肃迭部县境内)、洮(今甘肃临潭县西南)、岷(今甘肃岷县)、河(今甘肃临夏)、熙(今甘肃临洮)六州之地全部收复。在安史之乱300多年后,再度恢复由中原王朝控制这一地区的局面,这也是北宋结束十国割据后取得的最大军事胜利。
“国库渐丰、西北大捷”无不昭示着熙宁变法的卓著成效,也为以经济安全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论据。变法中的举措和思想不仅对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其作为我国古代治国方略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当代中国仍具有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鉴古知今,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把国家经济安全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努力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责任编辑:董常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