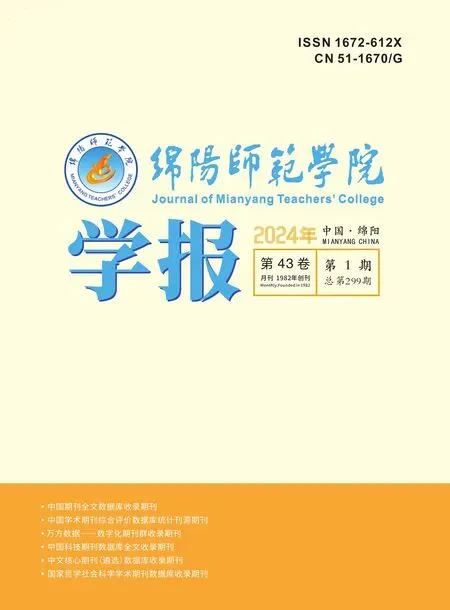佛教逻辑的研究径路论略
2024-04-14董英东魏雪园
董英东,魏雪园
(湘潭大学碧泉书院,湖南湘潭 411105)
佛教哲学家研究了论证和论证的技巧、方法,以及作为理性论证和推理基础的逻辑原则,这些研究始于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家。传统的和当代的佛教学者已经发展并研究了许多相互竞争的逻辑理论及其与推理和理性的关系。然而,在当代逻辑文献和逻辑哲学中,这种丰富的佛教逻辑材料却很少被讨论,甚至鲜为人知。本文以当代逻辑学家和逻辑哲学家比较熟悉的方式介绍其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并为全方位研究佛教思想中的一些逻辑思想的研究径路和方法提供一些建议。
一、佛教逻辑中的推理径路
印度佛教中的传统逻辑已经发展成为认识论的一部分,佛教逻辑学家①通常认为知识是一种有意识的意识状态,我们能确信知道的事物(我们知道什么)取决于我们是如何意识到它们的事物(我们是怎么知道的)。佛教逻辑学家认为知觉和推理是达到一种可以称为确信的意识状态的唯一途径。感知和个体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二者可通过因果关系进行描述且属于普遍性的概念。例如,当我们想到马时,我们就会意识到存在概念对象“马”,这是由于将某个对象想象成马的结果。知觉状态是涉及事物本身的一种意识状态,该意识状态是由和特定事物的接触而有因果地产生的。而推理往往会涉及到概念。例如,当我们意识到山上有烟时,因为我们把飘荡的东西想象成了烟,并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出那座山上有火。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意识到山上有火,并且那里确实有火时,从有烟推出有火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推理,而关于火的存在的知识被认为是由推理产生的。
为了在推理的论证过程中能够产生知识(或通常描述的“有效的”知识),“因”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遍是宗法性:因所描述的那个属性,必须是宗法,就是必须是宗的法,也就是宗的主词所具有的属性。在我们关于山上有火和烟的例子中,山是主词,烟必须存在于山上。第二,同品定有性:因三相之一,用以表示因与宗(命题)后陈(述词)之关系。故有因必有其后陈之宗依随之,例如,宗:人必有死,因:动物故,“死”中必有“动物”即可,而会死之物不一定仅限于动物,如植物也会死。以因之义成立宗之义故,因之义不必与宗之义全部相同,即与宗义同类之宗同品,有部分关系即可。例如,正在燃烧木材的炉子所在的厨房里必须有烟。第三,异品遍无性:宗的异品须普遍没有因的性质。同品必须具备宗上所说的那个属性,也就是宗法,异品就是说某物不具有宗法所要表述的属性[1]xliii-xlviii。例如,此山有火就是同品,就是同样有火的事物,异品就是没有火的某物,例如湖泊。那么异品遍无性,指的是在湖泊这一类事物里不存在火,也就不具备烟这样的属性。
对于佛教逻辑学家来说,知识意味着真理,但他们并不把碰巧使之正确的意识状态视为知识,而将我们在获取知识时所经历的认知过程视为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理性的三个特征是推理认知过程“有效性”的标志。但是一些佛教逻辑学家并没有将一种被视为知识的意识状态,与产生这种意识的认知过程区分开来。因此,通过“知识”,佛教逻辑学家想到的是认知事件,而不是认知状态。他们在谈论推理时重点关注的是,通过推理知道一种包含真理的特定类型的认知事件。
少数学者在认识论的背景下认识到这一点在当代不同立场的哲学背景下的重要性。然而,很少有佛教逻辑研究者强调上述观点,并将其应用于逻辑语境中[2]。当代逻辑学家/哲学家利用佛教逻辑材料进行研究同样也需要借助一些方法。因此,需要提出方法论问题,然后才能更好地考察当代逻辑学家/哲学家对佛教逻辑的理解。
二、佛教逻辑中的方法论径路
可以从学术的角度对佛教相关材料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探索如何利用佛教逻辑材料的一些方法。
首先,需要对佛教材料进行整理编写。由于佛教材料也是由语言编写的,特别是采用各种不同的典范语言编写的,同时由于掌握一种语言绝非易事,更不用说理解用这些语言编写的材料了。有时,被引用的文献也会出现缺失。另外,由于可接触到的文献是原件的副本,也可能会包含一些错误,所以都需要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
其次,一旦有了原始材料,就可以对教材材料进行分析。在这个层次上接触佛教材料时就涉及到解释,通过分析来突出材料中包含的一些思想。鉴于只对哲学类的材料感兴趣,因此通常会根据过去和现在哲学家经常使用的概念和术语进行分析。所以,如何在这个层次上理解佛教材料往往取决于如何理解哲学概念和术语。
参与的第一个层次,即整理编写材料的研究是佛教学者(佛学家)所从事的工作。他们接受过相关语言的培训,能够理解原始语言的主要材料,但他们几乎总是通过提供对材料的分析来解释如何理解译文。近年来,有的哲学家开始在第二个层次上接触佛教材料。由于他们对哲学家所使用的概念和术语有更为牢固的掌握,这就促使他们能够对佛教材料进行更加复杂的分析。
虽然哲学家的参与丰富了分析佛教材料的资源,但尚不清楚的是,哲学家和佛教学家之间是否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对话和交流。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虽然哲学可能没有(或可能)进步,但哲学的讨论确实在继续。佛教学家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也不知道哲学最新讨论的内容。第二,不熟悉佛教材料的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掌握佛教材料。问题不在于一般哲学家是否愿意,而是佛教材料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给哲学家。哲学概念被应用于对佛教材料的分析,希望哲学家能够掌握这些内容。然而,这本质上是一个应用反射。佛教的思想和观点可以通过哲学家使用的某一系列概念来理解[3]。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类似于(“西方”)哲学文献中的观点和术语,同样可以在佛教材料中找到。但这本身并不能说明哲学家们能用这些思想做些什么。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通过这个映射应用可以看出,佛教思想对于(当代)哲学家来说可能是多余的,无法展示佛教思想对哲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为了在哲学家和佛教学家之间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和交流,佛教思想需要以哲学家能够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
与佛教材料接触的第三个层次是在一定程度上抽象的佛教思想和观点,并将其与当代文献重新联系起来。严格地说,在这个层次上,不是在分析文本内容,也不再是挖掘思想史的领域,其本质上是没有考虑文本内容。相反,需要考虑的是在我们自己的环境中如何处理这些材料。要将佛教材料作为哲学史之外的哲学资源,这就是所需要从事的工作。如果希望(当代)哲学家和佛教学家之间有任何双向对话和交流,那么佛教材料必须以一种有助于当前哲学论证的方式呈现。
三、哲学视角下的佛教逻辑径路
如果需要进行哲学和佛教逻辑的双向对话和交流,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佛教逻辑的角度挑战一些被广泛接受的关于逻辑本质的哲学观点吗?在理解逻辑本质的背景下,这些挑战可能是激进的,但也可能是富有成效的。
佛教逻辑与佛教是有区别的,也即逻辑学和宗教学所研究的内容是不同的。佛教偏重于研究伦理道德的教化,佛教逻辑则偏重于研究论辩活动。佛教研究善恶、人性、宇宙本源,人生伦理问题是佛教理论研究的基石,以“大悲为首”“慈悲喜舍”作为佛教道德的起点,以“自利利他”“自觉觉人”作为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佛教逻辑,主要指因明,是在论争中竭力总结和研究论辩的理论和技巧,同时遵守逻辑规则。佛教以神秘直觉为基础,而佛教逻辑则以理性、有效性为前提。佛教以追求解脱为目的,佛教逻辑则以悟他为目标。佛教逻辑研究的推理问题与哲学诠释所研究的语言问题密切相关,这涉及“对真如的认识与言说”的佛教理论(二谛论)对认识和言说的辩证统一关系的研究。真如是佛教对世界本源的描述,一切对世界真实面貌的言说都是描述的,而一般认识中的真实就是所谓的世俗谛,认知和语言都以真、俗二谛开展,认知以真如为目的,语言以教化为宗旨,这就涉及佛教逻辑与认识论和语言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四、佛教逻辑中的心理主义径路
心理主义认为逻辑描述依赖于推理过程。在当代文献中,这种逻辑哲学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否定的思想。有人认为,如果逻辑以这种方式进行描述,就很难理解其规范意义。也就是说,如果逻辑与推理有关,并将其理解为一个认知过程,那么它只能告诉我们实际上执行了什么样的推理,却不能告诉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推理。由于逻辑规定了我们的推理实践必须满足的规范,它不能描述推理过程。因此,有人认为,逻辑必须独立于这些过程[4]194-223。
这种反心理主义的立场现在几乎很少受到质疑。然而,对于佛教逻辑学家来说,他们对逻辑研究的主要焦点是构成知识产生事件的认知过程。关于我们应该接受什么原则的论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存在的争论在于一旦我们接受了某些前提,我们是否应该接受某个确定的结论。有些人否认存在任何此类结论,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是应该做的。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并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声称自己是理性的,那么在我们的推理实践中就必须存在规范性约束[5]。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的过程中,有时矛盾也必须被接受为“有效的”,他不是通过论证真理的结构(比如弗雷格),而是通过研究我们执行和接受的推理来论证这一观点。因此,有人对心理主义抱着同情的态度。
佛教逻辑中的量学理论知识体系中的摄类学包括辩论学、心识学、因明学三个部分,其中心识学属于心理学的范畴。量学以识的性体将识分为七种,即现量、比量、已决智、现而不定识、犹豫识、伺察识和颠倒识,是属于佛教认识论的范畴。佛教的修行,其实就是修心,这就会涉及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理论。
五、佛教逻辑中的先验径路
一旦质疑反心理主义,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会突显出来,即逻辑的先验性。在许多方面,逻辑被认为是先验的。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我们的经验不会使逻辑原则失效。这种先验性的概念在量子力学中受到了挑战,其中某些粒子的活动似乎不符合经典逻辑的原则。然而,这些挑战者中的许多人认为逻辑最终还是先验的,而且很难看到有人会争辩说,观察到某个人或甚至许多人的推理是无效的,就需要拒绝或者修正逻辑原则。
第二,逻辑有时被认为是先验的,因为逻辑原则不能从涉及推理的任何特定认知中推导出来。这就是康德所主张的观点。他假设逻辑规则是没有这些规则,就不可能进行理解。对他来说,这意味着逻辑规则是理解的可能性的条件:没有逻辑规则,甚至连一般的理解都不可能。康德由此推出逻辑规则是理解的必然规则。特别是,它们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认知。也就是说,它们不依赖于经验的偶然性。因此,对于康德来说,逻辑原则是标准,而不是理解的工具[6]。
第三,逻辑有时被认为是先验的,在这种意义上,无论是经验的还是其他的,理论的发展和检验都必须符合逻辑原则。瑞斯尼克认为,逻辑原则作为生成和控制经验数据的机制,但它们与任何经验反驳和证实无关[7]。弗雷格以类似的方式认为逻辑是先验的。对他来说,逻辑原则是判断一个人推理有效性的标准。然而,要使逻辑原则成为这样一种标准,它们必须首先得到认可,然后才能对推理进行评价。因此,逻辑原则必须是先验的,并为他们设定推理标准。
佛教逻辑学家可以理解为拒绝所有这三种先验的形式。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他们没有将一种被视为知识的意识状态与产生这种状态的认知过程区分开来。当一个人被认为拥有知识时,他们因此就是可辩护的,这源于对知识的定义,知识就是可辩护的(或合理的)真信念。辩护不是一个额外附加的成分,而是将意识状态视为知识。因此,在将其应用于对导致其发生的推理过程的评价之前,没有任何东西是提前预备好的。佛教逻辑学家可以理解为拒绝接受第三种先验的形式。但这也意味着,如果不分析特定的知识事件,就无法表达任何事物。所以他们也拒绝接受第二种先验的形式。最后,如果推理过程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评价推理过程,那么“有效性”就是嵌入在人们的推理认知中的东西。如果是这样,逻辑原则的拒绝或修正只能通过观察推理认知事件的过程来实现。因此,佛教逻辑学家也可理解为拒绝第一种先验的形式。由此,他们可以被视为拒绝所有应用于逻辑的三种先验的形式。
一旦反心理主义和逻辑的先验性受到挑战,其他一些问题就会变得突出起来,例如规范的外延主义和非系统性。
六、规范的外延主义径路
规范性的外延主义:逻辑通常被认为是规范性的,因为它为思维或推理提供了规范。哈曼对这一普遍观点提出了挑战。他认为,逻辑作为一门蕴涵科学,是一门独立于推理的学科[8]。为了应对哈曼的挑战,麦克法兰提出了桥原则,将逻辑有效性的事实与推理规范联系起来,从而证明逻辑是规范的②。他认为,如果可以制定桥原则,逻辑就可以被证明是规范性的。
桥原则具有以下形式:
如果P1,…,Pn⊨Q,那么Φ(P1,…,Pn,Q),
斯坦伯格认为,“前件陈述了一个关于逻辑后承的‘事实’,后承采取规范性所主张的形式,体现了主体对相关命题的态度”[9]。因此,桥原则将“蕴涵的逻辑概念与推理和信念的认识论概念”联系起来了[9]。
斯坦伯格表明,无法制定任何合理的桥原则,尽管他不会复述无法制定桥原则的原因[9]。然而,佛教逻辑学家,至少是早期的逻辑学家,如陈那和法称,不会通过将逻辑事实与推理规范联系起来,并用以解释作为论证和推理基础的逻辑原则的规范地位。桥原则的形式表明,为了使蕴涵的解释具备规范性,它必须内化为一个人的认知态度,这种认知态度在推理实践中起着规范性的作用。因此,桥原则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上的,即接受蕴涵的解释是为了达到它为我们的推理实践设定的标准。继威瑟森之后,将推理中的这种内涵性称为规范的内涵性[10]。规范的内涵主义在逻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文献中被普遍接受或是假定的原则。
相比之下,一些佛教逻辑学家,特别是法称,认为是外部世界为我们的推理设定了标准。因此,他们是规范的外延主义者。然而,对他们来说,外部世界不是我们认知生活中可以内涵化的东西。佛教逻辑学家对我们的内心世界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认为概念化涉及被认为不具备现实的普遍性,因此将我们的内心世界视为使用概念化的一种建构。他们认为,必须是外部世界,我们必须对外部世界作出反应,并从理论上解释我们应该如何推理。我们的内心世界远不能为我们的推理实践或任何行为设定标准;事实上,这是需要纠正的。因此,佛教逻辑学家可以理解为拒绝规范的内涵主义而提倡规范的外延主义。
七、非系统性的径路
佛教逻辑中不怎么涉及数学领域。佛教传统中的逻辑并没有和数学一起发展。数学究竟对逻辑起了什么作用,这也许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它可以使逻辑更加系统化。由于缺乏数学,研究佛教逻辑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思考系统逻辑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去研究的问题。
坎德拉克的紧缩计划认为,所有追求真理的都是普通人的信仰和意见。从广义上讲,所有寻求有效性的东西都是人们的信仰和观点。然后,他们可能会认为逻辑形式及其实例之间可能是没有关联的。人们对逻辑形式的有效性(或无效性)的判断可能与其实例的有效性(或无效性)不同。如果有人想证明某些逻辑形式是无效的,他们不能简单地通过提供一个反例来证明。他们需要证明,普通人并不认为这种逻辑形式有效。这样,就有可能发展出一种不系统地对待逻辑形式的逻辑观[11]127-138。
八、结论
曾昭式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 年2 月11 日第4 版的《佛教逻辑学中的因明与量论》中,讨论了佛教逻辑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在中国与日本开展了对汉传因明的研究,从唐朝开始传到日本之后,主要从事的是对因明文献的整理工作,而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到近现代的中国,则主要从事的是对因明的逻辑研究。日本对因明的研究过程经历的从文本的注释到逻辑研究的转变是受到了西方逻辑学的启发和影响,从而形成了西方逻辑式的因明。这种佛教逻辑,与汉传因明文本内容是不太符合的。若希望构建佛教逻辑学科,首先,应给出包含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逻辑概念的界定。其次,要将逻辑理论与应用区分开来。佛教逻辑所涉及的范围是由佛教逻辑的研究对象制约的,对佛教逻辑的研究可以从论证的角度切入,对因明的研究应当关注论证者、论证目的、论证结构规则三方面的内容[12]。在藏传因明的研究中,关注较多的也是对论辩的形式及论辩的语言的研究。
如果我们不是从内部的角度(佛教传统的内部),而是从更广泛的、有点全局性的角度来研究佛教逻辑,我们能发现什么呢?我们可以找到用来质疑逻辑本质观点的材料,根据这些观点,逻辑是反心理的、先验的、内在规范的和/或系统的。仔细研究佛教逻辑学家提出的反对这些观点的理由,有助于批判性地阐明关于逻辑本质的正统假设。鉴于在当代文献中,逻辑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反心理主义的、先验的、内在规范性的和系统性的,本研究的结论是有意义的。如果佛教逻辑学家的观点能被证明是合理的,它将严重挑战当代正统的观点;如果这些观点缺乏连贯性,它将为思考为什么必须按照当代正统理解逻辑提供材料和证据。因此,多方面地研究佛教逻辑是重要的、有价值的行为。同时,对于和古希腊逻辑、印度逻辑并称为三大逻辑起源的中国逻辑,也可以借用这些思想开展研究,从而得出更多的、有价值的成果来。
注释:
① 本文中的“佛教逻辑学家”主要指陈那、法称等遵循逻辑规则的逻辑学家。
② 参见John MacFarlane.In What Sense (if any) is Logic Normative for Thought?Draft of April 21,2004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Central Division APA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