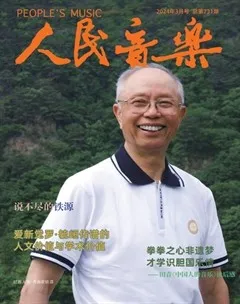音乐中的权力叙事
2024-04-13黄浩伦
音乐与权力之间有何关联? 当抛开传统的宏大叙事的文化讨论, 试图在繁复的音乐文化中探讨“权力”这一议题时,我们便不由得思考:作为一种人类文化复杂的存在形式,音乐是否必然包含着某种意识形态,为权力所“规制”? 在广泛的权力范畴的统摄背后,音乐又是否具有颠覆、抗争和制定新的社会秩序的“反叛”的可能?
面对这一议题, 法国政治思想家雅克·阿达利(Jacques(Attali,1943—)在其著作《噪音:音乐中的政治经济学》(Nois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usic)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解答。透过对各个历史阶段音乐的社会历史文化文本的解构式、具体化考察,阿达利将音乐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权力关系网络, 试图由此揭示音乐与权力的内在关联,并进而预测未来社会中的音乐实践。
在今天看来, 将文化研究置于权力叙事之中似乎已然不是什么新奇的尝试。早在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3Foucault,1926—1984)那里,便试图从权力与知识间的辩证关系切入, 由此揭示人的主体性的形塑过程实际为权力所规训的这一真相。①实际上,在20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伴随着根植于理性的传统理论话语的解体,作为西方学术界的一股重要思潮,一批学者都曾试图在对文化范畴的重审中引入“权力”这一意识形态话语,并进一步考察其存在的普遍性。
从这样的学术语境中来看,阿达利的《噪音》便具有其独特的理论意义: 在核心观点与方法论上,该著不仅反映了昔时学术潮流下的新兴研究视角,同时还是少有的一部以权力、意识形态属性对音乐进行考察的著作。 此外,在雅克·阿达利———这位政治经济学家、前法国政要的眼中,音乐不单是为权力所规制的政治符码,它同时还具有作为预示未来社会形态的“先声”的可能性。
一、阿达利的音乐权力观
在阿达利看来,作为一种声音符码,音乐在本质上从属于权力,聆听音乐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经济行为。正如他所言:“所有音乐与任何声音的编制都是创造或强化一个团体、一个集体的工具,将一个权力中心与其附属物联结起来。更广泛地说,它是权力——不论何种形式———的附属物。 ”②作为叙述权力合法性的必要力量,音乐是权力对“噪音”接纳、调谐并加以规制的新形式,而“噪音”则作为与“音乐”同为一种声音形式,但反叛、挞伐权力的异质性因素。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以权力为中介的,“噪音”與“音乐”间既同源却又分异的辩证关系,阿达利认为,在历史进程中,音乐实际上就是不断为社会权力所驯化的意识形态工具。
这一观点显然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具有相近之处,但更具野心的是,面对集中体现着的社会权力同音乐之间的复杂勾连, 阿达利的解答将整部音乐史纯然视作为一部为权力所规制, 或是反叛于权力的政治经济史———“音乐的每个符号都根植于它所属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科技中, 同时也制造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科技”③。这一略显激进的论调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那句老生常谈,“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④。倘若我们将之与阿达利的观点相观照,显然,阿达利透过音乐洞察社会权力变迁的尝试更为大胆———音乐被彻底抽象为顺从或反叛于权力的附庸。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观点,阿达利采用历史性与建构性相结合的模式,通过将各类历史上与音乐相关的文本纳入其政治性阅读,以便把音乐的形构和演变进程,纳入权力网络的实际运作活动中。在《噪音》中,音乐的历史进程被划分为三个断裂亦具共时性⑤的阶段,作者分别将其称为“牺牲”(Sacrificing)、“再现”(Representing)和“重复”(Repeating)的关系网络。
阿达利认为,在所谓“牺牲”网络,即资本主义制度普遍建立以前的早期社会中,音乐承担着导引暴力至社会和谐秩序这一象征意义的符码功能,“它象征性地显示出导正暴力和想象的重要性,将杀戮仪式化以替代一般暴力的重要性”⑥,音乐的功能有如祭牲仪式屠宰羔羊一般,其和谐因素来自对社会暴力的疏导。这种象征以和谐导引暴力的仪式化行为,其实际为权力所专擅独享:在古代中国这样的君主专制政体国家,为帝王所钦定音乐编制成为炫耀权力的表征;同样,在帝王以资助民众娱乐来确保其孚望的罗马帝国也不例外。
新的关系网络伴随着音乐的商品化出现。过去音乐的生产模式、表现形式和美学理念,均伴随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反叛和其相应政治经济规则的介入而变革———阿达利称之为“再现”网络。 它意指音乐的生产模式、表现形式隐喻着新的社会秩序,其目的在于使人们相信商业权力、物物交换的秩序及合法性,使人们深信理性及其组织的必要性。在此,无论是对法国大革命期间音乐“中央化计划”⑦的回顾,还是对以音乐会文化为主导的音乐生产活动的经济学分析,阿达利都意在说明,音乐已成为了代表新的社会阶层的权力中心所争夺的意识形态宣教的重要高地。在资本集中化的发达工业社会,伴随录音技术的推广与普及,音乐活动则为“重复”网络所替代。
在广播、电视等媒介的介入,以爵士、摇滚乐为主流的大众流行音乐文化的传播以及畅销排行榜的影响下,音乐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种行动的自由。相反,阿达利试图揭示“重复”社会中权力对音乐差异的消除与拘于“同一性”⑧的束缚———“权力以强力、震耳欲聋之势存在时,可以是平静的,因为人们不再交谈。他们不谈论自己,也不谈论权力。他们听到的是集体导引他们想象的商品的噪音,而他们社交的梦想与超越的需要便存在于这些商品的噪音之中”⑨,阿达利这一具有深刻政治意向性的批判,实际指涉于一个为“同一性”所主导的社会现实。伴随大量毫无差别的音乐消费品,权力以更为隐秘的形式存在,音乐在此以一种具有控制性的意识形态的身份成为资本主义的统治工具。
透过上述对音乐史的分析,阿达利提出了一个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即在一般的审美价值之外,音乐在社会中独特的政治意义与其意识形态内涵。在阿达利眼中,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符码”,音乐不仅仅是生理或心理意义层面的声音,它在表征、记录着特定社会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同时,也与社会权力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勾连,并时刻为权力所规制。
二、对音乐权力网络的未来预测
但是,在这样的一种音乐权力观之下,面对与社会权力的复杂勾连,音乐是否始终无法摆脱为权力所规制的政治命运? 对此,阿达利并未简单地拘于将音乐阐释为某一特定时代权力中心的“回声”。在他看来,音乐不仅受权力规制,作为反叛、挞伐权力的“噪音”, 它同时亦能够指向新的权力关系网络,预示社会的重大变革。在《噪音》中,为阿达利所定义的“作曲”(Composition)网络便宣告了一种更为自由、开放、消解权力中心的新的社会范式。“作曲”网络便孕育于既有的“噪音”———作为反叛、挞伐权力的异质性因素之中,它以一种革新的音乐形式预示着未来社会权力关系网络的变革。
对于真正具备革新意义的“噪音”而言,阿达利认为,传统音乐学学科对“伪新”(Pseudo-neuf)的音乐实践不加选择地定位为进步,但实际上,并非一切带有挑逗与亵渎特质的“噪音”都对现有的权力关系网络造成了真正的破坏。不同于阿多诺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否定视为音乐进步的准绳⑩, 在阿达利看来, 诸如奥涅格(Arthur4Honegger,1892—1955)在其管弦乐曲《太平洋231》(Pacific 231)中对火车行进的模拟, 与凯奇(John4Milton4Cage,1912—1992)在《4 分33 秒》中对传统符码和网络的批评,这些具有革新意味的创作否定了当下的权力规制,却未能提出新的社会组织模式的可能。
与之相比,阿达利在自由爵士(Free4jazz)輥輯訛中看到了建构新秩序的可能———作为一种区别于爵士乐传统,独有一套松散、自由的集体即兴演奏方式的音乐实践。在阿达利看来,类似于自由爵士的音乐实践预示着未来社会中差异的产生———音乐不再作为导引暴力,或是为资本权力所掌控的生产与消费的融合物。与此同时,伴随着音像录制科技的进步,作为消费者的私人化、自由选择的音乐聆听具有了更多的可能,而作为生产者通过自我录制制作音乐产品的自由,则使个体如作曲一般,在生产过程中便能获得乐趣。
这种“作曲”网络预测的指涉是明显的。倘若说音乐的自由象征着主体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的境遇便是旧有社会组织模式的转变。阿达利的实际意图在于,透过音乐的隐喻,我们得以预见新的社会组织模式的可能。如他本人所言,新的关系网络“预示了一个结构性的变迁,更深远地说是一种全新的劳动意义、新的人际关系、新的人与商品关系的出现”。可以说,阿达利预测的实质是为我们指向一个强调个体自由,消解阶级对立与绝对权力中心的自由的未来社会。
对于这种观点,值得肯定的是,阿达利并未拘于对音乐进行简单的上层建筑式的读解。不同于传统马克思式的反映论美学,《噪音》的原创意义在于,它试图说明在对音乐与其具体社会现实联结关系的认识之外,通过对“噪音”这一异质性因素的考察,存在一种依托上层建筑预见新的社会形态的可能性。阿达利并不满足于将音乐单视为一种反映历史权力中心变化的政治性符码,在此,他大胆地将音乐解释为一种超越社会政治与经济基础的预言般的“先声”。
此外,“作曲”网络的预测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积极的可能性。回望过去的一众社会批判理论,对现状采取拒斥与否定态度的观点似乎往往以这一热情的消退和堕入悲观为结局。阿多诺的困境在于,不断否定自身的辩证思维警惕着自我落入同一性的圈套,同时却也揭示了存在一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的真相。同样,马尔库塞则直言社会解放的前景是黯淡的,“没有什么能够表明, 这将是一个好的结局。既定社会的经济和技术能力之大,足以容下对失败者的调解与迁就,而其武装力量也得到了充分的训练和装备, 足以对付各种紧急情况”。在他看来,社会总体性的控制使人不断丧失批判与否定的意愿,作为社会变革的力量正不断地趋于消解。与之相比,阿达利则对未来表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积极姿态。在“作曲”网络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理想的音乐形式与社会模式———单一、绝对的权力中心将趋于消解,这种无权力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使“规制噪音并创造秩序”的权力被分散至个体之中。
然而,要质疑这一积极、肯定的解答尤有余地。阿达利所指向的理想社会无疑具有一种乌托邦的性质。从理论上看,我们暂不议他在阐释与预测上的大胆,就对“作曲”网络的论述而言,阿达利偏重对未来音乐实践的描摹,但对其相应的政治经济基础却语焉不详。作为《噪音》全书的论述核心,亦即原先曾作为论证社会变革必然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在“作曲”网络预测中却俨然成为一副含混不清的说辞。
从阿达利本人的立场出发,这种将音乐变迁视为社会进步寓言的举措或许便能够得以解释。不应忽视的是作者本人的社会角色,阿达利是一位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但同时也是一位阅历丰厚且老练的政客。在《噪音》成书的多年后,当我们置身于时下的社会变局中时,阿達利所允诺的“作曲”网络显然已经褪色,但这并不妨碍他本人对其预测的辩驳。在笔者对阿达利本人的信访中,个人在当今社会中音乐活动或是其他行动上的自由,被他作为社会变革的佐证。在2019 年于哈佛大学的讲演中,他更是毫无疑义地直言“作曲”网络的来临輥輴訛。依他所言,如今现实中已然有具体的表现:音乐以近似游牧主义(Nomadism)輥輵訛的形式存在于各类生活场景;人们为音乐付费的减少反映着私有与传统知识产权观念的松动; 与不同政治环境的中国相比,非洲音乐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更为普遍的关注……在他看来,“作曲”网络的来临,实际上印证了围绕所谓的市场、民主概念为核心的理性及其政治组织形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
显然,这番解释有其鲜明的政治意味。在批判与进步的话语背后,阿达利并不期待社会有其实质性变革。在今天看来,这一系列对音乐的过分读解似乎并无异于他本人所批判的先锋派的精英团体,这种预测同样能够被视作为现有社会组织模式提供合法庇护的绝佳辩词。考虑到阿达利的政治身份,“作曲”网络的预测或许更应当被读解为一种带有欺骗性的意识形态。就此而言,我们或许能够在哲学家齐泽克(Slavoj0譕i觩ek,1949—)的一段论述中窥见阿达利写作此书的动机:“它(意识形态)自称能够获得真理, 即它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谎言,而是一个被体验为真理的谎言,一个假设被严肃对待的谎言。”以这样的观点重审《噪音》,与其说这种对音乐的危险读解与阐释,是对权力话语的揭示与理想未来的预测,毋宁说是一种怀有虚假批判姿态与进步允诺的精明的政治游戏。
结语
近半个世纪以来,音乐学研究早已不再拘束于作品、传记分析这一类封闭的研究领域之中。在“语境” 中重新审视音乐与世界的关联, 在纷繁复杂的关联域中重新发掘音乐的意义,这种学科交叉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一股无可逆转的学术潮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面对如下问题:应当从怎样的视角切入,以定位并考察音乐? 又应当如何调节语境与音乐的关系,从而不影响音乐艺术自身的特殊性?
就此而言,《噪音:音乐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意义在于,阿达利尝试将音乐与政治权力并置讨论,进而揭示其历史的结构与演进,这种尝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鲜的理论旨趣。作为一位政治经济学家,阿达利尤为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其政治规训、教化功能。从前文所述内容可见,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将政治权力置于历史叙事的中心地位,将音乐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推到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极端。在阿达利看来,音乐是为权力所规制的“符码”,一部音乐史不过是一部政治权力对音乐的驯化史。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部演绎着权力变化更迭的“音乐政治史”中,阿达利并未忽视音乐自身的特殊性。本书的一大亮点在于,作者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揭示、还原复杂的历史原貌,他还辩证地关注到了音乐反叛、挞伐政治权力的一面。“噪音”,作为一种有悖于当下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异质性因素,阿达利试图将其解读为一种能够预测未来音乐活动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先声”。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噪音”的分析与把握,存在着一种打破“艺术为政治所统治”的观念的可能。基于这样一种理论模型,阿达利便通过音乐向我们预言了一个消解了政治权力中心的,自由且进步的理想社会。
阿达利对音乐的这一阐释与引申固然是新颖的,但更值得为读者所反思的是,作者缘何对音乐作出如此富于“进步”意味的阐释? 实际上,阿达利看似在进行属于学理层面的探讨,其写作前提却带有强烈的意識形态印记。此书的法文原著出版于1977 年,正值美苏“冷战”对峙的胶着时期。透过阿达利预言音乐进步,乃至于社会解放这一番话语的缝隙之间,我们能够鲜明地体认到,在这种看似视角丰富,强调批判观念的理论背后,其自身也依然可能挟带有思想成见与政治目的。就此而言,《噪音:音乐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可贵之处便在于,当面对当下不断拓宽新维度、求新求变的理论发展,置身于强调个性、差异与多元化的时代潮流中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反思的可能。
黄浩伦 中央音乐学院2021 级本科生
(特约编辑 盛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