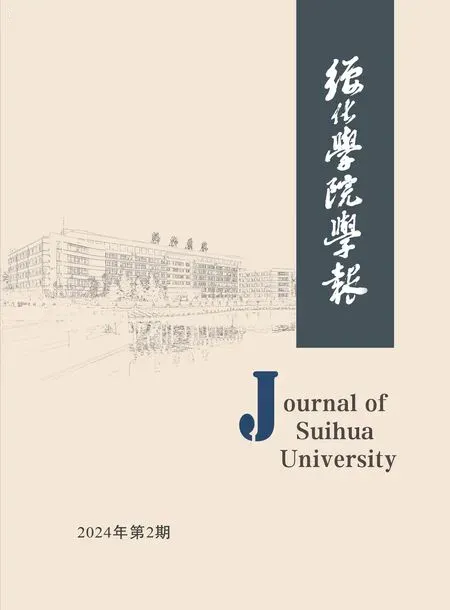边缘突破与思想实验
——中国新科幻小说的亚文化研究
2024-04-09王佳伟
王佳伟 夏 雨
(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伊宁 835000)
作为一种“与主文化相对立的局部文化现象”,科幻文学始终处于“非普适、非大众”的文学史边缘地位。尽管科幻文学在各时期都存在着试图突围主流话语、反思科学价值和局限的尝试,进而“将科学与富国强兵分离开来,将科学发明者与道德完善者分离开来,科学头上的神圣的光环消失了”[1],但这种“越轨”倾向,却始终无法实现对历史与政治话语的祛蔽。这种定性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重塑性尝试,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形成了新科幻作家群体对亚文化特质的自我身份认同。他们不再满足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摇旗呐喊和“乌托邦”憧憬,而追求作家与科学之独立主体性的双重回归。他们主动展现了在时代“共名”的语境下,对主导文化霸权的边缘突破和当代文学话语的理论实验。
一、自由与逃离的“脱逸”意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生代科幻作家群体较之于前辈,一是获得了更加宽松的文学环境与政策支持,二是或身为科学领域的从业人员、或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与文化视野,使科幻文学拥有了高屋建瓴、殚见洽闻的底蕴。这也催生了他们针对“旧”科幻文学和当代主流话语的低沉与无力,试图建构以“科学”为根本、“未来”为理想,重塑后工业社会下“启蒙新学”的尝试。重新自我反思、定位后的科幻文学,正在逐渐实现文学边缘地位的突破,进一步承担起为文学发展提供新的价值思考、反映时代精神向度的重任。
以科幻文学为文本中介,新生代科幻作家展现了自身的青年亚文化审美趋向,即自我与“他者”的文学审美差异和创作思想的不拘一格。就前者而言,针对文学在后工业现代化时代所面临的诸多困难,科幻作家拥有了较之主流更为坚实、宽广的视野和想象。他们有的以科幻想象和异化“空间”建构了既偏离现实的“恶托邦”场域,又与现实呼应的社会文化图景。如韩松的《地铁》,以一位远离时代发展中心、“被暗夜牢牢擒住的老人,什么都会被当做梦呓”[3](P27)的“落伍者”边缘形象,去观察体验具有“幽暗”性、不断前行的地铁空间。“列车从地窖中钻出了浮胖的、蛇颈龙似的头,紧接着是肿胀得不成比例的身躯,大摇大摆、慢慢吞吞停下……站台上的‘墓碑’们飘飘舞舞,像被吸尘器吸了进去”[3](P16)。小说隐喻着社会边缘的“时代遗民”在飞速发展的后工业时代被排斥抛弃的绝望。老人与“白昼的同盟军”存在着代际关系、价值观念、社会地位等诸方面的明显隔阂。他只是一个在空间与时间高速发展的洪流下被置换、被遗弃的“垃圾”,“正被搬运向一个秘密的焚化场所”[3](P78)。这种身份的不断解构和建构,是如亨利·列斐伏尔所言的“空间”的权利和政治性体现,使人在某一限定空间内被动地完成了身份的划分和价值的定义。有的作者则对个体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境遇表达出自己的思考,如何夕的《伤心者》、刘慈欣的《地火》。主人公都怀揣着在自己从事的领域做出新突破的梦想,可社会对功利价值的追求和研究基础的不足,导致知识分子价值的遮蔽和话语的旁落,最终使这类人的努力化为失意的人生。《三体》《流浪地球》等作品则借人类文明的末日想象,通过宇宙宏观视野的超脱性,去反思后工业现代化社会将要面临的科技、伦理、生态等一系列危机。最终以“留白”式话语将希望寄托于遥远而微末的未来,体现出“科幻”主题对未来的期待与不安。总的来说,不同于主流文学通过身体叙事、欲望发泄等后现代写作去戳破美好的“乌托邦”,以刺痛读者的感官体验和情感机制,这一批新科幻作家以全新的科幻审美视角、更加宏大的总体性叙述视野,强化了读者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接受能力。但美中不足的是,他们还未对这些社会异化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对主流话语的突破实验虽逐渐走向成熟,却仍缺少最后的方案。质言之,启蒙承续的方式得以更新,却仍在继续。
就后者而言,他们认为科幻文学是“一种消遣,是一种个人化的自我超越。科幻小说是为自己写的,是为科幻文学本身写的。除此之外,任何一种看法,都可能是创造力的桎梏”[3]。他们追求的是文学创作主体性的自由。继而可以发现,新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新启的文学类型,其作家群体虽均围绕在“科幻”母题之下,却拥有不同的文体风格和价值意识。他们不满足仅仅要求打破主流话语的规训,还希冀自我的张扬和野蛮的生长。90年代以来的科幻文学创作曾被学者宋明炜以“新浪潮”命名,但显然科幻作家创作的异质性并不适宜以某种指代性概念进行统摄,刘慈欣和《三体》也无法成为全体作家作品的审美路标。刘慈欣的文学思想是复杂的,是“对于文类成规的重构与创新”。他一方面曾多次声称自己是一个“技术至上”者,饱含“技术乐观主义”的价值倾向;主张科幻对未来的超脱想象,避免现实干预的成规。但另一方面,其作品亦显示了对古典人文主义传统的回归,继承了传统文学的宏大叙事和人性考量,呼吁“科幻文学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最后一个栖身之地,就让它们在这里多呆一会儿吧”[4]。相较之下,韩松的文学思想更具有英美“新浪潮”的反叛性与先锋性。在他的作品中,“科幻正在侵入现实”,不断呈现的是对科技发展导致人与社会剥离、隔阂的反思。科技异化带来身份意义的缺失、社会发展造成生存的焦虑,这些都反映了作者对科技与人性关系的“绝望”思考。王晋康则侧重于对科技与人的伦理关系和“人”的价值存在进行探索,情感较为温和而富于哲学意义。在《亚当回归》《生命之歌》《豹》等作品中,“赛博格”能否与“自然人”共存的想象性表述,二者在身份秩序、伦理道德、精神意识等维度所面临的冲突危机,是王晋康展望“后人类”想象的核心主题。此外,诸如何夕作品里物理、爱情、现实、宗教等题材的杂糅,郝景芳对社会矛盾的反思,陈楸帆对技术发展和社会退化这一悖论的批判等,都可以看出新生代科幻作家写作的主体自由和风格异质的特点。
“脱逸”的亚文化特质还体现在科幻文化圈的形成,典型代表如国内首个科幻博士姜振宇组织的的“靠谱科幻研究”群。这种文化现象被学者认为“对于大众读者、主流文学评论家等圈外人的进入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使科幻小说创作难以突破‘小众化’状态”[5]。困境固然存在,但从另一角度看未尝不是科幻爱好者们的被迫选择。刘慈欣曾无奈而讽刺地表示,“我们并没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表现手法,新浪潮运动不过是把主流文学的表现工具拿过来为已所用,后来又发现不合适,整个运动被科幻理论研究者称为‘将科幻的价值和地位让位于主流文学的努力’”[4]。“反观国内科幻的评论者们,却正在虔诚地拾起人家扔掉的破烂枷锁,庄严地套到自己身上,把上面的螺栓拧到最紧,然后对那些稍越雷池一步的科幻小说大加讨伐,俨然成了文学尊严的维护者”[4]。主流批判语境的持续恶化、价值观的干预和始终存在着的偏颇与矛盾,迫使他们形成完整的“创作—出版—研究”的内部消化体系,从而拒绝强势的话语霸权对科幻创作并不“靠谱”的管束和指点。
二、独立的文学面孔与现代性品格
科幻文学在20 世纪90 年代形成了对科学技术的再审视,它打破了以往盲目乐观的“科学万能主义”和“在地上爬行”的科学观,并以科学为基底,建构了不同于当代主流文学的审美视角。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对“科学”的现代性理解曾呈现出一种“万能主义”的价值盲从。社会、经济、人文等诸层面的发展被冠以“科学观”的口号予以指导,“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科乎!”[6]“科学”内在的求索与辩证精神被绝对化为一种形而上的“宗教式”信仰,从而“形成了一种类似涟漪效应的思想气氛,会对那个时代多数个人的价值观念和言说方式造成一种或明或暗的影响”。尽管在当时已产生了对这种价值崇拜的反对声音,却“以潜流或者说‘执拗的低音’的方式呈现”[7]。这最终导致“科学”的革命热潮消退后,人们发现这种“魔法”成为了空洞虚假的“戏法”。受鼓舞的人民“发现想象中的和平、民主、自由、繁荣等等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到来,失望之余连幻想也不要了,于是科幻小说迅速没落了”[8]。另一方面,由于科学被赋予介入现实发展和思想引导的功能,导致了追求线性发展的历史观、基于反映社会现实的唯物论、营造“真善美”的人性和社会“乌托邦”等话语霸权的生成。这使得科幻文学所特有的“未来式”幻想被消解,而落入“在地性”的窠臼之中,失去了科幻所追求的超脱性和空灵性。正如刘慈欣所言:“想看对现实的描写干嘛要看科幻……科幻是一种能飞进来的文学,我们偏偏喜欢让它在地上爬行”[4]。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思想的逐渐成熟,新生代科幻作家秉持着一种新的探究姿态去介入科学的内在机理,将其知识理念、社会认同乃至焦虑想象都包容进了科幻文学的表述范畴之内。在此之下,科幻文学独立的文学面孔和现代品格才得以确立。
(一)新科幻小说确认了以“科学”为中心的阐释话语,“科学家”成为文本青睐的主人公形象。这种与主流文学存在巨大差异的变化,主要源自作家主体面临知识分子话语旁落的困境,进而呼吁身份认同的冲动。与传统作家相比,部分新生代科幻作家作为现实的科学事业工作者,他们更善于凭借踏实的科学素养和独特的科学视野,去剖析当代工业社会的症结所在。他们将自己的现实身份内化进文本中,承担起人物与主题的叙述中心,从而建构“合法”的文学话语。此类文本在科幻小说中屡见不鲜,如《乡村教师》的李老师,《地火》的刘欣,《临界》的文少博等。这种文学话语不同于底层人物身体、情感的发泄和命运的共情,因为后者的文学意识在经过时间的沉淀和考量后,其“先锋性”已然被收编、祛魅。对个体生命的表达在将其苦难、欲望书写到极致后,已然是无根之萍。“远离讲故事形态的‘严肃’小说运动所留下的空白已经被带着超越了叙事刺激的虚荣感的‘大众化’的形式所填补。这些形式十分空虚,它们对文学的处理形成了另一个缺口——只满足读者的叙事需要而不满足读者的智力需要”[9]。因此,反思造成“启蒙终结”这一人文危机的时代因素、知识分子的社会认同和命运关照等成为了科幻文学的价值追求之一。它“能够满足我们的认知要求,还能满足我们的精神需要”。晚清至五四的人文危机,背景是民族危亡的战争国难;新中国以后批判话语的旁落,源于价值观的要求和“乌托邦”的过度强调;到了当代,科幻文学考量人文危机和社会发展的根源落实到了科学。这种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剖析,是科幻文学建构现代性品格的一个体现。
(二)作家的现实观察和生活体验引发了对科学的焦虑想象,确立了文学边缘群体反“乌托邦”的价值追求。新科幻小说对“科学”的把握并非是一元的,以“科学”为基底并不是将其奉为新神。相反,新科幻小说更多呈现出的是对科技发展带来的异化问题和文明冲突危机的反思。这就与以往主流话语规训下的科幻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传统科幻文学亦是以“科学”为价值基底,但其畅想的是基于破碎现实之上的未来世界,它急于寻求“乌托邦”来肯定现实的努力和希望。因此,“科学”是立足当下,憧憬未来。它成为了一种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更多起到的是鼓舞和慰藉作用。而到20世纪90年代,目睹了现实异象的新生代科幻作家秉持着知识分子的忧虑本能和批判眼光,形成了对科学理想与现实的考量。技术发展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和伦理问题,使科学率先主动打破了被遮蔽的面纱,宣布了“乌托邦”的破灭。其后,一系列由此呈现的形而上思考和未来描写,如虚拟与真实的不可把握、“人”的灵与肉的异化、末日危机和宇宙战争等等,都是作家学者们基于现实存在而产生的质询和想象。它不是空虚的幻想,也并非局限于传统现实场域的囹圄。相反,这种“跳脱”的背后是立足未来,观照当下。如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三层空间共享48小时的生活世界,但作者并没有投入笔墨去交代如“魔方”般折叠的高楼、翻转的地表等场面生成的科幻原理。换言之,作为一部科幻作品,其“科学”幻想并不是小说的阐释中心。它只作为文本先在的未来背景,以推动情节的叙述。这也是学界对其“科幻性”表示质疑的主要原因。但小说的重点不单是以科幻想象表达对阶层、分配的批判,更是以复杂的思考呈现出对上流精英和底层平民关系的探索。这也是作者在经历了相似的现实工作后,面对这一现状产生的思考与质询。在科技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上层决策者并没有采取机器流水线等形式去治理垃圾问题,而是为了底层人能有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采取了更费力、效果更差的人力模式。基于此,底层人的反抗也就无从谈起。因为所谓的剥削敌人并不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赋予他们生存机会的有恩之人,最可悲的是他们对社会的价值也是决策者所赋予的。相比于主流文学所钟意的二元对立,《北京折叠》则更多表现为底层人物社会价值虚无的残酷。在这里,郝景芳强调了对社会矛盾的反思,以及科技发展与底层平民关系的解构式质询。科技发展是否能造福整个社会、阶层差异带来的是否只有对立与仇恨、底层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如何实现,这些都是作者在科幻背景下做出的深刻剖析。质言之,新科幻小说是通过想象未来的姿态来确证自身特点,通过对现实的反思和重构来实现其终极追求。
(三)文学观念的更新,体现为对支配性话语的反驳。90年代以来的科幻文学打破了早期“科普性”和“工具性”的陈旧枷锁。拒绝承载政治任务和宣传功能的公共话语,使得科幻文学不再从属于主流文学的统筹之下,避免了沦为思想教育和价值传输的工具。因此,写作者的“导师”身份被直接解构,知识分子指引群众的“启蒙—被启蒙”关系得以消弭,转而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去分享、交流。文学高高在上的指导和灌输作用不复存在,转而形成的是期待读者通过文本实现自觉无意识的自我启蒙。这种“外部权威”的自我解构是科幻文学所做的反抗努力,为科幻文学现代品格的建构打破了牢笼。
三、“对话性”和“延伸预测”的思想实验
作为一种“具有生动的艺术感染力的审美形式”,文学形象在新科幻小说中已具有了独特的审美内涵。其塑造的族群形象、自然形象、科学形象,超越了主流文学所强调的自我与他者的“独白”形式,表现为一种对话沟通的“复调”性。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中,一方面是自我和他者存在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关系。双方通过“凝视”,把对方当成意识对象,甚至把别人虚化为一个存在物,即萨特所言的“他人即地狱”。每个人都会为了实现自我主体的独立性,而试图去收编他者,从而把他者变成客体,自己成为支配者。支配性话语所追求的,就是如巴赫金所言“致命的理论化”的独白思维,一种强调统摄性的普遍意识和普遍价值。另一方面即新科幻小说所追求的“对话性”。人物形象的脸谱化是科幻文学常被主流话语批判的原因之一,但若从文学形象这一维度出发,可以看出这是作家有意采取的颠覆性手法。具言之,简化人物形象的塑造使“我”的个体主体性被淡化,这是服膺于凸显族群视域的需要。基于此,文学视野得以完成超越,个人的情感机制、社会地位、文化心理等因素被置换成人类视域下的文明未来、生存危机和种族冲突等宏观想象。正是这种“宇宙诗学”下的族群视域,才使得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与自然、科学展开对话成为了可能。在陈楸帆的《荒潮》中,科技发展推动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展开了全球性的资源掠夺和生态殖民,由此导致的电子垃圾倾泻使自然生态面临如马克思所言的“新陈代谢的断裂”。社会劳动分工以及“铃木变种”计划使得人类社会处于阶级分裂和自我价值异化的危机当中,个体主体性的丧失和“身份”的模糊使人类文明退化到“丛林法则”的原始竞争当中。在《命运》《人与吞噬者》等作品中,作为地球主人的人类成为了被任意宰割的“小虫虫”。《微纪元》《超行星纪元》中,人类在太阳聚变和恒星爆发面前所做的一切自救都显得如此力不从心,只能无奈地接受被自然支配的命运。《赡养人类》里造成“终产者”把控地球全部生态资源、智能科技和社会秩序的原因,是“社会机器”的执法保护和科技发展带来的人力资源的被剥夺。诸如此类的文本表述将“科技”、“自然”的形象视为“自我”,人类反而成为了一种被支配、收编的“他者”形象,体现了“去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倾向。作家通过权力话语的转换阐释了人类与“他者”发展的悖论关系,意在表达人类与自然、科学应处于一种平等和对话的位置。若人类始终秉持着收编“他者”的心态,自然与科学将反过来统摄人类的命运,并催生人类内部的权力霸权,形成反噬效果。只有在这种对话中,任何一方的“自我”与“他者”形象才能不再是支配与从属的关系,神圣话语也将在这种沟通交流中被祛魅、消解。
主流支配性话语多善于建构一种终极目的,这种目的是当下社会所缺失而又具有可预知性的,被赋予了实现发展进步的超越性价值,遵循着历史唯物观的发展趋向。而科幻文学则与此相反,它所追求的是一种“认知解离”,“是一种想象的框架或一个在作者的现实经验环境之外同时并存的拟换性可能世界”[10]。它将当下社会未被确证的某种概念或现象,投放到虚构的未来世界里,进行演绎与类推的思想实验,使之成为某种业已形成的文学图景。由此,历史到未来的既定发展秩序被割裂,历史进程的向度被外延类推,从而形成了“延伸预测”的科幻史观。新科幻小说中时常出现的宇宙飞行、时空穿越、脑域链接,以及“真空衰变”“微连续理论”“宇宙坍缩”等理论,种种现阶段无法解释的问题并没有在文本中得到详细的解答,科幻作家的作用也不在于阐释此等现象的原理。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在自己营造的虚拟世界中,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向度,隐喻现实社会的危机。《三体》中,故事从经历“文革”苦难的叶文洁向太空发射广播展开。自此,历史发展的向度从现实走向了未来式的“科幻”想象。《人人都爱查尔斯》向我们展现了人类驾驶以核聚变为推动力的航天飞船竞赛,一种与现实相似却又割裂的未来世界。《六道众生》更是打破了历史唯物观的时空概念,创造出了并存于一个地球的六层空间异域。新科幻小说的这种想象,使循序渐进的历史进程被终止,科技发展的“终极目的”只作为科幻文本中的阐释背景和工具性而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文本的思想实验,作家借科技发展作为推动文本叙述的动力,将人类文明的历程向外延伸,去类推社会的未来前景,从而呈现出文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想象。由此,新科幻小说或出现时间的跨越,或出现空间的跳转,或呈现人类文明消亡后的“新生命”世界。这种史观的“延伸预测”,最终为新科幻小说建构起了开放、多远的想象空间和文学话语。进而使其跳出传统文学场域反映现实的单一维度,而展现出新的文学批判视域和审美维度。
综上所述,中国新科幻小说从“脱逸意识”“现代品格”“思想实验”三个维度,展现出了与传统主流文学相悖的亚文化特征,显示出对支配性话语的突围和重构。这种具有亚文化特质的边缘突破,使得科幻文学在当代确立了作家与科学主体性的双重回归,建构起了独立的文学批判话语和阐释空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科幻文学实现与世界科幻文学的主题契合和思想呼应,强化了科幻文学想象未来,观照现实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