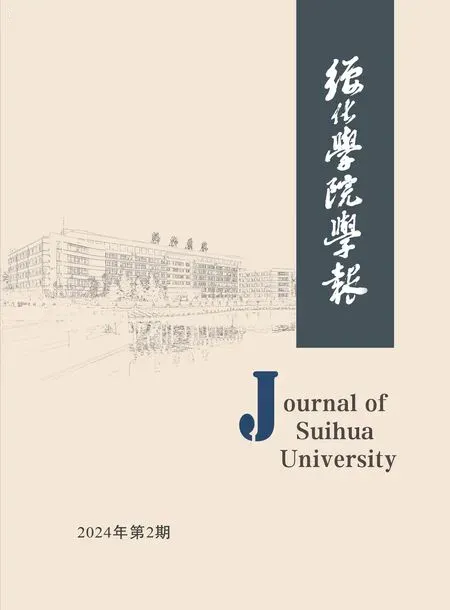王安忆“我们庄”乡土创作的记忆书写
2024-04-09洪何苗
洪何苗
(蚌埠学院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安徽蚌埠 233030)
王安忆有在淮河乡间与上海都市生活的经历,沿淮乡村承载了她青年时代的喜怒哀乐。她将乡土叙事与淮河流域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在小说创作中找到了“我们庄”。她以淮河流域“我们庄”生活为素材,以文学书写记录描绘“我们庄”的农耕记忆、水记忆、民间艺术记忆,保留了沿淮乡村丰富的审美文化形态,呈现更加鲜活的淮河历史,形成不可复制的文化记忆与生命底色。
一、“我们庄”的农耕记忆
(一)沿淮乡村劳动传统悠久。“对一个地方的域情,本地人或许是‘身在此山中’的缘故,未必都有很深刻的感受、很清晰的认知。外面来的人往往会于映照比较之中产生更加鲜明而敏锐的感触,反而能看得更加明了。”[1](P141)王安忆乡土创作正是如此,作为一名曾在皖北沿淮乡村生活过的“外面人”,她对沿淮乡村悠久的劳动传统有着更加鲜明而敏锐的感触。
王安忆在创作中着重书写了“我们庄”源远流长,有悠久的劳动传统。《流水三十章》中首先点出:“明天收麦了,明天第四千零一次的收麦了。……这播种了四千年的土地,是尽了全力才又培育出这一季收成,这是四千零一次麦收前夜中再平凡不过的一个。”[2](P310)通过强调“四千零一次”“四千年”说明沿淮乡村劳动传统悠久。其次,为了在创作中更好地展现“我们庄”历史源远流长,她在书写中不惜花大量笔墨从自然地理、农业耕作、日常生活等方面详细介绍“我们庄”,如“青砖到顶的房屋”“人口众多”“房屋密密匝匝”“掌握贮藏粮草和各类食物的技能”“放大刀”“燎麦子”等,再现沿淮乡村一定历史时期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面貌。最后,细致描绘“我们庄”的农田、坝子、庄稼、劳动号子、放大刀等情形。特别是沿淮地区围田防水的农业民俗的书写,从侧面反映“我们庄”有悠久的劳动传统。淮河流域经常水灾泛滥,围田防水可以使田地有效抵挡淮河汛期时洪水泛滥。如果洪灾太大,围田不能发挥作用,淮河流域农民还会将围田“反着”扒开,把水引到淮河下游,也称之为水利。王安忆称:“此情此景证明了我们庄劳动传统的悠久。”[3](P226)围田防水作为具有典型淮河流域特色的地域景观,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和积累,形成了独特的农耕文化景观,成为沿淮人民的共同记忆。王安忆凭借着对沿淮乡村的一腔热爱,用笔记录着沿淮乡村悠久的农耕传统。
(二)沿淮乡村劳动之美。沿淮乡村的农业生产从播种、生长到收割,其过程具有劳动之美。且这份劳动之美早已融入到王安忆的血脉之中,构成一份对王安忆看不见的影响,在潜移默化中切入作家的文学创作。
王安忆始终强调:“城市是一个人造的环境,讲究的是效率,它把许多过程都省略了,而农村是一个很感性的审美化的世界,土地柔软而清洁,庄稼从播种、生长到收割,我们劳作的每一个过程都非常具体,非常感性,是一种艺术化的过程。农村对我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它给我提供了一种审美的方式,艺术的方式。农村是一切生命的根。”[4](P107)“我们庄”为王安忆提供了一种审美的视角,她在创作中把劳动这一生存手段审美化,对于沿淮乡民的农业生产、农具等,总是不吝笔墨地进行赞美,如同刻在了她的记忆里,连同劳动细节的书写都是那么真切、清晰。
譬如,小说《69届初中生》“此地收麦全是男劳力用大刀割,他们叫作‘放大刀’。长长的刀把,夹在腋下,双手平端,而脚叉开,走一步,挥一刀,走一步,挥一刀。不但用臂力,还要用胯和腰的力量,因此,割起来,要转身,扭腰,那姿态十分雄健优美。”[5](P240)《青年突击队》中描写劳动能手刘业民,王安忆称“看过他装车吗?不用绳拦,就凭一杆叉,一扎,一挑,一送,一捆捆麦秸叉上去,码起来。”“金黄金黄的麦子,一排一排地倒下。实在好看得很。”[6](P207)王安忆极具动态感、节奏感、场面感的描写,生动展示了沿淮乡民劳动美。
(三)沿淮乡村劳动之乐。20 世纪70 年代,麦收的各个环节,俱要人们亲自手工操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割麦子时镰刀很容易钝口,为节约抢收时间,家家户户首先要做的是磨大刀头。《流水三十章》详细描写了农民“拽子”磨刀的情景:“他将它贴在磨石上,掬了一捧水,轻轻地一推,他浑身的骨骼全由了这一推舒展了,活动了,轻盈自如了。他的血液在血管里愉快地低吟,他手指的每一个小小的关节全如舞蹈一般优美而快乐地活动,刀刃在青灰色的浆水里发亮了,越来越亮,像一件活物似的,回应着他的手的舞蹈。世代相传的收割的快乐,世代相传的收获的激动。”[2](P308)因为丰收在即,王安忆笔下沿淮农民“拽子”在磨刀时,骨骼轻盈自如,血液愉快地低吟,手指关节如舞蹈一般优美而快乐地活动……农民“拽子”忙碌的喜悦在王安忆字里行间喷薄而出,大刀头仿佛都跳起了舞。
王安忆乡土创作中类似劳动之乐描写还有很多。“大路上,牛车轱辘轱辘地来回拉麦,赶车的吆喝声,象唱歌一样悠长婉转。到处洋溢着劳动的热情,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地被感染着。”[5](P240)沿淮乡村田间劳动不仅有赶车的吆喝声,还有劳动号子,都唱出了沿淮乡民们丰收的喜悦。
村里冬天挖干沟的时候,总会有节奏鲜明、气氛热烈的号子,一般由男劳力起句“上了个子肩哎。”王安忆称:那个“上”了是拖了符点的,一个切分,然后“了子”是合一拍,“肩”也是一满拍,却突然柔和下来,委婉地带出了“哎”声。听了这号子,本是抬着一筐很重的土,只要将扁担呦得老高,跟上了号子的节拍,一悠一悠地上了陡峭的沟沿,真地很来劲很欢腾,一点也不觉得累。
劳动号子唱掉了一天的辛劳,唱甜了日子的味道。大叔们赶牛时的号子,一张口,歌就出了喉。犁地、耙地、压场、赶车,凡是牛出力的时候,就有这号子在,牛听迷了,人也听迷了。沿淮乡民生产劳动时以唱劳动号子为娱乐,体现了沿淮乡民劳动的乐趣。这份劳动之乐,远不是有限农作物的收获,更是精神上的愉悦,使沿淮乡民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王安忆用劳动之美与劳动之乐讲述和展示淮河流域悠久的农耕记忆,使广大读者了解沿淮地区传统的农耕方式和生产习俗,展现了沿淮乡民们生产劳动过程中所折射出来勤勉、坚韧的精神。
二、“我们庄”的水记忆
(一)淮河水情变化的记忆。王安忆在安徽生活期间,有两年居住在大刘庄。该村南临淮河,北靠浍河,是水灾频发的乡村,王安忆充分感受到淮河水情的变化。王安忆笔下的“变”主要是指淮河水情阴晴不定,淮河水情平静时美丽的如同“天地之间,朦朦胧胧的一条绿线,再也望不过去了。”[5](P208)《蚌埠》中书写了淮河水情稳定时的近景,“柳树成荫的淮河大坝,大地宽阔平坦坝下的淮河,在这角度看起来,也是宽阔的,轮船从中走过,就像一叶小舟,突突的马达声,在开阔的天地间消散了,气笛声是柔和的。”[6](P9)那满目皆绿,是沿淮乡民在沿淮河滩上种植的作物,绿色的水和绿色的作物连接在一起,一眼望去绿茵茵看不到边。满目望去,皆是活力满满的绿,自有时光沉淀的韵味与情怀。
根据记载,淮河历史上平均每百年发生水灾94次,每当水灾来临时,淮河发威,咆哮,冲破堤防,淹没村庄……王安忆书写了很多洪灾时淮河变脸的情形。如,《小鲍庄》开篇在“引子”中直接描写恐怖的淮河水灾情形,“七天七夜的雨,天都下黑了。洪水从鲍山顶上轰轰然地直泻下来,一时间,天地又白了。……孩子不哭了,娘们不叫了,鸡不飞,狗不跳,天不黑,地不白,全没声了。天没了,地没了。鸦雀无声。”[3](P240)王安忆直击淮河水灾现场“水撵着人,踩着石子路往山上跑。有了这一条石子路,跑得赢水了。跑到山上,回头往下一看,哪还有个庄子啊,成汪洋大海了。”[3](P185)王安忆对淮河水灾没有激昂悲壮的痛哭与呐喊,只是用舒缓平静语调讲述了小鲍庄水灾情况,在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中展现洪水灾害给沿淮乡民带来深重灾难。
王安忆创作中还插叙沿淮乡民们记忆中的淮河水灾。《大刘庄》中小翠因为家乡“差不多年年闹水灾”,只得出门要饭。在小翠的记忆中,她刚满周岁那一年,淮河水灾闹得最凶。小翠说:“听俺娘说,没天没地了,只有水。”[3](P154)“庄东头大柳树是小鲍庄最高的地方,那年夏天,下了九天九夜的雨,一整个庄子,全淹在水里,只露出大柳树的梢。”[3](P134)正是这份淮河安澜与暴虐中的变与不变,让沿淮百姓对淮河又爱又恨,爱的是她平静时哺育了沿淮两岸,恨的是她时常给无数百姓造成难以忘却的伤痛。王安忆通过对淮河水灾的书写,将沿淮村民生活悲惨的画面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二)不变的淮河精神。从远古时期的大禹治水开始,沿淮地区历朝历代一直根治淮河水患,从未停止探索和治理的脚步。沿淮地区无数个水旱交潜、多灾多难的乡村,记载着几代人的磨难和奉献,传承了不变的淮河精神。
在王安忆沿淮乡土创作中,这份淮河精神可以滥觞于大人们纳凉时讲起大禹治水的传说,沿淮人民在治淮中所体现出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人定胜天的根治淮河精神,以及父老乡亲苦难生活中守望相助时所展现的仁义与善良。
淮河是新中国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1971年2月,治淮规划小组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把茨淮新河、怀洪新河作为扩大淮河中游洪水出路的战略性大型骨干工程[7](64)。王安忆所在的大刘庄参与到怀洪新河工程建设中,王安忆也是这其中的一员。她在创作中称:“要过冬了,这里的冬季是沸腾的冬季,要挖河。冬闲成了冬忙。这是一个大兴水利建设的时代。雯雯渴望参加这沸腾的工程,为此她下决心推迟回家。”[5](P244)“数九的天气,大伙儿却都脱了棉袄,穿着单褂子。”[5](P270)沿淮乡民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前去挖河,没有工程机械,有的只是铁锹、竹筐和双手,他们不畏严寒酷暑,在挖河时手磨出血,脚磨出泡……却从不叫一声苦和累。王安忆在文学书写中展现了沿淮人民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建设美好的家园的劳动情景。
王安忆以当代女作家的细腻敏感捕捉到了温暖大爱淮河精神。《小鲍庄》记录了沿淮乡民在洪灾面前的仁义坚守。小翠母女因为洪灾逃荒要饭,在饥饿与贫团线上挣扎;鲍彦山家收养小翠;涝渣为救五爷而淹死在洪水里时才9岁……
《隐居的时代》中书写了“县里有一处分洪闸,是这个县城最为壮观的景物。它是解放初期治淮工程的产物,一座巨大的水泥建筑,顶上刻着三面红旗,闸下过着大河,万舸争流。……有一年,为了保蚌埠,分洪闸的闸门,拉到了最高位,致使五河全面受淹。这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8](P242)五河全面受淹时群众全部撤离,万亩良田和村庄淹没在洪水中。每一位沿淮乡民眼看着自己的家园顷刻间被洪水吞噬,内心既是难舍,也是不忍。沿淮乡民们顾全大局,深明大义,舍小家护大家,牺牲自己的家园和利益,守护更多人的安全与家园。王安忆乡土创作中一系列温暖、友爱、仁义、牺牲的描写,凸显出淮河文化中不变的意蕴和精神。
三、“我们庄”的民间艺术记忆
(一)寻根故事:大禹治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等故事在沿淮大地广为流传。王安忆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在现实生活个体感受的基础上,在思考和表现沿淮乡民日常生活时,把对《大禹治水》神话故事的文学理解和想象纳入自己的记忆书写中,借助神话故事建构和传承淮河文化精神。汪曾祺的《受戒》、莫言的《红高粱》《生死疲劳》、张炜的《九月寓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阎连科的《受活》、尤凤伟的《泥鳅》等作品都有类似地域文化构建与传承的文学书写。王安忆《小鲍庄》也属于这一类型。
如《小鲍庄》以“大禹治水”故事原型,讲述了“小鲍庄”来历,先人是大禹的后代,一辈传一辈,直到现实的小鲍庄人。王安忆强调小鲍庄祖先虽是大禹后人,却不得大禹精神,受到惩罚,因而小鲍庄一直多灾多难。虽是野史,却引出故事,同时在创作中先抑后扬,指出一辈传一辈,现在的小鲍庄人知道了“大禹治水”和祖先的故事,格外注重传承大禹精神中的“仁义”。村子中“捞渣”是小鲍庄践行仁义的代表,他为救鲍五爷而死,政府给家中盖了新房,安排“捞渣”哥哥进了农机厂,小翠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全村修了路,建成了“捞渣”纪念馆……通过故事讲述告诫人们不要忘记文化的根与魂,要有做人的品德,要追寻“仁义”的义利观。“大禹治水”神话故事成为王安忆在新的时代历史语境中思考和表现“文化的根”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构成了《小鲍庄》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精神记忆:花鼓戏。王安忆笔下记录了沿淮乡民的唱古之声,其中花鼓戏昂扬着沿淮乡村泥土的芳香,流淌着淮河儿女最美的词汇和最动人的激情。可以说,花鼓戏既是淮河文化的母语和家园,更是淮河儿女的精神记忆。在沿淮乡民的眼中,花鼓戏的存在代表着驱邪、去秽、平安、健康和幸福,生长在淮河两岸的人们在稼穑、渔猎之余,每每于婚嫁、祭祀和庆岁之时,都会唱花鼓戏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感激和虔诚。
《小鲍庄》中,牛棚里孤老头子鲍秉义坐在凉床上唱花鼓戏:“关老爷门口字两行,古人又留下劝人方。这一字出马一杆枪,二字上横短来下横长。三字立起来象川字,四字好比四堵墙……”[3](P132)乡民鲍彦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听得出神,平时牛棚里照例挤了一屋人听他唱花鼓戏。[3](P160)《小鲍庄》中花鼓戏一共只有短短五十句,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唱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唱尽几千年的兴亡,既有英雄豪杰,也有奸臣顽夫,以及王母娘娘、孙悟空,追寻的真、善、美,情透唱腔,义透唱词,无不滋养着沿淮乡民们的精神魂魄。
结语
王安忆说:“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9](P110)沿淮乡村的岁月四季,春耕秋收,以及淮河水从王安忆的记忆书写中缓缓流出。王安忆用现在的眼光回望“我们庄”这片土地,既有艰难,也有温暖,更是碰撞与回味。可以说,王安忆乡土创作中的“我们庄”,丰富保留了地域审美文化形态,是社会记忆的文化存储载体。不仅是王安忆走过、路过、生活过的沿淮村庄,更是她想象的原乡、一个在生活中能寻到审美的文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