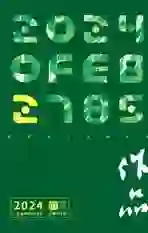点燃,照亮与温暖(评论)
2024-03-19
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如此动荡,如此喧嚣。乌克兰战火,巴以冲突,台海风云,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困境……文学无力改变些什么,文学又在改变着什么。文学评论亦然。
2018年3月,《作品》杂志组建评刊团,打破评论藩篱,邀请草根读者担任评刊员,免费赠阅刊物,以指定评刊和自由评刊两种方式,将作者、读者、编者的交流互动,原生态地呈现在大众视野,开文学评论之先河,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流。一些期刊紧随其后,纷纷开放了自己的专属评刊通道。迄今,《作品》评刊团已运行近六年,线上评刊如火如荼,为此,《作品》杂志的全体编辑老师们,付出了大量心血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评刊团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有资深评论家,有新锐评刊员,更多的是普通文学爱好者。他们怀揣庄敬之心,读《作品》,评《作品》,沿着文字的脉络,寻根滋养这坚实与丰盈之果的中华大地,写出了自己眼里心里的文学图景,并在探寻的过程中,茁壮成长,蔚然成林。阿探、石凌、洪艳、熊焕颖等几位老师的评论,厚重,有力道,辨识度高,影响深广;刘天宇、黎希澈、周晓坤、李天奇等青年一代,以其独特的视角、敏锐的洞见,令评论别开生面;尤为可喜的是,赵文等几位评刊员,在评刊过程中,摸索到了属于自己的写作路径,开启了文学疆场的驰骋与奔赴之旅。
本年度十佳评刊员金奖获得者胡岚,擅长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挖掘故事的精神内核,并着意于作家文字气韵与张力的营造,展开评述。她的评论大气,温婉,有穿透力。一年里,她深耕细作,熟读《作品》,写下了十六篇评刊文。这是怎样的一种热爱!评刊团里,除了阿探老师,少有人及。她的《谁是谁的人生》一文,将鲍十小说《我是扮演者》分析得入情入理。艺人孟千夫在虚拟人生与现实生活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却终因难以走出心理阴影而抑郁自杀,官场百态,社会沉疴,都在虚实莫辨之间露出本来面目。她敏锐地提炼出小说的隐晦寓意,让我们看到众生诺诺下的一记反戈。她从张伟明的短篇小说《一瓢》细碎日常的文字描述里,瞥见后疫情时代隐现的商业凋敝的冰山一角,感受充塞其间的人情冷暖,尤其是无症状感染者的焦虑、压抑与不安,以及人心动荡中的坚守。她一眼看穿了肖建国的短篇小说《同和麻将室》里各怀心思却不动声色的一众人等,洞悉了小小麻将室深藏的世相江湖。她捕捉那些不起眼的细节、不经意的话语里,流露出的朴素情感和小人物的精神风骨,捧出热气腾腾的生活日常与浩浩荡荡的家国大义,感染我们,打动我们。
小小说作家评小小说,当属行家看门道。银奖获得者余清平即是。他的小小说作品多有发表、获奖,他的小小说评论,曾被《微型小说月报》连续刊发,有的被选入高中语文试卷。他的评论、新颖、独到、有见地。他将内容的新鲜感、人物的丰满度、情节的饱满度作为文学审美标准,直言反腐题材小小说创作的圈禁,以及众多精品之作深陷的窠臼。他的《一篇别具特色的反腐倡廉小小说》一文,将读者带进青年作家刘帆的小小说《0471的报告》,六次未遂的暗杀,出人意料的结局,抓敌特的明线,原来却是贪腐分子一步步堕落的暗线。鞭辟入里的评论,使这篇小小说的历史厚重感和现实嵌入感得以彰显。他有敏锐的洞察力,小小说作者创作手法的任何一个细微变化,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从小细节入手,为我们梳理了符浩勇的小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欧·亨利笔法的延宕,指出小小说写作可行的新路径。余清平的评论,成为小小说创作的风向标,具有启发性和引领性。
银奖获得者张翠云,集评论、写作、主持于一身,她以悲悯之心,感受文本构建的生活热望与精神温度。她的评明亮、温暖、也活泼、又庄严。回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终极之问,她抽丝剥茧,从王祥夫的短篇小说《杀死姨妈》一文,抽出原谅与包容的金线,为主人公找回了失落的亲情,低伏在尘埃里的生命,从此有了光和暖。读者的情感,也从初见标题的惊骇,归于释然——杀死的,原来是姨妈的照片。她的《人性的完美与人生的不完整》一文,感知到樊建军的小说《马壳先生》的苍凉底色,她看见向世俗妥协的主人公内心不曾熄灭的那一粒珍贵火种。被淹没、被遮蔽的弱小者的声音,经由她的观照,得以放大,被倾听,被关注。她将王子健系列小说做了横切处理,使文本的层次纹理得以清晰呈现,她指出○○后写作者丰富驳杂的广阅读带来的知识储备优势,并在主持线上研讨时,跟青年作家做了坦诚直率的交流,给读者和写作者带来双向启迪。
铜奖获得者陈德轩,有着与生俱来的通感,每每将音乐与文学联系起来,领会其相通相融之妙。他的评论质朴,扎实,亦不乏跳脱。他以季札听《诗经·颂》乐之后所言直曲近远、用广处行为喻,指认阮德胜的长篇军旅小说《长缨在手》“节有度,守有序”的分寸感。他以条条支流汇主流为喻,抓取一段河床的面貌细细状摩,感受小说达成的如音乐变奏曲一般,“主题及其一系列变化反复,并按照統一的艺术构思而组成”的文学效果,来解读王子健的小说《小披头的恋情》。他赞赏王子健借由一首诗歌,调动读者想象力的巧妙,让读者“绕过故事的主题,像眺望一棵树,既而喜欢上树梢上高挑的那朵白云”。他心怀感恩,认真写评。他说,《作品》不仅仅是一本文学杂志,更是一部教材、一座学府、一间课室,担负起文学普及和推广的责任,并全力以赴,引导读者抵达更加美妙的文学秘境。
铜奖获得者崔会军以诗心观文本、以慧眼察幽微,拨开文字的云层和雾气,她寻到了光和美。她的评论,超拔于物外,又熨帖人心。她的《召唤一个新世界》一文,将索南才让的中篇小说《哈桑的岛屿》与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加以对比,托举起小说中的精神光焰和明亮气质,照耀和温暖着众人。她的《虚与实的无痕转化和衔接》一文,关注了冉正万的短篇小说《醒狮路》中不露痕迹的写作技巧,虚实转化的自然衔接间,作品强大的穿透力、黏合力和共情力的发散,并作出心安即归处的妙结。她从罗淑欣小说的日常新叙事,和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小清新,探触到文本的独特质感,指出现代年轻人纯粹的形而上的价值观,与老一辈人的生活既粘连又游离的特征,以及互联网覆盖下的时代症候。她感知到青年作家有如岩浆喷涌的炽热内心,与不可估量的写作未来。
铜奖获得者杨林鸿,注重文本结构与精神搭建,有自己的文学审美与认知体系。他的评论贵求证、善思辨、有向度。他在康坎的小说《从饥饿艺术家到清源山野人》一文,剖析了荒诞之梦与现实的种种纠缠,青春的挣扎与无奈,失望与无助,却又执着于寻找被异化的个体——一种精神光芒的坚定,他捕捉到康坎小说的语言张力,看到了青年作家力图摆脱小说创作的传统模式,构建起独属于自己的小说风景的勇毅。他跳出文本的藩篱,为我们还原了王子健小说细腻而惊艳的笔触下,以爱为基石构建的别样世界,指出小说对各种生存状态的描摹,实则是对精神世界的探索,是在垮塌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精神庙宇。他欣赏罗淑欣小说的纯净灵动和散发的蓬勃气息。他在诗意芬芳的小说丛林徜徉,感受文字传递出的青春温暖和光辉,感受文学的美好,并把这些美好,一一讲给我们听。
石凌是评刊团的三剑客之一。“要我闭上疾恶的声喉/我不能够/要我闭上倔强的双眸/我不能够”,多年前读到的诗歌,铿锵在耳,仿佛只为她量身定做。生活中的她,嫉恶如仇,敢于发声。她的评论大胆、犀利,勇于直面世相症结和人性幽微,令人常有“弓如霹靂弦惊”的讶喜与震撼。她直言“一部看似无懈可击的作品往往有失真实性”,指出阮德胜的长篇小说《长缨在手》故事格式化、人物脸谱化、性格扁平化的缺憾。她的《意象、留白与治愈》一文,为残雪的《西双版纳之夜》做了客观阐释,指出残雪先锋小说文本的小众性、实验性,自带的独特审美意蕴,将读者带入治愈的哲学思考之境的引领性。她的《都市镜像中的自我确认》一文,批判了特殊时代语境下主题先行、文学审美体验长期被忽视的现象,她褒奖罗淑欣非凡的叙事能力,洞察到青年一代拨开物、声、光、色的迷雾,确认自己社会价值的努力和意义。她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他们还处于成长期,青春的身影像灵动的小鸟在林间闪过,心灵的秘密在树与树之间的缝隙里忽隐忽闪,伴随着成长的喜悦与惆怅。”于千骑卷平冈中,忽见这隽逸,这灵动,实为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批评也是一种写作。”石凌的评论,亦如是。
热爱生活、热爱阅读的雍小英,有着敏锐的艺术嗅觉。她深度介入,从小说文本中洞察人性与人心,并借此觅得现实观照。她的评论,率性,通透。她将索南才让的中篇小说《哈桑的岛屿》与蕾秋·乔伊斯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朝圣》作对比,指出其主旨的异曲同工之妙,在文字的温度里,触摸人性本真之美。她从李亚的短篇小说《时间控制仪》一文,嗅到了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相同的魔幻现实主义气息,一语勘破天机——如今的我们,都是“在时间迷宫中左冲右突的孩子啊”。她发现了阿成小说《戛然而止》的动人细节:父亲的葬礼上不是哀乐,而是《志愿军进行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豪迈音乐。那是儿子对父亲,对一个真男人的由衷敬仰。她察细部,亦观宏大。“小说家只通过一个人的改变来暗示一个历史事件的沉重。”
李丽苹的线上评刊,不疾不徐,也温柔、也坚定。她留意作者的写作技巧,更关注小说文本的烟火气息和精神传递。她指出《玉朗拖在胡志明市》这篇小说中外爱情故事的完美糅合,是青年作家增强小说的历史感与厚重的通润感的制胜之宝,小说主人公遵循内心,勇敢逐爱的精神,成为一种鼓舞,一种指引。她从罗淑欣系列小说里,追踪到青年一代蜕变成长的痕迹。她解读文字里的岭南地域文化特色和平静内敛的叙事基调,并从其中传递的诸多新元素中,留取引发共鸣的生活气息,让读者去回味。那些青春的懵懂与忧伤,孤独与迷惘,都与个体生命有了惺惺相惜的关联。她从曹多勇的小说《宠物鸡》一文,发现社会的缩影,人性的幽微,人心的驳杂与多变,以及命运的乖戾,从而引出杨绛先生“你计较什么,什么就会困扰你”的警语。
向明伟是真诚的读者和评论者。他贴地而行,对作品的艺术之美和精神向度进行阐释和解读。他的评论,热忱,坦荡,有风度。他的《边地少年的奇幻之旅》一文,深度剖析了索南才让在《哈桑的岛屿》中,梦境的多次拓展使用给小说带来的神秘气息,以及借梦传声的虚实转换。他亦诚恳地提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那些按需而至的、频繁的梦境,沦为一种写作刻意,以致逐渐丧失了其迷人的一面,使小说陷入虚假做作和说教的套路。这无疑是给所有的写作者提了个醒儿,也给所有的评刊员树立了坦率为文、真诚为文的榜样。他的《被岛吸引亦被禁锢》一文,体察了华海的中篇小说《江心岛》的精神隐喻,“在某种意义上仿佛一块试验田,或者这么一群人像堂吉诃德一样,奋力地抵御着来自物质世界的侵蚀,努力地维护着这片心灵净土”。
作为评刊团纳新的青年组的一员,李天奇的第一次线上评刊,就让人眼前一亮。他从《阿德拉商店的招牌》中的冷叙事里,剖析其魔幻现实主义的隐喻目的,他提出康坎小说“人性试炼场”的设定与“牢笼”说,梯子上与梯子下的阶级之分。他捡拾文字的碎片,洞察到地下世界某种危险的存在,以及人心的暗流涌动。他指出,那盏昏暗之灯,代表秩序、稳定和希望。当灯被打碎,即唯一的光明被打破时,“情绪积压的人们彻底失去秩序,从而制造出血腥的开始。蜡烛的出现,是一种对于秩序的挽救,但仅仅是理想,当秩序被彻底打破之时,微量的挽救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他完成的,是极其难得的小说的二次创作。他在肯定康坎小说独特的社会批判意义的同时,指出了其语言逻辑上的某些漏洞。眼明心亮的他,在王子健的小说《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游吟诗人》中,看到了另一个漫无边际的牢笼——沙漠。跋涉其上的人们,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毋庸置疑,他打开了评论的新视界。
青年组的另一位获奖者马行空,将对文学的热爱倾注到评刊当中。她的《无限的希望,与无尽的哀伤》一文,对张系国的短篇小说《蒙罕城故事二题》做了公允之评。她指出科幻题材多种元素相融汇的写作手法,以及两篇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出彩塑造,使文字闪耀的人性光芒,成为一种星星之火的点燃,“极大地推动了整座城市的人心向善”。她以审视的目光,提出对《一〇一忠狗》的质疑:律师小崔人物性格细节描写的前后矛盾,以及小说结构上的失衡。读罢方丽娜的长篇非虚构小说《到中国去》,她一口气写下了四篇“漂流瓶”系列评刊文,解读小人物的家国情怀、大爱与大义,表达了对小说重点刻画的犹太民族这一群体深重的历史苦难、复杂的生存尬境的悲悯,及对其演变为侵略者的深度焦虑。
十二位获奖者,十二组关键词,十二种评刊方式。一年里,我们喜迎“大匠来了”,细听“中国故事”,更是见证了罗淑欣、康坎、王子健、杜峤几位“超新星大爆炸”,我们关注“网生代”,醉心于“质感记录”,在“探索与发现”里增长史识,透过“海外华文”开阔视野,于“微篇精选”中感知小小说的魅力,在“大家手稿”中得遇名家手迹,凭“天下好诗”一览诗歌高地,我们从“评刊选粹”里,发现熟悉的名字。一年里,我们在云上,聆听《作品》公开课,接受周晓枫、杨无锐、吴昕孺、季亚娅、谢有顺、付如初、杨庆祥、付秀莹等名家文学审美之境的熏陶与洗礼。《作品》杂志打造的文学生态场域如此美好,如此生机勃勃,而每一次线上研讨的思想碰撞,都是点燃,都是照亮与温暖。评刊团里,洋溢的是青春之气息,青春之精神。
“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评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他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
米歇尔·福柯为我们描绘了理想中的批评的样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点燃,照亮与温暖。评刊团的我们,一起,在路上。
责编:周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