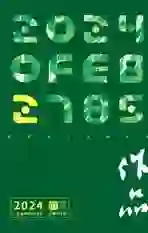隔帘唤住卖花声(专栏·文化岭南)
2024-03-19耿立
耿立
如果你有两块面包,你得用一块去换一朵水仙花。
——阿拉伯谚语
小引
旧时广州的花市白天有,夜间也有,男人簪花,女人插花,店铺有花,船上配花,夜晚的灯也成了花团锦簇的“灯球花”。大家东游西走,紧蹙街头,嚷嚷杂杂地,买些花束;家人友朋,挽手同游,更深了,夜半了,各自逶迤才散。
热闹了广州城。
满身花的清芬与星辰带回了家,花也看,人也看,快意了一个年节。
岭南人的赏花、爱花,是骨子里的活;广州人的爱花、赏花,是基因里的事。活着爱,不活了也爱。就像一种病。千年来,因了一种花,在这个城市,成了一个恒远的伟大陪伴:素馨,这是一个名词,更是一个动词,也是一个关乎花的形貌味道的定语,最后铺展成了花市花街:素馨花,才是始作俑者。
从根子上说,岭南不是素馨花的故乡,却把这千年的异乡,活成了离不开、抛不下的故乡。
对广州来说,上千年的市花是素馨花,而非现在的木棉。清代有一首清代《羊城竹枝词》写道:
珠女至今颜色好,一生衣食素馨花。
一、有花西来
一朵花,是因为迁徙还是贸易来到了岭南?因为美还是利?从海上,抑或是从陆路,跋山涉水,像肩负着使命,参与古老的东方民族美的构建,给他们的生活以荣华,以赏玩,在劳碌的日子里,稀释生活的沉重。
旧时的广州,是“通海夷道”,海外诸国大量珍奇源源不断地涌入广州,“货贝狎至。岭表奇货,道途不绝”。
唐段公路《北户录》记载:“耶悉弭花、白茉莉花(红者不香)皆波斯移植中夏,如毗尸沙金钱花也,本出外国,大同二年始来中土。今番禺士女多以缕贯花卖之。”
这段文字说明了素馨花来中土的具体时间。这里的“耶悉弭花”是个音译词,即素馨花来中土时原本的名字。嵇康的侄子嵇含在《南方草木状》中记载:“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陆贾在《南越行纪》中曰:“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缘自胡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
因异样的芳香与洁丽的颜色,耶悉弭改变了岭南的气质。但耶悉弭这个译词过于拗口,语素之间没有任何意义关联,读音和理解都不合乎汉人表达习惯。于是,等啊等啊,作为耶悉弭的素馨花,在等一个机缘,在等一个故事。
细花穿弱缕,盘向绿云鬟。(梁章隐)
分明削就梅花雪,谁在瑶台醉月明。(董嗣杲)
只向温柔乡里活,怕寒不許上林传。(郑域)
隔夜素馨厘戥秤,虽乃吾香念旧情。(佚名)
我越来越笃信,“名正则言顺,言正则事成,事成则礼乐兴”。在阅读史料的时候,发现“耶悉弭”罕见入诗入画,而将素馨一名一换,则风华绝代起来,好像成了精神致幻之药物,文人画士一朝服用,便再没有了免疫。
故事、美人、空间地点,三者皆备,给流传制造了势与能。在古人那里,不论什么物件,建筑也好,动植物也罢,他要有一种精神的仪式感、沧桑感,带来人的抒怀,带来人的感慨,或旷达,或飘逸,反正,这个物体给予人心境以影响,或有云,最好是个浪漫的故事,或者诗意的故事。
于是在宋诗里,我们就见到了番禺县尉在《南海百咏》之“花田”里的序和诗:
“在城西十里三角市。平田弥望,皆种素馨花,一名那悉茗。《南征录》云:‘刘氏时,美人死,葬骨于此。至今花香异于他处。”
千年玉骨掩尘沙,空有余妍剩此花。
何似原头美人草,樽前犹作舞腰斜。
这里面已隐隐透出故事的骨架了。
慢慢地,人们演义了一个关于素馨花的完整故事,慢慢地素馨花形成了一种户口的产业。《广东图说》还有这样的记载:“河南堡有庄头花市,为南汉花田故址。”庄头,南汉的花田,素馨花开时节,天地一白,古人以“弥望如雪”形容:“初夏之夜,开小白花,秋尽乃止,香味甚烈。”
老广州聊天,常会提起河南河北,但这不是指我们国家行政区划里的河南河北省,而是以珠江为界,珠江以南为河南,珠江以北为河北。在河南,现在的海珠区庄头公园的地方,原先叫庄头村,《觚剩》描述:“珠江南岸行六七里为庄头村,以艺素馨为业,多至一二百亩……花时珠悬玉照,数里一白。”相传这里是葬南汉宫女之地,《番禺志》说:“昔南汉宫人葬此,有美人喜簪素馨,殁后,遂多称之,名其冢曰:素馨斜。”
而民间的传说则是,南汉时期,庄头村这里有个美丽的种花女,名叫素馨,非常喜欢耶悉茗花。后来这姑娘被宣召入宫,深得南汉后主刘的喜爱。素馨去世后,被埋在故乡庄头村。后,庄头村的田地里长出了许多洁白的耶悉茗花,因此人们便把耶悉茗花叫作素馨花。而梁廷枏则说死者是宫女出身的妃子:“素馨,后主司花宫女,以色进御,封美人。性喜簪耶悉茗花,因名之素馨。”
父老乡间,三五月圆之夜,在庄头的田地里,墓穴旁,就隐约见这女子月下绰约的影子,还能听到她的浅笑低语。
于是这便成了文人雅士的素材、人们凭吊驻足打卡的地方。大家凭吊一番,唏嘘一番,放下一束素馨花,于是,情感有了依托物、抒怀点。至此,耶悉茗完成了身份的转换,素馨花成了被传诵、书写与流传的确切美。
花冢生花,多么浪漫的故事与想象。
关于素馨花的名字来源,还有一个版本,说是北宋时期的大理国,这个记载在清冯甦的《滇考》里:
(段)素兴年幼好佚游,广营宫室于东京,筑春登、云津二堤,分种黄白花,其上有绕道金棱、萦城银棱之目,每春月挟妓载酒,自玉案三泉,溯为九曲流觞,男女列坐,斗草簪花,以为时,有一花能遇歌则开,遇舞则动,素兴爱之,命美人盘髻为饰,因名素兴花,后又讹为素馨。
这个故事也够浪漫,花能遇歌则开,遇舞则动。但我对此是存疑的:大理国地处偏僻,哪有那么大的文化辐射,恐怕带动不了那么多文人雅士倾情而赋。庄头村的花田,那真实地理空间的花冢才惹人情思呢。
二、向“草语”致敬
我喜欢“草语”这样的名字。它让我们宁静,如同回到了自然,好像碰到了旧时的古人,看他们将生活与自然联手的情状,看他们与自然谐和同调且同行。那时人们循天时,狗守夜,鸡司晨。他们看黄昏,听虫鸣,人们的耳朵也生动,表情面孔也不乏味,明末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27这一章,他以“草语”为名,写了竹、芭蕉、朱蕉、蔗、兰、赛兰、菊、薏苡、素馨、蒌、西洋莲、秋海棠、凤尾花、凤仙花等七十二种岭南花草。现在的人,面对着妖娆草木,有几人能说出它们中多少种的名字?我们的祖先多么亲近自然,从《诗经》开始的多识草木鸟兽之名,这样对文人的要求,到后世诗词文章山水的摹写,在自然里,我们有了自己民族的诗的逻辑和体物美学。那时的文字和人,都是和大自然息息相通的,如近亲没有隔阂。屈大均在“草语”中,让我们看到了岭南的人、事、植物、动物,也听到了花语、鸟语、草语。
在《广东新语》里,屈大均给我们留下了素馨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完备的文字,我们既可把它当成一篇美文诵读,广见闻,增见识,更可觉察他对岭南家乡的拳拳爱意。我想把《素馨》这篇文字完整地立此存照,用眉批和评点的方式,穿插一些自己的解读和感慨来为这文字续貂:
珠江南岸,有村曰庄头、周里许,悉种素馨,亦曰花田。妇女率以昧爽往摘,以天未明,见花而不见叶。其稍白者,则是其日当开者也。既摘,覆以湿布,毋使见日,其己开者则置之。花客涉江买以归,列于九门。一时穿灯者、作串与璎珞者数百人,城内外买者万家,富者以斗斛,贫者以升,其量花若量珠然。(昧爽,明暗也,拂晓也,那时花农就起来做工,但在暗中,素馨的白,把她和叶子和夜隔开。旧时,人们多么喜欢用素馨来装点自己的日常啊。那些花客,渡江购花,素馨须插满头归)
花宜夜,乘夜乃开,上人头髻乃开,见月而益光艳,得人气而益馥。竟夕氤氲,至晓萎,犹有余味。怀之辟暑,吸之清肺气。予诗:“盛开宜酷暑,半吐在斜阳。绕髻人人艳,穿灯处处光。”花又宜作灯,雕玉镂冰,玲珑四照,游冶者以导车马。故杨用修云:粤中素馨灯,天下之至艳者。儿女以花蒸油取液,为面脂头泽,谓能长发润肌。或取蓓蕾,杂佳茗贮之,或带露置于瓶中,经一宿,以其水点茗,或作格悬系瓮口,离酒一指许,以纸封之。旬日而酒香彻,其为龙涎香饼香串者,治以素馨,则韵味愈远。隆冬花少曰雪花,摘经数日乃开,夏月花多,琼英狼藉,入夜满城如雪,触处皆香,信粤中之清丽物也。(素馨花,如昙花,但比昙花命久。这素馨也喜欢夜,在女子的头髻上才是自己最佳的表现,女子的发乌,这花洁白,互为映衬,互相成就。而夏日,素馨是避暑的佳物,是提神醒腦的良药,只消轻轻一吸。也适合做素馨花灯,可悬挂,可手提,如玉如冰,雕琢镂空,好玩之人有作车马照明之用的,既观赏又实用。这真是花灯,是夜色里人造的星辰;可取液润肤,可酿酒,可做饼。最妙者,冬日里,素馨也绽,给广府人造一场雪花;夏日更可造雪,入夜满城如雪,真是清凉一夏。我们可以想象,若是风起,那雪花,被吹起的那白色的萼片,如城市调皮的雀斑。)
庄头人以种素馨为业,其神为南汉美人,故采摘必以妇女,而彼中妇女多不簪戴。有咏者云:“花田女儿不爱花,萦丝结缕饷他家。贫者穿花富者戴,明珠十斛似泥沙。”可谓善言土俗也。语云:“珠浦之人以珠为饭,花田之人以花作衣。”是也。素馨本名那悉,亦名那悉茗。《志》称:“陆大夫得种西域,因说尉佗移至广南。”《南中行纪》云:“南越百花无香,惟素馨香特酷烈。”则素馨之名,在贾时已著。广南多花木,贾未尝言,惟言罗浮山桃、杨梅,及茉莉、素馨耳。素馨因陆大夫而有,今花田当祀陆大夫,以素馨为荐。犹梅岭之上,以梅花荐梅将军鋗也。花田者,陆大夫之汤沐也。(尉佗,即赵佗,是开发岭南第一人;而陆大夫,就是陆贾,曾给刘邦建言:“陛下能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他两次出使南越,让南越王赵佗放弃称王,归顺大汉。而这里说陆贾时已有素馨花,后被人考证是不确的。但后人还是不应忘记陆贾,岭南因他而避免刀兵,与中原兵不血刃而成为一体。因这,我们也要以素馨花的汤沐,洗去陆贾一生征尘与劳顿。)
东莞称素馨为河南花,以其生在珠江南岸之河南村也。儿女子以彩丝贯之,素馨与茉莉相间,以绕云髻,是曰花梳。以珠围髻,则曰珠掠。予诗:“珠掠盘明月,花梳间海棠。”
广中七七之夕,多为素馨花艇,游泛海珠及西濠、香浦。秋冬作火清醮,则千门万户皆挂素馨灯,结为鸾龙诸形。或作流苏,宝带葳蕤,间以朱槿以供神。或当宴会酒酣耳热之际,侍人出素馨球以献客。客闻寒香,而沉醉以醒,若冰雪之沃乎肝肠也。以挂复斗帐中,虽盛夏能除炎热,枕簟为之生凉。谚曰:“槟榔辟寒,素馨辟暑。”故粤人以二物为贵。献客者先以槟榔,次以素馨,素馨贵而茉莉贱,茉莉宜于女子,素馨宜于丈夫。(节日庆典或祭祀,要用到素馨,七夕节或者别的时日,广州人会装饰出素馨花灯,用以配合作醮,即祭祀鬼神。素馨花的香气非常独特,是为“寒香”,有很好的避暑及醒酒功效。“怀之辟暑,吸之清肺气。”“以挂复斗账中,虽盛夏能除炎热,枕簟为之生凉。谚曰:‘槟榔辟寒,素馨辟暑。”而当人醉酒时,素馨花就成了优雅的醒酒手段:“或当宴会酒酣耳熟之际,待人出素馨毬以献客。客闻寒香,而沉醉以醒。”如此醒酒的方法,被视为“冰雪之沃乎肝肠也”。今天,想想,都令人觉得,古时人们的生活才算生活,而我们,只是活着。)
广州有花渡头,在五羊门南岸。广州花贩,每日分载素馨至城,从此上舟,故名花渡头。花谓素馨也。花田亦止以素馨名也。盛平时,花多而价贱,十钱可得素馨升许,家有十余口簪戴皆足。今也人尽髡耏,花无所著,亦渐以稀少矣。诸花户皆贫,芜其花田而弗种,即种亦不蕃滋,盖时为之也。南人喜以花为饰,无分男女,有云髻之美者,必有素馨之围。在汉时已有此俗,故陆贾有“采缕穿花”之语。(花,有专用的码头,这也是世上的奇观;而花,在旧时的广州专指素馨,就像我老家山东菏泽或者河南洛阳,花,就专指牡丹。广州人对素馨已经有了情结,无分男女,素馨成了他们生活和精神的必须)
阅读屈大均先生的“草语”,我们知道了旧时广府人的生活是何等样式。世界那么大,可是真想穿越到那个时代,找几个朋友,喝酒赏花,或串个门,如此过上几日。那时的生活,多么的写意和接地气啊——人们与自然有着天然的亲近,他们如同一家人:人不仅仅是属于社会属于家庭,也属于山川河流,人的血液和草木的汁液都是同一的;而如今哪,我们在郊外或者荒野,能认识几个花木?能知道几种鸟?能辨别几种鸣虫的叫声?什么叫热爱生活?这是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
叶芝在《被偷走的孩子》里呼吁:
走吧,人间的孩子
与一个精灵手拉着手,走向荒野和河流
这世界哭声太多,你不懂。
三、袭人之香与花石纲
宋人尚雅。
宋朝大将潘美灭了南汉,广州的素馨花,也成了俘虏降臣,对宋家朝廷开始进行供奉了。
宋朝是偃武崇文的时代,执掌朝政的多是一些文学家、哲学家、诗人、画家。整个国家弥漫的是文艺范。
宋朝朝野崇花爱花,是一种时尚与生活方式。皇帝会在御宴赐花,花赐予近臣,得到花的大臣就有一种荣耀的资本。真宗时期,《渑水燕谈录》有记:“后曲宴宜春殿,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真宗顾文元及钱文僖各赐一朵。又尝侍宴,赐禁中名花。故事,惟亲王、宰臣即中使为插花,余皆自戴。上忽顾公,令内为戴花,观者荣之。”按人按级别赐不同颜色和品类的花。到徽宗时,赐花范围扩大到普通的驾侍卫。在春天三四月,徽宗巡幸金明池回宫时,此时俨然艺术家,艺术范十足:骑在马上,帽上插着花,像是一枝春天在招摇“御裹小帽,簪花,乘马,前后从驾臣僚、百司仪卫悉赐花”。
“为爱名花抵死狂。”历数陈抟、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王安石、陆游等人,都簪花、赏花、写花、种花、画花,乃至食花,甚至为花作花谱上户口。大家对花的品鉴,如现在的选美,取花如取友。他们说牡丹是贵客,兰花是幽客,桃花是妖客,石榴是村客,玫瑰属刺客,杏为艳客,而素馨,被评为韵客。牡丹因雍容,得一“贵”字;玫瑰有香,获一“刺”字;桃花之“妖”名,应滥觞于《诗经》对桃花风情的叙记。
素馨以韵字为前缀,人说“短笛无声,寒砧不韵”,而中华美学最讲的就是韵味。素馨的韵,我们可以理解为气质、气韵,也可理解为宁静、清逸,同时有着生命的律动。一个韵字太形象了,后人对宋朝的评价,也常常是把那独特的格调称为“宋韵”。
人们用列锦的方式,来形容居家日常: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物质的层面。而精神的则是:琴棋书画诗酒花。
宋人是把日常的物质与精神杂糅在一起的。他们痛饮花前、赏花、花前学唱、花种作诗、簪花、花容、题花、佩花、花朝、寄花、花市、花妆、卖花、嗅花、惜花、买花、醉花、献花、品花、浴花、赠花、种花、插花、折花、餐花、花信等等,不一而足。
我喜欢这样的场景:“天津帐饮凌云客,花市行歌绝代人。”凌云客,多么熟悉的酒友啊,我们喝高了不是身边就有吗?不喝的时候,我们在云彩下面;喝高了,云彩在我们下面。绝代人是谁?不知道,但我们觉得,在花市敢高歌一曲的,那一定有羞花之貌。我喜欢这个歌者,对着花,相看妩媚。
“头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这是以酒为镜子啊!酒杯里有一枝花,这枝花簪在头上。在宋朝,无论男女,无论节日、婚丧嫁娶,甚至是刽子手犯人,在监狱在杀人的刑场,都有花的角色在。
苏轼喜簪花,黄庭坚也喜欢簪花。陆游有“意适簪花舞,身轻拾杖行”。簪花,预示着好的兆头。辛弃疾在《柳梢青和范先之席上赋牡丹》言:“今夜簪花,他年第一玉殿东头。”韩琦喜簪花,《墨客挥犀》中载“魏公开宴,召三人者同赏。时王禹玉作监郡,王荆公为幕官,陈秀公初授卫尉寺丞,为过客,其后四人皆相继登台辅,盖花瑞也”。
相传韩琦在任扬州太守时,得到了一盆芍药花,其中四朵芍药花出现金边。韩琦便找来王安石、王珪和陈升,一同簪戴,后来四个人先后都做了宰相。
《钱塘遗事》载:“御宴赐花,都人叹美,三荣也。”登科之后,皇帝亲自赐花,这样的考生待遇,真的是像花朵如乘春风,得意春风。
最奇异的是南宋“绍兴间,汉阳军有插榴枝于石隙,秀茂成阴,岁有花实者”。这个故事原本讲的是,一个妇人被人诬陷,不能自明,便嘱托行刑者将头上簪戴的花插入石缝中,若是生根发芽,便能自证冤屈。
甚至赦免囚犯出狱,狱卒也要为囚犯成为自由人簪花,《梦粱录·卷五》中记载:“衣褐衣,荷花枷,以狱卒簪花跪伏门下,传旨释放。”
《水浒传》有许多的梁山好汉常簪花:浪子燕青“鬓边常插四季花”;小霸王周通“斜插一枝羅帛象生花”;病关索杨雄“鬓边爱插翠芙蓉”;短命二郎阮小五“鬓边插一朵石榴花”;而刽子手的名号就是一枝花蔡庆,他是在花枝乱颤中挥刀而去人的首级。
宋朝,即使是这些江湖人士,也是活得活色生香啊。
在宋朝,使素馨花大放异彩的是因它的香。那时人们认为飘着异香的素馨,才是花中魁首。人们把素馨和茉莉看作同一类花木,而广州是宋朝的制香中心,面积广博的岭南泛种素馨花(也叫大花茉莉)与茉莉花(小花茉莉或双瓣茉莉),为制香提供了充足材料。宋代的香坊品牌中,最知名的是广州的“番禺吴家”。其核心招牌就是“心字香”,制作的工艺就是先把多种香料合成小香饼,然后与刚采摘的素馨花一起密封,将香饼与素馨花放在同一个容器里,熏制一夜;第二天,换上新花,继续密封。在制作期内,素馨花与茉莉花相互交替。这样整整一个花季,回环往复,心字香就做成了,就有素馨花与茉莉花两种花香的香饼。
蒋捷的“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筝调,心字香烧”中,燃心字香,即是当时宋人的日常。焚香调琴,赏花宴客,独居幽处,月下独酌,自是少不了香的存在。杨万里一首《烧香诗》,记录了一次真实的焚香在场:
诗人自炷古龙涎,但令有香不见烟。
素馨欲开茉莉拆,低处龙麝和沉檀。
一枚小小的“古龙涎”香饼,衬在银叶做的隔火片上,由炉中炭火微烤,便开始幽芳暗生。在复合的香气中,首先隐约可辨的,是素馨花的气息,然后,似乎有茉莉花在房室中悄然开放。
像当时的所有士大夫一样,杨万里把焚香当作最高雅的审美享受,因此,他亲手在炉中焚炷了一枚“古龙涎”香饼。
“古龙涎”在宋代,实际是各类高档人工合成香料的一个通称。“素馨欲开茉莉拆,低处龙麝和沉檀”,恰恰写出了宋代上等合成香料的原料之奢侈,更写出了这些香料在香气层次上的丰富——素馨花构成了香芬的前调,中调是茉莉花香,尾调则以天然沉香、檀香为主打,但混合有少量龙脑、麝香。
在宋代,作为香花中第一佳品的素馨花,在生活中随处可见。郑刚中有诗云:“素馨玉洁小窗前,采采轻花置枕边。仿佛梦回何所似,深灰慢火养龙涎。”素馨花放在枕边,午夜梦回,花香袅然,正如在香炉中焚炷龙涎香饼一般美妙。
茉莉花和素馨花同属于木樨科(Oleaceae)素馨属(Jasminum),在生活中,有时人们就把它们统称为“茉莉”,有时则以“茉莉”与“素馨茉莉”加以区分。现在我们最熟悉的所谓的“茉莉”,是茉莉花茶中的小花茉莉。
而现在西方香水中,调香师运用的“茉莉”则是素馨茉莉,也叫大花茉莉。就是我们说的“素馨花”。
因为素馨花的地位,于是乎,在宋朝,特别是宋末年,素馨就成为有艺术气质的徽宗的宫廷消费里的重要花卉。崇宁四年,宋徽宗设立应奉局、造作局等机构,专事搜罗南方地区的奇花异石。在皇家园林中,大量南方木成为宫廷的消费品。当时的艮岳有所谓的“八草”,即“金蛾、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茉莉素馨均占其中。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写琼林苑:“苑之东南隅,政和间创筑华觜冈,高数丈,上有横观层楼,金碧相射,下有锦石缠道,宝砌池塘,柳锁虹桥,花萦凤舸,其花皆素馨、末莉、山丹、瑞香、含笑、射香等闽、广、二浙所进南花。”
那时京城汴梁的皇家园林里,开始把广东的花大量引进,就像现代北方的热带植物园。
而到了南宋,《武林旧事》记载,那时夏天炎热,“禁中避暑,多御复古、选德等殿,及翠寒堂纳凉……又置茉莉、素馨、建兰、麝香藤、朱槿、玉桂、红蕉、阇婆、簷葡等南花数百盆于广庭,鼓以风轮,清芬满殿”。这才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是啊,《水浒传》写了北宋的大乱,是始于宋徽宗的花石纲。所谓的花石纲,就是把南方的奇石与花木运送到京城,十只船为一纲。运送到东京汴梁,就是为徽宗建造园林,花木之奇异者,尽移供禁御,岭南自古多舶来之奇花异草,为中原所罕见。徽宗是个艺术家,这样的人治国,以自己的爱好和性子来,最后,因为花石纲天怒人怨,民怨沸腾,国力衰竭,最后靖康年,徽宗被金人掠走,留下了历史的笑柄。
花也何辜?素馨也何辜?宋陈宓《素馨茉莉》有“移根若向清都植,应忆当年瘴雨乡”的句子,这是写素馨背离乡土的乡愁吗?一朵花,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花香袭人,有谁知道它远抛乡土,漂流江海,来到中原,遭遇到了亡国之痛?
四、沿街都是卖花声
从宋代始,到明清,广州的大街小巷有了素馨花的叫卖声。黎明时刻,广州城门一开,首先涌入城市的是那些花农花贩,他们凑着花的新鲜,叮叮当当地进来讨生活。
他们从河南庄田撑船而来。而素馨花是需夜半开始采,才不耽误五更天在珠江上的码头装船。夜色里,莹白的素馨,如天上的星宿映在江上,那些花农们,不知船在水里,还是天上,只是觉得星光与花不可分辨。
我们在前面向“草语”的致敬里,有这样的一节:“广州有花渡头,在五羊门南岸。广州花贩,每日分载素馨至城,从此上舟,故名花渡頭。花谓素馨也。花田亦止以素馨名也。”那些花贩通过珠江把花运到城外,然后用担子一担担挑到大南门、归德门、小南门、正东门、正西门、大北门、小北门。若是来早了,就等城门开门,伴着馨香与星光与期待。“花客涉江买(花)以归,列于九门”,那城门就成了花市。当时有人形容“望通衢之凝雪,列七门而成市”。清代有很多的竹枝词写当时素馨花从花田到码头的繁忙:
“素馨花放近清和,花渡头前唤渡河。”
“入港索尝番舶酒,渡江齐贩素馨花。”
“花奴花叟各奔波,齐集花圩撑过河。
那些素馨花贩们,有在江上卖的,有沿街叫卖的,也有在固定地点卖花的:
“河头花郎惯卖花,河尾女儿常采茶。
谁道河南少风景,半为香国半农家。”
“素馨花贩担头轻,一路香风送入城。”
“担到七门花市去,卖花花债债无多。”
因素馨花而逐渐形成了花市,一天广州城的素馨花消费,就卖出不下数百担。这个数字是十分吓人的。通过素馨花的这个销售数据,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广州的繁华。人们形容,当时“生民之凑集如云,财货之积聚满市”。嘉靖年间,传教士费尔南·门德斯·平托在《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中写道:“(广州)城里的统治官员命令调查每日的食品消耗量,结论是光是猪肉就要五六千头,要不是有很多人吃黄牛肉、水牛肉、鸡及大量的鱼,猪的消耗量将达一万或一万头以上。”哈哈,明朝的广州城里的人,不尽是食肉者鄙,还有那么多的素馨来装扮生活。
“素馨花贩担头轻,一路春风送入城。蝉鬓晓状梳未毕,隔帘唤住卖花声。”
在一个城市里,在黄牛肉、水牛肉外,隔帘传来的卖花声,则是对心灵的一种按摩,一种诗意,一种对生活的润泽。
我觉得一个城市的韵味,是和各种市声分不开的。市声是一个城市的体温;而一个城市的韵味,是和卖花声分不开的。卖花声是一种市声。《东京梦华录》卷七《驾回仪卫》条这样记载宋朝时候的开封:
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
暮春时节,开封的大小街巷,各色鲜花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在这些热闹之上的是歌叫之声,与花相互映发。有时我看《清明上河图》,好像隐隐约约地,有叫卖声从画面中迤迤然荡漾而出。
明人陈继儒在《小窗幽记》里说,人的耳朵接受的自然和人世的声音,是有区别的。那谁是第一呢?他是按文人雅士的趣味分别的,不是市声,但我们无妨一观。我是心喜他把卖花声推为第一:“论声之韵者,曰溪声、涧声、竹声、松声、山禽声、幽壑声、芭蕉雨声、落花声,皆天地之清籁,诗坛之鼓吹也。然销魂之听,当以卖花声为第一。”
当以卖花声为第一。
是啊,在清晨的睡梦中,耳朵里就有了卖花声,可证时代安稳。陆游曾写有《临安春雨初霁》一诗,其中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最被人传诵。想必,当时的广州文人,听到素馨花的叫卖声,脑子里闪现的,一定是陆游这千古不朽的句子吧。
因为素馨花数百年地养护广州人的生活与心灵,于是,在那没有素馨花的季节,广州人也离不开了花。更因此,就形成了稳定的花市。人们像逛街买日常东西一样,就有了逛花市的习俗。那花市是四季,而不是后来的仅只春节。炎夏时节的花市,“在藩署前,灯月光辉,花香袭人,炎歊夜尤称丽景”。
夜间的花市,潘贞敏《佩韦斋诗钞》一书中,“花市歌小序”也记载了藩署前花市游人甚多的景象:“粤省藩署前,夜有花市,游人如蚁,至彻旦。”此时的花市,已由城门市场扩展到了城内的“藩署前”。再后来,又逐渐向南延伸,由“藩署前花市”发展至“双门底花市”(双门底曾经是旧广州的城市中轴线,十分繁华。现今已更名为“北京路”)。
春节的花市,张心泰在《粤游小志》中记载:“每届年暮,广州城内双门底卖吊钟花与仙花市,如云如霞,大家小户,售供座几,以娱岁华。”《浮生六记》里记载沈复在旧历年的春节到广州,曾记载:“十三洋行在幽兰门之西,结构与洋画同。对渡名花地,花木甚繁,广州卖花处也。余自以为无花不识,至此仅识十之六七,询其名有《群芳谱》所未载者,或土音之不同钦?”
看看这些史料,我们想见数百年前的这座伟大的城池,多少人和花,奔赴而来。借用柳永的《望海潮》,直把杭州作广州:“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这望海潮,可以置换珠江潮,“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不应置换;“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不应置换。“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可以置换成素馨、茉莉、木棉、榕树。
一个城市,就是一种生活;一个城市选择了一朵花,就选择了四季和花互动,就成就了一种生活的滋味和高度。
奔赴一个城市,即是奔赴一种生活。
五、下广去,吾家乡
我的故乡是中原地带的菏泽。中华民国以前称菏泽为曹州,明清时“曹州牡丹甲于海内”。明人谢肇淛在其《五杂俎》中记载,他曾路过曹州一带,“百里之中,香风送鼻,盖家家圃畦中俱植之,若蔬菜然”。又曾在曹州一诸生家观赏牡丹,见“园可五十余亩,花遍其中,亭榭之外,几无尺寸隙地,一望云锦,五色夺目”。《曹州牡丹谱》载:“曹州园户种花,如中黍粟,动以顷计,东郭二十里,盖连畦接畛也。”
确实,即使到了现在,我的家乡种植牡丹,就像种菜一样。也就是在明清时,曹州的牡丹就开始卖到广州,每到北方的秋深季节,推着红车子,每辆车子上,用铺草包连着土和牡丹植株,从黄河边,过淮河、长江,到珠江,然后在广州的郊外住下来,把牡丹栽在花地里,等春节前,那牡丹就开了。这样就卖个好价钱。
牡丹雍容华贵,象征着富贵吉祥。刘禹锡有诗句《赏牡丹》:“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李正封《牡丹诗》则云:“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皮日休《牡丹》诗云:“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自唐宋起,牡丹就有“国色天香”、“花中之王”(“花王”)的美誉。到了明代,牡丹被明确称作“国花”,李梦阳《牡丹盛开,群友来看》诗云:“碧草春风筵席罢,何人道有国花存。”邵经济《柳亭赏牡丹,和弘兄韵》咏道:“自信国花来绝代,漫凭池草得新联。”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里葛巾、玉版的故事即是关于曹州牡丹的。洛阳人常大用与其弟曹大器,与曹州牡丹所化的仙子葛巾、玉版产生了一段缠绵悱恻的爱。常大用本来自以牡丹著称的洛阳,却倾慕曹州牡丹,而流连不归。光绪《菏泽县乡土志》记载,牡丹“种色甚多,亦为本境出产大宗,……每年土人运外销售甚夥”,而牡丹商则“每年秋分后,将花捆载为包,每包六十株,北赴京津,南浮闽粤,多则三万株,少亦不下两万株,共计得值约有万金之谱”。
牡丹是讲究严格的气候条件的,王桢《农书》说九州之内,田各有等,土各有差;山川阻隔,风气不同,凡物之种,各有所宜;故宜于冀、兖者,不可以青、徐论;宜于荆、扬者,不可以雍、豫拟,此圣人所谓“分地之利”者也。
牡丹的花季,是每年的谷雨前后。每种植物,都有它特定需要的自然环境。在明朝的冬天,在北京就可看到盛开的牡丹,谢肇淛《五杂俎》:“今朝廷进御,常有不时之花,然皆藏土窖中,四周以火逼之,故隆冬时即有牡丹花。”刘侗《帝京景物略》:“草桥惟冬花支尽三季之种,坏土窖藏之,蕴火坑晅之。十月中旬,牡丹已进御矣。”
说白了,就是在土窖里,用火加温,制造春天的氛围。而广州的春节牡丹花开,则是源于我家乡花农的一次偶然。
2023年暑期,我回到了家乡菏泽,采访一些老花农,他们给我说出了“下广”参加广州花市的偶然。在明朝的时候,秋分后,曹州的花农就开始离家,到一些大的城市去卖牡丹。买花者多是一些大户人家,为求富贵的意头,买些牡丹栽种在花园里,以待明年牡丹花开。这些花农有时在徐州卖掉几棵,有时在南京卖掉几棵。当时花农的手推紅车子上,一般会载有60棵牡丹,什么时候卖完,什么时候就返回故乡。
有个曹州的赵氏花农,他的红车子上的牡丹,走到长沙,才卖掉30棵。于是他就推着红车子继续往南,翻大庾岭走梅关古道,走到大庾岭的时候,就接近了腊月,那时,大庾岭的梅花开了,这个赵氏花农红车子上的30棵牡丹,好像受到了启迪,也发芽了,长出了新叶,牡丹的花朵开始膨胀。
赵氏花农一路晓行夜宿,天天看着自己红车子上的牡丹,一天一个样,花朵一天天大起来,饱满起来。
赵氏花农越往南,身上的衣服就越脱越少,好像是中原的春天的天气。等他腊月二十走到广州的时候,他的一车子的牡丹,全部绽开了。那是曹州牡丹最喜庆的几个品种:胡红牡丹的肉红色,就如春节的对联的颜色,花大如盈尺,多层重瓣的如楼子;还有玉牡丹,那含着的花苞是浅绿的,而绽开的则是洁如玉色;更有名品姚黄牡丹,有的鹅黄,有的金黄,如金箔镂成,金衣曳地,金冠照云。
那时的广州,就像冬天没有见过雪花,他们更是没有见过这腊月的牡丹。这一下,是牡丹花开动广府。人们好像回到了唐朝的长安、宋朝的洛阳,大家在广州也能看到李白、杨玉环、欧阳修、苏轼等人看到过的牡丹。
那第一下广的牡丹,成了一个传奇。在广州的花市上,是按花骨朵和花头算银子的,一两银子一个花骨朵,一棵牡丹上有10个花头,就是10两,有8个花头,就是8两。
赵氏花农的牡丹,一天被人抢买一空。30棵从曹州来的牡丹,一共500多个花头。当他正月十五那天赶回曹州赵楼自己的家时,一进家,把院门关上,招呼家里人把屋门也关上,在家里的地上,他摆出了白花花的500多两银子。《明史》里记载,一个七品县令一年的俸禄是45两白银。
我这次暑期采访,听那些花农说,下一次广,置办家里的一个过活。这是方言,意思是到广州春节的花市上,卖一次牡丹,可以吃一辈子。
这年春天,赵氏花农买了两顷地,买了几头牛,盖了青砖到顶的瓦房。
从明到清,从清到民国,从民国到现代,我家乡的牡丹,都是广府花市上最抢手的花卉。
我到广东后,每年的春节前,都会收到家乡邮寄的牡丹。在去年的祭灶时候,我收到了家乡的牡丹,打开顺丰邮递的特殊的包装,那是两盆有几十个花头的牡丹。腊月二十三,北方的祭灶日,而岭南祭灶则在腊月二十四。那是紫红的“紫二乔”牡丹,花香馥郁,一下子整个房间和日子,都有了古意和吉庆。我写下了一段文字,在朋友圈:
她在腊月里长出翅膀/在天空里长出了翅膀/她陪我今天祭灶一次/按菏泽老家的规矩/她陪我明天祭灶一次/按岭南珠海的规矩//
她和我一样/也是性急的人/等不到珠海就把颜色/把层次在路上/打开/性急就性急吧,打开就打开吧。/她就是早早地把爱藏不住/或是路上/就让风给珠海传话:我来了/快接驾。//
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之上。这诗意,一定是和花朵有关。
六、走花街
一朵花的长度,丈量了魏晋,丈量了南北朝、唐宋、元明,一直到清再到民国。这素馨花,却在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有它而起的临近春节的花市花街,却是它播下的种子,形成了风俗,规定着人们的春节。张心泰撰《粤海小识》云:“每届年暮,广州城内卖吊钟花与水仙花成市,如云如霞,大家小户,售供坐几,以娱岁华。”说这是晚清的时候。分散的花市就开始固定在春节前,光绪年间《羊城竹枝词》写广州的花市:“羊城世界本花市,更买鲜花度年华。除夕案头齐供养,香风吹暖到人家。”
于是,逛花街,就成了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好像只有花的芬芳才是春节和春天的序曲。
我觉得,这千年形成的这种城市的审美,具有画家之眼,也有玲珑之心。春节了,把花请到家里,除掉一部分物质装点价值之外,还具有滋养愉悦的精神价值。
我们从素馨花千年的美学和长度和它的衍生里,发现了广府的历史;也在广州人与它千年耳鬓厮磨的生活中,发现了恒久的传奇。
现在的都市,越来越远离了自然,人们被钢筋水泥囚禁在狭小的空间里,再也没有了落日的记忆、虫鸣的低吟。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的“前言”中说:“现在我们面临着是否以舍弃自然的、野生的、自由的东西为代价,而求得一个更高的‘生活标准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些少数人来说,看雁群的机会比看电视的机会更重要,而寻找铁线海棠的机遇,就像言论自由一样是不可剥夺的权利。”
广东人过年,比北方我的故乡讲究。有一年,我在贴好春联时,环顾邻居家的门头,却比我家内容丰富。他们不只春联,还用红绳挂着红萝卜、香茅、芹菜、橘子,且都是成双的;门前备有几炷香,虽是楼房,仍觉出岭南文化里的扬扬古风。
“年卅晚,行花街;迎春花放满街排;朵朵红花鲜,朵朵黄花大;千朵万朵睇唔哂……”这是童谣,粤语说“唔行花街唔算过年”,年年我也到花市挤一挤,作为一个新客家人,也算过了一下老广的年。在花市,看到了曹州牡丹,一见,如对故人,如沐春风,枝枝善眼。
大家从花市把万紫千红带回家中,就如占领了春天,解放了愁苦。这广府春节前的花街上的那些颜色,就是给这土地和人,颁发的万紫千红的绶带。他们万紫千红的日子来了。
我喜欢到花街上,逛个半天一天的。它使我重回自然的怀抱,沉浸其中,我像接通了与土地的联系。我信服爱默生“自然是精神之象征”的话。他告诫人们,“无论在城市的喧哗声中,还是在政治的争吵声中,都不应当完全忘记大自然的教诲”。
不管你处在什么年龄,虽然春节正是冬季,但花市和花街对应的是春天,对应的是人的童年和青年,冬季并不是肃杀,在这个广府的冬季,一样阳光明媚,一样的鲜花盛开。
我觉得,这是千年形成的广州的气质。这样的春节,可看,可闻,可嗅,可触,可摸,可听。
花市,是自然的聚会;花街,是人对未来希望的集合。就如人需要定期聚会,花也如此。花的盛会和人的春节碰到了一起,有了那绿的枝叶、黄的花朵、金的蓓蕾,我忽然觉得,对一个人和一个城市来说美是一种神魄而并非装饰。
有一年,我逛花市,看到一位长者抱着一盆桃花归去,有桃花,一室春气,夭夭灼灼,灿如涂霞。我觉得这里面有无穷的内涵,是为孩子祈福爱情,还是装点自己的金婚银婚,反正在这个春节,桃花开了。
大家把花市的芬芳搬到了家里,不仅给日子镶嵌起了花边和惊喜,也使这个正月、这条街道、这个社区,有了甘美。一年的辛苦,人们与一个一个的日子悲欣与共。这些花朵,一下子使我们找到了辉煌,接近了辉煌。
尾声
泰戈尔在《新月集》里有一篇“第一次手捧素馨花”,我觉得十分契合此文的主题:
啊,这些素馨花,这些白色的素馨花!
我仿佛还记得我第一次双手捧满这些素馨花,这些白色素馨花的景象。
我爱阳光,爱天空和苍翠大地;
我听见河流在子夜黑暗里汩汩流动的声音;
秋天的夕阳,在寂寥荒原上大路转弯处迎接我,像新娘撩起面纱迎接她的新郎。
然而我是个孩子时第一次双手捧满白色的素馨花,回忆起来依旧是甜蜜的。
我生平有过许多快乐的日子,节日之夜我曾同逗乐的人一起哈哈大笑。
雨天灰暗的早晨,我曾低吟过许多闲适的诗歌。
我颈子上还戴过情人亲手用醉话编织的黄昏花环。
然而,回忆起我是个孩子时第一次双手捧满新鲜的素馨花,我的心里依旧是感觉甜蜜的。
是啊,素馨花,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异国,它是那么地被人追捧,而这一朵,和这个城市有着千年的、共同的、纠缠记忆的花,虽然它有点衰落,有点退隐,我觉得是功成身退的谦逊,它曾陪伴我们的祖先,荣枯与之,它守望着这个城市的灵魂。素馨花,曾是千年来这个城市的日常,它给了这个城市在日常生活里的意义,使生活有了滋味,它守护着日常社会,但这日常并没有束缚这个城市的想象与诗情,而是让这个城市的生活不再粗鄙。
还是以塞菲里斯的三行诗来结束这篇文字吧。
天黑也好
天亮也好
素馨花永遠是洁白的
责编:鄞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