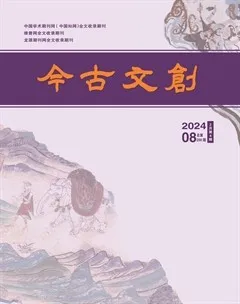秦汉时期特殊地方行政制度初探
2024-03-11付少聪
【摘要】道是秦汉时期与县平级的行政区划,也是中国最早的特殊地方行政制度,其在两汉时期逐步消亡。初郡制度创设于汉武帝时期,也属于特殊地方行政制度范畴。东汉成帝年间,属国制度进一步发展成为比郡属国,比郡属国与道性质相同,皆属特殊地方行政制度。初郡制度创设于汉武帝时期,也属于特殊地方行政制度范畴。秦汉时期道、初郡、比郡屬国的设置,使得特殊地方行政制度呈现出多元建构与一体进程两种态势,也从侧面反映出秦汉时期边疆地区治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关键词】秦汉;道;初郡;比郡属国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8-007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8.021
春秋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发展,郡县制度随之渐趋完善。秦灭六国之后,郡县制于全国施行,但战国秦国以至秦代,皆在部分边疆地区设立与县平级的特殊行政区划“道”进行管理。周振鹤将“道”此类行政区划称之为特殊行政制度。[1]对于国土的不同地区实施不同制度,其思想滥觞于先秦时期,如《禹贡》载“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緫,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2]这种描述以理想化的圈层结构将疆域划分为“天子之国—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而且明确了各服的贡赋责任,且由其不同表现天子之国政治控制力在空间上的不断衰减。[3]春秋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发展,这种政治控制力在空间上的衰减也必须在统治层次上有所反映,体现在地方行政制度上,就是特殊地方行政制度,对于秦国而言,就是道制。初郡制度创设于汉武帝时期,也属于特殊地方行政制度范畴。西汉时期,属国制度发生新的变化,并在东汉时期逐渐演变为比郡属国,成为郡一级的行政区划。本文希冀通过梳理秦汉时期道、初郡、比郡属国的设置情况,并对三种行政区划进行分析,从而一窥这一阶段特殊行政制度的发展趋势以及其典型特征。
一、道的数量变化与设置起止
道出现于战国中晚期的秦国,其与县平级,通常设置在边疆地区。道制一直延续至两汉,在三国西晋时期逐渐消亡。大抵西周尚为宗法封建时代,无地方行政制度之可言。[4]地方行政制度伴随着中央集权强化而诞生,而道制作为地方行政制度的特殊化产物同时产生。对于道制的研究而言,传世文献中史料价值最高的是《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这两份史料所记载的郡县表具有系统性,是其他传世材料很难替代的,对于复原两汉政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考古资料中最重要乃是张家山汉简中的《二年律令·秩律》,《秩律》提供一份系统的县道表,资料的系统性对于政区还原以及相关研究起决定作用,而其他不能提供系统性政区建置的文献能对上述文献起到补证作用。对于上述这三份文献,先行学者已进行充分而系统的利用和研究。其中《秩律》所载政区的断代为吕后元年,载录23道;[5]《汉志》所载政区的断代为成帝元延绥和间,[6]载录30道;《续汉志》所载政区的断代为顺帝永和五年前后,[7]载录19道。对于秦道的设置,马梦龙考证得出确定无疑的十二道,并推断以秦代道的总数大约在12—20之间,不会超过20个。[8]基于先行学者的研究可知,四个不同时期道的数量,从而时间上连贯起来,清楚看到秦汉时期道的数量变化。综上所述,秦代道的数量大概在十二到二十之间,随着时间推移,到了西汉吕后时期,道的数量有所增加,总数达到二十三道;再到西汉成帝时期,道的数量又继续增加,总数达到三十道;最后到东汉顺帝时期,道的数量又减少到总数十九道。道的数量总体来说,在秦西汉时期呈上升趋势,西汉末年到东汉时期道的数量呈下降趋势,因此道制的广泛设立应该在西汉后期。
以往限于传世文献对于道的记载稀缺,学界对于道的研究不够深入,且多为推断。马梦龙利用近三十年发现的出土文献,对秦汉“道”政区演变进行分析,考证严谨,其主要结论有:一、秦国为了应对伐灭义渠国、大量内附游牧民族需要进行管理的局面,创立了道制;二、道的数量在西汉初增加且有了令长的秩等区分,到成帝时继续增加,东汉时期减少;三、国家会灵活采用道制或县制对边疆民族进行管理,所以秦汉时代常有县、道相互转化的现象;四、从地域分布来说,西汉初年仍然延续秦代置道的基本方针,《汉旧仪》“内郡为县,三边为道”的地域格局是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的状况,汉武帝不再于新开拓地区置道。[9]在东汉之后,道作为特殊行政区划消失,旧道皆转称为县。对于这点而言,张悼已经指出:三国西晋时,残存的狄道,连道、故道等都被直呼为县了。[10]从东汉以后,道不再作为一种特殊行政区划的专名,而是成为称呼县的行政区划的通名中的一部分。总而言之,作为特殊行政制度的道制从秦代到西汉,道制成熟且设置较多,西汉到东汉开始,道的数量减少,逐步走向消亡,并在三国西晋时期结束。以政区地理角度考察,行政区划有四个要素,一是层次,二是幅员,三是边界,四是行政管理中心。[11]郡县制下的汉道无疑满足这四个条件,秦道是否诞生在郡县体制之下还需具体分析。县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秦在孝公之时已是郡县之县了。[12]秦与义渠国大规模作战至灭义渠国皆在秦惠文王,那么道一开始就属郡县制内涵之中。道与县同属于一级行政区划,在郡县制诞生之初,便已是郡县制的一部分。道与县共同构成了秦汉时期的县级政区,对于边疆地区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初郡制度的来源、性质
汉武帝统一岭南及西南地区后,设置“初郡”进行管辖,“初郡”作为一种新的模式与常态的郡有显著的区别。对于“初郡”的考证,刘瑞认为十七初郡当为越地苍梧、合浦、郁林、象郡、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西南夷牂柯、武都、越雟、零陵、沈黎、汶山、犍为、益州等八郡。[13]“初郡”最主要的特点是所施行的法律并不同于汉郡,而是“以其故俗治”,而且其并不与汉郡百姓征收同样的赋税和徭役,而且初郡内部的主要军事长官为本地酋长。这些显著特征是初郡与汉郡的主要区别。初郡虽然和汉郡有着显著的差别,但其满足行政区划的所有条件,也是正式的政区,但其又不同于汉郡。
汉武帝所开初郡皆位于南方新拓之地,是一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一种政区设置,并没有超出郡县制的框架。初郡制度实行地区经济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贸然使用汉郡制度而不加变通并不符合时宜,因此对郡县制进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变通的初郡制度应运而生,初郡制度对于稳定岭南及西南地区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初郡政策有利于南方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对汉朝初郡地区政治统治的稳定做出贡献,使得南方边地与中原地区联系加强,促进了初郡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而且这种政策常以其他形式被后世大一统王朝所继承沿用,对于维护边疆地区地方治安、巩固统治发挥重要作用。到了东汉时期,初郡制度逐渐失去活力,初郡地区与汉郡地区的差别减少,初郡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三、比郡属国制度的来源、性质
比郡属国的来源远复杂于道制,其存在两个阶段化的发展特征。比郡属国不同于道制,其一开始并不属于行政区划的一类,比郡属国的前身为属国制度,从属国制度经过长时期的演变才转化为比郡属国。首先,秦属邦是汉属国的前身,避高祖讳才改为属国,秦属邦由典属邦管理,汉改其为典属国;[14]其次,目前可考的秦的属邦只有蜀属邦。[15]属国制度是比郡属国的制度源泉。汉武帝元狩三年新置属国都尉,于是在属国内部有了两套行政体制,一为属国都尉及其下属的流官,这是汉廷派遣进行治理的主体;二为属国部众的原有社会政治体制,大多为部落制度。在这两种体制当中,属国都尉及其属官起主导作用。随着属国民众逐渐定居,属国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差距的缩小,使得属国逐渐地方化,向地方行政体系转变,终于,东汉安帝时属国都尉比郡治民,也就是“比郡属国”。比郡属国演变成了正式的行政区划,但其所处地区与中原地区不同,行政管理仍有差别,属于特殊行政制度,与初郡和道的性质相同。三国时期犍为属国改置为朱提郡,比郡属国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汉武帝置属国,是西汉广置属国的开始,置属国都尉也给与属国制度新的内涵。汉武帝时期的属国并不能满足行政区划的完整要素,仅仅是作为一种特殊管理制度存在。首先,从幅员和边界上分析,武帝时所增设的属国都尉统领下的属国是一种军事性组织[16],河西五属国所安置是匈奴降众,其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很难有确定的幅员和边界,黎明钊、唐俊峰也指出:降附的游牧外族被纳入属国体系统治后,虽然还保留原来的部族、文化,但因为居住地的改变,生活空间大大缩小,迫使部分族群不得不逐渐放弃原来游牧的生活方式,开始定居。[17]但是这种转变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时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其次,《汉书·百官志》中,县、道、国、邑并列,这是对其同属县级政区的说明,而属国都尉附属于典属国,其与郡、县并不构成上下从属关系,这一点说明至少西汉成帝元延绥和年间属国还不是一级行政区划,而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管理制度;最后,《汉志》中属国都尉有其治所,但农都尉、骑都尉也有其治所,这并不能说明其属于行政区划,行政管理中心不是判断是否为行政区划的唯一标准。所以,从初置属国都尉到其“治民比郡”这个时间段内,部分属国可能已经事实上拥有幅员、边界及行政管理中心三个要素,但必须要到其“治民比郡”时拥有层级要素,才完全符合行政区划的四个要素。
总的来说,制度来源上,道制和属国制度皆源于秦制,两汉承袭;不同点在于,道制在秦代是成熟的行政區划建置,而属国制度要发展到比郡属国阶段,才可称之为行政区划。在两种制度的最终归宿上,道演化为了常态的县,比郡属国演化为常态的郡,二者皆由特殊行政制度转为常规行政区划,这种演变模式在秦汉之后仍以新的面貌不断重复,唐代的羁縻府州制度以及元代以来的土司制度,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都是这种模式的另一种重演。
四、结语
道出现于战国中晚期的秦国,其与县平级,通常设置在边疆地区。道制一直延续至两汉,在三国西晋时期逐渐消亡。道的数量总体来说,在秦西汉时期呈上升趋势,西汉末年到东汉时期道的数量呈下降趋势,因此道制的广泛设立应该在西汉后期。道与县同属于一级行政区划,在郡县制诞生之初,便已是郡县制的一部分。道与县共同构成了秦汉时期的县级政区,对于边疆地区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武帝统一岭南及西南地区后,设置“初郡”进行管辖,“初郡”作为一种新的模式与常态的郡有显著的区别。初郡虽然和汉郡有着显著的差别,但其满足行政区划的所有条件,也是正式的政区,但其又不同于汉郡。初郡政策有利于南方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对汉朝初郡地区政治统治的稳定做出贡献,使得南方边地与中原地区联系加强,促进了初郡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而且这种政策常以其他形式被后世大一统王朝所继承沿用,对于维护边疆地区地方治安、巩固统治发挥重要作用。到了东汉时期,初郡制度逐渐失去活力,初郡地区与汉郡地区的差别减少,初郡制度退出历史舞台。比郡属国的来源远复杂于道制,其存在两个阶段化的发展特征。比郡属国不同于道制,其一开始并不属于行政区划的一类,比郡属国的前身为属国制度,从属国制度经过长时期的演变才转化为比郡属国。属国逐渐地方化,向地方行政体系转变,终于,东汉安帝时属国都尉比郡治民,也就是“比郡属国”。比郡属国演变成了正式的行政区划,但其所处地区与中原地区不同,行政管理仍有差别,属于特殊行政制度,与初郡和道的性质相同。三国时期犍为属国改置为朱提郡,比郡属国制度退出历史舞台。道制、初郡制度、比郡属国皆是郡县制度之下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历史产物,三者皆属于正式的政区设置,但却不同于常态的郡县,并有着向常态的郡县演变的趋势。秦汉时期道、初郡、比郡属国的设置,使得特殊地方行政制度呈现出多元建构与一体进程两种态势,也从侧面反映出秦汉时期边疆地区治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参考文献:
[1]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潘明娟.畿服制与择中立都[J].历史地理论丛,2022, (10):108-112.
[4]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M].台北:长达印刷有限公司,1990.
[5]马孟龙.张家山汉简《秩律》“县道邑缺失”问题辨析[J].出土文献,2022,(02):1-16+153.
[6]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
[7]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8]马孟龙.出土文献所见秦汉“道”政区演变[J].民族研究,2022,(02):106-112+141-142.
[9]马孟龙.出土文献所见秦汉“道”政区演变[J].民族研究,2022,(02):106-112+141-142.
[10]张悼.秦“道”臆说——兼向罗开玉先生请教[J].民族研究,1989,(01):93-97.
[11]邹逸麟.从我国历史上地方行政区划制度的演变看中央和地方权力的转化[J].历史教学问题,2001,(02):3-13.
[12]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3]刘瑞.汉代的初郡制度[J].唐都学刊,2017,33(02): 13-18.
[14]孙言诚.秦汉的属邦和属国[J].史学月刊,1987, (02):8.
[15]黎明钊.秦至西汉属国的职官制度与安置模式[J].中国史研究,2018,(03):43-62.
[16]孙言诚.秦汉的属邦和属国[J].史学月刊,1987, (02):8.
[17]黎明钊.秦至西汉属国的职官制度与安置模式[J].中国史研究,2018,(03):43-62.
作者简介:
付少聪,青海师范大学中国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