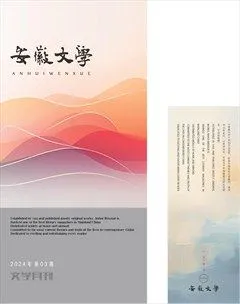在南方
2024-03-08陈元武
陈元武
一、线装书里的江南
江南是泛概念上的南方,而在南方人的眼里,江南并不算是南方,它是南方以北,长江以南的地域,有着无数的河汊和浜荡,是湖泊里的网格里的水乡。江南是婉约词里的唯美词句,是桃花杏花和烟雨里的白墙黛瓦。我想,江南也有另一种形象,那就是线装书。江南的徽州出产墨纸砚三物,加上湖州的笔,构成线装书的四大要素。单是墨一项,就足够濡染出一本厚厚的線装书了。徽州的墨碇是天下闻名的,墨的起源据说是先民们从火烧过的炭烬里发现了一种颜色,它能够染黑身体,能够让身上的刺青更为绚丽醒目,于是先民们尝试用它来涂画自己想象的一切,包括文字、符号。在岩石上画出许多人和动物的场景,画出太阳、月亮、河流、山川、水波和人本身。人们还发现火燎过的松柴上留下了更加湛黑的乌烟,带着油润的光泽,这种乌烟搽在身上更难揩去,于是,人们将它替代了炭烬的黑色,直到油灯的灯焰产生的浓郁的黑烟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收集油灯的焰烟成为采集炭黑的另一种途径。桐油灯是山区常见的照明用具,比起火焰跳跃不定的松明灯,有着更佳的照明效果。桐油是采自油桐树果的一种油脂,通常用来髹漆、胶织,做木器的表面防潮防湿处理。胶结的织物,像渔网和雨伞,渔网常年泡在水中,需要防水性的增韧处理,桐油和猪血成为渔网的增强剂。雨伞是南方必备的日常用具,油纸伞和油布伞,一个轻盈一个厚重。这些都成了古典诗词里的雅事,桐油烟的采集本身就像是雅事,在采烟室里,燃着一盏盏桐油灯,上边用竹筌支着一只倒扣的碗,碗内壁不断吸附着灯焰上升形成的浓郁的黑烟,那烟抹在手心,细腻柔和,有明亮的墨光。这些桐油烟灰和骨胶、冰片、麝香、珍珠粉、金箔、松香、鹿角胶等十一种原料,反复捣、揉、碾、酿和陈,直到墨胶如漆如饴如胶如抟,再压模成碇,所成“拈来轻、嗅来馨、磨来清”,“丰肌腻理、光泽如漆”,松烟或者油烟灰有个专有的字“炱”,烟炱、松烟,即炭黑。松烟墨墨色乌黑不张扬,浑厚、内敛、深沉、古拙。入墨的药物以麝香、大梅片、公丁香、冰片和没药为主,冬季用牛皮熬胶制墨,夏季则以鹿角胶入墨。徽州山水婉约,有青山为背景,有溪谷流水,水磨房里的捣药声,和灰后的杵捣抟碾锻轧。印墨碇前的摔墨声,像捣衣声,水磨转轮吱呀地缓慢转动着,那种声音单调而悦耳。
南方的山里,长着青檀、构树和楮树,田野间长着苎麻和稻草,山坡上郁郁青青的竹林,这些构成了纸的重要元素,剥取青檀皮、构树皮或者楮树皮,在溪流里漂浸数月,使皮沤烂如泥,浣洗干净后,剩下的青黄皮筋,是上好的纤维,还要放在屋场上晾晒经年,进一步陈化后,成为更加绵密纤细的纤维。同样的操作应用于稻草、苎麻和嫩竹,各种纤维按需要组合成纸纤维,经过碾细捣烂和增骨增韧助剂处理,入抄纸池中,抄成一张张纸,经过火墙烘干,堆压成摞入库陈化三年以上,即为宣纸。各种异形宣各有秘法,如云母宣和洒金宣,棉筋麻纸,煊烂如妙织之云锦,彩焕如水银之泄光。以其墨写其纸,堪称双妙,就差了笔和砚。徽州人从河谷里淘上来一块块石头,颜色青莹、纹理缜密、坚润如玉,磨墨无声,这本是远古时代的沉积岩,其泥质乌黑如墨,细腻而绵柔,抚之如婴孩肌肤,敲之则有金石之声。石磨成砚,有罗纹、眉子、金星、银星。“唐开元中,猎人叶氏逐兽至长城里,见叠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携之归刊刻成砚,温润甚于端溪石”,谓之瓜肤而縠理、金声而玉德。试将徽墨研之于歙砚,初闻其声如金石相交,磬鸣和应,继则墨发,汁如墨云涌起,渐成墨液如凝膏,掭笔于砚,濡墨无声,再游走于纸,如龙蛇。墨走之处,其质如风起云涌,如大江湍,惊鸟出林,如莽牛奋蹄,如龙角戟指,长兵指天,剑影飞舞,吴钩斜划。
当年石涛隐于黄山,采写水泽茅舍,蹑履于林下松荫,涂写如飞,其墨如霰,浅皴浓染,一竹一树、一草一径、僧庐竹舍,小桥流水,山不在其眼,水不在其眼,石不是石,树不是树,石涛的笔墨中,江南的徽州是浓墨重彩的,皴上加点,或轻描淡写,或刻意隐匿于雾泽山岚,或着意于石之憨厚可爱,树态千姿。石涛的画出自于心,他的心中有一本书,无线而成册,无字而炫然。石涛笔下的蕉丛、老树、古梅、怪石、桥栈、茅舍、幽径,无一不从心出,那一缕墨痕,牵绊跌宕,就像溪水从石中出,从云中落,下万仞矣,入碧涧中。线装书的模样,大概便是如此的风姿绰约,古灰色的纸卷上,泥版木刻的印迹,墨如画语,如私语,一笔一划,都如此的美妙。
二、且徐行,看一弯新月
江南如画,因此,要徐行而览,江如练,溪如凝,一弯弯的溪水放眼而去,再徐徐展开,远山如屏,近山如卧,一笔轻写,松榛茂然,小桥兀然横亘,像卧波之上的一处新月,新月明明在天,在野,在水间。于是,抬头,看天青如乍开之玉石,如初出窑之瓷盘素瓶,天青色就是云初霁,雨初收,天乍开,碧色横。天低处,山林仄仄,溪云依依。远远地看,天地浑然如盘中珠,荷上露珠。宛转灵动。江水中映天色如凝,村舍如随意点染之笔。云翕翕,水宕宕,江南的诗意在足底下一点点蔓延开去。草如黛,山如痕,带着一些微醺的混沌,古诗里所谓的山抹微云,那山不甚奇崛,亦非险崖绝。像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居图》那样:一江迤逦邈远,横亘天际,江山山水婉约细柔,减笔法加道士思维,以空茫入画境,以幽邈入山水,人物村舍,尽皆省略,远树如烟,远山如抹。大开阖的境界,需要主观上的审美,画风一转,近处的山,则详细尽列,虽无奇岩怪石,古松老柏,但每一株树,尽其妍秀,枝叶婆娑,画面上,横枝如叠眉,纵枝如戟张。画虽然烧掉了一部分,一画成二幅,甚遗憾,但画的风格一以贯之,谓之画气。黄公望为画此画,在富春江边盘桓了数年,每天步行一处坐观江景竟日,与僮仆相对饮酒数罂,饮罢抛向江中。“公望居小山,日以酒发其高旷,恒卧于石梁,面山饮毕,投其罂于水而去,卒悟山水神观。后村人发其罂,殆盈舟矣。”黄公望的酒是诗意的,他的画笔更是诗意的省减,山水在心中一横而过,不绝的诗意沿着富春江迤逦而走。
许多年后,在江南绍兴,一个醉汉的身影出现在曹娥江边,皂色幞头,缀一块联螭玉佩,步履蹒跚,风撩起他久未洗的长衫。他脸色酡红,双颧高兀而尤红,眼神迷离,一边走,一边指着江边升起的一弯新月,嘴里嘟囔着:“咄——去,咄——去。”像驱赶一只鹅,在他迷惘的眼神里,那弯新月如同一张笑脸,似乎在对着他笑。徐渭此时已经丧妻多年,孑然一身,以酒和老狗为伴。他一向在青藤书屋里绘画换酒,残缺不全的芭蕉叶,带着风咬虫破的残缺之态入画,以墨葡萄入画,枝蔓缠缠,却罕见硕果,零落的些许小果,连缀着枝蔓,从画面上垂下,藤叶俱随意率性,以墨之浓淡来体现葡萄叶之重叠参差,细须拂拂,而独枝孤兀。其蕉叶更是离经叛道,水墨洇出天地之境,枯笔勾勒出山石,也不皴擦,随意数笔以示其存在,或者稍加浓墨竹枝以衬其雅,蕉叶无枝无脉,仅数笔横扫出叶形,不勾勒不映衬,生硬的墨痕硬生生将蕉叶画成类似排肋的形象,瘦有其形,而终得其神。只有《黄甲图》用笔讲究,精到准确,简单的几笔浓淡墨,加上连筋叶脉的牵连,硕大的荷叶跃然纸上,而荷芰瘦劲,余处尽皆省减,一只螃蟹在荷叶底下,活灵活现,敛足怀螯,似若有所思。另一图《鱼蟹图》左右一鱼一蟹,鲤鱼仅见其首,怒张鳍甲,跃然于波涛之上,似是而非的鱼身和鱼尾,像是被网羁绊住的样子,螃蟹则紧紧钳住一根芦苇。徐渭旁白一诗:“满纸寒腥吹鬣风,素鳞飞出墨池空。生憎浮世多肉眼,谁解凡妆是白龙。”像是写自己,像是写人生。他将笔墨之精简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理解并喜欢他的画。葡萄图他画得最多,但多半是画毕即扔之于墙根底下。徐渭的画以疯病为泾渭,病前在胡宗宪幕府当差,生活滋润清闲,画的画用笔虽省减,但精致无他,病后失业兼失妻,疯病时常发作。贫病交加,画风骤变,以墨为彩,极尽主观的审美升华。以怪、丑恶的笔触来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不满。出狱后那段时间,他稍清醒些,游杭州、南京、富春江诸地。他对风月尤为抵触,不曾画过山水,也不曾为山水作诗。他的世界都是极自我的,极主观的。一世坎坷未转性,老友张元忭约束他,他勃然大怒说,我杀人,也只需吃一刀偿命,你这是要将我活活剁成肉泥啊!他不肯拘于俗礼,不尊世俗礼教,放浪形骸的性格到老未变。青藤书屋成了他最后的归宿,回山阴后至死不再出游。
若干年后,另一个画家奇人朱耷,想去绍兴访青藤书屋,吊怀这位他心目中的大师。但因为鼎革之际,到处乱蓬蓬的,终未成行。顺治五年(1648),其妻亡故,朱耷奉母带弟“出家”,至奉新县耕香寺剃发为僧,自号雪个。二十八岁到三十五岁间,带母及弟弟居南昌抚州门外绳金塔附近,此处通衢,茶室酒肆甚多,朱耷蓬头垢面,徜徉其間,酒量浅而喜醉,醉则大笔挥毫,一画十数幅,山僧、贫士、屠夫、孤儿向其索画,有求必应,慷慨相赠。转得薄酬,即付米炊以赡养老母幼弟。三十六岁后复入道,从此亦僧亦道,并以青云圃命名道观。入道后画风更趋空灵幽深,画中鸟兽俱青眼向天,白眼向世。晚年朱耷复居寺院,与僧友澹雪友善往来,澹雪为南昌北竺寺方丈,性格倔强,善书法,后因触怒权贵而入狱并死于狱中。澹雪死后,朱耷四处云游,访友作画,其间不乏应酬之作,并于郊外潮王洲上盖一草房,名“寤歌草堂”,其诗友叶丹曾作诗描写其居所:“一室寤歌处,萧萧满席尘。蓬蒿丛户暗,诗画入禅真。遗世逃名志,残山剩水身,青门旧业在。零落种瓜人。”朱耷同样不画山水,只写花草鸟兽鱼虫,像他一首题画诗所说的那样:“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枒树,留得文林细揣摹。”他内心的反叛只能表现在画作中,不融合不妥协,素眼青天,但个性独存。惊惧也好,忧思也罢,对着滔滔江水,他的身影恰如当年的徐文长,薄酒自醉,酹尊向天,明月浩然,沉浮江水中,一半是身世,一半是灵魂。枯枝上立个鸲鹆,回首相顾,却是白眼多,青眼少,那个惊讶之相,身形或缩或伸,俱委婉迁变,形似鸟而龙身,老鱼怒跳波涛间,树无一叶,形色枯槁,正所谓离世之相,不与世争一名。
江南的月一直这么照着,照着空旷的大江,照着青山绿树,照着芳草萋萋,时间轮回,一番番潮生,一番番潮退,江南的风景一直在行走中,翛然而风生,翛然而失所在。
三、烟火气中,青瓷的一声轻叹
江南是水做的江南,江南的人性格就多了点水性,除了烟雨之外,还有烟火气中的江南,江南人性格纤细婉约,吴侬软语,特别是女性腔调,有点甜糯。江南人日常用器,除了金属的就是瓷器了,比如喝茶,瓷器茶具仍然占着绝对优势。南方多湿,草木茏秀,一眼望去,满目苍翠。而江南的泥也似乎带着南方特有的细腻和绵密,像赤壤、高岭土和白垩土,高岭土是硅酸铝,洁白如云,且具黏结和耐高温易定型的特点。江南人不喜欢金属器皿,像青铜器,带着些铜腥味,也不易得。早期的南方人从烧陶中获得制泥坯器的经验,直到某一天,先民们在烈焰中试烧了一些用高岭土抟制的陶器,发现它们竟然比普通的陶器更加坚硬细腻,器形准确优美。浙江余姚的上林湖边,先民们用姚江水边沉积壤烧制出简单的陶器,那种橘黄色的南方黏质泥土竟然烧出器形纤薄精巧的陶器,一些陶器因为粘着砂子和草木灰而出现了微黄带绿的釉斑,先民们便特地将器坯粘上河砂和草木灰,青瓷从此诞生。为了获得更加均匀的釉面效果,人们将砂子碾细成粉,磨成稀浆,拌入草木灰,青釉瓷的出现是划时代的。湖边那些柘树、松树都被当成烧窑的燃料,简单的炉窑连成了长龙,成了龙窑,而烧窑的炭灰则成了配制釉料的材料。江南人追求一种器物的至精至美,他们不断努力,直到某一天,烧制出来的瓷器表面釉质光洁如玉,敲之如磬,色如三春之梅子,碧如春岭之芳树、莹洁灵动如三春之湖水、如雨霁天晴之霁光。烧器的工匠一声叹息,他并没有多少喜色,因为知道,他们的苦仍滔滔不绝。可工匠们只能从事这一行当,别无选择。
南宋的杭州,烟雨的巷陌里传来了茶肆酒楼里饕客们的大呼小叫。湿滑的石板街上,撑着油纸伞的小贩们在叫卖着新出的青瓷茶盅,葵花口、束口胆盅、仿尊酹器,有哥窑开片的,有梅子青的,有秘色釉的,竹挎篮里摆得满当,杯器碰撞着发出清脆的响声。彼时的上林窑已经荒废多年,窑器自然成了民间的物什,釉色参差,胎壁厚薄不一。老百姓的茶馆里不讲究,要的是便宜和耐用,茶杯当酒盅用也不稀奇。只有上等酒楼茶舍里的用瓷讲究。酒器中的四角杯、双耳爵、美人觚和豪饮用的觞觥大器,一色是哥窑的大开片,铁足薄胎,南宋的杭州光茶肆就有上百家,环绕着皇城周围。西湖边更是笙歌欢笑地,少不了酒楼和茶馆。《陶庵梦忆》里这么写:“世美堂灯:儿时跨苍头颈,犹及见王新建灯。灯皆贵重华美,珠灯料丝无论,即羊角灯亦描金细画,璎珞罩之。悬灯百盏尚需秉烛而行,大是闷人。余见《水浒传》‘灯景诗有云:‘楼台上下火照火,车马往来人看人。”茶器中以青瓷茶海为特色,收口,如茶洗带耳,茶杯俱内素外青二色,单釉多为薄釉梅子青,哥窑器较罕见。茶点则有云南蜜饯、丰城脯、福橘饼、山楂丁、松子糖、白圆、橄榄脯、马交鱼脯、陶庄黄雀、桃门枣、地栗团、窝笋团、鸡豆子、花下藕、细榧、龙游糖诸物。龙泉青瓷的兴起,与邻省福建的闽瓷兴起有关。当时,建盏已经冷落萧条,窑工们无所事事,便往浙江龙泉兴窑烧瓷,南宋以青瓷为上品,龙泉青瓷的高岭土采自当地,一半是来自福建的闽土,釉料的精细石英砂则来自福建,龙泉窑瓷出来后,成为青瓷的巅峰。青瓷的窑工则往闽南德化开窑烧瓷,以素白瓷为胜,兼烧青瓷。福建窑工的设窑经验甚于浙江窑匠,特别是梯形长龙窑的出现,使得烧制成本大大降低,使得后来青瓷得以走入民间。称大龙窑青瓷的瓷器,更加精致完美,釉质更加莹洁透明,那抹青绿在釉层里闪着神秘的光,仿佛是自然里活着的绿。称为梅子青的青瓷恰如其名,而梅子青的焰法则依赖于大龙窑的回火焰,即还原焰,一部分成了粉青釉,一部分则成了翠绿的梅子青。施釉法则是窑工们参照建盏施釉法,以淋釉替代浸釉,釉浆更细更匀。因此能够有露足釉胎,足则见铁口锈色。与浸釉的满底完全不同。宋高宗得梅子青瓷后甚是喜爱,说:“如蔚蓝落日之天,远山晚翠,湛碧平湖之水,浅草初春。”取代了失传的汝窑瓷器。哥窑与此类似,只是焰火少了道回焰,而纯透明的釉层在开窑时皲裂,发出清脆的声音,哥窑的铁线开片则是后期水浸的效果。也许,窑师想复制汝窑,失败后创制成另一种青瓷。南宋御窑在杭州的凤凰山下,土为赤红壤,故胎质实为陶器,而釉采用汝窑秘色釉工艺,而实得哥窑无汝窑特色,又独成一器,最早的哥窑始于青泉,完善于杭州。《遵生八笺》里说:“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窑在杭之凤凰山下……官窑质之隐纹如蟹爪,哥窑质之隐纹如鱼子,但汁料不如官料佳耳。”《春风堂随笔》里说哥窑的特征为:胎色黑褐,釉层冰裂,釉色多为粉青或者灰青。由于胎色较黑及高温下器物口沿釉汁流泻而隐显胎色,故有紫口铁足之说。而龙泉窑作为哥窑的创始者,其哥窑器特色更为多样,色有炒米黄、灰青、月白、粉青和豇豆粉,纹如铁线,清晰而多变,与杭州官窑的哥窑器有所不同。汝窑釉中有用玛瑙、珍珠、琥珀等物,而哥窑民器中确无此物,因地制宜,窑工的技巧可夺天工。哥窑的青口和紫口,也与工艺有关。南方有矿名赤蜡石,龙泉当地产页蜡石,色如火焰者名赤蜡,窑工以此添入釉药中,殆其得之于幽渺启训。晶砂即石英砂,闽地所产雪白洁净,名雪砂,龙泉诸窑无一日不用雪砂。
以青瓷官器陶土入胎,非青瓷制法,乃建盏秘法,而淋釉亦建窑工艺,建盏以石灰入釉,拌以赤壤为浆,得黑釉器,质坚如铁,亦闽建窑特色。闽砂得之于海滨,色灿如雪,离此处则复为黄砂。青瓷中的秘色瓷复为古青瓷法,釉药中加玛瑙和海青泥而已。
四、欸乃一声山水绿
南方的江曲折而婉约,四季分明,春水涨急,混浊如泥漉,夏水洪涌如奔,急湍猛浪,摧山裂石,秋水静娴,唯明波如涟,风吹一江皱缬,冬水枯瘦,一江横陈,尽是滩石砂砾,唯苔色青青。江柳亦名滩柳,着根于溪中乱石间,不高,如灌木,约数尺,幅亦不广,约一围,茎细如箸,或者如赤楠,盘根错节,非石不能固其根柢。水涨急时,隐于急流中,随波摇曳,如水中蛟舞,而鱼多得其荫而免为急流所荡失。江南的江流,是诗意的,青绿山水之间,一痕江影如练,扁舟浮江,两岸青山倒映水中,江流中行,甚是惬意旷然。古人或钓于石矶险滩,或舟行撒网于江心,各个得其所妙。江水是流淌着的诗,舟人、钓人是诗里的眼睛。春三月,桃花水泛,薄雨连绵,雨不甚大,细如牛毛,却无休无止,天地间仿佛堆积着无数的雨意,牛毛细雨恰好滋润了万物,了无声息。在树叶上,看得见雨丝飘落后的瞬间,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接纳了雨丝,并绾盘成无形的发髻,树叶上形成了莹润的水泽,像涂了油似的。而一些花刚刚开放即凌乱憔悴,花瓣经不得春雨,虽然只是牛毛般细柔,却还是太沉重了。花残凋谢,一片片绯红落入江中,引无数的鱼儿争抢。夏五月,龙舟水泛滥,江水如奔涌,舟不得行,洪水淹滩,江流转瞬成洪流,弄潮儿龙舟竞渡,声遏行云。擂鼓击柝,挥桨如飞,船似飞箭,射向前方,健儿们赤膊裸身,着一彩裈,足蹬腰弓,力尽于桨,水花如湍,急浪奔腾。龙艏在波涛和击桨的水湍间昂首向前,仿佛是古老的巫咒,是大地与人最激烈的一次较量。“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九歌·湘君》)秋水游于南浦,南浦在武夷山市东北郊,秋水如碧,湛然缥青。“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况秦吴兮绝国,复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这是江淹在建安郡吴兴县令,逡巡于南浦溪畔的命笔写下的《别赋》。秋天的南浦溪边,蒹葭苍苍,繁密如旌旗,高擎着灰青的花穗,迎风猎猎而舞,长叶如带,如旌旗的斾斿。南浦云连鹫岭巅,黑黪黪似连营垒,他的内心是绝望的,距离中原万里之遥,隔着秦楚吴越,每一片云都让他倍感凄凉和悲怆。何况秋声如柝,彻夜不息,即长空鸿雁声断衡阳之浦,何况他远离赣楚之地,身赴八荒之外。旷域无亲,闻秋风而魂断。江水清如许,可以照见山林和天空,唯独照不见故乡的亲人和远方的故友。此时的恨意何绵绵,简直是要摧毁他内心最后希望的雷火。至于冬天水泽枯竭,江流断涸。江山复如原始,一地的霜迹。冬天是水隐藏的季节,偶尔有霜雪,亦随下随化。萧瑟江天看苍茫,蒹葭满地随云飘。一个旅人,在冬天的原野,内心反而感觉寂静无波澜,无亦即有,有亦即无,这就是空的境界,有反而多累,心累、形累、神累,恍然一梦,到处是枯枝败草,苍黄的天底下,万物寂寥,想一是一,二是二,唯独不曾有三。玄门和太极里,称三横不断为乾卦,“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乾卦时属冬初,像寒冱之气,有如冰。
时值寒冬,正好可与友上天游峰饮茶赏雪。冬来少雪,偶遇雪落,路上行人稀少,雪落地无声。路两旁的竹子承载着雪,弯向大地,山峰间撒盐空中差可拟,地上微湿,雪触地即化。武夷山星村里,不少茶农正在烘焙年内最后一次茶,恰好是三焙收冬,至此茶性稳定,不复变味返青。天游峰甚高,高出天际,令人生畏。幸好一路上无甚积雪,磴道上微湿而已。茶人问,偌大的雪,你二人往山上做甚?我答道,上山看雪品茶,茶人性爽,便随我而上,带茶叶及白炭若干,拎着一桶山泉水。山上有亭,炭炉火忽明忽暗,风甚疾,只好将就着将水烧开,未闻其大沸之声,茶出,如红酒色,名白鸡冠,复焙三次。味甚清淡,只有火味甚浓,然三巡后,火味渐去,再品有雪中闻梅之妙香。第二泡为白瑞香,亦是奇罕品种,味如前者,复至奇丹,味如醴而醇香,色如琥珀,茶汤上浮一层沆瀣。风吹脸如刀割,然内心里感觉如沐春风。茶是百炼丹药,饮茶,服饵用丹而已,此茶名源自道家,以其茶合丸而服,虽隆冬犹觉身暖气暄。我指着山底下枯瘦的山溪,问彼二人,可曾从游过?二人哂不以为然。一溪风月,唯山上可俯拾之。想想春夏之漂游,满目苍翠,转瞬便枯槁失色,枝柯无叶,苍黄之间,那一声欸乃的桨橹声恍然似梦。江淹任吴兴县令(今浦城县),武夷山仅仅是荒村野岭,不曾聽说有种茶之事,亦不知茶为何物。否则,他若能品此茶,必忘机流连。茶能让人陷于仙风飘飘的错觉。这欸乃一声,如棒喝,是让人惊醒的一声,错愕之间,时间已经飞逝。
想想当年,苏子瞻夜游赤壁时,见一鹤凌空绝顶而去:“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顾笑,予亦惊寤。”白鹤翅大如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而过。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