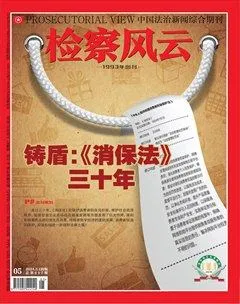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理论与实践
2024-03-08孙宋龙彭曦曹俊梅
孙宋龙 彭曦 曹俊梅
以“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为基本路径的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研发与应用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一度成为数字检察的代名词。本次研讨围绕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价值、模式、实践难点及优化方案等展开,特邀法律专家和实务人士进行交流。

许刚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
觉醒
许刚:数字检察工作推进以来,有研究者将数字检察与大数据法律监督的概念等同,也有观点认为大数据法律监督是数字检察工作的一部分。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其与数字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是什么关系,具有什么价值?
吴思远:数字检察是继我国智慧检务建设之后的又一重要的里程碑。构建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是实现数字检察改革目标的关键所在。所谓“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是检察机关依托数字化技术,通过数据建模发现风险点与监督点,探索智慧监督方式,更为主动地进行法律监督与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模式。运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价值在于,一是检察机关顺应国家数字化建设的体现,二是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可以进一步提高监督质效,三是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运用,赋予了检察机关积极主动履职的工具可能性。
章安邦:个人认为数字检察的内涵较为广泛。大数据法律监督是数字检察的一个方面,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是大数据法律监督的载体,“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模型是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主要模式。
路径
许刚:刚才专家提到“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是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主要模式,可见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有不同呈现样态,请各位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苗旖: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實现路径是“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三个环节的重点,分别是检察官的类案拓展思维、融合办案机制和让监督规则成为治理规则。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离不开业务主导这个关键点。
陈奥琳:与传统的诉讼监督办案模式不同,数字检察办案更加强调侦查思维,对线索的发现、研判、调查类似于自侦办案过程中的线索初查。监督案件的办理有明显的“类侦查”特性,办理的质效、成效很大程度取决于线索来源、数量和质量,监督办案的起点也远在案件受理或立案之前。明确监督方向、发现监督点是数字检察办案的第一步,关键在于立足法律监督职能,探索符合地域特性、业务特征、数据特点的数字化法律监督发展路径。
章安邦:当下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主要方式就是,透过具体的案件,总结共性、普遍性问题,解析个案、梳理要素,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方案,构建模型输出线索,再进一步进行问题核实、类案监督。类案监督的重要方式是构造类案的整体数字画像,最终实现“一地突破、全域共享”。当然,模型共享的时候不能简单地采用“拿来主义”,需要对不同区域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惯等因素做出一定的因地制宜的“变量调整”。
反思
许刚:当前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在实践中遇到了数据和机制方面的难点,各位专家对这些难点有何看法?
苗旖:没有数据,模型也只能是模型。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数据来源可以分为内生数据、共享数据和公开数据。“内生数据”是检察机关通过挖掘自身业务沉淀下来的数据资源;“共享数据”是检察机关通过“两法衔接”、政法协同及其他部门政务信息共享获得的数据资源;“公开数据”是检察机关通过接受控告举报或者网络公开信息获得的数据资源。“内生数据”是基础,“共享数据”是重点,“公开数据”是补充。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对共享数据、公开数据不加区分海量收集,这极大增加了数据收集的难度。

包旭娟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陈奥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苗旖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吴思远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教授

章安邦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陈奥琳:首先,海量有价值的法律文书没有结构化处理,尤其是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要素难以被机器精准、自动识别和提取,进而影响对这类数据的管理、存储、处理和分析运用。其次,从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应用机制上看,缺乏有效的检察监督线索管理制度,一定程度可能造成监督线索的流失和线索管理的弱化。
包旭娟:一是数据获取难度较大。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人工填录数据错误,导致法律监督调取的基础数据不够精准。二是数字检察类案监督促进社会治理的规模效应尚未形成。“办一案、牵一串、治一片”还需要推动职能部门对发现的社会治理问题进行常态化的预警防范。三是复合型人才不充足。具有数字思维的检察官和熟悉检察业务的程序员,二者紧密配合才能最高效地将数据背后反映的问题梳理出来并开展针对性监督,因此非常需要复合型人才。
章安邦:数字检察工作的开展需要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要求、基本规律保持一致。检察机关行使数据权力必须满足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要求,避免侵蚀数据权利。严格按照《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建立健全检察机关数据合规体系,制定相关法律監督数据的标识、存储、管理和调取规范,不得超越权限查询、使用相关数据,确保数字检察恪守法治的红线。
吴思远:在数据源方面,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建立的数据来源面较窄,司法数据多、行政数据少,且数据获取存在“知识鸿沟”,关键字段的抓取和结构化处理存在难点。在系统应用方面,监督模型业务规则的提炼还不够准确,进而转化成数据规则存在困难。模型建立具有“盲目性”,各模型之间系统性弱。数据模型的学习能力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核心业务方面的应用有待深入。从模型到实践阻力较大,监督乘数效应体现不明显。在机制方面,监督模型运行过程中的检察权介入边界有待明确,需要进一步探讨。
展望
许刚:面对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各位专家有何建议?
陈奥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背后蕴含了依法一体履职、融合履职、能动履职的理念,要求检察业务与数据技术深度融合,需要持续培养更多具备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和法律实践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提升完善检察人员数字应用能力。
包旭娟:我认为,在强化数据归集上,一要主动接入省级统一数据归集平台,打开数据通路。二要由点及面逐步拓宽数据共享范围,充分利用好政法机关执法司法信息共享工作机制和统一的政法一体化应用平台,在政法机关之间全面整合政法数据资源,以行刑正向、反向衔接业务流程推动行政执法数据与政法数据的流通互转。
章安邦:我从大数据思维角度谈一谈如何推进大数据法律监督工作。首先,要重视案件数据的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要摆脱传统的尤其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认定习惯,才可能把本身在传统认知中并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关联的案件因素结合起来,从而突破性地发掘出检察监督的可能对象与监督要点。其次,用大数据思维中的类推思维代替传统的逻辑推理思维。类推本身是刑事审判中严格禁止的推理方式,但是在案件的线索发掘上,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类推思维的重要意义。复次,在数字检察中需要运用全样思维代替抽样思维。检察监督模型的建构需要建立在全样文本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各个地域、各个层级和各个政法机关的案件数据共享。最后,要运用和调和大数据思维中的容错思维。容错思维而非全对思维是大数据思维的特点,这也是大数据思维与法治思维的必然冲突。需要客观的大数据监督模型运行与检察官的主观分析研判相结合。
吴思远:首先,疏通数据来源渠道、打通系统间的数据壁垒是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建设的必经之路。在制度框架下,应当从不同维度协同推进数据共享工作。
其次,复合人才的系统性培养是打通技术和业务的关键。一般而言,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研发包括了设计和开发两个过程。未来除了有意识地招录“互联网+人工智能法学”等交叉学科复合型人才,还可以采用与政府共同培训、互派人员交流挂职等方式来吸收专门人才。
最后,制定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标准,接入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是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有效推广的前提。随着数字检察改革的深入推进,为了防止改革的地方化、片面化,需要进一步整合各级检察机关的力量,尤其是需要破除地域限制,从更高范畴上调动检察权,实现不同区域检察机关之间的通力协同。
许刚:我们围绕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提了很多宝贵建议。特别是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探索和应用中需要立足检察权,尊重司法和社会治理的规律。本次的研讨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精彩发言!
(声明:本内容仅代表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编辑:张宏羽 zhanghongyuch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