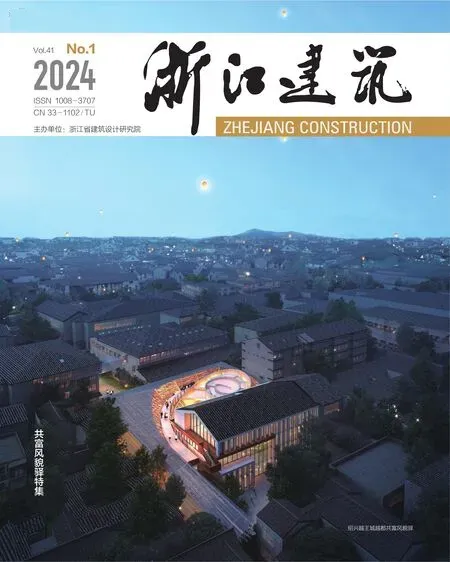浙江省乡村书院空间探析
2024-03-05陶伦
陶 伦
浙江工商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0 引言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自古有耕读传家、重教兴学的传统,乡村书院遍布乡野。现存地方志、书院志记载了众多的书院历史发展与社会背景,大量的乡村族谱更为细致地记载了鲜活个例,方志和家谱为研究浙江乡村书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一乡一村同姓同宗聚族而居,家族兴办书院、私塾学堂现象普遍,即便是杂姓村也多有兴办乡学、义塾、冬学的传统。书院是乡村典型的文教空间,起到了文化普及与教化乡里的教育设施作用。与县学、府学的办学主体不同,宗族是兴办乡村书院的主要力量。耕读伴随着宗族社会的发展、文教的需求进而催生了乡村书院的兴起和发展。自宋迄清,乡村书院一直是乡村教育的主要形式,承担着广大乡村地区从蒙学阶段直至科举教育的重要功能。为蒙学发韧、知识传播、孕育思想与普及社会道德标准、敦化社会风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土壤,涵养了具有文明主体性的文化传统资源,并深远影响了浙江地域性的文教气象。作为文教功能空间载体的乡村书院,如同压舱石一般,对宗族、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与稳定发挥着重大的“化育”作用,为孕育与传播传统文化观念,维系中国上千年超大规模的文教传承,提供了最为基础且真实的文教空间载体。
1 浙江乡村书院文教空间成因分析
建筑是文化的物质载体,建筑形式是文化的显性反映。浙江乡村书院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与教育资源,文教空间所呈现出的丰富性亦体现出受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人地关系(聚落生活)、经济发展(生产技术)、社会观念(乡土风俗)、文化传承(学派流脉)等。究其根本,首先是受限于地理气候的影响而形成特定的人地关系,进而影响浙江乡村聚落的格局,从而决定了乡村书院的文教空间形态。从浙江地理空间格局来看,由于水域与丘陵的分割形成了若干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加之浙江“西南高北东低、多山少平原”的地理结构[1],使得农耕的前提必须进行成片的排涝疏浚与山地开垦。同时,浙江持续输入型的人口压力、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以及非跃迁型的农耕技术水平,决定了在传统社会农业生产开发中,必须始终围绕如何平衡人地间的矛盾,合理并灵活地利用自然资源,持续性地进行乡村建设与生产生活、经济发展与文化教育。
人类的建筑活动伴随着人类自身的生活发展与文明进化[2],乡村书院是人与空间持续进行文教互动的空间场所,是文化生成与传播、教化普及与知识传续的空间载体,具备文化性与教育性合一的内在属性;教化功能的外化呈现则需要通过建筑的等级与形制得以彰显明确,辅以装饰性劝学意涵的字画与雕刻浸润默化,并在特定时段通过祭祀宗教仪式场景进而固化并强化,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依附于实体空间的文教设施系统。人参与文教互动中赋予其完整的文教意义系统。整体系统中乡村书院起到的是枢纽性的功能,多重身份人群共同的文教愿景凝结其中,包括宗族自身的发展意愿、乡里后生的求学上进、文化精英的知识传播、管理阶层的敦化风俗、地域学派的化民成俗等。基于传统耕读观念下的血缘宗族,其自身强烈的发展意愿与现实的科举、事功路径相统一,激发了乡村基层社会的建设意愿,从而自下而上自发地积极兴建书院,教化族人,耕读传家。与此同时,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治理的观念主张相结合,糅合了地方管理与敦化民风的风俗建设,从而使得主流认可的意识观念,自上而下地渗透到乡村书院的文教活动中。除此之外,精英知识群体推动的化民成俗进程,以乡村书院作为主阵地普及性传播知识、开发民智,汇聚形成家与国、基层与社会、平民群体与知识精英相向而行的统一发展逻辑。
2 文教传承的核心结构与演化推动力
从浙江现存众多地方志与宗族家谱记载可以看出,“崇文重教→兴建书院→负耒横经→耕读传家”的衍化脉络,始终是维系宗族世家发展的必要手段,也是赓续宗族兴旺的必由之路。江南历史上三次大的由北向南的人口迁徙,不仅带来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观念[3],也使浙江的人地矛盾进一步凸显。历史时期人地关系演变的实质,就是这种冲突与对抗之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内涵的演变[4]。村落选址、宗族发展、乡里建设是同一时空背景下共同演化的互动过程,三者之间互相交织并共生衍化,形成“三元互嵌”的环状结构,即:村落选址的地理面貌,约束着村落集聚的生产形式与生活形态;自组织特征的宗族,成为推动乡村社会发展与建构的担纲力量;礼俗观念的乡土社会关系,固化了乡里人群的行为准则,维系着社会基层的平稳运行。“三元互嵌”回应了乡村书院“在哪建—谁来建—为何建”的基本问题。环状的中心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的耕读观念根植其中,形成“中心+外环”的稳定结构。“三元一核”是解析乡村书院发生并演化的基本机理。
儒学观念规范的是农耕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秩序,体现为在相对稳定的群居社会中,通过定居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进而拓展大规模协作的人际网络。邓洪波提出乡村书院的两个界定:建于乡村并进行公共性的教育[5],指出了乡村书院由血缘型向地缘型的转化特征。从现有浙江传统村落分布的稠密程度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村落聚落的形成不仅受限于地理空间的约束性条件,还因为人地关系的演化进程而被深刻地影响(图1)。山区连绵、土地细碎又交通不便,中央的统治力量难以深入,宗族力量得以长期保存,根植于村落、宗族、乡里之中的乡村书院长期强韧。同时也应看到,这种强韧性折射出受社会历史变迁中生产力与经济发展的影响,文化传播的加速与文化的下移呈现出来的总趋势,以及社会进步与技术发展的叠加效益,合力加速推动了乡村书院的演化进程。

图1 浙江636个传统村落核密度[6]与主要山脉分布关系[7]
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在南北地域内耕地分布极为不平衡。北部为地势平坦水网纵横的杭嘉湖、宁绍平原,往南往西是连绵的山地丘陵地区(丽、台、温及金衢盆地),往东则是沿海地区的狭长细碎平原。山地丘陵地区较平原地区农业开发难度大,加之历史上大规模的南迁人口使得粮食问题突出,有限的耕地不得不承载增长的人口,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尤为迫切,例如普及双季稻种植技术与引进高产作物山地种植技术。浙江双季稻最早出现在唐代之前,但推广范围很小。北宋处州有“稻再熟”的记载(光绪《处州府志》卷十二)。南宋时期温岭出现了“黄岩出谷半丹”(《苏城志》卷三)。明《谷谱》所载:“浙江温州岁稻两熟。”随着明代中期大规模地引进北美玉米、马铃薯、番薯种植,光绪《宣平县志》卷十三说番薯“虽陡绝高崖,皆可栽种”[1],即便是在中南部山地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也极易推广,山地型村落的人地矛盾与粮食紧缺问题大为缓和,村落分布与数目趋于定型。
农业生产技术的提升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带来的是学习时间增加与教化意愿的不断深入。浙江高度发达的印刷业与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进一步促进了书籍在文化知识生产、传播、积累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8]。宋代开始浙江的造纸已居全国之冠,越州竹纸、杭州藤纸、温州蠲纸等产量巨大,纸张的普及降低了学习的门槛与成本。宋元以后统一规范了教材,清晰了从蒙学到科举的努力方向。这些都从技术层面推动了乡村书院的进一步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自宋开始由豪族社会转向平民化社会,科举进一步普及,宗族的自身发展要求不断拓展乡村书院教育职能;南宋迁都临安后,浙江政治、经济、文化功能高度重合,江浙学子通过科举参与国家治理的上升通道被完全打通;元明清帝国虽定都北京,然而大运河漕运的兴盛将浙江与北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江南仕子朝中为官参与治国比例全国最高;长时段来看,社会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支撑起浙江乡村书院亘古绵长的历史进程。
3 从“家国同构”探寻文教空间的文化教育合一属性
《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表述了古代教育的层级关系,蕴含着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国、政治与伦理融为一体的观念。作为传统社会长期维系其低成本运行而形成的一整套观念系统,不仅体现出自上而下的宏观构架整合与自下而上的微观秩序建构;还体现为家庭、宗族、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与对应性,渗透在日常生活状态中,“家国同构”观念被反复地强化。反映在建筑礼制上,显现为其轴线、朝向、前后、高低与建筑的等级呈现出强烈的对应关系,这样的一种“同构”特质,使得不论是官式建筑与民居建筑,皆反映出其建筑等级的形制高低、轴线关系、尺度大小、色彩使用,都严格遵循等级规范。合院式是最为基础的传统建筑布局样式,书院中的多个“合院空间”安排在主轴线上,前导性的祭祀与礼仪空间、主体性的教学与藏书空间、辅助性的起居与祈福空间等。文教功能通过空间的先后序列被组织起来,形成文化与教育统一实施的完整场景。作为合院式“外扩”形式的传统官学建筑,通常遵循“左庙右学”双轴线的布局样式,大小形制远远高于乡村书院。单从文教空间布局上讲,与乡村书院处理手法上均属“同构”(图2),在现存众多的浙江地方志所记载的县学、府学与乡村书院的建筑布局样式中屡见不鲜。

图2 海宁州学宫图与海宁安澜书院图对比[9]
聚焦到微观层面的文教空间。乡村书院分布于村庄乡野,有些就是直接坐落在宗祠、家宅、园林中。规模虽不及官学建筑,却能实现与周边环境的灵活协调布置,并追求清幽淡泊、隐逸高雅的文化氛围。环境和谐统一的自适应弹性、景观绿化的勃勃生机以及精巧营造的“书卷气息”,强烈透射出基于“文化传续与知识传承”的文教意愿,成为文化与教育意向表达的绝佳诠释。傳旭元在《东明精舍記》中这样描述:“……前为荣后为寝,东西分为四斋……其所问难曰敬轩,其所鼓琴曰琴轩,其所退休曰游泳轩。其琴轩少南有水一泓,不亏不盈,曰灵渊。之東百步許有泉泠,然老梅如龍横蹲其上,曰梅花泉。匕北有坛,当時延景濂教授其中。”[10]从布局上极力保持明确的轴线关系,保持流线的通达与序列的完整。贯穿于书院的祭祀、教书、藏书的三大主体功能,与生活起居、园林绿化、水体造景、沉思冥想等空间充分融合。大则“尽善尽美”,尽可能将文教功能配置到极致;空间小则“求巧求雅”,使文教功能分布在单个建筑内的不同区域中,表达出文教功能的核心诉求,确保空间能尽可能多地为教学活动所使用。
4 乡村书院是乡村文教空间的典型代表
4.1 山水格局、自然风景与化民成俗融合潜移默化
浙江山水格局丰富多样,乡村书院亦呈现出极其丰富多样的景观图景、民居样式,地域材质与乡土民情,展现出生机勃勃田园牧歌的景象,与自然山水环境相融为一体而又生生不息。宋代以来理学思想日渐丰盈并不断向基层渗透,持续进行的哲学思考、伦理教育和民间风俗建设,对浙江乡村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化民成俗的进程在客观上使乡村书院成为联系心灵精神世界的纽带,将文化精英的知识推广与敦化社会风俗的基层建设相统一,以有教无类的方式渗入广大乡村。儒家经典“比德山水”观念下的审美观与乡间朴素的“环农业”“适形”村落选址观念相互糅合[11],“择胜”环境观、“形胜”风水观、“文运”发展观、“传家”伦常观等凝结汇聚成“生生不息”的生命状态,于天地自然环境中参赞化育。
瀛山书院源于北宋熙宁间的詹氏族学,初期以本族子弟入学就读为主,后因朱熹讲学并作《题方塘诗》而影响深远。瀛山书院的建设过程历经宋元明清四代,“瀛山”的得名是由背山“银山”而来,因取“登瀛”之义,遂改银峰为瀛山,其书堂亦改名瀛山书院。《瀛山书院志·四刻瀛山书院志首卷》中的图述记载(图3):“呜呼!东南冠盖,春梦空凭,南渡风烟,冬青漫慨。先圣之化境,为终古之名区。万笏山排,翠篠白云开别馆,一环溪护,碧鸥红蓼指遥村……”[12]书院选址充分考虑了背山、环水、依托地势营造高点等综合地形因素,书院整体映衬在竹翠与冬青、碧鸥与红蓼之间,“别馆”与“遥村”进一步说明书院建造不在村内,而是超脱于市井烟火气之外,与自然景观环境浑然融为一体。在自然的四季更替中滋养读书的种子,在天地万物间吐纳思想的气息,在山林幽静之地怡情养性、潜心向学。

图3 瀛山书院图[12]
4.2 匠心营造、敦化乡里与公共服务延展相辅相成
乡村书院的首要职能是教育普及与人才培养,教育对象除宗族和乡里子弟之外,甚至扩展到外姓子弟与非本村子弟。其建设规模与支持财力各有不同,个人筹建、宗族出资、乡里集资、官府合办等形式多样。教学层次也不尽相同,有蒙学、冬学,有输送县、府学,有针对应试科举等不同阶段类目的教学形式。综合来看,乡村书院的衍化历程实现了由血缘型向地缘型的转化,由私学属性向公共服务属性的转变,其文教空间亦成为乡村公共服务延展的场所。由此,从公共性的文教服务视角切入观察乡村书院,可以看出,整体系统中不但包括建筑实体,如桅杆、魁坊、文峰塔、文昌阁、藏书楼、书院、文馆等[13];还包括装饰性质的教化内容,如室内的楹联、匾额、雕刻、族训、贤圣画像、碑记等;以及仪式性较强的教化场景,如每日课的神位祭拜、每半月的文会受题作文、日常的书院讲堂教授、大型的祭祖祭孔仪式等等。
建德新叶古村早期的重乐书院建于元初,兼收本姓与外姓子弟,北山四先生金履祥、许谦以及柳贯、章燮曾前后教学于此,虽明代颓败,但叶氏宗族办学则一直延续。至今村内保存大量的文教设施,建有旌表型(举人桅杆、“耕读人家”与进士第牌坊)、书斋型(华萼堂私塾,居敬轩官学堂等)、公共祭祀型(有序堂书房义塾)、祈福型(抟云塔、文昌阁、土地祠)等文教空间。有序堂位于村内核心区块,为叶氏外宅派的总祠,面朝一半月形的泮池,极目远眺朝山“文笔峰”,视野极为开阔。祠内设有大戏台,义塾设在总祠东侧书屋内。该区块是新叶村公共空间属性最为强烈的区域,承载了新叶村几乎所有的公共性仪式场景,包括集会、祭祀、演出、文教、交往等。历经明、清、民国的不同时期,在村落东南方位的水口位置,分别加建了抟云塔、文昌阁、土地祠三类建筑,功能上同为祈福文运的仪式性建筑(图4)。高耸入云的抟云塔与造型飞扬的文昌阁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极富视觉张力的村落入口地标建筑,昭示出叶氏家族世代祈求文运、传承文风、耕读继世的强烈意志。

图4 新叶古村抟云塔、文昌阁、土地祠
4.3 因地而生、因时而兴与文化地域交织共生共衍
文化总是具有地域性特点,文化的这种地域性是文化的本质属性之一。但同时,文化也并不完全局限于地理环境,通过种种方式突破空间地域的限制,使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得到交流、融合,相融且互补的地域性文化现象亦反映在建筑样式上。浙江的乡村书院保持着较为清晰的浙派民居建筑谱系特征,呈现为既有吴越文化地域中典型的水乡建筑特征,又兼具受相邻地域性建筑文化的影响与渗透。在浙江南部、北部、中部、西部区域均呈现出众多特征明显的过渡型民居建筑特点:浙西地区乡村书院建筑样式与皖南民居同源;浙南地区建筑样式虽原生性较强,也兼具闽东北大厝样式特征;浙中金衢地区样式则有较强的边际效应,过渡性特征尤为明显;东北部宁绍地区是越地文化发源核心区域,北部杭嘉湖地区与苏吴太湖地区水乡建筑样式相近。
湖州地区是水网交错型的平原水乡,乡村书院呈现出典型的浙江水乡民居特征——建筑邻水、院落进数多、朝向与河道成垂直关系、多布置花园等特点。如南浔荻港古村的积川书塾较为典型。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循环农业形态特征的“桑基鱼塘”环绕荻港村落周边,京杭大运河沿村穿流而过,至今往来船只汽鸣不绝[14]。积川书塾原为荻港大族章氏的私家书塾,后迁入具有道教文化背景的云怡堂中。乾隆34年(公元1769年),章氏家族出巨资扩建“南苕胜境”建筑群,形成多重进深的院落结构,主轴线上有八卦池、五孔架桥梁、文昌阁、纯阳宫。积川书塾位于主轴西侧,毗邻花园与御碑亭(图5),临水且环水、园林与水景相融,营造出超然脱俗清新俊雅的水环境文教空间。

图5 积川书塾平面
在清朝两百年间,区区一村中的积川书塾共培养出两位状元,五十多位进士。文运如此昌盛,与当地高度发达的“农业+工商业”经济形态,以及依托水网纵横的便捷交通所形成的商贸繁荣有着莫大的关系。大运河联通杭嘉湖一带四通八达的水网,明清时期通过漕运高效联系着国家南北方交通,交通便捷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湖州素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稻桑棉麻开发较早,农业与桑丝生产基础较强。早期资本主义在此萌芽,恰逢明清丝绸工商经济更加发达,加速形成了以血缘、地缘、业缘为联结纽带的浔商群体。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起继世教化、藏书、留学等文教事业,包括像嘉业堂、宜园(旁氏花园)藏书楼,中西合璧式的建筑、精致的园林、海量的藏书、精美的书画足以例证。在明清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地域性的浙江文化精英知识群体,参与国家政治治理、浙派朴学研究、初级工商业萌发,以及近现代先进思想传播等,均有尚佳展现。
4.4 文教传承、文化传播与人文流脉重合薪火赓续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15]。人是文化活动行为的主要载体,群体文化意识是文化共同经验的集中表达。书院是人才培养与人才汇聚之地,是不同地域文化之间互动交流与激发的平台。文教空间与人文流脉的重合,使文教传承呈现出纵向师承与横向扩展的双重意涵。成为书院传教者的山长、先生、教师是文化传承的主体角色,由于明确了师承关系,受教育的学子们往往继承学统,进行跨地域性的传播与生发。这是一个广泛的文化精英知识群体,不仅代表了浙江地域文化的人文流脉,在辽阔的时空背景下将文教传承事业薪火赓续,使之更具有深远的地域文化穿透意义。浙江文教空间与人文流脉重合现象历代延续,不胜枚举。南宋朱熹与浙江书院交往之密切,不仅表现在直接讲学于当时书院,也常因访友、问学、论道而成为各地书院之常客[16];元代大儒金履祥一生也讲学不辍,创办了仁山书院,还先后执教于严陵钓台书院、兰溪齐芳书院与重乐精舍,广授门徒,教育后进;元末明初大儒宋濂早年在东明书院求学,师从吴莱,后接任书院主讲一职,断断续续在东明书院学习、执教,学习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也有二十多年[17]。这种基于乡村书院的文化互动现象,既表现为横向“跨地域”间的薪火赓续,又展现出纵向“互动变迁”历时性的动态关联,在此意义上,文化与教育合一的属性已经突破了血缘、地缘、学缘、师承与学派的边界,使得乡村书院成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相互激荡、融合的场所,乡村书院成为文化传承最为真切的空间载体,并成为浙江传统社会中知识传播与思想孕育的孵化器。
5 结论
代代相续传承的浙江乡村书院,穿越千年且生命力强韧,不仅展现出体系性的民居建筑谱系特征,而且体现出创造性极强的营建能力和环境相适应的弹性,更反映出地域性鲜明的乡土情怀与传统观念传续中的韧性特质;其所具有的血缘凝结与地缘拓展相融合、文教空间与文化流脉相重合、耕读继世与家国情怀相聚合等核心特征,更加凸显了乡村书院作为心灵与精神纽带的强大黏性。首先,从空间维度上看,挖掘浙江乡村书院的在地性研究价值,探寻浙江乡村文教空间的生发机理与传续成因,将有助于理解地域性的浙江在中国主体性建构贡献中,所凝结形成的多元复合总特征的价值意义。其次,从时间维度上看,梳理浙江乡村书院丰富的形态特色与演化现象、风俗建设与学派流脉的互动进程,也将能够更为清晰地显现出,文教繁荣的浙江在文明长河的滚滚洪流中,不断地吸收、萃取、生发乃至反哺的互动进程。最后,从更广阔的人文视野来看,以乡村书院为载体的文教空间是一类融合了农业文明、儒家文化与商业文明、生态文明等多义文化载体,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互动意识,使之真正成为浙江地域精神塑造的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