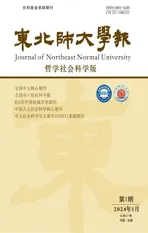古埃及神谕研究(公元前3000年至前1550年)
——基于原始文献与文化记忆理论的双重考略
2024-03-01李晓东
李晓东,李 雷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古埃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从古埃及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宗教一直是其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而神谕作为人与神双向交流的媒介,在古埃及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向神祇请询在新王国(公元前1550年—前1069年)(1)本文引述的古埃及年表依据《牛津古代埃及史》。参见:I.Shaw,ed.,“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3r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481-489.早期是法老的专属权利,神圣王权的合法性以及国家的重大决策都需要通过请询神谕的方式得到阿蒙神(Amun)的认可。在稍晚的阿玛纳时代(Amarna Period)(公元前1352年—前1336年),由于埃赫纳吞(Akhenaten)的宗教改革,基于阿蒙神崇拜的神谕仪式一度招致弃用,但在改革失败后旋即恢复,而且向神询问也不再是法老的专属。神谕实践从王室阶层延伸至贵族和祭司阶层,甚至传播至民间。世俗官员和神职人员的任命,皆须经由神谕决定。在麦地那工匠村(Deir el-Medina),神谕成为一种司法审判手段,用以裁决刑事案件或解决民事纠纷。总之,神谕不仅是法老掌控国家政治的工具,也成了官方、贵族、神职人员,甚至普通民众解决各类问题的重要途径。

神谕盛行于新王国已为不刊之论,其肇始于何时却是难以详考。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素来言人人殊,每每各执一端,向无定谳。以凯泽(O.Kaiser)、贝恩斯(J.Baines)等为代表的一派学者以新王国神谕仪式高度制度化的特征为切入点,基于形式逻辑和常理演绎出新王国之前存在早期原始形式神谕实践活动的结论,并试图从新王国以前的各类文献中探寻出神谕实践存在的证据(5)参见:O.Kaiser,“Das Orakel als Mittel der Rechtsfindung im alten gypten”,ZRG,Vol.10,No.3,1958,pp.193-208;J.Baines,“Practical Religion and Piety”,JEA,Vol.73,1987,pp.79-98;M.Römer,“Ist der Text auf den Blöcken 222/35/184 der Chapelle Rouge ein Zeugnis für eine neue ‘Dimension erfahrbarer Gottesnähe,’ (Assmann)?”GM,Vol.99,1987,pp.31-34.。以切尔尼)、扬·阿斯曼(Jan Assmann)等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则坚持主张在没有任何原典史料依据支撑的前提下,无法证明新王国的制度化神谕出现之前存在任何形式的神谕实践,也无法证明新王国神谕的出现是前人神谕实践的延续(6)参见:,“Egyptian Oracles”,p.35;E.Bedell,“Criminal Law in the Egyptian Ramesside Period”,PhD.Dissertation,Brandeis University,1973,pp.193,322;L.Kákosy,“Orakel”,p.602;J.Assmann,“gypten.Theologie und Frömmigkeit einer frühen Hochkultur”,Stuttgart:W.Kohlhammer,1984,p.188;P.Vernus,“La grande mutation idéologique du Nouvel Empire:Une nouvelle théorie du pouvoir politique.Du démiurge face à sa création”,BSÉG,Vol.19,1995,p.79.。职是之故,本文以古埃及文献和文化记忆理论为研究基础,重新考察了新王国以前神谕实践存在的可能性,并厘清了神谕兴起于新王国时期的多重原因,以期为古埃及神谕的溯源工作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点。
一、古埃及神谕的界定
汉语名词“神谕”,字面意思即“神的告知”。《说文解字》云:“谕,告也。”(7)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51页。通常语境下,“谕”作为告知之意时,专指由上级对下级的告知,如“上谕”“圣谕”等。日语中的“神谕”一词来源于汉语,写作“神託”(しんたく)。“託”在古代汉语中通“托”,有“托付”“委任”之意。以英语为代表的大多数印欧语系语言中,“神谕”(Oracle)一词的词源均可溯源至拉丁语动词ōrāre,意为“发起讲话”(8)J.Roberts,ed.,“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444-445.。西方学者遂以“神谕”(Oracle)这一术语来命名古埃及人向神祇请询并得到启示的宗教仪式。耐人寻味的是,古埃及人并没有为神谕仪式创造一个统一的名称。在古代埃及语中,没有任何一个单词可以被准确地译为“神谕”,只有一些与神谕仪式相关的术语。因此,这些术语成了界定古埃及神谕的重要依据。
起初,biAyt一词常被翻译作“神谕”(9)P.Lacau and H.Chevrier,“Une chapelle d’Hatshepsout a’ Karnak”,Vol.I,Cairo: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Égyptep,1977,p.160.。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这一翻译并不准确(10)T.Gillen,“The Historical Inscription on Queen Hatshepsut’s Chapelle Rouge:Part 1 biA.yt (‘Wonder’) and the Divine Oracle”,BACE,Vol.16,2005,p.2.。事实上,将其翻译为“神迹”(wonder)或“奇迹”(miracle)更为恰当(11)T.Gillen,“The Historical Inscription on Queen Hatshepsut’s Chapelle Rouge:Part 1 biA.yt (‘Wonder’) and the Divine Oracle”,p.6.。因为这个词在其所出现的语境中,通常是指神通过施展奇迹的行为,来表达对遵从他旨意之人的恩惠与认可。例如在《哈特舍普苏特加冕铭文》(TheCoronationInscriptionofHatshepsut)中,存在这样一段描述:“随后,她(哈特舍普苏特)匍匐在陛下(阿蒙)面前,说:‘您比以往更加伟大!是您,我的父亲,规划好了这世间的一切事务。我将忠实地遵从您的心愿与旨意!’随后陛下施展了诸多伟大的神迹(biAyt)。”(12)T.Gillen,“The Historical Inscription on Queen Hatshepsut’s Chapelle Rouge:Part 2 Translation”,BACE,Vol.16,2005,p.2.在这里,由于哈特舍普苏特忠实地遵从阿蒙的旨意,所以阿蒙施展神迹,以表达对她的恩宠,而非哈特舍普苏特有求于他而为其下达的神谕。尽管biAyt不可被直接理解为“神谕”,但其在神谕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常情况下,神在下达神谕的同时,也会为请愿者展示神迹,除了向请愿者表达恩慈之外,更是为了向旁观仪式的公众强调神谕的真实有效性(13)T.Gillen,“The Historical Inscription on Queen Hatshepsut’s Chapelle Rouge:Part 1 biA.yt (‘Wonder’) and the Divine Oracle”,p.3.。
nDwt-r直译为“建议”或“劝告”(14)L.H.Lesko and B.S.Lesko,eds.,“A Dictionary of Late Egyptian”,Vol.II,Providence:B.C.Scribe Publications,1984,p.41.,但在神谕叙事的语境,也通常被解读为“神谕”。研究表明,nDwt-r特指神祇在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上向国王提供的意见或建议。例如,哈特舍普苏特远征蓬特(Punt)(15)K.Sethe,“Urkunden der 18 Dynastie”,Vol.II,Leipzig:J.C.Hinrichs,1906,p.342.、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扩建卡纳克神庙(Karnak Temple)(16)K.Sethe,“Urkunden der 18 Dynastie”,Vol.III,Leipzig:J.C.Hinrichs,1907,p.833.以及图特摩斯四世(Thutmose IV)出兵努比亚(Nubia)(17)J.H.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Vol.II,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06,pp.115-118.时,他们都曾请示过阿蒙,而阿蒙所给予的回应在文献中都被称为nDwt-r。除此之外,在询问神祇关于其他事务的意见时,神的答复并不被称为nDwt-r,而是称为sr或xrtw。sr本义为“宣告”(18)L.H.Lesko and B.S.Lesko,eds.,“A Dictionary of Late Egyptian”,Vol.III,pp.69-70.,其应用范围比较广泛。xrtw本义为“陈辞”或“意见”(19)L.H.Lesko and B.S.Lesko,eds.,“A Dictionary of Late Egyptian”,Vol.II,pp.190-191.,在神谕语境中出现的时间较晚,常见于第十九王朝(公元前1295年—前1186年)以后的文献之中,并且特指非司法范畴的神谕(20)参见:D.Berg,“The Genre of Non-Juridical Oracles (xrtw) in Ancient Egypt”.。
pH-nTr和spr也是与神谕仪式相关的重要术语。pH-nTr意为“亲近神”(21)R.O.Faulkner,“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Oxford:Griffith Institute Ashmolean Museum,1991,pp.91,142.,spr意为“祈求”(22)R.O.Faulkner,“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p.223.。“亲近神”和“祈求”都是神谕仪式中的准备动作。在神谕仪式的正典叙事中,请愿者通常要先亲近神祇(pH-nTr),然后在神的面前祈求(spr),提出问题,并等待神的回应。例如《放逐石碑》(BanishmentStela)中记载:“随后,他再次走近伟大的神(pH nTr aA),并祈求(spr)说:‘我伟大的主啊!您可否以您之名下达一道伟大的敕令,以防止从今以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再被放逐到绿洲……’于是伟大的神表示十分赞同。”(23)R.K.Ritner,“The Libyan Anarchy:Inscriptions from Egypt’s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Atlanta: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2009,p.128.有鉴于此,pH-nTr和spr这两个术语成了判断文献中描述的宗教仪式是否为神谕仪式的重要依据。
卡科西(L.Kákosy)指出:“(古埃及)神谕和预言的边界始终是灰色的,许多神谕都是预示未来,(此外)神谕又常常被用于解决当前和过去的事务,如以神谕的形式发布敕令或以神谕的形式进行的司法裁决,而预言则不具备这些特征。”(24)L.Kákosy,“Orakel”,p.604.这表明,古埃及神谕与其他的占卜行为之间的界限相当模糊。因此,若要准确地界定神谕的具体内涵,不仅需要参考特定的术语,还需要考虑仪式的形式和内容。
古埃及的神谕仪式通常发生在宗教节日和祭祀活动的圣像巡游期间。此时,神祇的圣像在沐浴焚香后被安置于圣船或肩舆之中,由数名祭司抬出神庙,并沿固定的室外路线巡行。在一些特定的地点,巡行队伍会驻足停留以接受人们的询问。神祇将通过某些特定的方式以回应人们的请求。回应内容或为直截了当的“赞同”“反对”,或是给出明确的建议,无须由神职人员对神的话语进行二次解读释义。上文列举的《放逐石碑》中“伟大的神表示十分赞同”的表述足资证明。相较于神谕,预言在古埃及是一种更为常见的宗教行为。古埃及预言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例如对自然界中各种异常现象加以解释的预兆,或用天体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运动来解释未来命运的占星术等。《开罗第86637号历法》(TheCairoCalendarNo.86637)(25)参见:M.Bakir,“The Cairo Calendar No.86637”,Cairo:General Organization for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s,1966.对一年中每一日的凶吉做了定义,以指导人们趋吉避凶,这一做法类似于中国古代的黄历。但是预言通常是单方面就某种现象进行解释,它并不是人与神的直接沟通,更不是请愿者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下主动向神发起的请愿。在预言的语境下,同一种现象往往可以存在数种不同的解释,其中还不乏一些晦涩难懂或模棱两可的解读。由此可见,神谕和预言无论是在形式、内容和所发挥的作用上都存在显著的差异。
梦兆也容易与神谕相混淆。梦兆是通过解读梦境内容来占验凶吉的占卜形式,严格来说梦兆也属于预言的范畴,但情况又比一般的预言形式要更为复杂。多数情况下梦兆是基于对梦境内容的解读,而不是通过人与神的直接沟通来获得信息,因此较容易与神谕相区分。例如,《拉美西斯时代的梦书》(TheRamessideDreamBook)中记载道:“如果一个人梦到他嘴破了,吉兆,他所担心的事情,神将帮他解决……如果一个人梦到他正在吃无花果,凶兆,他将遭受苦难。”这类表述与中国古代的《周公解梦》十分类似。另一类梦兆,则是描述了人与神在梦境中直接交流的情形。例如著名的《图特摩斯四世梦碑》(TheDreamStelaofThutmoseIV)就提到了这种情况:年轻时的图特摩斯四世在吉萨大斯芬克斯(The Great Sphinx of Giza)旁小憩时,斯芬克斯出现在他的梦中,并请求他帮助清理掩埋在其身上的黄沙,斯芬克斯许诺如果他能帮忙,就会回报他在未来成功继承王位(26)W.Helck,“Urkunden der 18 Dynastie”,Vol.XIX,Berlin:Akademie Verlag,1957,p.1540.。不唯如此,第十九王朝的法老美楞普塔(Merenptah)也曾自述其在睡梦中收到了普塔(Ptah)的神谕,以帮助他反抗利比亚人的入侵(27)K.A.Kitchen,“Ramesside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Vol.IV,Oxford:B.H.Blackwell,1982,p.5.。第二十五王朝(公元前747年—前656年)末代法老坦沃塔玛尼(Tanutamani)同样声称其在梦中受到神的青睐,预示他将登基为王(28)T.Eide,T.Hägg and R.H.Pierce,“Fontes Historiae Nubiorum.Textual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Nile Region Between the Eighth Century BC and the Sixth Century AD”,Vol.III,Bergen:University of Bergen,Dept.of Classics,1994,pp.193-209.。梦境作为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情形。在古埃及,这类以神托梦为主题的梦兆经常出现在王室话语体系中。梦境中的内容,可以视为现实世界的延伸。其创作目的是向世人宣扬法老神圣王权的合法性(29)I.Shaw,ed.,“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p.254.。由此看来,其与神谕有着相似的功能,或可视为神谕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式。然而,就“做梦”这件事本身而言,并非神谕。因为做梦是人的潜意识行为,而非向神请示的主观行为。因此,在界定神谕时,只能涵盖现实语境中真实发生的仪式,而不包括梦兆。
概言之,古埃及的神谕仪式是请愿者与神祇之间在现实语境下进行的直接双向互动交流过程。请愿者亲近神祇并提出问题,神祇对问题做出回答并传达给请愿者,构成了一次神谕请询的完整闭环。请愿者向神请示的问题既可以是涉及当下的现实问题,也可以是对未来的预测。神谕的内容必须清晰明了地回应请愿者的问询。即使这个回答可能是由神职人员在背后操纵的结果,但明面上无须再由神职人员做进一步解读。通常情况下,神谕仪式应在特定的时间(如宗教节日或祭祀活动)及特定的场合(如神庙或圣像巡行路线)进行,并遵循某种特定的标准化仪式流程。在文献中,神谕仪式的流程以不同的术语作为呈现。因此,这些术语也是界定神谕仪式的重要依据。
二、新王国以前的神谕
“神谕”这个词的重点在于“神”和“告知”,强调的是神祇向人所传递的信息,即“神圣传达”。请愿者向神祇问询并得到启示,借此以解决当下问题或预知未来。这既是祈求神谕的目的,也是神谕所传达的结果。在新王国以前的文献中,既已出现关于神圣传达的表述。贝恩斯与帕金森(R.B.Parkinson)认为,第五王朝(公元前2494年—前2345年)的《马加拉旱谷石刻》(ARockInscriptionatWadiMaghara)中“神亲自书写之文书”的表述可以视为请询神谕存在的早期证据之一(30)J.Baines and R.B.Parkinson,“An Old Kingdom Record of an Oracle? Sinai Inscription 13”,in J.van Dijk,ed.,“Essays on Ancient Egypt in Honour of Herman te Velde”,Leiden:Brill,1997,p.10.。贝恩斯还指出,类似的描述也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古埃及经典文学作品《辛努西的故事》(TheStoryofSinuhe)(31)参见:A.M.Blackman,“Middle-Egyptian Stories”,Turnhout:Brepols,1972,pp.1-41.主要讲述了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985年—前1773年)的一位官员辛努西(Sinuhe),因担心自己卷入一场宫廷政变而被迫从埃及出逃,最终逃亡至巴勒斯坦一带的经历。至于为何会逃往巴勒斯坦,辛努西本人说道:“我不知晓何人将我带至此国度,这好似神的旨意,正如一个住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人发现自己身处象岛(32)古埃及南部地名,又名埃里芬梯尼(Elephantine),位于今阿斯旺附近。(Abu),抑或是来自沼泽之地的人却身在弓之国(33)古埃及对古代努比亚(今苏丹)的代称。(The Land of the Bow)。”(34)R.B.Parkinson,“The Tale of Sinuhe and Other Ancient Egyptian Poems 1940—1640 B.C”,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pp.21-53.故事中提到的“神的旨意”也是一种神圣传达。
两篇文本内容中“神亲自书写之文书”和“神的旨意”的表述,的确表明了神圣传达的存在和介入。然而,两篇文献均未提及传达信息的具体神祇,也未说明“文书”和“旨意”是以何种方式书写和表达,更未透露“文书”和“旨意”的具体内容。因此,仅凭零散的描述就断言文献证明了神谕存在,结论未免偏颇。诚然,“神亲自书写之文书”和“神的旨意”都可以被认为是神圣传达存在的证据,但却不能作为神谕存在的直接证据。神圣传达只是神谕仪式的表征之一,并不完全等同于神谕。以古埃及人的虔信程度,在神谕语境之外也可能存在神圣传达。而神圣传达与早期神谕实践之间的关系,仅凭这两篇文献中的表述还不足以给出明确的答案,故须审慎对待。
关于神圣传达的表述也出现在新王国以前的自传体铭文中,并且更为明晰。所谓自传体铭文,是指镌刻于古埃及达官显贵陵寝上层的一种铭文,主要记叙其生平事迹与成就,以供后世瞻仰。第一中间期(公元前2160年—前2055年)的赫拉康坡里斯州(Hierakonpolis)州长安赫提菲(Ankhtifi)在其自传体铭文中提到:“为了重建它,荷鲁斯将埃德弗州送给我,愿长寿、稳固和安康,我将(它)建成。荷鲁斯希望它能被重建,因此他把它送给我就是为了重建它。”(35)译文参见: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中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21页。根据铭文表述,安赫提菲重建埃德弗州是因为荷鲁斯神将其托付于他,并得到了神的祝福。换言之,安赫提菲对埃德弗州的统治权来自于荷鲁斯的神圣授予,奠立了其统治权的合法性来源。神圣授权是神圣表达的典型形式之一,也是新王国时期神谕仪式的主要目的之一。在王室神谕语境中的“君权神授”,以及通过神谕任命官员、祭司等,都是通过神圣授权来表达的。无独有偶,《霍姆哈乌夫自传体铭文》(BiographicalInscriptionofHaremkhauef)中也有关于神圣传达的描述。据此铭文记载,霍姆哈乌夫(Haremkhauef)生前曾是赫拉康坡里斯的荷鲁斯首席大祭司,他接受荷鲁斯的指派,从赫拉康坡里斯启程前往当时的首都伊奇塔维(Itj-tawy)。在此次任务中,国王委托他护送两尊为赫拉康坡里斯州全新打造的圣像回到荷鲁斯神庙,并将圣像安置妥当(36)J.Baines,“Practical Religion and Piety”,p.89.。根据铭文中的描述,霍姆哈乌夫的护送任务并非由国王指派,而是来自于荷鲁斯的神圣授权,这说明新王国以前的神圣传达不仅能授予世俗官员的统治权,亦可决定宗教领域的重大事务。
神谕仪式中的一些特定术语在新王国以前的各类文献中也有所呈现,这为勾勒神谕在新王国以前的图景提供了重要线索。例如,在第十一王朝(公元前2055年—前1985年)国王孟图霍特普四世(Mentuhotep IV)在位时期,有一篇来自哈玛玛特旱谷的石刻铭文(Wadi Hammamat),记录了在泛滥季第2月(37)泛滥季(Axt)为古埃及传统历法中一年中的第一季度,大致相当于公历的7月至11月,泛滥季第2月即相当于公历8月,是埃及一年中最为炎热干燥的季节。参见:J.P.Allen,“Middle Egyptian: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Hieroglyphs”,2n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07.第23日,敏神(Min)施展“神迹”(biAyt),以雨水的形象出现在沙漠中心,以滋养在沙漠中因长途跋涉而口干舌燥的远征团成员(38)I.Shirun-Grumach,“On ‘Revelation’ in Ancient Egypt”,in S.Schoske,ed.,“Akten des Vierten Internationalen gyptologen-Kongresses München 1985”,Hamburg:Buske,1989,pp.380-381.。在这篇文献中,作者用了神谕叙事中常出现的术语biAyt来描述敏神化身为雨的举动。另一篇文献为哈特奈布地区(Hatnub)的一处涂鸦,书写于第十二王朝,但具体年份不详,只知道记录于当地首领奈赫瑞(Nehery)统治的第6年(39)R.Lepsius,“Denkmäler aus gypten und thiopien”,Vol.II,Berlin:Nicolaische Buchhandlung,1849,pl.149f.。文献中写道:“当建议(nDwt-r)下达后,他(奈赫瑞)按照他(40)此处“他”指某位神祇,具体不详。的命令行事。”(41)E.Blumenthal,“Die Datierung der Nhri-Grafliti von Hatnub”,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Vol.4,1976,pp.35-62.根据文献的表述,一位神祇下达了一道敕令,并且文献中所用的术语是nDwt-r。上文提到,在神谕语境下,该术语仅为神给予国王的意见或建议。但是,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055年—前1650年)埃及地方割据现象比较明显,地方首领常常自居为国王,出现僭越行为也并不罕见。在古埃及文献中,通常只会以在任国王的统治年份纪年。然而,在这篇文献中,奈赫瑞并未采用当时国王的统治年号,而是使用其本人的在位年份纪年,这一细节体现了他的政治野心。不宁唯是,奈赫瑞还毫无保留地使用nDwt-r这一王室神谕语境下的术语来表述神祇传达的敕令,此举生动反映了地方割据政权企图与神祇构建关系以强化其自身的政治地位,并通过神圣传达甚至神谕仪式来获取权力合法性证明的初步实践。
在与《辛努西的故事》齐名的经典文学作品《遇难水手的故事》(TheTaleoftheShipwreckedSailor)(42)A.M.Blackman,“Middle-Egyptian Stories”,pp.45-48.中首次出现了pH-nTr这一术语(43)M.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Vol.I,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pp.111-113.。虽然pH和nTr都是埃及语中常见的基础词汇,但是pH-nTr作为一个固定搭配的词组,几乎只出现于神谕语境之下,而且是神谕文献的书写和表达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术语。该故事没有描写主角亲近神祇之后与神之间进一步的互动过程,也就是未能体现以特定目的向神请愿并得到回应的这一过程,所以无法推断后续事件一定与神谕相关。但是,故事中对于这一术语的使用仍然值得被关注和研究。
古埃及神谕请示的对象是“神”。古埃及宗教是基于自然崇拜的多神教,光是有确切名称的神祇就多达1500多位。新王国时期,神谕所请示的神主要是国家主神阿蒙以及其所衍生出的各种地方性神祇,其中还包括神化的国王阿蒙霍特普一世(Amenhotep I)。新王国以后的神谕中出现过托特(Thoth)、荷鲁斯等神祇,但总体而言,新王国以来的标准化神谕是基于阿蒙神崇拜的一种宗教活动。然而,阿蒙神崇拜的兴起是自中王国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即使假设存在神谕,其请示对象不应仅限于阿蒙,还可能为其他神祇。古埃及除了基于自然崇拜的多神宗教外,还存在先祖崇拜。古埃及人认为逝去的祖先会进入永恒的世界,并且可以护佑家人。因此,如果被请示的对象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神祇,而是包括其他拥有超自然能力的对象的话,那么写给死者的信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认定为一种神谕请询。写给死者的信是埃及历史上一种别具一格的文献类型,迄今共发现15封。死者的亲属在现世中遭受苦难、陷入困境时,会写信给死者求助,以期借死者的能力得到帮助(44)金寿福:《从写给死者的信看古埃及妇女的社会地位(公元前2100年至前1300年)》,《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这与请询神谕的目的并无二致。例如,在一封十一王朝末期的信中,一位寡妇声称自己遭受到他人迫害,希望亡夫能够在神所主持的法庭提起诉讼,让迫害她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45)金寿福:《从写给死者的信看古埃及妇女的社会地位(公元前2100年至前1300年)》,《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这说明古埃及人的信仰对象和求助对象并不仅限于我们所认知的“神祇”。事实上,我们也难以用一般的概念来限定古埃及的神祇。在古埃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甚至抽象概念,都可以被当作神祇膜拜,已故亲人自然也不例外。对于古埃及平民而言,以阿蒙为代表的国家神祇过于遥远和陌生,并不能与之产生情感共鸣。而他们逝去的亲人远比这些高高在上的神祇更为熟知自己的境遇,也更贴近自己的日常生活。因此,在古埃及普通平民看来,祈求已故亲人的帮助与祈求神祇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总之,向逝者发送书信求助的行为,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向“神”请示的交流沟通行为,具备神谕的部分特征。
综上所述,神谕仪式的典型特征,包括神圣传达、特定术语的运用、请愿者的主动祈求等,都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形式呈现于新王国以前的各类文献之中。这意味着探寻神谕起源的视域须从新王国回溯至更早的历史时空中。然而,需要注意,截至目前已探明的早期文献中的相关表述,都只能部分反映神谕的特征,并未完整展现神谕的全貌。埃及学是一门基于文献证据和考古证据研究的严谨学科,历史学家解释事实也以不违背证据为底线,不崇尚对证据的过度解释(46)赵轶峰:《历史研究的新实证主义诉求》,《史学月刊》2018年第2期。。因此,须辩证看待新王国以前的文献之于古埃及神谕研究的意义。既要根据文献所蕴含的信息探索新王国以前存在神谕的可能性,也须明晰这些早期文献并不能被简单粗暴地理解为证明神谕存在的直接证据。
三、“隐性文化”中的神谕
20世纪90年代,德国埃及学家扬·阿斯曼及其夫人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基于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构建的集体记忆理论,发展形成了文化记忆理论(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47)金寿福:《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外国语文》2017年第2期。。扬·阿斯曼的这一理论认为:“文化记忆并不一定与文字相联系,它也可以借助仪式、神话、图像和舞蹈保存下来。但是在有文字的文化里,文字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在古代埃及,文化记忆主要是借助文字和书写传播的。”(48)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金寿福译,《光明日报》2016年3月26日,第11版。凭借文字和书写传播的文化记忆在古埃及文明中又可以分为“显性文化”(Dominant Culture)与“隐性文化”(Recessive Culture)两种表现形式。所谓显性文化,即主流文化,其表达载体包含神话故事、教谕文献以及自传体铭文等。显性文化是由上层统治阶级书写表达,传递的都是统治阶级所认可并倡导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目的在于维系统治稳固与社会安定(49)J.Assmann,“Religion und Kulturelle Gedächtnis”,München:C.H.Beck,2004,pp.47-49;J.Assmann,“gyptische Religion:Totenliturgien”,Frankfurt am Main:Verlag der Weltreligionen,2008,pp.616-617;J.Assmann,“Altägyptische Totenliturgien”,Heidelberg:Universitätsverlag C.Winter,2010,pp.467-469,转引自金寿福:《从写给死者的信看古埃及妇女的社会地位(公元前2100年至前1300年)》,《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由于显性文化由国家机器所主导,文本被置于醒目的公共区域中,因此备受整个社会关注,影响深远,故而流传至今,为人所熟知。而隐性文化,作为非主流文化,往往被掩盖于显性文化之下,或隐藏在显性文化的主流叙事之外。金寿福指出,隐性文化反映的是“个体瞬间和偶然的感受”,“有时显得微不足道,容易被人忽视”(50)金寿福:《从写给死者的信看古埃及妇女的社会地位(公元前2100年至前1300年)》,《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因此,隐性文化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
在新王国以前,反映神谕某些特征的文献绝大部分都属于隐性文化的范畴,例如文学作品、石刻铭文、涂鸦、信件等。这些文献并非由官方机构所撰写,其书写目的也非宣扬正统价值体系与伦理道德,而是流传于民间,表达个体情感感受的非主流文化产物。自传体铭文本身属于显性文化的范畴,“是官吏们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媒介,以此表现他们生前尽职尽守,未曾滥用手中的权力,以期获得后人的纪念和回报”(51)金寿福:《从写给死者的信看古埃及妇女的社会地位(公元前2100年至前1300年)》,《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但上文列举的《安赫提菲自传体铭文》和《霍姆哈乌夫自传体铭文》中,涉及神圣传达和神圣授权的描写并非自传体铭文的叙事主体,更非铭文的写作目的。这部分描写只是自传体铭文写作的副产品,是隐藏在显性文化下的隐性文化。古埃及人极为重视的来世观念和祖先崇拜理应属于显性文化,那为何写给逝者的信件又归为隐性文化呢?金寿福给出的解释是,这些信所透露的是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生活处境和宗教情怀,并且其隐性特征还体现在它们被置于坟墓的下层,这一层在“死者入葬后不久便被封死,如果不是现代考古活动,置于其中的这些信可能仍旧尘封地下”,不会为人所知(52)金寿福:《从写给死者的信看古埃及妇女的社会地位(公元前2100年至前1300年)》,《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基于这一阐释,写给逝者的信件应当归属于隐性文化的范畴。总而言之,新王国以前各类文献中涉及神谕特征的文献都蕴含于隐性文化之中。鉴于此,即使提出“新王国以前存在神谕”这一假设性结论,那么这种神谕实践也只可能是个体的宗教自觉性行为,而非一项有严格规范的宗教制度。因此,显性文化中难以寻到神谕在此期间存在的证据,与之相关的书写和表述皆藏于隐性文化之下,被历史所忽视。
在新王国以前,神谕之所以未被纳入国家主流宗教体系,成为一种显性文化,主要是由古埃及早期神权和王权观念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在古埃及王权国家建立之初,国王在叙事语境中通常被描述为荷鲁斯神在人间的化身。例如,第一王朝(约公元前3000年—前2890年)国王荷鲁斯-奥哈(Hor-Aha)的名字意为“战斗者荷鲁斯”,荷鲁斯-登(Hor-Den)的名字意为“开辟者荷鲁斯”,荷鲁斯-杰尔(Hor-Djer)的名字意为“捕获者荷鲁斯”等(53)金寿福:《古代埃及神权与王权之间的互动和联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在这一时期,国王即是神,国王的权力是由于其与神相一致的身份而与生俱来的,并不需要通过后天获取,体现了王权与神权的相统一。自第四王朝(公元前2613年—前2494年)开始,太阳神信仰逐渐兴起,国王成为“拉神之子”(Son of Ra),是太阳神在人间的代表,金字塔与《金字塔文》(ThePyramidTexts)都是国王与太阳神信仰紧密联系的标志。在这一时期,国王的本体不再是“神”,其神性不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与神构建亲密关系而实现的(54)金寿福:《古代埃及神权与王权之间的互动和联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此时的国王兼具了人与神的双重属性。古王国(公元前2686年—前2160年)末期兴起的奥西里斯(Osiris)神话同样将国王描述为神祇的后代,并且是奥西里斯神的唯一合法继承人。金寿福指出,国王“拉神之子”的身份“意在明确国王谱系的神圣性”,而“奥西里斯之子”(Son of Osiris)的身份“强调了埃及国王所拥有的世袭的王位继承权”(55)金寿福:《古代埃及神权与王权之间的互动和联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总之,古埃及王权国家早期的王权的神圣性直接来源于神权。在这种神学体系下,王权的合法性不需要通过神谕向公众彰显,而是通过与诸神建立特殊关系得到巩固,所以神谕并未出现在显性文化叙事中。
在古王国末期,王权逐渐式微,随之而来的是动荡和无序的第一中间期。在这一社会背景下,王权的神圣性受到质疑。“中王国的统治者借助文学作品把第一中间期回忆成没有秩序、没有信仰的混乱岁月。”(56)金寿福:《古代埃及神权与王权之间的互动和联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因为信仰的崩溃,神圣秩序被奸邪之徒破坏,神祇们不得不选择离开人间。在这一神学语境下,中王国的国王被视为神在人间的代理人,以协助诸神恢复人间的和谐秩序,体现了王权的重要性,“虽然国王的神性有所淡化,但王权的合法性和绝对性得到神学支撑”(57)金寿福:《古代埃及神权与王权之间的互动和联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国王作为神在人间的代理人,有义务定期与神进行沟通,这既是国王的责任,也是维系王权神圣性的必要手段。为了实现与神的沟通,需要以神庙和神像作为媒介,并通过宗教节日和祭祀活动召唤神的降临。
古埃及神庙体现了一种由“隐秘”和“开放”两方面所组成的结构二元论(58)B.Kemp,“Ancient Egypt: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New York:Routledge,1991,p.185.。早期的神庙强调“隐秘”的特性,其建筑规模普遍较小,既没有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的公共仪式空间,也不对普通民众开放,普通民众仅能在神庙外围朝觐。神的圣像更是置于神庙主殿的最深处,只有少数高级神职人员可以接近。在中王国时期,进行宗教节日和祭祀活动的公共仪式空间开始建立,深居于神庙中的神祇也开始以神像巡行的方式将形象展现于公众面前。神像巡行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至第十一王朝。国王孟图霍特普二世(Mentuhotep II)建立了一条从尼罗河东岸的底比斯(Thebes)至西岸的巴哈里(Deir el- Bahari)的神像巡行路线,并在沿途设置了供巡行队伍休息的驻足点(59)M.Ullmann,“Thebes:Origins of a Ritual Landscape”,in P.F.Dorman and B.M.Bryan,eds.,“Space and Sacred Function in Ancient Thebes”,Chicago:Oriental Institute,2007,pp.7-9.。第十二王朝的国王塞索斯特利斯一世(Senusret I)建立了一条位于尼罗河东岸的南北向巡行路径,并固定于每年的重大宗教节日和祭祀活动时进行神像巡行(60)M.Ullmann,“Thebes:Origins of a Ritual Landscape”,pp.7-9.。神像巡行仪式将神的形象置于公共空间之中,这使得更多人有机会亲近神祇,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神权和王权概念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此外,宗教节祭与巡行仪式也为人们向神祇祈求请愿奠定了时间基础和空间基础。
起初,阿蒙神还只是底比斯的地方性神祇,斯时的底比斯也不过是埃及南部的一座规模相对较小的城镇,还不为世人所熟知。阿蒙神崇拜在中王国时期被纳入国家宗教体系,阿蒙逐渐发展成为国家主神。第十二王朝的开国国王阿蒙尼姆赫特一世(Amenemhat I)是最早与阿蒙建立特殊关系的君主。为了彰显其对阿蒙神的崇拜和敬仰,这位国王将其名字与阿蒙之名结合,取名“阿蒙尼姆赫特”,意为“居于前位的阿蒙神”(61)R.J.Leprohon,“The Great Name:Ancient Egyptian Royal Titulary”,Atlanta: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2013,pp.57-58.,进而可引申为“阿蒙是我的领路人”(62)金寿福:《古代埃及神权与王权之间的互动和联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之意。阿蒙尼姆赫特一世选择与这位普通的神祇建立联系可能与其出身平民但最终登基为王的身世有关,但这与本文的主旨相去甚远,在此不再赘述。他的继任者塞索斯特利斯一世更是为阿蒙大兴土木建造了卡纳克神庙(63)M.Ullmann,“Thebes:Origins of a Ritual Landscape”,p.8.。在此之后还有三位国王也采用“阿蒙尼姆赫特”作为自己的王名,进一步强调了阿蒙的国家主神地位,阿蒙神崇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在古埃及,观念的演化与发展通常不是通过全新的构思或对现有思想观念的反驳来表达,而是通过巧妙地转移重点,并且始终在同一神学语言的框架之内(64)S.Bickel,“Worldview and Royal Discourse in the Time of Hatshepsut”,in J.M.Galán,B.M.Bryan and P.F.Dorman,eds.,“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Reign of Hatshepsut:Papers from the Theban Workshop 2010”,Chicago:Oriental Institute,2014,p.21.。中王国时期,神权和王权的互动联动不仅推动了埃及神学体系的发展,还奠定了新王国制度化神谕的观念基础和物质基础。发迹于底比斯的第十七王朝(约公元前1580年—前1550年)政权也尊崇阿蒙。其首领阿赫摩斯(Ahmose)成功驱逐了外族统治者希克索斯人(Hyksos),重新统一埃及,建立了新王国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50年—前1069年),将埃及文明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阿赫摩斯的继任者阿蒙霍特普一世承袭中王国修建神庙的传统,倾注大量王室资源,扩建了塞索斯特利斯一世建立的卡纳克神庙。阿蒙霍特普一世强调神庙的“开放”特性,在神庙中建立仪式的公共空间,从而使阿蒙神崇拜的影响力空前壮大。底比斯作为阿蒙神崇拜的发源地,也成为新王国的政治和宗教中心。
阿蒙霍特普一世去世后,他的嫡子图特摩斯一世(Thutmose I)继承了王位。但是,图特摩斯一世的嫡子夭折,因此他去世后王位只能由其庶子继承,是为图特摩斯二世(Thutmose II)。按照古埃及的传统,作为庶出之子的图特摩斯二世必须娶一位拥有纯正王室血统的女子为王后,于是他娶了已故法老图特摩斯一世的嫡女,也就是他同父异母的长姐哈特舍普苏特为妻,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然而,图特摩斯二世自幼体弱多病,登基不久后即驾崩。由于其与哈特舍普苏特仅育有一女,故也只能选择由庶出的年幼王子即位,是为图特摩斯三世。图特摩斯三世出身低微且年龄尚幼,而他继母的哈特舍普苏特作为图特摩斯一世的嫡女,血统高贵,实质上将大小政务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国王的权力被完全架空。然而,哈特舍普苏特显然并不满足于此,遂在她摄政第七年时自立为法老,与图特摩斯三世实行共治,成了埃及的最高统治者。
在古埃及这个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中,女性夺取最高权力虽不说前所未有,但也实属罕见。这导致哈特舍普苏特的夺权遭受到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哈特舍普苏特统治期间,强调“复兴传统”(65)D.Arnold,“The Temple of Hatshepsut at Deir el-Bahri”,in C.H.Roehrig,ed.,“Hatshepsut:From Queen to Pharaoh”,New York: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2005,p.135.。一方面,她效仿古王国君主,宣称自己是“阿蒙之女”(Daughter of Amun),强调其与阿蒙之间的亲密联系。另一方面,她也追随中王国君主的脚步,宣扬这个世界受到了邪恶之人的破坏,而她的任务就是重建国家,恢复正义和秩序,以期通过神学的支持确立其王权的合法性(66)L.Gabolde,“Hatshepsut at Karnak:A Woman under God’s Command”,in J.M.Galan,B.M.Bryan and P.F.Dorman,eds.,“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Reign of Hatshepsut:Papers from the Theban Workshop 2010”,Chicago:Oriental Institute,2014,pp.33-48.。为了进一步强调自己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哈特舍普苏特新建了大型神庙,扩建了巡行路径,并且恢复了定期举行宗教节日和祭祀活动的传统。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扩展了仪式的空间单元,也扩展了仪式的时间单元。哈特舍普苏特在巴哈里的孟图霍特普二世神庙旁建造了一座规模空前的丧葬神庙,其位置正好与卡纳克神庙隔尼罗河相望。随后,她又在两座神庙之间建立了一条东西向的巡行路径,以卡纳克神庙中新修建的红色圣堂(Chapelle Rouge)作为巡行路线的起点,通过卡纳克第一塔门(The First Pylon of Karnak)由尼罗河水路最终到达巴哈里(67)G.Haeny,“New Kingdom ‘Mortuary Temple’ and ‘Mansions of Millions of Years’”,in B.E.Shafer,ed.,“Temples of Ancient Egypt”,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95.。卡纳克神庙至卢克索神庙(Luxor Temple)的节日巡行传统也可追溯至哈特舍普苏特统治期间。她进一步完善了塞索斯特利斯一世建立的南北向巡行路径。这条线路同样以红色圣堂为起点,经卡纳克第八塔门(The Eighth Pylon of Karnak)至公羊大道(The Avenue of Sphinxes),最终抵达卢克索神庙(68)M.Ullmann,“Thebes:Origins of a Ritual Landscape”,p.11.。
考古学家分别在巡行路径的起点红色圣堂和终点巴哈里丧葬神庙中发现了同一篇记载哈特舍普苏特加冕仪式的铭文的两个副本,遂将之命名为《哈特舍普苏特加冕铭文》(69)参见:P.Lacau and H.Chevrier,“Une chapelle d’Hatshepsout a’ Karnak”,pp.97-153.。这是截至目前已知的关于古埃及神谕仪式最早的记录,恰恰说明该片区域是最早举行国家神谕仪式的场所。根据铭文记载,在一次宗教节日巡行中,阿蒙神通过下达神谕的形式,授予哈特舍普苏特王权,并在公众的见证下“亲自”为其加冕。通过这种“君权神授”的神圣传达,哈特舍普苏特在众神的护佑和民众的拥戴下登上了国王的宝座,她的合法统治地位在神谕的加持下最终得以确立。神谕自此开始走进显性文化。此后,神谕仪式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并经常被记录于主流叙事之中。
结 语
古埃及新王国以前的各类文献零散地记载了神谕的部分特征。这些记录为追溯神谕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但切忌过度解读,不要将其作为神谕存在于新王国以前的直接证据,否则将违背历史学论证的逻辑。神谕在新王国以前可能表现为以祈求神祇为表征的个体自发性的宗教行为,应属于隐性文化的范畴。早期神谕未能进入显性文化,是由古埃及早期神权和王权观念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王权国家建立之初,王权与神权具有强烈的一致性,王权即为神权。古王国时期,太阳神崇拜和奥西里斯神话都强调国王与神祇的亲密联系,以彰显王权的神圣性与排他性。中王国时期,国王作为神在人间的代理人,其神性被淡化,人性被突显,但神学观念为维系王权合法性提供了保障。这段时期的神权与王权之间的交互形式,足以保障王权稳固,不需要借助神谕仪式的参与。中王国以来阿蒙神崇拜的兴起,仪式公共时空单位的建立,为神谕的制度化奠定了观念基础和物质基础。新王国的女法老哈特舍普苏特复兴传统,效仿前朝君主对于王权合法性的构建,但仍不足以面对云谲波诡的政治环境。出于统治目的,哈特舍普苏特通过直接面向公众的神谕仪式,以“君权神授”的神圣传达话语进一步强化了其对于统治地位合法化的诉求。神谕自此被纳入国家宗教体系,成了显性文化。神谕仪式开始形成标准范式,逐步趋于制度化,在古埃及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被广泛传播,为人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