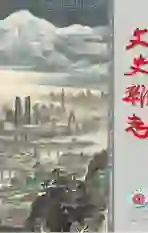鲁迅小说《药》中的“康大叔”与“黑的人”
2024-02-28唐雨
唐雨
摘 要:鲁迅小说《药》中“康大叔”与“黑的人”并非同一人。前者属于鲁迅所说“愚弱的国民”“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后者是杀害革命者的职业刽子手。比较后者,以康大叔为代表的社会普通人对生命的冷漠、对革命的漠不关心,更令人寒心与不安。而这,正是鲁迅要唤醒民众,一起为革命理想共同奋斗的原因。
关键词:人血馒头;抽象与具象;改造国民精神
鲁迅小说《药》中的“康大叔”到底是谁?他与刽子手“黑的人”是否是同一人?这些疑问自上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提出,并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最初学术界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大约从80年代开始,认为“黑的人”就是“康大叔”,“康大叔”就是“黑的人”的观点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此后的部分教科书和教师用书甚至直接将二人等同混用,以刽子手的名号来代指“康大叔”,似乎这一问题已经解决、已下定论。笔者重新思考“康大叔”与“黑的人”二者间的关系,以确定“康大叔”与“黑的人”不是同一人为起点,来探究鲁迅《药》的写作方法和思想深度,以及小说的多重主题和社会意义。
一、“康大叔”是不是“黑的人”
(一)认为二者是同一人
许多学者曾就“康大叔”是不是“黑的人”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并在上世纪80年代愈演愈烈,但是似乎“康大叔”就是“黑的人”这一研究观点最后占据上风。例如学者陈德滋1985年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中发表的《〈药〉中“黑的人”就是“康大叔”》,叶闰桐于1991年在《上海鲁迅研究》中发表的《我认为康大叔就是刽子手》等等文章,都一致认为“康大叔”就是“黑的人”,就是杀害夏瑜的刽子手。
后来的部分教科书与教师用书也承袭了这一观点。人教社《语文第四册教师教学用书》2001年版说,在肖像描写部分,对康大叔的肖像描写最为精彩:“浑身黑色的人”“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满脸横肉”“披一件玄色衣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这本教参书讲,只这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个凶残、蛮横的刽子手形象。[1]人教社《语文》第四册(2001年版)《药》的课后“练习”第三题第2小题例举:“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拴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拴,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练习题就此发问:上面两段文字表现了康大叔什么样的性格特征?)[2]显然,2001年版的人教社教材与教参均认为“黑的人”与康大叔就是同一人。
(二)二者不是同一人的证据
那么“康大叔”究竟是不是“黑的人”呢?笔者认为小说中并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康大叔和“黑的人”是一个人。恰恰相反,小说中却有许多材料足以证明康大叔绝不是“黑的人”。“一个浑身黑色的人”是夏瑜被执行死刑时直接参与行刑的刽子手;而康大叔则是负责牵线搭桥,为“客户”提供信息的中间介绍人。
一是从华老栓“买药”、刽子手“卖药”时的具体情景分析。原文中写道: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搶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3]
从描写的交易现场可以看出华老栓完全不认识刽子手。若真见到的是茶馆里的常客康大叔,华老栓就不会表现出那么慌乱紧张的模样——“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此时,老栓害怕的不是还在滴着温热的血的人血馒头,而是害怕面前站着的“眼光正像两把刀”的“浑身黑色的人”,害怕直视刚行刑完毕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老栓若是怕人血馒头,就不会在回家路上像揣稀世珍宝似的揣着人血馒头,“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人血馒头此刻于他而言,是救儿子性命的灵丹妙药,是花费家中大半积蓄,且好不容易有门路“运气好”才有机会买来的,此刻珍惜还来不及,又怎么会害怕呢?因此,华老栓唯一害怕的只会是面前这个“浑身黑色的人”。同时,还可以从刽子手称呼老栓是“老东西”看出刽子手不认识老栓。如果两人相互认识,并像在后文茶馆中那样熟识、常见,那么刽子手断不会使用“老东西”这样笼统且带有侮辱性的称呼,而应当顺口称呼他为“老栓”,也不会非常谨慎防备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二是从康大叔在茶馆中的言语来分析。在第三节中,康大叔终于缓缓在茶馆出场,现身第一句话便是“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首先,在这里康大叔直呼华老栓为“老栓”,说明二人相熟且关系不错,因此前文中直呼华老栓“喂”“老东西”的刽子手不会是康大叔。其次,这句“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这里的“信息灵”是指康大叔知道犯人会在何时何地被处决。一名刽子手能够轻易知道在何时何地杀人,这是职业分内之事,而只有行业外部人员通过特殊渠道层层打听后,了解到寻常人无法知晓的信息,才能称之为“信息灵”。所以,康大叔自称的“信息灵”就不能说明他就是刽子手,而是指他有渠道打听消息。在买卖“药”的交易中,康大叔实际上是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中介作用——介绍买卖双方,即老栓与刽子手建立起生意关系。因为康大叔提前知道夏瑜在后半夜就会被处决,华老栓不出意外现在肯定已顺利拿到人血馒头,所以才会一进门就高声问“吃了么?好了么?”
并且,当花白胡子低声下气地向康大叔打听夏瑜时,康大叔回应道:“……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康大叔如果就是杀害夏瑜的刽子手,那么他才在天亮前赚取了华老栓满满当当的一包洋钱,又怎能当着老栓的面高声抱怨说自己“一点没有得到好处”呢?唯一的解释就是“康大叔”不是那个刽子手,没有利用夏瑜的血赚钱,所以他才会认为夏瑜的可用价值全被华老栓、夏三爷和红眼睛阿义占去了。
三是从康大叔与刽子手的外在形象分析。康大叔身着“玄色布衫”,而刽子手也是身穿黑色衣服。这身“黑色衣服”也就常常成为人们把康大叔认同为刽子手的“铁证据”。但只要对刽子手的“黑衣”服饰加以分析,就能发现仅从衣帽看是不对的。
刽子手在大清是官方职业,其衣着打扮有着严格要求。影视剧中,古代刽子手也大都身着黑衣,可以说“黑衣”是刽子手们的职业制服。同时,《药》也描写了行刑前为防止夏瑜的“同党”劫法场而执行警戒的“兵”的装束:“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色的镶边。”可见清朝的官方人员在工作时着装都是统一规整的。由此可以表明,《药》中刽子手身着“黑衣”是其身份的代表、职业的装束。而康大叔出场的外貌形象,则更像是社会上成天无所事事的地痞流氓、小混混。其随意不讲究的穿着打扮(虽也着玄色布衫),说明康大叔不是行刑者,不是“黑的人”。
二、区分二人的意义
(一)丰富看客的身份类型
确定康大叔不是刽子手“黑的人”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康大叔是谁?他的身份信息、社会地位如何?
“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4]康大叔一点不在乎直说华小栓得“痨病”会让华大妈心生不满,更是加大了音量高声大叫地“嚷”,“嚷得里面睡着的小栓也合伙咳嗽起来”,说明他并不是因为关心病人真心地想要为其治病而积极询问病情和药效。他大声嚷嚷只是在向茶馆大众炫耀自己能耐通天,炫耀自己“信息灵”。“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绽放,越发大声……”在众人崇拜渴望的眼神中,康大叔的虚荣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康大叔此话是在旁敲侧击向华老栓一家邀功要赏。从他标榜“要不是我信息灵”的话来看,他认为自己在买卖药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华老栓一家应该将自己当做救命恩人一般地重金酬谢自己。这突显出他的贪得无厌、欲壑难填。
花白胡子向康大叔问话时低声下气,并且“康大叔显出看不上他的样子”;华老栓面对康大叔时脸上堆着笑,恭恭敬敬,华大妈也“很感激的谢他”;牢头阿义被驼背五少爷敬称为“义哥”,但康大叔要么直呼其名,要么叫绰号“红眼睛”。从茶馆众人对康大叔的言语和态度,可见其地位远在牢头之上。他在茶馆中的话语、神态和声调,无不显露出他的高人一等、目中无人、蛮横粗野。
不同于为给儿子治病耗尽家财的华家,也不同于驼背、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等闲谈的顾客,康大叔是主动向这些底层看客散播消息的上一级,无论是华家的人血馒头,还是夏瑜被杀的事迹,都是通过康大叔一人所言才满座皆知。所以康大叔在这些底层看客的心中是身份尊贵的权势者,是掌握话语权的核心人物。
小小的茶馆将人群分为了三六九等。这些不同阶级、不同立场的人物,映射出整个社会的普遍状态或心态,大大丰富了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让这些旁观者不再是一群无名无姓,没有清晰五官的模糊背景。通过多阶层的展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集合,让读者得知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看客们面对国之同胞受难,不会想着同仇敌忾;面对身旁邻居受苦,不会想着共渡难关。他们表现出来的只有对生命的毫无敬畏和对弱者的毫无悲悯。
(二)“抽象”与“具象”完美结合
“要讓接受者从小说的具体叙述中感受到超越性的意味,要让接受者从人物形象的言行举止中领会到普遍性的旨趣,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作品具有超越性的意味,具有普遍性的意旨,是小说家共同的梦想。”[5]但要实现这一点,却极其不易,这关乎许多方面的因素。诸多因素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一字一句的叙述中,把“抽象”与“具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鲁迅首次提出“看客”这一概念,可追溯到《呐喊》的自序部分。在文中,他指出“无论国民体格如何健全茁壮,然而一旦精神愚弱,便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由是,“看客”一词正式登上现代文学的历史舞台。毫无疑问,“看客”就是鲁迅小说中能够把“抽象”与“具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能够同时囊括普遍性和超越性的一个群体。
在对看客群体的塑造上,鲁迅给予读者的信息少之又少:或无名无姓,或没有身份信息,更有甚者模糊得只剩下若隐若现的轮廓。然而,笔者以为正是他有意地模糊淡化甚至抹去了每一个具体、确切的看客个体,从而更能使读者聚焦于看客的整体形象,进而从他们身上提炼出一个时代的缩影,集中反映出他们性格的弊病与弱点,以达到剖析因果、谋求出路之效。
若是清楚设定了康大叔就是“黑的人”,其职业就是刽子手,那么他所代表的社会群体范围将会大幅缩减。鲁迅为了最大限度地让康大叔这个看客的精神具有普遍性,便尽量控制对他的描绘。鲁迅刻意不赋予康大叔任何明确的社会身份;即使名字,也只给他一个明确的姓氏,却又是没有意义的。假若康大叔有过多的连贯性动作,让康大叔与具体的买药故事情节纠缠太多,那么这个人物形象的内涵便一开始就“具体化”了,他的精神便会具体化,便会让人感到只在特定情境中才具有意义。
但是,仅有抽象化的叙述,容易使作品枯燥乏味,容易让人物概念化、公式化、刻板化,从而让人难以卒读。而鲁迅十分自然巧妙地把抽象与具象结合在一起,以一个又一个鲜活、灵动的具体细节来装点、填充着抽象的人物符号。
在这篇《药》中,鲁迅以十分精细的笔法,把那些往往为常人所忽略的地方加以精雕细琢的叙述:“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刚进门,便对华老栓嚷道:……。”短短几句就将康大叔的衣着、神情、性格等向读者交代清楚,让读者在脑海中能粗粗勾勒出一个五大三粗、不修边幅、趾高气扬、蛮横粗鄙的混混形象,于细微处读出诸多信息。这些生动的神情、言行大大增强了人物的立体性,从而让读者对事件的真实性深信不疑,不再认为这是一个被虚构出的脱离社会实际的公式化符号。唯有身份信息模糊不明,但又兼具真实生动的看客形象,才能让读者自然地联想和代入到彼时社会上的诸多人物群体上,从而达到以小见大、尝鼎一脔的良好效果。
(三)深化和拓展小说主题
1.改造国民精神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明自己为何弃医从文:“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6]从鲁迅的原话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肉体健壮的康大叔,却是精神的靡弱者,从而显出强烈的讽刺和批判意义。康大叔正是鲁迅笔下的那种“看客”。
如果康大叔只是朝廷的爪牙、行刑的刽子手,是一种传统意义上本就冷酷无情残暴的代名词,那就无法符合鲁迅所提出的“愚弱的国民”“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定义。只有让康大叔作为普通群众的“领头羊”,作为行刑者的帮凶,才能更好展现出“示众”的含义。这样的“看客”代表也才能更好地揭示《药》的深刻主题——“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因群众的愚昧而带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截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7]这一特殊看客形象的存在,进一步深化了“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的主题,使这部小说呈现出复杂的象征意义和强烈的讽刺意义,进而鲜明地表达了鲁迅对于改造国民精神的愿望。
2.强调生命价值
过去对于《药》这部小说主题的解读主要集中在“反思说”和“启蒙说”,即要么认为它批判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反映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脱离群众等缺点;要么认为《药》批判了精神腐朽、愚昧麻木、不理解革命先锋的落后国民。但说到底,这两种解读思路的出发点和着眼点还是落在“革命”上面,是从“革命”的角度体验鲁迅小说的,是从外部分析、研究鲁迅小说的客观意义,而忽视了作为创作主体的鲁迅自身对人类生命存在的感受。
康大叔作为全篇小说的重点人物,直到第三节才缓缓出场,但他一出现便显示出身份地位的不一般。不同于茶馆里的其他客人,康大叔身居高位,是在“包好,包好”的喊叫中出场的。他的喊叫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药,二是药源。关于药,康大叔明显带有炫耀的色彩。“包好,包好!……什么痨病都包好!”“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这是包好!这是与众不同的。”从始至终康大叔都在通过夸大药的功效来显示自己的非凡本事;至于这药能否真的能治好华小栓的病以及华小栓病情如何,他则全然不顾、漠不关心。
在茶馆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华老栓和康大叔构成了病人华小栓生命环境中的两极——极度关心与极度冷漠。沉默忙碌的华老栓与聒噪喧哗的康大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华老栓为儿子病情担忧得“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而康大叔只专注于吹嘘药的功效。这是一个极具反讽意义的叙事结构。在这个反讽结构中,病人的生死退居于末席,而“药”这个主体意象被推至首位。人们关心的是药,而不是吃药的人;关心的是药的来源,而不是吃药的结果。
但人们对于药的来源,即夏瑜被砍头的关注仍然只是听个热闹。花白胡子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事”,却在听到夏瑜被亲人出卖,被牢头欺辱后却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哩”“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在他们无聊空虚的生活里,在这样冷漠又虚无的生存环境中,生命是无关大体的,生命在人们的生活中的重量占比不过是茶余饭后的一点调味剂,是可有可无的,是被漠视甚至被蔑视嘲笑的。生存的冷漠与生命的重量构成极具张力的反讽结构,其中的荒诞和可悲由此而生。
作者如果安排康大叔的职业就是刽子手,那么他每天杀人已经司空见惯,则无所谓什么麻木或冷漠了。比较刽子手与寻常普通人,显然是普通人对生命漫不经心、视如草芥的态度更加令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更能激发读者的愤慨和反思。作者只有将康大叔归入单纯的百姓群体中,与华老栓、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等无异,才会更加显出这些麻木冷漠的、残忍冷血的人群实为社会大多数这一时代的悲哀。这样的大多数只关心各自眼前的利益:华老栓只关心自己儿子的命,不关心人血馒头的血是哪来的;康大叔只关心自己没有捞到好处,不关心人血馒头是否有效;大众只关心今日“新闻”,不关心革命者为何而死。正是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下,“大清是我们大家的”——夏瑜拼死留下的遗言才不会在大众心目中泛起哪怕是极微小的波澜。社会的整体愚昧、麻木比之朝廷的疯狂、刽子手的凶恶,显然更令人感到可怕、寒心与不安,更能构成生命的反讽结构,产生巨大的时代的反讽张力。
3.扩大群众范围
作者在描写康大叔时尽管极力刻画其邋里邋遢、目空一切、高高在上、夸夸其谈的混混形象,却并没有粗暴莽撞地将他直接划分在革命的对立面,确立为社会的敌人,而仍然只在于揭示他作为群众一方所受到的精神荼毒之深之重,说明他既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受害者,又是助纣为虐的封建统治的维护者的情况。作者笔下的康大叔的致命缺点是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眼界狭隘,缺乏阶级观念和阶级感情,但本质上并不是反革命分子。
归根结底,康大叔与华老栓夫妇、夏四奶奶等人一样,都是封建专制社会下被压榨的底层民众,只是被压抑的境况和展现出的奴性程度不同罢了。鲁迅从启蒙主义角度出发,有意识扩大被启蒙群众的范围,奉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原则,尽力团结和争取一切底层民众,其目的是使整个民族觉醒。唯有唤醒更多民众,才能推翻清政权,完成民族革命的神圣使命。
推翻清朝暴虐统治是当时民族革命的直接目标。革命者向群众呼号不要替清朝统治者卖命,要有民族骨气、民族尊严、民族感情、民族自尊心。在夏瑜的心目中,民族革命大业是排在自己的生命之前的,是第一位的。他坚信“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关在牢里还念念不忘民族的利益,将牢头阿义当作争取对象。在民族国家观念尚未深入人心的时候,革命家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思想支撑着他们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完成革命伟业。这正是夏瑜成为革命家最为宝贵的个性,是革命家与一般国民最本质的区别。
阿义、康大叔、夏三爷等人由于他们自己“中毒”太深,故对革命家一味地痛骂和攻击。诚如《阿Q正传》里阿Q对革命“向来深恶而痛绝之”,他进了一次城,回到未庄,便向未庄人吹嘘“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我们绝不能简单凭据阿Q对革命“深恶痛绝”的态度和他说“杀革命党好看好看”的麻木语言,就笃定他是汉民族的敌人。鲁迅写阿Q,写康大叔,都是将他们视为群众,从启蒙主义角度出发,有意识扩大被启蒙的群众范围,虽挖掘出国民的劣根性——鼠目寸光、见利忘义,丧失民族气节和道德良心,但其根本目的还是落在启蒙与救亡上,想要叫醒更多的人,从而一同启蒙、一同拯救。
结语
康大叔是否是“黑的人”,是否是杀害夏瑜的行刑者,这并非是一个可以模糊和忽略的小问题。当我们将二人区分开来后,便能从这篇短小精悍的小说中,发现鲁迅更多精细的写作笔法和深邃的社会思考,从而对其文本和文学观有进一步深入准确的认识和理解。
注释:
[1]《語文第四册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第50页。
[2]《语文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第49页。
[3][4][6]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第468页,第463—472页。
[5]王彬彬:《赵太爷用哪只手打了阿Q一嘴巴——〈阿Q正传〉片论》,《文艺争鸣》2022年第2期。
[7]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28页。
作者: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