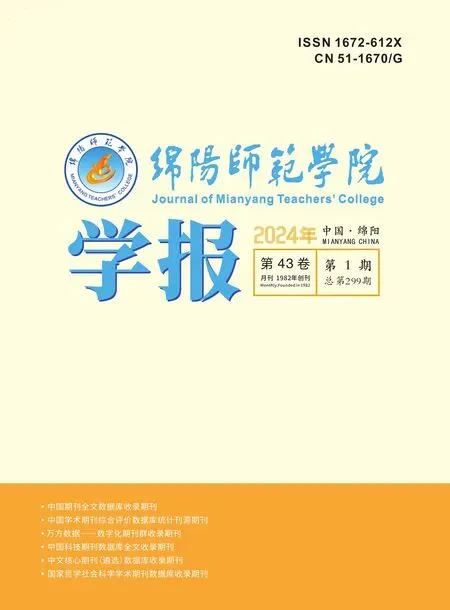苏辙《诗集传》初名考
2024-02-26易均
易 均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68)
宋代苏辙的《诗集传》是一部对《诗经》进行注解的专著。自汉代以来,依据《诗序》解释《诗经》的传统,无人可动摇。苏辙《诗集传》的最大成就在于打破传统《诗序》的束缚,第一次做到从整体上对《诗序》进行“腰斩”,即只保留《小序》首句,而把首句之后的所有文字全部删掉。例如《周南·关雎》之《序》,只保留“关雎,后妃之德也”[1]266,而将此句之后的序文尽皆删除。这种做法为宋代《诗经》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对《诗序》的这种做法,上承欧阳修《诗本义》,下启朱熹的《诗集传》,在宋代《诗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苏澈的《诗集传》也被后人频繁征引。但在实际的征引过程中,经常发生一书多名而名实混淆,导致难以稽考复核的现象。朱熹、王应麟等人的征引都曾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关于苏辙《诗集传》的研究,前人于校勘方面多集中于文字训诂、版本源流等问题的考察,但都未有讨论过该著作一书多名的问题。笔者通过翻阅历代各类目录与典籍,发现其书名繁杂混淆,莫衷一是。有鉴于此,故特撰此文,试图正本清源,探析此书成书之初的称谓原貌。
一、问题的提出
苏辙的《诗集传》存在一书多名的现象,在后人征引的过程中,发生过将此书之名与苏辙其他文章之名相混淆,以致难证其引的情况。朱熹的《偶读谩记》有这样一段记载:“或云程邑在雍州之东二十里,王季所居。又引苏黄门《诗说》:‘周之程邑,汉扶风安陵县也。’”[2]3416文中,朱熹记载了某人为说明程邑的位置,曾引用苏辙《诗说》的原文为证,但考苏辙的《诗说》①,并无此文。按此文实出自苏辙《诗集传》中对《大雅·皇矣》一诗的注解:“文王既克密须,于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谓程邑是欤?或曰汉扶风安陵,周之程邑也。”[1]494而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混淆,以致难以复核原文,就在于朱熹把苏辙的《诗集传》称为《诗说》,于是导致同苏辙的另一篇杂文《诗说》相重名。这种张冠李戴的错误做法,造成了学术上的严重困扰。此并非孤例,《朱子语类》卷八十记载:“欧阳修会文章,故诗意得之亦多。但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促了《诗》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头者。苏黄门《诗说》疏放,觉得好。”[3]2763在此处,朱熹又称苏辙的《诗集传》为《诗说》。但在同书同卷的另一处,却记载:“子由《诗解》好处多,欧阳公《诗本义》亦好。”[3]2764在这里,朱熹把苏辙的《诗解》与欧阳修的诗学著作《诗本义》相对比,显然是用《诗解》之名来称呼苏辙的《诗集传》。而在另外一处朱熹又说:“苏氏《诗传》比之诸家若为简直,但亦看小序不破,终觉有惹绊处耳。”[4]2428朱熹此处说“看小序不破”是指苏辙《诗集传》中仍保留《小序》首句而未能尽弃《小序》的做法。显然,这里是用《诗传》之名来指称苏辙的《诗集传》。可见朱熹对苏辙《诗集传》的称谓既有“诗说”又有“诗解”“诗传”,并无一定。另外,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三里也把苏辙的《诗集传》称作“子由《诗说》”[5]97,却又在《玉海》里著录为“苏辙《诗解》二十卷”[6]724。朱、王二人皆为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但他们对苏辙《诗集传》的称谓却都是一书而多名,自相矛盾。他们这样的做法无疑会造成征引、复核此书的困难,进而导致学术上的混淆。由此,清人戴震曾引用王应麟《困学纪闻》的原文,也随之作“子由《诗说》”[7]548。戴震是清代的著名学者,但他只是引用前人成说,未加核对,因此也造成同样误用的情况。
从版本与历代目录书的著录来考察,目前所存最早的苏辙《诗集传》的版本,是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苏辙曾孙苏诩在筠州公使库刊刻的本子。已题名为《诗集传》,此本也是现存唯一可知最早的以《诗集传》命名的本子。苏辙的《诗集传》现存三个版本,除苏诩刊本之外,焦竑《两苏经解》本与《四库全书》本均题名作《诗集传》②。但考宋代著录苏辙《诗集传》的目录书,最早者为两宋之际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其文载:“《苏氏诗解》二十卷。”[8]67-68《郡斋读书志》约成书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比苏诩的刊本早了近三十年。这说明至少在绍兴二十一年之前,苏辙的《诗集传》已经存在不同的称谓,此时距离苏辙《诗集传》最后成书的时间也不过四十多年。其后宋理宗时期,陈振孙编撰的《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为“诗解集传”[9]37。降至明清,又有称之为《颍滨诗传》《诗颍滨传》《苏氏诗集传》《颍滨先生诗集传》等名,可谓名目繁多,莫衷一是(详见表1)。

表1 历代主要书目著录苏辙《诗集传》称谓表
后世学者征引苏辙《诗集传》而使用的书名称谓,也大都互有出入。例如上文提到的宋人朱熹、王应麟称之为“诗说”“诗解”等;明人何楷的《诗经世本古义》、清人顾广誉的《学诗详说》称之为“苏氏辙《诗集传》”;但清人胡承珙的《毛诗后笺》、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民国吕思勉的《经子解题》则称其为“诗传”;清人顾栋高的《毛诗订诂》、朱鹤龄的《诗经通义》则直接称作“苏《传》”。综上所述,宋、元、明、清、民国等五代学者对于征引苏辙《诗集传》所使用的称谓混乱无序,不仅前后时代称谓不同,甚至同一时代的不同学者,亦有不同。
到了当代,对于苏辙《诗集传》的研究虽然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与丰富,但对此书的称谓仍存异议。例如洪湛侯在《诗经学史》中称之为“《诗经集传》二十卷”[10]324。夏传才主编的《诗经学大辞典》中把此书标示为“苏辙《(颍滨先生)诗集传》”[11]385。戴维《诗经研究史》中称之为《诗解集传》,并且认为:“《宋史》本传说苏辙著有《诗传》,而《艺文志》著录:‘苏辙《诗解集传》二十卷。’《四库全书》说是《诗集传》,本传及《四库全书》应是《志》中的简称。”[12]262他认为《诗传》与《诗集传》二名可能是《诗解集传》的简称。然而,其他的绝大部分学者,则将苏辙此书称为《诗集传》。上述现象说明,即便到了当代,人们对于苏辙此书的称谓仍具有分歧,异名的问题仍旧悬而未决。后人在称引苏辙此书时,出现如此众多的称谓,必然会给学术研究带来不利的影响。
苏辙《诗集传》的这种一书多名的现象,在我国古代的典籍中,其实并不少见。所谓“一书多名”,即同一本书在同一历史时期或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不同的称谓。这些不同的称谓,随着时间的累积,致使同一本书拥有多个不同的书名。据今人杜信孚等编撰的《同书异名汇录》统计,具有一书多名现象的古代典籍多达13 500 余部[13]1。据考,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一书多名的现象便已存在,例如先秦时期孔门六经之一的《诗》,最开始只单称“诗”,后来又有“诗三百”“诗经”之名。但在先秦时期,这种一书多名的现象并未被视作一个问题。到西汉成帝时期,刘向奉命校正图书时,这种现象才被正式当作问题提出③,却并未引起时人的重视与探讨。一直到明清时期,这种现象才引起学者的深入讨论④。例如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繁称》中明确谈到这一现象:“一书两名,先后文质,未能一定,则皆校雠者,易名著录,相沿不察,遂开岐异。”[14]458章学诚指出,一书多名的现象是由于校雠此书的人,更换了该书的书名,后世之人便随之沿用,于是导致同一本书出现书名各异的现象。其实,章学诚说的这种现象在古代很常见,古人的著作大多为后人整理编撰,在整理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整理者另立新名的情况。例如刘向整理的《战国策》,其原名有《国策》《短长》《事语》《修书》等,但后世之人多沿用刘向所定的《战国策》之名。章学诚又进一步指出一书多名现象的四种具体表现形式“有本名质而著录从文者,有本名文而著录从质者,有书本全而为人偏举者,学者不可不知也”,接着列举《老子》《鸿烈解》《吕氏春秋》《史记》等七书为例,作为佐证[14]459。从这些记载中,可知章学诚已经明确认识到一书多名现象的各种外在表征,但他却未能全面揭示出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刻社会历史原因。当代学者马刘凤在2013 年发表的《古籍同书异名与同名异书原因探析》一文中,归纳出造成同书异名现象的十种原因以及同名异书的三种情况,可以说是对一书多名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但,苏辙《诗集传》一书多名现象的特殊与复杂之处在于,它并不是马刘凤此文所指出的某种单一的原因所致,而是几种原因共同导致(后文有详述,此不赘)。也正因其特殊性与复杂性,才导致学界长期以来对苏辙此书称谓的混淆与繁乱。
综合上述所有的苏辙《诗集传》的称谓,其名称多达十几种。但是通过仔细的分析可以发现,这十几种不过是把书的本名再加上官职、姓氏、字号等,以示区别于其他同类诗学著作。其称谓可主要归纳为“诗说”“诗解”“诗集传”“诗传”四种。可即便如此,苏辙《诗集传》称谓的混乱现象已经造成历代学者学术研究上的困难与混淆,这是无可回避的事实。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苏辙《诗集传》的初名进行考订,这有助于加强我们对苏辙《诗集传》初始面貌的认识,也有助于厘清此书历来的繁杂称谓给学术界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苏辙《诗集传》初名《诗传》
苏辙《诗集传》之名最早见于其曾孙苏诩的宋刻本题名,然而《诗集传》并非苏辙的这部《诗经》学著作的初名,其初名当作《诗传》。苏辙之孙苏籀的《栾城遗言》记载:“(苏辙)年二十作《诗传》。”[15]59《诗传》应为文献所载苏辙《诗集传》最早之名。孙汝听《苏颍滨年表》记载:“及归颍昌,时方诏天下焚灭元祐学术,辙敕诸子录所为《诗》《春秋传》《古史》,子瞻《易》《书传》《论语说》以待后世君子。”[16]1412按孙氏所说,则《诗集传》最终成书于苏辙在颍昌时期,并且苏籀的父辈应是参与过苏辙《诗集传》的编纂工作。《栾城遗言》又说:“籀年十有四时,侍先祖颍昌,首尾九载,未尝暂去侍侧。”[15]65据此可知,苏籀曾陪伴苏辙九年,直到苏籀年满二十三岁。此时的苏籀已是成年男子,对父祖辈著书之事,必然深知,也必亲见其事。再按《苏颍滨年表》的记载,苏辙在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返回颍昌居住,一直到政和二年(1112)因病去世[16]1408-1411。从苏辙六十六岁回居颍昌,再到其七十四岁去世,其间也正好九年。综上可知,苏籀曾在颍昌陪伴其祖父苏辙度过人生最后的九年,而《诗集传》也是最终成书于这个时间段,所以苏籀应该亲自见过苏辙《诗集传》的最后定本,其所言《诗传》之名也必有所据。
其实在苏辙《诗集传》最后定本之前,关于《诗传》之名的记载还有两处。第一处在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即苏辙四十二岁之时,苏轼曾在《与王定国》一文中写道:“子由亦了却《诗传》,又成《春秋集传》。闲知之为一笑耳。”[17]1519-1520此处苏轼明言《诗传》之名,并与《春秋集传》并列对举。由此可知,苏辙此书必以《诗传》为专名,绝非泛称或《诗集传》的简称,否则绝不可能与《春秋集传》并题。第二处则在苏辙第二次给《道德经解》写作的跋文中:“予昔南迁海康,与子瞻兄邂逅于滕州,相从十余日,语及平生旧学,子瞻谓予:‘子所作《诗传》、《春秋传》、《古史》三书,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所不及……政和元年冬……十二月十一日,子由再题。’”[18]483据苏辙自己在文中所说,这篇跋文的创作时间是在政和元年(1111)冬十二月十一日,即在他七十三岁之时,此时距离苏辙去世的时间仅剩一年。在这个时候,苏辙的《诗集传》必然已经定稿。在这篇跋文中,苏辙借苏轼之口所传达的《诗传》之名,必然也是苏辙自己所认定之名。苏轼是苏辙之兄、苏籀是苏辙之孙,后世著录者没有比此二人更加亲近苏辙的。再加之苏辙本人在去世前一年也曾提到《诗传》这个名字,所以可以肯定,苏辙《诗集传》的初名就叫作《诗传》,并且这个称谓在当时已被相互使用。
南宋孙汝听《苏颍滨年表》中亦有关于《诗传》之名的记载:“辙有《诗传》二十卷,《春秋集传》十二卷。”[16]1412在此处,孙汝听也和苏轼一样,将《诗传》与《春秋集传》并提,此为《诗传》必非简称或泛称的又一确证。孙汝听的生平不详,考历代文献只有一些零星的记载。据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碑记目》卷四记载:“眉山人孙汝听修《成都古今前后记》六十卷,见《眉州江乡志》。”[19]561《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记载:“《三苏年表》三卷,右奉议郎孙汝听撰,汝听当是蜀人,叙蜀甚详。”[9]502《蜀中广记》卷九十六记载:“《梓潼古今记》(今潼川州),淳熙间郪令孙汝听作。”[20]565《眉州属志》卷十一载:“孙汝听,州人,绍兴进士。”[21]161绍兴是宋高宗的第二个年号,淳熙是宋孝宗的年号。据上述四条材料,至少可知,孙汝听应当生活在南宋高宗、孝宗时期,并且他与“三苏”同是四川眉山人,对于蜀地之事特别详熟。孙汝听撰有《三苏年表》,可见他对“三苏”的生平往事应当是非常了解的。由此可见孙汝听对苏辙《诗传》的记载,可信度是非常高的。而他不仅在苏辙的年表中著录了《诗传》这个称谓,而且标注了卷数。这说明孙汝听曾经见过这个本子的原貌,而这个本子极有可能源自苏辙最后写定成书的《诗传》版本。
《宋史·苏辙传》亦载有《诗传》之名,本传记载:“所著《诗传》《春秋传》《老子解》《栾城文集》并行于世。”[22]10835元末编成的《宋史》由于其多抄录原始档案,疏于剪裁,芜杂不精,一直受史学界诟病。赵士炜在《宋国史艺文志辑本·序》中批评道:“元以异族入主中华,其史官学识浅陋,故宋史疏略而《艺文志》尤纰缪,重复颠倒,不可枚数。四库讥其为诸史志中最丛脞者。”[23]455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宋史》也因此保留了一大批未经篡改的珍贵原始材料。而苏辙本传所载的《诗传》之名,极有可能就是因为本传主编者直接抄录北宋时的原始材料所致,而这也为考察苏辙《诗集传》的初名提供了佐证。至于《宋史·艺文志》著录苏辙此书为“《诗解集传》二十卷”,则是因为《艺文志》的编撰者直接抄录南宋李焘的官修目录《四朝国史艺文志》所致⑤。李焘此书成书于南宋孝宗年间,晚于苏轼、晁公武等人对苏辙此书的记载,所以《宋史·艺文志》所载《诗解集传》之名绝非苏辙此书的初名。
综上,可以明确苏辙的这部《诗经》学著作的初名就是《诗传》。那么何为“诗传”呢?从训诂学的角度来考察,这里的“诗”指的是儒家经书《诗经》。所谓的“传”,朱熹云:“传,所以解经也。”[3]3422许威汉也说:“‘传’是传述之意,用以解经。”[24]144可见,所谓的“传”就是指对经书进行注释。因此,从“诗传”这一名词本身来说,其本意只是泛称那些解释《诗经》的著作,并非专指某一部书。但是,随着西汉今文三家诗的相继消亡断绝,大小毛公为古文《诗经》作的《毛诗诂训传》因各种社会历史原因在中国《诗经》学史中一家独大,于是又导致后世有部分学者偶尔把《毛诗诂训传》直接简称为“诗传”。如此“诗传”又成了《毛诗诂训传》的代称。例如,孔颖达在《毛诗·小雅·鱼丽》一诗中,注云:“郭璞引《诗传》曰:罶,曲梁也。”[25]417再如《文选》收录的左思《招隐诗》二首中,李善注云:“毛苌《诗传》曰:‘琼瑶,美玉也。’”[26]1028这两例说的《诗传》就是《毛诗诂训传》。到了宋代,有一些学者却都以“诗传”这个名词来命名自己注释《诗经》的著作。这种把表示泛称的名词用以指称专名的做法,使得“诗传”这一词汇完成了从泛称到专指的过渡。考《宋史·艺文志》记载的以“诗传”为书名的《诗经》学著作有鲜于侁《诗传》六十卷、李常《诗传》十卷、沈铢《诗传》二十卷、郑樵《诗传》二十卷、陈寅《诗传》十卷,共计5种,占《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诗经》学著作总比的5%。因此,在宋代疑古惑经的这种特定历史时期的风气影响之下,苏辙把自己注解《诗经》的著作定名为《诗传》,便也不足为奇。并且,定名为《诗传》也更符合苏辙自己所说的“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指,欲更为之传”[27]1017的人生追求。苏辙的《诗集传》原名为《诗传》是无疑的。
综上所言,《诗传》之名并非是戴维在《诗经研究史》中认为的可能是《诗解集传》的简称。苏辙此书就叫作《诗传》,不仅在最终成书之前,他的兄长苏轼以《诗传》之名指称其解《诗》之作,并且最后在颍昌写定成书时,也是以此名冠之。而后,苏辙的《诗传》应当被抄录流传开来,他的孙子苏籀与眉山孙汝听都见过这个以《诗传》为名的本子。孙汝听与晁公武大致是同时期的人,而他们同著录此书却又称谓各异,说明此书在南宋高宗至孝宗时期,至少应有两种本子在流传。一个是以《诗传》为名的本子;一个是以《诗解》为名的本子。可惜的是,在苏籀、孙汝听二人之后,以《诗传》为名的这个本子再也不见有历史记载。
三、驳《诗说》《诗解》《诗集传》三名
苏辙的《诗经》学著作的书名,虽然称谓众多,然归纳起来,除《诗传》这个称谓之外,最显者不过《诗集传》《诗解》《诗说》三种。仅据《宋史·艺文志》所著录,以《诗传》为名的著作共有五种,以《诗集传》为名的著作仅有一种,以《诗解》为名的著作共有三种,以《诗说》为名的著作共有七种⑥。可见,除《诗集传》这一名称外,另外三种称谓在宋人著作中并不少见。但《诗说》《诗解》《诗集传》三名并非苏辙此书的初名,以下依次辩驳:
首先,将苏辙《诗传》称之为《诗说》的记载最早见于上述所列朱熹、王应麟的著作。“诗说”之名在历史上出现较早,至少在西汉前期就有大量的此类著作。在《汉书·艺文志》中就记载有《鲁说》二十八卷、《韩说》四十一卷。那什么是“说”呢?周大璞认为:“说既说明、解释的意思,引申为用以解说的词语。”[28]36“说”与注释的意思其实差不多,在这里就是指鲁诗学派、韩诗学派注解《诗经》的著作《鲁诗说》与《韩诗说》。朱熹、王应麟二人把苏辙此书称为《诗说》,但《诗说》绝非苏辙此书的初名。原因有三:其一,朱熹、王应麟对于苏辙《诗传》的称谓,既有《诗说》又有《诗解》,自相矛盾;其二,《诗说》此名相较于《诗传》《诗解》《诗集传》三名,出现得最晚;其三,《诗说》之名并不见他人著录、征引,唯见于朱、王二人的著述之中,且只有此两条。由此可断定,《诗说》绝非苏辙此书之初名。而造成出现《诗说》之名的原因,应当是朱、王二人只是随意称引,并未留意,以致舛误,这种情况在古代并不少见。
其次,将苏辙《诗传》称之为《诗解》的记载最早见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而后《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玉海》《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等书皆有“诗解”之名。什么是“诗解”呢?苏建州指出:“解的本义是剖析、分析。训诂就是分析语义,所以也叫做‘解’。如《管子》有《牧民解》、《形势解》。汉人注书常以解、诂连言,亦作‘解故’。”[29]119如此看来,“诗解”也是对《诗经》的解释、注释。然而《诗解》并非苏辙此书的初名,因为《诗解》的这种称谓不仅苏辙本人及其亲友从未提及,并且在南宋以前也不见他人记载。但奇怪的是,此名在南宋至元的整个时间段,主要的目录书却皆有《诗解》之名的著录。其原因,极有可能如马刘凤指出的“因后人改易,一书具有多名”[30],即是苏辙的《诗传》成书以后,有人另外抄刻了其他的本子,而改名作《诗解》,于是后人相继沿用这个改动后的称谓。这个时间应该发生在宋室南渡前后,并且这个以《诗解》为名的本子在当时甚为流行,其知名度甚至超过《诗传》这个初名,以致各类主要书目都著录了这个名字。
最后,将苏辙《诗传》称之为《诗集传》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宋苏诩的重校证刊本。然而《诗集传》也非苏辙此书之初名。原因有三:其一,从记载来看,苏辙本人及其亲友从未将这部诗经学著作称作《诗集传》;其二,在整个宋元时期,也无任何目录书把苏辙此书以《诗集传》之名著录,此名唯见于苏诩的刊本;其三,从注释体例来说,苏辙此书并不符合“集传体”的体例。以下针对其体例问题再次进行辨析。
秦汉时期把解释经书的著作称为“传”,这是从它的应用对象的角度来谈的。而从“传”的具体注释内容来说,苏建州认为:“从前人的解释和古书的实际情况来看,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解释字词义为主的,即何休所说的训诂,如《诗经》的毛传、《三礼》的郑注;另一类是阐述、引申经义或补充事实者,如《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29]74-75苏建州从秦汉时期的实际案例中归纳出“传”具有解释字词义与补充背景、阐释经书内容两个特征。这样看来“传”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注释的意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也说:“毛君、孔安国、马融、王肃之徒,其所注书,皆称为传,郑玄则谓之注。”[31]1712可见“传”与“注”从本质上来看是没有区别的,就是指的注释。既然“传”等于“注”,那么“集传”与“集注”的意思也就差不多了。那什么是“集传”呢?苏建州指出:“《集传》与《集注》同义,乃集合多家的传解,择善而从。”[29]75考《宋史·艺文志》的记载,以《诗集传》为名的著作仅有一种,即朱熹的《诗集传》二十卷。朱熹此书是一部非常经典的集传类诗《经学》著作,笔者以此为例来对比说明“诗传”与“诗集传”在体例上的区别。
赵长征点校朱熹《诗集传》时,在《前言》中说道:
朱熹反对汉学那种烦琐注疏的学风,力求简明扼要,所以此书也并不因为“集传”的体例而庞杂枝蔓。“传”,是传述的意思,指注疏家们阐释经义的文字。所谓“集传”,与“集注”一样,意思是汇集各家传注,加以鉴别,择善而从,并间下己意。朱熹既杂取毛、郑、也间采鲁、齐、韩三家,还吸取了不少当代学者的解说。其中有些学者,与朱熹解读诗经的思路很不一样,如吕祖谦,是尊《毛序》的,朱熹仍然引用了他的很多见解[32]2。
在这段文字中,赵长征解释了“传”与“集传”的区别在于后者必须是“汇集各家传注”,更说明了朱熹此书,除他自身的见解之外,还大量引用他人注解《诗经》成果的事实。据耿纪平统计,朱熹《诗集传》“共引用本朝学者214 条学术成果,其涉及的诗篇约在全部作品的七成以上”[33],还未包括宋代以前的诸家成果。朱熹此书真可谓是“集传”之大成,也完全符合“汇集各家传注”的“集传”定义。
反观苏辙的《诗传》,据笔者统计,除了引《毛诗序》《毛诗诂训传》《毛诗传笺》等毛氏之学外,另引《韩诗》《齐诗》《书》《易》《礼记》《仪礼》《周礼》《春秋》《春秋传》《春秋外传》《论语》《孟子》《庄子》《司马法》等十几种书。其中引用最多的是《毛诗序》26 次,其次是《春秋传》14 次。上述书目大都是西汉以前的书。苏辙引用上述诸多著作,只是将它们作为注释材料,以此来注释《诗经》的内容,是为阐释己见,作理论支撑。而不是像朱熹《诗集传》那样“汇集各家传注”,兼采并蓄。苏辙除《毛诗序》外,没有征引其他任何一家诗说,即便是征引毛氏之学也是因为其有足够的学术价值,离开便不能立说。下面列举四条苏辙《诗集传》的征引以作说明:
《秦风·驷驖》引《周礼》:“礼,冬献狼,夏献麋,春、秋献鹿豕群兽故虞人翼兽以待公射。”[1]358
《大雅·灵台》引《孟子》:“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1]495
《周颂·閟宫》引《春秋》:“齐人归郓、欢、鬼阴之田。”又 “郑伯以壁假许田。”[1]570
《小雅·棠棣》引《春秋外传》曰:“周文公之诗也,盖伤管、蔡之失道而作之以亲兄弟。”[1]392
上面列举苏辙注解《秦风·驷驖》《大雅·灵台》所引用的《周礼》《孟子》原文的目的,是为了分别对“辰”与“灵台”二词进行解释。而《周颂·閟宫》《小雅·棠棣》所引《春秋》《春秋外传》原文的目的,则是为了给诗歌的背景作内容补充。由此可见,苏辙征引上述诸多著作的目的只是为了注释字词、辨析诗义、补充事实等。苏辙引文的这两种目的,正与苏建州从秦汉“经传”的实际用例中总结出的“传”义相合。可以说苏辙的《诗集传》就是他的一家之言,并不符合学界传统上对“集传”“汇集诸家专注,加以鉴别,择善而从,并间下己意”的定义。所以,如果用“集传”之名来指称苏辙这部注解《诗经》的著作,明显有牵强之义,反而用“诗传”之名才更加符合该书的实际情况。
综上所言,在苏辙此书的这三个称谓中,《诗说》之名出现得最晚,并不见宋元时期的著录与征引,当是朱熹、王应麟误称,以致舛误。《诗解》之名始见于《郡斋读书志》,宋元著录多以此名,可见以《诗解》为名的这个本子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而苏诩刊本的《诗集传》之名的出现时间晚于《诗传》《诗解》,又不见宋元人征引、著录,亦不符合苏辙此书的实际注释体例。苏诩是苏辙的曾孙,苏诩的父祖辈苏籀、苏适⑦都见证过《诗传》的最后成书,苏诩不应不知此书的初名。那么只可能是,苏诩在重新整理勘定此书时,将《诗传》之名改作了《诗集传》。
四、结语
苏辙《诗集传》的初名就是《诗传》。苏辙的《诗传》之所以出现一书多名的现象,并非仅由某一种原因所致,而是几种原因共同作用之下的结果⑧,即苏辙此书在宋代重新刊定时,被刊者改易初名,而宋代以后的学者各凭己义,或相沿旧籍已改之名,或添字号、官名以示区别,最终导致苏辙此书异名繁多,延误后学。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上文所引《栾城遗言》与《苏颍滨年表》的记载推测,苏辙必然是亲自审定过自己《诗传》的最后定本,文字、释义应当也无讹误。而苏诩刻本上有“重校证刊于本州公使库”[34]十个字,李冬梅由此认为:“证明在北宋末南宋初以前已有抄本或刻本传世,这种抄本或刻本极有可能就是苏辙门人抄录或刊刻的。”[35]其实可以更进一步从其“重校证”三个字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在苏辙《诗传》最后定本成书再到苏诩“重校证”之前的这个时间段中,《诗传》必然出现过某些问题,也许是出现了不同版本的异文,也许是文字舛误等,才导致苏诩必须要去“重校证”此书,否则只需翻刻此书就行,无须多此一举。虽然,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苏诩刊本之前的苏辙《诗传》版本的流传情况,以及书的内容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但这时的《诗传》已非苏辙最后审定时的原本,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注释:
① 舒大刚、李冬梅已考证在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中所存有的苏辙《诗说》,确是苏辙的佚文。此文亦见《类编增广颍滨先生大全文集》与《三苏先生文萃》二书,前者题名为《诗》,后者题名为《诗论》。参见舒大刚、李冬梅:《苏辙佚文二篇:〈诗说〉、〈春秋说〉辑考》,文学遗产,2003年1期。
② 焦竑《两苏经解》本题名为《颍滨先生诗集传》,标上“颍滨先生”四字只是为了与其他《诗集传》相区别,实际上此书之名仍是《诗集传》。
③ 例如刘向在校订《战国策》时,面对此书的多种异称说道:“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书》,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示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见刘向:《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95页。
④ 明代叶盛说:“古人制作,名集编次,多出于己;或身后出于门人故吏、子孙学者,亦莫不然。周必大所识《欧阳文忠公集》亦可见已。今人不知此,动辄妄意并辏编类前人文集,如处州《叶学士文集》,又曰《水心文集》,曰《文粹》。”见叶盛著,魏中平点校:《水东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页。
⑤ 《宋史·艺文志》序载:“宋旧史,自太祖至宁宗,为书凡四。志艺文者,前后部帙,有亡增损,互有异同。今删其重复,合为一志,盖以宁宗以后史之所未录者,仿前史分经、史、子、集四类而条列之。”见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033-5034页。从《宋史》记载的这段文字“宋旧史,自太祖至宁宗,为书凡四”,可知其增损删减的是记载宋太祖至宋真宗三朝书目的《三朝国史艺文志》,记载宋仁宗、宋英宗两朝书目的《两朝国史艺文志》,记载宋神宗至宋钦宗四朝书目的《四朝国史艺文志》,以及记载宋高宗至宋宁宗四朝书目的《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苏辙《诗集传》最终成书于宋徽宗崇宁三年以后,那么只可能记载在李焘等人的《四朝国史艺文志》中。
⑥ 《宋史·艺文志》载以“诗集传”为名的著作仅有:朱熹《诗集传》二十卷,共计一种;以“诗说”为名的著作有:孔武仲《诗说》二十卷、张载《诗说》一卷、张贵谟《诗说》三十卷、黄度《诗说》三十卷、辅广《诗说》一部、高端叔《诗说》一卷、曹粹中《诗说》三十卷,共计七种;以“诗解”为名的著作有:范祖禹《诗解》一卷、黄櫄《诗解》二十卷、项安世《诗解》二十卷,共计三种。
⑦ 舒大刚认为:“谔、诵既为苏策之子,则诩当为苏简之子。”见舒大刚:《苏辙年谱》,成都:巴蜀书社,2018年,第143-144页。
⑧ 马刘凤归纳出十种导致一书异名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第六种是“因后人改易,一书具有多名”,第八种是“为将书名区别而改书名”,第九种是“史料记载不同”。见马刘凤:《古籍同书异名与同名异书原因探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10期,76-79页。苏辙《诗传》一书多名现象的出现,是上述这三种情况共同作用之下的结果,而非某一种原因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