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作为一种诗歌方法
2024-02-21赵刘昆
摘要:近年来,文学地域性书写的相关探讨、研究持续升温,形成一种文学现象。与此同时,文学地域性书写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引人深思。其中,新疆书写的问题就是一个值得被探讨和反思的问题。长期以来,新疆书写一直被置于类型学与地理学的视域之内加以探讨,不断突出和强化其地域特色与文化的异质性,而忽视新疆作为一种诗歌方法的意义。90后诗人苏仁聪的新疆书写在青年一代中独具特色,因此,以苏仁聪为中心,探讨新疆书写作为一种诗歌方法、诗学观念的意义,不仅必要,而且重要。
关键词:新疆书写;苏仁聪;地域性;诗歌方法;诗学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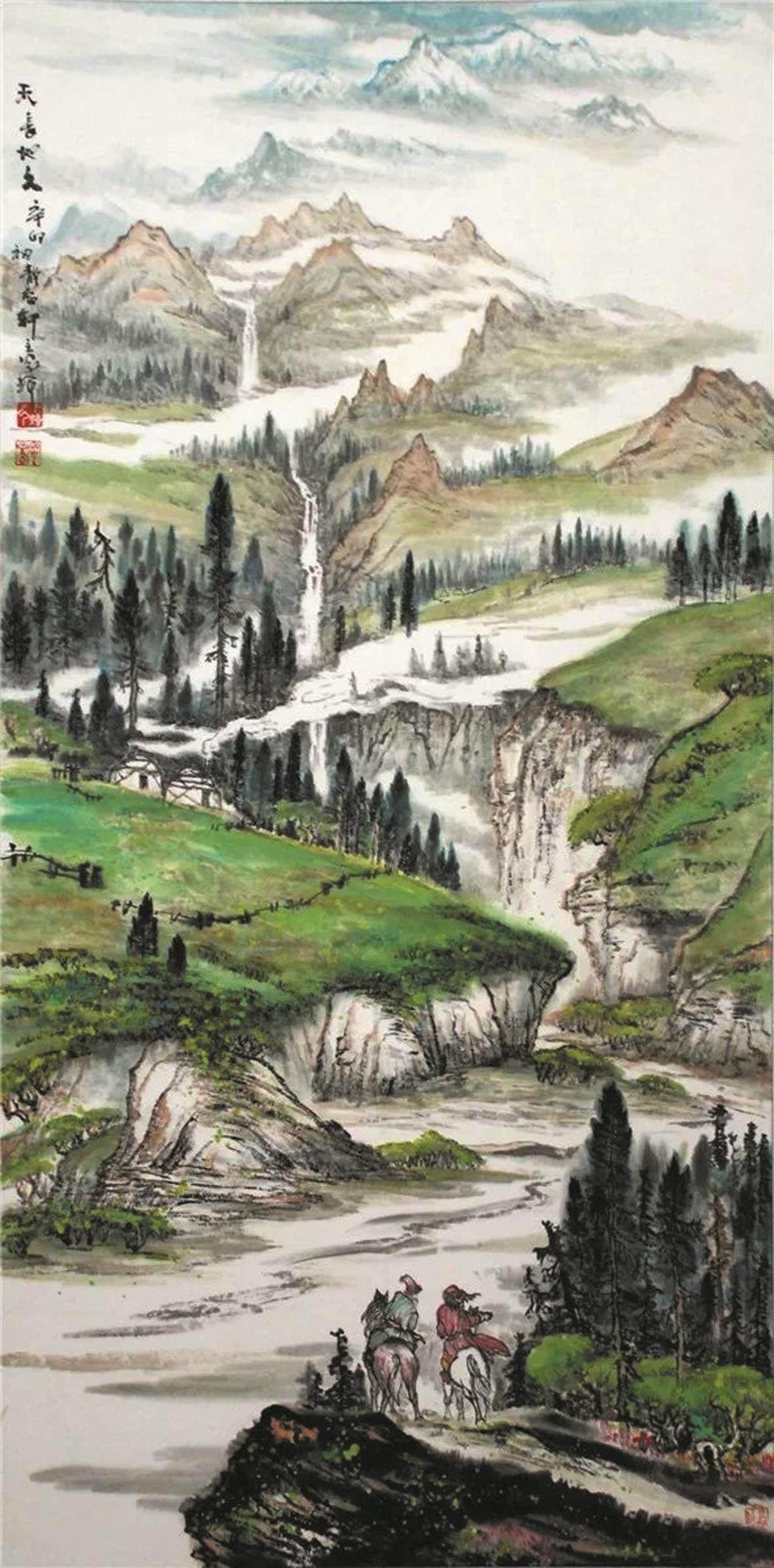
一、关于文学地域性的反思
近年来,文学的地域性话题逐渐成为一个持久而热门的文学话题,前有“文学地理学”概念的提出,后有“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等文学话题的持续升温。这些似乎都在暗示着在当代文学写作中,能够彰显作品独特性的地域性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如果仅从文学生产属地的地域性加以解释的话,地域性之于文学的价值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重要。但如果将其视为一种方法论,则又另当别论。
事实上,“写作本质上不需要被挂上地域标签,进行分类,以示区别”[1]。但作为诗歌创作主体的诗人就不一样了。“就写作本身来说,地域的重要性只是和个体紧密关联,这涉及写作者的成长因素,他赖以生存的一方水土,耳濡目染的语言习俗等因素,只有这一切形成合力才会对写作造成影响。或者可以说,地域生活首先塑造的是写作者个人,然后才可能影响作品。其中的环境浸润、建立的思维惯式,与写作激发的风格彼此交织,呈现复杂的态势。”[2]因此,在谈及文学的地域写作时,一个首要的因素是文学创作主体的地域性,它与诗歌文本自身的地域性既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诗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故乡的地域色彩和地域气息多多少少会在他们身上散发出来,但诗歌文本却未必如此:有的诗歌文本中含有强烈的地域因素,而有的诗歌文本中却几乎觅不见地域性的气息。可见,这与诗人自身的诗歌观念和诗人选择进入世界的诗歌视角和方法有关。
在现当代作家的长期写作中,地域往往与乡土相关。比如沈从文的文学与他的湘西世界之间的关联,孙犁与他的荷花淀之间的关联,赵树理与山西农村的关联,柳青与陕北农村之间的关联等。在许多人眼中,地域标示出作家的某种独特气质,似乎这些作家的文学独特性是完全由地域赋予的一样。其实,在这里面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沈从文文学中湘西世界的独特性,并不来源于湘西这个在现实中实存的地点,而是来源于沈从文的文学想象。所以,在湘西生活过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唯独沈从文能写出这样一个独特的湘西,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暗示着,湘西并不独特,所谓的独特,乃是人们在各种比较中赋予的。而这种赋予,依靠的正是人类的想象力,在作家这里,则是文学的想象力。可见,伟大的并不是像湘西这样的地方,而是赋予地方性以文学想象独特性的作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探讨的文学地域性,其实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并不是其内容上的地方性,如果说得更绝对一些,真正具有地域性的其实是作家,而非作品。任何一部好的作品,都应该在最终的文本呈现上摆脱偏狭的地域意识。
在越来越多人的心目中,地域往往与特色挂钩。在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上,地域性也已经形成一套所谓的研究理论和研究范式。但凡涉及作品的地域性研究,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从民俗、方言、地方性仪式、地方性知识等诸方面去研究,少数研究得好的还会去深入探讨一下隐藏在这些表层的地域性概括背后的文学构成,但大多数都是在套固定的话术,得出的结论也大同小异,使得各个明显差别很大的地域在实际呈现上竟然出奇相似。归根究底,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白一个事实,所谓的民俗之类的表现并非文学作品所独有,它的社会性价值更为重要。如果单是研究这些,没有必要非要到文学里去寻找,若是从文学的角度,探寻文学是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展现民俗的,倒还稍有文学价值,但很少有人把这个问题做出彩来。
其实,很多时候,所谓的地域性特点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正如上文所说,它是一种文学想象的生产,但这种生产并不都能取得成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地域性的书写容易陷入一种反现代的等级制关系中,并暗含着一个文化和身份权利层次的问题。在文学史上,最典型的莫过于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的书写模式。“地域文学强调的是一種‘地缘’与文学的关系,尤其注重作家的籍贯以及创作和精神原乡之间的内在互动。”[3]在现代文学中,地域在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乡村,城镇似乎不具有地域性。于是乎,对地域的书写就逐渐演变为对乡村的书写。当然,这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在中国现代化初期,中国的大城市极为有限,有关城市的书写自然就较为有限,而且,在传统的文化视域内,城市常常处于一种文学的悖论中:一方面城市所代表的现代化进程是人们孜孜追求的,但另一方面,城市中的腐化堕落又是作为批判的对象而出现的。因此,现代作家对待城市的态度,一直都是十分暧昧的。此外,现代化的城市进程是一种舶来品,与传统的城市化不同,因此,在现代作家看来,这种城市化并不具有归属性,而是一种陌生化的事物。自然,现代作家不可能对其产生归属,也就不可能将其视为自己的精神原乡,城市化写作也不可能被视为地域性书写。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虽然城市的异化属性被消除,但城市所象征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仍被排斥,于是,城市也就面临一个接受改造的命题。社会主义化的城市成为工厂所在地,不再是消费的象征,转而成为生产力的象征。但社会主义化的城市依然面临新的难题,即现实中的城市与乡村被置于几乎绝对对立的状态,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所带来的对立与隔膜,身份认同上的对立等诸多问题皆由此产生。于是,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陈焕生上城和高加林的故事依然在演绎着。城乡对立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等级制观念在作祟。过去是乡村优于城市,而现在彼此的位置却倒置过来。但无论如何,等级制关系一直存在。于是,地域性的书写就变成一种等级制关系下的话语书写。
“从五四时期开始,在讨论文学话语中的‘地域性’因子的时候,一种以严肃、正统著称的‘启蒙话语’对此进行抗辩。‘启蒙话语’认为所有的‘地域性’应该如城中村一样被拆除,被改造。在这样的阴影之下,文化有层次分明的等级,有优质与次等的二元对立。农村边远地区或边疆地区的地域文化面对自身时,则难免露出‘次等’文化的羞愧之色。这样的文化环境久而久之也促生地域性诗歌写作的诸多尴尬局面。在地域诗歌发展的过程中,有的诗人往往采用雷同的意象去表达地域性的特征。由于没有足够和深刻的对生命的真切感知与思考,诗人往往陷入模仿的窠臼或同质化的境地。另外,地域性诗人群将自己的地方特色或個性发展到顶端的时候往往会遭遇瓶颈期,诗歌语言的枯竭和资源的匮乏也导致地域诗歌的式微。”[4]而且,更为严重的一个倾向是,一些诗人为了追求某种地域上的独特性,制造诗意,以一些偏涩的故事、传说、神话入诗,而不顾及这些素材是否有价值、是否与诗歌相合。在意象的组合、使用上,同样也有这一倾向,很多意象突出诗歌的存在性,但诗意的营造却并没有跟上意象的转换,这就自然造成二者之间的脱节。
很多时候,文学创作者们对地域性资源的过度依赖,并以此支撑自己的创作,不经意间就形成一种创作惰性。尤其是对于那种“深深植根于地域文化、历史风情并偏于一隅的诗人而言,或许只有进行独特的地域式创作,才会使其位置和风格凸现出来” [5]。这些诗人的创作“在反映他熟悉的地域生活以及故乡记忆时显得得心应手”[6] 。诗歌创作过于依赖地域资源,而一旦离开故土,或者走进新的创作题材和创作领域时,则往往茫然。而且,依靠地域性的创作往往难以持久,也很少能取得超越性成就。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长期浸润在地域性中,创作渐成格套,慢慢便沉浸其中,不知不觉形成一种创作的惰性,而创作出的作品也难免有些“千篇一律”的味道。当然,对于一些具有反思意识的作者而言,他们对此十分警醒,这一点在宁夏诗人单永珍的论述中得到某种呼应,单永珍曾说:“地域性仿佛方言,更是一把双刃剑,在营养自己的同时,可能会伤着自己。说起‘地域性’,我似乎有点儿悲伤。因为地域性成全我,让我漫游西部,似乎找到自己的地理背景和精神背景,找见精准的表达切口,为此而自得其乐。但当我发现别人送我一顶‘西部诗人’帽子的时候,仿佛我只在‘西’,‘东南北’似乎与我无关。这顶帽子实在有点儿小,盛不下我不羁狂野的心。何况我还有愤怒的双腿、批判的牙齿,目空一切的逍遥。”[7]
一些文学史上的大家,很多都是从地域写作开始的,但到后来,文学功夫愈加炉火纯青之时,我们往往会看到另一番景象:对地域意识的摆脱,或者将地域意识转化为一种内在的方法论,成为一种书写人性的方法论。对此,单永珍也有精妙的分析:“福克纳一生都在写邮票般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小镇;艾特玛托夫写天山草原、沈从文写凤凰小城……似乎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大作家,难道没有地域性?我们回到‘人’的话题。文学作品写的是人,挖掘的是人性。人性就是真善美与假恶丑,这是根本。所谓的描写,不过是叙述的必要,一切都是为‘人’而服务。就像读《红楼梦》,如果被大观园的景色所遮蔽,看不出人物命运的悲欢,笔者想,哪怕读一千遍,也是白读。有个词叫‘风土人情’,有很多作品把主要的笔墨放在‘风土’的描写上,而忽略对‘人情’的深度挖掘,本末倒置,作品成了几张废纸。原来,福克纳、艾特玛托夫、沈从文他们在写人性,而不是写‘风土’,地域并没有拴住他们的思想,而是让他们更加深刻。”[8]
文学是“人学”,文学的书写最终要落脚于对人性的发掘上,也就是说,在文学中,地域更多地是作为一种书写的方式、途径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和呈现加以使用的,地域只是为了抵达人性中的一个中间物。但就当前存在的地域书写而言,显然是有些南辕北辙的。
此外,在当前诗歌的地域书写中,书写内容虽然复杂,但书写的维度却是较为单一的,一种“反讽式”的诗歌写作几乎还未出现,地域大多数时候还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神秘的理想,一种更为复杂的地域书写仍有待于被发掘。
二、“新疆”作为一种诗歌方法
——关于“地域性”的一种诗学考察
(一)“新疆”不仅仅是一种地理学和类型学
在一个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世界”逐渐成为一种同质化的公共知识体系,而地域性书写吸引人眼球的地方在于其稀缺性和奇异性。与诗歌中书写内容的不断推陈出新一样,地域性在大量的书写中必然会逐渐走向“熟悉化” “自动化”,从而逐渐丧失这种稀缺性和神奇性,其制造“陌生化”的能力也在逐渐丧失。地方性的反复书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诗歌创作的同质化。为避免同质化,寻求差异,大多数诗人的第一思维惯性不是变革诗歌的写作技术和结构体系,而是继续挖掘更为隐秘的地域文化与地理知识,直到这些隐秘成为众所周知的陈词滥调。说到底,这样的问题源于诗人的懒惰和认识的局限。诗人们不愿意深入语言的深层结构和事物的深层结构中,不愿意进行技术和方法上的更新,他们往往聚焦于诗歌内容表层和语言表层的变革,试图以内容上新事物的入诗推动诗歌的奇异化,试图通过语言表层的词汇、意象的更新实现诗歌语言的迭代升级。殊不知,这样的认识只停留于对诗歌的内容认识,具体到新疆书写上,就是把“新疆”的奇异性当作一种内容的奇异性,而不是一种方法的奇异性。“新疆”仅仅是作为一种内容上的地理学和类型学加以使用的。但事实上,作为一种方法的“奇异”和“惊讶”,比在内容上的“发现”要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尤其是在对地域性内容的发现逐渐倦怠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方法的新疆书写逐渐呈现出其新的可能性,并有望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这是一种聚焦的转移,它提示我们,在新的历史背景和对象已逐渐浮出地表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进行思维的转换,使新疆书写成为一把诗歌的手术刀,清理掉一些陈旧的地域性观念,使其长出新的诗歌粮食。
(二)“新疆”如何书写——语言、视角、技术与方法
“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它真正的意思是每一个词语都渴望成为诗。诗人的职责就在于响应词语的这一要求,并以自己全部的才智和心灵服务于词语的这一要求。”[9]语言是诗歌的本体,因此,谈论如何书写“新疆”,语言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语言不仅是一个个词语串联起来的语句,更是一种生活的观念和方式。人,当进入新疆这一广袤的语境中时,便与新疆发生关系。而关于这一关系和体验的诗歌表达,则构成关于新疆的书写。诗人使用何种语言表达,决定他以什么样的态度和生活去阐释与之相对应的生活。语言,不仅仅包含方言词语,而且更是这种方言背后的生活方式。特殊的生存环境和生存体验,生成特殊的地方性词语和地方性表达方式,与之紧密相关的是其背后的生存命题。因此,方言入诗,绝不仅仅是意象的增加和词汇的更新,而是一种新的生存体验的增加、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进入。诗人在诗歌中启用方言,不应该是出于猎奇的心理,而应该是出于以此挖掘新的生命体验,借以表达新的生命感受,由此丰富诗歌内在感受力的目的。关于新疆的一些地域性词语的使用同样如此,诗人启用这些词语,是在唤醒一个地方尘封的历史,重温在这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些历史和故事中与当代生活相连接,“它在这些历史和故事中重新辨认出自己,生成关于自己的故事”[10]。同时,方言的使用,也要考虑其对诗歌句式、节奏、体式变换的意义。
在苏仁聪的《吐鲁番盆地的日落》中,诗人是这样书写新疆的:
“这一生的其中一夜,一位美丽的姑娘与我比邻而坐。在一节老旧的绿皮车厢,我们拉开窗帘,使晚霞包围小桌上的茶杯。晚霞布置在河道,她恬静而优雅,使晚霞轻轻掠过她的鼻尖。对坐的维吾尔青年在这时候弹起他的萨塔尔,唱起他的歌。我不明其意,也无法询问。我沉浸在它奔泻的悲凉中,并认为这是我送给这位姑娘的见面礼和告别礼。这是落日的一瞬,高昌王国灭亡许多世纪后的某一个黄昏。我欢喜而忧愁。”[11]
這是一首节奏舒缓、充满抒情意味的诗,诗歌中那些遥远的新疆词语,每一个都有其沧桑的历史生命,诗人在火车行进途中与之相遇。当代的生活体验与古老的新疆故事撞个满怀,碰撞出火花,由此展开新的故事。这种碰撞性的交流既丰富诗人自身的生命感受,也丰富和延续古老的新疆故事的生命力。在诗人那里,新疆在此时此刻仿佛活了过来,成为近在身旁的生命,彼此感受生命的体温,彼此交换故事、交换心事。诗人从自身体验出发,借助冥想、回忆、虚构,穿越到一个既独立但又与现实时间相关联的世界,却并不是为了表达某个“哲理”,而只是为了重新返回自身,回到一个经过想象和反思的“新疆”现场。而这些地域性的词语、意象及其构造的句群和段落,则成为一种写作的基点,它像一个诗人的工作台,为新疆的重构提供支点。
但这种地方性语言的启用也并非百利而无一害,在一些诗人那里,他们“总是把来自与历史语境有关的变化看作是个人才能使然的产物,和来自由地域提供的语音差异的产物,因而在他的诸多结论中,便出现了只要有了才能和说某种语音,就可以解决所有诗歌的质量问题,写出所谓的‘本真’的诗歌”[12]。这种有所偏颇的观念导致诗人对地方语言的依赖,尤其是当他们“试图把这些本质上属于私人性的命题上升为普遍的写作原则时,就成为对诗歌真理的遮蔽。而当它被进一步用作攻击他人的口实的时候,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其后果是缩减我们写作的空间,贬损我们写作的权利,使丰富、健康的写作现实重归于某种单一的写作图式并趋向贫乏化”[13] ,这既不利于诗歌观念的更新,也不利于新的诗歌技艺的创造。正如诗人西渡曾猛烈抨击的那样:“正是这种把诗歌题材限制在中国特点的企图,这种对地方色彩的过分强调,暴露了这些人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对西方文化的迷信。”[14]尽管“每一种语言都有其难以为其他语言所复制的特殊魅力,对汉语方言来说也是如此。但是我同样相信,每一种语言也有其各自的局限性,它是保持或形成其特殊魅力所付出的必要的代价。对汉语方言来说,这一代价就是语汇的贫乏,而造成方言词汇量贫乏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方言语言系统的封闭性。而这种封闭却正是保持方言的特殊性和纯正性所要求的”[15] 。方言的稀缺和特色是以封闭性为牺牲代价的,这种封闭性导致过量使用方言,进而往往造成表达的晦涩,甚至使诗歌成为一种“黑话”;另一方面,方言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也降低词语表达的精度,分散词语的凝聚力,使诗歌的张力过于分散。因此,诗人使用这种地方性词汇,主要应当取其独特而具有普世性的地方性精神,将其转化为一种精神方法加以使用,而不应当单一地使用地方性语言。
“新疆”也是一种诗歌视角。谈及新疆,大多数诗人的笔触都还停留在对新疆自然景观和对古代人文景观的赞叹和歌咏中,殊不知,新疆的这些奇异性在代代诗人的书写中已经不那么“陌生化”了。甚至都很少有人注意到,新疆的现代城市和现代文化同样绚丽多彩,引人瞩目,而且可能具有更大的奇异性。这是一个视角的问题。它似乎在提醒我们,我们对新疆的书写和想象是有偏差的,而换一种视角,可能更有利于祛除某些偏见和遮蔽。
此外,新疆的视角意义还在于,通过新疆,我们得以从新疆这一视角出发,去观察和审视新疆之外的世界,去发现新的存在。“诗歌所以是发现,不仅仅因为它提供给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重要的是它提供给我们关于未来的知识。” [16]以往,在“看”与“被看”的模式中,新疆似乎总是处于“被看”的位置,似乎没有“看”的主动权。因此,新疆的形象也总是外在于自身的。它不是由自己建构的,而是在他者的言说中构建起来的。因而,新疆往往具有一种遮蔽性的神秘气息,但如果从新疆自身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会发现这种神秘性其实并不存在。而且,由这种神秘性引发的陌生化和“间离”效果其实也不存在。当然,这是一个视域的问题,而视域的背后则明显存在一个参考背景,是以他者为参考还是以自身为参考的问题。笔者觉得,两方面都要兼顾,但从目前来看,更多的是以他者为参考,缺乏一种内心的参考。这就导致其所塑造的新疆形象是不够准确的。
因此,书写新疆的一个问题是要解决“看”与“被看”的问题。新疆不能总是被看,而要主动去描述自身,不能总是等着被认识,而要主动去阐述自身。新疆是怎样的,不应该仅是一个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更应该有一个在自己心中的形象,而且还应该主动去把这个形象表达出来,两种形象相交流,才会形成一个更为丰富,也更为真实的新疆。但从目前来看,这种从自身出发,书写自身的“新疆书写”还没有发展起来,这种主动性的视角还没有展开,新疆自身的主体性诗学还没有建构起来。
比如在苏仁聪的《栖尘客栈》一诗中,这种新疆形象的发掘和建构依然是非主体性的:
“我以一个贫穷游客的身份爬上二楼,楼顶有鹰的雕像。花瓶空空,门面有大象售卖,合金的,彩色的大象。有阿拉丁神灯,神已搬家多年。有断裂的木楼梯,我小心翼翼爬上顶楼。这是高台的高处,据说国王曾带领他的人民在这里躲避洪水,洪水如今不再泛滥,风和阳光抚摸着盛世人民。栖尘客栈,老板解释说每个人都像是塔克拉玛干的沙子尘埃,在尘世栖身。我轻抚落在枯木上沙子,寻找和它们的相似之处。天空染上暗黄,傍晚一群东北人在院子里喝酒划拳。我从楼顶下来,暮色如同夯土建筑群,使我误入疏勒古国的城堡。”[17]
在苏仁聪的描述中,诗人自己没有融入新疆的身体里,诗人仍以一种客体的身份审视新疆。新疆仍是一个被诗人“看”的事物,新疆的形象不是自身的形象,而是诗人眼中的形象。诗人没有成为新疆,甚至也没有站在新疆的立场上去描述新疆,刻画自身的形象,诗人终究还是在借新疆表达自身的情感,而不是表达新疆自身的情感。从这一点而言,他们之间存在隔阂,没有真正的理解和融合。
新疆当然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整体性的诗歌技术和诗歌方法。这种“技术”和“方法”是一种基于新疆的独特性,通过这种独特经验的总结、提炼和升华,使经验成为一种技术和方法。当然,这里谈技术和方法其实也是一种总体性的理念,它不是一种具体的技法,而更像是一种“操作原理”式的东西。在诗歌中,“新疆”的技术和方法不是内容性的,而是一种属于新疆的表达技术和表达方式,它有独特的气质,使人一读就能感受到其属于新疆的独特性。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技术和表达方式一样,新疆区分于其他地方,也有独属于自己的表达技术和表达方式。这就提醒我们,认识新疆、书写新疆,不要局限于新疆的呈现,更要挖掘这种呈现背后所代表的新疆技术与新疆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没有技术和方法的革新,诗歌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革新的。就像很多书写新疆的诗歌一样,内容上的差异如果被放在技术和方法层面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所谓的特色是表层的,换个地方依然成立。这就导致没有技术和方法革新的地域书写,在经验上的雷同和书写中的同质化。因此,地域性书写一定要放在技术和方法的层面上加以分析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所在,而地域性也只有“转化为一种独特的诗歌技术、诗歌方法甚至是一种独特的诗学理念,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一种诗歌现象或诗歌流派”[18]。也只有在技术、方法和诗歌诗学理念的层面上,诗歌地域性的命题才真正成立。
(三)关于新疆诗学的观念建构
在文学史上,地域性书写曾作为一种先锋性和异质性写作方式出现。比如东北作家群的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东北作家群之所以引起文坛关注,与其鲜明的东北书写分不开关系。那时的作家普遍习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写作模式和通俗文学的写作模式,这时候突然涌进一种具有先锋性质和异域特质的写作方式,人们自然会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所谓先锋和异域,除了地域,还跟当时与抗战相结合有关,可见,地域性不是唯一的因素。后来,地域性引起关注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中。地域书写,尤其是对偏僻地域的书写,成为人们挖掘民族生命力的一种途径,其实彼时地域性就已经逐渐显露出其方法性特征。当然,地域性同样也是以先锋和异质的姿态引起关注的。在对待新疆书写的问题上,地域性同样可以成为一种先锋和异质的姿态,只不过这种先锋应该被以一种诗学方法看待。在这一维度上,新疆书写可以成为一种革新的诗学力量,推动诗歌创作乃至文学创作的发展。
但是,地域性只是写作的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诗歌文本最终的价值不能仅仅体现为地域性。诗歌的新疆书写应该从地域性这一自身语境出发,以此为中介,抵达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触及人类的根本命运。就像苏仁聪的《火车经过龟兹故地》一诗。
“龟兹国灭亡若干世纪后,我坐一列慢火车,在深夜穿过曾经属于它的国土。没有驼铃,丝绸和茶叶,睡去的人鼾声和火车声奇妙地融合了。盛产铁器的龟兹,它的铁已彻底锈蚀,和它的国家一起埋于黄沙。只有那些坚强的植物还生长在他们的坟地,戈壁上空那轮寒冷的月亮照耀着,最后一位死去的君王。我用一夜就穿越他的国土。他必定感到惊讶,但他已无力起身。”[19]
这些富有新疆特色的意象不仅仅是一种布景,而且还是一种经验的实体,是诗人思绪、意义绵延的重要依据。在这首诗歌中,新疆的历史、新疆的文化是诗歌表达的起点,诗人将自身的经验注入其中,颇有起死回生之功效。但诗歌最终的目的并不在此。召唤一个久远的历史并不是单纯地让它复活,而是为使之具有新的生命力,使之成为新的自己。这个新的自己中包含着广阔的历史,包含着自己沉睡的时间,包含着一个独特的生命体验。而这种独特的生命体验最终通向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生命世界。在这个生命世界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发现自己的位置。
在历史上,地域性写作形成地域性写作群体,抱团取暖,更易获得成功。“为了‘突围’,便选择群体的方式制造大规模‘哗变’的景观” [20],以吸引人的注意,从而获得一定的话语权利,但“‘团伙’的集结方式与诗艺的建设无关(有时甚或受到损害)” [21],这种一时的成功是有代价的——作家个性、作品个性的泯灭和消散。基于此,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鲁迅的作品与浙江地域文化息息相关,但鲁迅不会被贴上浙江作家群的标签,他的创作也不会首先与浙江相关联。这是为什么?首先,作为一个世界级的作家,鲁迅的写作是从浙江出发的,他笔下的环境及环境中的人物,是与浙江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因此,在这一维度上讲,鲁迅的作品其实也具有地域性特征。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这种地域性为什么没有成为审视鲁迅作品的第一性要素?甚至不会成为鲁迅作品的标签?其实,这是因为鲁迅的作品虽然是从地域性出发的,他笔下的浙江风物如流水一般行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但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止于地域性书写,而是超越地域性,上升到人类的普遍人性上,揭示人性的种种“劣根性”。不像某些缺乏思想的作家,除了地域就没有其他能拿出手的东西了,没有在地域性的土壤上生发出更多的想象和思想来。
三、超越地域性的局限
——在历史和时代性中书写人性
诗人王家新在编选《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的序言中说:“一个独立的、有远大目光和创造力的诗人完全有理由超越现实纷争,完全有理由拒绝将自己归属于任何一方。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是:谁都不可能不与历史发生纠葛就能超越历史,诗人也没有这个特权。” [22]在新时代,真正的诗歌不可能不与当下的历史与现实发生纠葛,但也绝不能在当下的历史与现实中纠葛而停滞不前,而要像王家新所说的那样,超越现实纷争,将目光投向具有终极关怀的远方。新时代的诗歌大有可为,诗人大有可为。同样,也正是因为新时代的广阔,为我们提供一个重新认识地域书写,认识新疆书写的新视野。新全球化理念及与之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提出,为超越地域书写的局限提供一种方向。它提示我们:新疆书写或书写新疆要从新疆的具体性出发,但最终不能停留于这种具体性上,而要实现对这种具体性的超越,最终抵达的是一种新全球化背景下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存在和表达。但同时也要防止走向一种空泛的普遍性,正如王家新提醒的那样:“中国诗歌肯定具有超越其政治、歷史语境限制的可能,但那种普泛化的‘国际诗歌’却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背弃自身的写作依据而‘走向国际化’,为一顶虚设的桂冠角逐,很可能会将自己架空为一种可疑的、不真实的存在。且不说背离中国性与政治性之不可能,即使果真背离这一切,达到一种纯之又纯、国际了又国际的程度,它还会对中国诗歌(以及对其他诗歌)构成意义吗?”[23]超越地域性不意味着抛弃地域性,更何况我们也不可能将其完全抛弃。
“诗人善于从普通的事物中攫取深奥的玄思,以普通的事件烛照普世的哲理,从而召唤人类的普世价值。他往往超越洪湖的狭小空间去透视与折射整个人类与整个世界。”[24]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其实每个人都处在这样一种场域中,都会受到这种场域的影响,只不过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因此,在其诗歌的书写中也就不可避免会有这种因子在里面反映出来。在新全球化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中,人类的自由、平等,人性的完善、人类的团结、生命的尊重等诸多普世性话题都得到照拂。这也是地域书写最终要抵达的精神远方。只不过,地域书写是通过具体性与具体性的克服和超越而实现的。正如西渡所言:“从诗歌的本性上说,它始终是对现实和常识的超越。说到底,现实只是事物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诗歌不拒绝现实,但是把诗歌等同于现实,并进一步等同于常识(现实也比常识拥有更丰富的内涵),就是要扼杀诗歌的诸多可能性,是使诗歌贫乏化的一个企图。”[25]诗歌又不得不从现实的具体性出发,但最终却要超越这种具体而固定的现实,“而能够超越细节本身,把读者引向对细节中所包含的特殊历史境遇的关注”[26] 和人类共同话题的关注。
苏仁聪诗歌中的新疆书写也不例外,对新疆的书写只是其出发的地方,而不是终点。它通过对新疆风物、新疆故事、新疆典志的挖掘和书写,叩响历史长河中的生命之音,并在地域性的當代转化中,走向当下的生活,走向人类普遍追寻的共同离合悲欢,而在离合悲欢中,暗藏着人类共同的命运、寄托与梦想。这些有关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的事物并非一些空泛的、凌空高蹈的修辞,并非一些宏大的政治理念,而是一些经过诗人艺术化处理的、同表达自身独特的经验联系起来的、同诗歌发展联系起来的具体的、日常化的事物,它们一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同我们接触,与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同频共振的世界里。因此,这里所说的超越并不是一种摒弃一切世俗的宗教式超越,而更接近于一种日常的超越,它不是超验的或先验的,而是一种依靠日常生活积累式的升华。也许更像马丁·路德·金的宗教改革中宣扬的那样,因信称义,人人都可以同上帝交流,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人类的超越性则孕育于人类自身,在每一个渺小的个体中。在诗歌的表达中,这种超越性基于日常性而又超越日常性,但最终又以一种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时,这种超越不是一种普泛的、无针对性的终极或永恒,而是能“在一种更开阔的视野中反观自身的历史形成”[27]的具体而又有所依托和归依的超越。在此,我们应当记住,超越是相对于具体和日常而言的,离开具体和日常,超越可能什么也不是。
在某种程度上,地域性并不能完整地构成诗歌的价值来源,真正有价值的并不是单纯的书写地域,而是书写在地域中生活的独特而又具有普遍人性的人生。苏仁聪书写新疆这个地方的历史和人物,书写新疆的人和生活,这种书写既普通又伟大。在对普通生命的书写中,诗人揭开人性的伤疤,而这些伤疤我们每个人都有。在苏仁聪的书写中,这些内容是如此具有新疆气质,同时又是如此普遍,我们总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这就是一种相对有效的书写,始于地域,而又超越地域,抵达更为广阔的人性和生命。
参考文献:
[1][2]李晁.来源与消隐——浅谈“新南方写作”的地域及地域性[J].广州文艺,2022(02).
[3]姜汉西. 当代地域文学研究的困境与新的可能性 ——以21世纪“中原作家群”研究为例[J].地域文化研究,2019(05).
[4][24]李琳. 试论湖北诗歌应如何走出地域写作的困境[J].现代交际, 2019(14).
[5][6]张立群.新诗地理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5,5.
[7][8]单永珍.文学课堂之五:地域性[J].六盘山,2023(05).
[9][12][13][14] [15] [16] [22] [23][25][26][27]王家新.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9,16,22,32,32,28,3,280,27,326,285.
[10]赵刘昆.守望大地 回归传统——郭文斌散文的文化选择与思想内涵[J].新疆艺术(汉文),2023(03).
[11] [19]苏仁聪.无边[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4,3.
[17] 苏仁聪. 栖尘客栈[J]. 诗歌月刊,2020(07).
[18] 赵刘昆.“90后”诗歌的“技术主义”倾向[J].星星(诗刊),2022 (32).
[20] [2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10,210.
作者单位:重庆城市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