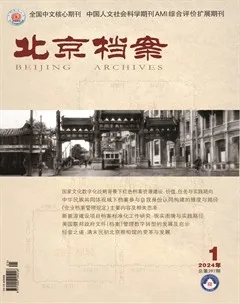居庸关云台
2024-02-21张幼欣
张幼欣

居庸关云台(又称“过街塔”)为元代所建藏传佛教造型的建筑,至元末时佛塔损毁,明初又在原塔基上修建佛寺。它矗立在群山之间,两侧尽是峰峦叠翠,明人惊叹其景观之壮丽,将之列为“居庸八景”之一,因其“远望如在云端”[1],始有“云台石阁”之称。康熙四十一年(1702),因上方佛殿焚毁,仅剩塔基,故俗称“云台”。在云台券门下方石壁上雕刻有四天王、佛像,以及八思巴文、汉文、藏文、回鹘文、梵文、西夏文六种文字的《造塔功德记》和《陀罗尼经咒》。其中,多元艺术元素的交相辉映、各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使得居庸关云台成为北京地区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居庸关为“天下九塞”之一,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细数从辽至元的王朝更迭,如金灭辽、金灭北宋、元灭金,居庸关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不仅见证了王朝政权的更迭,更见证了游牧民族向“汉地”进军、游牧与农耕文明的互相冲击与渗透。居庸关地处游牧与农耕文明交融带的文化意义为元廷所重视,元顺帝在居庸关建造佛塔,主要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居庸关云台的修建直接与元帝在大都与上都间的巡幸活动有关。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出于兼控中原汉地与蒙古的需要,以及对游牧风俗的继承,实行两京制(即元上都与元大都),每年巡幸于两地。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帝两京巡幸活动开始于中统五年(1264),“中统元年,为开平府。五年,以阙庭所在,加号上都,岁一幸焉”[2],即每年二月至八月(或三月至九月)在上都度过,并固定下来,这种巡幸活动被时人称为“纳钵”,居庸关作为巡幸两京的必经之路,又有“纳钵关”之称。元至正年间,顺帝提议在居庸关修建佛寺和佛塔,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为自己在巡幸两京的途中建造一个休憩之所。据《析津志》记载,居庸关永明寺修建前,元帝巡幸至居庸关处往往连夜出关,无处休息,因此在居庸关修建永明寺作为落脚之处,居庸关云台(即过街塔)则是永明寺整体建筑群的一部分。永明寺修建竣工后,元顺帝巡幸两京时常在此驻跸休息,这里也就逐渐成为巡幸途中的一个固定休息地点。
其次,元代居庸关云台的修建也受统治者宗教信仰的影响。忽必烈在建立元朝前便开始接触藏传佛教,元朝建立后,藏传佛教的势力在忽必烈的支持下继续上升。忽必烈对藏传佛教的支持和崇信,除自身宗教信仰原因外,还是为巩固自身统治寻找一个精神支柱并借此宣扬其统治的正统地位。[3]此后,元朝历代皇帝都信仰藏传佛教。而元顺帝在承袭信仰藏传佛教的同时,也注重发挥藏传佛教的教化功能,因此,他下令在居庸关建造藏传佛教造型的佛塔,并在券门下方铭刻多种文字的佛经、佛像,使过往的各族人士经过塔下时如同礼佛,皆能“皈依佛乘,普授法施”。
第三,元代居庸关云台的修建也与元大都风水格局存在一定关联。张谷林从风水堪舆文化的角度探讨居庸关与元大都建都形胜的关系时认为,以居庸径北口即现今关沟八达岭“北门锁钥”长城关城门为起点,“经长城居庸两关城门、再经元大都西北城郭的健德门,至元大都的中心点(钟鼓楼)为终点,可拉出一条笔直的堪舆‘天门线’”,而元代的居庸关岭应该是元大都城的第一“天门”,这样元大都城郭便有12座门,这样的布局符合《周礼》礼制,[4]可见居庸关在元大都风水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元人欧阳玄在《过街塔铭》中谈到当时修建居庸关云台的其中一个目的便是“令京城风气完密……由是邦家大宁,宗庙安妥;本枝昌隆,福及亿兆,咸利赖焉”[5],建过街塔是为了使“京城风气完密”,可见云台的修建也受到汉地风水堪舆文化的影响,这也反映出元朝统治者对传统中原文化的吸收和应用。
元朝版图之广堪称中国古代历朝之最,在其统治的广阔疆域内,各族文化背景不同,有着较大的文化差异。面对如此境况,元朝统治者实施开放的文化政策,国家内部文化类型呈现多元景象,推动了各族群间的文化交流。受此影响,统治者广纳贤才、选贤任能,招揽、吸纳各族士人参与国家治理,如任用畏兀儿人、西夏人担任官职并承担一定的文字、语言的翻译工作;在宗教方面倚重吐蕃人,并将藏传佛教“喇嘛教”定为国教;军事上任用骁勇善战的西夏人和女真人,这种对各族精英的吸纳与任用彰显了元代文化的开放与多元并充分体现在居庸关云台的建造中。
至正二年(1342),元顺帝下令修建居庸关过街塔,命右丞相阿鲁图、左丞相别儿怯不花、平章政事铁不儿达识及御史大夫太平总领建塔事宜。据八思巴文《造塔功德记》记载,御史大夫太平为建造此塔的实际总负责人,[6]阿魯图、别儿怯不花等似为挂名;在具体施工中,负责官员主要是来自西夏故地的党项人,如平章政事纳麟及主持译写西夏文的智妙咩布和显密二种巧猛沙门领占那征师等,此外,管理相关具体事务的还有藏人南加森;[7]在过街塔券门内各种浮雕纹样的刻画上,由僧众亦恰朵儿、赛罕、金刚吉、普贤吉、八剌室利等人设计样式并“授匠指画,督治其工”[8],经谢继盛考证,云台券门内出现萨迦传普明大日曼荼罗图案应是受帝师喜幢吉祥贤的影响,[9]可见帝师喜幢吉祥贤亦参与或指导过街塔的设计。在过街塔建成之日,元顺帝敕令汉人翰林学士欧阳玄撰文记述赞美其事并由学士张起岩篆刻匾额。
在过街塔修建过程中,各族人士广泛参与其中,虽然限于史料部分族群属性难以考证,但可以确认的是其中各族人士文化背景各异,如阿鲁图、别儿怯不花(燕只斤氏人)、铁不儿达识(康里氏人)等承袭的传统蒙古族草原文化;南里剌麻徒弟亦恰朵儿和南加森等代表的藏传佛教文化;欧阳玄、张起岩等所代表的汉地传统的儒家文化;纳麟等来自西夏故地的党项人所承袭的西夏文化等,各民族、地区的文化由此碰撞交融。

在元代开放多元的文化政策背景下,各族文化伴随着社会流动,在各族人士的交往之中不断影响、渗透乃至交融,居庸关云台券门内的铭文与浮雕艺术造型也融合了当时蒙古、中原、西域等地各民族的文化元素。
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居庸关云台券门内东西两面墙壁的铭文所记载的内容是蒙古族佛教仪轨文中的赞颂诗和祈愿诗联壁的姊妹篇,其中有歌颂元帝信仰藏传佛教、修建佛寺之举功德无量,荫及子孙万世的,还有借“天意”论证元代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10]由汉文、八思巴文、梵文、西夏文、藏文、回鹘六种文字铭刻《造塔功德记》和《陀罗尼经咒》,反映了元代各民族文化在北京地区交流交融的盛况。
元代文化政策的开放性,使得“此一时期的多民族物质文明更显生机,其中融合了多民族文明元素的元代艺术具有强烈的气势与爆发力”[11],居庸关云台券门之下精美的浮雕便是多民族文化元素融合的体现。居庸关云台券门内的浮雕,按照所处位置及表现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券门内顶的“五曼荼罗”,南北券门的“六拏具”,门内东西斜顶的“十方佛”和东西内壁的“四大天王”像。这四部分内容无论从内容题材还是艺术风格来看皆是藏传佛教雕塑艺术,但也具有明显的汉地文化色彩,如四大天王之一的东方持国天王,其形象特征据《般若守护十六善神王形体》记载,本是紫发,身着红色甲青,肤色为青色,面带愤怒之相,左手伸臂下垂持大刀,右手屈臂向前托一宝珠。由于受《封神演义》的影响,内地大多佛教寺庙中的东方持国天王被塑为手持琵琶的中国武将形象,居庸关云台券门内的持国天王像则符合内地佛教寺庙的特征。在审美特征上,居庸云台的佛像融入了许多汉地造像的特点,如券门“六拏具”中的龙子和骑瑞兽的童子与四大天王形象,已然具备了汉式造像面容饱满的典型特征;另外在人物服饰、衣纹的刻画上也更加注重立体感和穿插关系的表达,增强了线条的表现力,可见尼泊尔式、印度帕拉式注重简洁的衣纹处理手法在汉地文化的影响下得到改良,汉地文化的色彩更加浓厚了。[12]
在元代多元共生的文化政策影响下,各族文化交流愈渐深入。在居庸关云台修建过程中,文化背景不同的各族精英人士共同参与,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云台券门内多种语言文字书写的佛教经文、多种文化元素共融的浮雕艺术作品,不仅是元代多元共生文化政策的结果,也是元代各族人士心血的结晶,更是北京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元、明“大一统”秩序变迁中的居庸关云台佛寺》(项目号:BZKY2023038)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周硕勋.延庆卫志略[M].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3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49.
[2]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350, 3374.
[3]陈高华,张帆,刘晓.元代文化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149.
[4]张谷林.论中华魂与根文化(第二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251.
[5][8]熊梦祥.析津志辑佚[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253,253.
[6]宿白.居庸關过街塔考稿[J].文物,1964(4): 18.
[7][9]谢继胜.居庸关过街塔造像义蕴考——11至14世纪中国佛教艺术图像配置的重构[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5):51,63.
[10]双福.《居庸关东西壁铭文》研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2):117-118.
[11]谢继胜.从多民族共创佛教艺术看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建构[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10-26(A03).
[12]关于元代藏传佛教雕塑艺术特色的研究,请参考201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专业陈健的博士学位论文,第38-43页。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