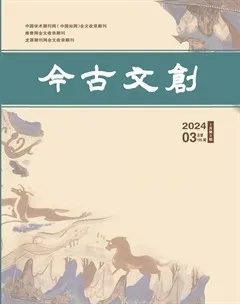福建平潭方言母系核心亲属称谓词研究
2024-02-02高佳丽

【摘要】词汇是文化在语言表达上最直接的体现。亲属称谓词蕴含着使用者对亲属关系的认识,在整个词汇系统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平潭方言亲属称谓词,能够从语言词汇的角度对平潭的地域文化做最直接的关注。文章通过描写平潭方言母系核心亲属称谓词,以点带面,对其作纵向的梳理和横向的比较,从接触视角看平潭方言亲属称谓词的特点,关注平潭方言今后的发展路径,并分析现有亲属称谓系统背后的文化机制。
【关键词】平潭方言;亲属称谓;母系;历时;共时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3-0111-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3.036
平潭综合实验区,简称“岚”,古称海坛,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由126个岛屿和702个礁石组成,主岛海坛岛为福建省第一大岛,全国第五大岛。平潭东濒台湾海峡,与台湾新竹港相距仅68海里,是中国大陆距台湾省最近的地方,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时代契机。西临海坛海峡,与福清、长乐、莆田隔海相望,距离省会福州市区仅128公里。
平潭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平潭方言既受周边方言相接触的影响,也有其相对独立、保守的一面。平潭话在《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2012)中被划归为闽语-闽东片-侯官小片。
词汇系统中的小类—亲属称谓系统,是由所有表示亲属关系的亲属称谓词共同构成的,它反映了使用者对所有亲属关系的认识。在一种方言中,对同一亲属关系的表示可能有不同的亲属称谓词,即“同指异名”;相反地,同一亲属称谓词也有可能用来表示不同亲属关系,即“同名异指”。亲属称谓系统的这种“形—义”不对等的情况在各个方言中都有表现。亲属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一种关系,研究亲属称谓词能够直接观照当地人的思想文化内涵,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同时关注历时源流与共时比较,注重描写平潭方言的母系核心亲属称谓系统,并从接触视角总结特点,关涉平潭方言在新时期的发展路径,同时借亲属称谓词研究探索其背后隐含的文化机制。
一、福建平潭方言的母系核心亲属称谓系统
由于当前学术界对亲属关系的分类标准不一,导致亲属称谓词的分类存在差异。既有从是否有血缘关系切入,分为血亲和姻亲;也有根据是否与自己有直接关系,分为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也有同时选取两个标准,将亲属关系分为直系血亲、旁系血亲、直系姻亲、旁系姻亲。还有直接从传统宗法观念入手,直接分为宗亲、外亲和妻亲三类。还有一种从谱系出发,将亲属称谓体系分为四大类,父系、母系、夫系、妻系,每一体系中再分上辈、平辈、下辈。或直接考虑辈分因素,分为祖辈、父辈、平辈、子辈、孙辈。各种分类方式各有侧重点,本文选取谱系分类标准,具体关注母系核心亲属称谓词,即上下三代中最基础、使用频率最高的亲属关系。
平潭方言亲属称谓词调查的发音人是五十岁的中年男子,同时参考冯爱珍(1993)《福清方言研究》、李荣(1998)《福州方言词典》中亲属称谓部分。
(一)祖辈
1.外祖父:平潭话称外祖父为“外公”。即在表示祖父的“公”前加上代表亲属远近关系的“外”表示外亲,也即母亲的父亲。
2.外祖母:平潭话称外祖母为“外妈”。与“外公”的构词方式相同,在表示祖母的“妈”前加上代表亲属远近关系的“外”表示外亲,也即母亲的母亲,也可记作“外嫲”。
(二)父辈
1.母亲:平潭话称母亲为“依娜”。在《汉语方言地图集》(2008)中,平潭话中对母亲的称呼被划为“其他”,也即与闽方言,甚至与全国其他方言的称呼都不相同。故无从得知其准确的字形,本文参考冯爱珍(1993)《福清方言研究》中对母亲称呼的别称,即“依娜”,借此表示平潭话的母亲称谓词。福清方言中称母亲主要使用“依奶”,福州方言中早先也主要使用“依奶”,后来还出现称“依妈”表示母亲。福州方言和福清方言中表示母亲的称谓在许宝华(1999)《汉语方言大词典》中都有记录,但平潭方言却没有任何相关文献记载,由此可见,平潭方言还没有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平潭方言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平潭话中用“依娜”称呼母亲,主要是用在面称,而背称时则常使用“X+奶”的结构。“X”主要是人称代词“我”“汝”“伊”,即“我奶”“汝奶”“伊奶”,依次表示我妈、你妈、他妈。“奶”大概是个后起字,最初写作“嬭”,《说文》未收录。《汉文典》收“嬭”,释为母亲。《广韵》:“嬭,楚人呼母。”《古音汇纂》引《合并字学集韵》:“奶,乳也。”同时引《中州全韵》:“奶,乳母。” ①由此可见,“奶”的本义即母亲,而后引申为母乳。“奶”表母亲,最早见于北宋《太平广记》:“其家树上,忽有灵语,呼阿嬭,即会妻乳母也。”此后文献记载也较少,故可以断定“奶”是个活跃在口语中的词。平潭话的背称中还保留中古时期的这种叫法,由此可见,平潭话中还存有中古汉语的遗迹,从中也可看出平潭话保守封闭的一面。
2.母亲的兄弟及配偶:平潭话称母亲的兄弟为“阿舅”,称其配偶为“阿妗”。这里有新老派称呼的不同,“阿舅”“阿妗”主要是老派称呼,而新派大多以叠音“舅舅”“妗妗”称之。“舅”在平潭亲属关系中代表至高无上的地位,当一个家族中的女儿结婚了,她的舅舅是整个婚礼中最重要的人,也是被奉为最上座的,其次才是父母長辈等。《说文·男部》:“舅,母之兄弟为舅,妻之父为外舅。从男臼声。”《广韵》:“舅,夫之父也,亦母之兄弟。”《释名·释亲属》:“舅,久也,久,老称也。”《释名》用声训解释“舅”,但含义不明,《说文》和《广韵》皆认为“舅”有“母之兄弟”义,故可以断定“舅”的本义为母亲的兄弟。相同地,若在平潭方言中给舅舅排行的话,则称“大舅”“细舅”“三舅”“尾舅”等。至于“妗”则并非一开始就表示舅母义。朱夏蔚考证“妗”具有舅母义最早是由“舅母”二字合呼而来的,并且引宋代张耒《明道杂记》:“经传中无婶与妗字,婶字乃世母二字合音,妗字乃舅母二字合呼也。”即“妗”是假借字,由“舅母”二字急读而成。②“妗”最早出现于哪个朝代还不明确,但它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分布较广,南方方言与北方方言区皆有涉及。苏新春(2000)运用词频选取法调查“妗”,发现“妗”在北方的三个点中拥有2个词,而在闽、粤方言中构成的词语多达14个,由此得出“妗”在北方统一程度较高,在南方的构词则存在相当分散的结论。在平潭方言中,“妗”的组词能力也比较强,有“阿妗”“妗妗”“妗妈”等称呼。
3.母亲的姐妹及配偶:平潭话称母亲的姐妹为“姨姨”,称其配偶为“姨丈”。“姨姨”实为新派称呼,老派称呼则会以“排行+姨”表示。例如“大姨”“细姨”“三姨”“姨姨”等。称最小的姨姨还可用“尾姨”。而对“姨丈”的称呼则跟从姨姨的排行称呼,直接在“大姨”“细姨”等后加上“丈”即可。
(三)平辈
母亲兄弟姐妹的子女:平潭话称母亲兄弟姐妹的子女为“表兄弟姊妹”。该亲属关系的称呼与父亲姐妹的子女的称呼相同,但与父亲兄弟的子女的称呼略有不同。对父亲兄弟的子女称为“叔伯兄弟姊妹”。称呼母亲兄弟姐妹的子女以及父亲姐妹的子女一律将前缀“叔伯”替换为“表”。由此可见,在平潭人眼中,只有父亲兄弟的子女关系最为亲近,母亲兄弟姐妹的子女与父亲姐妹的子女则拥有相同的地位。
(四)孙辈
1.本人的外孙及配偶:平潭话称本人的外孙为“外甥”,称其配偶为“外甥人”。这里称“外甥”与上文父系子辈中表示本人姐妹的儿子的称呼一样。按照本人称孙子为“孙”的标准,外亲孙子则应前加“外”表示,即正常情况下平潭话称本人的外孙应是“外孙”,但此处却往低了一辈称,因此可以认定此处是从子称。大概是因为外亲与宗亲本就有隔阂,再加上祖辈与孙辈年龄差距较大,为弥补这种差距和隔阂,故选择从子称。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为强调亲属关系,有时也称“外甥孙”。至于称呼本人外孙的配偶,参考“弟新妇”“孙新妇”,按理说应该是在“外甥”后加上“新妇”表示,例如《汉语方言大词典》(1999)中记载吴语-上海崇明区称外孙妻子/外甥妻子为“外甥新妇”。但平潭话中没有这样的称呼,而是称作“外甥人”,与福州方言称呼相同。笔者认为是因为在平潭人的观念中,本人外孙的媳妇不是来到自己家里的妇人,终究到底是外亲家的媳妇,故在构词方式上不使用“新妇”二字以示区别。
2.本人的外孙女及配偶:平潭话称本人的外孙女为“外女”,称其配偶为“外女孙婿”。同上文,这里称“外女”与上文父系子辈中表示本人姐妹的女儿的称呼一样。同样是选择从子称拉近与孙辈的距离。表示外孙女的配偶称呼“外孙女婿”,与表示外孙的配偶称呼不同,它没有另造构词方式,而是直接参考孙女的配偶称呼,在“孙婿”前加“外女”表示外亲关系。
总结母系亲属称谓词,大都是在表示亲属关系的词根前加上“外”或“表”等表示外亲关系,以区别父系亲属称谓词。
二、从接触视角看平潭方言母系核心亲属称谓词的特点
美国语言学家坎贝尔认为“语言接触会引发语言变化”,在其著作《历史语言学导论》中列举了语言接触的研究内容,包括借用、区域语言学、洋泾浜、克里奥尔语、混合语等。其中,语言接触最基本、最典型的表现是词语的借用。从母系核心亲属称谓词的描写中可以窥见,平潭方言中有与闽方言共通的一些性质,也有与普通话共通的一些性质,这些相关的词语表达体现了平潭方言与周边方言、普通话的积极的语言接触。吴喜(2012)称平潭方言呈现出一些语言过渡地带混合型方言的特点。
(一)与周边方言的共性
平潭方言是闽东方言,更是闽方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闽方言存在较强的内部一致性,因此,平潭方言与周边其他闽方言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共同点。
平潭方言与周边方言的亲属称谓词大都是由“词缀+词根”的形式构成。包括加前缀、中缀、后缀。例如平潭话大都是“阿+亲属称谓词根”:阿舅、阿妗等;厦门方言也多以“阿+亲属称谓词根”:阿公、阿母、阿娘、阿姑等;福州方言则大都是“依+亲属称谓词根”:依公、依爸、依姑、依姨等。
平潭方言背称亲属时常加人称代词“我”“汝”“伊”。福清方言中“我”“汝”“伊”皆为词语前缀,称本家亲属时,在称谓前加“我”,称别家在称谓前加“伊”,称对方亲属时加“汝”。③ 由于词汇双音化,若在称谓前加人称代词,则會对原称谓作相应的简化,例如“阿舅”—“我舅”,“阿妗”—“伊妗”等。
平潭方言重视同辈间的排行次第,区别同辈排行有特殊的前缀“大”“细”“尾”。福清方言中也使用这一套排行称谓,但有一点不同,表示排行第二时,福清方言可以使用“细”也可以使用“二”,平潭方言只能使用“细”。例如,平潭方言称呼母亲的兄弟:大舅、细舅、三舅、四舅……尾舅。福清方言称呼母亲的兄弟:大舅、细舅/二舅、三舅……尾舅。
(二)与普通话的共性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即从明清官话发展而来。普通话与平潭话也存在一些共性,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普通话作为强势语言在各地方言中大肆发展,平潭方言也深受其影响,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出现向普通话靠拢的现象。平潭话是从福州话发展来的,据吴喜(2012)统计,平潭话与福州话基本相同的亲属称谓词占85.65%。由此可见,平潭话大致上与福州话一致,但也有自身的发展变化。这一部分变化中就有平潭话向普通话靠拢的结果。
例如前缀“伊”和“阿”。福州话在亲属称谓词根前大都加“依”,但平潭话则大都加“阿”,平潭话的这个特点就是受普通话影响。普通话中多用“阿+人名”表示亲切,还有“阿姨”等亲属称谓泛化成社会称谓,基于此,平潭话多以“阿”为前缀,方言中仍然以“依”作前缀的亲属称谓词,例如“依娜”等都是较为存古的说法。
普通话影响平潭方言最明显的就是当代老、中、青三代人在使用方言时出现的词汇上的差异。老年人用词最存古最稳定,中年人既受方言影响、又受普通话影响,很多时候出现两说的情况,至于青年人则很多已经只会普通话不会方言,出现“方言失语症”。例如对母亲的兄弟的称呼,老年人称“阿舅”,中年人称“阿舅”/“舅舅”,青年人只称“舅舅”。
可以预见,随着推普工作的进一步完成,平潭方言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狭窄,方言使用也会越来越老龄化,这种发展是不可逆的,也是时代的诉求。因此在平潭方言逐渐消失在口语之前,应重视对现有方言的保护与传承,语保工作应尽快全面地深入地开展,让平潭方言至少可以留存在书面语或一些音像视频中。
三、平潭亲属称谓词体现的文化内涵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不同民族特定的文化。称谓词语有着深刻的文化烙印,它的历史变迁反映了新旧文化观念的变化。” ④如郑献芹所言,体现亲属关系的亲属称谓词是文化在语言上的外显,透过当地语言特征可以洞视该地特定的文化内涵。
1.严明有序的大宗族观念。宗法制度影响华夏子孙长达三千多年,商周时代的宗法亲族组织、秦汉以后的宗族组织、唐宋以后的姓氏宗族组织、明清以下直到近代的乡党家族组织 ⑤,不同时期具体形式不同,但都是以血缘为纽带、以亲族关系为框架建立起的家庭-社会制度。在平潭亲属称谓词中最明显的就是父系称谓体系较母系复杂、母系称谓体系又较姻系称谓复杂。母系亲属称谓大多是在父系称谓基础上前加“外”“表”等表示外亲关系的前缀构成。例如父亲的兄弟的子女要称“叔伯兄弟姊妹”,但母亲的兄弟姐妹的子女称“表兄弟姊妹”。
2.长幼有序的传统等级观。这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延伸影响。要想维护宗法秩序,必须有尊卑观念,而体现尊卑观念则必须明确辈分和长幼。亲属称谓词先辈分后长幼,配合宗法制度维护宗法秩序。祖辈、父辈、平辈、子辈、孙辈等都是辈分观念的直接体现,每个辈分中的称谓有相应的词根,例如祖辈有“公”“妈”,父辈有“奶”“舅”“妗”“姨”,平辈有“兄”“弟”“姊”“妹”,孙辈有“甥”等。这些词根各司其职,不允许越位,不可能出现用“公”称孙辈,用“甥”称父辈的情况。即使出现辈分长于自己,但年龄却小于自己的,也一定得按称谓称呼,不可直呼其名。辈分中又必须明确长幼次序,在称呼中强调排行,即平潭盛行的一套表示排行的“大”“细”“尾”前缀。
3.尊卑有礼的儒家文化。传统社会尊孔、尊儒,儒家文化作为主流文化长期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在亲属称谓中也有直观的体现。儒家文化讲求仁义,重视礼法,认为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益,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其中有三项都和家庭亲属关系有联系,先齐家再治国是孔子一直信奉推崇的,由此可见孔子对家庭伦理的重视程度。传统中国社会大家庭大都四代、五代同堂,且妻妾、子女众多,旁亲外亲人数也很可观,且亲邻间常走动联系,那么就急需建立一套能够体现权威、尊卑、长幼、亲疏的亲属称谓系统。这样一套亲属称谓系统除却能够保证家族内管理,对维护社会稳定等也有明显的作用。例如古代刑法的连坐制度,“夷三族”“株九族”等都是从亲属关系入手。平潭亲属称谓系统完善,从以上所描写的核心亲属称谓系统中即可窺见,每个亲属关系都有相对应的亲属称谓词表示,决不会出现混淆、不明所以的情况。
4.新时期的婚姻生育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提倡男女平等,废除一夫多妻制,实行一夫一妻制,20世纪70年代起国家还推行晚婚晚育和独生子女政策,这些都使得中国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大家族已难以存见,取而代之的是简单的三代亲属,且许多旁亲距离较远、联系渐少,与之相应的亲属称谓也就逐渐消失。未来或许仅存“外公”“外妈”“依娜”“外甥”“外女”等称谓。至于其余的称谓,史宝金认为:“它们将从今后家庭的人伦关系中逐步消失,或者只是作为一种非实际的血缘或姻缘亲属关系的社会化泛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社会交际语言中。” ⑥
“语言是文化的产生和关键,文化的发展也促使语言更加丰富和细密。” ⑦语言和文化的发展互相交织,互相促进。因此,本文通过关注平潭方言亲属称谓词,分析现有称谓系统背后的文化内涵,展现平潭历史文化风貌。
注释:
①宗福邦等主编:《古音汇纂》,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97页。
②朱夏蔚:《亲属称谓词“妗”的历时考察》,《汉字与历史文化》2021年第16期,第94页。
③林学阳:《福建福清方言亲属称谓特点》,《汉字文化》2021年第24期,第8页。
④郑献芹:《近十年来汉语称谓词语研究概况及分析》,《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1-2页。
⑤李树新、杨亭:《汉语亲属称谓泛化的文化心理考察》,《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年第3期,第89页。
⑥史宝金:《论汉语亲属称谓的特征及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语言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140页。
⑦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福建省平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平潭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1-2,687-691.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编.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第2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11.
[3]曹志耘.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42-56.
[4]胡士云.汉语亲属称谓研究[D].暨南大学,2002:1-2.
[5]冯爱珍.福清方言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186-188.
[6]李荣.福州方言词典[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467-469.
[7]陈章太,李行健.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词汇卷(上)[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2387.
[8]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9:244,309,3441-3442,3687.
[9]吴喜.福建平潭本地话词汇比较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2:2.
作者简介:
高佳丽,女,汉族,福建平潭人,上海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