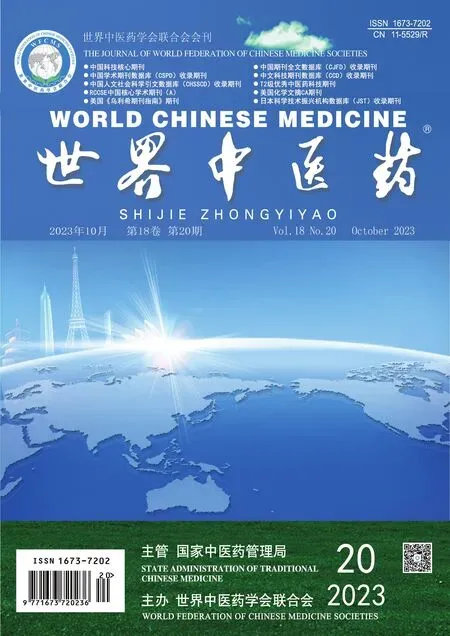基于“传承”理念的温病血分证“凉血散血”再认识
2024-01-27赵岩松侯雪雍谷晓红
赵岩松 窦 豆 侯雪雍 谷晓红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当前,中医学正面临着发展的机遇和挑战。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发布,提出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的守正传承是创新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解决临床问题”是医学发展的首要目标。温病学血分证是中医学特色经典理论。现以解读剖析血分证为例,探讨中医传承的意义。
1 衷中参西,辨识血分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和优势互补……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传承精华,保留住中医学宝贵的临床实用经验;守正创新,彰显出中医药经典理论的真正内涵,并使其在当代发挥更大的临床价值,中医药发展才能源远流长。中医学与现代医学有效结合,病机认识和治疗相互促进,才能彰显中国的医疗特色。
随着对疾病病理机制认识的深入,血管内皮炎性改变、微血栓相关疾病在临床占相当比例,以血管病变为基础的疾病涉及多种感染性疾病、免疫相关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及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如大动脉炎、川崎病、过敏性紫癜、白塞病等。以血管炎症反应为靶点的干预方法,也正在成为慢性炎症性疾病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新治疗手段[1]。中医学认为此类疾病的病机与热毒邪气及血瘀相关,与温病血分证热损脉道,灼伤阴血,热瘀胶结的病机相似。现以温病学血分证经典理论认识为例,尝试从“传承精华”的角度对血分证病机及“凉血散血”治法的认识进行深入挖掘,从“守正创新”探讨其当代临床应用价值,为拓展其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进而摸索传统中医药继承、发展和应用的模式。
2 “承”古籍精华,明理正源
古人基于临床真实世界的观察,结合治疗经验,为后世留下中医学知识宝库。对其经典理论的学习,既不可臆断解读,也不能浅尝辄止字面注解,对文字含义的准确把握,且结合现代科学的深入理解,是传承中医经典的要诀,也是能将其有效应用于临床施治的保障。无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人的认识,总是变化发展的,人体和疾病受自然、社会环境及物质水平发展变化的影响,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所以中医学的理论认知及用药规律也应随之进行相应调整。符合客观规律而彰显实用意义的变化才会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即中医经典首先要准确继承下来,再融入到当今临床中去进一步发展创新。
2.1 叶桂论治血分证的智慧
2.1.1 血分证的病机认识 卫气营血辨证是温病的辨证方法,其中血分证是热邪深入,引起耗血动血之变而产生的证候,典型临床表现为身热夜甚,躁扰不宁,甚或谵语神昏,斑疹显露、色紫黑,吐血、衄血、便血、尿血,舌质深绛,脉细数;或兼见抽搐,颈项强直,角弓反张,目睛上视,牙关紧闭,脉弦数等动风表现,是感染性和传染性疾病重症危重症的典型表现。血分证的病机为热毒入血,扰动心神,迫血妄行,热瘀胶结。病机的提炼是确立治法的基础,也是处方疗效的决定性因素[2],血分证病机中的“瘀”是认识难点。
《说文解字》记载:“瘀,积血也。瘀又有郁积;停滞之意。”《伤寒论》曰:“伤寒瘀热在里,身必发黄。”中医学中血瘀概念是指体内血流不畅,经脉受阻,血液瘀滞。温病血分证虽以急性出血为突出表现,但病机存在发热导致的脉内阴液耗伤和出血所致的阴血损伤,加之热毒邪气对脉道的损伤等多种因素,导致脉内血行不畅,从而形成血瘀状态。现代研究发现,血瘀的形成与感染密切相关,感染因子可通过几种病理生理机制影响动脉和静脉血管的稳态和功能,如血管舒解功能失调、血栓栓塞并发症、动脉粥样硬化的起始和进展、血管周围脂肪组织的改变、招募炎症细胞和分子等。既往研究提示,H3N2等流感病毒可感染人微血管内皮,导致细胞外基质暴露于循环血液中,促进血小板的聚集,还可通过整合素(纤维连接蛋白)结合诱导血小板-肺内皮细胞黏附,最终导致血栓的形成。研究已证实,疱疹病毒、肝炎病毒、结核分枝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白色念珠菌等感染因子等常见感染源与血管疾病的发病病理生理机制特别相关[3]。2019-nCoV通过ACE2损伤血管内皮细胞,由炎症导致的内皮功能受损,进而引起血管闭塞[4]。这也部分诠释了外感热病血分证中“瘀”的含义。借助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医学理论从“认识”跨越到“解释”的高度。
2.1.2 血分证中“瘀”治疗必要性 治瘀多用活血药,而活血药使用不当会加重出血,是不是在热证出血急性期可以暂时不治疗“瘀”呢?中医学认为瘀血属于病程中继发的病理因素,也为无形邪热提供依附载体,所以瘀血不祛,邪热不能除,故凉血需与治瘀并行。且凉血止血药和收涩止血药,易于凉遏恋邪,有止血留瘀之弊。中医素有“止血不留瘀”之说,治瘀防瘀尤为必要。
研究显示,血管病变、血管闭塞,可进而导致脏器功能丧失、脏器梗死的危重症。瘀血的状态与炎症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如血管内皮功能受损,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重症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并发症和心肌损伤的病理生理机制[4]。COVID-19临床特征包括炎症和血栓,肺部组织病理切片中证实了内皮破坏和血管血栓形成。肺中巨噬细胞的浸润,以及巨噬细胞、补体、血小板活化、血栓形成和促炎标志物(包括C反应蛋白、mx、IL-6、IL-1、IL-8、TNFα和核因子κB)的上调。炎症和血栓通路之间的关键相互作用导致了COVID-19诱导的血管疾病,因此血栓或为COVID-19的潜在治疗靶点[5]。COVID-19引起的严重炎症反应和内皮损伤以及潜在的并发症可能使患者易处于高凝状态,促进血栓事件的发生。COVID-19患者常发生血栓性事件,包括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等。实验室检查表现为血小板减少、D-二聚体升高和凝血酶原时间延长。病毒可直接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导致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抗磷脂综合征和血管炎,最终引起血管损伤,尤其是危重患者,多有血管组织样表现,甚至在四肢出现坏疽。COVID-19重症患者中合并高血压和糖尿病等血管性疾病的比例偏高,这类患者也多数存在内皮功能障碍,其血栓事件发生率明显升高。有报道新生儿重度感染时,患儿可出现血流动力学的异常变化,导致局部血栓的发生,降钙素原(PCT)、APTT、D-二聚体(D-Dimer,D-D)水平随病情加重而升高[6]。
因此,在热病血分证的治疗中,瘀血的治疗是必需的,甚至是治疗及防控危重症关键治法之一,也体现出叶桂所说“入血……直须凉血散血”的真知灼见。
2.2 如何识别血分证中“瘀”的存在 为用好“治瘀”法和药物,首先要诊断热证中“瘀”的程度。中医属“象医学”,中医诊断始终遵从“有诸于内必形之于外”的原则。舌色紫红或青紫,或舌体有瘀斑、瘀点,舌下静脉曲张,口唇紫暗,或目周暗青色;出血多暗红或夹有瘀块;若出现斑疹则有青紫色,或有明显体痛;另如口渴不欲饮、黑便、神志不清(如狂、谵妄)、脉数细中见涩象等,皆可提示血分证中血瘀的存在[7]。
感染性疾病中,如细菌、病毒、螺旋体、高热、持续的缺氧、酸中毒、抗原抗体复合物以及内毒素等,在一定的条件下,均可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内皮细胞损伤,启动内源性和外源性凝血系统。血小板、血液凝固伴随纤溶在细菌、寄生虫和病毒诱导的感染性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中都有的参与。严重的血管内皮损伤可表现为明显的充血,伴随血栓形成。先天免疫系统和止血系统机制的密切关联,决定了血小板、凝血和纤溶在细菌、寄生虫和病毒感染性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8]。内在的微观变化亦可作为判断血瘀存在的依据,如实验室检查指标如D-D为纤维蛋白、纤溶酶水解相互交联后生成的降解产物,常作为反映高凝状态、纤溶亢进的分子标志物,该指标可出现在多种疾病中,D-D增高提示与体内各种原因引起的血栓相关性疾病相关,同时也说明了纤溶活性的增强,临床上常见于弥慢性血管内凝血、深静脉血栓(DVT)、肺栓塞(PE)、急性心肌梗死、脑梗死、恶性肿瘤、卵巢癌、肺癌、败血症、肝病、妊高征、先兆子痫、烧伤、外科手术、创伤和脓毒血症等。如有报道重症肺炎患者D-D显著升高,提示D-D可作为重症肺炎预后判断指标[9-10]。细菌感染性疾病重度感染组较轻度感染组凝血指标D-D升高有统计学差异,血小板减少及凝血功能的紊乱可能升高危重症患者死亡风险[11]。D-D定量检测可用于反映药物的溶栓效果,辅助诊断新形成的血栓,亦可作为中医血瘀辨证的参考信息,是现代科技赋予中医的内视之眼。
3 传承医理真谛,创新应用
只有对中医学概念和理论进行精确而深入的解读,不草率曲解古籍本意,后学才能准确掌握并继承中医学,这既是传承中医药的前提,更是将中医精华应用于当今临床,并创新发展的基础。
3.1 “散血”的解读 “凉血散血”是温病血分证的治法,也是温病辨治特色之一,出自《温热论》原文第8条:“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凉血散血”多用于急性外感热病的治疗,现代临床多用于感染性、传染性疾病的危重证。根据病因清解热毒,同时针对出血和热病病程适当补充阴血都是易于理解的对症治法。而病机中“瘀”的认识,及叶桂提出的“散血”法,既是血分证认识和治疗的难点,也是中医治疗特色的体现。叶桂针对温病血分证病机中的“瘀”提出“散血”而非“活血”。“散血”二字也出现在《本草纲目》论三七“止血,散血,定痛。”“散”字本意由聚集而分离。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下焦篇犀角地黄汤治疗瘀血溢于肠间,时欲漱口不欲咽,大便黑而易者,条下“地黄去积聚而补阴,白芍去恶血,生新血”的内容明确了“散血”的含义,地黄以其性凉而补阴,可解散因脉内阴液受损,而导致血液黏稠所致的血行不畅,即此“散血”是通过补充阴液和活血法共同实现的,与内伤病推动血液运行的“活血”不同。
“散血”如何实施呢?《温热论》提出“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药味,表面看多为咸寒甘寒的养阴、凉血、活血止血之品,体现出养阴促进血行在血分证中治疗的重要性。而叶桂又有“营分受热则血液受劫”,可知营分证的治疗“如犀角、玄参、羚羊角等物”是防控血分阶段病情的关键。针对血分的解毒清热治法同样是必须的,而到了血分阶段养阴散血又尤其需要被重视,故采用代表方犀角地黄汤,该方由犀角、生地黄、牡丹皮、芍药组成。热证中活血药首选凉血活血之品,如赤芍、丹参、牡丹皮、紫草、茜草等,而养阴药对凉血和散血起到双向的辅助治疗作用,解毒也间接地控制及缓解血分证的血瘀状态。
3.2 血分证各治法间的关系
血分证的基本治法包括清热凉血解毒、养阴、活血化瘀等几方面,各治法之间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古人的逻辑思维可以被现代科学认知解释得更加清晰合理。
3.2.1 热毒是血栓形成的始动因素,有效地清热解毒是血分证治疗的前提和保障 无论是感染性疾病还是内伤杂病,对炎症的有效控制,能有效地保护血管内皮从而防治继发的高凝状态。炎症多表现为中医的热毒之象,清热解毒法可减轻血栓形成。如研究显示,解毒通络合剂(黄连、水蛭、连翘、野葛根、地龙、大黄、冰片)中剂量预防性给药,可降低IL-1β、TNF-α值,抑制炎症反应,使抗凝血酶-Ⅲ(AT-Ⅲ)活性增强,D-D含量降低,从而减轻角叉菜胶所致的大鼠尾部血栓形成[12]。热毒是血栓形成的始动因素,这种认识对临床的指导可体现在血分证中凉血解毒药需足量使用,更重要的是,对热毒较重的证候可在血分证呈现之前早用解毒散血药。清热解毒药合理足量使用可防控血瘀状态的形成,从而避免进入治疗棘手阶段。而实际上一些清热解毒药可兼有活血化瘀功效,如《本草纲目》载黄连有“去心窍恶血”的作用,《本经》黄芩:“主诸热黄疸,肠澼,泄利,逐水,下血闭。”《别录》载黄芩:“疗痰热,胃中热,小腹绞痛,消谷,利小肠,女子血闭,淋露下血,小儿腹痛。”《药品化义》中载连翘可使“一切血结气滞无不条达而通畅”的作用。毛冬青苦涩凉,清热解毒、活血通络,既可用于风热感冒,肺热喘咳,咽痛,乳蛾,痢疾,牙龈肿痛,又可治疗胸痹心痛,中风偏瘫,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中心性视网膜炎,丹毒,痈疽等;虎杖苦微寒,利湿退黄清热解毒、散瘀止痛、止咳化痰,大血藤苦平,清热解毒活血、祛风止痛,用于既可肠痈腹痛,热毒疮疡,又可治疗血滞经闭痛经、跌扑肿痛、风湿痹痛;败酱草苦辛微寒,清热解毒、消痈排脓、活血祛瘀止痛,肠痈肺痈,痈肿疮毒,产后瘀阻腹痛;另如半枝莲、冬凌草、地锦草等皆兼具清热解毒和活血化瘀之效。
3.2.2 阴亏是热证血瘀的伴行状态,养阴法是血分证血瘀的治疗特色 营血分证是温病病程中的重症,邪热炽盛而营阴、阴血受损为病机特点,养阴法是其重要治法,代表方清营汤中使用生地黄、麦冬、玄参;犀角地黄汤中用大量的生地黄。温病中的瘀血状态可以分为瘀血形成和瘀血倾向2类[7]。后者以养阴为主要防治法,养阴药同样可发挥活血化瘀作用。
地黄既可凉血,又养阴,又可通过养阴充养脉道而改善血液的瘀滞状态,是治疗血分证的主药。《本经》谓生地黄有“逐血痹”的作用,《本草纲目》载玄参具有“通小便血滞”的作用。《本经》明确指出麦冬有“润泽心肺以通脉道”的作用。血管内皮细胞排列紊乱、脱落,使内皮下层直接暴露于血液,可引起血管反复血栓、管腔狭窄、炎性病变等,引发局部组织并发症。生地黄、丹参均能稳定内皮下基层的完整形态,保护血管内皮超微结构[13]。地黄可抑制心脏Ca2+、Mg2+-ATP酶活力,保护心脏组织避免ATP耗竭和缺血损伤,对脑组织也有同样的作用。地黄中可能含有钙拮抗活性物质[14],其中地黄多糖(RPS)可能抑制大鼠血管细胞凋亡,从而阻止血管细胞成骨样转化及钙化有关[15]。滋阴地黄丸(熟地黄、生地黄、柴胡、黄芩、当归、天冬、地骨皮、五味子、黄连、人参、枳壳、甘草)可显著抑制兔脉络膜组织中组织因子、组织凝血活酶(Tissue Factor,T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的表达。TF被促炎症介质、内毒素、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ox-LDL)、黏附分子等诱导在平滑肌细胞、单核/巨噬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的高度表达,通过与凝血因子作用启动内源性和外源性凝血过程,因此TF的过度表达及活性异常可导致血栓的形成。TF途径是生理性凝血过程与病理条件下血栓形成的启动环节,说明滋阴地黄丸也可防治血栓形成,从而抑制脉络膜新生血管性疾病(CNV)[16]。有研究显示,阿胶可以抑制血液黏度的升高、快速稳定血压等,抑制血液的肝素化,并激活凝血因子对一些出血症状有止血趋势[17]。麦冬有抗心律失常、改善心肌缺血、增强心肌收缩力和减慢心率的作用。
3.2.3 血瘀作为热盛阴伤的继发病理因素,化瘀有助于清解热毒,改善炎症状态 既往研究已证明中医的血瘀证与血液循环和微循环障碍、血液高黏滞状态、血小板活化和黏附聚集、血栓形成、组织和细胞代谢异常、免疫功能障碍等多种病理生理改变有关,可见于心脑血管病、感染、炎症、组织异常增殖、免疫功能和代谢异常等多种疾病[18]。有效地化瘀也有助于清解热毒,改善炎症状态。如脓毒症状态下白细胞黏附因子的异常高表达及其与血管内皮的黏附作用可介导多种脏器功能障碍,活血凉血中药凉血活血方浸膏(红藤、赤芍、牡丹皮、延胡索)可通过抑制血管内皮系列黏附分子高表达而发挥治疗作用[19]。有些凉血活血药也可有解毒之功,如紫草,味甘、咸,性寒,具有清热凉血、活血解毒、透疹消斑的功效,用于血热毒盛、斑疹紫黑、麻疹不透、疮疡、湿疹、水火烫伤;益母草,味苦、辛,性微寒,具有活血调经、利尿消肿、清热解毒的功效,用于月经不调、痛经经闭、恶露不尽,水肿尿少、小便不利,跌打损伤,疮痈肿毒;西红花,味甘,性微寒,具有活血化瘀、凉血解毒、解郁安神的功效,经闭癥瘕,产后瘀阻,温毒发斑,忧郁痞闷,惊悸发狂;马鞭草,味苦,性凉,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散瘀、利水消肿的功效,治外感发热、湿热黄疸、水肿、痢疾、疟疾、白喉、喉痹、淋病、经闭、癥瘕、痈肿疮毒、牙疳。血分证应选用凉血活血药,如丹参、牡丹皮、赤芍、桃仁、红花、紫草之类,另如茜草、三七、藕节、花蕊石、大黄等,止血不留瘀,活血而不动血。
3.3 “凉血散血”的临床应用 温病血分证“凉血散血”治疗特色体现为凉血解毒、养阴、活血化瘀治法的随证联合应用。动物实验也表明,清热解毒、益气生津等方药本身就具有一定降低血液凝固度、降低血小板聚集性、扩张血管、抑制体外血栓形成、减轻血管内弥散性微血栓形成等多种类似抗“血瘀”的作用。生地黄、连翘等在体外抗血小板聚集作用实验中,显示对血小板聚集抑制率最高,且高于传统的活血化瘀药如赤芍、牡丹皮、丹参、郁金等。生地黄、玄参、麦冬组方的增液汤对血栓形成的抑制作用最强,其次才是活血化瘀、理气及清热解毒制品。说明清热解毒(金银花、连翘、黄连、黄芩)、滋养阴液(生地黄、玄参、麦冬)、活血化瘀(赤芍、牡丹皮、桃仁)等多种治法都可抑制体外血栓的形成[20]。又如研究显示,具有养肾阴、解热毒及活血瘀三方面功效的养阴化瘀方(女贞子、墨旱莲、白花蛇舌草、丹参、银花藤、知母、蚕沙、益母草、僵蚕),用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治疗,有助于调节免疫损伤相关炎症介质、β-抑制蛋白质-1及血栓调节蛋白表达,显著控制临床症状,降低疾病活动度,改善血液流变学指标[21]。
“凉血散血”治法不但在外感热病的治疗中发挥作用,也被拓展应用于内伤杂病中。有些与感染相关的出疹性疾病表现为明显的营血分证临床特征。以川崎病(又名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为例,因全身血管发炎导致的以发热、皮肤出疹、黏膜充血、淋巴结肿大为主要症状,可归属中医温病范畴。其治疗的关键是防止冠状动脉血栓形成,防止出现心脏并发症。川崎病亚急性期患儿有血小板增多的特点,血液黏稠度增高,这是导致冠状动脉瘤、心肌梗死和冠状动脉血栓等的主要原因。恢复期治疗以活血化瘀方药为主[22]。又如,社区获得性肺炎归属“风温肺热病”范畴,临床中主要以痰热壅肺证型最为常见,气分证中适当加入由凉血活血药组成的自拟清热解毒扶正汤(太子参、丹参、鱼腥草、芙蓉叶、翼首草、麦冬、柴胡、甘草),能有效改善血浆D-D、IL-6及PCT水平,加速炎症状态的好转,其控制感染的作用机制可能与降低患者的高凝状态,抑制炎症反应有关[23]。
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色,决定了对证候病机的准确把握是取得疗效的关键。因此,具有相似病机证候的内伤杂病同样可以应用外感热病血分证的治疗思路。“凉血散血”已被拓展应用到冠心病、化疗后血小板减少、肾性血尿、亚急性甲状腺炎等疾病的治疗[24-27]。炎症在动脉粥样硬化等血管性疾病的不同阶段中可能具有独特作用[28]。生地黄、牡丹皮、赤芍、水牛角、阿胶、当归、川芎等药,通过抗炎、抗血小板聚集、抗动脉粥样硬化,从而改善心功能在心血管系统疾病中发挥较好的治疗作用。如“瘀热”理论指导下,通过辨瘀、热的轻重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辨治,热重于瘀者,多用玄参、牡丹皮、平地木等凉血不留瘀;瘀热并重者,丹参、酒地龙,黄连、升麻、鸡血藤、赤芍、大黄等配合使用,体现出典型的温病血分证清热化瘀、凉血养阴的治法特色[29]。
4 总结
冯友兰先生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是其哲学史研究和哲学创新的基本方法,同样适用于中医经典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对中医学“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准确且深入解读古人对病证的认识和治疗经验,讲好经典的本来样子,是做好传承的根本,也是使其在当代临床中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的前提。叶桂揭示出血性热证中的瘀,并提出“凉血散血”以化瘀的治法,是中医经典智慧的体现。而除了将“凉血散血”法在外感热病治疗中进行恰当、灵活应用,同时结合现代科学的深入理解,拓展其临床应用范围,如急重症气分证中提前使用化瘀散血的思路,并广泛应用于疑难杂病的异病同治,发挥经典的临床应用价值,也是传承经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