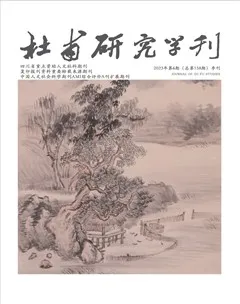王维晚年陷伪行实考
2024-01-26黄鸿秋
〔摘 要〕 安史乱中的陷伪经历是理解王维晚年心灵世界和文学写作的一把钥匙,对于考察“后盛唐时代”的文学走向亦具有特殊意义。通过重新发覆《太平御览》所引“唐书”中的相关材料可知,王维乱中的“伪疾将遁”实是“佯中风”以制造瘖疾假象,同时辅以“服药取痢”的程序。王维在长安伪疾失败被捕后很快被缚送至洛阳,度过了一段遭遇非人囚禁以致“秽溺不离”但仍力图保全气节的晦暗岁月,终于在《韦斌神道碑铭并序》中所述与韦斌推诚交谈以前迫受了伪署。学者否定《太平御览》所引“唐书”中王维“佯中风失音”的记载以及认为王维不曾受伪署的新说都是缺乏说服力的。
〔关键词〕 王维 “佯中风” 服药取痢 秽溺不离 伪署
天宝十四载(755)十二月和十五载(756)六月,东、西两京相继陷落,玄宗携少量亲信、宗室仓皇出逃,大批唐廷臣僚因脱逃、扈从不及,为叛军所俘。“群贼陷两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黄门宫嫔乐工骑士,每获数百人,以兵仗严卫,送于洛阳。至有逃于山谷者,而卒能罗捕追胁,授以冠带。”其中包括了李华、储光羲、郑虔、卢象、赵骅、邵说等大批重要的开天文士,尤以“当代诗匠”王维的声名最著。陷伪经历是理解王维晚年心灵世界和文学写作的一把钥匙,对于考察“后盛唐时代”的文学走向亦具有特殊意义,历来为学界所瞩目。但目前学界对于王维陷伪期间的一些关键史实存在不少歧解和误读,故有必要通过对相关史料和不同说法的重新检覆、辨析予以澄清,以尽可能还原出王维晚年生涯中的一段特殊经历。
一、“佯中风失音”再辨
记录王维安史乱中陷伪经历最为直接的材料来自于他本人约乾元元年(758)为已故同僚韦斌所作《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铭并序》一文:
上京既骇,法驾大迁,天地不仁,谷洛方斗,凿齿入国,磨牙食人。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实赖天幸,上帝不降罪疾,逆贼恫瘝在身,无暇戮人,自忧为厉。公哀予微节,私予以诚,推食饭我,致馆休我。毕今日欢,泣数行下,示予佩玦,斫手长吁,座客更衣,附耳而语。指其心曰:“积愤攻中,流痛成疾,恨不见戮专车之骨,枭枕鼓之头,焚骸四衢,然脐三日。见子而死,知予此心。”之明日而卒。某年月日,绝于洛阳某之私第。
约作于上元二年(761)春的《责躬荐弟表》中的“托病被囚”句亦述及此事。关于所伪之疾,《旧唐书》本传载为“服药取痢,伪称瘖病”,《新唐书》本传记为“以药下利(痢),阳瘖”,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所成《太平御览》卷七四三《疾病部·阳病》则谓:
唐书曰:“安禄山陷西京,王维佯中风失音,贼犹强授伪官,后蒙原罪。”
景德至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所成《册府元龟》卷九四〇《总录部·患难》目下亦云:“安禄山陷两京,维在西京,作中风失瘖久之。贼重其名,追赴洛阳,伪授给事中。”周祖譔主编《〈旧唐书·文苑传〉笺证》认为:“(《御览》)记王维乃‘佯中风失音,与碑文所载及《旧传》不符,《御览》当误。”按,唐人吴兢、韦述曾递修而成唐代国史《唐书》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而史官令孤峘等复于纪、志、传后随篇增缉而不加卷帙”。作为一代文宗、两朝重臣的王维死后必入国史,故疑《御览》所引“唐书”中关于王维的一段文字,当即出于当朝史官令孤峘等当时之手笔,而所谓“唐书”,当即为于休烈、令孤峘等史官所续补而成之国史《唐书》。当然,《御览》所引“唐书”条目并不限于此,关于其性质,学者除了认为是某版国史《唐书》之外,或认为是《旧唐书》之逸文,或认为是刘昫《旧唐书》之前的某个旧版本,又或认为是包含了《旧唐书》《通典》《唐会要》、国史、实录乃至笔记小说等多种史籍的通称。所述来源虽异,要之成书上均早于今本《旧唐书》则同。是故,无论《御览》所引“唐书”性质为何,其关于王维“佯中风失音”的一段记载,从史源学的角度看,应比后来才出现的五代史臣编修的今本《旧唐书》更为接近于事实本身。而《册府元龟》卷九四〇中所保留的“作中风失瘖(音)”的关键信息,当即来自于这一渊源更早的“唐书”系統;欧阳修《新唐书》的叙述,则显是据今本《旧唐书》改写简化而成。
又,《〈旧唐书·文苑传〉笺证》以《御览》与诸书记载不同为“不符”“当误”,恐亦不确。按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云:“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府,即不识人;邪入于藏,舌即难言,口吐涎。”旧传晋张湛、道林等撰《太清道林摄生论》亦云:“古来忽有得偏风者,四肢不遂,或角弓反张,或失音不能语。”可见重度中风患者会出现“半身不遂”“口吐涎”“失音不能语”等症状。史籍中多有相关病例之记载,如西汉成帝时班伯“道病中风……数年未能起”,北魏张彝“因得偏风,手脚不便”,北齐宋绘“晚又遇风疾,言论迟缓”,南朝陈司马延义“以中风冷,遂致挛废,数年方愈”,稍后于王维的德宗时期河东节度使李说、华州刺史卢征亦“皆中风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王维所谓“伪疾”“伪称瘖病”“阳瘖”,当系伪装成重度中风以致不能言语行动的症状,以图躲过叛军搜捕。重度中风不仅意味着言语功能的障碍或丧失,还伴随着由“半身不遂”导致的大小便失禁不能自理。如南宋严用和《续济生方·诸风门》云:“但眼闭口干,声如鼾睡,遗尿者,皆所不治。”明代徐凤《中风论》:“且夫中风者,有五不治也。开口、闭眼、撒屎、遗尿、喉中雷鸣,皆恶候也。”清代魏之琇《续名医类案》亦载一病例:“景氏妇年近五旬,中风已五六日,汗出不止,目直口噤,遗尿无度,咸以为坏症。”两《唐书》谓王维“服药取痢”“以药下利(痢)”,按《玉篇》:“痢,泄疾也。”曹操《魏武令》:“凡山水甚强寒,饮之皆令人痢。”旧题梁陶弘景集《养性延命录》亦云:“贪美食令人泄痢。”皆指人因饮食不当或其他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排泄(次数频繁、粪便溏稀等)现象。王维显是为将中风的症状伪装到极致,故除噤口不言、卧榻不起外,更服用特定药物以造成大小便失禁不能自理的假象,只是未能成功,“以猜见囚”罢了。易言之,王维所伪之“疾”当是风疾,意在“阳瘖”,而“服药取痢”“以药下利”是为了进一步迷惑叛军、加强风疾的假象而增加的辅助。《御览》所引“唐书”与两《唐书》记载表面看似“不符”,实则只是分别捕捉到王维佯风疾系列程序中的不同方面而已,并无内在矛盾。至于王维碑文中仅自称“伪疾”,并未说明所伪何疾,就更谈不上“不符”。
与此不同,学界对于新、旧《唐书》中王维“服药取痢,伪称瘖病”“以药下利,阳瘖”的记述则有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如杨军《王维受伪职史实甄别》一文认为:“所谓‘服药取痢,指服用特效药物以致身体现出某种严重病态(‘痢通‘疠,恶疾),王维的办法是用药把嗓子搞哑,企图以此种自我戕害的办法摆脱叛军的搜捕和安禄山的利用。”毕宝魁《千古沉冤 应予昭雪——王维安史之乱“受伪职”考评》一文亦以为:“‘服药取痢,伪称瘖病,即用一种特效药而使身体出现某种严重病状,把嗓子搞哑,说不出话来。”这种解读的关键是在“服药”与“取痢”“瘖疾”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即通过服药达到“取痢”“瘖疾”的效果以迷惑叛军,同时以通假之法将“痢”与“瘖疾”等同起来。但“痢”固可因音同形近通假于“疠”,却没有直接使用前述传统文献中更为常见的“泄疾”之义,转成迂回之解;更为关键的是与欧阳修《新唐书》所谓“下利(痢)”的叙述产生龃龉。若说《旧唐书》之“取痢”尚可在通假的语境中解为“取疠(疾)”,却无论如何没有“下疠(疾)”的说法。相反,“下痢”倒是传统社会和医学中的常见语汇,如三国刘备《遗诏》:“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菰首蜜,食下痢。”五代冯贽《云仙散录》:“饮罢但苦头痛下痢。”欧阳修《新唐书》的叙述是自《旧唐书》改写而来,对于后者所谓“取痢”一词的理解,是符合传统社会和医学中的常见义涵的。易言之,王维的伪疾行动中,“痢”与“瘖”是两种症状,“下痢”是“服药”的结果。那么“瘖疾”(即所谓“把嗓子搞哑”)是否也是“服药”的结果?这在情理上也是说不通的。按《后汉书·封观传》载:“封观者,有志节,当举孝廉,以兄名位未显,耻先受之,遂称风疾,喑不能言。火起观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后数年,兄得举,观乃称损而仕郡焉。”足见所谓“瘖疾”,完全可以人为控制,而不必通过实际的自戕把“嗓子搞哑”。且纵然当时的医学条件允许,王维既非医家,陷贼的仓促之中恐亦难以保证毒哑之后再将自己完全恢复到原状。是故,“服药”与“瘖疾”之间并无必然因果联系,王维仅是利用前人屡试不爽的称疾伎俩制造中风后的“瘖疾”假象,因大小便自遗亦是中风之象,故为更保险起见,多加了一道“服药取痢”的程序而已。杨、毕二文是在没有注意到《御览》所引“唐书”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对《旧唐书》记载强行作出解释的结果。这又反过来说明《御览》所引“唐书”对于理解新、旧《唐书》叙述的重要性。由于今本五代史臣的《旧唐书》将更为原始的《御览》所引“唐书”中“佯中风失音”之“中风”的关键信息删汰,《新唐书》又一仍其删汰,遂致今人在信息缺失下的误读。
叛军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八日破潼关,玄宗及少量扈从十三日黎明自长安延秋门出逃,“禄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关,凡十日,乃遣孙孝哲将兵入长安”。则孙孝哲入长安在六月二十三日以后,此后,“禄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宫女等,每获数百人,辄以兵卫送洛阳”。王维“伪疾将遁”殆即发生于叛军大肆搜捕的背景之下。当时搜捕力度之大,“至有逃于山谷者,而卒能罗捕追胁”,王维大约是来不及脱逃者。叛军搜捕意在“以兵卫送洛阳”,两京相距八百五十里,这就要求被缚送者须是手足康健、能行远途之人。王维应是看中这一点,才故意伪装成“半身不遂”、“失音不能语”的中风病人,并加以“服药取痢”的程序,以期瞒过敌人。《旧唐书》本传的叙述将王维“取痢伪瘖”的行为置于其“扈从不及,为贼所得”之后,《新唐书》本传因之。但既为贼所得,恐已无操作“服药取痢”的自由和空间,尤为重要的是王维作为手足康健之人“为贼所得”,却在为贼所得之后突然“半身不遂”、“失音不能语”,这样拙劣和明显的表演恐怕连普通人都难以骗过,何况狡猾的叛军。检《御览》所引“唐书”,即无所谓“为贼所得”之语。显然后者的记述更合于情理。
二、關于“秽溺不离者”数句的解读
安禄山将长安被俘唐臣“以兵卫送洛阳”,意在招降安抚,署以伪职,以在人心和声势上抗衡肃宗的行在。陈希烈、张均、张垍等原唐廷高级臣僚即是在此时出任伪职。《通鉴》载禄山至德元载八月“宴其群臣于凝碧池”,更早的《安禄山事迹》一书则载为“宴伪官数十人”,可见八月时已有大批被俘唐臣接受了伪署。王维及大批长安俘臣被缚送至洛阳的时间当在紧随长安陷落和大肆搜捕后的七月上中旬,而安禄山针对长安俘臣的大规模迫授伪职即发生于从七月上中旬至八月行凝碧池宴会前后约一个月的时间内。禄山行凝碧池宴会时王维正被囚于洛阳菩提寺(一说为“普施寺”),并因听闻“逆贼”宴集行乐于旧朝故池并残忍杀害乐工雷海青,伤心赋成后来“闻于行在”的《凝碧诗》,则彼时王维尚未接受伪署。由于西京沦陷之际“服药取痢,伪称瘖病”的前科,王维应是被缚送至洛阳后不久即被囚于菩提寺。面对敌人的伪署诱降,王维仍坚持着西京搜捕以来的不合作态度,故直至八月凝碧池宴会时仍缧绁在身。
碑文于叙述王维“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后又云:“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对此四句学界有不同理解。陈铁民认为:“‘勺饮四句写己被囚后情状。秽,指粪;溺,同‘尿。盖‘服药取痢,故‘秽溺不离。”则所写为王维长安被执期间而未至洛阳前之事,大约是受了两《唐书》将王维“服药取痢”置于“为贼所得”之后、“迎置洛阳”之前叙述的影响,并进一步将碑文中“秽溺不离”解释为王维自己“服药取痢”的结果。这种解读是基于王维伪疾失败被捕后仍有一段被短暂关押于长安的经历。由于叛军的搜捕和集中缚送需历一定时日,故王维于伪疾失败被捕后、缚送洛阳前,被短暂囚禁于长安是有可能的。但王维本年八月已被系于洛阳菩提寺并赋成《凝碧诗》,而两京途程所需时日,“通常盖十日,日行约三驿;缓或十六日,日行约两驿”,再刨除伪疾、搜捕、集中俘臣队伍所需时间,则王维被囚于长安的最长时限恐难超过半月。也正因此,陈氏不得不将与这一时限迥不相侔的“秽溺不离者十月”中的“十月”解为:“极言时间之长;或‘月为‘日之形误字。”“十日”倒是颇为符合王维长安期间短暂被囚的猜测,但无版本文献上的依据;解“十月”为夸饰性修辞是有道理的(详后),但又未免过于夸大以至迹近虚伪。另从碑文本身的叙述看,“勺饮不入者一旬”四句显是“伪疾将遁”不成以致“以猜见囚”后的结果(毕宝魁将“勺饮不入者一旬”解为王维“绝食十天”,亦不确),故“秽溺不离”亦不当解为王维自己“服药取痢”所致,而是应与其他三句一样,均指王维被囚之后的遭遇(因长期被拘于一室以至秽溺不离身)。杨军、毕宝魁二文则将“十月”坐实理解,进而将“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划归到王维洛阳被囚期间。将“十月”坐实理解是不妥的(详后),但划归到洛阳被囚期间确乎较为合理。王维被囚洛阳的时限虽同样不可确定,但他对安禄山的伪署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抗争,故而没有进入敌人八月凝碧池宴会的名单,相反赋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凝碧诗》,这些都发生于洛阳,所历时日应要长于长安期间的短暂囚禁。以王维七月被缚至洛阳,八月赋《凝碧诗》向裴迪昭示气节、九月即受伪署计,前后也已经三月,则夸张为“十月”就合理得多;以王维受伪署到安禄山被弑的至德二载元月计,则前后历七月,就更在适度夸张的范围之内了。且“白刃临者四至”亦当指幽囚期间叛军迫以伪职之频繁,置于长安临时被拘期间就显得没有着落。当然,以上四句不管指的是王维被囚长安还是洛阳期间的景况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四句揭示出王维伪疾失败被囚后曾有过一段遭遇非人虐待而仍力图保全气节的苦涩而晦暗的岁月。这些新、旧《唐书》所没有的细节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王维陷贼期间的生存遭际和心灵状态提供了有益帮助。
三、王维曾迫受伪署
最后探讨一下王维迫受伪署的问题。《御览》所引“唐书”、两《唐书》、辛文房《唐才子传》均谓王维曾受伪署,《册府元龟》卷九四〇《总录部·患难》目下、《新唐书》本传进一步载王维所受伪职为“给事中”。此事古今原无疑义,惟近来毕宝魁撰《千古沉冤 应予昭雪——王维安史之乱“受伪职”考评》一文提出新解,以为王维被俘后,“曾住过长达十月之久的监狱,并没有接受伪职”,“如果王维接受伪署(即使是被迫的),又何必要住十个月的监狱呢?”对此,王辉斌《王维“接受伪署”考评》一文曾重新梳理相关史料予以驳正。但考虑到王文未能揭示出毕文立论的关节所在,而毕文的说法也仍流布世间有可能造成影响,故此问题仍有再究的必要。
详按毕文之说,其立论的关键在于将前引王维碑文中“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的描写划归到王维被囚洛阳期间,并将“十月”坐实理解的解读。在毕文看来,王维是经过叛军“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的俘获之后,被缚送至洛阳囚禁并受到“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的困辱。王维被缚送至洛阳囚禁是在至德元载七月,十月后已为至德二载五月,但安禄山早在至德二载正月已为其子安庆绪伙同严庄所弑,故自无受禄山伪署之理。毕文由此又进一步推出王维碑文中所载韦斌“见子而死,知予此心”的托付名节之举在王维“秽溺不离者十月”之后的至德二载五六月间,亦即安禄山死后。实际上,同样将“十月”坐实理解的杨军《王维受伪职史实甄别》一文就已如是理解,不同在于杨氏认为王维被困十月获释之后,接受了安庆绪的伪署,时在至德二载四月之后;毕氏则认为王维获释之后仍然没有接受伪署,而是以自由人身份存在,“脱离囚徒生活仅四五个月,唐军便收复两京,王维便回到了朝廷的怀抱”。但杨、毕二人的理解恐怕都是不确的。按碑文载韦斌向王维托付心事时云“恨不见戮专车之骨,枭枕鼓之头,焚骸四衢,然脐三日。见子而死,知予此心”,连用大禹杀不臣的防风氏以致骨节专车、(意欲斩杀)以鼓作枕的汉代奇士巨毋霸、司马懿设计诱杀并焚首反魏之臣孟达、吕布斩杀图谋篡汉的董卓四个典故,表达对毁其名节的伪朝之主的痛恨,并以“恨不见”逆贼被杀为憾。临汝太守韦斌陷贼于天宝十四载十二月,“伪授黄门侍郎”于他者为安禄山,且典故中汉代巨毋霸“长丈,大十围”、董卓“素充肥”的形象亦与安禄山为众周知的“肥壮,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的体态特征相吻合,而不闻后继之伪主安庆绪有此特点,故此处所指斥的对象只能是安禄山。易言之,韦斌对王维的推诚交心必发生于安禄山死前,而韦斌“之明日而卒”,亦先亡于安禄山。再从韦斌与王维交谈所谓“毕今日欢”“座客更衣”的描写看,亦绝不类探视囚人的场景,而像是一次小型的宴集。对比王维《凝碧诗》长题中所谓“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的探囚描写,可明显感受到二者的差异。所谓“公哀予微节,私予以诚,推食饭我,致馆休我”,殆指韦斌深怜王维是与他同受伪署而心意相通、心系唐室的忠节之臣,故推心置腹之外,更尽可能地给予生活上推食致馆的照拂。此时王维既已不在囚中,则是已受伪署;而“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的遭遇自当发生于此次交谈亦即至德二载正月安禄山死之前。如将“十月”坐实理解,就不免与韦斌所诉内容及碑文所见二人交谈之场景相抵牾。是故,将“十月”作为一种夸饰性修辞理解是更为合理的。此外,从王维两京克复后频繁的“罪臣”心理及忏悔、自赎举动看,亦可反推其曾受伪署。频繁的忏悔自赎正是其迫受伪职名节有亏后的一种自然心理反应,而碑文中“一旬”“十月”夸饰性话语的出现,正是其内心深处急于寻求自我辩护、自我慰藉的结果。
此外,还有一小问题值得稍加辨明。杨军认为王维被囚十月之后获释,并接受了安庆绪的伪署。但王维缘何得释?且为何关押十月之久不接受安禄山的伪署,反而在获释之后接受了安庆绪的伪署?这两个重要疑问都没有给出解释。毕宝魁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王维获释当与韦斌托付名节之举有关,“当(韦斌)下决心(自裁)时,一定要把自己的整个心事及后事托付一位知己,以便在乱平后替自己向朝廷表白心迹,洗雪‘叛臣之恶名。”邵明珍《王维安史之乱“受伪职”真相辨析》一文不同意毕氏所谓王维始终不曾受伪署之说,但接受了毕氏关于王维脱狱与韦斌有关的说法,而将碑文中所谓“公哀予微节,私予以诚,推食饭我,致馆休我”,理解成是韦斌帮王维“脱离牢狱,请至家中,托以后事后,才假意答应出任伪职,以便日后为韦斌向朝廷表明心志”。但这种理解恐怕也是不妥的。首先,所谓“公哀予微节”云云,当指王维已受伪署获释之后,因同病相怜,故为韦斌推食致馆以照拂,并推心置腹地托以后事,并非是帮王维脱离牢狱之灾的描写;其次,韦斌既有能力助王维脱狱,“请至家中,托以后事”,却又没有能力使之免受“伪署”,还需王维“假意答应出任伪职”,才能在“日后为韦斌向朝廷表明心志”,实在自相矛盾。盖王维若受伪署,自能出狱,何必韦斌大费周章,多此一举?再者,托付名节与王维是否出狱、受伪署并无必然关系。裴迪就曾至菩提寺探囚相谈并得到王维口诵的《凝碧诗》,韦斌自亦可于探囚间达成其事;而王维仅仅为了“以便日后为韦斌向朝廷表明心志”,就放弃牢狱之中长达十个月之久的坚持,接受了伪署,未免也太不知轻重,前功尽弃了。
那么王維大概在什么时间点接受了伪署?目前无确切的材料可指明这一点,可以肯定的时间段是在至德元载八月菩提寺赋《凝碧诗》之后到碑文所述与韦斌推诚交谈以前(同时也是在安禄山死之前)。禄山集中胁迫长安被俘唐臣受伪署在长安陷落后不久的七八月份,故八月行凝碧池宴会时已有在座“伪官数十人”。也许正是由于伪朝勺饮不入、秽溺不离、白刃四至、赤棒困守的反复折磨,终于迫使王维屈服,实际也是当时大多数被俘唐臣的选择。但最终的屈服并不能否定王维前期为护全名节所做出的努力,这与那些并无抗争乃至抱着政治投机心理主动趋附于安禄山者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责任编辑 贾 兵
On Wang Weis Late-Life Experience and its
Historical Reality
Huang Hongqiu
Abstract:Wang Weis late-year experience during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is a key to understanding his spiritual world and literary creation and holds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studying the literary development of the post High-Tang period. By revisiting the relevant materials in the“Tang Shu”quoted in Taipingyulan,this article reveals that Wang Weis“pretending paralysis to escape”during the chaos was actually a deception of pretending to be struck with apoplexy to create an illusion of speechlessness,along with taking medicine to induce diarrhea. After Wang Weis disguise failed in Changan,he was quickly arrested and sent to Luoyang,where he underwent a dark period of inhumane incarceration,leading to a state of“depravity and dissoluteness”but still struggling to maintain his integrity. Finally,according to the description in the“Shinto inscriptions for Wei Bin”,in a sincere conversation with Wei Bin,Wang Wei confessed that he was forced to accept a false appointment. Some scholars have question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record of Wang Wei“pretending to be paralyzed and losing his voice”in the“Tang Shu”quoted in Taipingyulan,as well as the claim that Wang Wei had received a false appointment. However,these new interpretations lack persuasive power.
Key words:Wang Wei;pretending apoplexy;taking medicine to induce diarrhea;depravity and dissoluteness;appointment by An Lushan
作者简介:黄鸿秋,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所讲师,20023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唐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48)、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安史之乱时期的政治文化重构与文学新变研究(23BZW052)”阶段性成果。 〔唐〕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1页。
〔唐〕苑咸:《酬王维并序》,〔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二九,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17页。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卷一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51-1052页。
〔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〇《王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52页。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〇二《王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65页。
〔宋〕李昉、徐铉等编:《太平御览》卷七四三《疾病部六》“阳病”,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册,第3300页下栏。
〔宋〕王钦若等编,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九四〇,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93页。
周祖譔主编:《〈旧唐书·文苑传〉笺证》,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516页。
〔宋〕王尧臣等编:《崇文總目》卷二,《丛书集成初编》第21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6-47页。
详参罗亮:《〈太平御览〉中的“唐书”考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03-112页。
所谓今本《旧唐书》,其文字的形成亦早于欧阳修编撰《新唐书》之时,故可能为欧阳修所袭用。吴玉贵《唐书辑校·前言》即认为,今本刘昫《旧唐书》乃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为官方做了大量修订后的《旧唐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页)。
〔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四部备要》,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65册,第11页。
旧题〔南朝梁〕陶弘景撰,王家葵校注:《养性延命录校注》附录一,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33页。
〔汉〕班固:《汉书》卷一〇〇上《班况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99页。
〔北齐〕魏收:《魏书》卷六四《张彝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29页。
〔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二〇《宋显传》附,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71页。
〔唐〕姚思廉:《陈书》卷三二《司马延义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30页。
《旧唐书》卷一四〇《张建封传》,第3831页。
〔宋〕严用和撰,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文献组、湖州中医院整理:《重订严氏济生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明〕杨继洲:《针灸大成》卷八引,《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96册,第258页上栏。
〔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84册,第55页下栏。
杨军:《王维受伪职史实甄别》,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王维研究会编:《王维研究》第1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按:此文先发表于《铁道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第16-20页。再发表于《王维研究》时,文字、细节上略有增订,代表了作者最终的观点。故本文引用、评述,以后发表者为准。
毕宝魁:《千古沉冤 应予昭雪——王维安史之乱“受伪职”考评》,傅璇琮主编:《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按:此文先以《王维安史之乱“受伪职”考评》为题,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65-68页。再发表于《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时,细节上略有增删,代表了作者最终的观点。故本文引用、评述,以后发表者为准。
〔晋〕陈寿:《三国志》卷三二《蜀书》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91页。
〔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一一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40册,第570页上栏。
〔五代〕冯贽编:《云仙散录》第338条“鸡头肉”,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60-161页。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五《封观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27页。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八,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979页。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6980页。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6994页。
〔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6页。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二“王维”条(陈铁民执笔),第295页。又陈铁民《王维新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53-54页)、《王维年谱》(《王维集校注》附,第1363页)同。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一《京都关内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
《唐才子传校笺》卷二“王维”条(陈铁民执笔),第295页。又陈铁民《王维新论》(第54页)、《王维年谱》(《王维集校注》附录,第1363页)同。
详见杨军:《王维受伪职史实甄别》,《王维研究》第1辑,第20-21页;毕宝魁:《千古沉冤 应予昭雪——王维安史之乱“受伪职”考评》,《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第254页。
以兵刃胁以伪职是当时陷贼士人的一种普遍遭遇。如李收在史思明再陷洛阳后“假病自辞”失败,也是被“舆至贼庭,胁临兵刃”。李纾:《唐故中散大夫给事中太子中允赞皇县开国男赵郡李府君(收)墓志铭并序》,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九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6页。
当然,接此四句之后的“刀环筑口,戟枝义颈,缚送贼庭”叙述的是王维被缚送洛阳伪廷之事,故将夹于长安伪疾失败与缚送洛阳之间的“勺饮不入者一旬”四句划归到长安短暂被囚期间亦不无道理。但这种理解难免“读死”文字了。盖骈文句法本身具有跳跃性,并不一定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叙述的。
《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第258页、第254-255页。
王辉斌:《王维“接受伪署”考评》,《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7第2期,第35-39页。
毕宝魁:《千古沉冤 应予昭雪——王维安史之乱“受伪职”考评》,《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第256页。
《旧唐书》卷九二《韦斌传》,第2963页。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第4157页。
《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第2332页。
《旧唐书》卷二〇〇《安禄山传》,第5368页。
又如杜甫《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中“然脐郿坞败”一句,同样以燃脐之董卓指称伪朝之主,而历代注家皆以为指安禄山而无异议。参見〔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5页。
按:张炳尉《两〈唐书·王维传〉与〈韦斌碑〉所载王维陷贼事异同辨析》(《文教资料》2005年第31期,第136-138页)一文已指出,所谓“戮专车之骨”是指杀安禄山,韦斌宴请王维当在安禄山死前,故杨、毕二文将“十月”坐实理解不确。但张氏又据碑文“秽溺不离者十月”在“缚送贼庭”之前的叙述顺序,以及陈铁民“盖服药取痢,故秽溺不离”的解读,而认同陈氏所谓“月为日之形误”的说法,恐怕又是不确的。
“十”在古代可作为表示多的虚数。如“一目十行”“一曝十寒”“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等。
如《谢除太子中允表》云:“伏谒明主,岂不自愧于心;仰侧群臣,亦复何施其面?跼天内省,无地自容。”(《王维集校注》卷一一,第1003页)《责躬荐弟表》云:“顷又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王维集校注》卷一一,第1126页)如王维不曾受伪署,则固当如后世之遗民,以“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贞气节自许,焉得反有自愧“何施其面”“无地自容”“负国偷生”之理?
毕宝魁:《千古沉冤 应予昭雪——王维安史之乱“受伪职”考评》,《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第255页。
邵明珍:《王维安史之乱“受伪职”真相辨析》,《励耘学刊》2020年第2期,第89页。邵氏之说又见其《唐宋经典作家仕隐思想研究》第三章第三节《王维“怀禄”“奉佛”以及“变节”问题辨正》(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77-80页)。按:实际上,毕宝魁在1998年先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的《王维安史之乱“受伪职”考评》一文中即认为王维获释后,“是否出任伪职尚无法论定。即使任伪职,当与韦斌之托有关”(第67页),同年稍后此文的修订版《千古沉冤 应予昭雪——王维安史之乱“受伪职”考评》发表于《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才将王维或曾受伪职的相关句子删去,明确提出新解,认为王维从始至终都没有受伪署。邵明珍的解读,不过是重新捡起曾被毕氏自己否定过的说法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