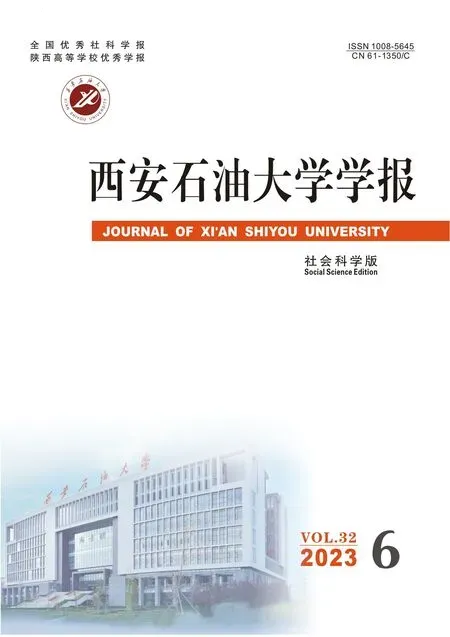理学与心学:陈淳孝道思想的两重性研究
2024-01-22石真龙
石真龙
(河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0 引 言
陈淳将孝认定为是一种道德先验的存在。在陈淳孝道思想中,孝的存在以及合法性需要一种形而上的终极依据,这便是天理。同时陈淳心学思想的倾向使其认为“天之理”同于“心之理”,因此如同天理的元、亨、利、贞,孝作为一种伦理以及道德属性则是对应着由心发用所生,这便产生了孝被发用的原理机制。而孝自心发用之后,对孝根原问题的发问则是需要理学中的天命作为依托,故天作为一种人格神的依据来对孝本原进行解释,此谓“所以然之故”。在对孝从终极依据到发用乃至根原进行探讨之后,具体到践行层面则是需要落实到现实关怀中,这便需要用心行孝的“所当然之则”进行阐释来以求心安。陈淳孝道思想中暗含着对心学与理学的调和,这也使其孝道思想始终徘徊于理学与心学之间。
1 孝源自天理
陈淳继承朱熹“理一分殊”的理学思想,因此在对孝道思想的终极依据方面,陈淳认为天理是万事万物共同的理,也是万事万物的终极依据。此外万事万物也存在着属于自己的理,依据自身之理进行运动、发展和变化。陈淳在对天理与孝二者之间关系进行推理时主要从两层逻辑理路来进行:一是天理与仁。陈淳认为理在人心中的体现是为人性,因此“性即理也”。同时人性与天命之间也是互通为一的关系,二者之命皆为天道所赋予,在天即为命,在人则为性。天命之中的元、亨、利、贞则是与人性中的仁、义、礼、智相照应,因此在对天理与仁二者之间关系的建构中,陈淳建构起天理—人性—天命—仁的理论脉络。二是仁与孝。陈淳认为孝为仁之发用,仁为孝之本,孝为行仁之本。陈淳打通了由天理至仁再由仁至孝的理论脉络,这就为其孝道思想的合理性提供了形而上的理论支撑。
1.1 天理与仁
陈淳继承朱熹“理一分殊”的思想并进行了明晰的释义。在朱熹看来,万事万物皆因天理成性,天理为万事万物的最终依据,这便是“理一”。除此之外万事万物也会禀受阴阳之气且因阴阳二气的高低、厚薄以及纯净与否而各自成形,此为“分殊”。陈淳也是秉持朱熹“理一分殊”的理念,认为天乃“一元之气”并且以“流行不息”的状态而存在,此为“理一”,也便是“大本”或“太极”。而万事万物便是从此“一元之气”中分化而来,此为“分殊”。其还用“月印万川”来映照“理一”和“分殊”二者之间一贯的关系,“陈几叟月落万川处处皆圆之譬,亦正如此”[1]46。
在“理一分殊”的宇宙本根原理下,陈淳认同“性即理也”的观点。在其看来“性只是理”,人作为接受方在大化流行的过程中,禀受气质之性化为人之形体,禀受天地之理化为人性。同时陈淳将“性”与“理”二者具体归纳为“公共之理”与“在我之理”的区别,“性”为人心之理,也就是“在我之理”,将“公共之理”的“理”放置于心,则是“性”。换言之,“性”乃为人人心中之“理”,是月印万川中的“万川”,是大小太极中的“小太极”。
陈淳认为“性”为人心之中的“理”,“性只是理”,“理”的运行变化的法则是“太极”,因此“性”的设定与运行也会有相应的规定,这便是天命,天命便为性。天命不可违,因此人性也是不可逆转的。“天道流行而赋予于物者”,天道以自然流行的状态进行运转并且赋予世间万物之命,因此天命便为承受天道所赋予,陈淳认为“天即理也”,因此“天道”也就是天理。天道同天理一样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以“大化流行”作为轨迹作用于万事万物。
陈淳认为“性”与“命”二者“本非二物”,天命便为性,“在天”便“谓之命”,“在人”便“谓之性”。天命中的元、亨、利、贞,与人性内涵中的仁、义、礼、智相呼应。天命与人性并非二物,天命中的元、亨、利、贞生发至在我之性中便为仁、义、礼、智。同时天命的设定来自天道,性本身来自天道,故天道也为天理。由此来看性本于天理,性是天理在人心的彰显,天理本身具有至善性,进而人性在道德层次上也具有至善性。
在人性所涵括的仁、义、礼、智等内涵中,陈淳认为仁是人性中最重要的内涵,并且将仁分为“爱之理”与“心之德”两条脉络来进行阐释。一是仁为“爱之理”。“爱之理”是由心发用产生恻隐之心,并且将这种恻隐之心进一步扩大至爱物层面,将这种由本我所生之情感转化为爱,而这种爱再具体生发至万事万物之中。二是仁为“心之德”。仁由心所生发,且包含着义、礼、智等其他义理。正是仁的存在才会使心时刻保持鲜活性与主动性,有仁则心生,无仁则心死。心若已死,便不会发用出仁,更不会出现义、礼、智等其他内涵。陈淳通过对天理、天道、人性、天命和仁的关系演进推理,进而打通天理同仁之间的逻辑理路。
1.2 仁与孝
孝在中国古代伦理纲常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说文解字》中对孝解释:“善事父母者。”[2]1208将孝认定为对父母的赡养侍奉,这也是为实现孝道所需做的最基本的层次。而《孝经》则对“孝”给出了更深层意义的解释:“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3]1在古代认为有五教,其中便有“教子以孝”,在儒家伦理纲常中,孝是一切道德和教育的根本以及出发点,尤其是在家庭伦理之中,更是要遵守以孝为本的理念。今人张岱年先生在其编纂的《中国哲学大辞典》中认为:“原意为子女对父母的敬重、奉养和服从。”[4]73张岱年先生将孝道思想从古至今的发展给出了很好的总结,认为“孝”最初见于西周文献中,在春秋末期孔子将孝与仁理念进行逻辑关联,之后孝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其价值内涵也被不断发展、扩充与完善。
仁孝二者自古就是难以剥离的话题,自孔子开始揭开了“仁孝之辩”的序幕,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5]2在此孝与仁的关系并非看作为孝乃仁之本根,在杨伯峻先生看来,孝乃是仁的基础,将“仁孝之辩”简单认定成孝为仁本也并非符合孔子初衷。在孔子的儒学理念中,仁为孝、忠、礼、德、义、智、信等诸德之本,仁在根本层次上是高于孝的存在。在有关“仁孝之辩”的解释中,程朱理学的解释更为精确,程颐将二者认定为本体与功用的关系:“言为仁之本,非仁之本也”[6]125。在程颐看来,孝是“为仁之本”而并非“仁之本”,换言之,仁的具体践行则是依照孝作为本根来实现。朱子曰:“论仁,则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则当自孝弟始。”[7]689朱子将仁与孝二者上升至体用高度,仁为孝之体,孝为仁之用,孝的实现要以仁为本,仁的实现要以孝为起始。徐复观说:“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国文化,其最高的理念是仁,而最有社会实践意义的是孝(包括悌)。”[8]131由此可进一步得出仁孝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仁经发用成为孝,仁为孝之本。而孝则经由现实践行给予个体以道德自主性,个体在道德自律和道德主动的双向前提下将这种道德属性赋予现实意义。
陈淳继承了程朱“仁孝之辩”的思想,认为孝为仁具体到事亲中的发用,由“亲亲”到“仁民”,再由“仁民而爱物”。仁的发用对象是天地间万事万物,具有普适性原则,但是这种原则并不是讲爱无先后差别,而是具有前后之序。陈淳用树木的生根发芽到长枝干与树叶来解释仁的发用顺序,这种顺序是依次完成且不可颠倒。不仅如此,陈淳解释因为仁所发用的感情深厚程度不同,依序所发用的感情浓度是逐渐削弱的,而孝则是由血缘关系所联络的一种融合自然与道德双向因素的情感,是一种得天独厚的其他爱所无法比拟的情感,因此孝必然为仁所最先发用产生。事亲之孝为仁首要发用,其次便是兄弟姐妹、他人以及他物的情感,感情程度逐渐削弱,故仁所发用的次序也是逐渐靠后。
在孝为仁所发用的普遍性基础上,陈淳认为孝为行仁之本,也是行义、礼、智、信的根本,行仁的开端也是自孝开始。仁的发用有先后次序,同样行仁也要依照“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先后次序,行仁“须从孝弟处起”,进而“可及民物”。因“孝弟”分为“爱亲”与“敬长”两条脉络,故行仁依照爱亲—敬长—仁民—爱物的顺序来进行,由衷且真挚。除此之外,孝也为义、礼、智、信的根本。“爱亲之诚”为“仁之仁”,故心诚求孝为仁;“谏乎亲”为“仁之义”,故谏亲求孝为义;“温情定省之节文”为“仁之礼”,故温情求孝为礼;“良知无不知”为“仁之智”,故能知求孝为智;“事亲之实”为“仁之信”,故笃实求孝为信。
综上所述,陈淳在对孝与天理二者关系的梳理中由两条逻辑进路来进行,其中的理学思路也是占据主要位置。天理在人形体中所化便为人性,人性便是天理在人的形体中的彰显。人性的始发也是天命所赋予且不可违背,这种天命的命定便是来自天道,也就是天理,由此便建构了一条“理”由天至人的理论逻辑。理在人的形体中表现为人性,仁便是由人性生发所致,孝便为行仁之本,是仁之首要发用,仁也为孝之本。这样便建构了一条天理(天道)—天命—人性—仁—孝的理论架构,也是验证了孝的终极依据来自天理。
2 孝发用自心
陈淳师从朱熹二十多年求道问学,其理学思想大多继承朱子且进行了进一步的发问。在对待陆学的心性论之时,陈淳则是极力地排斥与批判。但令人费解的是,陈淳在孝道思想的发用问题上,却有着明显的心学主义态度。陈淳认为心是一个大“太极”,万事万物之理则是由心发用所生“道理流行”为小“太极”。人的本心也是万事万物的本体,万事万物所蕴含之理便是本心的发用所产生。同样,在事亲问题上,陈淳提出了与朱熹不同的观点。朱熹认为事亲之理需要格物致知以求得,孝不过是事亲所需遵守的一方面原则。陈淳则是认为孝是同万事万物之理一样由本心发用所生,本心为万物之理的本原。
陈淳认定心为内在主宰者,在谈及心与孝二者关系时,通过以下三个步骤进行推断:
其一是理于心中。在理学和心学层面对二者的关系具有不同的论断。陈淳认为心为“个器”,性便是里面的“贮底物”,二者之间有着容纳包含之义。同时陈淳也将理与心二者之间的关系上升到已发与未发的高度来进行阐释,其曰:“心有体有用。具众理者其体,应万事者其用。寂然不动者其体,感而遂通者其用。”[1]11心在本身体现在体用两个层面,心所容纳万事万物之理时便是为体,在应对万事万物之时便为用,换句话说,“心之本体”展现的是心在超越性角度的意识层面的可能性,为未发;“应万事者”为心在超越性角度的意识层面的具体展开,为已发。将心分为“性”与“情”两个层次来看,“性”是“心之本体”,也就是说理是心之所以为心的依据,因心的稳定属性故而“寂然不动”;将心“感而遂通”,能够感应万事万物的关联并且将其贯通以用之,此便为“情”,也就是心的功用。由此来看,心和理二者关系可以看作为心具万事万物之理,理为心在“体”的体现,是心之所以为心的依据。
其二是情为性之发动,也为心之发用。陈淳曰:“情者,性之动也。”[1]14情与性二者相对,性为未发,当性与万事万物接触便会发动出情感,情为已发,“性之欲便是情”[1]14。既然情为性之发动,那么情的感通也要在向善的道德驱动下来进行,在陈淳看来,情的作用则是将天所赋予道德属性的生来就有的自然情感作为依托,以此来对性所生之情进行说明。陈淳认为,情的生发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并无善恶之分,对于情的尺度把握则是需要思考的重心,“情者心之用,人之所不能无,不是个不好底物”[1]14。情由心之发用的这个过程是顺其自然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被阻止抵消,同时情的发动也要合乎“中节”,“合个当然之则,便是发而中节”[1]14。“中节”作为情的调制器,可以使情在道德规范内发动。“情者心之用”与“情者性之动”二者内涵并无二致,故可总结为情由心发用所生。
其三是孝为心之发用。情包含着万事万物由心所发不掺杂私欲之情,这种情包含着为人子对父母的孝,情为性之发动,“性即理也”,理于心中,进而可得性也于心中,情为心之发动,故陈淳认为孝为心之发用。万般变化皆由心出,“万物无一物而非心”,心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万事万物之理皆是由心发用,这也是陈淳认为孝由心发用的总的依据。此外陈淳用“心之理”与“天之理”来佐证心是无所不包的观点。“心之理”即是性,性所内涵的仁、义、礼、智同天所内涵的元、亨、利、贞所对应,天理为万事万物之理的本原,万物作为接受方禀受“天之理”成为了“心之理”。陈淳还将孝归于由“圣人之心”此“大本”发用而生,“进而指出‘圣人之心’是‘大本’,事物大小粗精的理均是此‘大本’的发用。”[9]430“圣人之心”在全体浑沦状态便是“大本”,“大本”发生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不同身份个体之时又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流出至父子时便是为仁,为孝慈,孝便是为“大本”所发用,也就是为“圣人之心”所发用。“圣人之心”或者“大本”没有任何私欲,因此孝也是一种来自心所发用的纯粹情感。
综上所述,陈淳将孝归于心之发用,并且事亲之理以及孝的粗疏精细之理都被其视为心之发用,在此方面陈淳与其师朱熹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在朱熹看来,孝仅仅是作为事亲中的一项要义而被人们简单知晓,而事亲之中所包含具体之理则是通过格物致知的工夫路径来发问取得,而并非由人心发用所产生,其有着明显的理学主义倾向。而陈淳对此却认为这些事亲之理由心发用所生,其将心学思想倾向多发于“情”“性”“意”“志”“理”“命”的角度并对各自范畴进行了释义。陈淳将心视为主宰且发用至人的不同角度来进行窥探,由此可见其明显的心学倾向。
3 理学与心学的调适
陈淳继承了其师朱熹的“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的观点。朱熹认为万事万物之理包含着“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两大类,侍奉父母双亲为何要“孝”,听从长兄为何要“弟”,对此的回答便是“所以然之故”。而侍奉父母双亲以及听从长兄的孝弟之类行为便是“所当然之则”。在朱熹看来,孝“所以然之故”要归根于天命,同时孝也是事亲的“所当然之则”。朱熹这种观点被陈淳继承且有所发展,在陈淳看来,孝的“所以然之故”要追溯到天命的立场上,孝根原于天命,而孝也是人子侍奉父母的“所当然之则”。在“所当然之则”中,陈淳并不是一味地去宣扬理与天命,而是注重心所发挥的效用。陈淳认为孝不仅是至高无上的天命,孝心也是人们行孝的主要来源,并主张行孝要真情实意以求心安,且要及时行孝,如此才能“吾心始安”且“俯仰无愧”。
3.1 所以然之故
“所以然之故”是对于“人为何行孝”问题的回答,也是通过上升到本体论层面来对孝根原进行解答,“思考问题需打破就道德理论的藩篱,应上升到本体论层面探究事物的根源。”[10]68陈淳在《孝本原》中对孝根原的回答则是“为天所命,自然而然”。天命便是陈淳对“人为何行孝”问题给出的答案,乃是由“天之所命”至“人之所受”的运行理路。在陈淳看来孝的根原来自天命,为何行孝皆是天命自上而下所赋予。在此天已经被上升至人格神的角度,天命由天下达无法改变,而父母和子女作为孝关系中所存在的具体成员则是对孝的根原无法干预,这两种角色只是作为天命意志的工具而存在。为此人作为天命意志的被接受方,在行孝时应该遵从天命,顺行孝道,人在天命面前的能量微乎其微,不要试图去改变和违背孝道。而为厘清天命的作用机制,陈淳则对天、命与人三者之间的关联进行了论证。
孟子对天与命二者有过这样的解释:“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敬而至者,命也。”[11]184陈淳对此认为“非人所为便是天”且“非人力所致便是命”,命作为“莫之为而为者”,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现象且不受人为因素的干扰,是天道所致且无法逆转。天与命的内涵皆是理,不过在命中还包含着“吉凶祸福”等具体内容。因此天是发出方,命是天的接受方,而人则是命的接受方,这个过程不可逆转且皆来自天对人的规定。人在这个天命施为过程之中只需要被动接受无需改变,天命对人的施为是一种顺乎天道自然而然的行为。如果人这个角色不存在,天命同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天命和人是在“所以然之故”这个体系中皆不可缺的存在,天命也是作为人的孝道根原顺乎天道的存在。
在天对命的影响方面,陈淳通过梳理天与理、气的关系以及气与命的关联,进而推断出运命之天作用到人类个体时产生不同之命的缘由。陈淳认为“天即理也”,“天者,理而已矣”[1]5。陈淳将天与理、气相关联,认为天就是理,同时理和气二者相融,“上天之体以气言,‘上天之载’以理言。”[1]5气是上天之体,同时理是上天之道,而人作为接受方,在禀受理的同时,也禀受气。因人禀受“二气”不断“流行”,“万古”因此也“生生不息”来进行运转。作为上天之体的气,与命中之理二者互相融合且不可分离,气具有流动性且被理所主宰,气之运动则是依照理的规定来流行,因理在气的运动变化中起到枢纽调节的作用,“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尝止息。”[1]1
因人作为接受方在运命主体之天赋予人以相同之命时,个体之间的差异使不同的人接受天所赋予之命的程度不同,因此人们所禀受的气在清浊薄厚程度有所不同,气的不同便会影响到命。陈淳将这种现状比作天“沛然下雨”,天所下雨量是一定的,但是雨施落在不同地点,就会引起不同的现状,雨落在江河时“其流滔滔”且“不增不减”,落在溪涧便会“洪澜暴涨”,落在沟浍之时便会“朝盈暮涸”。同样的雨落在“沼沚坎窟”“盆瓮罂缶”和“螺杯蚬壳”之时,雨水也会有清浊的不同状态,同样接受一方的差异便会导致所受之气不同,“随他所受,多少般样不齐,岂行雨者固为是区别哉?”[1]5天赋予每个个体的命是相同的,“天之所命则一”,但是因个体之间气的不同,故气会反作用到每个人的命而有所差别,气有长短薄厚,命就会有贫贱富贵以及夭寿祸福,也就是“死生有命”与“莫非命也”的区分,气有清浊,命便会有“智愚贤否”。
在对天命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后,“人为何行孝”的问题也有了具体的答案,天命便是在形而上的角度作为一种不可或缺且无法改变的存在,为孝道提供了一种合理性存在的证明。孝道的存在来自天命,是上承天道且顺其自然。天作为施为方对人类个体授予相同之命,而人作为被动接受方,因自身个体差异的不同在接受天施为时便会有着不同之命,同样孝道在每个人身上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也并非遐迩一体,而是千差万别。无论是天命对人的施为,还是人的个体差异影响自身之命,皆因天命而起,这便是孝道的“所以然之故”。
3.2 所当然之则
“所当然之则”是对“人如何行孝”问题的回答。在厘清“人为何行孝”的问题之后,对于孝根原问题有了明晰的解释,而具体回归到孝本身之时,在对孝道现实关怀层面的发问则是需要“所当然之则”来具体践行。陈淳在面对“所当然之则”的问题时并不仅仅是讲如何去做,还注重孝本身情感的脉络以及子女对父母在孝心上的发用,除了侍奉父母,还注重真情实意来换取自身的心安理得。对此,陈淳在对“所当然之则”的具体落实中,可以分为三个层面进行阐释。
首先是奉养父母,这也是对子女行孝的最基本的生理层次的要求。父母年迈之后只能依靠子女,子女是侍奉父母的唯一寄托。如果是他人来替自己尽孝,自身的孝心便会难安。并且子女的身体是“父母之赐”和“天所与”,父母给予子女生命抚养他们成人,使他们身体发育健全拥有强壮的体格,并非是让他们“安闲空饱饮于天地间而全无所事”,而是使其竭尽所能事养双亲,绝对不能“空负人子之名”。
其次要及时行孝。及时行孝的理念在《孔子家语》中有被明确提及,“夫树欲静而风不停,子欲养而亲不待。往而不来者,年也;不可再见者,亲也。”[12]55同样在陈淳看来及时行孝也是身为人子需要做到的方面,天命作为根原施为至孝,“天命流行不曾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在不断流逝无法逆转,父母也在一天天变老同样无法“复壮”,身为子女对父母也不能“得而再事”。因此要及时行孝侍奉父母,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不要等到“大愿未偿”并“终天之隔”之时而感到“大欠缺大悔恨”。
最后要用心行孝且要做到真情实意,以求心安。这种由心所发真心实意的情感自先秦开始便是在孝道思想中不可忽视的要素。在先秦儒家看来道德情感是人们道德行为实现的驱动力,孔子对孝的理念认为“能养”仅仅是作为事亲最为基本的要求,只能满足生理方面的需求,除此以外还要在赡养父母时具备充分的敬亲、顺亲、遵礼和使乐等道德情感,这种情感统摄一切对于父母的真心实意,并且通过孝行为来将其进行阐发。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5]19在孔子看来血缘关系的关联仅仅是子女对父母产生的血亲之爱,这种爱却是不包含“敬”的元素在内,能养仅仅是作为一种饲养来满足生理需要,在此方面牛马与人无异,这是养口体之孝,真正区别人与动物的在于是否敬亲,是否为发自肺腑。在李振纲先生看来,“敬”也为孝的核心,其发自真情内心,是一种情感基础的表达,其言:“孝为百行之本,是实现人道之仁的心理情感基础。”[13]10同样陈鹏先生对此认为:“事亲要与敬养结合,以养为本,以敬为先,还要体现礼、乐。”[14]44
陈淳在讲到行孝时的观点同样也具有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映照。如果子女让外人来奉养自己的父母,自己便会内心难安,既不能做到“理之宜”,也不能完成“事之安”。陈淳在讲及时行孝之时,也是注重“无跬步不切于心”,如此才能够做到“吾心始安”且“俯仰无愧”。其在讲行孝之时并未过多着墨来阐述心的重要性,但是在对行孝的讲述中可以看出,心在行孝之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行孝是为了求得心安,而对父母的孝则是由心发用且真情实意。
综上所述,陈淳在面对“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的问题上对理学和心学二者皆有牵涉,其理学思想也是具有了心学主义倾向。在“所以然之故”问题上,陈淳坚定地站在理学角度以天命作为根原对“人为何行孝”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天命的存在为孝道提供一种根原性依据,此皆因天道而为且自然而然发生,人为不可逆转。而在“人如何行孝”的“所当然之则”问题上陈淳则是产生了明显的心学主义倾向,其重视心在行孝过程中所起到的效用并且给出了事养父母、及时行孝以及真心实意三条路径:子女事养双亲作为最基本的要求来满足父母基本的生理需要;及时行孝则是因时间的单向性而提出的要求,为此来避免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真心实意侍奉父母则是为了以求心安,并且真心实意的侍奉父母并不仅是处在基本的衣食住行的养口体之孝,还要求子女本身发自肺腑地做到敬与诚,进而能够进一步使父母的精神得到满足愉悦,这也是对父母“养心之孝”的要求。由此来看,陈淳在对行孝问题的根源和现实关怀角度对理学与心学二者之间进行了调适,陈淳的理学立场坚定,但是也并非一味打压与忽视心学作用,而是对理学与心学二者之间的配合与调适起到了一定的参照效用。
4 结 语
理学与心学二者在诸多内涵论证方面持相对态度,一者认为世界的终极根源来自于理,另一方则是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包括陈淳自身也是站在理学立场贬斥陆学为“吾道之贼”。但是难以置信的是,陈淳思想中却有着浓厚的心学倾向。理学与心学的二重性并非只在陈淳孝道思想中显露,也出现在其思想的多个层面,其认为“心有体有用”,“万物无一之非吾心”,“内在主宰者是心”,其师朱熹也批评其思想在“尊德性而后道问学”方面出现偏颇。有关陈淳心学倾向的言论颇多在此不过多赘述,而在陈淳孝道思想中同样是出现了心学思想的倾向。陈淳在其孝道思想中一方面将理学作为自身的思想依据,无论是孝的终极依据来自天理,还是“人为何行孝”的“所以然之故”问题上,陈淳坚定地站在理学立场来进行阐释。但是在孝的发用问题上,陈淳则是出现了明显的心学主义倾向,其认为孝由心发用产生,并且在“人如何行孝”的“所当然之则”问题上,陈淳同样重视在现实层面行孝之时心的效用,讲究发自内心的用心行孝来以求心安。正如曾振宇先生所言:“他的思想徘徊于理学与心学之间,决定了其孝论也徘徊于理学与心学之间。”[9]436陈淳孝道思想注定是具有理学与心学的两重性,其在占据理学立场的同时,也在心学这条道路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