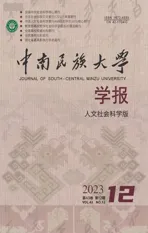南宋严子陵钓台的地标生成与书写
2024-01-20王淋淋王兆鹏
王淋淋 王兆鹏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桐庐县西四十里,有山名富春,山麓有石,“上平可坐十人”,“东西两台对峙,高百余丈,俯瞰大江(富春江),水木明瑟”[1],即为严子陵钓台。钓台因东汉高士严光(字子陵)得名。严子陵为汉光武帝刘秀少时同学。刘秀即位后,子陵隐姓更名,数诏不出,渔耕于富春江畔,直至终老。后人慕其高风,名其垂钓处为严陵濑、钓台[2]。钓台也成诗文中经典的隐逸意象之一。到了南宋,各种条件成熟,使其成为严州的地标之一。子陵钓台具备哪些地标特征,如何成为地标,又有哪些意义?笔者将一一探讨。
一、地标特征
地标,指某地具有标志性特色的景观或建筑物。作为严州地标的子陵钓台,吸引往来文人的关注,成当地的典型景观之一,而它本身蕴藏的精神文化内涵,又使其具有了象征性。
(一)吸引性
地标或因其鲜明的特色与辨识度,引人注目,或藏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人心生倾慕和景仰。地标景观严子陵钓台不仅吸引着往来者的目光,激起他们的游览之兴与朝圣之心,而且还成为绘画、造园的题材以及建筑的借景点。
取道富春江的行人,往往会留意钓台,就像宋人曾丰在《再题严子陵钓台》中所写:“桐江自汉至今日,依旧行人指钓矶。”[3]30281-30282对于旅者来说,钓台是途中一个具象化的存在,如姚镛的《桐庐道中》云:“两岸山如簇,中流锁翠微。风帆逆水上,江鹤背人飞。野庙青枫树,人家白板扉。严陵台下过,不敢浣尘衣。”[3]37092陈文蔚的《自吴重归过钓台》曰:“水绿山青从所好,一帆风过钓鱼台。”[3]31944青山、绿水、风帆、江鹤、野庙、枫林,都是普泛化景象,在其他旅途也能见到,而子陵钓台,有具体名字,是严州独有的景观。钓台能抚慰旅人疲惫的身心。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正月,41岁的杨万里从故乡启程,赴临安任。他在新安江的白沙渡口买好船,行往目的地。舟小路遥,客途倦人,直至严州钓台下的清泉,终于让他“未酌意先清”[4]223。淳熙十年(1188年),他出京返乡。想起过了胥口渡,钓台即近,倒可借机去访古寻幽[4]1246。钓台也引往来者沉思,杨万里认同严子陵的价值取向:“断崖初未有人踪,只合先生著此中。汉室也无一抔土,钓台今是几春风。”[4]224姜特立在《过钓台》中赞他“贤哉羊裘公,不肯仕汉光”[3]24091。
当然,行人们并非只在舟行时凝望,他们似乎更喜泊船观览或攀登。例如,陈畴“绿竹丛边系客船,钓台千古薄云天”[3]45523,王自中“扁舟夜泛,向子陵台下,偃帆收橹”[5]2235,华岳“遐想高风殊未厓,舣舟夜访子陵台”[3]34380等。绍熙元年(1190年),陈傅良欲辞免两浙西路提点刑狱,不允。于是赴阕奏事,船过钓台,登临时感慨无限:“一再登临万事非,裹头还已雪垂垂”,慕子陵“论功汉鼎吾何有,自是风流百代师”[6]230。四年后的腊月,他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返故乡瑞安途中,又泊船钓台下,叹曰“此舟三泊此江沂”,借咏子陵事迹,倾吐心中悒郁:“遭逢明主还遗恨,惭愧先生独见几。”[6]248
钓台不仅引得文人们的关注,还激发他们的朝圣之心。登临者赋诗抒怀,致礼膜拜,比如金履祥的《题钓台》云:“我来一瓣香,敬为先生拈。陟彼崔嵬冈,想此仁义心”[3]42580;陆游的《夜观严光祠碑有感》曰:“登堂拜严子,挹水荐秋菊。”[7]1805-1806如果游程被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阻挠,将成为他们的遗憾。淳熙七年(1180年),陆游自蜀东归时,本想租船到七里滩拜谒严光祠,却未能如愿,所以他写诗发牢骚认为客星祠下的浩渺烟波,欠了他的披蓑泛舟行[7]1029。徐集孙“所恨钓台眠里过”[3]40330,怨自己经过钓台时,竟沉溺在梦乡中。至于计划游钓台的旅者,更是心心念念,如林希逸的《有感》曰:“得归须谒严陵去,梦已先经七里滩”[3]37234-37235;韩淲的《雪晴可喜》云:“明年脱绶乘潮去,舟过钓台尤要吟。”[3]32601还有一些人,虽然自己不在严州,却嘱咐到那里赴任的亲友,记得观览钓台。比如,郑刚中赋诗告知将要出守桐庐的友人胡德辉,桐江众所周知的幽胜佳景无数,像绿水浩荡、千峰参差,斑鸠啼过、桑叶蓊郁,雨水停后、稻花低垂。不过公事之余,更值得经常探访的是严陵祠[3]19088。叶茵在饯别族侄入幕僚时,除了叮嘱“少年先器识,实地作功名。太守贤明甚,当如事父兄”,也让他“冲寒谒子陵,好挹钓台清”[3]38250。
探访和观览之余,南宋人也喜以子陵钓台作为装点庭院或绘画等的题材。如,国博郎中喻良能在自家园亭中模仿“狂奴旧钓台”,设了“钓矶”一景,得欧阳修称赞曰“至今犹带汉莓苔”[4]1064;莹上人绘作“羊裘老子钓鱼处”,使陆游“开卷”便觉“双眼明”,未经许可,匆匆取去,因为“夜窗吾欲听滩声”[7]1153;僧人释宝昙见钓台图,题了三首绝句,从描述画作本身开始,一直衍生到对严子陵人生抉择的价值探讨[3]27107。另外,如果条件允许,人们建房修舍时会向钓台借景。如严州太守曹耜在郡圃“撤材易地为堂,买地以广之,正对南山”,建成聚山堂。新堂广收富春江山之胜境,建筑物次第错落,恰可窥寸许钓台[4]367-368。子陵钓台因其吸引性,成为行者的关注点、文人的朝圣地、画稿中的题材以及园林里的缩景和建筑的借景点。
(二)典型性
地标是一地的典型景观,往往能代表其所在地,譬如寒山寺之于苏州,乌衣巷之于南京。子陵钓台亦如此。文人在书写桐庐时,经常不可避免地提及钓台。如韩淲“唤得扁舟一叶轻”上富春滩后,首先看到“钓台波上夕阳明”[3]32606。他的“孙祖墓荒犹巃嵷,严陵台在更沦漪”[3]32636句,提及值得“访古怀贤”的意象,便有同“孙祖墓”形成对举的“严陵台”。此外,王柏的“香火严兰若,烟霞老钓台”[3]38006,刘一止的“千古严陵濑,清夜月荒凉”[5]1032等诗句,皆将钓台作为严州的代表景观。
子陵钓台因其典型性,成为严州的代称。僧人释元肇的《送致政许朝请》曰:“城外钟寒寺,山阴雪夜舟。还经钓台过,不愧客星游。”[3]36882诗中提及了三个地点,山阴是直书其名。姑苏和严州,则分别用钟寒寺和钓台指代。韩淲寻找僧人朋友时,行遍姑苏的“灵岩”和“虎丘”,游尽余杭的“洞霄双径”(1)据朱文藻等“余邑有洞霄双径之胜”句,得知“洞霄双径”当在余杭(参见《余杭县志·卷二十八》,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最后到严州的“钓台”[3]32738。徐照赋的《路逢杨嘉猷赴官严州》则表达了对偶遇即别的友人的思念之情,诗末“思君还有梦,前到钓台边”[3]31371之句,以钓台代指杨嘉猷的任所严州。
此外,钓台也经常被当作参照物,来描述陌生的场景。试以徐瑞的《舟行书感(壬午)》为例:
断崖斗绝小舟行,烟树崔嵬草一汀。宛是钓台台下路,杨梅卢橘正青青。[3]44661
诗人泛舟经行断崖,见崖底的高树、草汀,仿佛昔年严陵钓台下,那长满青青杨梅和卢橘的山间小路(2)原诗有注:“余甲戌三月登钓台,杨梅芦橘青青两山间。”。在这里,他用较出名的钓台及其山间路作参照,来书写这片不甚为人所知的崖下场景,使读者更加明了知晓。同样,陆游作有“秋郊多烈风,夜壑起松籁。初闻尚萧瑟,髣髴听严濑”[7]1176之句,选择“严濑”这一经典的钓台元素为样本,以便具体形象地描述自己听到的松籁。总之,作为严州的典型景点之一,严子陵钓台不仅代表了当地的众景观,成为了严州的代名词,甚至还可作为陌生景象的参照物。
(三)象征性
地标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物象,还承载了丰富的精神和文化内涵。在文人们不断探访和书写的过程中,子陵钓台也具备了各种象征意义。超脱名利的精神境界是其最核心的意义。当年严光拒官归隐的行为,赋予钓台高洁的内涵。于是文人们借钓台表达对名利的规避,如林季仲的《袁居士来自桐庐索诗赠二绝句·其二》云:“君看仕路风波恶,孰与严陵七里滩。”[3]19970钓台石下的七里滩虽然风浪湍急,但远不如仕途凶险。方岳在《寄别季桐庐》中劝任桐庐县令的朋友季著道:“底须政事喧京辇,例合诗人管钓台。”[3]38368与其随波逐流,不如急流勇退,诗人的本分就是管理钓台,而非沉湎在喧嚣的政事里。
对于有些诗人来说,钓台代表了他心中的理想家园,比如陆游。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任建安提举的陆游写下一系列思乡诗:
秋风有句君知否,合在严光钓濑边。(《建安遣兴·其三》)
秋风严濑清,春雨戴溪绿。(《初秋梦故山觉而有作·其四》)
空堂饱作东归梦,梦泊严滩月满舟。舟行还山阴,道出七里滩。(《客思·其二》)
戴溪寒酿千峰雪,严濑声酣七里秋。(《平生》)
严濑、七里滩这些钓台元素,频繁出现在诗人的心里与梦中。尽管这些景象并不属于故乡山阴,但它们却是诗人理想家园中最不可或缺的部分,接纳并抚慰他那奔波辗转在薄宦生涯中的疲惫身心。
严子陵钓台吸引文人、旅者慕名关注。在他们的书写与传唱过程中,钓台渐成当地典型之景。此外,它还象征着淡泊名利的精神、理想家园的温情,以及与之相关者的气节、品质。叶适为薛姓严州太守赋挽词:“瘴雨蛮烟尽扫清,钓台方轨净无藤。堪怜独立沧江上,不许朱轓更一登。”[3]31269钓台在地理上代指严州,它那平坦洁净、无藤蔓攀援的特点,又象征薛太守廉洁正直的品质。张镃的“千古风高仰钓台,朱轮新拥得通才”[3]31614诗句,借钓台蕴含的千古高风,含蓄褒扬了叶景良的品行。
二、地标生成
地标景观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时间与空间因素的共同发酵与酝酿。譬如,严子陵钓台由东汉苔迹斑斑、蓬蒿丛生的寻常断崖发展为南宋时期严州的地标景观,经历了初萌、生发到成熟三个阶段,其间少不得各种天时、地利与人和。
(一)初萌期:南朝至盛唐
南朝至盛唐是严子陵钓台地标化的初萌期。子陵躬耕渔隐富春江畔的事迹,在《东观汉记》《高士传》以及《后汉书》等史书中都有记载。不过其间涉及到的钓台,仅是传主的一个活动场所而已。它真正为文人书写,则从南朝开始。刘宋永初三年(422年)秋,谢灵运从故乡会稽始宁出发,折返萧山,取道钱塘江,赴永嘉任。经桐庐七里濑时,水流奔急,峭壁林立,荒林落叶,哀禽相啸,不由伤怀自己贬谪的遭遇。然当严陵濑闯入视野时,失落的心灵瞬间得到抚慰,他吟道:“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8]在谢灵运看来,严陵濑不仅是途中的一个景点,还蕴含了“异代同调”的归隐情结。相关诗作还有任昉的《严陵濑》、沈约的《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以及王筠的《东阳还经严陵濑赠萧大夫诗》等。另外,这时期的地方志——《舆地志》中有条目介绍钓台曰:“桐庐县南有严子陵渔钓处。今山边有石,上平,可坐十人。临水,名为严陵钓坛也。”[9]这说明它也引起过地理学家的关注。
到了初盛唐,严子陵钓台获得的关注度有些许增加。一方面,它多为人谈及,比如身为异乡人的孟浩然,听闻过严陵濑的地理位置:“湖经洞庭阔,江入新安清。复闻严陵濑,乃在兹湍路。”[10]1633另一方面,人们在钓台附近为严光修建了祠堂。唐睿宗时期诗人洪子舆在《严陵祠》中如是说:“客星今安在,隐迹犹可见。水石空潺湲,松篁尚葱茜。岸深翠阴合,川回白云遍。幽径滋芜没,荒祠幂霜霰。”尽管祠已荒弃,但在这里“垂钓想遗芳,掇蘋羞野荐。高风激终古,语理忘荣贱。方验道可尊,山林情不变”[10]1079。此外,一些文人也开始为钓台所吸引。崔颢在船行新安江时,心生“行行泊不可,须及子陵滩”[10]1328的期许。孟浩然游钓台后,颇有“观奇恨来晚,倚棹惜将暮”[10]1633的遗憾。李白的《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独酌清溪江石上寄权昭夷》等涉及钓台的诗篇,尽管都在他乡所写,但似乎可说明,他将漫游吴越途中所见的钓台,记挂在心里。
总的来说,从南朝到盛唐,严子陵钓台开始走进文人的审美视野。既因其风光秀绮,也由于它蕴含的隐逸文化与部分文人的心境相契合。不过此时严州依然偏僻,经行者较少。加上初盛唐国力强盛,士人满怀积极昂扬的用世之心,也就不会完全认同子陵的“激流勇退”。但这阶段的诗文,让世人得知子陵钓台的地理位置、风光特色、文化底蕴等,为它在后来成为严州的地标景观打下了基础。
(二)生发期:中唐至北宋
安史之乱后,中原政权逐渐衰弱,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开始南移。严子陵钓台借时代之势,迎来它地标化的生发期。
其一,钓台的知名度持续提升。相较之前的行者只是恰好路过,被动地注意到它,中晚唐的文人则多了几分刻意与用心。他们或停船留宿,比如大历四年(769年)秋,刘长卿奉使新安,经过严陵钓台时,宿七里滩下,望钓台怀古,怅羁旅行役之劳,思功名之外的意义[11];或带着对严子陵的景仰去登台,像权德舆“我行访遗台,仰古怀逸民”[10]3654,李德裕则“我有严湍思,怀人访故台”[10]5443,刘驾更是“我来吟高风,髣髴见斯人”[10]6832。有的文人赋咏之余,还刻碑铭,如梁肃曾“涉江自富春而南,访先生遗尘,则钓台尚存,仰聆德风,刻颂于石”[12]。
除作为景点外,此时的钓台还成了地理参照物之一。杜牧借其指出睦州州治的位置:“州在钓台边,溪山实可怜。”[10]6014方干也据此描述自己曾经的居所:“吾家钓台畔”[10]7504“我家曾寄双台下,往往开图尽日看。”[10]7534可见,大家对钓台已经比较熟知。
其二,子陵钓台在隐逸情怀的基础上,又衍生出节义精神。这种道德文化首先为范仲淹挖掘并发扬光大。仁宗景佑年间,谪守严州的范仲淹在钓台下构建祠堂,绘子陵像以奠,并作歌赞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目的“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13]120。当他看到钓台附近方干的旧居,拜访得知“其家子孙尚多儒服,有楷者新策名而归”,于是“又图处士像于严公堂之东壁。楷请刊诗于其左”[13]64,将方干和子陵共同立为严州的道德典范。祠堂建成之后,“往来之人,鲜不登堂致礼者”[14]269。未至严陵者,像梅尧臣、王安石、谢薖等人也深受感染。比如,梅尧臣读完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后,题诗称赞曰:“有客乘朱轮,徘徊想前轨。著辞刻之碑,复使存厥祀。欲以廉贪夫,又以立懦士。千载名不忘,休哉古君子。”[3]2761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钓台的地标特征渐显,旅者视之为不可错失的景点,书写者亦多,宋人赵抃的诗即可为证:“见说桐江鱼亦好,昔贤多作钓台诗。”[3]4217同时,它又得贤士大夫增建祠堂,拓展文化内涵。不过,处于生发期的事物,不一定都能顺利向前发展。此时的普通民众,并没有完全领会钓台的意义,比如鲁有开遗憾曰:“乡人不识钓台意,空指山头是钓台。”[3]7340后来子陵祠堂也未得有效地维护,“岁月滋久楝宇渐堕,上漏测穿,像亦故暗”,加上“至者喜留名迹”,“狂易之徒,往往及像之面目甚非”。幸得元祐元年(1086年),县令叶棐恭重新修葺,以塑像替绘画,这样才使得“二高人之清标,俨然长存;而文正之遗迹愈远不泯也”[14]269。
(三)成熟期:南宋
已颇有一定知名度的严子陵钓台,到了南宋,得各种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条件,真正成为严州的地标景观之一。
当赵宋政权迁至临安后,严州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辐射区内,于是子陵钓台迎来了地标化发展的天时,并且它还处在交通枢纽之上,占尽地利之优。杭州城“枕带江海,远引瓯闽,近控吴越,商贾之所辐辏,舟航之所骈集,则浙江为要津焉”[15]。这里的“浙江”即钱塘江,它发源于安徽黄山山麓,流经淳安、建德等地,最后从杭州湾汇入东海。干流各段,依地命名,流经桐庐、富阳段的,就叫富春江。既然钱塘江是“通江渡海之津道”[16]214,那么富春江自然也成了从临安前往瓯、闽、越、婺、衢等各地的枢纽要道,陆游在《严州钓台买田记》中说:“大驾巡幸临安,以朝士出守者,与夫人对行殿,被临遣而来者,大抵多取道于富春。”[17]释文珦的朋友从杭州去金华,走富阳水路,严陵是必经之地[3]39697。陈元晋在甲申、乙酉、丙戌三年间,四次经过子陵台[3]36024。当时江岸、渡口处,船只贸易发达,如“海舶大舰、网艇、大小船只、公私浙江渔浦等渡船、买卖客船皆泊于江岸”[16]215。杨万里在“建德县西南六十里新安江渡口”[18]的白沙渡即可买到船[4]223,陆游则于严州购舟下七里滩[7]1029。因此,富春江在北宋时即“台下千帆过”[3]10219,到南宋更出现“千家画栋前朝屋,百里清江过客船”[3]45599的场景。
地利之优,使钓台获得被瞩目的频率,而人和之力,让它拥有了被关注的强度。绍兴十年(1140年)三月初八,宋高宗追封严子陵为奉议大夫:“抒抱匡时,勋业固垂万世;羽仪示则,清标永著千秋……一字之褒,有光泉壤;万民之式,永表寰区。”[19]钓台得到了最权威的认可,从此真正为天下人所知。
同时,地方官员和乡绅们对它的营建工程也在继续进行。绍兴四年(1134年),知州颜为增建了“客星”“羊裘”二轩[20]28。绍兴八年(1138年),县令董棻在州治的左边建“高风堂”,“以景慕子陵之贤,且立文正范公所述祠堂之碑于其旁”[21]。又淳熙五年(1178年),郡守萧燧“复大葺祠宇,以续先人之绪”[22]383。但后来,接管的僧人用火不慎,导致钓台一夜之间葬于火海。郡守陈公亮与地方官、乡贤募款重修,“工力颇裕,视前之轮奂有加焉……规模高耸,皆逾旧制。则别创‘遂隐’‘记隐’二区,以翼于‘三贤堂’之左右”[23]412-413。还有钓台书院,知州陆子遹在绍定元年(1228年)首创,后来者王佖、赵汝历继续扩建[20]28。
本着景仰先贤、树立典范、利于教化的目的,人们修缮、增建相关建筑,却无意间促进了钓台的地标化发展。一方面,巩固并发展钓台所蕴含的德性之美,使之更加深入人心。比如章才邵说:“汉家名节君知否,尽在君家一钓竿。”[3]27688俞桂道:“只将节义高千古,岂钓人间利共名。”[3]39054缪瑜言:“遂令千古重名节,于乎先生真汉杰。”[3]32215文人们相信,较于政治功业,道德光芒更能光耀后世:“方信先生大有功,光皇祇是暂时雄”[3]40109,“名教扶持真百世,岂徒当代慑曹瞒”[3]40445。他们感念的不止子陵高风,还有前贤的品格与功绩,如洪咨夔的《严陵道上杂咏·其三》云:“玄英范老闻风起,俱为羊裘一钓丝。堂扁三贤非本意,何如只号子陵祠。”[3]34472他认为方干、范仲淹等隆德之人,当同子陵一起,为世人铭记。另一方面,修建工作也开发和完善了钓台的旅游资源。例如,郡守萧燧修缮子陵祠时,还在“岸江立表以识路,缘山作亭以待憩”。经他重新规划和布置后,“溯沿上下者,欸门而心开,升堂而容肃,风清越,濯寒泉,吟哦山高水长之诗,致足乐也”[22]383-384,可获得极佳的旅游体验。还有陈公亮增修祠堂时,充分考虑到旅者的生活便利与舒适:一则开发新的区域,构建旅舍,使“寓僧有舍,客休有馆”;二则修山阶,“辟登坛之道而级之以石”,方便攀爬;三则增建亭子,以供休憩[23]413。
由此,钓台从单纯的自然风光,转化为综合自然与人文的景观。加上宋代文人本身对文化旅行的热衷程度超越前代,如北宋的胡瑗引滕公“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鄙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24]之言,以证文旅能让学者增长见识、体察世态人情的作用。南宋士子对此兴趣尤甚,陆游入蜀途中,特别关注富有历史背景和文化意蕴的碑石和亭台;罗大经非常推崇“登山临水,足以触发道机,开豁心志”[25]类的道德文化旅游;等等。严陵钓台既让人接受道德熏习、志趣陶冶,又能满足旅者生活便利,吸引更多游人慕名前来登台、谒祠、览轩亭,如范成大“癸巳岁正月一日,巳午间至钓台。率家人子登台,讲元正礼。谒二先生祠。登绝顶,扫雪,坐平石上”[26]。
严子陵钓台从东汉的沉寂,南朝时偶得行人关注与书写,初盛唐进一步走进文人的审美视野;至中晚唐多为旅者青睐,又有北宋时文化精英开掘其道德文化;到了南宋,天时之势、地利之便与人和之力终于齐备,遂成严州的地标之一。
三、地标意义
严子陵钓台,不仅是南宋文人旅途中的必经地,还是他们文化的朝圣处、心灵的皈依所。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严子陵钓台还成为民族精神的升华点。这些才是它作为地标真正的意义所在。
(一)文化朝圣处
严子陵钓台承载着的历史记忆、精英文化和道德标准,成为南宋旅者心中的圣地。在这里,他们可回顾历史,表达着对子陵的景仰,也可审视反思自我,完成一场精神和文化上的朝圣之旅。经行的文人,总容易被牵惹起一番历史感怀:汉家的山河社稷早已更迭作他姓,当年的王侯将相、丰功伟绩,又归往何处呢?君不见,“四百年间将相谁,丰功伟绩竟何归。生前有望荣招辱,死后无明是反非。麟阁故基为草鞠,云台遗屋与烟飞。桐江自汉至今日,依旧行人指钓矶”[3]30281;“汉室兴亡一聚尘,山河社稷几翻新”[3]41178。只有眼前的钓台,任凭风侵雨蚀和世间的改朝换代,始终屹立在富春江边,与天地共存:“当时冠剑今何在,独有高台万古留”[3]16801;“岂但云台高不似,钓台草木至今春”[3]40464。在这里,子陵急流勇退式的清醒抉择、淡泊自持的品质,穿越了历史的风尘,获得永恒的生命力:“云台貂冕成堆土,钓濑羊裘照九秋”[3]34046;“高风今尚在,江水与俱长”[3]29545。同时,它也赢得后人无限的敬慕与追念:“高踪卓绝横今古,瞻拜桐江感叹俱”[3]28936;“缅怀台上人,老藓双骭存”[3]38419。
文人们不仅以敬仰的方式来认同严子陵钓台的价值取向,而且还在行动上追慕与践行。比如,南宋名臣王十朋奉祠返乡,路经严陵,作《钓台三绝》,兹列二首:
圣主中兴急用人,小臣无术赞经纶。功名分付云台士,愿学先生事隐沦。(其一)
窃食三州愧不才,扁舟又过子陵台。心知敬慕先生节,乞得祠宫归去来。(其二)[27]480
据“圣主中兴”“扁舟又过”等词语,可推断该诗当作于隆兴元年(1163年),王十朋第二次辞官去国途中。张浚北伐失败后,自劾。时任侍御史的王十朋屡屡进言,然孝宗力图恢复中原之心动摇,起用“主和”之臣。性情刚直的他,忧愤不已,上书自我辞免,拒绝朝廷的任命[28]。既然功业受挫,孤忠难展,那就学子陵“事隐沦”,守自己所敬慕的“先生节”。尽管“圣主雅恢光武量”,但“微臣当遂子陵高”[27]264。王十朋这种不恋权与利,为志向舍弃功名的行为,是对子陵高风的回响与践行。
“圣地”不仅可触动人们的崇敬之心,也能引发他们忏悔式的自我反思。不少奔赴在宦途中的文士,经过严陵钓台时,心生惭愧,如陈必敬在《钓台二首(其一)》云:“公为名利隐,我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3]43927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同钓台所象征着的不慕名利的精神相违背,惭愧不已;李昴英亦是“如今羞见先生面”,选择“夜半撑船过钓台”[3]38862;胡仲参“只行山后路”,因为“羞过钓台前”[3]39849。李清照的《夜发严滩》亦曰:“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29]261她本在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闻淮上警报”,同“江浙之人,自东走西,自南走北……亦自临安溯流,涉严滩之险,抵金华”途中所作,逃命与追名完全是两回事[29]367。李清照在诗中提及的“有愧先生德”,当是代他人言而已。其实这些满怀愧疚的“名利客”们并非真正的追名逐利之辈,相反他们恰是厌倦了羁旅奔波、功名役身的生活。由此林季仲抒怀道:“脱身归去亦何求,刚被声名落钓钩。买得扁舟在祠下,从公觅取旧羊裘。”[3]19967可以代表“忏悔者”们共同的心声。
无论是来膜拜,还是忏悔的朝圣者,他们都在钓台进行精神沟通、互动的过程中,寻找到了文化和价值的契合点与认同感。既然实现不了经世济国的理想,那么就选择放下功名,独善其身。这不是逃避,也不意味着失败,而是实现人生的另一种价值。
(二)心灵皈依所
皈依所,指可依托和归向的地方。严陵钓台本身所蕴含的精神和文化,除了让“朝圣者”寻找到认同感,也能安抚失意者,为疲乏无依的心灵提供一个得以安顿的栖居所。它时常萦绕在中晚年时期的陆游的心中和梦里。淳熙五年(1178年)冬,自蜀被召回的陆游,改任建安提举。相较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第一次仕闽时的意气风发,此刻他的内心满是愤懑与失落。抗金许国的梦再难实现,还遭遇被“诬为牛李之党”的“铄金之谤”[30]287-290。思念故乡,便成他排遣郁闷的一种方式。不过在他的怀乡诗中,时时出现桐庐的严濑、七里滩等钓台元素。比如“秋风严濑清,春雨戴溪绿”[7]897和“戴溪寒酿千峰雪,严濑声酣七里秋”[7]874等句。戴溪,即嵊州境内的剡溪,据《嘉泰会稽志》载,它的得名源于东晋王子猷在夜雪初霁时,乘小舟夜访居于剡县的戴逵,至门却不前,随即而返的雅事[31]。严濑和剡溪,都是可以接纳漂泊游子的故乡风景。他的《客思·其二》曰:“空堂饱作东归梦,梦泊严滩月满舟。舟行还山阴,道出七里滩。”[7]895梦里返乡的船停泊在严滩,满载月光,行回山阴。陆游回乡若取道衢州、金华,严滩确实是必经点之一,但在梦里只有它,足见其在诗人心中的分量。
对于客居他乡的陆游来说,严濑可作家乡的代表意象之一,承载他对故园的思念。但回到山阴后,他的心里还是绕不过严濑。淳熙十年(1183年),乡居故里的陆游作《秋夕大风松声甚壮戏作短歌》,有“初闻尚萧瑟,髣髴听严濑”[7]1176句。秋风过,松涛声起,不由想到严濑;淳熙十五年(1188年)又作《舟中大醉偶赋长句》,亦有“画楫新摇严濑月,清尊又醉戴溪秋”[7]1555之句。但是,陆游在严州上任时,却甚少提及钓台。为何钓台只存在于他的记忆里?
在建安时的陆游,将严濑看作可以躲避世间风雨、抚慰失意创伤的理想家园。乡居山阴后,严濑的意义可能进一步加深。陆游一生奔波于薄宦,颠沛辗转,营营役役。现实与理想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他一方面试图借钓台的隐逸文化,让失意的心灵有所依托,以此忘却壮志难酬之伤;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慷慨用世之人,满腔热血,渴望建一番功业,不甘心彻底退隐。因此,当他身处严州时,反而产生一种近乡情怯之感,发现自己做不到淡漠一切,也无法与日常的庸庸碌碌、琐琐屑屑疏离开。所以,严濑、七里滩等钓台元素,只能存在于他的回忆里,至少回忆会剥离掉一部分现实,然后再补偿性地建构缺失的部分。于是他“借助于回想,事后补充性的回忆,这个伤口可以减缓疼痛,但是不能治愈,治愈的力量来自于回忆的另外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被涤清了时间的痕迹,以及想象的主观和主动的特点”[32],最后将回忆里的严濑、七里滩等钓台元素沉淀为一缕风、一弯月和一舟楫,以润泽他枯竭的灵魂。
(三)民族气节的升华点
严子陵钓台所蕴含的,为南宋旅者钦慕的淡泊名利和节义忠贞的精神,随时代风云突变,上升为民族气节和大义。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冬,宋遗民谢翱登西台恸哭、悼念殉国的文天祥。这是他第三次哭悼文公,“望夫差之台而始哭公焉。又后四年,而哭之于越台。又后五年及今而哭于子陵之台”。此番哭祭,仪式皆备,“与榜人治祭具。须臾雨止,登西台,设主于荒亭隅,再拜跪伏祝毕,号而恸者三,复再拜,起。又念予弱冠时,往来必谒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予且老,江山人物眷焉若失,复东望,泣拜不已……乃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曰……歌阕,竹石俱碎。于是相向感唶”[33]。谢翱选在钓台泣拜文天祥,认为文公的忠肝义胆与严光忠贞节义的人格相契合,这也是对其精神的回应和共鸣。同样“文信公为宋社而死,忠也;晞发(谢翱的字)翁为信公而恸,义也”[34],他们的忠和义,构成整个民族风骨的大经大纬,“成为明末清初遗民心态中最常见的秘传符号”,“晚清民初时期,面临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此一意象又再度复活,成为时代最重要的文学精神之一”[35]。清人严懋功说:“自古胜境名迹,大都地以人传。至以钓台垂名,则史志所载,实为繁伙:如陕西宝鸡县渭河南岸之周吕尚钓台……是皆卓著寰区,有令人慨慕无穷者。其他钓游所在,因以留名者,乃更不可胜数。其其间得诸传记、形诸歌咏者,惟吕尚、韩信、任防诸钓台较为著称,而终不若桐庐钓台之名之尤著。”[36]可见,严子陵钓台不仅仅是中国文学之意象,更是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综上所述,富春江畔的严子陵钓台,从东汉的寻常荒石逐渐发展成南宋时期富有吸引性、典型性和象征性的地标景观。这一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南朝至盛唐,钓台开始走进文人审美视野的初萌期;中唐到北宋,旅者青睐、书写频繁,又贤士大夫建祠以立名教的生发期;南宋得天时之势、拥地利之便、聚人和之力,吸引无数旅者啸歌而来、慕名造访的成熟期。它真正的意义不仅仅是文人们旅途中的必经点,还成为他们文化的朝圣处,心灵的皈依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它又升华为民族精神和风骨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