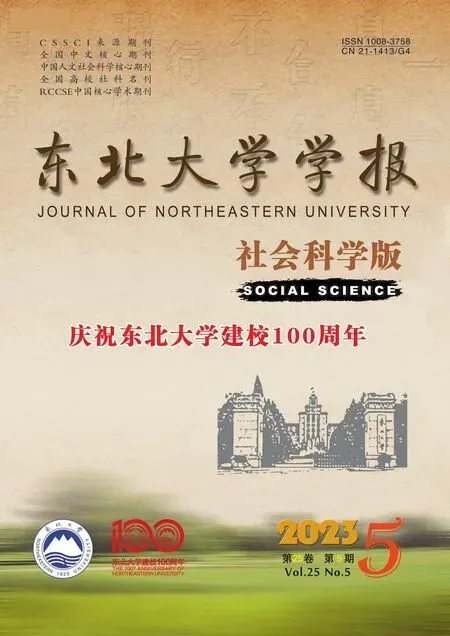情感文体学的理论建构
——认知文学研究的新视角
2024-01-18黄荷
黄 荷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875)
目前,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领域的学者普遍认为情感是一种认知现象,包含我们对他人行为意图或行动目标的评价,而且情感一旦被唤起便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过程[1]。以2002年《认知诗学导论》(CognitivePoetics:AnIntroduction)和《认知文体学:语篇分析中的语言与认知》(CognitiveStylistics:LanguageandCognitioninTextAnalysis)的出版为始,两部著作均强调要探索读者进行文学阅读的认知过程须将读者的情感体验纳入到分析之中。此后的20余年,情感在认知文体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在此期间,认知文体学领域的认知观也悄然发生了从狭义到广义的转变,即从强调读者在获取信息和意义建构过程中所依赖的认知机制,关注文学阅读的理智体验(intellectual experience),转变为强调认知与情感的相互交融,关注文学阅读的情感体验(emotional experience)。自此,情感文体学便出现在文体学研究舞台之上。然而,与语料库文体学等文体学新兴研究领域相比,情感文体学未获得与其前沿地位相匹配的重视,文体学研究者尚未对情感文体学的基本概念作出清晰的界定,对其研究对象、理论框架及与相邻研究领域间的关系等一系列元问题亦未形成系统的认知与共识。为此,本文以回答上述问题为要义,以厘清情感文体学与认知文体学间的研究界限与互补关系为任务,以探讨情感文体学今后的发展方向为旨归。
一、 感受、认知与情感——情感文体学的界定
要理解何为情感文体学及其研究优势,需从理解何为认知文体学及情感文体学与认知文体学间的关系入手。认知文体学旨在通过对文本语言特征的分析来揭示作者、人物及读者的认知方式,其前提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认知方式与读者在真实世界中的认知方式间存在必然的连续性,即文学阅读依赖于人类所共有的认知能力,其理论基础主要是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与之相比,情感文体学通过运用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体验哲学等领域中相关的情感理论和情感研究方法来揭示情感之于文学阅读的重要作用[2],其理论基础主要是“情感科学”(affective science)[3]。由此可见,情感文体学是认知文体学的延展。然而,深入剖析可发现,二者不仅存在明显的研究界限,更存在潜在的互补关系。
认知文体学将读者阅读中的认知加工过程明晰化,系统解释读者为何能形成某种阐释,为解释文学效果提供了更为科学的分析工具,这是认知文体学的研究优势。然而,正是这一研究优势束缚了认知文体学的发展。《认知诗学导论》的作者斯托克维尔(Peter Stockwell)曾言,认知文体学早已因为过于强调“意义性”(meaningfulness)和“信息性”(informativity)忽视文学的情感体验而备受非议[4]4,这也是情感文体学产生的背景与原因。斯托克维尔指出读者进行文学阅读的审美动机往往大于对信息的需求,其试图将读者的移情或反感等情感反应纳入认知分析之中,这一点在其2020年再版的《认知诗学导论》[5]70-85中可明确看出来。在《认知诗学导论》(第二版)中,斯托克维尔新增了“文本肌理与共鸣”“心智建模”和“沉浸感与氛围”等三个章节,专门探讨文学阅读带给读者的情感共鸣,读者对人物情感体验的识解和共情以及文学阅读带来的身临其境之感等核心情感议题。斯托克维尔以行动践行了认知文体学的自我修正,凸显了情感之于文体学研究尤其是认知文体学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由此可以说,情感文体学与认知文体学间的研究界限与互补关系在于前者强调情感对于文学阅读和文体学研究的重要性,后者仅关注文学阅读中的认知过程,而正是情感文体学的出现弥补了认知文体学重认知轻情感的研究趋势。
从广义上来说,文体学研究中探讨读者“参与”(involvement)、“介入”(engagement)、“沉浸”(immersion)、“着迷”(absorption)、“身临其境”(transportation)等阅读现象的研究均属于情感文体学的研究范畴[6]。这类研究往往聚焦读者的情感体验并试图回答文学情感的本源。然而,目前绝大多数进行情感文体学研究的研究者并未对此领域冠以“情感文体学”之名,不同研究者出于不同研究目的使用不同的词汇来描述读者的情感体验。此外,文体学研究领域甚至尚未对“情感”的术语达成共识,常常交替使用emotion、feeling、affect、mood等情感词汇,比如,文学叙事的情感模式(affective model of literary narrative)[7]、情感诗学(a poetics of emotion)[8]、文学阅读的情感模型(a model of emotion in literary reading)[9]、情感美学(an aesthetics of feeling)[10]等。换言之,虽然情感文体学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文体学分支,但其已形成了一个研究集群。为此,一个能够囊括文体学研究领域中所有情感研究范畴的统一术语呼之欲出。
在此背景下,美国认知文学研究学者帕特里克·霍根(Patrick Colm Hogan)在《劳特里奇文体学指南》(TheRoutledgeHandbookofStylistics, 2014)中首创性地使用了“emotional stylistics”来表述情感文体学。霍根将情感文体学视为文体学与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相结合的产物,其研究对象是文学中能够激活读者情感反应的各种诱发条件(eliciting conditions)[11]516。鉴于情感文体学对情感科学(affective science)的依赖,霍根又将情感文体学的术语调整为“affective stylistics”,以此与他提出的情感叙事学(affective narratology)形成呼应[12]。霍根随后又将该术语修改为情感认知文体学(affective-cognitive stylistics),以避免与读者反应批评的倡导者费什(Stanley Fish)提出的感受文体学(affective stylistics)相互混淆[13]。可以说,情感文体学与感受文体学既存在一定的联系,也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感受文体学出现的背景是针对当时文体学领域重文本轻读者的研究趋势,呼吁将文体学研究的重心从文本转向读者,从研究文本的形式特征转向研究文本如何唤起悬念、期待和预测等心理效果。费什指出,所谓的“感受”是指读者在逐字逐句的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原始瞬间反应,既包括“眼泪和刺痛”等带有生理标记的情感反应,也包括读者形成连贯解读的过程、对文本的判断以及观点的修正、对逻辑序列的辨识等认知活动[13]。值得注意的是,费什虽提及了读者的情感反应,但其侧重点在于各种认知过程以及读者在意义建构中的主动参与。从其文章所用的表述可以看出,费什与新批评学者持有类似的观点,对情感作为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仍持有保留态度,认为强调读者的情感将会使“感受文体学”陷入不成熟的“印象主义”批评之中[13]。因此,虽然感受文体学为认知文体学和实验文体学的发轫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情感文体学的前身,但我们应认清其与当前情感文体学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异。为了避免与感受文体学相混淆,本文建议将情感文体学译为“emotional stylistics”。
二、 情感、语言与文体——情感文体学的研究对象
情感文体学的研究对象为何?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澄清文学中情感的表现形式。一直以来,情感在文学中都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其既涉及作者和读者等真实个体的情感,也涉及人物和叙述者等虚构个体的情感;既涉及故事本身的情感内容,也涉及事件安排所带来的情感效果;既涉及诸如悲伤和快乐等可辨识的情感,也涉及相互交织甚至难以言状的复杂情感;既涉及读者的喜恶和偏好等态度评价,也涉及读者对人物的共情、同情和认同等情感的亲疏与距离。
综上,基于文学中情感的表现形式,我们可将情感文体学的研究对象作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情感文体学将文本分析奉为圭臬,聚焦读者与文本间的互动关系,挖掘文学文本中能够唤起读者情感反应的语篇机制。因此,从狭义视角来看,文体学研究者的主要任务便是考察文学中实现情感效应的语言特征,探究情感的再现方式[14]。与之不同,广义上,情感文体学的研究焦点不拘泥于读者的情感反应及其产生的语篇机制,而是囊括所有主体——作者、人物和读者——的情感及其产生的内在机制,涵盖整个阅读过程中的所有情感表现形式。以霍根为例,他提出了由故事(story)、情节(emplotment)、叙述(narration)和文本(verbalization)等多层级构成的小说情感文体学分析模式,区分了情感在每个层级的不同表现形式[11]522-523,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①故事层的情感主要包含依恋、情欲、愤怒、仇恨和傲慢等驱动人物行为的“持续情感”(sustaining emotions)和在故事结尾处所形成的“结果情感”(outcome emotions);②情节层的情感主要包含悬念、好奇和惊讶等关于小说完整性和预判性的情感;③叙述层的情感主要包含读者对叙述者的信任或质疑;④文本层的情感主要包含兴趣和赞叹等审美情感。在霍根看来,所有这些情感的表现形式均可视为情感文体学的研究对象。情感文体学不仅要探索每一类情感的具体表现形式,还要考察不同情感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看出,霍根对文体学的理解与沉浸在文学语言学传统的欧洲文体学研究者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所遵循的是广义的情感文体学。广义的情感文体学不仅抹去了文体学与叙事学间的学科界限,亦消除了“内容与文体”和“故事与话语”这两对术语间的对立,这也充分体现出当前情感文体学在欧洲和北美两大阵容中的不同侧重点及两大阵容间相互借鉴的巨大潜力。
可以看出,不同研究者从不同学科和不同研究目的出发,对情感文体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各不相同。如何从当下学说林立的现状中把握情感文体学的研究对象,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法是从情感文体学与认知文体学的关系中来作出界定。鉴于情感文体学与认知文体学的研究兴趣都是文学阅读的过程,即文本与读者的互动过程,我们可以从语言生成和语言接受两端去区分情感文体学的研究对象:一是聚焦语言生成背后的情感,即以文学文本中人物情感再现为研究对象,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各种语言和文体手段来再现人物的情感体验;二是聚焦语言接受背后的情感,即以读者对人物和文本世界的情感反应为研究对象,探讨读者对文学文本的情感和审美反应。换言之,情感文体学研究可以从文本和读者两个维度展开:从文本的维度出发,情感文体学强调人物情感如何在具体语言表征和文体策略中得以实现;从读者的维度出发,情感文体学强调情感是心智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读者的认知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两种研究对象的共同点在于二者均以文学文本的前景化文体特征为出发点,无论是人物的情感再现,抑或是读者的情感反应,都产生于读者与文本之间自下而上和由上至下的双向互动过程中。需要指出的是,探讨人物的情感再现并不等于忽视作者的存在;相反,作者在对人物情感的研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所谓的人物情感是作者想象的产物,是作者情感与态度的艺术性表达。
三、 情感文体学的主要研究范式
依据前文对情感文体学研究对象的分类,我们可归纳出情感文体学的两类研究范式,即聚焦人物情感的研究范式与聚焦读者情感的研究范式。
1.聚焦人物情感的研究范式:心智解读、仿拟与建模
为何文本中的人物犹如现实中存在的人物一般让读者动容?从认知的角度来解释,这是由我们大脑进行心智解读或他心感知(mind reading)的认知能力所决定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不断地从他人的面部表情、肢体语言和其他外部特征中推测对方的内心意图,以此对其行为作出判断,并相应地调整自身的行为,这种社会认知能力是我们与他人进行正常交流的基础。与之相似,在文学阅读中,读者对虚构人物产生情感反应的机制与我们现实生活中进行心智解读的原理是一致的,读者在推理人物动机的过程中想其所想、感其所感,从而产生共鸣并获得情感体验。鉴于此,美国认知文学研究学者丽萨·桑塞恩(Lisa Zunshine)将心智解读应用于文学分析,开创了认知文学研究的新范式[15]。需要指出的是,桑塞恩认为,情感与文体是反复出现的关键词[16]。她强调,情感在心智解读的过程中无处不在,情感识解是读者进行心智解读的重要维度,同时文学文本也常常呈现出高度前景化和陌生化的文本现象,挑战读者心智解读的能力。可以说,桑塞恩通过对文本的细读使阅读过程中情感认知的过程明晰化,进而揭示了文学情感体验的复杂性和隐蔽性。
事实上,读者在阅读时不仅能够由外及内推断人物的情感状态,亦可由内而外地体会人物的情感。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解释,这种情感体验是大脑的仿拟(simulation)能力所决定的。在此,有必要对仿拟理论进行阐释。仿拟理论由多伦多大学认知心理学家基斯·奥特利(Keith Oatley)提出[17],其核心观点是:在文学阅读过程中,读者犹如演员一般进入一个角色,将自己置于叙事中行动和思维的中心,仿拟故事中人物的一切经历。这样的运作就如同在计算机建模一般,可以让读者得以认清故事中人物的行为、人物与人物之间互动背后的动机和目标。可以说,仿拟理论为解释文学阅读带来沉浸感提供了认知理据,亦被广泛运用到认知文学研究之中[18-19]。
心智解读理论和仿拟理论都聚焦读者对人物情感的识解过程,二者均强调自下而上的文本输入对读者信息加工的重要性。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聚焦读者推理他心的过程,而后者则聚焦读者通过想象重构他心的过程,这也使得二者在文本分析中的优势各有不同。前者能够有效分析文学中独有的思维嵌套现象,将其中涉及到的他心解读和误读机制明晰化,以此挖掘文本的深层主题意义;而后者则能够有效地解释文学阅读的共情现象,阐明读者在阅读中获得的审美和道德体验。当然,进行推理和想象的两个过程在读者的实际阅读过程中往往同时进行,缺一不可。基于此,斯托克维尔将心智解读理论和仿拟理论相结合,提出心智建模(mind-modelling)理论[5]176-193。通过使用建模的概念,斯托克维尔凸显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进行心智解读的主动性和连贯性。换言之,一方面,无论文学文本中呈现出多么奇特和不合常理的心智,读者总是能够主动识别和理解其心智;另一方面,心智解读不单单停留在对人物具体行为进行归因化处理,而是全面构建一个关于人物心智和生活的心理模型。
2.聚焦读者情感的研究范式:注意、共鸣与氛围
倘若将注意力从人物转移到读者,我们则需要回答:为何阅读文学会是一种享受?文学为何打动我们?我们所感受到的难以言说的情感力量是怎么一回事?这些问题均指向文学强烈的感染力和意蕴。然而,这种情感反应和审美体验一直被视为过于主观和难以捕捉,属于停留在读者潜意识层面的心理感受,不是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因此,对这种体验的探讨往往停留在印象式批评,未能遵循行之有效的分析框架。相较之下,情感文体学研究则将目光投向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阅读效果,将其视为可观察、可分析的现象,力求让抽象、模糊和主观的个人感受具象化、精确化和客观化,对文学批评和认知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背景下,斯托克维尔提出的注意-共鸣(attention-resonance)理论[4]17-55,[5]70-85现已成为情感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分析框架,并应用于各种文学文本分析之中。简单来说,该理论的出发点是认知心理学中注意(attention)的概念。认知心理学认为,我们的大脑时刻都在对庞杂的外部刺激进行选择性加工,这种认知过程就是注意。认知心理学往往通过检验实验对象对物体大小、形状和颜色等视觉特征的辨认来研究注意的加工机制。在文学阅读中,唤起读者注意的对象变成了各种文体特征。斯托克维尔将这些特征称为吸引因子(attractor),类似于认知语言学图形与背景(figure and ground)和射体与界标(trajector and landmark)两对概念中的图形和射体成分。该理论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的渐增的情感体验称为“共鸣”(resonance)。这种共鸣体验往往能够在阅读结束后持续存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萦绕于心、挥之不去的感受。吸引因子是一个程度的概念,一个文体特征的吸引程度可以体现在不同维度,具体包括新奇性、施动性、话题性、共情性、明确性、主动性、邻近性、明亮度、饱满度、大小、高度、声响度、危险指数、审美距离、否定性等维度[5]79。通过追踪文学文本中的吸引因子并考察吸引因子维持与变化的规律,我们可以有效解释文学阅读的共鸣效应。
除了共鸣效应以外,斯托克维尔还探讨了另一种由文本操控读者注意力所造成的情感体验——读者所感受到的文本氛围(ambience)[5]201。他将氛围分解为两个维度,即文本的基调(tone)和气氛(atmosphere)。前者与作者或叙述者的声音和文本中再现的思维风格相关,因此可以通过分析指示语标记等语言特征来加以说明;而后者则主要指读者眼里小说世界中的环境气氛,这种感受虽然切实存在但却难以得到较为客观的解释。为此,斯托克维尔运用认知语法中的认知参照点、认知域和语义启动等概念来阐明这种情感体验。根据认知语法,一个词汇具有若干项约定俗成的意义,这些意义构成词汇的语义网络或认知域。在认知域中,不同意义的显著度不同,显著度最高的意义往往是一个词汇的本义,构成该词的原型意义;相较之下,显著度较低的意义往往是该词的联想意义,与文化语境和个人经历紧密相连。与此同时,认知域中显著度较低的意义虽未得到正式启动,但仍停留在读者认知加工的背景之中,形成一种光环效应(aura effect)。当这些未被启动但仍潜在的意义被反复唤起时,就形成了所谓的文本氛围。
四、 情感文体学研究前景展望
如前所述,情感文体学是文体学研究的新兴领域,具有显著的跨学科性,其与广义的认知文学研究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是新的学科增长点。其增长潜力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对真实读者阅读体验的剖析、人物情感的再现及文学认知和情感功能的深入挖掘。
首先,关于对真实读者阅读体验的剖析。一直以来,文学批评领域的研究者始终将目光聚焦在理想读者上,从而忽视真实读者的阅读体验。情感文体学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唯理想读者至上的倾向,将研究重心转向真实读者。对于真实读者而言,他们关心的往往是文学的魅力是什么?为何文学能够安抚现实中受伤的心灵?为何文学能够点亮凄惨的现实生活?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均指向了阅读的本质,即真实读者的情感反应与审美体验,而这也是文学批评领域一直所欠深入研究之处。随着情感文体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重视真实读者的体验,并通过设计实验或问卷调查等方式来收集真实读者的阅读体验,以此从认知的视角审视文学的情感体验,明晰我们习以为常却难以言表的阅读体验,尤其是阅读过程中出现在潜意识层面的情感反应。
其次,关于人物情感的再现。情感文体学以呈现文学文本中人物情感再现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主要任务。通过构建读者与文本间自下而上和由上至下的双向互动机制,情感文体学搭建了文学批评与认知科学之间的桥梁。文学批评领域的人物研究一直存在人物符号论和人物摹仿论两种极度分化的观点,或将人物视为黑白的文字符号,从而拒绝文本内未直接出现的人物信息,或将任务等同于真实存在的个体,过度想象文本外虚构的人物意识。情感文体学的出现为传统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和思路。根据情感文体学,对人物形象的解读由读者的认知能力所决定,同时,读者对人物的认知不仅受到文本内部信息的影响,还与读者在日常生活中用来理解他人的心智解读能力有着直接联系。
最后,关于文学认知和情感功能的深入挖掘。情感文体学研究将不再单向运用情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文学情感,而是反过来从文学情感观照情感科学。霍根在其专著《文学教会我们认识情感》(WhatLiteratureTeachesUsAboutEmotion, 2011)中指出,文学是一种情感书写,是对各种复杂情景中具体情感进行精彩书写,为我们进行情感研究提供了绝佳语料[20]。与其他学科研究情感的学者相比,文学研究者可以依赖经典文学文本中的情感书写,而不用特意编撰出脱离实际交流语境的情感场景作为分析语料。
五、 结 语
可以说,情感文体学是认知文学研究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关注的对象——人物情感与读者情感,指向了阅读理解过程中的深度阅读和高阶认知,对进一步理解文学本质和文学的审美价值有着重要参考意义。此外,借助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情感理论和研究方法,情感文体学研究回答了文学为何打动人心以及文学如何打动人心这一古老的话题,不仅刷新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学阅读本质的认识,也让我们得以从经典文学文本中挖掘出新的阐释,读出新意和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