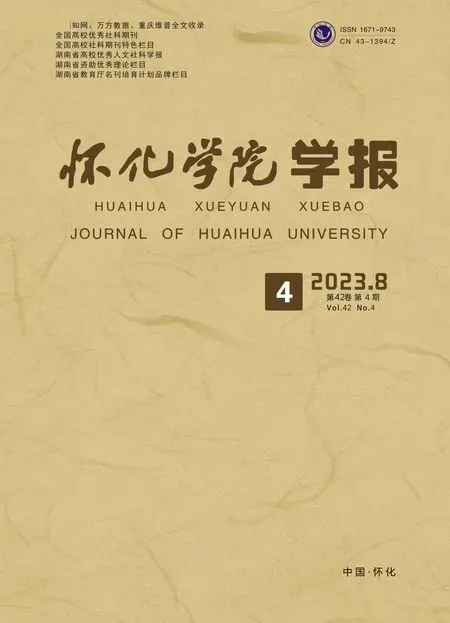秦汉家庭劳动性别分工研究
2024-01-17沈名昭
沈名昭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81)
关于秦汉时期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活动、性别分工以及涉及父权制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了一些成果①。目前,对父权制的讨论仍较少,但对这一命题也已形成一定的认识。对秦汉时代男女性别的分工习惯采用“公—私”“内—外”的分法[1],但这是基于屋宅空间和礼制规定所做的区分,却拆分了家庭实际包含的生产和分工。故本文将对讨论的范围进行重新分类。
家庭是国家、社会可以分割的最小单位,也是各种活动运行的基本场域。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由联合家庭组成宗族共同体是当时最普遍的基层单位,父子兄弟“同室内息”则是商鞅变法前秦国最常见的家庭生活方式。而在秦国商鞅变法之后,分异令与名田宅制的实行从两个方向促进了大型家庭的析分,大量的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涌现,主要的家庭组成人口是“夫妻子”或“父母夫妻子”,这样的家庭在秦及西汉时期被承袭下来并成为主流。在东汉,联合家庭的比例有所上升,而主干家庭仍占据较大比例。李根蟠认为有必要注意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之间的流转,随着时间推移,家庭成员会发生增减、析分,同时也要注意阶层情况,不同阶层的家庭结构可能很不一样。[2]但不论家庭结构如何变换,家庭内的性别分工还是存在着清晰的性别分野。从家庭劳动分工上看,以时间为坐标轴,先秦秦汉前期与秦汉后期呈现相当不同的面貌:越靠近先秦秦汉的早期,女性与男性的劳动分工差异越小,女性可广泛地参与到社会与家庭的各种劳动中;越靠近秦汉后期,家庭性别分工越符合父权制的期待,女性的劳动参与迅速收缩,且被驱出主要的劳动部门,而父权制在这一变化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一、秦汉家庭及其性别分工
“劳动”本用来指工业社会中的无产者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力而换取报酬的行为[3],但本文采取其扩大含义,将中国古代人民付出的各种维持家庭经济运转的劳力都称作“劳动”。在秦汉时代,最主要的劳动力是农民,而在农民家庭中,农耕、纺织等属于常见的、典型的劳动。同时,还有家庭内劳动(做饭、洗衣、清洁等家务)、再生产劳动(本文主要指生育)等劳动,这些劳动常常不被看作是劳动。②本文将上述劳动类型进行重新分类,并使用“本位劳动”和“边缘劳动”来指称。
本位劳动是家庭中最主要的、价值可计算的、产品可进行市场交换的劳动。秦汉国家以耕织为本,《后汉书》有“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受其寒”[4]之语,反映出耕、织是小农经济的主要内容。其劳动产品也是国家赋税的主要内容,因而耕与织是本文要讨论的最典型的本位劳动。此外,其劳动产品往往是昭然可见、被广泛承认的、易于计量且常被用来进行市场交换,其价值量往往是明显且可视的,所以本位劳动常常被作为家庭收入的计量主体和标准,基于此特性,其又可称为“有形劳动”。
边缘劳动是家庭中非主要的、价值模糊难辨的、产品大多无形或大部分不进行市场交换的劳动。“再生产劳动”“家庭内劳动”都属于本位劳动被确定之后所剩余的部分,是与国家赋税离得较远、在制度上不被重视的劳动。同时,由于边缘劳动的价值量往往被隐没,其劳动的性质极易被忽视,所以其又可称为“隐形劳动”。这一重新分类与传统的“内外”分类是极为不同的,“内外”作为一种礼制规定被提出,它实际上是父权制最终想达到的目标。
(一)“内外”之别的秦汉家庭劳动性别分工
我国古代的性别分工在周代就有文字记载,男子应从事的是“外事”,是“国之大事”、“祀与戎”、军政外交、籍田农耕之类的事物,而女性应从事的是“内事”,是桑蚕纺绩之类的屋宅之内的事,这或许是内外分别之滥觞。[1]至春秋战国时期,也同样有这样的规定。《墨子》卷一:“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5]《孟子》卷六:“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6]《管子》卷二二《海王》:“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7]《管子》卷二三《揆度》:“上农挟五,中农挟四,下农挟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农有常业,女有常事。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8]不论作为社会性别分工还是家庭性别分工,妇女都被认为应从事“内事”,这在各家思想中都有所体现。及至秦汉,这一理念得以延续。《后汉书》载《浮侈篇》注引《文子》曰:“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力者,无以衣形。’”[4]而“不修中馈,休其蚕织”[9]则指妇女在家不从事厨事与纺织,这被当做反面例子举出。从以上文献可知,“内外”“男耕女织”“男耕女爨”的礼制规定形成较早,且代代承袭。
但秦汉时代女性的劳动分工原本并不限于纺织、中馈,她们的工作曾经多种多样;而“内外”分别最初也并没有那么严格,妇女的工作都可走出家门而延伸到社会当中。以下事例即可看出女性对“内外”架构的突破。纺织、厨爨是妇女从事的最普遍的家内工作,但它们常常超出家门的界限。《韩诗外传》卷二载:“鲁监门之女婴相从绩,中夜而泣涕。”[10]《汉书》载,冬季“妇人同巷,相从夜绩”[11]。可见纺织之事在当时并非妇女封闭于家庭之内的活动。“中馈”中厨爨之事也是如此,如四川彭县画像砖就描绘了妇女采芋的场面,而芋头就是当时家庭最普遍的食材[12]。《汉书》载朱买臣“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13];《后汉书》有大司徒直王良之妻“布裙曳柴,从田中归”[14]。然后是烹饪厨事:韩信寄食南昌亭长家,“亭长妻苦之,乃晨炊蓐食”[15];刘邦未发迹时“时时与宾客过其丘嫂食。嫂厌叔与客来,阳为羹尽,轑釜”[16]。由于秦汉时代的市场还不发达,这些在现代看来可以通过货币购买的材料以及通过社会分工分化出去的劳动过程,在当时都是“家庭内劳动”的一部分,而这些工作也并不完全是家门之内的事,它们已然超出“内事”的空间范围。
除了以上两项礼制规定内的工作外,秦汉妇女从事的许多工作都直接超出了“内事”的范围。吕后、窦太后、窦太主、王太后以及东汉诸多临朝称制的太后们在政坛上大显身手;巴寡妇清、乌氏倮等女性依靠自己的才能富甲一方,其财力让秦始皇都为之侧目;相士许负可以相面的才能封侯。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其他的工作。如战国时期,女性就曾参与到军队中,《商君书》卷三《兵守》载,“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陈而待敌”,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17]吴王阖闾令孙武以宫中妇人“小试勒兵”,孙子以军令行之,最后使“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18]秦汉时期也有这样的记录,《史记》载楚汉大战刘邦被困荥阳时,“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楚因击之,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去”[19]。《汉书》载:“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20]而《后汉书》也有“关西诸郡,颇习兵事,自顷以来,数与羌战,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21]的语句,一些学者认为这就是汉代女性从军的实例[22]。此外,秦汉妇女也曾广泛参与到农耕中。《史记》记载,吕后昔年常常“与两子居田中耨”[23];《后汉书》,庞公“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24];高凤“家以农亩为业”,其“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25]考古资料则更加直观地展现了女性承担农耕劳动的景象,如南阳汉画像石绘农妇肩扛一锄,柄端系罐,锄头挂篮,农妇送食田中还要兼及劳作;[26]山东藤家岭汉画像砖描绘农田上有五人耕作,其中有三位妇女锄地,女子人数比男子还多。[27]
上述材料反映的女性突破“内外”礼制规定而在外从事的社会职业和社会劳作有很多,并且在家庭内部,女性的劳动既有“本位的”也有“边缘的”,且秦汉妇女曾经进行的劳作应该还不止这些。从此处可以看出,尽管从周代开始就基本形成了性别分工的规定,然而从周到秦汉,这一规定的约束力似乎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女性能够突破礼制的限制,进行各种职业和劳作。从这个角度来看,秦汉妇女地位在帝制时代是相对较高的。但在政治上取得优势的男性需要巩固其自身地位,而父权制统治也需要借助政权力量伸张。为了拉开男性与女性的差距并更彻底地贯彻父权制统治,父权制对家庭性别分工实施了干预,使得秦汉妇女的劳动分工逐渐走上其所期待的方向。
(二)以父权制家庭的外部干预为主的秦汉家庭性别分工
先秦至秦汉初期仍处在父系社会未完全成熟的时代,仍然存在大量母系时代的特征,牟润孙称其为“母系制的遗存”[28],赘婚、女性重组家庭都与此有关。为了保证男性主导家庭内部性别分工,父权制采取了外部干预的方式,借助武力与法令来达到目的,对赘婚与女性重组家庭进行严格限制。
战国与秦汉时,大量的赘婚家庭出现,魏国、秦汉都出现打击赘婚的法令也证明这并非少数情况。《睡虎地秦简》的《为吏之道》篇附录了魏国《魏户律》与《魏奔命律》,《魏户律》曰:“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民或弃邑居野,入人孤寡,徼人妇女……叚(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而《魏奔命律》曰:“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叚(假)门逆旅,赘婿后父,或率民不作,不治室屋……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29]秦统一后,统治者对赘婿的打击面扩大到整个赘婿群体而不只是“赘婿后父”,并加重了处罚力度,《史记》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30],即征发赘婿谪戍。汉朝则将“赘婿”列入“七科谪”,《汉书》载武帝“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发天下七科谪”注引张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31]打击赘婚即是打击女性主导型家庭,并巩固男性主导型家庭。
秦代同样还有限制女性重组家庭的法令。杨振红通过研究发现,《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简001-008 可编联成一条叫做“戊寅令”的法令:“禁毋敢谓母之后夫叚(假)父,不同父者毋敢相仁?为兄、姊、弟,犯令者耐隶臣妾……后夫、后夫子及予所与奸者,犯令及受者皆与盗同法。母更嫁,子敢以其财予母之后夫、后夫子者弃市,其受者与盗同法……有后夫者不得告辠(罪)其前夫子……女子寡,有子及毋子而欲毋稼(嫁)者,许之。”[32]这明显是保证男性家庭成员的财产继承与地位,但却并未对男性做出限制。在确立了男性主导型家庭之后,绝大部分男性在各自的家庭单位中建立了相对权威,致使父权制拥有了进一步强化的优势与可能性。
战国秦汉有许多妇女进入军队或参加军事活动的记录。《墨子》之《城守》就有记载:“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广五百步之队,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四千人而足以应之,此守术之术也。”[33]田单御燕,将士卒“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又“使老弱女子乘城”,终致燕军败走。[34]而秦汉时期也有上文提及的《汉书·贾捐之传》《后汉书·郑太传》的女子参军故事。虽然女性曾经投身于军事行动中,但父权制介入之后,女性在军事部门开始被边缘化,甚至最终退出。《汉书》中,李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35]这即是一种“女性随军将于军不利”的观念建构,是一种父权制意识形态。而《汉书》:“丁男被甲,丁女转输。”[36]《三国志》:“男子当战,女子当运。”[37]《后汉书》:“男子疲于战陈,妻女劳于转运。”[38]这三条记录则反映了父权制在现实层面将女性的军事分工从作战、守卫转变为运输、后勤。《三国志》载吕布率军攻曹操,“(曹操)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而曹操则领士卒“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39]因此,汉末时女性参军的记录已较为罕见,与战国秦汉初时妇女参战的普遍情景形成鲜明对比。
彭卫、杨振红认为,“女性是远离军事职业的群体”[40]。但从上述可知,女性远离军事职业经历了被动退出的过程。在战国时代,女性参军作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然而秦至汉末,女性参军的历史记述越趋减少,这反映了父权制影响下女性在军事部门的被边缘化趋势。同时,武力是帝国政治赖以生存的核心之一,女性在军事上的参与也意味着女性对武力的部分掌握,这对于父权制来说是绝对无法忍受的,因此遏制女性进入军事部门、将女性逐回家庭中就是父权制的要务了。当女性与武力绝缘之后,父权制终于达到了对国家机器和强制力的完全掌握,这也为其从家庭外部施加干预提供了基础。
政治象征同样也是对性别分工进行干预的方式。如《汉书》载:“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诏曰:‘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41]西汉文帝时开立皇后亲桑礼仪。又《续汉书》志第四《礼仪志上》记载,仲春“是月,皇后帅公卿诸侯夫人蚕。祠先蚕,礼以少牢。注引《汉旧仪》曰:‘春桑生而皇后(视)[亲]桑于菀中。蚕室养蚕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今)[祭]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凡二神。’”[42]还有《汉书》中记载景帝所下的诏书:“朕亲耕,后亲桑。”[43]这都是以政治象征作为性别分工的标准与榜样。文帝、景帝之世距离高帝时期较近,但此时的“朕亲耕,后亲桑”和当年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44]相比较显然是一种不同的表现了。
同样,政治象征的方法也可以用于边缘劳动的安排,并且还可以配合社会意识形态武器共同发生作用。如对“浣衣”这项劳动,《续汉书》志二六《百官三》载,少府属官御府令“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补浣之属”[45],即宫廷中的浣衣工作被安排给了宫中的婢女。如果说秦汉国家是以皇室为中心扩展出去的名为“家天下”的差序格局,那么宫廷之内的皇室就是那个“最高家庭”。在皇室这个家庭中,边缘劳动之一的浣衣部门就以制度方式被固定在了女性身上,虽然承担这一任务的不是主妇(皇后及嫔御),但那也只是因为有奴婢代劳,其劳动被以阶级压迫的形式转嫁出去了而已,若把这个差序推至其末梢——也就是一个个平民家庭之中,那么承担这一任务的就无疑是主妇了。虽然这一制度也不是直接针对全部家庭的,但制度是沿着权力结构这条路径向下传导的,其影响力是广布于天下的。同理,“官婢浣衣”这种性别分工也不是局限于宫廷内的,而是要施于全社会的。
意识形态干预表现为思想武器的干预,往往以礼仪教化、道德伦理的形式出现。先秦时即有“五伦”,《孟子》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46]它强调夫妇是“有别”的,这为性别分工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它未规定夫妇之间是怎样的“有别”,因而又具有模糊性,且儒家在先秦至秦时并非“正统”,因此它的规定也就收效甚微。继承这一思想的是东汉的班昭,她撰述的《女诫》发展了“五伦”之说,以“妇行”规定家庭中的女性必须“盥浣尘秽”“专心纺绩”“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既要求女性退居“本位劳动”中的纺织部门,还要求女性自觉包揽家庭中的“边缘劳动”。[47]《女诫》的本质就是对父权制主导的性别分工进行了意识形态上的固定,并内化成为女性对自己的要求。
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缔造者几乎都来自于上层阶级,其中不乏高门显贵,班昭就是其中的一员。意识形态常常自上而下传播,因为社会中的所有阶层都以高一阶层的风尚为榜样,因而社会中处于最高阶层的风尚与意识形态就以这种方式贯穿于全社会,塑造着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女诫》原本是班昭撰写的家训,但经人不断传抄,最后竟成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父权制就借助着这股力量间接影响着全社会。为何班昭身为女性,却会与父权制合谋来规训女性自身?笔者认为,不能忽视的是她的“代理身份”。班昭所在的家庭居于所谓的“有闲阶级”③之中,有闲家庭中的妇女因其微乎其微的经济贡献而完全处于依附地位,妻妾女儿甚至和奴仆一样都沦为以父为主的家长的财产。在这样的家庭中,班昭这类“代理有闲阶级”看似是特权阶级,但相比于一般家庭的女性,她们对父权的依赖性更强,父权制对她们的改造也更深。从性别压迫这个角度来看,上层贵妇与平民妇女所受到的父权制压迫从实质上相差不多,但从家庭实际地位来看,平民妇女仍具有一定话语权,而班昭这类上层妇女却被迫成为自身性别的背叛者。这就不难理解,为何部分女性也参与到父权压迫之中,且产出《女诫》这样的意识形态工具的也是女性了。
二、父权制干预下秦汉家庭劳动分工的变化
借助家庭外部的优势与强制力,男性已经取得主导性别分工的条件,那么父权制如何安排分工、如何巩固并加强这种安排,则需要通过家庭内部干预的路径来达到。
(一)父权制使妇女在农耕部门被边缘化并丧失劳动价值
前已提及秦汉妇女曾广泛参与农耕,如吕后、庞公妻、高凤妻等等,而《论衡》卷四七《乱龙》记汉季立春祀仪“立春东耕,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锄”[48]也证明了男女曾在田间共同耕耘。当时还有关于妇女刈麦的童谣,如《后汉书·五行志》载:“桓帝之初,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每战常负,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49]从考古资料来看,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简牍记录了从事耕种的“田者”有大奴大婢各4 人,同时墓中也出土了许多手持农具人俑,其中女俑11 个,男俑6 个,女俑的数量几乎是男俑的两倍;[50]江陵凤凰山8 号汉墓遣策中记有婢19 人,其中“操柤(锄)者”有8 人,约占总人数一半。[51]以上证明,在秦汉时代的前期,妇女曾经居于农耕部门的中心位置,她们的劳动曾和男性无甚分别。但到汉代后期,妇女在农耕部门的劳作由中心位置向边缘转移。《汉书》卷二四《食货上》载:“同我妇子,馌彼南亩。注引师古曰:‘此《豳诗·七月》之章也。馌,馈也……农人无不举足而耕也,则其妇与子同以食来至南亩治田之处而馈之也。’”[52]《三国志》卷二三《魏书·常林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常林)带经耕锄。其妻常自馈饷之,林虽在田野,其相敬如宾。”[53]河南南阳汉画像石,其上描绘了男性农夫除草,妇女持壶浆于旁的景象[54];而山东滕县画像石则绘有妇女挑担送餐的画面[55]。这些均反映出妇女由“耕作”转为“馈饷”的辅助工作,已与《论衡》所描述的“秉耒把锄”大相径庭。进一步说,妇女在家庭收入中的贡献比例大大削弱,这成为以父为主家长安排性别分工最有力的一个理由。
(二)妇女对边缘劳动的完全承担与生产力的削弱
在男性取得家庭中的核心生产部门之后,配合家庭外部干预,妇女的生产力被“削弱”,父权制开始进一步安排家庭内性别分工——让女性完全承担边缘劳动。秦汉女性事实上承担了大部分的边缘劳动。首先“家庭内劳动”。除了前文提及的“中馈”之外,女性还要“浣洗”,《韩诗外传》卷一载,孔子南游,适楚,至于阿谷之隧,有处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妇人其可与言矣乎!”[56]《史记》载:韩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注引韦昭曰:‘以水击絮为漂,故曰漂母。’”[57]《四民月令》“八月”条提到女子有“浣故”,即浣衣的任务;《后汉书》:“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遁水”[58]。其次,还有舂米,江苏泗洪汉画像石描绘的两个农妇,一个用木杵舂米,一个双手握横木弓步推砻[59];重庆化龙桥东汉墓也出土了持杵捣舂的女俑[60]。再次,妇女还要进行手工业制作,睡虎地11 号秦墓两件漆杯分别刻有“小女子”“大女子臧”“大女子军”。此外还有“钱里大女子”、“大女子”等,这些女性即是漆器的制作者[61]。还编席织履,《汉书》载“(翟方进)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履以给方进进读”[62];《三国志》载:“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63]缝制衣装也是妇女必须承担的劳动,居延汉简有“妻治裘”的文字,《汉书》记载女子“桑蚕织纴纺绩缝补”为王莽时期商业税征收项目之一[64]。
除上述劳动外,妇女还要包揽所有的“再生产劳动”,是包含生育在内的一系列生产培育劳动力的劳动。首先是哺乳,汉代母亲常跪坐哺乳,四川彭县出土了妇人乳儿俑,妇人左手怀抱婴儿,右手扶喂孩子,孩子还戴了围兜。彭县也出土了4 尊相同类型的哺乳俑,它们来自3 个墓葬之中,这足见妇女哺乳之普遍性和日常性。[65]其次是给孩子喂食,《易林》卷一《乾之第一》“同人”云:“子号索哺,母行求食;反见空巢,訾我长息。”[66]卷十《履之第十》“同人”云:“婴孩求乳,母归其子,黄麑悦喜,自乐甘饵”[67]。秦汉母亲常常要将孩子襁负于背,时时看顾。《史记》孔子曰:“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68]《史记·卫将军列传》正义曰:“襁长尺二寸,阔八尺,以约小二于背。”[69]山东嘉祥汉代画像石绘有母亲负子,婴儿被襁束于母亲背上的情景,可见秦汉妇女时常要将婴儿带在身边照顾。甚至在妇女进行本位劳动时,也同时要照顾孩子。如武梁祠后石室第一画像石绘有一妇人在田中劳动,一手抱孩子,另一只手劳作的情景。[70]江苏铜山汉画像石描绘了4位妇女纺织的画面,其中一位妇女抱着婴孩。还有类似情景也出现在江苏沛县汉画像石中[71]。将孩子带在身边也为了看护孩子的安全,《汉书》载有“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72],“垂堂”即坐在厅堂之边缘,“骑衡”则指骑于横栏之上,这些行为可能危及孩子生命,所以需要母亲时常看护。东汉《鲜于璜碑》记载鲜于璜幼年“在母不瘽,在师不烦”[73]。再次,秦汉妇女还要保障婴儿的清洁卫生,《新论·辨惑》载吕仲子婢女死后留下四岁女儿,注引《太平御览》:“(婢女)葬后数来抚循之,亦能为儿沐头浣濯”[74]。《后汉书》记载了和熹皇后邓绥五岁时,其祖母“太傅夫人爱之,自为翦发”之事[75]。
彭卫、杨振红通过观察四川乐山东汉墓与重庆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石后认为,秦汉时期绝大部分的育儿工作都由妇女承担,而男性基本是缺位的。[76]因为在关于“家庭内劳动”的历史记述中,几乎看不到男性的身影。还需要看到的是,妇女由于同时承担本位劳动与边缘劳动,她们需要花费巨大的时间与精力进行纺绩、浣衣、采集、馈饷、育儿、清扫等劳动。根据冯立天的调查,在拥有洗衣机、煤气灶等高科技设备的情况下,现代都市女性的日均休息时间略少于男性。[77]以现代科技发展水平以及科技对家务劳动的替代程度,女性休息时间尚且少于男性,那么若以秦汉时代的科技水平来衡量,妇女的休息时间可能更短。而男性则认为边缘劳动理所应当由妇女承担,如《说文解字》第十二篇下,女部“妇”字条:“妇,服也。从女从帚洒扫也。注曰:‘妇,主服事人者也。’又‘妇人,伏于人也。’”[78]又有《汉书》载,吕公欲将女儿吕雉嫁与刘邦为“箕帚妾”[79]。这都反映出当时男性对边缘劳动的安排痕迹及其倨傲姿态。
(三)妇女劳动的隐没与父权制统治的循环
由于父权制的干预与塑造,妇女从事的劳动常常被隐没。此处的“隐没”涉及两方面:劳动性质的隐没与劳动价值的隐没。劳动性质的隐没指的是妇女从事的边缘劳动往往不被人看作是劳动,即其作为“劳动”的性质被遮蔽了。劳动性质如依据“是否可市场化”来判定,边缘劳动中包含的“家庭内劳动”与“再生产劳动”都是“劳动”无疑。因为当时出现了雇佣劳动,而这些雇佣劳动常常被用来进行边缘劳动,比如《搜神记》“张车子”条:“有张妪者,尝往周家佣赁,野合,有身,月满,当孕,便遣出外,驻车屋下,产得儿。”[80]《搜神记》“郭巨”条:“巨独与母出居客舍,夫妇佣赁,以给供养。”[81]《太平御览》卷四一一引《东观汉记》说姜诗“与妇佣作养母”[82]。这些雇佣劳动的出现代表这些活计都是可被用于市场交换的,然而父权制干预过后,这一劳动性质被转化成了自然生成的义务。正如上引《说文解字》“妇”字条所述,其是家庭中弱势对强势的服从,男性通过家庭外部干预的方式取得了家庭中的强势地位。因此拥有性别分工的主导条件;“从女从帚洒扫也”既是性别分工在物质层面的实现,也是在意识层面的建构,父权制将边缘劳动作为一种责任、义务、经验附加于女性身上,让女性从思想上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甚至将这种强制性分配与压迫转化为指代妇女的字符本身。
对于妇女纺织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值,彭卫、杨振红根据《九章算术》的材料计算出,一位秦汉妇女在理论上一年可织1012.5 尺布,约合25 匹。结合汉代每匹布价格浮动于300~400 钱的情况,取折中价350 钱,则一年可赚8750 钱。加上其他因素带来的影响,将收入减半,也有4000 钱以上。结合妇女进行的其他生产劳动,他们推算出,秦汉女性(主妇)至少承担了1/3以上的家庭收入。[83]纺织贡献之所以折半计算,就是因为妇女一天中的相当一部分时间被边缘劳动占用,若男性能够分担一部分,妇女纺织能够创造的贡献只会更多。基于前述,这些边缘劳动的许多成果无法用市场交换的劳动产品体现,同时,其产品往往在家庭中被当场消费,这使得边缘劳动的劳动价值被隐没。纺织贡献被转移到边缘劳动中,其价值又被隐没,最终导致妇女的家庭贡献也随之隐没。
更进一步看,父权制通过家庭内、外干预相配合的方式创造出了一个内循环:男性先决优势主导性别分工→将女性从农耕部门边缘化从而削弱其家庭贡献→女性话语权降低→将边缘劳动安排在女性身上→边缘劳动挤占女性纺织的时间与精力,家庭贡献进一步“下降”→女性话语权更加微弱→女性被安排到更多“边缘劳动”……这一循环能够不断运转,并自我加强巩固,最终受益者总是男性与父权制,被压迫者总是女性,这一循环也成为父权制实施其统治的物质基础。
总之,对于秦汉时期的父权制与性别分工研究,学界一般采用“内外”的传统分析框架,但这一框架并不符合实际,它打碎了家庭内实际的劳动与分工。家庭内的劳动可重新区分为本位劳动与边缘劳动,前者是家庭中最主要的、价值可计算的、产品可进行市场交换的劳动,而后者是家庭中非主要的、价值模糊难辨的、产品大多无形或大部分不进行市场交换的劳动。在周代确立“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后,两性分工在社会与家庭中还未呈现出明显区别,越靠近先秦秦汉的前期,越能发现女性在各种领域活跃的迹象,这表明秦汉时期的性别分工发生了实际的变动。这一变动是为满足父权制进一步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同时也是在父权制的主导下逐渐完成的。父权制利用其相对优势地位,通过家庭外部和内部两条路径对家庭劳动的性别分工施加干预,逐步将妇女由家庭外推向家庭内,由本位劳动部门推向边缘劳动部门,并且在家庭内部形成了一个可以循环的系统,这个系统不断对父权制进行巩固与强化。妇女则由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被迫走上了父权制安排的道路,并且最终使得两性地位差距进一步拉大。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被动性在不同的阶层表现出不同的样貌,越高阶层的妇女其被动性反而更强,这使得她们被改造成父权制的工具,形成了女性自己规训自己的奇观。
注释:
①目前对秦汉妇女经济活动、性别分工以及父权制有所涉及且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杜芳琴:“华夏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浙江学刊》,1998 第3 期;管红:“论秦汉女织”,《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 第2 期;彭卫:“汉代女性的工作”,《史学月刊》,2009 第7 期;徐畅:“秦汉时期的‘夜作’”,《历史研究》,2010 第4 期:70-86+190;彭卫,杨振红:《中国妇女通史·秦汉卷》.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
②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德尔菲创见性地提出“家庭内劳动”一词,用来指称古代农耕“家庭中进行的无偿劳动”,工业社会将农耕时代的部分“家庭内劳动”市场化之后,家庭中剩下的就成为“家务劳动”。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认可并发展了德尔菲的观点,提出不仅“家庭内劳动”“家务劳动”属于“劳动”,从“可市场化”这一标准来看,劳动力的再生产同样也是“劳动”,因此她进一步主张“再生产劳动”等概念。参看Christine Delphy,Diana Leonard.Close to Home: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s Oppression,Amherst: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4:78;[日]上野千鹤子,邹韵,薛梅:《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27-28.
③“有闲阶级”指称的是那些拥有大量资产、不需要有固定职业、不从事生产性劳动而大量参与社会活动的阶级。其特点是不参与“本位劳动”,也不用承担“边缘劳动”,这一阶级的构成人员都是男性。“代理有闲阶级”指称的则是有闲阶级的妻妾、奴仆。他们因服务于有闲阶级而脱离生产性劳动(“本位劳动”),但未脱离“边缘劳动”,其作用在于使有闲阶级得到享乐或使有闲阶级更有荣誉。参看[美]托斯丹·邦德·凡勃仑:《有闲阶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