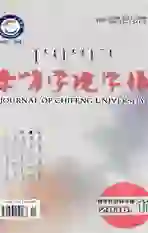压迫、疯癫和“胜利”
2017-01-05李俊风
李俊风
摘 要:《黄色墙纸》是美国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最著名的代表作,也是女性批评者所探索的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品之一。小说叙述者从多种角度展现了所遭受到的压迫和她的疯癫,揭示父权制社会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摧残和压迫。虽然《黄色墙纸》的叙述者的反抗及“胜利”具有不彻底性,但是,吉尔曼用反传统的手法,在叙述者逐步迈向疯癫的过程中叙述其不断变化的心理状态,借助一个疯癫女人之口,表达了女性追求独立和自由的愿望,为后人对女性主义的探索开辟了道路。
关键词:《黄色墙纸》;压迫;疯癫;胜利;女性主义;父权制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137-03
夏洛特·帕金森·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1860-1935)是美国女作家,同时也是美国首次女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吉尔曼在女儿出生后得了产后忧郁症,当时著名的精神科专家塞拉斯·维尔·米切尔对她进行了“休息疗法”:让她休息,停止一切脑力劳动和社交活动。结果这种与世隔绝的治疗方法,差点让她崩溃,因此,吉尔曼不得不放弃了这种治疗,积极参加社交活动,反而渐渐痊愈了。
吉尔曼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黄色墙纸》,相当于一部半自传体小说。《黄色墙纸》是一部第一人称日记体的中篇小说,由9篇日记组成。被作者隐去姓名的女主人公就是小说的叙述者,女主人公作为一名中产阶级的知识女性,由于得了产后忧郁症,被丈夫安排在一栋乡村别墅里强制性地进行“休息疗法”,因为女主人公的精神世界遭受到了严重的压抑,所以才最终走向了疯癫崩溃的边缘。这部小说刚出版时不被世人所接受,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才重新得到了文学批评界的重视,成为表现女性主义的一部重要作品。以往对《黄色墙纸》的研究者大多数是从象征和意象角度入手来对小说中所蕴含的女性主义进行探析,本文以压迫、疯癫和“胜利”为切入点,来探析和解读《黄色墙纸》中的女性主义。
正如西蒙·德·波伏娃所说:“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后天才成了女人。”[1]这句话的意思表明,由于受到了后天男权社会的压迫,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才处于被动的地位。在《黄色墙纸》中,叙述者和丈夫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种地位的差异使得她处处遭受到丈夫的压迫。丈夫像对待孩子一样地俯视她,操纵着她的生活轨迹,并习惯在她的称呼前加个“小”,比如“幸福的小鹅”“小宝贝”等等。这些称呼表明了丈夫把她置于如同弱者的从属位置,并没有把她看成一个有自己独立想法的成年人,不但对她内心的真实感受及想法充耳不闻,而且对她写作的才华及愿望也是置若罔闻。然而,对于叙述者来说,起初,她的一半意识知道丈夫的“休息疗法”是错误的,但她的另一半意识却屈服于丈夫的身份和权威。当叙述者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阴暗的禁闭,身心受尽冰冷的煎熬之后,渐渐疯癫,进入到疯狂的幻想当中,最终歇斯底里。小说叙述者以疯癫的形式来争取自己身心的自由和“胜利”。
一、叙述者所遭受的种种压迫
小说中的叙述者所遭受到的压迫主要有3种:首先是居住环境的压迫。故事发生在远离各种社交的别墅里,让叙述者觉得有些诡异。虽然她对楼下窗外开满玫瑰花的房间很向往,但丈夫约翰并没有顾及叙述者“我”的感受,把“我”强行安排在二楼狭窄而闭塞的育儿室里。同时,育儿室内的摆设也让人感觉很压抑:焊了围栏的窗户(以防小孩意外跌落)、被紧紧定在地上的床架以及让主人公作呕的黄色墙纸。且叙述者每日只能独自呆在这个狭窄的育儿室里,无人与其交谈。这些都说明了囚笼一般的居住环境给叙述者带来的压迫。
其次是主人公话语权的缺失。正如福柯在《规诫与惩罚》一书中提到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时所说:“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2]从福柯的话里可以看出,知识是具有权力的话语权。正如小说中,丈夫约翰自以为是地对“我”采取“休息疗法”,当“我”告诉他自己的体重没有增加,反而减少时,约翰则转移话题,剥夺“我”的话语权,说道:“我作为一名内科医生对你说,你能信赖我吗?”[3]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约翰利用医生的绝对权威,通过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叙述者身上来剥夺她的话语权,同时叙述者又受到父权制社会的压迫,在婚姻和家庭中,“我”也经常失去话语权。比如“我”好奇地问约翰所租的房子之前长期没人租的原因时,约翰则是一笑,而“我”如文中所说早就预料到了,“John laughs at me, of course, but one expects that in marriage.”[4]这句话不但说明了“我”对约翰的嘲笑已经习以为常,几乎到了失语的地步,哪怕只是他的一个眼神,就足以把“我”的声音压制下去,而且“我”在婚姻中一直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他在广阔的社会空间里工作社交,而“我”的活动却被限制在狭窄的阁楼上,这体现了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这种地位的悬殊导致了男女双方在婚姻中缺乏沟通,从而使得两性在婚姻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最后是叙述者写作的权利被剥夺。约翰自以为是地为“我”的健康考虑,禁止“我”进行任何形式的创作,他给“我”每天的安排是吃饭、休息和睡觉,不允许“我”进行任何形式的写作。正如“我”的心理活动所反映的那样,“他很讨厌我写作,哪怕只是一个字”[5]。这句话表明了,约翰剥夺了“我”唯一能够进行情感宣泄的方式——写作。
除了以上3方面的压迫,叙述者还受到同性的压迫。比如,约翰在外出时,让他深受父权制毒害的妹妹充当称职的女管家来监督“我”在生活中的举动,并将“我”的一言一行报告给约翰。她坚信是写作摧残了“我”的精神和身体,同样作为女性,她并没有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来帮我逃离父权制,反而帮助男性共同压迫同性。正是由于遭受这种种压迫,最终才导致了“我”后来的疯癫。
二、叙述者所爆发的种种疯癫
由于父权制社会的影响,男性在家庭中处于中心地位,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因而,叙述者在家庭里本身就没有话语权。当面对约翰采用的比疾病本身更可怕且让人窒息的“休息疗法”来对“我”进行精神治疗时,“我”几次都试图鼓起勇气与约翰交流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但是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同时,“我”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狭小的育儿室内,并且受到严密的监视。由于无事可做,“我”终日不得不面对四壁正在脱落的黄色墙纸,精神思想开始病态地自由驰骋。就这样,“我”日复一日地沉浸于黄色墙纸的探索中,最终,渐渐地走向了癫狂。在小说刚开始,“我”对黄色墙纸的颜色和图案是感到极其厌恶的,甚至恶心,“我”认为黄色墙纸的纹理和颜色是对艺术的严重亵渎,但后来“我”的心态却发生了奇怪的转变,“我”对黄色墙纸上的图案开始着迷,甚至喜欢上了育儿室的黄色墙纸,并试图从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这种病态的着迷暗示着“我”的精神状态也正在渐渐地恶化。通过“我”的仔细观察和研究,发现黄色墙纸的图案有两层,第一层是图案,图案下边囚禁着很多满地爬行的女人,墙纸上带有纹理的图案变成了一道道的栅栏。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黄色墙纸恐惧的纹理背后,有一个女人的轮廓开始若隐若现,在拼命地摇动着栏杆,并试图从栏杆后面挣脱出来。这个女人就像“我”一样被囚禁在带有栏杆的育儿室里面。于是,“我”试图透视那个女人的内心世界,渐渐地出现了幻觉,总感觉有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看。当夜深人静时,看见图案中的女人在地上开始蠕动爬行时,“我”也像她一样开始沿着房间的四周慢慢地爬。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墙纸外边的纹理图变成了一个个栅栏,这些栅栏的后面是一个女人或者多个女人在爬行,有个人影似乎在摇动图案,在暗淡的地方,她就猛烈的抓住栅栏摇动。”[6]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我”的精神世界开始越来越发狂。“我”渐渐地幻觉到:“地上爬行的女人一直想强行通过,然而,图案却把她们紧紧地扼住,她们的眼珠都快泛白了。”[7]从这些试图想强行通过却被遏制住的女人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缩影,这激起了“我”内心深处的反抗和疯狂,逐渐将自己想逃离这种囚禁式疗法的愿望和图案中女人艰难爬行的形象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正如贝尔·胡克斯所说的姐妹情谊,“这种相互扶持的姐妹情谊,解救黄色墙纸里女人的同时也把主人公给解救出来了。”[8]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我”试图帮助墙纸里的女人挣脱束缚,以便能够帮助她们获得自由。于是,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她摇我拉,我拉她摇,在黎明前我们就撕掉了好几页墙纸。”[9]“我”和黄色墙纸中的女人以姐妹的情谊相互扶持,实现了精神上的统一。在小说结尾,等约翰见到“我”时,惊恐地发现“我”在碎纸堆里缓慢而艰难地爬行着,一向强势的约翰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得直接昏了过去。这说明了“我”精神上的疯癫状态已经达到了极致。
三、叙述者所取得的“胜利”
正如《简·爱》中阁楼上的疯女人用疯癫来反叛父权制社会一样,主人公“我”也用疯癫来对父权制进行抗争,并试图冲出父权制社会的囚笼,从而来争取精神上的“胜利”。小说中丈夫约翰以温柔的面纱对“我”进行父权制的压迫,禁止“我”进行任何形式的社交和创作,还把“我”囚禁在如同监狱般的育儿室里。再加上育儿室里的窗是带有栅栏的,床也被锁链固定在地板上,房顶上还有门,这些令人压抑的摆设使得“我”不得不沉浸在黄色墙纸的世界中,以至于渐渐出现了幻觉,因此,“我”开始疯狂地撕掉黄色墙纸来帮助墙纸后边的女人获得自由。在疯癫之前,“我”在约翰面前是没有话语权的。“我”提出的各种要求,都会被他嘲笑或者以各种理由对“我”的要求加以拒绝。
然而,“我”在经历种种压迫且进行反抗之后,最终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在小说中一共体现了两次。第一次是指约翰有一次按“我”的指令行事。在小说结尾,“我”用最温柔的声音告诉约翰,房间的钥匙放在前门台阶上的一张大芭蕉叶下,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我用十分温柔而缓慢的声音重复了多遍。我说的次数多了,他就不得不去看,然后,他找到了钥匙,打开门就进来了。”[10]这是丈夫约翰唯一一次听“我”的指令行事,而没有对“我”的话语进行忽视和反驳,表明了“我”在象征父权制权威的丈夫约翰面前唯一一次拥有话语权。最终,约翰用斧头砍掉了门上的锁链,破门而入,打开了囚禁“我”的阁楼,这表明“我”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胜利”,尽管这种“胜利”是以疯癫为代价的。然而,在疯癫时,主人公“我”还是用最温柔的声音来向约翰发出指令,这与“我”当时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是完全不相符的。这种现象说明了主人公“我”内心深处是畏惧父权制的。这种所谓的“胜利”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并不彻底。
第二次“胜利”是指“我”敢于从象征父权制权威的约翰身上“跨”过去。当丈夫约翰进来时,“我”正在歇斯底里地撕扯着育儿室里的黄色墙纸,黄色墙纸被“我”撕扯得洒落了一地,而“我”犹如墙纸里的女人一样在地上慢慢地爬行着。作为父权制代表的约翰看到这种场景之后却被吓得昏过去了,而“我”则从约翰身上勇敢地“跨”了过去。女主人公以自己在丈夫约翰身上爬来爬去来表现她冲破父权制的牢笼,获得了所谓的“胜利”,继续在追求精神自由的道路上前行。正如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一个男子汉难道真的能昏下去吗?他确实昏过去了,昏倒在墙边,正好横在我前行的道上,所以每次都不得不从他身上跨过去。”[11]“我”是在精神崩溃以及约翰昏迷的前提下,才敢从约翰身上“跨”过去,这是“我”用疯癫的方式来挑战父权制权威,并用行动呐喊出了自己追求身心自由的强烈愿望。与之相反,如果在头脑清醒的状态下,“我”是绝对不敢公然挑战父权制的权威的,只能蜷缩在父权制的压迫之下。显然,叙述者是以疯癫为代价才敢表达自我,这说明叙述者所取得的“胜利”是短暂性的,是不彻底的。因为约翰总有醒过来的那一刻,而“我”在他苏醒之后还会像以前一样生活在父权制的囚笼里遭受压迫。
从压迫、疯癫和“胜利”的角度来解读《黄色墙纸》中的女性主义,旨在说明叙事者疯癫的原因和内涵,揭示父权制社会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摧残和压迫。虽然《黄色墙纸》的叙述者的反抗及“胜利”具有不彻底性,但是,吉尔曼用反传统的手法,在叙述者逐步迈向疯癫的过程中叙述其不断变化的心理状态,借助一个疯癫女人之口,表达了女性追求独立和自由的愿望,为后人对女性主义的探索开辟了道路。在父权制文化中,男性对女性充满了歧视与压抑。因此,只有进行彻底地反抗,女性才能跳出父权制的囚笼,从而获得独立和自由。
参考文献:
〔1〕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The Yellow Wallpaper [M].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1973.
〔2〕Norton. Anthology of Short Fiction (5th edition) [Z].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1995.
〔3〕〔5〕〔10〕福柯.规诫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4〕〔11〕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6〕〔7〕〔8〕〔9〕夏洛特.帕金森.吉尔曼.黄色墙纸[J].名作欣赏,1997,(3):107-116.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