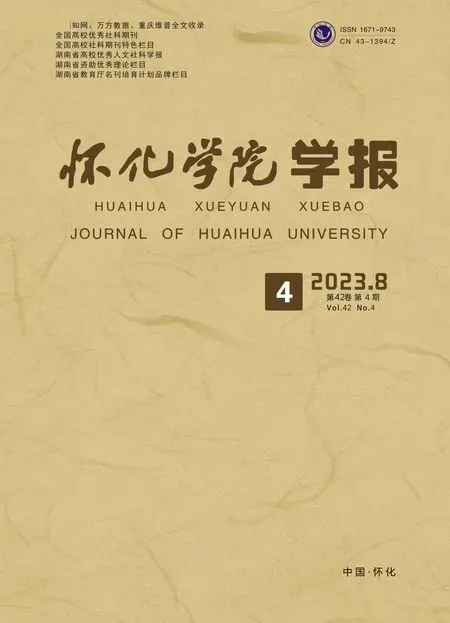论沈从文对狄更斯底层书写的文学接受
2024-01-17张莉莉弓皓然
张莉莉, 弓皓然
(1.怀化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0; 2.西北民族大学,甘肃 兰州 730030)
自20 世纪20 年代末起,沈从文以自觉的写作态度创作出诸如《龙朱》《神巫之爱》《阿黑小史》《山鬼》等湘西少数民族题材作品,他对自己早期刻画的湘西底层人物曾自述:“唯一特别之处,即一生受社会或个人任何种糟践挫折,都经过一种挣扎苦痛过程,反报之以爱……所谓生动背后,实在都有个个人孤寂和苦痛转化的记号。”[1]由此观之,沈从文有意地将时代语境下社会问题对湘西少数民族个体的倾轧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表现之一,这种创作思想上的自省,受到同是以书写底层民众生活为代表的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影响。沈从文自青年时期起就广泛阅读狄更斯的作品,并坦言:“狄更斯的小说,真给了我那时好大一份力量。”[2]这份力量展现了狄更斯对沈从文文学创作上的陶染。目前学术界对两位作家的比较研究较少,胡全新以狄更斯作品的审美性为基点,深入挖掘沈从文将这种审美启示糅合进自己的小说作品与文学争论中。[3]此研究立足于沈从文作品对狄更斯小说的文学吸收,但是只进行两位作家作品内部的单向度比较,忽略了20 世纪20 年代湘西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在地域文化上的差异,削弱了湘西百姓与英国劳动民众同属于底层人民的主体性,他们各自展现的消解或抵抗就此被埋没。
如果我们将历史语境中的湘西与狄更斯的小说世界建立起关联,赋予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的观照,就会发现两者所描写的底层人物是多面的,乡下人身份的界定不仅与湘西的文化象征意义有关,更是沈从文对于异乡与异国想象的直接产物。换言之,沈从文作品中湘西与英国并非作为无连结的地域存在,它们呈现为同属关系的底层人物建构。
一、对他者想象的共同阐释
从文化模型建构的意义上来看,想象成了作家丰富文本内涵的催化剂,而不再以实地情景遭遇作为文本的主要内容。因此对小说人物语言和日常生活的虚构,特别是沾染了地域神秘色彩时,想象可以为读者呈现更为强烈的阅读观感。狄更斯虽然是批判现实社会的文学大师,但他在创作中仍然为浪漫主义保留了一席之地,糅合他者的想象,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塑造,都变得意味深长。沈从文则置身北平眺望千里之外的故土湘西,字里行间充满着别样的异域想象。
(一)狄更斯小说的他者想象
作为19 世纪西方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狄更斯在25 岁写下的《雾都孤儿》描述了伦敦贫民窟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控诉了资本主义的黑暗与罪恶,但他运用的浪漫主义笔法却令整篇小说蒙上了神秘阴影。赛克斯将南茜杀死后惶恐不已,陷入自身想象的鬼魂包围中,那双黑暗里睁得大大的眼睛犹如幽灵一般缠绕着他,使他终日不得安宁,最终赛克斯在神情恍惚之下失足身亡。狄更斯假借鬼魂之手渲染赛克斯的内心恐惧,让他的死亡变得合情合理。除此之外,在故事的开头,狄更斯将奥列弗的出生设定在“某镇”,这个不知名的小镇,其实就是狄更斯为奥列弗建造的空中楼阁。“某镇”作为他者,帮助狄更斯用这个虚幻的空间完成对奥列弗的人生安排。奥列弗看似可以在小镇自由生活,掌控自己的命运,但他的悲惨生活在降临这个小镇时就已注定,无力挣脱。
正如法国评论家丹纳对狄更斯小说的评论:“狄更斯有着如此清晰和强烈的想象力,一定能够毫不费力地使没有生命的事物变成有生命的事物。”[4]“有生命的事物”便是作家通过想象而抒发自身感想的直接产物,那些看似没有生命力的客观存在,在狄更斯的笔下被唤醒了,被赋予强烈的主观情感,作者的个体情绪借此得以宣泄。《老古玩店》用喷火的巨口形容虚构的英国某大城市的炼钢厂,而魔鬼则象征着炼钢厂的工头,于是一个充满着压迫和苦难的劳动场所被构造了出来,“喷火”和“魔鬼”成为罪恶的象征。我们无法说这是完全真实或者虚拟的产物,但因为加入了他者想象的成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资产阶级压榨给予读者更强烈的冲击,从而侧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城市里的底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二)沈从文的他者想象书写
相比于狄更斯将现代事物的丑恶性加以叠加,沈从文则从湘西美好人性入手产生积极的想象。沈从文在创作以苗族为代表的地区少数民族题材小说时,总会赋予文本以巫傩文化的浸染,构成对湘西巫神的可视化表达。如在《神巫之爱》中描写神巫独具地域风情的装扮和“傩仪”做法时大幅度的动作。又如在《龙朱》开头,作者更是不惜笔墨地用长段篇幅介绍白耳族苗人的神巫文化。沈从文早期的小说均是在北平等异乡空间完成的,于是其笔下涉及巫傩文化的奇异故事并不是一种方志式的写实建构或田野调查,而是以在异乡回溯湘西记忆为主,再“运用无处不及的想象”和“丰富无比的常识”[5]进行技巧式的湘西建构。
想象对于沈从文创作小说极其重要,他曾在《一个人的自白》中透露了自己创作的叙事策略:“作品中的乡土情感,混合了真实和幻念,而把现实生活痛苦印象一部分加以修饰,使之保留童话的美和静。”[6]我们的确应该承认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存在异乡的他者想象,但这种想象的视景服务于“美和静”的创作理念,使得湘西被构造为供奉着人性的古希腊小庙,又使得作者在其中得以阐述他所希望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7],由此达成统一性的写作链条。更重要的是,较之于纯粹的考察书写,沈从文在想象中摒弃了“痛苦印象”——传统儒家文化对“苗蛮”的教化与“域外人”的区别化,而是以湘民为主体,立足于湘西的真善美民族性与地域特殊文化价值,达成了对湘西民族的积极发声。如在后期创作《沅陵的人》时,沈从文由衷地写道:“他需要人信托,因为他那种古典的作人的态度,值得信托。同时他的性情充满了一种天真的爱好,他需要信托,为的是他值得信托。”[8]这种“祛蛮式写作”使得读者对湘西人民的看法有所改观,并由湘西理想世界过渡到中国救亡图存的文化折射,进而也为沈从文刻画底层人物生活留下了结构上的阐释空间。于此来说,他者想象便更具有从立人到立国的时代价值。
二、狄更斯对沈从文底层关照意识的影响
虽然沈从文通过对异乡的他者想象构建了符合祛蛮价值和时代立场的湘西世界,但面对湘西少数民族底层人民的艰苦生活,他却始终秉持现实主义的记录与深沉的关照意识,这种关照意识离不开狄更斯对沈从文从观念价值到文本创作的多重影响,从时代背景、底层阶级和写作笔法三个方面便可窥见狄更斯对沈从文的影响踪迹。
(一)由工业革命到湘西的现代性入侵
沈从文曾多次提及狄更斯的《雾都孤儿》《董贝父子》《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大卫·科波菲尔》等小说让他印象深刻[9]。这些小说均以19 世纪工业革命的英国伦敦为背景,描述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对底层人民的压榨和现代性对百姓的双重影响,如《大卫·科波菲尔》中的航海贸易、跨国运输,对本国和他国百姓生活有极大改变。沈从文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并不无惋惜地说:“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氛,这些东西又如何被外来洋布煤油逐渐破坏。”[10]所谓“破坏”即为英国率先出现的工业革命导致的现代性入侵湘西,这种入侵又明显以“洋布煤油”等外来商品作为呈现。沈从文早期的小说如《柏子》《凤子》《三三》对此进行了饶有兴趣的探讨,其中《柏子》里描写外来商品对湘西百姓物质化侵袭最为深刻。
《柏子》在开篇就描写了黑汉子带着“方形用铁皮束腰的洋布”“药箱”等西方工业革命批量化生产的商品来到辰州码头下货,给人一种现代性意象在传统地区流行的迷幻感,而随后水手柏子爬到了心上人所在的吊脚楼,妇人的第一动作便是搜索柏子身上的东西,搜出的东西往床上丢,又念着东西的名字。“一瓶雪花膏,一卷纸,一条手巾,一个罐子(化妆粉)”[11],接着,二人才开始久别重逢的感情交流,并在最后互唱歌谣,倾诉爱意。在这里,“歌谣”作为湘西百姓传统的情感交流工具已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进口商品,且大多为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奢侈品。奢侈品代表的是对物质的高等要求,因此对奢侈品的占有、使用与支配承载的是人的消费能力、社会关系和身份归属。从批量工业化产品——进口货物——奢侈品的逐级追求,代表了湘西底层人民无论在生活还是在精神层面,都被西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物质追求所感染,发出“现代人”的自我身份暗示,这也表明了现代性已经渗入湘西内部世界。对照《大卫·科波菲尔》的主人公科波菲尔为追求荣誉和地位行遍欧洲大陆,并经历律师见习生、作家等多种职业后终于抱得美人归的故事,《柏子》更可以引申出现代性的理想发财之路在他国语境下的唐突、绵软和无可比拟。
(二)由工人阶级到小农结构的变动
狄更斯以描写工人阶级底层人物为代表的小说主要是《雾都孤儿》和《董贝父子》,前者描写了工厂主对童工的剥削与暴力,后者则以大批发商董贝为第一视角,描述其对公司员工和子女亲戚的残忍冷漠。无论是工厂主还是批发商,他们都属于工业革命时期掌握金钱和权力的资本家。
人类学家简·施奈德说:“贸易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只是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通过限制性的法律以及对特定身份象征的垄断,来使自身卓然独立于其他群体,这更进一步涉及某种直接的、有意识地对各种半边缘化社会群体以及社会中间阶层的操控。”[12]工业化在使资本家概念构成的同时,便同构了与底层人民的社会分层。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社会无法阻挡的资本操纵使得权贵者欺压底层人民成为常态。此现象在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的全球势力扩张中波及了中国,影响了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农结构。对此,沈从文深有感触,他目睹近代湘西底层人民的种种遭遇后感慨:“许多事情都极不合理,远比狄更斯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英国社会还野蛮恶劣。”[13]所谓“野蛮恶劣”的事件,如官府士兵对湘民的欺辱,地方势力对百姓的迫害,均是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时期对弱势群体进行的价值压榨。《山鬼》《丈夫》《会明》均体察了社会阶级分化对湘西原有小农结构的冲击,其中,以《山鬼》里都市文明对猫猫山的影响最为突出。
《山鬼》描写了湘西老虎峒中一位游离于山涧水沟的“癫子”,而后回到了毛弟妈家中居住,不知何时会再一次外出。沈从文极力刻画了湘民百姓淳朴可爱的性格与简单纯粹、自食其力的小农经济。除了男耕女织的劳作模式外,小农经济还包含借助猫猫山晚间集会进行村民内部自然化教育的重要生活模式。但在结尾,毛弟妈想到了其他可怕的事,担心在她死后癫子被人虐待,遭受痛苦的折磨。透过悚然的文字,“官府亲兵”这个带有现代都市文明的意象侵入了乡村世界,并用收去房屋的行为表达对湘西底层人民的物质化欺压。居于权力中心者给处于权力边缘的群体带来了阴影,而究其根本,阴影的核心是资本,阴影的外化是权力。这构成了处于湘民小农结构语境下更为离奇且无法阻止的自英国至中国深化的二次资本操纵,于是沈从文痛苦地喊道:“其实详细经过、情形却远比狄更斯写的自传式小说还离奇复杂得多。”[14]
三、中西底层民众自救途径的差异
无论是狄更斯还是沈从文,他们描写的底层百姓生活都体现着现代社会对人性异化的悲愤与无助。这些百姓消解或抵抗着大时代的不合理困境,并努力完成个体自救。细分到中英两国的底层百姓群体,他们在自救途径上存在着某种差异。
(一)常与变的不同态度
在沈从文笔下,湘西底层人民的生命形态分为“常”和“变”,包含对自然和常态生命的肯定,及对多变人事纠纷等悲惨处境的疑虑。湘西内部环境的牧歌性古老而悠久,人人都有善良的性情,但地域无法预测的天灾、生命的脆弱、爱与美的稍纵即逝皆是湘民生命形态中不能承受之重,它往往使我们的人事难以完满,爱与美很难保留和长久存在,如《阿黑小史》中毛伯悲痛于儿子五明的突然发癫,感到“胸中已储满眼泪了,他这时要制止它外溢也不能了”[15];再如,《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描写水手被瞬间爆发的激流冲走溺毙:“水手赤裸着全身向水中跳去,想在水中用肩背之力使船只活动,可是人一下水后,就即刻为激流带走了。”[16]而随着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对世界各地区的现代性辐射,“变”的生命形态已经由传统意义上的天灾和人事因素转为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无所适从。对现代都市文明的种种变动,尤其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功利主义和人性伪善,沈从文借小说表达了对现代文明之变的态度,他讨厌一切的社会标准,特别是所谓的思想家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认为这只是为了扭曲压扁人性而已。沈从文对于工业革命以来持续发展的现代性进程持有怀疑而采取保留态度,他并不认为现代社会对湘西底层人民产生了积极影响,而是“扭曲压扁”百姓的人性。
反观狄更斯,他对现代都市文明对人性的影响则抱有较为理想友善的态度,他坚信凭借个人努力可以产生无穷的力量,足以抵抗人世间的阴暗与萎靡,并推动社会由衰落至繁盛的发展。狄更斯创作的一系列“流浪汉文学”是其理想进程最鲜明的体现:小说主人公由无人可依靠的底层阶级孩童一步步变为具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如《雾都孤儿》中的小奥利弗走出了童年时期的黑暗,长大以后查清了自己作为富商私生子的身份并获得幸福生活;《大卫·科波菲尔》中科波菲尔以孤儿身份起家奋斗,终于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和家庭的圆满。与沈从文同类型作品中弥漫的淡淡忧愁和悲悯情怀不同,狄更斯刻画的底层世界极富激情和“乐观向上、欢快、温和”的人道主义思想。这种善于从丑恶中挖掘美好的视角,突出了狄更斯底层书写中“变”因素的合理性与积极作用,作者“像一个孩子观察一座陌生城市那样地观察着这一个巨大的世界,但他用的是成人的智慧和洞察力。他所看到的亮光比一般人所看到的更为强烈”[17]。于是现代都市文明的“变”成了小说主人公通往成熟与成功的催化剂,再加上个人主观能动性的自觉苏醒,所造就的“光亮”甚至可以战胜资本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
正如吉·基·杰斯特顿在《匹克威克外传》中所言:“与其说狄更斯是一位小说家,不如说他是一位神话作家……他并不是总能把他笔下的人物写成人,但他至少能把他笔下的人物写成神……狄更斯的目的并不在于显示时间和环境对人物所产生的影响,甚至也不在于显示人物对时间和环境所产生的影响。”[18]狄更斯的“神话式”底层书写使人物带有传奇色彩,那么常态的生活和变数的都市文明也就成为服务于文本的工具。从这个层面来说,沈从文抓住了狄更斯所忽略“变数”的重要性,底层人民可敬的品格固然重要,但正是自然与社会对生命形态的破坏甚至毁灭,使沈从文把握了在时代语境下湘西人民独特的韧性。
(二)泛神倾向与精神救赎的双重解读
狄更斯通过对底层人民的神话化完成了对现代都市文明冲击的消解,除了在小说转折点上制造巧合服务于小说,作者还会在情节缓和时让底层人物诉诸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关怀。如在《小杜丽》中,狄更斯的核心思想便是宣扬基督教的善良和团契的圣诞精神,通过世俗的行为验证自我的存在,同时也赢得了世俗的回报。由此引申的“圣诞精神”充盈了狄更斯的心灵乌托邦,即世人不再以金钱权力为衡量人的标准,而是以小杜丽等底层百姓为代表,通过他们富饶的心灵感召,实现对精神家园的守望。[19]这种由悲悯他人到净化他人的价值观影响了沈从文对自我牺牲、道德净化的重要认识,并对他文学创作中理解人性具有深刻观照。沈从文在《一个人的自白》中提到的“微笑”既带有湘西底层人民泛神倾向的自救意味,又混合了英国基督教中的天主救赎。
泛神倾向指湘西百姓人神共存的本土生活方式,是湘西民族自繁衍以来对其信仰的尊敬以及对神灵的具象化表达与泛化理解。当湘西底层人民面对日常生活中任何不理解的人事变动时,他们都必须加入“神”的成分缓冲、消解或抵御天灾人祸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山鬼》中毛弟娘将癫子的发癫认为是“得罪了霄神,当神撒过尿,骂过神的娘,神一发气人就癫了”[20],还有《神巫之爱》中的百姓遇到仇家去世,便认为是“凭了神的保佑将仇人消灭”[21]。神在湘西底层人民心里变成了一个精神支点,构筑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凡事诉诸神”成了他们对外来事物与面临变数的自救工具,并体现了他们由民族韧性转向神性的叠加。
当沈从文随着时代变动发觉湘西传统性处于越来越边缘的状态时,他逐渐认识到了这种时代变迁的不可逆性与不可抗拒性,并转化为自身理解世界的一部分观念,其笔下湘西人民对变数的消解也由“泛神倾向”开始向基督教的“精神救赎”转变。他在后期创作的小说《被刖刑者的爱》中写两兄弟与他们的妇人在沙漠遇险时,弟妇为其他人能活而割肉自尽,并说:“把我身体吃了,继续上路,做完你们应做的事情,我能够变成你们的力量,我死了也很快乐。”[22]于是除了“神”的成分以外,为了湘西得以延续,沈从文加入了以基督教为原点的“爱”的因素。《旧约》写道:“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忍耐与恩慈恰对应着湘西百姓淳朴友爱、坚韧顽强的民族性格,于是这份爱可以超越肉体,转变为一种摩西式的献身精神。在20 世纪50年代的书信《致布德》中沈从文说:“这种悲悯的爱和一点欢喜读《旧约》的关联,‘牺牲一己,成全一切’,因之成为我意识形态一部分。”[23]正是以这种西方化对人生悲悯的爱做底色,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中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抵触与湘西传统世界的抒情才更具沉甸甸的意蕴——无论湘西底层人民自救行为是否可以真正成功,其中依旧存在沈从文对完美生命境界的追求,它给予底层阶层以关心,又给他们以希望。从这个立场来说,沈从文的希腊小庙供奉自然人性与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实现了中西观念的融合,他们共同追求着一种普世意义上的神性。
沈从文倾注精力创作了一系列湘西少数民族题材小说,这些作品均以在异域的他者想象切入文本,书写湘西底层人民的生活。如果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追溯沈从文的底层书写,我们无法绕开19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背景和狄更斯小说对他的影响,其中共同体现的现代都市文明不仅改变了20 世纪20 年代以来的湘西世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沈从文的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都市文明的现代性虽在不同国别或地域存在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变体,但正如法国学者巴登斯贝格所说:“在仅限于人类精神范围本身的文学史内容显得纷繁多变的情况下……模糊一团的物质,越是不确定和不可捉摸,就越应该明确和坚固它的核心。”[24]就影响关系的同源性来说,它在各民族文学中仍有着稳固的同一性,正是这种同一性,向我们揭示了文学呈现人性本质的意义,即无论身处何种时代背景,遭遇怎样的变数,都能依靠韧性与神性,实现人类希望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