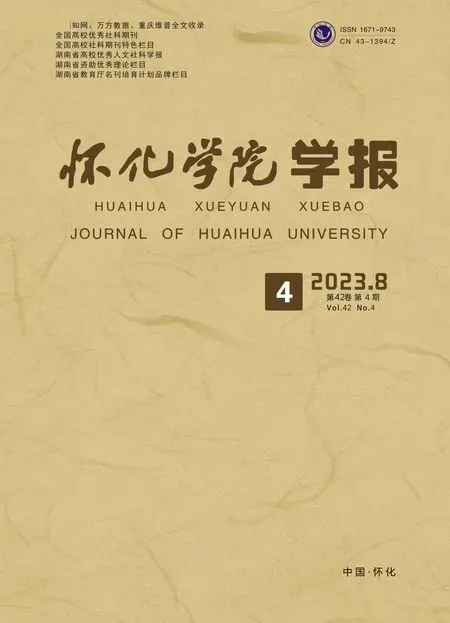本土生态知识的内涵与价值探析
2024-01-17农仁富杨庭硕
农仁富, 杨庭硕
(1.南宁市博物馆,广西 南宁 530219; 2.吉首大学,湖南 吉首 416000)
本土性知识是20 世纪后期学界才提出并普遍接纳的学术性概念,其内涵极为丰富。在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本土性知识中必然包含着的生态知识日益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并展开了热烈了探讨,成果丰硕,逐步形成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但为何要深入探讨传统的本土生态知识,时至今日人们还存在着诸多认识上的分歧和差异,并直接影响到这一术语的准确运用。为此,本文围绕这一概念的内涵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和澄清,希望对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促进作用。
一、本土生态知识的内涵
20 世纪后半叶的西方国家学术界出现了一个具有很大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即后现代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给传统的学术观念构成了重大冲击。“地方性知识”正是这种学术观念变革的派生产物和重要方面。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观念虽然早在古希腊哲人的思想中就已经被多次提及过,但明确提出这一概念并展开系统论证的代表人物,则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他赞同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的观点,于是,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1]。因此,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概念。“文化模式是历史地创立的有意义的系统,据此我们将形式、秩序、意义、方向赋予我们的生活。”[2]在不同民族和地区中客观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文化差异,这是因为不同的文化是不同的民族对其所处世界的不同理解的产物,文化的各种符号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该文化中行为者的行为组织方式。因而文化模式并非普遍性规则,而是具有多样性的特殊意义系统,并由此构成了所谓的地方性知识,一种具有地域文化特质的知识形态及构成方式即一种具有地域文化特质,并具有特定时空场域的知识形态及构成方式[3]。
地方性知识这一学术概念与普同性知识相对应。“广义地讲,地方性知识是一定地域的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体力和脑力劳动创造并不断积淀、发展和升华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部成果和成就,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它反映了当地的经济水平、科技成就、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文化修养、艺术水平、社会风俗、生活方式、社会行为准则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狭义的地方性知识专指地方的精神文化。作为一种经过长期创造、积淀和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地方性知识有其鲜明的地域特色、独特的价值体系和丰富的内涵,生存其间的每一个个体总是天然地与本地域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4]
王鉴和安富海认为“地方性知识最初只是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学术概念而存在,但目前它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了文化人类学的范畴。在许多学者看来,‘地方’是以祖先领地和共同文化为核心内涵的,这就把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植入了‘地方’复杂的历史和文化多样性背景之中,以至于难以做出简单的界定”[5]。陈来认为“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文化乃是人们适应环境的产物,不同的地域共同体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下造就了自己的文化,从而造成了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地方性知识意味着一地方所独享的知识文化体系,是此地人民在自己长期的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与此地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及其历史密不可分”[6]。
目前,“学术界主要从肯定地方性知识的实践价值出发,力图在政治层面上去理解和把握地方性知识的内涵。然而,这种理解方式不可避免地淡化了地方性知识的权力维度,掩盖了地方性知识的历史负荷”[5]。在生态人类学界,为了避免这一提法隐含着的歧视意味,杨庭硕将其定义为“本土知识”,即“特定民族针对特定地区的自然与社会背景,通过世代积累而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这样的知识体系服务于特定的民族和地区,具有明显的民族归属性和地缘性”[7]。而作为本土知识一部分的本土生态知识,则是“特定民族、特定地域社群对所处自然与生态系统做出文化适应的知识总汇,是相关民族和社群在世代积累上健全起来的知识体系。这样的知识体系总是间接或直接地与该民族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相关联,担负着引导该民族成员生态行为的重任,使他们在正确利用自然与生物资源的同时,又能精心维护所处生态系统安全”[8]。这样的研究取向与我们今天正在从事的生态文明建设,明显存在着认识和理解上的高度一致和实践应用价值。
“本土知识”强调的就是所有知识的平等与特性,反对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欧洲文化中心主义。本土生态知识认为任何一种地方性知识都有其不可替代的魅力和优势,对人类自身发展的认识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也许很难被异种文化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但它却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含义。作为知识观念和认知模式的地方性知识而言,它决不仅仅只是一种批判性的知识观念和话语武器,其实践性与建设性才是它最有价值的特性所在[9]。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想要研究某一民族或地区的地方性知识,必须秉持宽容、接纳、适应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因为这是决定其能否承认并客观研究地方性知识的基本条件。
由此可见,“地方性知识的确对于传统的一元化知识观和科学观具有潜在的解构和颠覆作用。过去可以不加思考不用证明的‘公理’,现在如果自上而下地强加在丰富多样的地方性现实之上,就难免有‘虚妄’的嫌疑了”[10]。地方性知识的存在是多元化的,是与特定民族所处的自然生境和社会生境相对应的,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用简单的因果模式去处理。这样看来格尔兹对本土知识的理解可拓展到我们跨文化的研究当中。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是多样性的统一体,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或者为保持本文化的纯洁而拒绝与他文化进行交流,就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孤立主义。符合当前时代潮流的本土生态知识观,才可望得以彻底的澄清,并在这样的观念转型中能够对那些从表面上看上去似乎不可思议的、形形色色的各民族、各地区的本土生态知识,保有进一步认知的激情,从而才有望公平理性地去认识和接纳他们,并为此展开深入的研究。客观存在着的本土生态知识在当代的传承弘扬和高效创新利用,也才能落到实处。
二、本土生态知识的价值
鉴于本土生态知识是众多经验、技术、技能的复合存在,其中还不缺乏理性总结出来的生态哲理和生态智慧,内部构成极其错综复杂,因而在当代传承弘扬和创新利用时,不仅仅需要系统的把握具体的操作方法,还需要辅以当代科学知识和理论的验证,更需要向世人揭示本土生态知识的可行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为此对本土生态知识的当代价值就其实践应用而言,展开分门别类的讨论,实属必不可少。
(一)生态维护价值
一切本土生态知识都是特定民族文化在世代调适与积累中发育起来的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都系统地包容在特定族群的文化之中,本土性生态知识的本质在于对生态环境的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11]。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土生态知识必然与所在地区的生态系统互为依存,互为补充,相互渗透。相比之下,普同性知识则不可能具备如此精准的针对性。“若能凭借生态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发掘和利用相关地区的地方性知识,一定可以找到对付生态环境恶化的最佳办法。如果忽视或者在无意中丢失任何一种本土性知识,都意味着损失一大笔不可替代的精神财富。”[12]发掘和利用一种地方性知识,去维护所处地区的生态环境,是所有维护办法中成本最低廉的手段,因为本土知识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与当地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当事的个人在其日常活动中,几乎是在下意识的状况中贯彻了地方性知识的行为准则,地方性知识中的生态智慧与技能在付诸应用的过程中,不必借助任何外力推动,就能持续地发挥作用。”[13]
我国少数民族多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生态平衡的观念与认知,在生态制衡上有许多有效的乡土措施。如居住在滇南地区的彝族撒尼人,每年农历十一月都要隆重举行为期七天的“祭密枝”仪式,又叫密枝节。“祭密枝”仪式的祭祀对象为密枝林,几乎每个撒尼村寨都有自己的密枝林,撒尼人认为密枝林里住着“密枝神”密枝斯玛,是撒尼村寨的守护神。因此“密枝林”在撒尼人心中是神圣不可冒犯的,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在密枝林中进行破坏活动,并且每年还要举办盛大的祭祀仪式,以获得密枝斯玛的保佑。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生态理念和行为规则,只要是在撒尼人的生息区,一定能够看到属于他们的茂盛的密枝林,这几乎是在传统文化的延伸中建构起了与当代生态保护区功能与效用完全重合的生态维护行动。而使密枝林发挥生态保护区功能时,相关部门乃至社会组织,根本无需投入任何意义上的人力、物力、财力代价。这一切都可以在撒尼人传统文化的正常运行中,做得十全十美。由此看来,本土生态知识用于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维护,显然是一种最经济、最节约的路径和手段,而且实施的成效比当下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经管的自然保护区,其保护成效更为理想。
在羌族地区的自然宗教信仰中,杉树、白石与柏枝都是他们心目中的圣物,当地人不仅对这三种自然物的崇拜和保护有加,而且在生产和生活中都严密地监控这三种自然物的样态,确保它们不受任何人类活动的干扰,以期它们能够按照原样超长期的稳定存在[14]。这样的崇拜同样事出有因,杉树、白石与柏枝是其生息地带自然生态灾变的警示标志。羌族的生息地,位于青藏高原的东缘,海拔都在3000 米上下。加之,这里是地质结构极不稳定的地震带,海拔的相对差又极大,高山峡谷所在皆是。即令没有受到人类的干预,冰川、地震与地表径流都可能造成大面积的滑坡和山崩。在如此严酷的生存背景下,山体植被的超长期稳定,关系着羌族人们的日常生活。以至于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三种自然物的稳定存在和匹配,是他们得以安居乐业的基本保障。正是因为羌族民众将生息地自然结构的稳定视为人类社会得以稳定延续的首要前提,于是在他们对这些自然物崇拜之余,不仅其自身不敢轻易触动这些脆弱性的自然物,而且也会阻止其他民族民众的接近。这样的保护活动持之以恒,就必然可以坐收稳定当地脆弱地质结构的保护成果。在这个问题上,看似不合理的自然崇拜,却在无意中避免了当地自然环境脆弱环节的失效。即使到了今天,这样的自然崇拜对提醒生态保护的专家和执行者,意识到当地自然生态保护的要害就在于确保地表的稳定,还可以发挥直接的警示作用。
在唐代,南方少数民族曾利用蚁来除蛀养柑[15]。具体做法是,他们一旦发现黑蚂蚁蛀食柑橘树,就会起用相关的防治技术,做出有效的控制。这是因为柑橘树被黑蚂蚁蛀食后,在柑橘树的树干上都会留下蛀洞,洞口还会留下它们的排泄物,柑橘树的树叶渐渐地也会变黄。只需要找准黑蚂蚁出洞饮水留下的痕迹,那就可以在野外寻找黄蚂蚁的洞穴,找到后将蚁巢搬运到受害柑橘树的附近,黑蚂蚁出洞必经之路旁,让黄蚂蚁在这里安家落户,那么黄蚂蚁就会主动地攻击黑蚂蚁。黑蚂蚁群受到这样的入侵干扰后,就会自然地迁往他处,否则将会导致整个蚁群全军覆没。
各族乡民之所以能够找到这些本土生态知识的独特技术和技能,显然是通过长期观察后,不断试错,最终总结出来的经验和可行的防虫除害的特种知识。这样的知识虽然看上去不起眼,却符合当代生态学和植物保护技术的科学原理。而且其技术操作简便,一看便会,收效明显且稳定,经得起当代科学意义上的反复验证,并不缺乏科学性、合理性与实用性。
(二)农业经济价值
本土生态知识是当地人思想观念和实践的复合体,它通过经验代代相传,在发展的过程中并不封闭自守,也会发展和吸纳新的知识、技术和技能。我们不能把本土生态知识简单地看成普同性知识的对立面,它实际上不仅包括文化,也包括当地的政治、科技和社会实践的生产和生活,特别是与当地的农林牧各业的生产息息相关[16]。因此相关部门在规划农业生产发展时,特别是在选定产业项目时,启动时就应对本土生态知识和技术给予更多的关注。
众所周知,马铃薯和玉米都是原产于拉丁美洲的农作物品种,但这两种农作物在川西彝族地区引种的效果却截然不同,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玉米为高秆作物,植被郁闭度较低,而马铃薯匍匐生长,植被郁闭度较高,因此种植马铃薯不会像玉米那样容易引起水土流失;其二,马铃薯比玉米更耐寒,生长季更短,与彝族的传统农作物圆根和芋头具有很好的兼容能力,套用传统的粪种技术,种植马铃薯,容易获得高产和稳产。在这一驯化种植马铃薯的历史过程中,不管是国家还是地方官员,都仅仅是一般性的建议或倡导,各族乡民可以试种马铃薯。反倒是乡民套用传统的圆根和芋头的种植方法,种马铃薯意外地取得了成功。国家农业部门最终认定四川省凉山州的布拖县和盐源县产出的马铃薯是最好的繁殖用种薯,不仅组织有关部门在这两个县建立种薯基地,而且组织力量批量出售种薯。这使凉山地区的马铃薯生产不仅提高了其经济效益,还使得其他温暖潮湿地区的马铃薯种植也获得了丰收。
在川滇黔毗邻地带的彝族地区调查时,我们发现,当地的彝族乡民会把畜圈中混入牲畜粪便的草料厩肥定时翻出来,放在自己的家门口,在阳光下暴晒。不少农学家对这样的操作办法颇有微词,认为这样做以后,厩肥中的氮肥会被无效浪费掉,从而极大地降低了施肥的效果。而当地的彝族乡民却反诘到,如果不用这样晒干的厩肥垫在种植的农作物马铃薯下,马铃薯就很难及时发芽,而且结出的马铃薯块也会很小,单位面积的产量反而大大下降。凡是在彝族地区长期做过田野调查工作的民族学工作者,最终都会接受乡民的做法,这样的种植方法恰好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本土生态知识,而且可以当地彝族种植圆根、芋头为例,证明这样的本土性技术操作,恰好适应了当地独特的自然与生态环境。经过自然地理学的验证,这些民族学家的判断是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其原因在于,这些彝族生息的地区海拔偏高,其地表下都存在着长期的冻土层,整个地表的土温即使到了夏天也会明显的低于10℃。如此偏低的土温,对于大多数植物的根系发育而言,肯定是禁区。因而,如何避免气温偏低地层土壤的干扰,自然成了种植块根类作物最难以攻克的挑战。而彝族乡民们的做法,是将脱水后尚未完全腐烂的厩肥垫在土中,将马铃薯种子放置在厩肥上,再用地表的土掩埋种子,就完成了播种工作。如此一来,种子有了厩肥的保护,马铃薯的根系就能在厩肥中生根,等到气温回暖后,再进入土壤中生长。以这样的方式种植马铃薯,出芽、生根都可以提前半个月。这乃是本土生态知识的运用使四川省布拖、盐源县的马铃薯种薯得以行销全国的原因。此项本土生态知识的科学性、合理性毋庸置疑。
除了用粪种法种植马铃薯外,当地彝族种植圆根、芋头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延续了同一套本土生态知识。他们会在夏季高山放牧时,晚上收牧后将羊群、牛群集中到栅栏中,通常要在这样的轮牧点留驻一个星期左右,等到转换牧点时,地表留下的厚厚的牛羊粪便,在太阳的暴晒下,早就脱水干燥,而且粪团与粪团之间也留下了很多空隙。他们会把圆根的种子撒在这些干粪层上,就再也不予理会。到了冬天,牲畜群下山后,播下的圆根种子不需要翻耕、除草、除虫,也会长出高大的植株,结出肥大的块根来。来年,牲畜上山前,肯定可以获得丰收。通常每一亩地可以收获三千到四千斤鲜圆根。这些圆根,既可以作为牛羊的饲料,也可以晒干后作为人们的粮食。当地彝族谚语言:“有了圆根,就不怕挨饿。”由此可见,圆根在他们文化中的重要价值。从表面上看,这样的种植方式似乎与马铃薯有些差距,但其实其原理均是一样的,都是利用粪便脱水后发挥绝热作用,避免底层的低温干扰农作物的根系发育,从而可以用最小的劳力投入获得最大的生产效益。此前的研究者之所以会误读这样的本土知识,其原因也不复杂,那是因为他们习惯于用固定农耕的思维定式去理解高海拔山区的自然和地理环境。在汉族的农耕区,地下根本不存在永冻层,入春后解冻时间较早,一般的农作物都会正常生长。而《齐民要术》所提到的粪种法,仅是为了提供土壤的肥料。问题的症结在于,在凉山地区,施肥仅是其效用的有限构成部分,最大的目的在于使种子根系发育免受低温的伤害,以等待气温的回升后能够正常生长。故而,保暖才是这里使用粪便法的关键所在。如果不这样去作出解释,不同学科为此肯定是争议不休。
在凉山州,当地各民族还有一项独特的本土知识和技术,那就是马铃薯与荞子、燕麦实施间作轮种。此前的研究对这样的做法往往持有不同的认识,认为这样的种植方式,由于成熟期参差不齐,收获时很难实现规模化的效益,也不便于现代农耕机械的推广。植物保护要耗费的人力、物力会很高。但在当代的田野调查中却发现,这些疑惑其实是多余的。原因在于在彝族的传统农业生产中,耕地和牧场用地要实施规律性的轮回使用,农作物收获后都要开放做牧场使用。一旦要复耕时,牲畜排放在地上的粪便只需翻耕就可以成为肥料使用。投工投劳都不多,但土地的肥力却有充分的保障,不会退变。更重要的还在于,在这样的农耕体制下,农作物的秸秆乃至地里长出的杂草,都是牲畜最好的饲料来源。收获时虽然投工较大,但在固定农耕区的众多农事操作中,中耕、除草、防虫,对秸秆的再处理,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在这里却可避免以上的各种农事操作。因而从综合的整体操作着眼,其投工投劳的总量,比种植单一作物还要节省得多。单项作物每亩的平均产量虽然不高,但多种间作作物,收获量的总和却比种植单一作物高出一倍多。而且参与间作的作物,还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做出灵活的调控和匹配,并可坐收货币化的市场收入。此前的研究往往是沿用固定农耕区的测量手段,只计算其中某一种作物的产量作为评判依据,这样的结论不言而喻乃是偏离了事实的真相,不可偏信。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川西高原的各民族中,他们的生息环境海拔高,灾害性天气频发,地表容易遭逢流水的冲刷,地下还有永冻层造成的地温偏低的制约。如果大面积地种植一种作物,即令获得高产但经受不住灾害性天气的打击,要稳产通常都不大可能。此前的研究者往往是根据某一年的产量提升就匆忙下结论。但这里的实情恰好相反,生产的瓶颈不在于某种作物的产量可以提升,而在于能否成功地应对灾害性天气的打击。这样一来,当地各族乡民实施多作物复合间作,恰好可以成功地规避各种气候灾害的风险。比如冰雹的袭击,在这里经常发生。但间作的各种作物,生长季长短不齐,即令其中某一种作物受到冰雹的袭击,其他作物还可以填补留下的空缺,综合产量不会因此而下降。再如,倒春寒和早霜,在这样的地区也会频繁发生,也会影响到作物的生长和收获。但受害的对象,由于作物的生长季参差不齐,仅是其中的某一种作物受害明显而已,也不会影响产出量大势。应当看到各族乡民的这些传统生态知识,本身就是适应自然灾害频发的智慧之举,这也是本土知识和技术精华所在。套用其他地区的普世性规范做出的得失评议本身就偏离了事实真相。而生态人类学倡导的文化适应理论更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此前的“唯产量”论恰好在这一问题上,无意中犯下了错误,理应尽快得到匡正才是。
(三)恢复受损生态系统价值
地质史上形成的纯自然性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可以独立运行的生命实体总成。它有其存在和运行规律,根本无需人类插手加以维护。受损后也可以完全凭借生物的本能实现自我恢复。但人类来到这个地球后就不一样了。人类得凭借自己建构的文化将人的单个个体,凝聚成一个稳定的群体,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对早已存在的纯自然生态系统实施加工、改造和利用,以满足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但绝不是为了纯自然生态系统的需要。于是在这样的两个系统并存的大背景下,相关的民族和社会一旦所实施的加工、改造和利用,偏离了纯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延续机制,相关的生态系统就会因为人类的干预而发生退变,甚至酿成难以挽回的生态灾变。
有幸之处仅在于,任何意义上的民族文化都具有能动认知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禀赋,一旦对人类不利的生态灾变发生,相关民族都会启动相应的补救措施,助推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而与此相关的本土知识、技术、技能,任何一个民族文化中均有相应的储备,可以做出有效的应对,确保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各安其位、各得其所。
洪涝灾害频发地带的民族,其文化中肯定有防洪排涝的本土知识和技术于其中,即使遭逢灾害,也可以做到应对有方。生息在雷击频发地带的各民族,不仅在宗教祭祀中有祭雷神的传统,村寨选址也会做到避开雷击区。面对兽害频发的民族,其文化中肯定储备有应对兽害的本土知识和技术、技能,可以确保人畜两安。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因为单一的自然灾害而趋于灭亡。反而是在外人看来极具挑战性风险性的地带,生息的民族对当地的自然灾害,会从容应对,防范有力,其生存与稳定延续都不会成问题。生态人类学家正是凭借这样的认识和理解,做出认定越是生息在恶劣环境中的民族,局外人看来无法掌控的自然生态风险,他们的文化建构中肯定有正确应对的本土知识和技术,即令生态退变,也能做到恢复有方。
我国西南部的中山、低山喀斯特地貌出露带,是石漠化灾变的重灾区。连片分布的石漠化灾变带遍及湖南、湖北、四川、重庆、贵州、广西、云南等省市,连片分布面积广达十多万平方公里。不仅在我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表现得十分明显。欧洲的克罗地亚,亚洲的印尼的苏门答腊岛都有严重的石漠化灾变带,但连片分布的范围,都比我国中南、西南地区小得多,灾变程度虽然很高,相关的国家通过生态移民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我国石漠化灾变区则分布着上亿的人口,灾变程度虽然参差不齐,但牵涉到的各级行政机构却数量不小,要达到协调综合治灾,组织管理上挑战不小。不同学科的学者,虽然都做出了相应的努力,国家相关部门也能做到尽职尽责,并收到了一定的治灾成效,但就总体而论,至今还无法令人满意。据此有人公开宣扬石漠化灾变是治不好的土地“癌症”。这样的论断尽管是出于无奈,但容易造成误导。因为我国的石漠化灾变区生息着苗族、土家族、壮族、瑶族、彝族等10 多个少数民族,在他们的传统文化中,一直保留着应对石漠化灾变,有助于生态恢复的本土知识和技术技能。仅仅是因为此前的治理行动,往往是按照不同学科各行其是,不同行政单位分别规划治理方案,从而在无意中造成相互之间难以协调,治理的方略难以统一,具体的治理操作往往各行其是,这才是治理成效达不到预期目标的关键原因所在。
事实上石漠化灾变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成灾的原因仅一个,那就是地表植被的生物多样性水平遭到了人类不合适利用方式的干扰,从而派生的负效应。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直到20 世纪中期,我们今天看到的石漠化灾变表现得并不明显。相关各民族的社会经济,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还能产出诸多的名特优产品足以供应国内外大市场的需求。石漠化灾变的蔓延,其实是以大规模推广种植单一粮食作物而派生的负效应,这样的做法恰好是当地各民族传统资源利用方式的对立面。只有正确认识到各民族本土生态知识和技术技能对环境的实用性价值,在行政管理层面,在科研的层面上都达成共识,那么凭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再起用,凭借文化的常态化运行,石漠化灾变才可以做到在常态化生产的同时实现自然恢复,而且巨额的投资和人力、物力的消耗,都可以大大节约,也能实现对原有藤乔丛林生态系统的恢复。
所谓藤乔丛林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类型,主要分布在石灰岩、白云岩大面积出露的中低海拔山区,越是温暖湿润的地带,这样的生态系统分布面越广,生物多样性水平越高,生命物质和生物能,单位面积产量越高。这是因为在温暖湿润的大气环境下,出露地表的石灰岩和白云岩,溶蚀作用发展会极为迅速。地表崎岖不平,地下伏流、溶洞密布。原先地表的珍贵土壤资源,都会顺着溶洞和岩缝开口被流水携带入溶洞中去,从而导致地表的土壤资源稀缺。以至于原有的植被,一经人类扰动,生物多样性水平有所下降,就会演化为牵连性的灾变后果。随着生物多样性水平的降低,生物物种间的相互依存就会丧失,生态系统对地表的覆盖度就会降低。流水的冲刷作用和地下的溶蚀作用就会加快,从而生态系统自身就会走上萎缩的道路。如果人类利用的方式不改变,石漠化灾变也就不可避免了。正确的灾变救治方法,就是需要各地区各民族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启用各民族本土知识和技术技能。按照传统的生产方式去利用,哪怕是最重的灾变带,也实施有效的利用,才是正确的做法。具体的操作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以各民族此前种植农作物的经验记忆为依据,去找寻和发现地下含有土壤的溶蚀坑和岩缝的开口,但不能用于种植常规的农作物,而只能种那些地下带有块根的藤蔓植物,或者是有经济价值的低矮灌丛。目的是让这些作物长大后,其藤蔓和叶片能够最大限度将裸露的岩石和砾石遮盖起来,以此抑制当地可贵水资源的无效蒸发。
第二,同样是借助当地各民族传统本土知识,收集动物的粪便或者苔藓类、蕨类植物的孢子,撒播在已经被藤蔓植物所覆盖的岩石上,进行引种。这些低等植物只要不直接暴露在阳光下,即使没有土也可以旺盛地生长,将整个裸露的基岩覆盖起来,并且能够发挥截留大气降水的功能,缓解缺少水土的缺陷。
第三,及时的引进当地已有的低等动物以及相对耐旱的低矮植物,以此恢复相关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水平,靠动物的粪便在地表提供更多的有机质,以缓解水土垂直流失的趋势。
第四,也是按照当地各民族的经验,引进有经济价值的草本或者灌木类、藤本类的农作物,如中药材、纤维植物、香料植物、油料植物等,以期更多层次的覆盖裸露的基岩和砾石,确保看不见岩石,只看得见绿色植物。
第五,定植有重大经济价值和可持续发挥经济价值的木本作物。如可以因地制宜考虑种植桄榔木,桄榔木全身都是宝,其桄榔子的药用价值很高,桄榔粉则是药食同源的食品,广西龙州县的桄榔粉已经成为地理标志产品,桄榔木的树干部分可以拿来做家具、筷子、笔筒等物品。
以上五个操作,必须严格按照以上顺序推进,但需要整个石漠化灾变区各民族协同推进,切忌各自为阵、各行其是。具体的操作,只需要激励各族乡民按上述次序推进即可。因为相关的种植知识、技术和技能,各族乡民均已具备。只要鼓励他们做,他们会做得很好。接下来只要不再扰动这样的生态格局,那么即使持续产出,也不会妨碍整个原有的藤乔丛林生态系统得到完全恢复。
综上所述,本土生态知识是不同民族的经验积淀,所包含的生态智慧与技能可以帮助我们突破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限制,凭借最小的投入获得现代自然科学难以获得的古代生态资料,抵御自然风险,规避学科分野的干扰。本土生态知识也是省钱省力的生态建设的经验总结,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针对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在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当然需要大力推广运用,但在这样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忽略各民族本土生态知识和技术技能的特殊价值。因为他们是落实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抓手和路径。在地性强,可操作性大,普及面广,因而只要对这样的本土知识和技术技能,在现有的学术水平上,做出其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验证,并上升到政策层面,加以统一规划,协同推进,那么不管是生态维护、经济发展、生态恢复都可以合为一体,协同推进,将生态文明建设熔铸于常态化的文化运行和生产生活中去。相关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就可以实现事半功倍,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