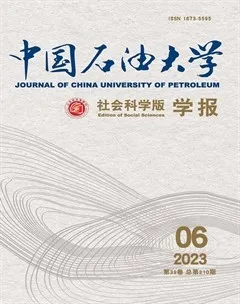气候变化风险的系统不确定性及其规范因应
2024-01-16杜健勋黄一帆
杜健勋 黄一帆
摘要:风险的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揭示了气候变化风险的系统不确定性,气候变化风险互联、级联影响的系统化倾向及其在生成结构、发展过程、影响受体上的不确定性,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规范因应提出了挑战。现有政策和法律体系为气候变化风险的应对提供了初步的规范基础,而渐趋停滞的气候变化综合立法、分散游离的气候变化相关立法、政策与法律的发展不均衡,又显示出气候变化风险因应规范体系应对系统不确定性的困境。在此双重背景下,气候变化风险的规范因应须重新审视气候变化的风险特征与规范路径,明晰系统不确定性对规范因应协同性、社会性、动态性的功能期待,以及系统不确定性下规范体系政策和法律交织的应然架构。在此基础上,通过气候变化风险因应政策话语的法制转译,实现气候变化风险因应既有规范架构的系统优化,进而通过抽象性和实施性政策的协同转化、政策法律化限度判断的民意考量、政策法律化主体和结构的动态调整,实现对气候变化风险系统不确定性的功能回应。
关键词:碳达峰碳中和;系统性风险;不确定性;政策法律化
中圖分类号:D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3)06-0073-11
一、引言
气候变化作为在自然中生成的风险,对其因应的研究从来就不止是法学,甚至不主要是法学。只有当气候变化风险的社会建构渐显而具有价值判断的色彩时,法学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研究才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当我们以法学的规范视野为起点去思索气候变化风险的规范意蕴时,更要从法学之外的知识和方法出发,去审视气候变化风险特征对规范因应的功能期待。
自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来,“双碳”或“气候变化风险应对”高频作为研究背景或内容进入各个学科的视野。法学领域关于“双碳”或“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的论文数量较为丰富,大部分文献聚焦于政策目标实现的整体性法治保障[1-2],或是政策目标规范化的立法、司法、守法等具体路径[3-6]。关于气候变化风险特征对于政策目标法治化、规范化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少,涉及该领域的研究也仅仅片段性地对气候变化的复杂性、跨界性、不确定性进行了描述,缺乏系统化的研究,鲜有的较为全面涉及气候变化风险特征的文章也仅仅将其作为背景而非逻辑基点予以研究。[7-8]以风险特征为逻辑基点的气候变化风险规范因应尚待深入、系统地研究。本文拟通过对气候变化风险特征的全面剖析,尝试揭示气候变化风险特征的演化机理及功能期待,以此为基点,探索气候变化风险因应的既有规范框架对气候变化风险特征的回应。
二、系统不确定性:气候变化风险规范因应的特殊难题
风险的特征分析为气候变化风险的规范因应预设了情境,是本文的研究前提。Otway等较早提出了风险特征分析视角的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之分,前者将风险视为具有危险性质的物理属性,一种独立于主观价值的客观事实;后者将风险视为具有社会建构的属性,一种不能够独立评估主体的客观实体。[9]
气候变化风险具有自然建构与社会建构的双重属性。自然建构的气候变化风险本体以一种系统性的方式展开,其社会建构并未与本体分离,而以认识论视角纳入的方式叠加在气候变化风险的自然建构之上,随着社会建构不确定性的凸显,气候变化风险由系统性发展为系统不确定性。故气候变化风险系统不确定特征的揭示应综合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视角,以展现气候变化风险规范因应情境的全貌。
(一)气候变化作为一种系统性风险
风险的实证主义认为,现实与观察之间存在一种镜像关系,风险被视作可能性的大小或否定性的范围。从实证主义视角来看,气候变化是一种典型的系统性风险[10],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DRR)在《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2022》中指出,系统性风险的概念界定应以以下观念为基础:政策、行动或灾害事件的不良后果风险,取决于受影响体系的要素如何相互作用,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可能会加强或削弱体系的整体效应,互动进程的正反馈或负反馈也会相互影响。[11]系统性风险的主要特征为时间维度上的演变性和空间维度上的复杂性。气候变化符合系统性风险的特征。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风险—灾害—危机”三位一体的连续综合系统。[12]气候变化的风险是指气候变化引发某种损失的可能性,是未发生的可能性;气候变化的灾害是指气候变化引发某种损失的状态,是已发生的事件;气候变化的危机则是指由气候变化引发某种损失所造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是已产生的影响。气候变化的风险及其影响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累积和显现,风险在前,灾害与危机在后,经历一个由刚开始的量变发展为质变,致使风险爆发为灾害乃至危机的过程。其次,由于气候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的紧密联系和交互影响,气候变化往往具有跨时空、跨部门的大尺度特征,这使得其风险及后果易在自然和社会系统内及系统间传导、转移,从而形成复杂的风险互联与级联系统。[13]例如,气候变化风险会通过产业网络在社会经济系统中传播,在食品—能源—水系统中产生直接风险和互联风险。一方面气候变化风险会对单一系统造成直接风险,例如,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降雨和高温会导致农作物减产,直接引发食品供应链风险,而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高温和干旱也会导致电力需求上升(尤其是空调降温需求)、电力(尤其是水电)供给下降,引发电力供需不平衡的能源风险;另一方面,气候变化风险会在系统之间传递而产生互联风险,例如,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干旱会造成水力发电量下降和冷却水短缺,从而影响能源系统的安全,而能源供给量下降和能源价格上涨进而对食品的生产、仓储、消费等环节造成影响,气候变化引发的能源风险会间接传导到食品系统中。
(二)从系统性风险到系统不确定性风险
实证主义视角主要通过共识性较强的科学知识来认识气候变化风险,揭示气候变化风险的系统性,但简化了对气候变化风险不确定性的分析。而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性,现实观察并不是在自然世界的“真空”中进行的,风险的可能性与否定性后果受到认知、文化等因素限制。风险认知、风险文化是相对主义视角分析的重要方面①,由于社会建构要素的考量,相对主义视角下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的“可计算性”②受到质疑,气候变化风险的不确定性凸显,系统性风险向系统不确定性迈进。
1.风险生成结构的不确定性
从风险的生成来看,风险有社会建构的属性。世界本无风险或遍布风险,风险的重要性不在于风险本身,而在于其附着对象,风险是被“制造”出来的。[14]在Fischhoff的风险感知—认知理论下,风险不仅与现象本身的概率和后果相关,也与风险感知者的心理因素相关。[15]心理测量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体验的分析模式,而情感“从来就不是判断真理的标准,它取决于教育、习惯、职业、禀性等, 总而言之是一种偶然”[16]。当气候变化风险进入个人情感叙事后,主观性和变动性的增强使得对风险感知者“多安全才算安全”(how safe enough is safe)的分析将更具不确定性,风险的生成结构从自然不确定占主导向更加复杂的社会不确定占主导转变。
2.风险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
从风险的发展来看,如前所述,气候变化是一个“风险—灾害—危机”
三位一体的连续系统。然而风险发展为危机的因果关系往往是隐匿的,只有当作为损害状态的灾害事件爆发之后,这种因果关系才会显露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气候变化风险作为“信号”会受到公众、科学家、规制系统等“放大站”的影响而使得不确定性“剧增”或“衰减”,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揭示了风险不确定性的加剧。[17]例如,在公众层面,受制于知识有限和信息短缺,一般民众不会将社会公共安全与气候变化风险联系起来,更多是将其与社会关系失调、社会结构失衡相联系,气候变化风险与社会公共危机的因果关系是隐性的。与此相对,这种因果关系对科学家则是显性的,一项科学研究表明,“当气候变化向极端高温趋势变化时,人际间暴力频率会增加4%、群体间冲突频率会增加14%”[18],在科学家的视野里,气候变化风险会间接地影响社会公共安全。在整体社会层面,只有当气候变化风险以极端天气等灾害性事件的方式,被规制主导者重视、被普通老百姓接受时,气候变化由风险演变为社会公共安全危机的因果链条,才在全社会层面得以显现。③
3.风险影响受体的不确定性
从风险的影响来看,由于自然、社会系统间与系统内的交互,气候变化风险自身呈现出互联和级联的系统化样貌。然而,气候变化风险发展为灾害后的损害范围和程度不仅与风险本身相关,还与风险受体的脆弱性相关。脆弱性通常是指受体在外界干扰下容易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程度或状态。[19]以气候变化风险造成的贫困危机为例,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确定的集中连片区域中,有11个与生态环境脆弱区域重合,这些地区多位于胡焕庸线以西,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弱、敏感性强,导致气候灾害暴露性高、适应能力弱,由生态环境条件引发的气候变化脆弱性加剧了贫困危机的爆发。[20]由于气候变化脆弱性在自然和人类系统的动态分布,较大的区域差异使得气候变化风险更加难以分析和规制,气候变化风险向系统不确定性发展。例如,华北地区、华中地区作为重要的农业产业基地,农业产业面积广但基础条件差,面临着气候变化风险与农业脆弱性叠加的风险。但是,华北地区因水资源承载力不足而常年缺水,其农业脆弱性更多与气候变化加剧的干旱灾害叠加,而华中地区位于長江流域,气候变化加剧了长江流域的丰水期暴雨、枯水期干旱,其农业脆弱性更多与气候变化引发的干旱和暴雨洪涝灾害叠加。再如,华南地区、华东地区人口稠密、城市化比重高、大型与特大型城市较多,都面临着气候变化风险与城市脆弱性叠加的风险,而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发展不均衡、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也加剧了气候变化风险不确定性的叠加。[21]总而言之,气候变化脆弱性因植根于特定地区的自然、人文状况而具有“当地”的特殊性,对其脆弱性的分析也会受到“当地文化的自然而然的、固有的东西”影响而成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22],脆弱性的不均衡分布和阐释的地域性关联使得气候变化风险转向系统不确定性。
三、系统不确定性下气候变化风险规范因应的实然状况
一方面,因应气候变化风险的规范体系应当对系统不确定性予以回应,并且这种回应须建立在我国现有的政策和法律体系之上,这意味着,现有的政策和法律体系成为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系统不确定性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其困境又成为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系统不确定性的现实阻碍。
(一)法律体系化程度不足,难以发挥因应的法制性力量
从宪法中生态文明的纳入、国家环保义务的规定,到部门法中散见的减排、适应气候变化、能源低碳发展等条款,逐步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支撑,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为重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初步法律体系。然而,体系化法律的形成应当符合内容完整、前后一致、结构合理、逻辑严密的形式理性要求和以法律理念为基石的价值理性的融贯。[23]在上述初步体系之中,虽然法律条款繁多,但体系化程度不足。
1.渐趋停滞的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综合立法
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把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立法纳入立法工作议程。然而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至今尚未出台直接针对气候变化影响及其风险应对的法律。一方面,学界对气候变化应对综合性立法的制定已经进行了相对系统的研究,虽未考量到气候变化不确定性的深层维度,但也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系统性和社会复杂性要素进行了考量④。然而由于综合性法律文本的缺失,无法将应对气候变化的直接目的确立下来,更不能满足对气候变化立法精细化构建和体系性融贯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综合性立法的缺失,分散的地方立法规范和间接规制规范也缺乏上位法依据和全局性统筹。例如,山西省、青海省分别出台了气候变化应对的地方性法规,对适应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等内容作出了规定,突出了气候变化风险的系统应对和地方性特色,但由于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涉及碳排放总量控制、碳排放核算技术标准、碳排放交易市场运行等事项,需要国家层面的立法予以顶层建构,综合性的国家立法缺失反映了法律的体系化不足,难以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系统不确定性。
2.分散游离的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相关立法
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的相关立法,是指没有直接针对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的立法目的,但其协同效应足以产生气候变化风险规制功能的法律。按照气候变化风险系统性演化的时空之分,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与气候变化所致灾害、危机管理相关的法律,主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下简称《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以下简称《气象法》)。2007年出台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主要针对2003年“非典”疫情中暴露出来的应急管理制度统筹不利、协调不足、配合不够等问题,能够较好地应对一般性常规突发事件,然而在高度不确定、全面、复杂、长期的全球性危机面前展露出不足。[24]此外 ,《突发事件应对法》也未能协调好与风险管理的关系,例如,该法第2章“预防与应急准备”中,将应急预案制度置于风险评估制度之前,使得风险评估制度长期被架空。重事中事后处置、轻事前预防的《突发事件应对法》,难以有效规制作为全球性危机的气候变化风险。《气象法》第1条规定:“为了发展气象事业,规范气象工作,准确、及时地发布气象预报,防御气象灾害,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气候资源,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气象服务,制定本法。”这表明该法更多是将气候作为一种资源予以合理利用,而忽视将气候作为一种风险予以规制,《气象法》对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的支持不足。
另一类是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能源法等法律。一是环境保护法体系。首先,作为环境保护法体系的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第1条规定,立法目的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为气候变化风险的系统性應对提供了基础。但从立法技术和规范上来看,立法目的的彰显应当有一定的法律规则作为支撑,《环境保护法》中关于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的具体规则付之阙如,难以为气候变化风险规范因应提供有效支持。其次,由于减污降碳在总体上有显著的正协同效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大气污染防治法》)是与气候变化风险应对关联紧密的法律,该法第2条第2款规定“将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明确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从体系解释上来说应当服务于该法第1条“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目的。然而,由于减污降碳在某些领域不具有协同效应甚至是负效应[25],再加上温室气体是否属于大气污染物,在立法上语焉不详、在学界存在较大争议⑤,无论是从科学上还是规范上,温室气体减排并不应然地指向改善大气环境治理。再次,环境影响评价法律体系为气候变化环评提供的支持并不全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下简称《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条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从法律实践来看,评价范围限于气候变化通过规划和建设项目间接造成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加之由于温室气体未被纳入“污染物”的范围,规划或建设项目的环评很容易排除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的间接影响;即使未排除气候变化间接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但由于气候变化风险造成的生态或环境影响往往是跨国境、大尺度的,这使得个别计划导向(从战略环评在我国的发展受阻可看出)、议题处理方式分割化的《环境影响评价法》难以承担对气候变化风险有效规制的制度功能。[26] 二是自然资源法体系。以发挥固碳作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以下简称《草原法》)为例,《森林法》和《草原法》分别在第28条和第42条对森林和草原“调节气候”的功能予以明确,从法律实施的效果来看,两部法律通过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的方式间接减轻了气候变化风险,但由于具体规则的缺失,规范的指引功能是有限的。另外,《森林法》《草原法》的立法目的主要是“合理利用资源”“保障生态安全”“改善生态环境”,并未明示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立法意图。三是能源法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通过“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立法表述,明确了“碳减排”“低耗能”的意愿,发挥着气候变化风险规制的间接作用。然而,该法未能及时回应“双碳”背景下不断推进的能源体制改革,存在立法滞后性,也未能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意图置于法律体系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旨在通过“促进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等方式,实现“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目的,暗含推动“碳减排”的意愿,但其立法的主要目的仍是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而温室气体在现行法中未被规定为“污染物”。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其他能源单行法的立法目的更多旨在合理利用资源、保障能源安全,未直接就气候变化应对作出规定,难以为气候变化风险规制提供法律保障。
(二)法律与政策发展不均衡,难以形成规范的体系性合力
1.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政策的主导性地位
相较于法律的体系化不足,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的政策体系较为成熟,在气候变化风险规范因应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从《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气候变化风险应对开始,我国从战略布局、目标宣示、总体规划等宏观谋划到温室气体控制、碳排放权交易、林业碳汇交易等具体行动,全方位为气候变化应对提供了政策指引。在“双碳”目标驱动下,气候变化风险规制政策以气候变化减缓或适应的战略行动为主线,在国家、部委、地方、产业层面已经相对系统地展开。现有的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政策是相对体系化的。从减缓政策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直接对气候变化减排目标进行了设定,作出碳排放强度和总量双控、减污降碳协同推进、生态碳汇系统提升等总体部署,全国18个省在其指引下发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或相关规划;同时,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委就碳交易市场、产业政策、能效政策也作出了具体规定。从适应政策来看,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应急管理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业农村部、林业和草原局、气象局、能源局等部委联合制定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为当前阶段气候变化风险的适应作出总体谋划,在其指引下,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林业和草原局、能源局等部委就碳汇政策、农业政策、水资源政策、林业和生态政策、环保政策、金融政策也作出了具体部署。
2.政策与法律发展不均衡的体系性困境
法律与政策的不均衡发展使得气候变化风险规范因应难以发挥制度合力。首先,超前于立法的政策缺少明确的法制约束,使得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的行动只是临时、短期的政策性规定,难以为其行动目标的实现提供稳定、有效的法律预期,容易滋生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违法行为。其次,滞后于政策的法律难以贯彻政策的要求。实际上,政策发展较为成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政策工具本身的灵活性,面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系统不确定性,灵活的政策工具可以适时地因应气候变化风险在时空维度上的延伸和拓展,逐渐形成相对完备的政策体系并可灵活调整。而法律的调控具有确定性和有限性,其制定和修改也有更严格的程序,难以对相对不确定和系统性的政策要求予以适时回应。例如,自2020年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提出以来,相关政策体系不断向纵深发展,但2021年提请审议、2022年实施的与湿地碳汇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仅在“湿地修复”中片段性地提到修复措施的碳汇功能,未能较好回应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要求。同时,2021年修订的与草原碳汇相关的《草原法》也未对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要求作出回应。
四、系统不确定性对气候变化风险规范因应的要求
气候变化风险规范因应对系统不确定性的回应不足,反映了规范体系对于风险特征的审视不够。故应当重新审视气候变化的风险特征,以明晰系统不确定性对气候变化风险规范因应的功能要求和系统不确定性下气候变化风险规范因应的基本架构。
(一)规范因应的协同性
从时间维度上看,由于气候变化风险—灾害—危机是一个演变的连续系统,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风险、灾害、危机的管理也理应是一个全过程的应对体系:风险管理在前端,灾害应急和危机管理在末端,气候变化风险管理应当与灾害应急、危机管理协同,以发挥制度合力。这就要求“拟议形成”的气候变化应对法、“风险预防转身后”的环境保护法[27]、“双碳目标”和“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的相关政策作为“阀门”,在前端发挥好风险的预先规制功能,同时与具有灾害应急和危机化解功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气象法》等法律以及相关政策实现功能上的配合。
从空间维度上看,气候变化风险在自然与人类系统交互的过程中形成了互联和级联风险。故在风险应对过程中,一方面,应当协同考虑气候变化引发的气候系统风险与其他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双向交互,这不仅要求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立法,在规范制定和优化时应当综合考量环境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能源合理利用的目标;也要求环境法、自然资源法、能源法、气象法等既有实证法律,在实现自身特定目标时兼顾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的目标实现。另一方面,由于气候变化所致自然风险会通过其他系统传递到次级系统,应当对风险跨系统后级联传导的潜在链条予以梳理,在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立法综合其他环保领域目标时,审慎探索其具体路径;在其他环保领域立法兼顾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时,严格划定其具体边界。
(二)规范因应的社会性
气候变化风险不仅关乎自然事实,其生成、发展、爆发的全过程都受到风险感知、风险文化、社会背景要素的影响,这意味着气候变化风险的规范因应不仅仅是一个事实识别的过程,还应当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气候变化风险的规范因应不仅要从整体上凸显其规范立场,在风险规范因应的具体环节也要实现气候变化风险的社会性回应。
首先,在气候变化风险识别环节。作为客观事实的气候变化风险在规范意义上由法律界定,根据剩余风险、风险、危险的三分理论,法律所应对的风险范畴是指既在损害的生成概率上不具高度盖然性、又可通过适当的预防和控制措施予以排除的风险。前者通过经验法则判断与具有高度盖然性的危险加以区分,后者通过经济、社会的成本效益分析与社会应当忍受的剩余风险加以区分。实际上,無论是作为已知事实或生活经验的经验法则,还是经济、社会成本效益分析的过程和结果,都是一个范围而非一个确值,为法律确认和界定留下了空间。进而,由于气候变化风险的生成受制于受众的风险感知,即如果某一风险是受众自愿承受的,那么其损害生成概率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就无关紧要了;同理,如果某一风险是强制施予受众的,那么其损害生成概率在某种程度上就无须考量了[28]173。这就要求气候变化风险规范因应在对风险定义和范围规定的过程中,应当对于“自愿性”等受众的心理要素进行特别考量。
其次,在气候变化风险评估环节。气候变化风险的社会建构使得价值中立的定量分析方法存在局限,不同主体的价值偏好应当被纳入风险评估的过程中。实际上,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调整经“气候变化—拟议项目—环境影响”间接产生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气候可行性论证制度调整“气候变化—拟议项目”中的气候影响,在气候变化风险因应的规范框架下,二者都应评估公众对于气候变化风险的“关注度”[29],将风险受众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熟悉度和既往经验、对气候变化风险本质和影响的理解、对风险规制者的信任程度等要素[28]173纳入气候变化风险评估的范围中。
最后,在气候变化风险决策环节。面对系统不确定的气候变化风险,政府不再是唯一的专家:一方面政府会因为没有充分审视内部或周围环境,存在对风险特征感知缺乏的问题[30];另一方面,“民众的知识也许欠缺清晰的科学思维与逻辑,但这恰恰可能是真实世界的运作生态与宝贵的生活经验”[31]。 所以气候变化的风险决策不应仅由科学理性主宰,社会理性也应当参与到风险的决策和行动中。具体来看,一是作为规制主导者的政府官员,在制定和实施气候变化应对法律或政策的过程中,不仅应从技术和经济维度考虑,以寻求真相和经济效益,也要从政治和道德的维度考虑,以回应民意、衡平民众的价值冲突;二是作为规制相对方的公众,不能仅消极地接受风险,而应当作为主动的规制主体,参与到气候变化风险的规范因应过程中,这要求优化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既有规范框架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在制度建构、实施中确保公众对气候变化风险决策的参与,使得社会理性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得以表达。
(三)规范因应的动态性
从实证主义模式到相对主义模式,气候变化风险社会建构性的揭示是对风险结构的再认识,由于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的难以测量、风险文化的非线性放大、社会背景要素的不均衡分布,这种再认识需要不断面对风险“可计算性”的降低。因此,全面、准确地掌握风险的真实图景逐渐成为气候变化风险规制难以实现的事情,这使得知识有限和信息短缺成为气候变化风险规制的重要场域。在这种场域下,气候变化风险的规范因应应尽可能地将特定时空的风险受众、社会理性纳入到规制的主体和知识结构之中,通过规范的社会性因应,最大范围地补足风险规制所需的信息和知识。
更重要的是,应意识到特定时空上“有限”的信息和知识会随着时间的流变而更新,从不确定走向相对确定或更加不确定的状态,所以气候变化的风险规范也应当随之进行动态调整,以实现风险的适应性管理。[32]根据复杂适应系统理论,面对系统不确定性的动态调整应当是一个“刺激—反应”的过程,在系统及其环境面临不确定性变化时,主体应通过自动调整主体结构和系统结构,在与变动环境的交互中分化、聚合而产生新的主体和系统,以保持结构平衡,进而减少不确定性。[33]为了实现这种动态调整,一是作为气候变化风险因应规范结构的政策和法律,应当处理好确定性与灵活性的关系:政策通过法律化和自身稳定性机能的发挥、法律通过政策化和自身适应性机制的发掘,不断以自调和互动的方式实现对于气候变化变动事实的调整[34];二是作为气候变化风险规范因应主体的决策者和公众,应当放弃风险决策的“毕其功于一役”,转而通过不断学习和持续反思来面对知识和信息的拓展[35];三是应回应风险受体脆弱性的不确定性分布,气候变化风险的规范因应在架构和实施过程中,要对风险脆弱性的分布状况及其“地方性知识”予以挖掘,在地方政策试点或中央立法经验成熟后致力于横向、纵向拓展的过程中,应考量特定地域自然和人文的脆弱性差异,同时基于“地方性知识”难以全然普遍化的特质,还要对地方性特色加以突显。
五、系统不确定性下气候变化风险规范因应的应然路径
气候变化系统不确定性的风险特征对其规范因应提出了协同性、社会性、动态性的功能要求,应当在气候变化风险因应政策和法律发展不均衡的既有困境中展开。一方面通过政策法律化实现既有规范框架的系统优化;另一方面,在规范框架优化的过程中实现对系统不确定性的协同性、社会性、动态性回应。
(一)系统不确定性下气候变化风险规范因应的基本架构
1.政策与法律相交织的规范架构
法律与政策在经济基础、社会目标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在实施方式和稳定性等方面存在区别[36],政策和法律不断交织、互动所共同构成的规范体系,对于系统不确定性下气候变化风险的规范因应十分重要。
一是由于气候变化风险是依托在自然和社会交织的空间结构与不断流变的时间结构之上的,一方面气候变化风险的规范因应应在广阔场域中对经济发展、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等目标综合考量,除了直接、强制式的法律规制手段外,还需要经济规制等间接、协商式的手段,这就为政策的宏观指导留下了空间;另一方面,由于法律的确定性和普适性追求,有关气候变化风险因应的法律总是在有限的时空中生成,难以在因应气候变化时布局长期性目标、动态调整阶段性任务,而政策可以以其宏观性和灵活性对此予以补足。
二是虽然法律与政策由于实施方式和稳定性的差异而具备分化的制度功能,但在气候变化风险规范因应的过程中,二者应呈现出互动的状态。一方面,为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不确定性,相对稳定的法律会出于灵活性的考量,在法律建构和实施中应对相关政策予以偏好和适用,以法律政策化的方式拓展法律的治理功能;另一方面,为回应气候变化风险因应的规范化诉求,气候变化因应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需要合理配置相关权利(力)和义务、厘清因应行动的法治边界,通过政策法律化的方式对符合条件的政策进行立法化处理。在气候变化风险规制领域,政策与法律作为具有内在合理性的指引工具,应共同作为规范架构的主体为气候变化风险治理目标的达成贡献力量。
2.政策话语法制转译的路径选择
政策和法律交织互动基本架构的厘定为气候变化风险系统不确定性的规范因应提供了框架性基础,而框架性路径的具体选择又应当在法律体系化程度不足、政策與法律发展不均衡的既有困境中展开。卢曼的法律系统理论为此指明了出路,他认为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必然存在相互开放、联系的关系[37],这意味法律与政策之间存在衔接和互动的通道,即可沟通性。具体到气候变化风险系统不确定性的规范因应,表现为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的政策法律化和法律政策化。法律政策化具体是指法律通过框架性结构的设定、管制性制度的弱化,从而突出政策的整体方向、原则和基础性制度;政策法律化是指将政策的目标和规定以法的价值、目的、原则、规则等形式予以规范。[38]在气候变化风险规制政策主导、法律体系化不足的现实境况下,政策法律化具有对公共政策所涉权力合理约束、以条款转化推动法律体系化的功能,理应成为改善政策与法律发展失衡的良方,是规范因应气候变化风险系统不确定性的合适路径。
(二)政策法律化对系统不确定性气候变化风险的回应
1.抽象性和实施性政策的协同转化
政策是指“党和国家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或是党和国家为了完成某一历史时期的任务而制定的行动计划和方案”[39]。在此定义基础上,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政策可分为抽象性政策和实施性政策,两者在政策法律化的具体路径上存在区别。
抽象性政策多以条款形式(不具备行为模式+法律后果的法律结构)将政策中的话语、目标、规定直接转化在立法中,这种转化虽不具备直接调整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法律关系的功能,但可以通过立法价值、立法目的宣示的方式,为后续立法和规则的细化提供指引。故应当通过条款形式将现有政策中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加强能源节约、增加生态系统碳汇、控制重点领域(工业、城乡建设、交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等减缓气候变化的总体部署,以及农业、林业、水资源、海洋、卫生、住房和城乡建设、生态系统保护等适应气候变化的宏观要求,规定在正在形成中的气候变化应对法之中。同时,在考量气候变化应对与相关法律协同和排斥效应的前提下,选择合适路径将“双碳”“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的政策目标融入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能源法等法律之中。例如,由于《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目的主要是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简称《水法》)的立法目的主要是合理利用水资源,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的目标可以直接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目的条款,而《水法》只有在涉及水资源、水工程保护的具体制度时才有必要和可能将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的政策目标纳入。
实施性政策多以条款实质转化的方式将部分政策以“行为模式—法律后果”的结构转化在法律规定之中。例如,2021年1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环境影响评价”;随后,2021年5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在“两高”项目内将碳排放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同年7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开展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的通知》,确定重庆、浙江、山西、河北、吉林、广东等地为试点地区,在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开展将温室气体排放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试点。经此,将碳排放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成为明确的政策目标,中央和地方也出台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和方案。将碳排放等气候变化因素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政策及其实践,涉及评价对象、评价主体、评价程序、公众参与、法律责任等一系列具体事项,在其试点成熟、满足立法条件时,应在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既有结构之上,以“行为模式—法律后果”的结构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立法之中。
最终,满足政策法律化条件的抽象性政策和实施性政策,分别通过形式和实质转化进入法律的政策条款和管制条款之中,政策条款以价值目标引领管制条款,管制条款以规范手段约束具体行为[40],协调统一地回应系统不确定性对气候变化风险规范体系的要求。
2.政策法律化限度判断的民意考量
气候变化风险因应的政策法律化存在条件限制,只有在相关政策符合法律系统的标志或对法律系统产生有效“激扰”时[41],法律这种“条件性程式”才会开放,有学者将该条件界定为:全局、成熟、稳定、立法必要[42]。全局是指法律作为具有最高位阶的社会规范,往往以一种普遍化的姿态纳入最大范围的社会生活整体,所以拟法律化的政策也应当具有对全局和长远利益予以规制的功能。气候变化风险应对作为一场广泛而持久的深刻变革,需要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推进,相关政策应满足法律化全局性、必要性的要求。成熟是指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政策被社会公众普遍认可、默许、接受和遵行,“认可”“默许”“接受”的判断具有很强的主体性特征,不能独立于事实,作为政策法律化的内在限度而具有价值判断的空间。因此,在判断是否成熟的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和立法者应当对公众的心理要素予以切实考虑,在一定时间内公开征集公众意见,以反映民意;另一方面,政府和立法者也应当提供制度化的通道,使得社会理性可以多渠道、多方式地进入立法和政策的视野。稳定是指气候变化风险因应政策自身并非“朝令夕改”,而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实质上是一种外在限度,作为实然的状况而无需价值加以衡量。
3.政策法律化内在结构的动态调整
一是主体间的互动。鉴于在气候变化风险规范因应中政府的主导地位,在政策法律化的过程中,主体结构的动态调整并非要对科层制组织机制彻底颠覆,而是在科层制基础之上通过对利益相关者、风险分担者最大程度的包容性面向予以实现。其一,政府的自我反思。政府与官员个人要加强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学习,由于危机后政府学习与变革的能力受限于政府危机管理的迫切性[43],一方面,系統不确定性的规范因应需要对既有权力结构进行较大的改变,或许会带来某些政治激励,但更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政府在较低预期的政治激励与较大的政治风险衡量下,往往选择不反思和不行动;另一方面,在知识和信息有限的场域下,风险演化为危机的因果关系往往是隐匿的,科学家给出的风险危机信号经由政府和民众系统等“社会放大站”的“熵增”或“熵减”而变得模糊、不确定,这更加使得政府对危机反思和采取行动的“迫切性”不足。所以在政策法律化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明确规定政府的风险治理责任、建立健全持续的跟踪反馈机制和政府的考核评价机制等方式予以补足。其二,社会的共同学习。在政策法律化的过程中,由于政府主导的风险治理发挥了对于科学理性、社会理性的吸纳功能,政府应与社会公众共同加入这个社会学习过程,协同进行知识生产,以尽可能地推动风险从不确定向相对确定的状态迈进。然而,受限于对知识和信息的掌握,社会的共同学习只能“逼近”而非“到达”确定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上述考量风险受众的心理要素、提供民意制度化表达的渠道,以实现社会性回应的目的不再是作出最符合科学理性的决定,而是作出最符合民众期待的决定[44],故对知识有限的考量和社会性的回应,也成为政策法律化过程中对知识和信息的流动进行回应的合适路径。
二是新结构的生成。为实现动态调整,政策和法律交织互动的规范结构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发生自组织化相互作用”[45]。政策法律化作为规范结构内部互动的重要方式,需要对外部变动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民众的生产生活需求予以回应。“双碳”和“气候变化风险应对”作为政策目标,需要通过贴合实际的政策试点、回应民众需求的制度探索,来推动政策的不断成熟,为气候变化风险因应的政策法律化提供源头活水,从政策法律化到法律体系化,最终形成气候变化风险规范因应结构的闭环更新。
三是脆弱性的考量。在政策法律化的过程中,要对各个地方的特殊性予以考量,在试点推广的过程中要考量其“地方特质”。例如,《关于开展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的通知》提出在河北、吉林、陕西等地开展试点,陕西以煤化工为重点行业,吉林以电力、化工为重点行业,由于重点行业同属于高能耗高污染,所以试点之间有一定的借鉴性。但由于电力和煤化工在能源类型、碳排放标准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既使在某地试点相对成熟,在进行推广时还要考虑地方之间的差异性,并且政策的“地方性知识”是独特生长于地方之上的,在将较为成熟的地方试点模式上升为普遍化的立法时,应当保留一定限度,对难以普遍化的地方性特色政策条款予以保存。
六、结语
尽管气候变化风险的因应应当在规范的视野中,但气候变化风险作为一个由自然科学研究渐次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并非自生成之初就直接进入了规制领域。事实上,气候变化风险具有自然和社会建构的双重属性,自然建构下的气候变化风险是一个“风险—灾害—危机”的连续系统,并对自然和人类社会产生了系统性的互联和级联影响,而社会建构下的气候变化风险受到风险感知、社会文化、社会状况的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自然和社会建构下的系统不确定特征成为气候变化风险规范因应的逻辑起点和现实挑战。因此,现有规范体系既要在系统不确定性下检视自身困境,又要回应系统不确定性的功能期待。据此,应从风险特征出发,以政策法律化的规范框架优化以及过程中协同性、社会性、动态性的功能回应来实现系统不确定性因应。此外,本文更多从宏观上讨论了气候变化风险特征的演化机理及其进入制度的合适路径,而对于具体制度的建构和调适还有待进一步深耕。
注释:
① 随着风险的研究进入风险感知和风险沟通等领域,社会建构要素的考量成为相对主义视角的核心。虽然相对主义视角下的风险感知—认知的心理测量范式、风险文化的研究范式、风险社会的研究范式、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的分析模式存在差异,但都强调由于社会建构要素的增强使得风险的不可计算性增强。
② “可计算性”是富兰克·奈特总结出的对“风险” 和“不确定性”的区分标准,前者所涉情境可通过先验概率计算或以往经验统计,所以结果的分布是已知的;后者由于所涉情境的唯一性使得无法对其进行分类,所以结果的分布是未知的。参见富兰克·奈特《风险、利润与不确定性》,王宇、王文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234页。
③ 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极端高温直接威胁社会公共健康,据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消息:欧洲遭遇罕见高温天气,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已经造成1 700多人死亡,世卫组织呼吁各国民众和政府远离高温,共同面对气候变化。据咨询公司益普索(Isop)集团的民调:20多个欧洲国家2.2万多名年轻人列举了“人类面临的三大严重问题”,其中近50%选择了“全球气候变暖”,排名第一位。
④ 法学相关研究逐渐意识到气候变化风险是嵌入经济社会结构之中的,气候变化风险的应对不仅需要减缓和适应风险本身,也需要协同化解社会经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社会问题。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目的上,冯帅提出“碳减排+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梁平等提出“促进低碳发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常纪文等提出“促进低碳发展、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和2060年碳中和愿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体参见:冯帅《论“碳中和”立法的体系化建构》,刊载于《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2期,第15-29页;梁平、潘帅《“碳中和”愿景下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的完善》,刊载于《重庆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第6-22页;常纪文、田丹宇《应对气候变化法的立法探究》,刊载于《中国环境管理》2021年第2期,第16-19页。
⑤ 关于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关系的研究,学界主要分为三种观点:一是应将温室气体纳入“大气污染物”,理由是这种方式是《大气污染防治法》应对气候变化最便捷的途径,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司法经验(参见唐双娥《美国关于温室气体为“空气污染物”的争论及对我国的启示》,刊载于《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1-4页)。二是不应将温室气体纳入“大气污染物”,理由是这不利于我国工业的发展(参见常纪文《二氧化碳的排放控制与〈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刊载于《法学杂志》2009年第5期,第74-76页;胡苑、郑少华《从威权管制到社会治理——关于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几点思考》,刊载于《现代法学》2010年第6期,第150-156页)。三是不讨论是否将温室气体纳入“大气污染物”,转而寻求两者协同效应的最大化(参见徐以祥、刘继琛《论碳达峰碳中和的法律制度构建》,刊载于《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20-31页)。
参考文献:
[1] 秦天宝.整体系统观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法治保障[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2):101-112.
[2] 韩立新,逯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多维法治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21(9):1-12.
[3] 孙佑海.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策略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157-166.
[4] 杨解君.面向碳中和的行政法治保障[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1-16.
[5] 周珂.适度能动司法推进双碳达标——基于实然与应然研究[J].政法论丛,2021(4):13-22.
[6] 周娴,陈德敏.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反思与重塑[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10):115-123.
[7] 朱炳成.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规范应对[J].中州学刊,2020(4):56-62.
[8] 张忠民,王雅琪,冀鹏飞.“双碳”目标的法治回应论纲——以环境司法为中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4):44-56.
[9] Otway H,Thomas K.Reflections on Risk Perception and Policy[J].Risk Analysis,1982(2):69-82.
[10] Bi J,Yang J X,Liu M M,et al.Toward Systemic Thinking in Managing Environmental Risks[J].Engineering,2021,7(11):1518-1522.
[11]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Global Assessment Report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2022)[R/OL]. https://www.undrr.org/gar.
[12] 童星.風险灾害危机连续统与全过程应对体系[J].学习论坛,2012(8):47-50.
[13] 杨建勋,刘苗苗,毕军.气候变化风险互联网络及系统性管理[J].中国环境管理,2022(1):7-13.
[14] Douglas M, Wildavsky A. Risk and Culture[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5.
[15] Fischhoff B.Risk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Unplugged:Twenty Years of Process[J].Risk Analysis,1995,15(2):137-145.
[16] J·H·冯·基尔希曼,赵阳.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在柏林法学会的演讲[J].比较法研究,2004(1):138-155.
[17] Kasperson R E,Renn O,Slovic P,et al.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A Conceptual Framework[J].Risk Analysis,1988,8(2):177-187.
[18] Hsiang S, Burke M, Miguel E. Quantifying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on Human Conflict[J].Science,2013,341(6151):1235367.
[19] Turner II B L, Kasperson R E, Matson P A, et al. A Framework for Vulnerability Analysis in Sustainability Science[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3,100(14):8074-8079.
[20] 郑艳.气候变化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及其应对策略[J].环境保护,2021(8):15-19.
[21] 秦大河.气候变化:区域应对与防灾减灾——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事件相关灾害影响及其应对策略[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47-74.
[22] 吴彤.两种“地方性知识”——兼评吉尔兹和劳斯的观点[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11):87-94.
[23] 徐以祥.论我国环境法律的体系化[J].现代法学,2019(3):83-95.
[24] 钟雯彬.《突发事件应对法》面临的新挑战与修改着力点[J].理论与改革,2020(4):24-37.
[25] 阿迪拉·阿力木江,蒋平.推广新能源汽车碳减排和大气污染控制的协同效益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环境科学学报,2020(5):1873-1883.
[26] 叶俊荣.气候变化治理与法律[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5:174.
[27] 张宝.从危害防止到风险预防:环境治理的风险转身与制度调适[J].法学论坛,2020(1):22-30.
[28] 戚建刚.风险概念的模式及对行政规范之意蕴[J]. 行政法论丛,2009(1).
[29] 陈思宇.论将适应气候变化的要求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4):27-37.
[30] 黄杰,吴佳.中国大都市的“灰犀牛式危机”与政府风险治理模式的重塑——基于两个典型案例的分析[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5):79-94.
[31] 杜健勋.论环境风险治理转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10):37-42.
[32] 张宝.环境规制的法律构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98.
[33] 约翰·霍兰.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M].周晓牧,韩晖,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9:1-40.
[34] 周少华.适应性:变动社会中的法律命题[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6):105-117.
[35] 金自宁.科技不确定性与风险预防原则的制度化[J].中外法学,2022(2):504-520.
[36] 舒国滢.法理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00.
[37] 尼古拉斯·卢曼.社会的法律[M].郑伊倩,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2.
[38] 于文轩,胡泽弘.“双碳”目标下的法律政策协同与法制因应——基于法政策学的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4):57-65.
[39] 陈庭忠.论政策和法律的协调与衔接[J].理论探讨,2001(1):64-66.
[40] 郭武,刘聪聪.在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之间——反思中国环境保护的制度工具[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134-140.
[41] 杜健荣.法律与社会的共同演化——基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反思转型时期法律与社会的关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2):109-117.
[42] 陈潭.浅论政策合法化与政策法律化[J].行政与法,2001(1):53-55.
[43] 阿金·伯恩,保羅·特哈特,埃瑞克·斯特恩. 危机管理政治学:压力之下的公共领导能力[M].赵凤萍,胡杨,樊红敏,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152-175.
[44] 金自宁.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4):60-71.
[45] 张立荣,方堃.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的政府治理公共危机模式革新探索[J].软科学,2009(1):6-11.
Systemic Uncertainty and Normative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Risk
DU Jianxun, HUANG Yifan
(Economic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The positivism and relativism of risk reveal the systematic uncertainty of climate change risk, and the systematic tendency of climate change risk to interconnect and cascade impacts, as well as its uncertainty in the structure of generatio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and the recipients of impacts, have posed a challenge to the normative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risk. The existing policy and legal system has provided an initial normative basis for climate change risk response, while the stagnant comprehensive climate change legislation, the fragmented climate change-related legislation, and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policy and law show the dilemma of the climate change risk response normative system in coping with systematic uncertainty. Against this dual background, the normative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risks must reexamine the risk characteristics and normative path of climate change, and clarify the functional expectations of systematic uncertainty for synergistic, social, and dynamic normative response, as well as the apodictic structure of the normative system that interweaves policy and law under systematic uncertainty. On this basis, the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of the existing normative framework of climate change risk response sh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legal translation of the policy discourse on climate change risk response, and then the functional response to the systematic uncertainty of climate change risk sh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synergistic transformation of abstract and implementable policies, the public opinion’s consideration of the judgment of the limit of legalization of policies, and the dynamic adjustment of the main body and structure of legalization of policies.
Key words:emissi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zation; systemic risk; uncertainty; legalization of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