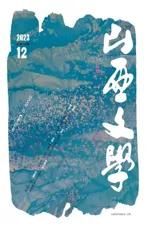除害
2024-01-11江红斌
江红斌
有天接到一项工作,让我去护理李庄镇病重不能下床的疯兰兰。我听了差点蹦起来,结结巴巴地说,她,她,她有刀……
仁爱路各家门前空地上种的蔬菜经常被偷,大家知道是疯兰兰所为,纷纷找她理论。疯兰兰永远不搭话,从身上掏出经常携带的水果刀恶狠狠地指着来人,眼里冒出怒火,让人们见了胆寒。
尽管多年过去,我清楚记得,疯女人兰兰刚被她父亲送回李庄镇时,她的口袋里就装着一把明晃晃的水果刀。而且,那次她父亲回省城时,她乘其不备,用那把刀在她父亲脸上捅了好几个血口子。那血流如注的情景让我每每想起来不寒而栗。
后来我转念一想,疯兰兰已经病得在床上起不来,哪里还会握刀子捅人!况且,我一个粗壮结实的男子汉难道还怕一把小小的水果刀?再说了,我这人极富爱心,岂有见死不救的道理。于是,我释然了,接下了这个工作。
疯兰兰的家在仁爱路上。她们全家早已随她父亲迁居省城,留下一所旧房子。疯兰兰自从患了躁狂性精神病后,赤身上房,见人就杀,危害四邻。父亲管不住,才把她送回老家,让她独自一人生活,大有让其自生自灭的意图。由于疯兰兰不是李庄镇人,镇里只能临时救助她,给些米面和油,却不能按时供应蔬菜。无奈,疯兰兰只好在仁爱路路边偷菜吃,偷到就吃,偷不到就忍。经过几年,在饥一顿饱一顿的岁月煎熬下,本就瘦削的疯兰兰变得像一张薄纸,走在李庄镇的街道上,仿佛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跑似的。
与李庄镇其他街道喧嚣热闹氛围截然不同,仁爱路寂寞冷清。每个院落的漂亮大门都死死关着,听不到惯常的鸡鸣狗叫,阒寂的街巷落下一片树叶都能让人心惊肉跳。偶尔,某个街门被人打开一条小缝,做贼一样露出头颅,左右看看没情况,倏然跳出门外,迅速锁上街门,逃也似地消失在仁爱路的尽头。我经过仁爱路的时候,大门后的锁眼里一只只独眼怒视着我,眼睛里喷着火,令我的后背发紧。仁爱路散发着肃杀的戾气。
疯兰兰的家在仁爱路中间,斑驳陆离锈蚀严重的两扇木门在邻居豪华气派的门楼衬托下愈发显得寒酸破烂。木门虚掩着,转动十分艰涩,我使出好大力气推开半扇门挤了进去。
碎砖块铺就的坎坷小路直通堂屋。堂屋门虚掩着,我推开门,一股闷热腐败的味道扑鼻而来,让我浑身一激灵。凭多年护理濒危病人的经验,我嗅到了死亡的味道。偌大的堂屋空旷而寂寥,几只破家具胡乱摆着,靠后墙的老式木床上堆着一堆破布。光线太暗,经过仔细辨认,我才在破布里发现一颗毛茸茸的头颅和一具破劈柴一样的身躯。
这就是疯兰兰吗,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记得疯兰兰刚被父亲送来时,袅袅婷婷,林黛玉一样的身材,在李庄镇粗笨的街巷里十分显眼。尤其是她那忧忧郁郁的清瘦面庞,让人瞬间记起金庸笔下的梅超风或《雷雨》里的繁漪。
疯兰兰的乌黑长发不知道什么时候剪掉了,蓬乱短发纠结一起垫在脑后,好像她的头枕着一只鸟巢。鸟巢上横着一张拖鞋底似的瘦脸,双眼半闭,眼窝塌陷,嘴唇皴裂结着厚厚的干痂,让人想到了死鱼。凭我多年护理经验判断,疯兰兰重度脱水了,必须迅速补水,否则马上会有生命危险。
我从随身水杯里倒出水,把水碗放在她的嘴边。疯兰兰感觉到了,使老大的劲儿撑着眼皮。她的眼睛晦暗无光,眼皮一眨不眨,死死瞪着我,很吓人。她就是不张口喝水。饮水自救是人的天性,她反行其道,令我疑惑。
我动了恻隐之心,一心一意伺候床上这具木乃伊似的、行将就木的疯子。为了让她迅速补水,我一趟趟到超市去买蜂蜜、鸡蛋、白糖、奶粉,忙碌让我无暇理会仁爱路大门里向我投来的怒视目光。我变着花样做好各种饮品端给她;她始终咬紧牙关不张嘴,只用眼睛死死瞪着我,眼里冒着火。那火仿佛会把一切燃烧。
一连几天,我徒劳工作着,眼里喷火的她日见衰竭。她离死神越来越近,我心痛不已,只恨自己没有起死回生的本领。终于有一天,在我眼睁睁的注视之下,疯兰兰熬干身体里的最后一滴水,永远闭上了那双喷射火焰的眼睛。
既然拦不住死神,我只有给疯兰兰找个妥善的归宿,才能心安。没有人要求我去办,但我要义无反顾干这个事情。
疯兰兰入土为安后,我却很烦躁,心里一直放不下她。我时常回忆起她最后时刻的冒火目光,在心里无数遍咒骂疯兰兰的父亲。这个在省城街头贩卖半辈子蔬菜、没文化的老顽固,在女儿与心爱的人私奔后,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疯兰兰吊起来往死里打!想起这些,我的身体仿佛被皮带抽过似的疼痛战栗,身不由己来到仁爱路,祈盼还能看到疯兰兰,想为她做些什么。
与我初来那天截然不同,仁爱路一下子热闹起来。各家的街门洞开,主妇们端着碗,站在街中心,嘴角溢满唾沫、扯着嗓子与邻居们大声说笑,仿佛要把几十年该说而没说的话一股脑儿说完似的。尤其是见到我来到仁爱路的时候,她们更是一个个激动万分,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纷纷跟我打招呼,把我当成为民除害的大英雄一样,夸我太了不起,终于把疯兰兰从仁爱路上弄走了。
也不知是受宠若惊,还是受之有愧,我听了热血上涌,有挥刀捅人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