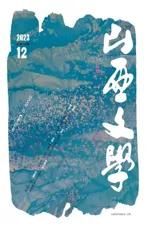不近不远
——读艾达《黑白分明的世界》有感
2024-01-11李苇子
李苇子
第一次知道艾达,是因为学校的另一位“著名校园作家”抄袭了她的作品,几位同事在群里愤愤不平,要为她讨个说法。我找来她的文章看,觉得,至少在语言方面,她有极高天赋。我始终觉得,语言能力是天生的,比如张爱玲对语言的独特感受,她说,时间是“无涯的荒野”,白房子是“薄荷酒里的冰块”,广告牌倒映在水里的影子“刺激的反冲的色素,在水底厮杀”。这些微妙的感觉,是创意写作课堂上,怎么都教不出来的。
后来,艾达参加了创意写作学院的征文大赛,获了一等奖,那篇文章是关于她阅读《红楼梦》的感受,某些见解和文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概是2016 年的某天吧,艾达来到我班旁听,在此之前,她刚上完一学年钟小骏老师的课。那时候,我的小组在做一本关于山西古村落的散文集。艾达也参加了这个项目组。半年后,她提交了自己的作品,文字相当华丽,酷似某旅游区的软文。我告诉她,文章写成了万能模板,假如我们将村名隐掉,便会发现,任意一个古村都适用,你丝毫看不出此古村非彼古村的独特之处。后来她就毕业了,又后来听说她考取了西北大学的创意写作研究生,又又后来,她写了几篇小说,让我提些建议。
之前,艾达给我的印象是,语言极好,但缺乏建构故事的能力。同事们私下交流,都担心她过度雕琢语言,最终成为安妮宝贝这样的作家。经过几年专业训练,艾达的变化很大,她的语感还是一贯的好,但,她已摒弃华丽的文风,开始学着使用平实的语言叙述故事,别管故事讲得如何,有了讲故事的意识,我们就会一点一点,通往故事讲述的大门。
《黑白分明的世界》最初的名字叫《美术艺考生》,是她写的非虚构。我觉得名字过于直白,劝她改。另外,我也不觉得这个作品是非虚构,其实有点儿像散文,还带有小说的某些气质,我甚至联想到了萧红的《呼兰河传》。总之,你很难给这篇八千字的作品归类。据说,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在发表之初,也曾引起过小说还是散文的讨论。
《黑白分明的世界》没什么大的矛盾冲突,也缺乏起伏的情节性波澜,人物是扁平的,假如当小说看,它的确缺乏太多太多。它有的是什么呢,或者说,这篇文章最打动我的地方在哪里呢?那便是,我们能从大量的细节处看到作者的写作天赋,她对现实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她是这么写双眼皮的:“光线会在你的两层眼皮间投下一个小小的阴影”。没错,这种观察人人都能做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主动观察的意识。假如说这个句子通过观察就能获得的话,那么,“除了画画,你一辈子也没有这个机会,盯着一个人看一整天。云朵有些感动。”“长时间画这种画,云朵觉得,仿佛自己的生活被简化了,收缩成一个黑白分明的概念的世界。”“云朵看到这样的画就会感觉心里很稳,没那么浮躁了。”“云朵在北京的十几天……一直有一种受辱的感觉,这种细碎的感受白天来不及咀嚼,晚上却像蚂蚁一样咬得你不舒服。”这些部分实在是需要一颗敏感细腻的心,才能恰如其分,将情感褶皱里最微妙的东西传达出来。我也见过很多作者,写了多年依然粗疏,这没办法。
《黑白分明的世界》能够引起我强烈的情感共鸣,大概还是因为,我和艾达有着同样的经历,我们都是艺考生,不同的是,我比她接触画画更早,我理解那种所有人将你视作异类的感受。还记得某位表妹曾用居高临下的口吻说我:“你学习肯定不好,学习好为什么要去学画画呢。”我心中猛然一凛,一方面是因为知道了自己在她心中的不堪,一方面是明白她代表着大多数人。在大众眼里,学艺术等于文化成绩不好,约等于学渣。我们的教育率先教会了我们要将人分成三六九等,我们永远没有学会,也不屑于学习如何尊重个体的不同选择。《黑白分明的世界》就呈现了诸种歧视——
理科生歧视文科生,文科生歧视艺术生,艺术生歧视体育生;大城市画室的学生歧视小地方的学生;北京的老师歧视外地的学生;画画好的歧视画画差的;就连面对至亲骨肉,父母也会更疼爱学霸儿子,而对女儿说,“行啦,我们对你没要求,你巴结着点你哥,以后要饭要到他跟前,让他赏你碗饭吃。”
作为“边缘”群体的一员,艾达对这一身份带来的“屈辱”表述得非常精准。那些微妙的心绪流动,那些倔强的尊严和在尘埃中开出花朵的期许,曾经一度,也是我的心境。但我几乎没写过自己学美术的任何经验,无论散文还是小说,也许因为我在那个环境里待得太久,久到早已麻木,久到认同了那些规则与歧视,也认同了一切反常。艾达告诉我,她只学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后来也没走艺术生的路,所以,她对这段生活记忆犹新,也能用细腻的文字进行还原。这给了我一个启示,关于作者和写作素材的熟悉度,也就是所谓的距离,太近,容易失焦,太远,又会过于概念,我们始终在失焦和概念之间寻找一个让人舒服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