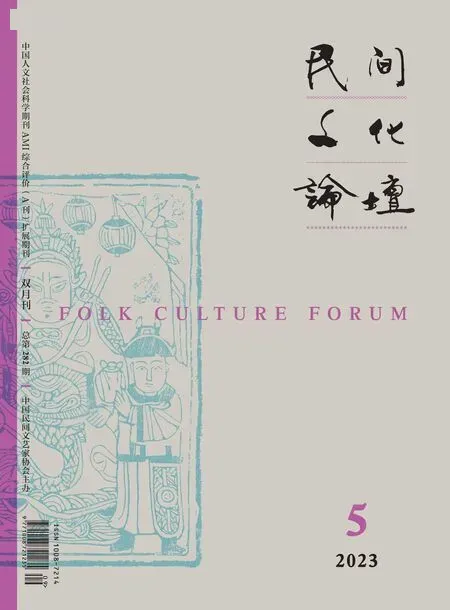殖民时代荷属东印度群岛影视人类学实践述略
2024-01-08阮艳萍代湘云
阮艳萍 代湘云
特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印度尼西亚成为欧亚大陆海上贸易的咽喉要地,也成为殖民扩张时代各国争夺的重要对象。在长达数百年的被殖民过程中,出于殖民需要、基于殖民便利,各国记录者在这里进行了为数不少的社会文化记录,其中也包含摄影、电影等方式的记录。处于文化多样性发展的背景下,作为殖民地与宗主国合一的印度尼西亚,其影视人类学实践及其理论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富于启思的发展过程。
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有数百个民族,二百多种语言,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从16 世纪开始到印度尼西亚独立,荷兰人一直主导着这里的政治经济。正如学者罗伊·艾伦(Roy F. Ellen)所总结的那样,“荷兰人类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目前所涉地区的关系的性质和程度”“深深植根于一套特殊的殖民关系之中”,“人类学发展与不断变化的殖民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学者的思考,它“没有独立的学术传统和起源”“在本质上是经验主义的,并且狭隘地关注着荷兰领土的描述性民族志”,因而“是殖民经验的直接产物”。①Roy F. Ellen,“The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hy and Colonial Policy in the Netherlands:1800—1960,”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 12 (1976),pp. 303—324.在很大程度上,印度尼西亚人类学的目的也不纯粹是追求科学知识,功能主义在这两个地方都不是重要的阶段和角色。印度尼西亚的人类学从广义上说不仅包括民族志和民族学,也研究国内各民族的习惯法、农业经济及农民的经济生活。殖民统治者的研究意图,自然更多的是加强殖民统治。印度尼西亚独立之后,人类学与社会学紧密合作, 着力研究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探索以人类学视野和方法观察社会文化、解决社会问题的新视角。同时,更多的美国人类学家来到印度尼西亚做研究。印度尼西亚最初的本土人类学家也出现于这个时期。
这个历史进程是印度尼西亚影视人类学发展的基本背景。从为殖民服务,到传统文明与历史研究、社会文化研究,以及为国家社会发展服务、促进民族文化发展,是印度尼西亚人类学,也是其影视人类学发展的基本主线。影像不仅是人类学研究中精细的记录工具,也成为描述和阐释的工具,甚至本身就成为一个研究对象和视角。本文将对殖民时代荷属东印度群岛上的影视人类学实践发展进行梳理,对影视人类学活动、作品和观念进行发掘,力求厘清其发展阶段及其特征,为影视人类学研究增加史料,也反思影视人类学“何为”“为何”的现实走向与理论抉择。
一、来自殖民阶层的记录
从16 世纪初葡萄牙人抵达东印度群岛开始,对这片盛产香料之土的征服欲望和殖民扩张,就在这里开展得声色并茂:先是荷兰人和他们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然后是荷兰政府;短暂的英荷易手,再次交回给荷兰人……从1602 年东印度公司成立开始,直到1942 年日本人进入这片区域,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统治了三百多年。1945 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成立,才让这片土地真正回到印尼人的手中。
在漫长的殖民扩张过程中,对异族(无论是对殖民者或是被殖民者皆然,本文讨论的主要是前者)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和态度形成了影视人类学在这里最早的基调,也伴随着整个素材积累的过程——就像很多学科实践那样,也像影视人类学的许多早期实践一样,这种实践的开始是早于学科的正式命名的。殖民扩张初期欧洲人对群岛地理生态和民族文化的早期记录,是保留下来的最早的民族学人类学资料。零碎、片面,带着偶然、主观甚至偏见,其实可能更多的是欧洲中心主义,旅行家日记、传教士记载、官员报告、文学作品、博物笔记,虽然今天看来质量并不高,但它们携带着群岛的炽热信息,既在当时走向了欧美世界,也在今天走向了当代社会。
为了更好地进行殖民统治,19 世纪荷兰政府开设了东印度文化培训课程,囊括了从语言(爪哇语、马来语等)到地理、法律、经济等殖民地知识,学习对象主要是殖民公务人员(政府派驻工作者、教师、传教士和印度尼西亚企业的荷兰职员等)。正如东印度学课程创始人P.J.维特所说,“一个好的行政官,应该熟悉当地人的观念和需要,应该得到当地人的信任。他应该尽最大努力用当地语言与他们沟通,要收起他们的知识才能,放下他们的架子,以身作则,并以此为荣。”①刘正爱:《一个“边缘”的传统——人类学在荷兰》,《中国农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 年第4 期。一个好的殖民公务员也几乎同时就是一位好的人类学专家,他们在荷属东印度各地任职,将自己了解的材料写成报告。这些类似民族志的工作报告促进了荷兰的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作为结果,一门区域学科——(东)印度学(Indology)②1492 年,哥伦布到达美洲,误认为印度,后来欧洲殖民者就称南北美大陆间的群岛为西印度群岛,同时指称亚洲南部的印度和马来群岛为“东印度”地区。随着航海技术发展,“东印度”地区成为西方各国的殖民区域,英国、荷兰等国家在殖民初期都在这一殖民地设置了以贸易为外壳的殖民机构,名曰“东印度公司”。形成了。二战后,这门学科被称为“印度尼西亚民族科学”,其研究大致包括三个研究领域: 印度尼西亚历史与文献、社会政治、社会经济。有些荷兰人类学家还鼓励当地学生研究自己的文化,希望他们可以建立本土的民族学人类学,虽然有时这也被认为是分散人们对殖民剥削关注的策略。这些学生中的佼佼者在日后的印度尼西亚本土人类学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正如艾恩·尔特肯和凯米·迪普瑞兹所言,“与英国和法国相比,荷兰的殖民纪录片制作是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传统。然而,尽管没有具体的比较数据记录,但任何一个殖民地政府所制作的非虚构电影数量都是极其庞大的,而其中荷兰政府在东印度地区——我们今天称为印度尼西亚的这个殖民地地缘政治结构——所拍摄的影片数量很可能是最多的。”①Ian Aitken&CamilleDeprez,“Introduction”,from Ian Aitken,Camille Deprez:The Colonial Documentary Film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Edinburch University Press, 2017p10.来自荷兰的纪录片不是一个小数目。
1910 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一个私人基金会“殖民研究所”,其目标是收集和传播有关殖民地的知识。研究所研究者认为,制作电影是提供殖民地状况的可视证据的一种有用方式,也是说服荷兰平民为东印度群岛的社会经济发展感到自豪的一种有效方式。因此,在基金会成立早期,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制作电影以提供信息的创新方案。1912 年,基金会提供资金,招募在殖民地工作的人士制作短片,在一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制作电影胶片或摄影图片,来展现荷兰在东印度的存在感,同时也把现代性带给殖民地的普通民众。作为这个方案的成果,殖民地的农业、健康、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工艺美术、移民等一系列问题,以及一些较为暗面的效果(如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系统对劳工的剥削),都在基金资助完成的短片中得到了反映。这些作品既有政治的、也有社会的意义。除此之外,基金会还雇用了两位非电影人出身的制作人,J.C.·拉姆斯特(J.C.Lamster)和L.P.H. ·德布西(L.P.H.de Bussy),他们先后拍了好几十部电影。由于追逐商业利益的公司相继投资电影制作,1922 年开始,资金不足的基金会逐渐退出了制作领域,但一直坚持放映和推广这些电影,在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重要工作。拉姆斯特和德布西拍摄的电影后来也得到了私人公司的支持,在大型制片公司,如宝丽金(Polygoon)和海格菲林(Haghefilm)的旗下制作。不过绝大多数影片的放映是在荷兰进行的,几乎所有的影片都没有在殖民地放映过。
殖民研究所认为他们的电影应该是“有教育意义的”,因而有一项特别的政策,就是不将这些电影进行商业放映。据殖民研究所1918 年的年度报告,这一年中研究所收到了63 次放映申请,有314部电影在殖民研究所或其他教育机构放映。②Van Dijk et al,J .C. Lamster, An Early Dutch Filmmaker in the Netherland East Indies, Amsterdam:Kit Publishers, 2010p57.
当时荷兰最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威利·穆伦斯(Willy Mullens)看到了机会。由于自己的职业声誉,他获得了几份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拍摄电影的合同。1924 年穆伦斯正式到达荷属东印度群岛,得到了包括殖民事务与教育部、男爵波特的企业等各界的热情欢迎和支持。据称,所有对荷属东印度群岛有兴趣的实体都成为了他的支持者。到1927 年回到海牙时,穆伦斯已经拍摄了长达34 公里的连续镜头。③Hogenkamp Bert,De Netherland documentaries film 1920-1940, Amsterdam/Utrecht:Stichting Film En Wetenschap, 1988p21.
穆伦斯的巨大成功,引来了其他专业的电影制作人纷纷效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伊斯多尔·阿拉斯·奥切斯(Isidor Arras Ochse)。他于1925 年来到这片殖民地,担任荷兰—印第安什电影公司(Nederlands-lndischeFilmmaatschappij)的摄影师,开始拍摄私人公司资助的纪录片。奥切斯仿佛是特意来这里与穆伦斯竞争的,他带来了最好的装备,打算推出一系列高质量的产品的非虚构电影。无论在当时或是后来,人们对他的到来持乐观态度。直到本世纪,著名纪录片《道之母》(Mother Dao)④这部著名的纪录片在1995 年对1912 年至1932 年的殖民时期的镜头进行了重新剪辑。的导演文森特·蒙尼克丹姆(Vincent Monnikendam)还在一封邮件中评论道:“毫无疑问,那个时候最好的美国电影人是奥切斯。他是唯一带着三脚架和照相机靠近人群的人。他似乎是唯一尊重土著人的人。”①Ian Aitken&CamilleDeprez, “Introduction”,Ian Aitken and Camille Deprez, The Colonial Documentary Film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Edinburch University Press,2017.p12.直到新世纪到来之后,人们仍然保持着对这位制作人的尊重。
1930 年以后,由于题材饱和、经济大萧条造成的资源困境,荷兰殖民时期的非虚构电影的狂热生产,几乎完全停止下来。
有学者说荷属东印度群岛是人类学应用于殖民管理的最佳范例,影视人类学无疑是这种应用中的有力途径,前后生产的影片总计达到数百部。
二、虚构电影中的非虚构记录
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随着影像技术的逐步成熟和普及,受商业电影的影响,从澳大利亚到加拿大,以及本文所关注的荷属东印度群岛,世界上出现了大量表现各地风土人情的民族学故事片。在传统民族科学研究手段的基础上,研究者在这里开始了世界上最早的有意识的影视人类学探索。
在民族志电影中创造叙事情节,将重现的场景融入到非虚构的镜头中,是当时国际纪录片电影的新趋势。在这种虚实相生的记录探索中,荷兰的电影人也是开先河者之一。20 世纪20 年代,最后一个对荷兰殖民电影制作做出贡献的实体是一个宗教团体,名为“唯我社会”(Societas Verbi Divini,简称SVD)。SVD 与荷兰殖民政府的合作,希望促进东印度本土对福音的认识和皈依。神父西蒙·布伊斯(Simon Buis)是一位充满活力的牧师,他后来转行成为一名电影制片人。布伊斯和他的同事们在荷兰接受过完整的民族学和语言学的训练。他认为,拍电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描绘不开化或不文明的行为,并帮助他们改变宗教信仰。他的尝试为这些地区留下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志历史记录。在这样的理念支持下,他继续着摄影师威利·拉赫(Willy Rach)②威利拉赫是德国电影制作人,曾在荷兰教区的支持下在中国拍摄非虚构影像。1924 年前往东印度群岛的弗洛雷斯,拍摄了15000 英尺关于旅程和土著生活的胶片。的努力,把前者的纪实报道和土著生活记录融入到重现和脚本结构中,将他心目中缓慢松散的人类文化记录转变成了一部节奏更快、情节更清晰的电影。③Willemsen, Marie-Antoinette, De Fictive Kracht: Demissiefilm van de Missionarissen van Steyl(SVD), in J.P.A.vanVugt and Marie Antoinette Willemsen(eds),“Bewogenmisse: Hetgebruik van Bet Medium Film Door Netherlandsekloostergemeenschappen,”from Ian Aitken,Camille Deprez, The Colonial Documentary Film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Edinburch University Press,2017,.p108.这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掀起了混合电影制作的新浪潮。
布伊斯将拉赫在弗洛雷斯拍摄的镜头组织成一个故事,讲述天主教神父们离开荷兰,踏上穿越弗洛雷斯的史诗般艰辛旅程,同时观察那里的“原始”文化。布伊斯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都没有回过弗洛雷斯,他在荷兰编辑制作了一部两小时长的电影。他甚至还在一艘停靠在阿姆斯特丹港口的船上拍摄了几场戏,以表明他要踏上漫长的东方之旅。布伊斯是一个完美的电影推广和布道者,他和他的影片使“弗洛雷斯”在荷兰的天主教会中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地名。
1926 年,布伊斯在荷兰发行了《弗洛雷斯电影》 (Simon Buis)。这是一部盛况空前的影片,也许因为镜头中丰富独特的弗洛雷斯早期生活的视觉记录;更因为嵌入其中的民族志影像和福音内容;也可能是当地演员的参与,因为“这对于真实地描述当地人民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①Sandeep Ray,“Containment of Islam in Flores in the 1920s” from Ian Aitken,Camille Deprez:The Colonial Documentary Film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Edinburch University Press,2017pp.121.;还可能是布伊斯精心设计的激动人心的故事:这部电影为那些把自己想象成去一个未知的遥远国度传教的人创造了一种替代性的冒险感。《弗洛雷斯电影》展示了从斯泰尔神学院学生生活的各种场景直到到达弗洛雷斯之后的传教生活。跟着画面观众可以匆匆访问意大利、直布罗陀、开罗和科伦坡,直到巴达维亚和弗洛雷斯。其中有些镜头是在拉赫把材料交给SVD 很久之后拍摄的。布伊斯出镜了几次,将自己插入重构的叙述中。在影片中,弗洛雷斯的河流山川,甚至史前生物科莫多龙,都进入到故事情节之中。这部片子得到了热烈的评价:
简单的观众欣赏《弗洛雷斯电影》,是因为它的美丽的画面和令人愉快的各种各样的表演。学者,东印度的鉴赏家欣赏它,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更多:富裕热带的美丽呈现,我们印第安兄弟姐妹的恩典。这是植物学家、人种学家、地理学家、心理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所喜欢的。这是一个非凡的事实——这部电影吸引了每个人,但每个人都是基于自己对东印度的了解。这是《弗洛雷斯电影》最大的优点。
——《时代》(荷兰文版)1926 年12 月15 日②Sandeep Ray,“Two Films and a Coronation: The Containment of Islam in Flores in the 1920s”, from Ian Aitken,Camille Deprez,The Colonial Documentary Film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Edinburch University Press,2017.pp.110.
在最好的时候,这部片子甚至取得了一周之内放映八场的优异成绩。如前所述,布伊斯既没有拍摄,也没有在拍摄期间出现,而是拉赫四处奔走拍摄的。但很明显,SVD 是将布伊斯作为项目更重要的创作力量。布伊斯也直言不讳地表示,他坚持不懈地编辑拉赫的镜头,使这部影片力求完美。在1926 年的《时代》访谈中他说:“我花了七个月的时间来完善它的观察。目前已发行13 份。他们在奥地利、波兰、德国、北美和南美都有放映。不幸的是,我在鹿特丹不得不停下来。我很乐意再待14 天。大厅里直到最后一晚都挤满了人。”③Sandeep Ray,“Two Films and a Coronation: The Containment of Islam in Flores in the 1920s,”from Ian Aitken,Camille Deprez,The Colonial Documentary Film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Edinburch University Press,2017.pp.111.但是在多次放映和报纸上各种评论甚至讨论之后,布伊斯和他的影片一直悄无声息。直到1996 年,荷兰影视人类学家艾迪·阿佩尔斯(Eddy Appels)在他获得阿姆斯特丹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④Appels Eddy 于1996 年获得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博士学位。中隆重肯定了他作为民族志电影制作人的角色之后,布伊斯才在学术上被认定为民族志电影研究的先驱。
布伊斯后来还导演了完全虚构的《丽雅·雷戈》(Simon Buis,1930)等几部影片⑤此外还有《阿莫里拉》(1930)和《阿纳克·沃达》(1933)。。《丽雅·雷戈》是在自然环境中拍摄的,使用了当地人参与表演,并讲述了合情合理的故事。虽然与《弗洛雷斯电影》相比,它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几乎没有原始资料的价值,但后世人类学家的研究证实,这部影片在人类学上还是具有一定的说明作用,例如万物有灵论和民间仪式,以及丽雅父亲所穿的纱裙⑥Sandeep Ray,“Two Films and a Coronation: Containment of Islam in Flores in the 1920s,”from Ian Aitken,Camille Deprez:The Colonial Documentary Film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pp.122.,这些使它成为次级来源状态的相关历史记录。
1931 年,曼加拉的第一位基督徒巴鲁克当选为国王。在巴鲁克的加冕典礼前夕,布伊斯在4000 名村民和38 名区长面前放映了这两部影片。这应该是荷属东印度聚集规模最大的电影观众群体,银屏上的动态画面引起了人们的阵阵欢呼……这些来自弗洛雷斯的影片虽然只是20 世纪早期荷兰宣传人员在群岛各地拍摄的数百小时影片中的一个小部分,但无论在荷兰,或是在作为拍摄地的殖民地,《弗洛雷斯电影》和《丽雅·雷戈》的放映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值得记录的。
几乎与布伊斯的影片同时,美国探险家威廉·道格拉斯·伯顿在科莫拉多岛拍摄的《科莫多龙》(William Douglas Burden,1926)也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许受此影响,曾在波斯拍摄人类学影片《草原》(MerianCooper& Ernest Schoedsack,1925)的电影制作人欧内斯特·肖得萨克(Ernest Schoedsack)在苏门答腊拍摄了《拉贡》(Ernest Schoedsack,1931),表现人与大猩猩的互动。之后,他和梅瑞安·库伯(Merian Cooper)的合作又向前迈了一步,拍了一部名为《金刚》(Merian Cooper& Ernest Schoedsack,1933)的影片,虽然这部片子是在好莱坞的电影棚里拍摄的。他们把背景布置得就像爪哇附近的一个小岛,这个“岛”上的“土著”居民说着带有班图语音和马来语音的方言,挥舞着新几内亚风格的盾牌,追赶一个像大猩猩一样的汉子,把创作者心目中的当地文化背景与人物活动进行了典型化的“组合”与“搬演”。虽然“这种片子在文化观念上容易带上种族主义的偏见,且内容也易失之肤浅”,但正如影视人类学家海德所言,“民族学故事片的主要长处在于它能集中表现有关人际关系的重要事件,并以此来发掘人们在做出种种行为时细微的动机与情感”;“如果民族学故事片能与所表现的文化相吻合,那么,它就能真实地再现客观实际中的社会文化”。①[美]卡尔·海德:《影视民族学》,田广、王红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年,第60 页。因而这是影视人类学在苏门答腊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实践。
这一批来自东南亚的野生动物题材影片引起了人类学研究的注意。正如克里·英莱特、提姆斯·伯纳德等人都在研究中指出,在这一时期,丛林在西方想象中呈现出新的概念。这是一个“用科技和消费主义挑战西方文化的地方”,“成为一个可以投射西方欲望的地方。电影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科学考察队(通常由电影制作人陪同)开始进入热带地区时,他们不仅寻找科学信息,还寻找文化叙事,以便向公众传达常见的比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一种广泛的文化紧张和对西方文明之外的野蛮和暴力的焦虑。”②Timothy P.Barnard,“Sufficient Dramatic or Adventure Interest: Authenticity, Reality and Violence in Pre-War Animal Documentaries from South-East Asia,”from Ian Aitken,Camille Deprez:The Colonial Documentary Film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Edinburch University Press, 2017.p 125.在虚构电影中引入非虚构的纪录,一方面与虚构电影有相似之处,他们的基本的特点都是以虚构的故事情节、非现实的人物去展示社会文化的某一基本形态及其核心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其非虚构的部分又是在基本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进行纪录,既有对特定族群文化现象的影像记录和真实展示,又有以表演、描述、表现、反思、重构等方法和技巧,展示并挖掘深藏于表象之下的内在世界。正如研究者桑蒂普·雷所言,“这些场景不仅证实和补充了现有的学术研究,有时也作为事件唯一幸存的主要来源。拉赫等人通过艰苦旅程到达许多未被特许的弗洛雷斯地方,密切观察其社会仪式,这些场景记录是独特的文件,带领我们进入保藏记忆的地点,这些记忆长期以来被现代性和不可避免的时间前进所侵蚀。”③Sandeep Ray,.“Containment of Islam in Flores in the 1920s,”from Ian Aitken, Camille Deprez, The Colonial Documentary Film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Edinburch University Press, 2017.pp.125.这种记录方式不排斥虚构,有时甚至是以虚构的情节为架构。这种虚构与非虚构混合的影像类型其实源远流长。从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开始,就有把客观记录和虚拟建构作为主要摄制方法。分享人类学家让·鲁什正式把“虚构式影像民族志”的概念引入到他的人类学研究中。这种探索也曾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盛行。在对真实的文化现象进行展示和挖掘的过程中,纪录片与故事片之间,原本森严的界限开始在某些区域变得模糊。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影片的拍摄时间,只比弗拉哈迪《北方的纳努克》晚了不到十年。
三、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和格雷戈里·贝特森在巴厘岛的实践
荷属东印度群岛影视人类学历史中的标志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英国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到来,和他们在这里进行的一系列人类学影像实践。这也是世界影视人类学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1936 年,作为“文化历史学派”重要成员的米德和贝特森前往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 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田野调查。与米德著名的青少年成长与文化关系研究相承接,这次研究她依然“专注于个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①To the Field and Back,https://www.loc.gov/exhibits/mead/mead-field.html,浏览日期:2020 年2 月23 日。,特别是文化在人格形成中的作用,她此行巴厘岛研究的重点是幼儿经历与成人性格之间的关系, 以及这种性格在艺术作品和仪式当中的表现。
在这项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除了传统的田野笔记之外,紧随其师弗朗兹· 博厄斯(Franz Boas)使用摄影机记录夸扣特尔田野的自觉探索,米德不仅以新近出现的影像手段(静态图片和电影胶片)对研究对象进行记录,也把这些手段应用于研究过程中,甚至把他们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思考。玛格丽特认为,除了文字之外,“在能够用更好的各种记录形式来保存文化时”,“一些有天赋的、有独创性的电影摄制者对这些正在消失的行为进行了拍摄;一些人类学家也逐渐对此作了拍摄”,“我们完全有可能把传统的分析民族志与摄影、电影摄制和录音结合起来”,甚至“让被拍摄的人参与其中,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表达方式,让他们参与计划、制定程序、拍摄以及电影的剪辑”,电影的运用“将为人类的历史留下一份可靠的、可复制的、可再度分析的文化典籍”,因而电影和摄影应该成为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②[美]玛格丽特·米德:《文字训练中的影视人类学》,杨静、杨昆译,载[美]保罗·霍金斯:《影视人类学原理》(第二版),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3—9 页。一方面按照所受过的人类学训练,严格遵循田野调查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探索性地将影片拍摄与人类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成功地使用摄影机进行记录和研究,他们拍摄出影视人类学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批影片:包括25000 张相片和大约22000英尺的电影胶片,这些电影胶片被剪辑成总长约90 分钟的影片,配上文字资料,于1950 年发行。③这些影片包括《三种文化中的婴儿沐浴方式》《巴厘岛与新几内亚儿童的竞争》(配米德的系统叙述)、《一个新几内亚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天》《卡巴的童年:巴厘儿童研究》《巴厘的跳神与舞蹈》和《一个巴厘人的家庭》。由于有较为翔实的文字资料与之配合,具有较强的学术性。这种成果呈现被称为“现代人类学成果的最佳表述手段”④陈刚:《人类学纪录片的历史、现状与展望》,《当代电影》,2002 年第3 期。,为影视人类学发展做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他们首次将人类学纪录片视为研究工作的一种方式,记录了巴厘岛居民的生活,以及舞蹈、宗教仪式以及手工技艺。在拍摄影片的同时,还思考了民族志影片的特点,把它与一般的纪录片进行了区分。这被认为是世界影视人类学的形成期。
有意识地把影视手段用于人类学研究,米德与贝特森设法在摄影机与田野工作对象之间建立一种适应性的关系。他们强调影像资料“客观记录”的科学价值,“尽量拍摄正常状态下自然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先定下标准而后在适当的光线条件下引导巴厘人来表演这些行为”,“无需征得特别许可,贝特森就把拍摄‘作为日常工作’,也习惯于把注意力放在他拍摄的小婴儿的身上,让父母围过来却没有注意到他们也被摄入的事实,从而即使拍摄敏感题材也很少需要或者说很少使用棱镜取景器。为适应摄影机的工作原理,一些戏剧性的表演特别安排在白天进行。”①[美]埃米莉·德·布里加德:《民族志电影史》,杨静、杨昆译,载[美]保罗·霍金斯主编:《影视人类学原理》(第二版),第26 页。作为结果,就是米德和贝特森开创了具有研究性质的人类学影片。米德和贝特森的这些影片后来成为世界影视人类学影片的典范作品, 至70 年代仍在广泛播放,对新一代民族影视片摄制者有深刻的影响。米德被称为影视人类学在萌芽时期的“庇护女神”②朱靖江:《田野灵光: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历时性考察与理论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 年,第31 页。。
米德和贝特森在巴厘岛从事田野工作时的基本模式,也成为人类学者运用电影和照相手段进行观察与记录的基本标准和规范:“米德和贝特森发展了一种方法,在他拍摄静止和动态图片的同时,她在场景上做笔记,让她将注意力转移到视野之外的场景上。当她键入笔记时,她会在右上角键入包括事件的日期,并在左上角键入日期。她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插入时间,以便她的笔记可以与收集的其他数据同步,并且还指出了拍摄静止和动态胶卷的时间。米德对事件的连续叙述在左栏中,其他想法或舞台方向在右面。”③“To the Field and Back,Online Exhibition of Margaret Mead: Human Nature and the Power of Culture”,https://www.loc.gov/exhibits/mead/field-bali.html.浏览日期:2020 年2 月23 日。对整体性的生活现象的完整记录,是人类学研究的显著特点,而影像手段的加入,无疑为人类学的记录、描述和阐释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从而把社会事件、文化现象以及对此进行考察记录的过程和方式,多层次、线性、有序地呈现出来,建立了一整套完备而科学的田野考察档案。“米德和贝特森设计了一个精确的系统,用于在巴厘岛记录现场数据。他们与他们的巴厘岛秘书玛德· 卡勒(MadéKalér)同步了他们的手表。当贝特森为事件拍摄静止影像和电影胶片时,米德和玛德·卡勒做笔记,并定期记录事件的发生时间。他们在笔记中以‘LEICAS’或‘ L’标注何时使用拍摄照片的方式,以‘CINE’或‘ C’标注何时使用了拍摄电影胶片的手段。”④同上。正如高丙中教授所比喻的,“讲事实的一方明确知道,自己所说的并非唯一被听到的叙述,对方也要说话的”,在多重的主—客体关系中,“有更多的坦白,交代更多的背景”,在一个“前现代”的时代中完成了一种“后现代式”的“反思的、多声的、多地点的、主—客体多向关系的”⑤高丙中:《〈写文化〉与民族志写作的三个时代》,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6—17 页。民族志的实验记录。
在国会图书馆的在线展览中,有一组米德田野工作的资料: 1937 年 11 月 4 日,米德和贝特森观察和记录巴厘岛皮影的人偶制作过程。他们的记录及其过程是全方位的:米德用文字记录了艺人制作巴厘皮影人偶的全部过程。与此并行,贝特森以电影胶片和静态图片的方式记录了这一过程。

图1 米德的笔记① 米德田野笔记。国会图书馆手稿部,http://www.loc.gov/exhibits/mead/images/fieldnotes/0017_gif.jpg。
米德的笔记和贝特森的影像记录之间以田野笔记加场记式的记录把考察研究过程和对象一起建立了一个有序的时空结构,如米德笔记图中所示。
贝特森拍摄了一段巴厘岛艺人制作皮影人偶的活动影像,这段影像包括三组镜头,以“全景—近景—全景”的景别组合,用固定于三脚架上的摄影机在同一机位摄制。影像记录了艺人绘制、雕镂、打磨人偶的主要环节。他还同时拍摄了一组静态照片,更为细致地介绍了皮影人偶的制作工具、原材料、不同景别和机位拍摄的制作流程以及制成的作品等。②Online Exhibition of Margaret Mead: Human Nature and the Power of Culture,https://www.loc.gov/exhibits/mead/field-bali.html,浏览日期:2020 年2 月23 日。。

图2 贝特森拍摄的图片③ 米德现场照片。国会图书馆手稿部,https://www.loc.gov/exhibits/mead/images/fieldphotos/mm04-14877.jpg,https://www.loc.gov/exhibits/mead/images/fieldphotos/mm01-14871.jpg。
在米德的精心编排之下,这一系列反映巴厘岛民众的日常家庭生活、亲子育儿、宗教艺术活动内容的影像形成了一套直观生动的例证体系,证明了米德一以贯之的“文化人格”理论。而且,在作为研究资料保存工具的基础上,米德和贝特森还尝试把影像作为文化描述和阐释的手段,丰富了研究方法,拓展了研究深度。以其中的纪录片《卡巴的童年》为例,当时11 月龄的巴厘婴儿卡巴活泼好动,依恋母亲。影像记录中,无助的他因为与母亲的互动而感到沮丧:母亲不时用手去触摸卡巴,但常常当卡巴兴奋起来做出回应时,母亲却停止了和他的接触,而将注意力投射到别的地方。接受了这种令人沮丧的互动方式之后,卡巴慢慢地在他人的刺激下也变得无动于衷。文化人格就是这样被逐渐培养出来的。正如博厄斯体会到的,人类学家应该“拍摄的是被他视作文化要素的行为方式和体态变化”①转引自[意]保罗·基奥齐:《民族志电影的起源》,知寒译,《民族译丛》,1991 年第1 期。,利用影视的图像语言,米德巧妙地表达了图像背后更深刻的、研究中作为论据和结论的内容。巴厘人“稳定的”“没有高兴奋点的”的文化人格,成为米德作品中所描述行为的结局。20 世纪50 年代早期,米德将十多年前拍摄于巴厘岛和新几内亚岛的影像素材进行剪辑,其中《不同文化之中的性格形成系列片》的民族志影片,不但实践了米德以电影工具辅助人类学研究的理想,也是人类学界最早出现的较为纯粹的学术性影像民族志。因为其由人类学家制作、有着人类学学科框架的概念化,意图处理社会文化问题,这些影片被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影视人类学片。
当然,作为开创性的成果,米德和贝特森的这些作品也有一定的局限。采用画外解说的方式对影片内容进行引导,这个系列的影片中画面最主要的功能是图示式地配合米德的理论阐述(而且这种图示往往是不完备的,这既有技术上的原因,也出于记录研究过程本身带来的不可逆性),而不是独立形成一个自洽的视觉叙事系统。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米德作品和研究方法的学术说服力,但这批最早问世的民族志电影意味着一个人类学新时代的到来。
四、过渡时期日本的宣传性记录(1942—1945)
这个时期是荷属东印度群岛影视人类学发展的尾声,这时正值日本的过渡期。为了实现其“南进”的侵略目的,日本从1930 年就开始搜集中国南部与东南亚各地情报资料,进行调查研究。但在本过渡期内,日本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人类学研究几乎处于搁置状态。
1942 年开始,日本接替荷兰成为东印度群岛事实上新统治者,虽然在这里并没有升起日本国旗。但是,日本的统治相对较为友善,不仅大力提倡印度尼西亚语,还帮助印度尼西亚人建立自己的武装军队,更从监狱里释放了印度尼西亚的民族领袖苏加诺,许诺将给印度尼西亚人自由和独立。至今印度尼西亚仍是对日本最友好的海外国家。
进入印度尼西亚之初,日本军政府就成立了信息部,后更名宣传部。宣传部下设的大众教育中心(又称印尼语文化中心),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部门。其任务是:(1)发展印尼传统文化,(2)介绍和传播日本文化,(3)教育和培训印尼艺术家,其中包括电影艺术家②Misbach Yusa Biran, Sejarah Film 1900-1950:Bikin Film di Jawa, Jakatar: Komunitas Bamdudan Dewan Kesenian Jakatar ,2009.p326.。宣传、教育和传播日本文化,同时使印尼人产生归顺愿望,是日本在东南亚军事管理中的重要任务,而电影在所有的工具中尤其受到推崇。日本学者仓泽爱子(Aiko Kurosawa)曾对爪哇地区日本的电影宣传进行过专题调研,认为“在文盲率非常高、语言状况复杂的爪哇,诉诸人们视觉的艺术是最有效的”,“特别是电影,利用移动放映队等最简单且广泛使用的方式,再加上被认为会渴望娱乐的战时居民电影”,所以电影宣抚工作很早就列入到军政府的议程中。除了在这里放映当时所有的日本电影之外,日本军政府关闭了中国人开办的电影公司,接收了荷兰的所有电影制作设施和材料,安排了一家日本电影制作公司日本映画社(Nippon Eigasha)在雅加达设立制作所,先后制作了一系列新闻、文化和科教、武侠等电影。著名的乌思玛·伊斯梅尔(Usmar Ismail)等本土电影人在这个阶段成长起来。
印尼纪录片制作人、摄影师R.M.索塔托(R.M.Soetarto)等人进入到日本映画社雅加达制作所,和日本人一起工作。出于其宣抚目的,在内容方面,爪哇本土题材的纪实影像主要是新闻(总共达到89 部),文化电影的数量不多,只有30 部,其中政治与民众4 部,乡土防卫9 部,经济方面10 部,教育相关2部,居民保健储蓄等5 部;爪哇的活动与生活只出现在9 部新闻片中①倉沢愛子(1989)「日本軍政下のジャウにおける映画工作」『東南アジアー歴史と文化』No.18,41 ー69 頁。。而这些影片在日本撤离时几乎悉数损毁或篡改。因此,日本过渡期内关注社会文化的影视人类学实践其实处于停顿状态。
这个时期值得一提的还有,乔里斯·艾文斯在1944 年被任命为荷兰东印度群岛电影专员,他的工作是宣传荷兰将印度尼西亚从日本占领下解放出来,以及战后荷兰统治下有限的印度尼西亚自治计划。在这个任务下,艾文斯导演了《印度尼西亚召唤》(1946),在影片中,荷兰包租的船只满载军队和军用物资离开澳大利亚港口前往印度尼西亚,这一行动遭到了民众的阻止。艾文斯冒着被捕或被驱逐出境的危险导演了这部电影。这部只有22 分钟长,黑白35 毫米的电影再现了阻止行动。短片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波,荷兰向澳大利亚政府施压,要求起诉参与制作这部短片的人。从一开始,影视人类学干预现实生活的应用传统在这里就不曾断裂。
结 语
在影视人类学领域,印度尼西亚不是一个有抽象理论建树的国度。甚至,长期以来这个国家里人类学本身的发展也非常有限。直到1998 年后,随着各地的语言、民族、地域、宗教、性别等现象爆发,地区、民族和国家认同等成为急需解释的问题,人类学开始重获学术自由。在这一时期,影视人类学的理论思考尚未呈现出显著的结果,研究者、创作者更多地只是在创作的层面上对作品和过程进行着描述和总结。
从殖民时代开始,由于殖民的需要和外部世界对这片具有丛林色彩的神秘土地的兴趣,不同的实践者以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眼界用静态的图片和动态的影片,向世界呈现了这里的土著生活和微妙变化。也许有着某些机缘巧合,从实践及其效果来看,这里的影像记录活动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拍摄剪辑和放映方式,印证着今天影视人类学世界里人们关心的话题——人类学的“自治”与“他治”、拍摄研究中的“自我”与“他者”、对象的国家认同与个体意识、内容的虚构与真实、影片的干预与普通人的参与、文化的少数与多样……一一进入这个地区的影像实践,不止在历史上、在昨天为我们提供作为反思依据的材料,也在今天、在现在为我们提供影视人类学实践及其理论定位的坐标,甚至,为影视人类学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提供某种有益的尝试。我们不能不说,这在世界影视人类学上是不可遗漏的一个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