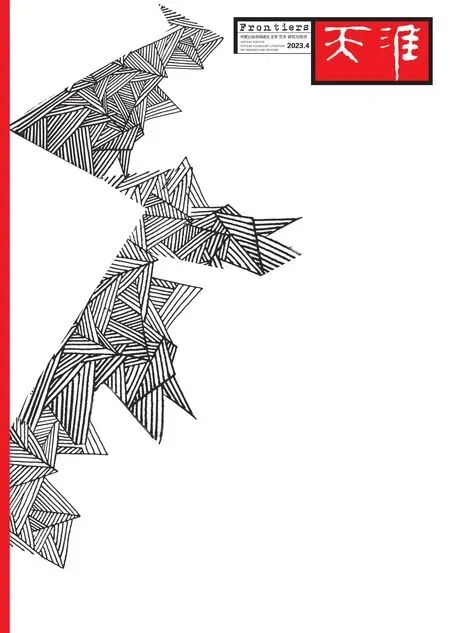借问梅花何处落
2024-01-08王西愚
王西愚
一
从大雪山起飞的老鹰停留在淡青色的高空中,秋风在翼下流动,雏鹰在周围嬉戏,河山尽收眼底。近处的凉州,远处的长安,灰尘般细小的人们愚蠢地劳作、厮杀,卑微地欢笑、哭泣,从未离开大地,不知身在何处。
老鹰知道,自己老了,像长安城里的皇帝那么老,当年的神勇已经是背影,生命和力量终有穷尽时。可皇帝不知道。皇帝还有无穷无尽的雄心和丹药,配得上年轻妃子真挚的爱情。粟特胖子大臣跳胡旋舞时,皇帝挽起袖子,亲自打鼓。咚咚,咚咚,咚咚,鼓点如同皇帝的怒吼,劈头盖脸砸向那些谄媚的笑容——你们觉得朕老了吗?
年轻时,老鹰也曾四处游荡,暴雨前捕鱼于青海之上,也曾御风而行,落在大明宫闪亮的殿顶。长安九月好风光,仓鼠肥,燕子香。可惜,羽毛艳丽的锦鸡,机敏温顺的白兔,若不是关在用金箔、银环、象牙、碧玉装饰的笼子里,若不是圈在有小径、池塘、仕女、秋千的花园里,味道该是多么鲜美。金殿,碧瓦,蓝天,顾盼睥睨,眼神不用说肯定是骄傲锐利。可迎接这旷世英姿的是纷纷的羽箭!卑鄙的人类啊!抓伤了十几个衣着光鲜的御林军,啄瞎了一个大呼小叫的军官的左眼,老鹰不幸也中了一箭,它带箭归来,在大雪山里度过了一生中最漫长的冬天。
由西向东通往凉州的大道上,沙尘滚滚,长长的队伍中,有马匹、车辆、琴师、舞女,又是胡商的马队。两只雏鹰眼尖,看到还有狮子、豹子施施然行走在马队中,俯冲下去看个稀罕。历经沧桑的老鹰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不屑一顾,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二
驿卒、斥候早就流水一般报来,任何一只西边来的胡鸟都别想悄悄飞过凉州。城下长戟森森,军士挥动令旗,示意马队在大校场暂驻。马队执事递上关文,军士再呈送给骑马而来的高适。高适五十岁以前虽已颇有诗名,仕途却极不顺遂,好不容易得到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赏识,在幕府中充任掌书记,日常工作无非是文书号令、礼仪来往。
那几个白衣白帽、高鼻深目的胡人,其中一位是粟特胡在沙州的大萨保康末蔺延,一年前来过。唐朝时,胡人多指西域的波斯人、粟特人等,而突厥人、契丹人、吐蕃人、回纥(后改称回鹘)人等通常并不包括在内。粟特胡,又称昭武九姓、九姓胡,擅长营商,多信奉火祆教。康末蔺延笑容满面,抚胸致意,另外几位想必是康国使节,也纷纷行礼,高适微笑回礼。开元天宝盛世,正是大唐如日中天的年代,域外来使,无论何等身份,入唐矮三分。高适却始终学不会那些官场习气,迎来送往之际,只是不卑不亢四字。康末蔺延与康国使节开口便郑重向他告罪,说是他们的一位尊贵人物随队驾到,有要事紧急求见西平郡王、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河西节度使哥舒大将军。究竟是何方神圣,径自闯来凉州,没有在龟兹禀报安西府,更没有知会沿途府衙驿营,斥候居然也一无所知!高适心下略有不快,不过还是差人去禀报哥舒大夫,自己先去迎接。
来到大校场上,只见几十匹大宛天马,数百头各种牲畜,战战兢兢,肃然站立,又见一辆装饰华贵的车辇停在中间,左雄狮、右雪豹赫然在列,猛兽转颈低吼,令人心惊。康末蔺延与康国使节等人面对华辇毕恭毕敬,躬身说了一大串粟特胡语,康末蔺延又用华语说道:“恭请女神座下尊者、圣女祭司、新月使移驾!”
此后十年,高适不断回忆那一瞬,阳光耀眼,青山失去颜色。
高适不好女色,寻常女子不会多看一眼。近年来,他修心向佛,河西、陇右的寺塔佛事颇多,他常与同僚拜谒亲近,去年不空三藏应哥舒大夫之请,来凉州开元寺说法译经,正是他操持的。覆盖于白骨之外的姣好皮囊,只是枯枝败叶上的皑皑白雪,佛光一照,无影无踪。如今即便是华清宫最美的贵妃、平康坊最艳的歌伎来到面前,想来他最多也只看她们……两眼。
可眼前这十七八岁的胡人少女,却是全然不同的美艳尊贵:眉弯新月,眼横秋水,唇染红焰,头戴八棱金冠,冠角上星芒闪耀,塞上秋风吹过,扬起她白裙外的玄色斗篷。
在作势欲吼的狮豹头上轻抚数下,猛兽立时安静下来,那胡人少女笑吟吟道:“康离嘉朵,叨扰大唐上国各位。”康离嘉朵声音清丽,说华语与唐人无异。见她如此谦和,高适连忙施礼如仪。康离嘉朵道:“这位高书记,是久仰的了。‘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西域绝远之地也传诵书记的名句呢。‘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据闻也是出自书记之手?”高适心下惊讶,不知她为何对自己如此熟稔,又为何对自己青眼有加,一时语塞。这《哥舒歌》只有四句,不知何人所作,原为:“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吐蕃总杀尽,更筑两重壕。”高适将这后两句改了,众人都赞好,不料竟传到康国去了。康离嘉朵见他未即答话,转头对康末蔺延、康国使节与众扈从道:“还好,在凉州的第一场雪之前赶到了,不然明天可不好走。”众人头顶骄阳,连连称是,高适看在眼中,心想,看来这康离嘉朵虽然年纪轻轻,但在康国人心中却是威望极高,即使是随口妄说,众人也如闻佛旨纶音。
不多时,节度使府衙飞骑传令,西平郡王、河西节度使哥舒大将军要在演武场观看舞马之戏。宾主尚未晤见,就先观看舞马,未免不合礼仪,然而众人不敢怠慢,慌忙分头准备。
演武场在城内,与城外的大校场只是隔着一道城墙。众人来到演武场,准备停当,哥舒翰不久也现身城头。粟特众人远远见哥舒大将军一身戎装,百战之身,威武轩昂,果然气势不凡。站在他身边的年轻小将,英姿飒爽,便是左车。这左车原是哥舒翰的家奴,十几岁时就随大将军四方征战。哥舒翰最厉害的,一曰“金枪术”,二曰“雷霆怒”。追上敌人,长枪往肩膀上一搭,大吼一声,敌人无不魂飞魄散,此时一枪刺出,向上一挑三五尺高,再往下一摔,左车再一刀砍下头来,没死的也死了。两人如此这般,吐蕃人无不闻风丧胆。哥舒翰在长安兴庆宫陪皇帝观赏过舞马之戏,百匹天马,盛大堂皇,眼前这个未免相差甚远,奈何左车未曾一见,说想见识见识,他自是慨然应允。
康国虽也产良马,但始终不及大宛,这回康国朝贡的天马正是购自大宛(如今称宁远国)。几十匹装饰华丽的天马踏着整齐的步伐走来,演武场上,沙土虽然铺得平平整整,如何可比氍毹,天马不惯,有些犹疑。好在舞乐一起,天马就开始翩翩起舞,喷玉生风,忘了这个小小烦恼。高适对舞马之戏毫无兴致,看这些天马神驹不能奔驰天际,只能取悦权贵美人,仿佛是自己在折腰受辱,只想尽快结束才好。舞了好一阵子,只见那驯马人在每匹马前放下一个银质酒杯,随即,马嘴衔杯,昂首举高,再作不胜酒力的醉态。舞马原是皇帝寿辰“千秋节”祝寿定制之戏,贡马未至长安,《倾杯乐》习练已熟,康国要讨皇帝的欢心,也算是用心良苦。高适见这些马匹眼泛红光,意犹未尽,怀疑驯马人是不是给它们饮用了火祆教的秘制豪麻汁。演武场上的舞马场面虽然不大,但在这小小边城却实属难得,两旁的战马也随着舞乐摇头晃脑,甚是滑稽。一曲舞毕,众人就要喝彩,却见城楼上哥舒大将军正与左车低声交谈,众人不敢出声,待听见哥舒大将军爽朗笑赞,众人才纷纷应和。
三
来到河西节度使府衙,宾主坐定,四个精赤上身的昆仑奴抬上来一个硕大的红色酒桶,桶上雕刻着繁复的纹样,想来是装满了珍贵的康国特酿葡萄酒。这是送给哥舒大将军的礼物。康国此番进贡物品,除了舞马、方物,还有送给贵妃娘娘的一对康国子,送给皇帝的一队胡旋舞女,当然也少不了玛瑙、琉璃、水晶杯这些殊玩名宝。不过,这些俗艳之物怎么会被西平郡王哥舒翰放在眼里?可哥舒翰是出了名的贪杯,一见酒桶,登时眉开眼笑。只听得新月使康离嘉朵提议道:“麾下何不此刻便试试我石堡城的美酒。这酒味道就像美女在嘴里跳胡旋舞,颜色就像大将军刀上的鲜血呢。”哥舒翰一听,心下一凛。
五年前的石堡城大战,众人记忆犹新。血雾染红了天空,漫山遍野的尸体,鹰都不够用了。唐军死伤数万,才攻下这个只有几百名吐蕃守军的城堡,是荣是耻也很难说。还好哥舒大将军与左车合力生擒了守城大将铁刃悉诺罗,只有几匹比弩箭飞得还要快十倍的汗血宝马驮负老妇幼女四散逃逸,唐军众将士也不甚在意,将那些吐蕃守军大大折辱一番后,杀了血祭英灵。
这新月使的话让哥舒翰听着甚是别扭,一旁的通译幕僚忙上前解释,原来康国又唤作萨末建,译成华语也正是“石堡城”之意,哥舒翰听罢方才释然。众人皆想,这年轻胡女不过十几岁,无知少识,侥幸居此夷教高位,出使上国,说错了话还不自知,仔细惹恼了大将军麾下。至于此“使”不是彼“使”,众人一时也分辨不了那许多。哥舒翰不欲与这胡女计较,说不定昨日她还在拾马粪呢,他甚有气度地笑道:“不忙,贪杯误事,尊使既有军机要事,先叙不妨。”康离嘉朵笑道:“也好,敢请麾下屏退左右。”
少顷,大厅里空旷了许多,哥舒翰只留左车、高适一武一文分侍左右,粟特一方则只有康离嘉朵一人。只听得康离嘉朵娓娓道来,她的声音就像芙蓉园里的画眉鸟唱歌一样动听,就像大雪山上的冰泉一样清冽,可是在高适耳中,只听得炸雷一般的两个字:造反!
大唐皇帝的太子与皇帝最宠信的大臣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合谋造反。更骇人的是,康离嘉朵不是来报信的,而是来策反的。你道安禄山是谁?他乃是火祆教的赤焰使!火祆教并非如外界以为只是以火为尊,而是崇拜日、月、光、火诸神。虽然安禄山手握重兵,分量不轻,甚至渐有尾大不掉之势,但康离嘉朵乃是神意指定的女神座下尊者,掌教大祭司又是她的祭司导师,安禄山远在幽州,教中事务鞭长莫及,一般西域教众只知有新月使,不知有赤焰使。掌教大祭司一直有心想要扩大火祆教的版图,得知太子殿下意图,居中谋划,各方也算是一拍即合。他们约定,一方起兵,三方呼应,吐蕃据西域,安氏据北方,太子据中原。至于诸小国,国贫兵弱,向来没有开疆拓土的野心,只求一份安稳与往来经商传教之便。康离嘉朵说道,大将军也算半个胡人,虽然一向与安禄山不睦,但大祭司希望麾下念在同出一脉,捐弃前嫌,共襄盛举云云。
高适心想,这新月使果然还是太年轻了,莫说是你这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小胡女,就算是太子殿下亲临,加上安禄山大军压境,哥舒大夫也未必会稍假辞色。
不出所料,哥舒翰听罢,轻蔑地哈哈大笑,道:“小娘子你有所不知,策反我哥舒翰的,官道上络绎不绝,每日一打开城门就扑来刀尖上寻死,拦都拦不住。凉州大牢里还有好几个,等着秋后问斩。小娘子与他们先作个伴,等某提兵灭了你夷教胡国,再来听你关说不迟。再说,安禄山那胡……那反贼,一旦得了北地,哪里又肯画地为牢?真当某是只会舞刀弄枪的武夫么?来人!去把那两头狮豹炙了,美酒佳肴当前,莫要辜负了康国贵客的一番心意。”
左车微微一笑,得令起身。
四
谁也想不到,康离嘉朵此时突然发难!只见她手上腾出明亮的火焰,双手一递,手臂上的一条金链如细蛇般飞出,与火焰合为一体,嗤嗤飞向数丈之远的哥舒翰,火蛇倏地一转,成了一个圆圈,围绕着哥舒翰,并不点燃周遭物事,却也不灭。
这一下子变故突然,左车收住脚步,噌,拔出鞘中雪亮的长刀,却滞在手中。
“你这……妖术!”哥舒翰突然忆起,“你是……石堡城的那个小胡女……十一娘?”声音之中竟然有一丝多年未有的恐惧。哥舒翰其实并不记得她的容貌,只是那双腾飞火焰的手,他这一生中只在石堡城见过。那时她手上的火焰还很微弱,腾不过尺余,只能用来吓唬吓唬人。
康离嘉朵的父亲正是石堡城(吐蕃称之为铁刃城)的守将悉诺罗,她母亲却是出身粟特望族。十一娘七岁就被选为火祆教圣女,那年潜来石堡城,用她粗浅的神通相助阿爷抗击唐军,直到有一天,她心乱如麻,不能再帮阿爷,阿爷就败了。她与阿娘日行千里逃回康国,五年后,跨过八百里流沙、三千里瀚海,带队前来。
康离嘉朵道:“不错。铁刃大将军即是我阿爷。我阿爷尸首分离,遗骸未葬,我娘哭瞎了眼睛,都是拜哥舒大将军与这位左二郎所赐。”
左车上前,隔在火圈与康离嘉朵之间,身后的火焰灼得头发焦臭,也不理会,他正色道:“两军交战,性命相搏,各凭天意。嘿嘿,尊使可知我阿爷、阿娘是死于何人之手?”高适听了,心下黯然。他曾听闻,左车父母正是惨死于吐蕃军之手,吐蕃人在大唐边境烧杀抢掠,又何曾留情!
康离嘉朵凄然一笑,道:“两军交战!尔等折辱够了,再杀了他,更砍下我阿爷的头颅供在祭坛之前,又待怎讲?”高适当时虽不在石堡城,也知这都是实情。
左车年轻气盛,哪肯说一句软话:“你阿爷砍我唐军的头,还少了么?石堡城数万大唐勇士——”话未完,他将手中长刀掷出!高适心下惊呼不忍。这左车幼时就膂力惊人,如今只怕哥舒大夫也不过胜他一筹半筹,长刀去势奇快,势必将康离嘉朵钉在墙上!
只听一声巨响,节度使府衙那巨大的落地窗门四分五裂,眼前豁然开朗,向外望去,晴空辽远,九月鹰飞。康离嘉朵靠在窗门边,轻咳一声,云淡风轻地掸了掸衣衫,居然是毫发未伤。高适心下不知是喜是忧,这康离嘉朵果然有些门道,并非只是口舌便给,而是妖术……异术傍身。
康离嘉朵招招手,两只雏鹰竟然乖乖飞下来,停在她身前,瑟瑟发抖得像冬雨淋湿的麻雀,眼神无辜得像说错话的鹦鹉。高空上的老鹰定力虽强,也不由得意乱神迷,盘旋彷徨,想要夺回雏鹰,远走高飞,从此不再与卑鄙的人类有任何纠葛,却又不敢靠近。康离嘉朵向前一指,两只雏鹰立时又精神抖擞,兀地欺近惊惶呆立的左车,向他身上一抓。康离嘉朵再向天一指,两只雏鹰如蒙大赦,迅疾飞出窗外,随老鹰飞远,渐渐不见。再看左车,兀自站立不倒,双眼茫然。高适目心骇:原来世上真有摄魂之术!哥舒翰仍被火圈所阻,火圈如影随形,人向前它向前,人向后它向后,虬髯早就燎去多半,戎装上的铁片钢钉炙得火烫,哥舒翰无计可施,不再与火圈相搏,血脉贲张,仰天怒吼:“妖女!我——”声音却哑在喉中,在高适听来,一如耳语。
康离嘉朵径自上前打开酒桶,又拿来一个水晶杯,斟满葡萄酒,原来真是色红如血。她自顾自饮了一杯,然后举袖腾足,左旋右旋,裙裾飘扬,竟跳起胡旋舞来。只见一袭白裙的康离嘉朵时而从容,时而怒放,时而又似悲喜交集。不闻鼓笛琵琶,但见风雪飞旋,这胡旋舞高适也不知看过多少回了,似今日这般诡异……奇异的,却是从来没有。
康离嘉朵旁若无人地旋舞了半日,哥舒翰全不在意,只是看向左车,眼中满是关切。康离嘉朵停下,柔声对哥舒翰道:“放心吧,哥舒大将军,左二郎他不会死,要想他魂魄归来也不难,本座也不要你反了,你哥舒翰身为胡人,只需莫与我族人为敌。这也不算很难为你呢。”哥舒翰听了先是心下一宽,又再一紧。某最多只能算半个胡人,一半为敌可乎?而且我娘是于阗人,又不是你们粟特人,何来族人一说?也罢,待得左二郎平安无恙,再慢慢周旋就是。康离嘉朵继续道:“否则,本座虽立誓不杀族人,却必将开坛祭告明光大神,你是生不如死还是三族尽诛,大神自有旨意。”康离嘉朵双手一抖,袖中飞出来两只黑色小雀,乳燕大小,飞到火中,转了一圈,火立时就灭了,小雀也不知去向。高适猜这就是传闻中的却火雀,这新月使袖中到底还有多少神通?火一灭,衣衫褴褛的哥舒翰疲乏至极,缓缓倒地,知觉全失。
五
高适呆坐椅中,浑身绵软无力。诸多变故纷至沓来,是真是幻,一时也分不清楚。大厅里这一番纷乱打斗,奇怪的是大厅外没有丝毫动静。
康离嘉朵再斟满一杯酒,却是递给高适。高适接过康离嘉朵用过的那只流光溢彩的水晶杯,不知道她要如何折磨自己。石堡城之战的时候,他还没有来到哥舒大夫帐下,她的仇恨账照理说算不到自己头上,但高适也不打算开口辩白,国仇家恨向来如火燎原,如风覆巢,哪理会你是草泥还是卵蛋?也罢,百年过半,寸功未建,今日命绝于此,未尝不是解脱。
康离嘉朵道:“高书记……使君莫惊,且听我慢慢道来。我此行并非为策反哥舒翰而来,我知他两载之内必不肯反。令他有所忌惮,不敢轻举妄动,就足够了。我乃是专程来求使君相助于我,来日起事,阻遏哥舒翰统兵攻打安禄山。”
高适闻言,大出意外,怔了半日,叹道:“尊使莫来消遣在下。以尊使今日之能,十个百个哥舒大夫都杀了,即使真有誓约,也未必能缚住尊使双手。何必如此大费周章,陷我于不忠不义?我又何德何能,能够襄助尊使?”康离嘉朵一双深潭似的美目看着高适,并不答话。高适避开她的目光,略一低头,却见她雪白的颈项之下,隆起的胸乳之上,有一粒黑痣,如《妙法莲华经》上的句读,目光连忙再下移,看着她红色鹿皮靴上所系的金丝带,道:“是了,哥舒大夫能征善战,又与安禄山不睦,来日安禄山若真的反了,皇帝必会起用哥舒大夫讨伐……攻打。杀了哥舒大夫,皇帝就用高仙芝,也是一样。不如留他性命,尸位素餐,反而大计可成。”
此时的高适还不知道,数月之后,他将陪伴哥舒翰赴长安见皇帝,而哥舒翰将在途中洗浴时罹患风疾。明年十一月安禄山反,皇帝先用名将高仙芝、封常清迎战,不敌叛军,高、封二人受诬被杀,皇帝命称病在家的哥舒翰挂帅出征。
至于再后来,哥舒翰固守潼关,被朝廷逼迫出战而大败,被帐下叛将火拔归仁绑去,降了安禄山。潼关一失,无险可守,玄宗皇帝逃往川蜀,途中杨贵妃魂断马嵬驿。不久,太子在灵武登基,是为肃宗皇帝。这说不尽的大唐十年动乱,此刻如何得知?
而高适自己,潼关之战后,西追明皇,北依太子,平永王之叛,靖川蜀之乱,出为封疆大吏,入为刑部侍郎、左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退隐终南山。这位诗人的十年传奇人生,此刻又如何得知?
康离嘉朵道:“我不但不杀他,我还要拜托使君千方百计护他周全。我要他长命百岁,身败名裂。”高适听了,心下掠过一丝寒意,又想到她身世悲苦,终是情有可悯。康离嘉朵又缓声道:“哥舒翰于使君或有薄恩,使君也算正好报答。不利于他的种种,都是我一人做下,与使君没有半点干系。此外,康末蔺延于我族人之中薄有威望,我命他即日起主祭凉州,杜绝事端,不令使君有半分为难。至于忠字一节,来日太子登基,不也是你李唐的皇帝?唉,那安禄山,注定不能成事,我不过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我知使君有经略之才,胸中千军万马,眼前岂不正是建功立业、一飞冲天的良机么?”康离嘉朵见他似有所动,继续道:“治世则庆民安,乱世则慕雄起,治乱更迭,世代兴亡,是千古不易之理,我侪无非顺势而为,岂有他哉!纵然安禄山不反,你道太子不谋么?太子不谋,你道吐蕃不犯么?吐蕃不犯,你道那皇帝不会自毁江山么?”
这几句话掷地有声,高适无言以对,明知康离嘉朵说的半点不错。皇帝这些年宠信奸佞,沉湎女色,斗鸡舞马,哪里是明君的作为?如今太子将反,宠臣将叛,皇帝懵然不知,哪有唐隆、先天时的英明神武?忽然又想,这舞马之戏莫非也是胡人的布局?君不见演武场舞马之时,军马情不自禁随靡靡之音舞之蹈之,若我唐军冲锋陷阵之际,胡人也如法炮制,那……那……真是不堪设想。高适如此想了一回,道:“安禄山有反意,今上不信,我早就是信的。”话说出口,高适又觉语气放肆,不禁哑然失笑,道:“但他与太子势成水火,如何可能合谋?”不待康离嘉朵开口,他就自问自答:“嗯,事成之后,再徐徐图之就是。”他又摇摇头,缓缓道:“一样还是生灵涂炭。”两人一起沉默半日,均知这是无法可想的事。
高适道:“如此说来,九姓及宁远等西域诸国,俱是一体了。”康离嘉朵摇摇头,道:“我西域诸国,从未一体。宁远国多良马,但少有人擅驭驯之法;我康国人善商贾,无奈物产却不丰盛;石国人善战,终不能以一当十。说来我九姓胡,只不过是暗夜里几个胆寒可怜人,各自惊惧,结伴而行罢了,大唐上国,又何曾体恤呢?”
高适不知如何回应,略一沉吟,道:“日前有一方外之人,唤作金梁凤,游来凉州城,道,‘来日天下大乱,三日当空,一向东京,一入蜀川,一来朔方’。我等只道是妄人故作妄语。今日悉知尊使大计,那金梁凤所言似也并非空穴来风?”东京即是洛阳,日后安禄山将在那里称帝,而朔方则是宁夏,正是太子登基的地方。
康离嘉朵听到这个名字,神情古怪,欲言又止,轻描淡写道:“异人所在多有,能否窥见天机,各凭造化。此行我正要将先知之术传于使君。此术虽不能明世运至毫厘不爽,也不能断吉凶于瞬息之间,更不能改逆天命以利一己之私,然而仰观俯察,知机识变,如依舆图而驾御,如谙律吕而乐舞,再凭使君的本领,封侯拜相,却也不是难事。”
高适心潮起伏,思量再三,又问道:“我还有一事不明,既然明知那《哥舒歌》曾经我手,得以流传广布,哥舒翰又素以亲厚待我,尊使十一娘恨他入骨,如何便肯将大事托付于我,再传我先知神术?”
康离嘉朵轻笑一声,道:“吐蕃总杀尽!使君仁慈,大笔一挥,总算留我等蕃胡一条活命。使君妙笔,所虑者自然是文辞雅驯、意境幽远,而非怜我化外贱民,然则暴戾之气因此消减,也算是你佛家一分所谓功德。使君可是嫌我谢得迟了?谢得少了?”这句话颇有些调笑的意味,高适哪敢接口。康离嘉朵又道:“恨与不恨,从此放下了。今日与使君同坐同饮,皆是明光大神的指引与旨意,使君莫再相疑才好。”她望了望高适手中的酒杯,道:“有一事,好教使君得知,大神授我这先知之术,固有助益,却损阳寿。得此术者,尘世之游只余十载。若使君不肯……”
高适心下一苦,接口道:“十一娘说笑了,若十一娘这般天生丽质、聪慧神通之人,不能存于这世上,在下桑榆之年,苟活人间,更有何意味!”他说完又觉不妥,却不知该如何改口,索性不说了。
康离嘉朵似乎浑然不觉,道:“那好。这先知之术还有一样古怪之处,只能传授,并不能教习。所谓传授,或神授,或亲传。既然神明未肯授之于君,也罢,我只好代劳亲传。”康离嘉朵稍一停顿,道:“此‘亲’,乃是肌肤之亲。”说毕,她嫣然一笑,在高适身边坐下,俯首过来,吹气如兰,在他耳边悄声道:“信与不信,肯与不肯,在君一念。说不定只是奴倾慕使君之才,愿荐枕席而已,还望不弃。”
这一番话,直听得高适心惊肉跳,嗅到康离嘉朵秀发上的香气,分明不是自己的绮梦,他不由得呆了。唐人于男女之事其实不甚拘泥,胡人没有中华礼教约束,更加是异彩纷呈,可如此急转直下,云雨欲来,却也未免……
高适心中还在“未免”,康离嘉朵却已正色道:“使君放心,你是汉人,我是胡人,各为其主,各为其族。此事一了,来日待你手绾兵符,与我族人血战沙场,我也不来怪你,只望你念奴一分恩情……”却待如何,她竟没有再说下去。前尘如梦,有谁知道那年的铁血刀锋之城,敌军围困万千重,小小年纪的十一娘春心萌动,莫名爱上了一个传奇英雄,而她爱的却是身边的男人?有谁知道一旦亲传神术,则大限立至,她将香消玉殒?
良久,她伸出纤纤玉手,轻轻腾起的火焰中,依稀是兵荒马乱、哀鸿遍野。高适心中迷茫、摇晃,如九曲黄河怒涛中的革船。“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乃知兵器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李太白李十二啊,你告诉我,乱世凶兵之中,应该引颈受戮,祈求佛祖,还是吟诗作赋?二十年前,长云暗雪山,不度玉门关,与王昌龄、王之涣旗亭画壁;十年前,大道如青天,水边多丽人,携李白、杜甫同登吹台、琴台。如今,故人星散四方,渐行渐远。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诗歌如美酒一杯,可以浇胸中块垒,章句平仄的尽头不过是个弄臣,得宠或失宠。庞大的唐帝国,似悬浮在茫茫夜空中灯火辉煌的一片孤城,在这荒凉的边缘,眼前低低黑云,身后漫漫黄沙,随时可以吞噬我于无形。我抓紧可以攀附的枝干,粉身碎骨前的呼喊没有人会听见,当人们顺着文字的藤蔓找到我的尸骸时,还剩几块值得连缀拼凑的碎片?一个人只拥有诗意的世界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此生此世。渤海高氏的祖先们啊,让你们光荣的名字继续照耀我吧,东去长安两千里,我渴望回到那千百年来被江河冲刷得平整的大地上,登上金色的楼宇,俯看绿色的植被,四面八方的人们走进春风槐荫,走过秋凉梅香,道路延绵无尽。
手掌上的火焰忽明忽暗,大约过于耗费心力,康离嘉朵脸色苍白,额头上冒出汗珠,不觉靠向他的肩头,汗水濡湿了高适青色的官服。高适举起手中盛满红色酒浆的水晶杯,凝神看了半晌,仰头饮下。原来此酒与寻常的葡萄酒颇有不同,入口淡,入喉浓,入腹燃烧,体内淤积的暗影须臾成灰,身体轻盈欲飞,却又鼓胀欲裂。抬头看时,康离嘉朵不见踪影,只见一匹天马在身旁,毛色银亮,头顶热气蒸腾。
六
他搂着白马修长的脖子,紧张而笨拙。白马蹦跳、转圈,像是在考验他,又像是下决心把他摔下来。束在腰间的长带,挂在身前的环佩,绕在腿上的珠链,都不见了,金色冠冕早就跌落在秋日的长草丛中,银丝般的长鬃像往事一样随阵阵凉风起舞。
暮色浓了,他也累了,身子软了下来,手在白马胸前滑动,心跳一下下用力敲打着。白马也静下来,竖起耳朵,听他的呼吸,渐渐从粗重到平缓,如狂风远去的大漠,只留下一波一波静美的沙丘。白马伸出舌头舔他的手,又扭过头来,鼻息喷在他脸上,舔他的面颊、嘴唇,使他满脸湿漉漉的。他闭着眼睛,也用嘴唇去回吻白马,这时白马反而又扭头避开他,他用力抓紧白马的银鬃,双腿一夹,这一次,白马畅快地奔驰起来,越来越快,到后来,没有重量,没有声响,好像离开了大地,踩乱了白云。
下雪了!天宝十三载凉州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早一些。转眼间,雪就填平了苍老的沟壑,填满了落寞的山谷,夜色也因此如玄纱包裹着明珠,又暗又亮,他们像是无意中闯入了一个藏着无数秘密的银白世界,又像是他们本来就属于这个银白的世界,只是在外面流浪久了,今晚终于回来。他在白马紧致光滑的屁股上用力一拍,白马昂起头,高嘶一声,蹬起半天高的雪雾,怒奔向前。红色的汗滴,沿途抛洒在绵软的雪地上,如血,如赤珠,如火流星,如葡萄美酒,如盛开的梅花,如凋谢的梅花。
他们厌倦了平坦的官道,又厌倦了通向山间戍楼规规矩矩的石阶。越荒凉,越兴奋,他们嗅着山的气息,在幽暗中摸索前进,或者索性走进溪流,溯流而上,冰冷的溪水先减了快意,再溅了快意。险要的地方,他想停下来,从马背上跳下来,白马反而不依,奋力一跃而过,惊飞了一群乌鸦。爬上了天梯山的高处时,雪停了,他们也就停了。月亮没有出来,最好不要出来,风中有几声呻吟,几声羌笛。向下看去,山下还是不是同一个人间?几粒金黄的灯,随意洇在深深浅浅的暗黑里,形状如鸟如龙的凉州城,枕着山峦,覆盖着白雪的衾被,高高挺立,那是三百年前北凉王沮渠蒙逊建造的七级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