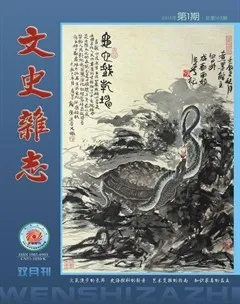清代宋诗运动与碑学比较研究
2024-01-04杨阳
杨阳
摘 要:清代早期,“祢宋”诗风和书写金石文字各为诗学、书学的取法方向,也是宋诗运动和碑学兴起的萌芽。至清代晚期国运衰微之时,文艺思潮从主流的追求秀美风格,转变为追求雄强风格。宋诗运动与碑学正是晚清文艺思潮追求雄强风格过程中,趁势而起的两大高峰。
关键词:称宋;碑学;雄强;相互影响;高峰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它曾经历了“康乾盛世”;中期社会矛盾逐渐凸现;晚期则内忧外患骤至,政治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清代早中期,在清王朝高压统治下,社会经济得到很好的发展,文艺主流思潮偏向于“秀美”的风格,文学上如王世贞主“神韵”、纳兰性德工小令,书法上推崇董其昌、赵孟頫,流行秀美的帖派书法。而清代中晚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变化,学术上“乾嘉学派”和今文经学兴起,并逐渐成为学术主流;文艺上则从各方向不自觉地探索求变,都转到追求雄强的风格上来。宋诗运动与碑学的兴盛即为追求雄强风格的例证。
宋诗、碑学运动兴起的比较
胡适在1922年为《申报》创刊50周年所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说:“这个时代之中,大多数的诗人都属于‘宋诗运动’。”[1]这大概是最早提出“宋诗运动”的文献了。其实,从清代一开始,黄宗羲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为改变明代前后七子“诗必盛唐”、师法唐诗的做法,而转向学习宋诗,这便可看做“祢宋”的宋诗运动之滥觞。但清代早期诗学主流,仍主要宗法唐诗,游国恩称之“祧唐”。
以王士祯为例,他的一生大半处于清朝政权逐渐稳固的时代。作为顺治进士,他也逐渐成为当时颇有创见和影响力的诗人,被称为“一代正宗”,其主张学习唐代“神韵”诗风。他曾选录王维以下四十二人的诗为《唐贤三昧集》,目的是为了“剔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2]。又如沈德潜主张学习汉魏盛唐的体格声调,称“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3]
清代早期,反映民间疾苦的诗文大大减少,转而为政治歌功颂德,或注重体裁。在书法艺术上,豪放雄强的书风与清初需要的稳定统治格格不入,灿烂辉煌的明末浪漫主义书风也只是昙花一现,为统治者宗“二王”、宗赵、宗董所取代。“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竟讲子昂。”[4]统治者的提倡,加上张照、刘墉、王文治等书家的推动,帖学达到极盛。
清初王朝政权稳定后,经济、文化都有极大发展,但统治者对于汉族士大夫的思想管控极为严格,文字狱可称空前绝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极盛,士大夫人人自危,经世致用之学充满危险,动辄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所以学术界也大多逐渐转为考据之学。考据之学则对诗文取向和艺术取向都有重要影响。
以诗学来看,在考据之学直接影响下,产生了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肌理说”。在考据学间接影响下,清人与宋人重读书、以学为诗相契合,与宋人“史诗”说相契合;另一方面,宋诗本身叙事详明、淋漓奥博的风格,与考据学影响下的清人思维刚好契合,于是宋诗风尚逐渐流行。朱彝尊为考据的领军人物,他是先宗唐诗后改宗宋诗的较为有影响力的诗人,向来被视为清代“宋诗运动”的前驱,备受后来宋诗派和同光体诗人的推崇。同时朱彝尊浸淫金石,又以隶书著称清初书坛,被视为碑学萌芽阶段最重要的书家之一。书法上,考据学者寻碑过程中增加了取法对象,逐渐形成苍茫雄强的审美意识。
清代早中期,宗宋诗学与碑学萌芽主要是通过考据学的兴起联系起来的。而这样的联系太过于偶然性,或者说,宗宋诗的诗学审美和好碑学雄强的审美都还处于不自觉阶段。例如袁枚反对诗学唐宋之分,但主张“当变则变”:“夫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也,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子之胸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已失矣。”“当变不变,其拘守者迹也。”[5]与袁枚齐名的赵翼,有诗曰:“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上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又云:“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常。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设唐?”又如“扬州八怪”的书法,并不是都取法金石,而是多方探索,艺术追求上都是求新求变,但各自风格突出,独具创造。在这个阶段,并没有较为突出的唐诗、宋诗对立,也没有突出的碑学、帖学的对立。
宋诗运动与碑学高峰比较
清代后期,爆发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清代学术由古文经学转入今文经学,宋诗运动与碑学逐渐兴盛,并迅速风靡全国,分别成为诗学和书学的主流。包世臣《艺舟双楫》有记录:“宋氏以来,言诗必曰唐,近人乃盛言宋。”[6]也正如前文提到胡适先生所说,那个时代的诗人大多属于宋诗派。碑学方面也正是因为阮元、包世臣、何绍基等碑学理论大家的宣扬,碑学影响逐渐扩大,形成取代帖学之势。
如果说清代中期宗宋诗、学金石还不够自觉的话,那么,到咸丰、同治以后,宋诗派和碑派已经成为人们自觉追求的主流风尚了。
考察宋诗运动代表人物,无不是以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为宗的;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但赞成碑学,甚至有的就是碑学大家。而一般碑学家则多赞成宋诗运动,很难找到反对宋诗的。
程恩泽是宋诗派的直接开启者,在诗法上,明确主张效法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独于江西社,旆以杜韩帜”[7]。同时,程恩泽也研究金石,[8]且与碑学家阮元并称为嘉庆、道光间儒林之首。何绍基、莫友芝、郑珍是程恩泽门生,更是宋诗派的中堅力量,而何绍基、莫友芝皆为碑学代表书家;郑珍亦好金石,篆书学习邓石如,是典型的接受碑学思想的人物。曾国藩作为宋诗运动的赞成者和推动者,也明确主张碑帖兼之,并不反对碑学。
作为宋诗运动的接续者,“同光体”代表人物沈曾植、陈三立、陈衍、郑孝胥等,皆为赞成碑学的诗人,沈曾植、郑孝胥还是重要的碑学大家。可见宋诗运动和碑学有着较为特殊的联系。
“祢宋”和碑学在清代早中期都是不自觉形成的。它们都受考据学的影响。至清代中晚期,随着社会的巨大变动,主流学术转为今文经学。今文经学主经世致用,以改变内忧外患的国势,体现在文学和艺术上则是崇尚雄强和壮美的风格;而宋诗风格足以畅情,碑学风格足以雄强,宋诗运动和碑学便迅速成为文艺主流的追求。
清人邵长蘅在《研堂诗稿序》中有一段重要的论述:“诗之不得不趋于宋,势也。盖宋人实学唐而能泛逸唐轨,大放厥词。唐人尚酝藉,宋人喜径露。唐人情与景涵,才为法敛。宋人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畅之情,故负奇之士不趋宋不足以泄其纵横驰骤之气,而逞其赡博雄悍之才,故曰势也。”[9]可见诗于“祧唐祢宋”过程中,宋诗成为师法主流,而唐诗则成为这种主流的对立面。
萧华荣先生在《中国诗学思想史》里评述道:“在风靡于整个清代‘祧唐祢宋’诗学主潮中,在当时须大声疾呼、纵横议论、铺张描述的维新世运下,所谓‘旧风格’只能是‘祢宋’风貌。如果说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是通过今文经学向变法改良的‘西学’接榫过渡,那么在诗学上便是通过‘祢宋’诗学向‘诗界革命’‘移花接木’。”[10]
所以“祢宋”的宋诗运动成为诗界主流,又成为“诗界革命”“同光体”的实际崇尚方向。与此同时,碑学也以其雄强的风格成为书坛主流。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写道:“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泾县包氏以精敏之资,当金石之盛,传完白之法,独得蕴奥,大启秘藏,著为《安吴论书》,表新碑,宣笔法,于是此学如日中天。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11]此记述碑学兴起的原因以及盛况。
更深层次,康有为则举碑学与帖学审美上的不同:“即论书法,视覃谿老人,终身欧、虞,褊隘浅弱,何啻天壤邪?”“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帖学终致“浅弱”,碑学笔法“雄奇”,所以康有为极力推崇碑学,其理论被认为是碑学的总结。对此,侯开嘉先生评赞道:“清代碑学,是中国书法史上最自觉的艺术阶段。”[12]这种自觉也体现在众多书家对这种雄强风格的一致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诗学中,原本主流的“祧唐”被视为宋诗运动的对立;书学上,原本主流的帖学也被视为碑学的对立。艺术发展过程中,一种风格过盛,必然导致其走向另外一面,如“尚法”的唐代出现狂草的高峰。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沉醉于泱泱上国的士大夫终于惊醒,不管是以今文经学变法图强,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都是想要重振国势,这种心态成为清末士大夫的不懈追求。宋诗运动与碑学,以其容易抒发“泄其纵横驰骤之气”和展现“雄奇角出”的气势,成为士大夫一致赞成的文学艺术取法方向。
而两者到清末民初皆有新发展,如康有为提出“汉唐格律周人意,悱恻雄奇亦可思”;“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13]。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作《饮冰室诗话》,倡导“诗界维新”,此则从宋诗派过渡到更为广阔的取法天地之风了。而碑学方面,随着金石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和发展,碑学取法更为广阔。玺印、钱币、砖文、瓦当、甲骨文、汉晋简牍以及敦煌文书等等都成为后来碑学的取法对象了。
结语
清代宋诗运动与碑学在一开始只是文艺上一个可轻可重的取法风尚,至清代末期形成两大风靡全国的文艺流派。它们在到达顶峰时,诗学与书学艺术理念和追求相同或相近,因而相互影响,形成了宋诗运动的代表人物往往是碑学家,而碑学家亦往往成了宋诗运动的中坚人物。宋诗运动与碑学,合力形成了清代末期追求雄强的文艺思潮。如今宋诗运动随着时代变化已经烟消云散,碑学仍是书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艺繁荣的今天,我们已经能找到比宋诗更能直接宣泄纵横才气的艺术形式。碑学,站在帖学追求“二王”神态为宗的对立面,以开放的理念,敢取古代各种形态文字作为艺术表现形式,为书法艺术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注释:
[1]胡适:《胡适文存》,第二集第二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144页。
[2]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四》(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8页。
[3]邬国平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明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28页。
[4]康有为:《书镜》,杨素芳等编《中国书法理论经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2页。
[5]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5页。
[6]包世臣:《艺舟双楫》,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页。
[7]黄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
[8]程恩泽:《程侍郎遗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9]陈伯海:《历代唐诗论评选》,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74页。
[10]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華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页。
[11]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0年版,第755页。
[12]侯开嘉:《中国书法史新论》(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13]桑咸之、阎润鱼译注《康有为诗文选译》,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99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