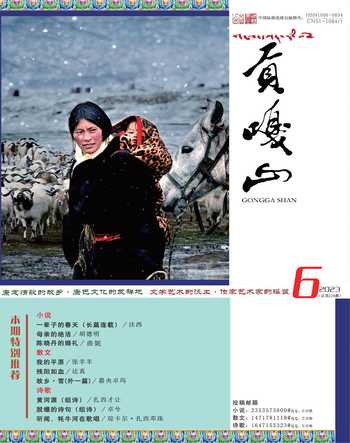母亲的绝活
2024-01-03胡德明
胡德明
在我印象里,母亲拥有一双微蓝的眼眸,显得清澈、明亮,时常流露着柔和温暖的光,衬得本来就白皙的面庞愈发透亮。她总是将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绾于一方黑色的头帕下,十分精神。她的性格看似温柔,实则坚毅,骨子中就透出一股子不服输的气质。她朴实、善良,始终藏着一颗乐于助人的心。
母亲心灵手巧,见什么学什么,学什么会什么。她在娘家时喜欢跟外婆学做纺羊毛、绣毛线、织褂子等各种针线活。她喂猪喂羊喂禽,各种家务活样样在行。尤其是做过年糖、磨制豆腐是她的绝活,远近闻名,常常被人称道。与我父亲成家后,母亲把在娘家学会的这些本领全部运用到新的家庭中,使得新家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
一
过年糖是我们这个山寨庄户人家必须要准备的过年食品之一。过年期间亲朋好友相互串门时,家里的女主人都会拿出自制的过年糖给大家品尝。大家围坐在火塘旁,喝着醇香的美酒,啃着脆香的坨坨肉,吃着甜甜的过年糖,畅谈着热闹的过年景象,展望着未来美好的愿景……
制作过年糖需要近一个月的时间,母亲从上个月初起,就着手准备了。制作过年糖的主要原料是玉米,但玉米含糖量低,做出来的糖不够甜,这就需要用麦子发酵成的麦芽糖汁来调和。但我们这个山寨海拔较高,气候寒冷,不适合种植麦子。如果要吃麦子馍馍或者做过年糖,就需要用洋芋或者圆根等土特产到低海拔地区农户那里去调换。他们非常喜欢我们这里的洋芋、圆根,也就很乐意调换,这叫“互通有无”吧。
这天早上,母亲把我从床上叫起,让我吃过早饭后到阴山寨找一家农户,用家里的洋芋、圆根等土特产调换一点麦子回来做过年糖的“药引子”。我有些为难,嘟嘟嚷嚷地对母亲说道:“可我不认识那些农户呀,我可能办不好这件事!”因为我还小,基本上没有出过远门办事。母亲想了想后说道:“那个寨子里的人确实不认识你,加之你生性腼腆,可能也办不好这件事。”父亲对那个寨子里的人是很熟悉的,但他今天正与本寨几个小伙子约好,要砍家里的过年柴,实在抽不开身。母亲想了想后说道:“快要过年了,做过年糖的事不能再拖了,干脆我去办这件事!”
母亲做好一家人的饭菜后,从屋里拿出一些洋芋、圆根之类的土特产,装了满满的一背篼,挎在背上向阴山寨走去。
这个寨子的人大多数认识母亲。他们看见母亲来,都非常热情,纷纷端茶递水,问寒问暖。有的还端上热气腾腾的饭给母亲,母亲说已经吃过了。当母亲说明来意后,他们都面有难色,有的说麦子除留的种子外,都已磨制成面粉了,有的说已制成挂面了。不少人家里没有麦子可供调换,实在难为情,于是便从家里拿出挂面送母亲,母亲说这些家里都有,坚持不要。
母亲想到要是调换不成麦子,过年糖就没办法做了。过年时,如果没了过年糖,那年味会淡很多。家里几个孩子也喜欢吃过年糖,在那里眼巴巴地等着自己换回麦子做糖呢。过年期间,邻里邻居相互串门,家里只有美酒、坨坨肉,而没有过年糖招待,也是一件憾事。母亲想到这些,心里十分焦急。她背着沉重的土特产,继续走到这家看看,走到那家问问。她累得直喘粗气,白净的脸上汗流如注,背上的衣服直冒热气,湿漉漉的,没有一处是干的。
母亲仍咬着牙关,提了提裤裙,振作精神,翻越一座山坡又一垄田坎,蹚过一条又一条小溪,走村串户,不厌其烦地打探着麦子情况。当她坐在一个山梁上休息片刻时,只见寨子边缘高高的山坡上一家房顶上冒着炊烟的农户引起了她的注意。于是,她踉踉跄跄地背着沉重的背篼向这家农户走去。她一边走一边想,看看这家农户有没有麦子可供调换。要是没有的话,今年确实是做不成过年糖了。
随着狗的一阵阵狂吠,房门“吱”的一声开了。里面走出一个戴青色头帕,身着蓝色衣服,外套一件厚实羊皮褂子的中年妇女。当她看见满脸汗珠气喘吁吁地背着沉重背篼的母亲时,禁不住迎声走了过来,热情地说道:“原来是尼木大姐呀,真是稀客,真是稀客!”原来这户人家姓龚,男的叫龚永贵,女的叫龚刘氏。他们都与父母亲很熟悉,特别是龚刘氏经常来我家串门,带一些豆儿、瓜瓜、嫩苞谷等矮山出产的农产品给我家。母亲也经常到菜园里采一些矮处所没有的土特产给她。
当龚刘氏知道母亲的来意时,十分爽快地将剩下的三十多斤麦子全部调换给了母亲。母亲喜出望外,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母亲背着调换来的麦子,喜滋滋地迈着轻快的步子,很快回到家,开始忙起做过年糖的事来。
母亲将调换来的麦子全部倒进清水里洗净后,放进木盒里泡着。第二天,她将已经泡涨的麦粒放进簸箕里,盖上一层薄薄的纱布,用旧棉絮将其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放到火塘旁边腰着。
过了二十多天,母亲将旧棉絮打开,将簸箕上的纱布轻轻掀开,只见那被泡涨的麦粒一个个都长出了绿茸茸的麦芽。母亲见状,十分高兴地说:“这么好的麦芽,完全可以做好多过年糖的药引子了!”这时,母亲把早已准备好的苞谷面倒进木盒里,加上适量温开水泡着。过了两个多小时,苞谷面已完全泡涨了,软软的、黄澄澄的。她将麦芽捣碎放进苞谷面里搅匀,并加上适量水后拿到石磨旁,开始磨起过年糖的面浆来。
用了两个多小时,母亲把一大盆苞谷面全部磨成了金黄色的面浆。她將苞谷面浆装进木盆,端到堂屋的火塘边小心地倒入放置在三锅庄上的大锅里,用旺火煮着。她叫我看着锅里的苞谷面浆,不要让它煮沸溢出锅外。她将木桶洗净后,放在火塘边,在上面放上筲箕并在里面先铺上一层棕树皮和垫上一层薄薄的白纱布。
过了一会儿,锅里的苞谷面浆开始咝咝地沸腾起来,伴随着甜香的味道时不时地飘进鼻里,感到甜润和舒心。母亲不断地搅动着锅里的面浆,防止它溢出锅外。她一边搅动着,一边时不时地用木瓢将面浆舀出,拿到嘴边轻轻尝尝,看看是否煮熟。
这时,母亲对我说:“面浆已经煮熟,可以过滤了!”我小心地扶着木桶,母亲不断地将面浆舀进木桶上的筲箕里。被过滤出的面浆水唰唰地流进桶里,很快将桶装满。
母亲将滤好的面浆水又放进锅里继续煮着,并把滤出的面渣放进猪食桶里。还有十多天才到过年时间,圈里的两头过年猪还需要继续喂精饲料。因此,这些面渣正好派上用场。火塘里的火正在毕毕剥剥地燃烧着,锅里的面浆水也在热烈地沸腾着。在这空隙时间里,母亲给我们几兄妹做了饭,让我们吃得饱饱的。
夜幕已经降临,夜空中的星星闪烁着眼睛,俯视着茫茫的大地。吃饱了的两头肥猪已经打着呼噜沉沉入睡了,忙碌找食的鸡群也已经进圈,悄无声息地蹲在那里睡着了。偏僻的山寨已一片寂静,火塘上方石台上的松光在摇曳着柔和的光芒,火塘上锅里的面浆哗哗地开着。不一会儿,锅里冒出浓浓的蒸气,向四周飘散开去。这意味着面浆已完全煮熟,摇动面浆做糖的时机已经成熟。母亲首先将火塘里正在燃烧着的两个柴火拿出,使整个火势减弱一些。锅里的面浆渐渐停止了沸腾,蒸腾着的热气开始消散开去。母亲开始用摇糖板在锅里搅动起面浆来。开始时她搅得很慢,只见面浆水在锅底微微泛起波浪,发出咝咝的脆响。母亲慢慢地、慢慢地加快了摇浆的速度,而且越来越快,使得锅里的面浆水荡漾起来,荡起了一层一层的圆圈。整个锅里躁动不安了,面浆水你拥我挤汹涌着、呜咽着。狂躁的面浆水拍打着锅边,企图寻找一个突围的缺口,可是很陕就失望了。于是,愤怒的面浆水无奈地退回来了,喘息着重新编队,准备作最后一搏,但都无济于事,因为一切都在母亲娴熟技巧的掌握之中。此时,已经劳累了一天的母亲用摇糖板在锅里摇动着面浆,可眼睛已困倦得快要睁不开了。我和几个妹妹央求着母亲去睡一会儿,母亲努力睁开疲倦的双眼说道:“没事,我再坚持一会儿。”当她看到几个妹妹也有倦意时说:“你们快去睡吧!”我和妹妹们都一再坚持让母亲先去睡一会儿,母亲只好拖着困倦的双腿,进屋休息去了。
我和妹妹们做了分工,她们负责从门外抱进木柴,不断燃烧着火塘。我负责用摇糖板不停地搅动着锅里的面浆,不让其煮沸煮煳。没过一会儿,几个妹妹也一个个地耷拉着眼皮,困倦得快要坚持不住了,我只好让她们上床去休息了。不—会儿,她们均匀的鼾声便此起彼伏起来。说实话,我也有了倦意,嘴里不停地打着哈欠。但我强打着精神,一边往火塘里加着木柴,一边不停地摇动着面浆。此时,我感到更加疲倦了,眼皮上好像承受着千斤沉重的力,已经快要支撑不住了。随着“吱”的一声响,母亲已打开里屋门走到了火塘边。她一边往火塘里添加木柴,一边从我手中接过摇糖板开始摇动起面浆来。
锅里的面浆已经下降到离锅底不远,而且浓度越来越高。随着摇糖板的不断摇动,一股股浓烈的甜味已从锅里飘出,弥漫在整个屋子里。母亲笑着对我说:“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成面浆糊了!”母亲从锅里舀出一点放进碗里,让我尝尝。我用鼻子嗅了嗅碗里的面浆糊,只觉一股浓浓的甜味瞬间直钻进鼻孔里。面浆糊滚烫滚烫的,呈黄褐色。我用嘴轻轻地吹了吹,便喝进嘴里,顿感满满的热甜。当它沿着我的喉舌缓缓地咽下去的时候,那种甜暖通过食管,一点一点暖到心底,不久,扩散到四肢、指尖和脚尖。啊,这种甜味儿,闻起来沁人心脾,尝起来让人喜悦。母亲不停地摇动着面浆糊,锅里的面浆糊也越来越醇厚,味道也越来越甜美。过一会儿,我又困得快睁不开眼了。母亲催促我快去睡一会儿。我迷迷糊糊地向里屋走去,母亲在后面叮嘱道:“睡一会儿就起来帮帮忙哦!”我吸吮着沾在嘴角上淡淡的糖汁,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当我睡得正酣时,忽然被一阵“咚咚咚”的摇糖声惊醒。紧接着,我家那只红公鸡已经奏响了黎明前的第一曲交响乐。我透过窗缝往外望去,只见东边山顶上的那颗启明星已高高悬挂在那里,不停地眨着眼睛,正在俯瞰着这片寂静的山野。从窗缝里钻进来的冷风,使人感到一阵阵寒意。
我赶快穿上衣服,走到火塘边,只见母亲不停地使劲摇动着摇糖板,脸上唰唰地滴落着豆大的汗珠。我从母亲手里接过摇糖板,开始摇起糖来。火塘里的火已经基本熄灭,只有几根没有烧尽的木柴还残留着一点点星火,在微微地闪烁着。母亲不断地往灶台上添加松光,努力让它燃烧得更大更亮一些。我不断地摇动着,使锅里的面浆糊不断地发出“咚咚”的沉闷而巨大的响声。慢慢地、慢慢地,我感到摇糖板越来越沉重了,面浆水也变得越来越黏糊了。母亲说:“这时是关键阶段,不能停止摇糖板!”原来在这个时候如果停止摇动,形成的糖就会变硬,颜色不耐看,甜味也会变淡很多。
我使着浑身力气摇着摇糖板,锅里的面浆被摇得发出沉闷的响声,面浆糊的颜色由黄色渐渐地变成了淡白色。我脸上的汗珠不断地滴落着,身上的衣服已全湿透,嘴里不断地喘着粗气。母亲接过我手中的摇糖板,吃力地摇动着、摇动着。很快,母亲脸上也徐徐浸出豆大的汗珠,顺着红润的脸颊窸窸窣窣地滴落到衣襟上。她摇着摇着,嘴里不断地喘着粗气,摇糖板也慢慢地停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我很快从她手中接过摇糖板,鼓足力气,狠命地摇动起来。只听得锅里的面浆糊的声音显得更加沉闷、呆滞,仿佛是滚动的雷声渐渐沉静下来。这时,摇糖板似千斤重担,越来越沉重,最后纵使我使尽全部力气,再也摇不动了。这时,母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挂着胜利的喜悦说:“差不多了,准备出锅吧!”锅里黏糊糊的面浆已经全部变白了,而且甜味也很浓很醇了。这一切都标志着,由面浆完全变成甜甜的过年糖了。
“喔、喔、喔、喔”,一阵阵高亢有力的鸡鸣声又响起,这是我们家那只公鸡进行第二次报晓了。我从窗缝处往外眺望,只见天边已泛起了鱼肚色的曙光,启明星已隐去了许多光芒。母亲从楼上拿下早已洗净的竹簸箕,在里面垫上一层香喷喷的苞谷烧面后,拿到火塘边。她用木瓢把锅里的糖全部舀进簸箕里,并盖上木板盖子后,端到楼上放着。她又从楼上取下早已准备好的炒苞谷花花放进锅里翻动搅匀,将附在锅里的残糖全部吸附进苞谷花花里,并用手捏成拳头般大小的坨坨,一个挨着一个地铺在簸箕里。母亲拿起其中的一坨给我,笑着说:“这个叫坨坨苞谷花花糖。”我掰了一片放进嘴里咀嚼,感到酥脆甜润,味道特佳,非常好吃。
这时,太阳在东边的山坳里露出了笑脸,大地开始朗润起来。公鸡第三次引吭高歌后,便率领着鸡群,在房前屋后觅起食来。猪圈里的过年猪,拖着沉重的躯体在圈里蹒跚地踱着步,嘴里不停地哼着要食吃。
母亲没有来得及休息,就从木箱里舀出苞谷籽走出门,全部撒在院坝里,并呼唤着鸡早已熟悉的口令。鸡听到口令后,从房前屋后扑楞楞地跑到院坝啄起食来。母亲看到鸡那悠然啄食的神态,露出了倦意的笑容。旋即,她又从背篼里拿出猪草,坐在房檐下用菜刀捣起来。我知道母亲那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我已十分困倦,实在帮不上她什么忙,只好拖著沉重的脚步回到了房间。我刚躺上床便呼噜呼噜地进入了梦乡。
大概睡了两个小时,我被几个妹妹嘻嘻哈哈的笑声惊醒。我穿好衣服走出寝室门时,只见几个妹妹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过年糖和苞谷花花糖。簸箕里的过年糖呈黄白相间,而且已经凝固了。母亲用棒槌轻轻地叩击,过年糖被粉碎成大小不一的块状。她拿起一个巴掌般大小的过年糖给我,说:“你昨晚辛苦了,要多吃一点。”我从她手中接过糖,只见上面敷着一层薄薄的苞谷炒面,软软的,呈淡黄色。我将过年糖放进嘴里啃着,慢慢地咀嚼着,细细地品味着。过年糖在口中慢慢地融化了,于是感到五脏六腑都灌满了糖,酥酥软软的,甜甜的。母亲又给了我一坨苞谷花花糖,我用菜刀将它切开,拿了一片在嘴里咀嚼起来,只是与纯糖比较起来,甜味稍淡了一些,但酥脆香甜,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几个妹妹吃了一点后,说吃得闷到了,就蹦蹦跳跳地到外面玩去了。我一会儿吃着过年糖,一会儿啃着苞谷花花糖。吃了一个又一个,啃了一坨又一坨。到了最后,拇指和食指被糖粘住,分不了家,连整个手也被粘住了。肚儿渐渐地鼓胀起来,嘴里也不停地打着饱嗝。吃罢了过年糖,我慢慢地吮吸着拇指和食指,再去将手洗净,继续帮着母亲做起了家务事。
今年这个寨子里我家是第一个做过年糖的人户。这第一锅过年糖,母亲照例是要送给那些没有粮食做过年糖,或者是没有技能做过年糖的人户。母亲弄早饭给我们大家吃,并在喂完猪食后,就将第一锅剩下的过年糖和苞谷花花糖装进竹制背篼挎在背上,走出门向着寨子边缘的那户人家走去。当她走到这家人的门口时,只见门虚掩着,屋里叽里咕噜地说着话,听不真切,好像正在做饭。母亲知道这家人姓莫潘,没有小孩,夫妇俩有些智障,家庭经济条件差,是全村最贫困的农户之一。父母亲经常关心他们,常常把家里节省下来的粮食接济他们。
母亲轻轻敲了一下门就径自走进屋去,只见一个约莫五十来岁的男子正站在火塘边做饭,一滴滴汗珠顺着他宽阔而褶皱的脸上流下。火塘边坐着一个衣杉槛楼、披头散发的中年妇女,正在往火塘里添着柴火。两人见到母亲后都傻傻地笑着,但笑容亲切,因为他们对母亲很熟悉。男的让母亲坐到火塘边,并递上一碗开水让母亲喝。母亲一边喝着水,一边从背篼里拿出一些过年糖和苞谷花花糖递给他们,说道:“这是我家今年做的第一锅过年糖,请你们在过年时尝尝。”男的咧着嘴傻傻地笑着说:“你们家年年都给我们两个送这送那的,我们十分过意不去啊!”女的在一旁也叽哩哇啦地说着大概是感谢之类的话。临走时,母亲还跟他们说:“我家宰杀过年猪时,我再绐你们拿一些来。”两个人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眼眶里贮满了感激的泪水。
母亲走了几家农户,把背篼里剩下的过年糖和苞谷花花糖全部送给了小孩和老人。他们都赞扬母亲过年糖做得好,也赞扬母亲心地十分善良。
在重新做过年糖之前,母亲从柜里拿出仅有的一点燕麦,放进盆里洗了洗,然后放进锅里,加上适量的水煮着。待水煮干后,继续在锅里炒着。一会儿,锅里响起了燕麦籽毕毕剥剥跳跃的声音,随之而来的是燕麦的醇香味。随后她用锅铲将已炒熟了的燕麦籽铲进木钵里。接着她又用同样的方法炒了荨麻籽、天须籽和黄豆籽。她还从楼上竹篓里拿出一些干核桃,让我们剥。这些核桃是住在矮山的一些朋友送来的,已在楼上放了很久。核桃不多,我们很快就剥完。母亲舍不得让我们吃,全部装进木钵里,说是在做过年糖时再做混合的花花糖。
过了几天,母亲又重新做起了过年糖。这次她做了两锅过年糖,而且出糖量很高。家里的两个竹簸箕已装得满满当当的。特别令我惊奇的是,她做起了许多花花糖。她特意留了一盆刚出锅的原糖浆,黏糊糊的。首先她将炒燕麦籽放进瓷盆里,放上适量的原糖浆,用手将其搅匀和揉搓,然后一把一把地抓出,使劲将它捏成拳头般大小的花花糖,并轻轻放在簸箕上。母亲高兴地对我们说:“这个叫燕麦花花糖。”接着,她又以同样的方法做起了天须籽花花糖、黄豆花花糖和荨麻花花糖。最后,她将剩下的荨麻籽、燕麦籽、天须籽和核桃米子全部倒进盆里,并将剩下的原糖浆也全部倒进去,用手搅动揉均匀,搓成一个一个拳头般大小的混合体花花糖。我细细品尝后,感到这种花花糖绵柔、酥脆、清香,甜而不腻,腻而不油,甚是色香味美,别有一番风味。
母亲将花花糖放进簸箕里,一个挨着一个地铺放着,足足装了五六个大簸箕。她将它们全部放到屋楼上,待过年时再慢慢地食用。
我家畜圈里的那两头猪,是准备在过年时宰杀的。它们皮肚光滑,毛色乌黑发亮,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憨态可掬。但家里粮食不充裕,用来喂肥猪的就十分有限,肥猪也就长得慢。后来母亲把家里的粮食留足日常口粮外,其余均制作成了糖。她将糖渣子与洋芋、圆根、饲草混合,做成精致的混合体饲料。两头猪对母亲制作的混合饲料十分喜欢,因而长得特别快,没多久就长成硕壮的大肥猪了。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我已到县上读高中了。那年的农历十月,一年一度的彝历新年悄然来临。学校没有放假,我们只好在校继续上课。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我们在寝室里休息。突然班上要好的一位同学給我说,有人带口信叫我到城里取包裹。我将信将疑地来到了嘎尔坝国营食堂旁。只见这里拴着很多马匹,马夫们正在给马喂饲料。这时,—个正在上着马鞍的马夫抬起头来,一眼就认出了我。原来是我所在生产队的王马夫,我亲切地叫他“王叔叔”,因为他与我父亲是老朋友。他从马驮子里拿出一个包裹,递到我手里说:“这是你父母亲给你带的过年吃的东西。”
我谢过马夫王叔叔后,飞跑回寝室,迅速将包裹打开。刹时,一股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原来是母亲给我带的过年香肠、猪蹄、过年糖和各种花花糖。香肠和猪蹄已煮熟。我将猪蹄和香肠用小刀切开后分送给寝室里的所有同学品尝,同时还分了一些过年糖和花花糖。
我慢慢吃着香喷喷的猪蹄、香肠,细细品味着甜甜的过年糖,啃着酥脆香甜的过年花花糖,眼里浮现出父母亲,特别是母亲那慈祥的目光,几个妹妹活泼可爱的神态以及那浓浓的彝历新年的年味,禁不住从眼眶里落下几行思念的泪水……
二
再过几天,一年一度的彝历新年就要到了。整个山寨的庄户人家为了使年过得丰盛一些,便热热闹闹地忙碌着,做着拾遗补缺的活路。我们家也不例外,尽管从年初开始为彝历新年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但确实还有许多补缺的活路要做。这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磨制过年豆腐。
年初,父亲从中良队姓牟的农户那里买来了一些优良黄豆种子,在自家苞谷地里种起来。为了提高有限土地的利用率,父母亲在苞谷地和洋芋地间种了大量黄豆。到七八月份,挖出洋芋并将其秸秆捣碎后作为有机肥料,深埋在黄豆根部。得到充足肥料的黄豆长得很快,结的豆果一个挨着—个,一颗接着一颗,密密麻麻地挂满了枝干。种在苞谷地里的黄豆,也由于苞谷种植间距宽,加之施了很多羊粪、猪粪等有机肥料,长势也非常喜人。这样到了晚秋时节,我们家就收获了不少黄豆。
这天早晨,母亲从堂屋里跑到堂屋外,从堂屋里循着木梯爬到楼上,到处翻箱倒柜,好像在寻找什么重要的物件。父亲见母亲这样忙里忙外地折腾着,有些诧异,问道:“你在找啥子贵重的东西嘛?”母亲神色有些焦虑地说道:“我家的岩盐已经没有了。”“去年我才挖了那么多,咋就没有啦?”父亲感到有些奇怪。我们一家人平时都喜欢吃豆花豆腐,消耗的岩盐自然就多一些,可也不至于这么快就用完了。“哦,对了!”父亲若有所思地说道,“前段时间下甘海子有两家亲戚来找岩盐,我就送了他们一些。”母亲着急地说:“都快要过年了,我们家还没有磨制豆腐,你看咋办嘛!”
岩盐是我们山寨人磨制豆腐豆花时用的卤水。用岩盐做出来的豆腐细嫩、有光泽、润滑,吃起来口感好。这时,父亲用火钳夹着火炭将烟锅里的烟点燃,吧嗒吧嗒地吸了几口后,慢条斯理地笑着说:“孩子他妈不着急不着急嘛,我自然会想办法呢!”
那时,父亲是生产队大队长,工作本来就很忙。恰巧在我们家磨制豆腐的关键时候,乡上来了通知,说乡上要开会,会后要到大铺子村参观考察学习,前后要耽搁一个星期。乡上的通知不可违抗,父亲只好去开会了。离过年越来越近,磨制过年豆腐的时间不能拖。于是,母亲决定自己去野外挖岩盐。
这天鸡叫头遍,东边的山顶上还挂着明亮的启明星时,母亲带着苞谷馍馍,拿着绳索和麻布口袋,肩扛着挖锄,踏着蜿蜒崎岖的山路,向对面的鸡公山走去。
鸡公山高大巍峨,横亘在我们山寨对面的东南方向,浩浩荡荡,绵延几十里。山渐渐近了,光秃秃的。山脚下,嘎尔河奔腾而来,在这里转了个弯,便蜿蜒向雅砻江边奔流而去。母亲小心翼翼地往上攀登着。那岩石峭壁,犹如天堑。前段时间,生产队为了方便村民挖岩盐,专门在峭壁缝中长着的一棵粗壮的松树上系上了一根粗壮结实的钢丝绳索,供挖盐人攀缘。母亲一手握绳,—手扶壁。手疼了,不肯放弃,也不能放弃,喘着粗气继续往上攀登。
通过艰苦努力,母亲终于登上了挖岩盐的地方。这里岩石嶙峋,地形凹凸不平,行人很难走。母亲循着这条石径小路慢慢往前挪动着脚步,渐渐地那悬崖峭壁下的山洞映人眼帘。山洞很深,幽暗阴森,不时从里面往外飘出一股股刺鼻的岩盐粉末味。母亲从衣兜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手电筒,借着光亮慢慢地侧着身钻进了山洞。
两个钟头的光景,母亲从山洞里拖着胀鼓鼓的装满岩盐粉的麻布口袋,来到洞外。她从头到脚沾满了灰白色的岩盐粉末,像冬天里浑身上下积满了雪的松树那样。母亲拍了拍身上的岩盐粉末,就拿着细绳把麻布口袋扎紧,并用粗绳将装满岩盐的麻袋捆绑结实,沉沉地背在身上,又一边握着悬崖上的钢绳,一边扶着岩石头也不回地往家里走着。
第二天,母亲吃过早饭后,将岩盐粉末倒在竹制的大簸箕里,用细筛将杂质筛干净。她把筛好的岩盐粉末拿到大瓷盆里,加上适量的热水搅动,并拿捏成拳头般大小的岩盐饼,放在楼上晾干。
这天吃过晚饭,母亲点着松光在瓷盆里洗着过滤豆浆用的棕树皮,这是已经用了好多年的棕树皮,中间细密的棕树毛已经脱落得差不多了。有几次母亲磨出的豆腐,由于过滤豆浆用的棕树皮破洞多而在豆浆里漏进了许多豆渣,使本来很好的一锅豆腐变成了豆渣。为此母亲经常埋怨父亲:“叫你找一点新的棕树皮,你就是不找!”于是父亲吩咐我说:“这点事你去办吧!”第二天,我一早就蹦蹦跳跳地来到赵家湾子姓赵的家里。因这家的当家人跟我父亲关系好,经常你来我往,互通有无。当我说明来意后,赵叔叔二话没说,拿起弯刀就爬到房背后的那棵高大棕树上,噼里啪啦地割着棕树皮。棕树的树干上总是有一层黑黄色的纤维,那就是棕树的皮了。棕树皮用途广泛,在我们这个山旮旯里,主要是做滤豆腐和制作蓑衣用。父亲经常用别人送的或者用钱买来的棕树皮,找人用篾块或细麻绳把它们紧密连接制成蓑衣给爷爷,让他在下雨天放羊时披在身上遮风挡雨。不—会儿,十几张上好的棕树皮就装在我的背篼里了。我谢过赵叔叔后,背着棕树皮很快回到了家。父母亲见我这么快就将棕树皮拿回来,着实夸了我一阵,我感到心里喜滋滋的,满脸乐开了花。
点豆腐的岩盐粉有了,过滤豆渣用的棕树皮有了。母亲从这天上午起就张罗着磨制过年豆腐的事了。母亲是我们这个山寨里做豆腐的能手,她做的豆腐白白净净、老嫩适中,绵软而富有弹性,而且香味十足。
母亲将锅和磨制豆腐用的木盆及石磨槽清洗得千干净净,还特意将棕树皮洗了又洗,直到没有异味为止。看着母亲为磨制过年豆腐而忙碌,我鼻子里似乎闻到了年夜饭里那缕缕的香气,耳朵里似乎听到了杀过年猪时猪的嗷嗷叫声。
母亲将磨过年豆腐用的黄豆从屋里搬了出来,轻轻放在篱笆筐里,开始進一步筛选起来。母亲说:“制作过年豆腐用的黄豆要颗粒饱满,更不能被虫蛀和老鼠啃过。不然,供奉给祖先,祖先会不高兴,而且搞得不好,还会降祸给主人家。”
去黄豆皮可以采用两种办法,一种是浸泡去皮,一种是磨制去皮。母亲在平时制作豆腐时,两种方法都使用,而且都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前一种要提前两天用温开水浸泡,直到把那些小小的黄豆泡得鼓鼓胀胀的,用手轻轻地把外皮搓落,把脱了皮的黄豆放进石磨里推磨成豆渣,然后做成豆腐。
因为过年时间临近了,母亲直接采用磨制去皮法,这样比较节省时间。母亲将黄豆装进竹钵里,放到屋檐下的石磨旁,开始去豆皮。我家的磨子是奶奶去世后,爷爷从朵洛搬家时带过来的,已经用了好几十年了,泛出一种文物般的光芒,上下两片非常好用。母亲叫我协助推磨,因我是我们家老大,弟弟妹妹们还小,只有我可以随时帮父母一点忙。母亲一只手紧握着磨柄,另一只手抓出竹钵里滚圆的黄豆,一把一把地往鸡蛋大小的磨孔里放。我右手握着母亲手上的磨柄,使劲地推起来。由于两手合力使劲,上半片的磨盘飞快地转动起来,使得破碎的豆壳和豆粉从两片石磨的契台处飞速地流进磨槽里。磨槽是凹形的,是爷爷从山寨旁的一片森林里,精心挑选的一棵粗壮的青杠树做成的,质地坚硬,经久耐用。两片磨盘放在上面,无论磨子怎么飞速转动,磨槽始终稳稳当当。
磨豆浆的程序跟破豆皮一模一样。不过磨豆浆,感到磨杆很沉,推起来非常费劲。我协助母亲推了一阵后,累得心儿怦怦直跳,汗珠子不断地从脸上簌簌滚落下来,嘴里不停地喘着粗气。这时,母亲叫我停下来休息一阵,但她自己并没有歇着,而是艰难地继续磨着。因为做豆腐还有很多工序,母亲还得赶时间。石磨飞速地推动着,豆浆从磨缝隙里汩汩地流了出来,沿着磨盘的边沿急急地流进磨槽里,冒着无数个小气泡,散发着一阵阵的清香。豆浆呈白色,像冬天里挂在树梢上的雪,玲珑剔透,煞是好看。
母亲将磨好的豆浆端到火塘边,放进锅里煮沸。她从楼上取下岩盐,放进木碗里捣碎,加上适量水浸泡备用。她又将洗净了的棕树皮一层一层地小心翼翼地铺在竹制筲箕上,准备过滤豆浆。一会儿,放置在火塘上的豆浆煮沸了,母亲用木瓢将其一瓢一瓢地舀进筲箕里过滤。所谓滤浆,就是将浆水中的豆渣滤净,以免影响豆浆的凝结。按我们这个山寨里的习俗,过年时的豆腐一定要凝结成形,不然会视为不祥,要重新做,直到凝结成形为止。
母亲将过滤好的豆浆放进架在灶膛锅庄上的大锅里,重新煮沸。待豆浆煮沸后,她将灶里的火灭掉,让滚烫的豆浆慢慢冷却下来。过一会儿,她将有一定浓度的岩盐水,滴进锅里已经冷却下来但还有温热气息的豆浆里,用木瓢轻轻而均匀地搅动着。豆浆在锅里飞快地旋转着,不时地冒出小小的气泡。母亲给我说,只要豆浆久久往—个方向旋转,说明需要继续点岩盐。—会儿,沿着锅边转动的豆浆减慢了速度,而且向相反方向慢慢转动—会儿就停止了,这说明点进豆浆的岩盐已恰到好处。这时,母亲将木制锅盖盖在锅上,等待豆浆凝固起来。
大约半个小时,母亲揭开锅盖,映人眼帘的是豆浆已经凝固成块状的豆腐雏形。同时迎面扑来一股股清香的豆腐味,使人垂涎欲滴。我忍不住用木瓢舀了一口尝尝,感到鲜美可口,令人回味无穷。当我再要舀一瓢喝时,母亲轻轻拍着我将要伸进锅里的手,嗔怪道:“馋鬼,不要再吃了,如现在吃完了,过年那天吃什么呢?”我只好停住了手。几个妹妹向我做着鬼脸:“谁叫你嘴那么馋呢,活该!”于是禁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将手缩了回来,感到心灼热脸发烧。
母亲将滤豆腐用的筲箕放进锅里,左手使劲摁在上面,让墨绿色的豆窖水缓缓溢进筲箕里。她用右手握着木瓢将豆窖水不断舀进放在火塘边上的木桶里,直到一点豆窖水也没有,只剩下干干的豆腐为止。
母亲看见已经好久不见油荤的我们几姊妹,感到有些于心不忍。于是,她跟父亲商量后,决定将这锅豆腐先给娃娃们打牙祭,另外再做一锅过年时用。听到父母亲的决定,我们几姊妹高兴得跳了起来,妹妹们都一个劲地亲着母亲的脸说:“爸爸妈妈真好!”为吃上这可口的豆腐,全家人都忙乎开了。我和几个妹妹按照父亲的吩咐,跑到菜园子里扯了一把葱子,还摘了一把藿香叶片,回到家里洗净后交给父亲。父亲将葱和藿香切细放进碗里,然后放进一些花椒油和辣椒,做成浓浓麻辣味的蘸水。
母亲将热气腾腾的豆腐端上了桌,还给每人舀上了一碗黄澄澄的苞谷饭。我迫不及待地将白净的豆腐蘸上蘸水,和着苞谷饭狼吞虎咽起来。母亲做的豆腐滑嫩细腻,与父亲做的蘸水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其味道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几个妹妹也不甘示弱,都争先恐后地吃着鲜嫩可口的豆腐,使得母亲不断地从锅里舀豆腐进桌上的木盆里。
我们几姊妹一个个都吃得肚儿滚瓜溜圆,嘴里不停地打着饱嗝,可心里还想吃很多很多。
我们正吃得高兴时,我家那只黄狗疯狂地吠了起来。父亲叫我出去看看,是啥东西让这只狗那么撕心裂肺地狂吠。我放下碗筷,快步打开房门跑出去,只见院坝边缘一角站着一个年轻的少妇。她手里拿着一根木棍,神情慌张地防备着狗的袭击。我三步并作两步奔到狗的面前,很快将其唬住了,并顺势将客人引进了门。父母亲热情地将客人招呼到饭桌上,并舀了一碗飯,叫她吃一点豆腐。原来这是吉克家过门不久的新媳妇,名叫石布莫。她头戴花包帕,上身穿着呈红、黄、白三色的绣花衣服,下身穿着一条白里透蓝的褶裙。她圆润白净的脸上沁出滴滴汗珠,胸脯一起一伏的,嘴里不停地喘着粗气。她没有动筷子,说是剐吃过饭。她神色慌张地说道:“我在家中连做了两锅豆腐,都是松松垮垮的,没有形成像样的豆腐,婆婆为此说我手艺不到位,连一锅豆腐也做不好。她还说,过年豆腐做不好,是不祥之兆,弄不好有祸凶出现。”她说着说着,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母亲急忙安慰道:“年轻人有时做不好豆腐也是常有的事。做得多了,就会巴巴适适的。”
石布莫站起身对母亲央求道:“您是我们寨子有名的做豆腐能手,求求您到我家里看看,这两锅豆腐到底是什么原因做不成功的……”家中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需要收拾,圈里那两头过年肥猪还等着喂食,明天还要磨制过年豆腐……但母亲毅然地说:“好吧,我跟着你去看看到底是啥原因。”她给父亲和我们几姊妹吩咐了今晚必须要做的几件家务事后,就跟着石布莫走出了门。
这时,正接近黄昏,太阳也渐渐隐没在八安山背后,它的余晖还远远地挂在东边鸡公山的峰顶上,显得异常绚丽多彩。一阵阵冷风扑面而来,使得母亲微微寒战。石布奠家住在下甘海子寨,离我家有两三公里远,且道路崎岖,很多路段凹凸不平,碎石嶙峋,母亲走起来有些吃力。石布莫毕竟年轻,走起路来像一阵风似的,步伐特别轻快。母亲也不甘示弱,紧紧地跟在她后面。这样,他们约莫走了半个小时,就来到了吉克家。
见母亲来,吉克全家人十分高兴。吉克家当家的老莫苏(老母亲)给母亲递了茶水,并倒上了一杯酒。母亲不爱喝酒,只是不断地抿着茶。她认真听了他们家制作豆腐的过程后,就明白了豆腐制作不成功的问题出在哪里了。母亲放下茶杯,系上围裙,并用裙裾擦了擦白净的脸上滚落下来的汗珠,就示范做起豆腐来。
母亲将石布莫早已磨制好的豆浆倒进锅里煮沸,用木瓢将其舀进已铺好棕树皮和白纱布的木桶上的筲箕里,小心翼翼地将豆渣滤出。过一会儿,她又将滤净的豆浆水放进锅里,用微火将其慢慢煮沸。待豆浆煮沸后,将火塘的柴火全部退出,让豆浆水慢慢降下热度。这时,母亲从石布莫手中接过岩盐,用纱布将其渣渣滤出,并装进木瓢一点一点地滴进豆浆水中。同时,不断地将豆浆水摇动着、摇动着。母亲将岩盐水滴到适中时,则停止了木瓢的摇动,让豆浆水自由地旋转着。豆浆水在锅中急速飞快地向一个方向转动着,转动着。过两分钟后,豆浆水慢慢向相反方向转了几圈后,则停止了转动。这时,母亲果断地用锅盖将锅中的豆浆水紧紧地盖住。大家屏声静气,谁也不愿也不敢说一句话,生怕搅乱这宁静的空气,进而影响锅里豆腐的生成。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母亲轻轻地将锅盖揭开,只见锅里的豆浆已成块地凝结成形。母亲将筲箕放进锅里,一边摁住筲箕,一边将溢进筲箕里的豆窖水舀出。没有一会儿,一锅白净、细嫩的豆腐呈现在主人家的面前。主人家的老婆婆拉着母亲的手激动地说道:“我原以为家里有什么神灵在作怪,原来是做豆腐的技巧出了问题。”她转身对站在一旁面有愧色的媳妇说道:“看人家做豆腐的技巧是那么娴熟,手艺是那么出色。要多学着一点。”媳妇石布莫“哎”地答应了一声,低下头,脸儿红红的,双手不住地摆弄着裙裾。
母亲脱下围裙,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便坐在火塘边的竹席上,慢慢地说道:“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得了的技巧,只是做得多了,自然也就熟练了。”这时,母亲才将主人家前面两次做豆腐不成功的原因做了解释。原来石布莫第一次在滤豆浆时,漏进了许多豆渣,使其无法凝结成块状,结果一锅豆腐给做砸了。第二次是在点岩盐水时,在豆浆里滴进了过量的岩盐水,使得豆腐变硬,无法凝结成形,呈灰色状,味道很差,难以咽下肚。
母亲为了让石布莫学会做豆腐,特地当场让其演练一番,结果做成一锅很好的豆腐。老婆婆着实夸奖说道:“看来你还是心灵手巧嘛,一看就会。”引得大家爽朗地笑起来。石布奠脸儿红扑扑的,像熟透了的桃子,羞涩地说道:“以后还要经常请教婶娘呢。”母亲高兴地拉着她的手说:“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尽管说就是了。”
当晚,母亲又被寨子里的两家新媳妇请去做了磨制豆腐的技术指导。她尽管很是疲倦,况且夜已很深了,但还是坚持着去做了技术指导,做到使其学会为止。
母亲回到家中时,已是后半夜了。我家的那只公鸡引吭高歌起来,使得寨子里的其他公鸡也跟着呜叫了起来。此时,母亲也十分疲倦了,便踉踉跄跄地上了床,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吃过早饭,母亲又开始为磨制过年豆腐的事而忙乎开了。她一会儿去豆皮,一会儿磨豆浆,一会儿清洗棕树皮,一会儿准备岩盐。这样,她一直忙了大半天。
晚上,母亲又做成了两锅过年用的豆腐。她把已做成的豆腐用锅铲切成方块状,一块一块地放进簸箕里,然后放在楼上通风处将其水分沥出。
此后的几天里,我们在堂屋里走动时,不时闻到一股股扑鼻的豆腐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