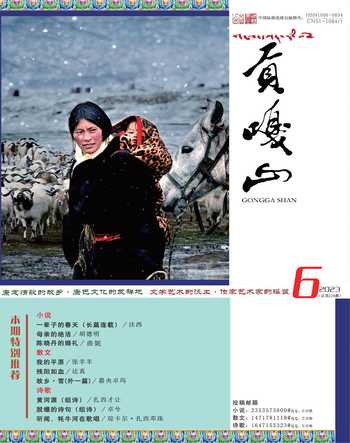我的平原
2024-01-03张羊羊
张羊羊
霜
霜快起时,青菜最初就知道了。青菜怕冷,它为了取暖越冬,将身体内的淀粉类物质转化成糖分,它的细胞液就不容易被霜冻坏了。被霜打过后的青菜,味道就变得甜甜的,尤其受人喜爱,这个也叫“霜打菜”。
我小时候住的屋子前,有一畦畦这样的霜打菜,够吃上一个冬天。
霜与瓦,像人与狗,是一种古老的温情结构。瓦不是指现在斑斓的琉璃瓦,而是那时黛青色的瓦,它有着迷人的旧。秋末冬初之际,一层薄霜铺在瓦上,毛茸茸的,常年被风吹日晒的瓦终于可以有了休憩的片刻,仿佛盖了床被子可以睡会了。沟瓦凹,瓦头向上瓦尾朝下;盖瓦凸,瓦尾向上瓦头朝下。凹凸相扣,鳞次栉比,这情景被诗人看见了,会用上四个字“霜瓦鳞鳞”。于是,“瓦上霜”似乎成了一个固定的词。
我可能像陆游,尤其喜欢瓦上霜这一道风景。陆游在《初冬》里的表述极为直接:“绝爱初冬万瓦霜。”他也是吃过不少苦的人,在《咸齑十韵》就袒露过自己的储备忧患意识:“九月十月屋瓦霜,家人共畏畦蔬黄;小甓大瓮盛涤濯,青菘绿韭谨蓄藏。”陆游对霜的喜爱也不是随便说说的,在《闻笛》里有“雪飞数片又成晴,透瓦清霜伴月明”句,他甚至还有句子只改一字,《落叶》里便是“万瓦清霜伴月明,卧听残漏若为情”。可能对瓦与霜的结构爱得过了,转身在《梅花绝句》里再有“万瓦清霜夜漏残,小舟斜月过兰干”,到最后在《读》诗中感叹人生易逝也用了句“人生忽如瓦上霜”。
虽然学过多年物理,却一直存有霜与雨雪一样的错觉,从天空洋洋洒洒而下,落在柳枝、芦苇以及矮草之上,就像多年来把霜降等同于降霜一样,实则这个时节的天气还不够寒冷到水汽凝结成这种白色晶体。古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为务农岁序,秋日霜降,万物收缩,而农事已然收成。段玉裁在《说文》以霜为喻,既是万物丧失,也是成就万物之征。
自古以来,很多人喜欢雨、喜欢雪,即便哆嗦着也能看到几分暖意来,五字一句、七字一句,冒也冒不完。唯独霜,总带了几分冷色调。好好的美女偶有不开心的时候,得说她冷若冰霜;好好的小伙子恰好连续遇到两件糟心的事,得说他是雪上加霜。这霜似乎变成了一种阴影。
“霜”这个字唯一给我带来暖意之事,是小时候因为天冷干燥,长了一副“萝卜丝脸”,妈妈会用热水为我捂会儿面孔,用食指从扁圆形铁盒中一层薄薄的锡纸下面掠出一种叫“百雀羚”的霜,细细地涂抹在我脸上,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盒子上是四只鸟的图案,什么鸟我记不起来了,其中有一只应当是燕子吧。这种霜产自上海,那时连城里都没去过,别说是上海了。这可能是我儿时仅有的护肤品,甚至有家里买不起“百雀羚”的同学会羡慕地闻着这香味。多年以后,我好像少有被凛冽寒风吹割的日子,久安温室,长不出“萝卜丝脸”了,虽然皮肤易干燥,天一冷脸上会起白屑,却不用任何润肤之物。只是常想,那些如“百雀羚”之类的物品为什么要叫霜呢?面霜、眼霜、防晒霜……玻尿酸、甘油、氨基酸、胶原蛋白、维他命原B5、AHA,原本物理的霜落于万物,现在变为化学的霜涂满肌肤。“百雀羚”已少见,我的爱人也不用这个牌子了,它曾在民国时期十里洋场陪伴过阮玲玉、周璇、胡蝶等佳人的芳华。以致几年前看到一张“百雀羚”的宣传海报,—个老上海名嫒托着一只经典的“小蓝罐”,下面的两排字让我有点百感交集: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女。我也想着买回一罐来,找个机会再吹出一张“萝卜丝脸”,用这霜涂抹涂抹我这差不多也饱经了点风霜的脸。
有一种菊科植物叫五月霜,有一种茜草科小灌木叫六月雪。五月霜只是在北方见过几次,并不起眼。六月雪我养过两回,没侍弄好后来就枯了。
五月降霜、六月落雪,看起来都缘于大冤之事。实则极端天气越来越多,没什么可奇怪的。张岱的《夜航船》有词条“五月降雪”——《白帖》:“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入狱。衍仰天而哭,五月为之降霜。”这个事《论衡》《后汉书》《淮南子》《昭明文选》等均有记载。许多诗句也用了这个典故,包括李白《古风三十七首》里的“燕臣昔恸哭,五月飞秋霜”。李白有时挺没意思的,在另一首《上崔相百忧章》又提“邹衍恸哭,燕霜飒来,微诚不感”。赐金放还出长安时,你不是写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吗?好好喝酒便是,想那么多干吗。
渐渐地,“燕霜”一词成了蒙冤之典。
天还未亮,河岸边的芦苇一片苍黑,深秋的白露,已经凝结成寒霜了;天已微亮,河岸边的芦苇一片凄清,未干的白露,还在苇叶之上;天已大亮,河岸边的芦苇泛出白光,深秋的白露,所剩无几了。《诗经-蒹葭》说的是北方—个清晨露水在苇叶上变化的故事,這幅景象,我在南方一个村庄旁的小河边也能常见,只不过是气候的缘故,季节略微比北方要推迟些。
二十四节气的表意是很美的,但有些较为约莫,比方说霜降时,霜未必就已来临,小雪时,雪未必就落了下来。
关于霜,我最爱的还是庾子山那句“霜随柳白,月逐坟圆”里古老中国的清寂气息,这气息在一千多年后,我依然能够嗅见。虽然霜附在光秃秃的柳枝上,而不是外婆采摘用来裹粽子的芦苇叶上,我还是写下来“外婆的粥碗空了,坟头一筛霜降”,而且筛得那么均匀,仿佛外婆从泥土里跑出来亲自筛的那般。北宋晏几道有诗“天边金掌露成霜,云随雁字长”,这一句有了庾子山之句的妙。霜与云都有可托付之物,那是柳与雁。
可无论从李白“疑是地上霜”“我无燕霜感”,还是苏轼“鬓微霜”到“鬓如霜”,无论从张继看到“月落乌啼霜满天”还是杜牧看到“霜叶红于二月花”,霜已是汉语长河里涌动不歇的流水,我们该拥有“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活法。
霜降过后一周,因有事去乡间几日,见那些葱郁的红萝卜缨子、白萝卜缨子、山芋藤时,心里很是盈实。尤其看到垄间一茬茬的青蒜叶和憨厚的大头青,我只想着三个字“等霜来”,等霜抹过你们的身体,那滋味就更是妙极了。
草木灰
老丝瓜孤零零地从天空垂了下来,像一个半蜷半松的拳头。
奶奶略显多余地踮了几下脚尖,远远够不着,这可不能笑话一米五几的奶奶。我时常明明知道够不着的东西,也会多余地踮踮脚尖,因为这些多余,人括着的部分才显得不那么多余。随后通过一根竹竿,再绑上镰刀后,它终于割落在地。“扑通”一声,滚了几下。她弯腰时,皴裂的手指上,似乎住得下平原上所有的河流。
河水担回灶间,柴火的余烬还温热着铁锅,奶奶扔掉搓缩了的丝瓜筋。新摘的老丝瓜晒干去掉外层表皮后,她用网状瓤一遍又一遍刷洗碗筷上不多的油渍。若没有这些亲眼所见的部分,我断然想象不到,那么入口嫩滑的丝瓜瓤会老成这个样子。
邮差骑单车时急促的按铃声慢慢消失在乡间的小路……这是出生地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如果仔细点,旋转的地球仪上,我还能看见瓦片间的一株檐头草,草旁躺着我掉落的第一颗门牙。耳边是奶奶的声音:下面的牙齿掉了,要扔上屋顶;上面的牙齿掉了,要扔到床底。《小偷家族》里的小女孩由里下边的门牙掉了,祥太帮她扔到了屋顶,日本也有这样的习俗,这个做法似乎源于祖训,可以长出—颗坚固的牙齿。我的牙齿落第二遍了,第二遍的时候再不要这么干。
我继续看旋转的地球仪,少不了我出生的那片小小的平原。它离大海有点距离,却就在辽阔的大海边,“我总能看见收获满满的黄昏,那个田野边手握茅针的少年/平原上是他汲鼻涕的声响/和妈妈扑打痱子粉的气味”(《馈赠》)。是的,我能看见金黄麦芒与稻穗交替的田野,白茫茫的不是雪是棉花,以及屋前屋后挂满了比范成大的诗更水灵的四季瓜果蔬菜。
那里,都是熟悉的味道,长满了一眼就可以认出来的事物。那里,少年“噗噗”地吹口琴,在一缕炊烟下,和“吱吱”的稻草声、“噼啪”的麦秸声交织在一起。
灶火映红了母亲们的脸,老灶柴火烧的草木灰多么洁净。妈妈用簸箕装满它,撒在收割过的韭菜畦上,又一茬葱绿使劲地冒了出来;一些加上盐、泥搅拌后裹好鸭蛋,过阵子剥开就成了晶莹的皮蛋;奶奶用它加以泥土捣成糊状,和起香瓜的种子,笃在正对灶膛口的墙壁上,储藏好下一个甜甜的夏日;阉小猪的师傅手脚麻利,像汪曾祺在《兽医》里描述的那般从容,用笤帚将事先准备好的稻草灰往小猪的伤口上拍打一遍,小猪一下子又能站了起来;我呢,也会隔三岔五惦记着装些草木灰,铺好潮湿的羊圈,白羊毛通常会变成灰羊毛,那小小的地方是南方田野肥沃的原动力。
艾克瑟·林登有本薄薄的《我的牧羊日记》:“羊儿不只是吃青草、干草和青贮饲料,它们简直就是和草融为一体。羊毛里夹杂着稻草,膝盖上有草渍。不知道的,还以为它们的耳朵、眼睛甚至皮肤都能吃草呢!”羊儿与草之间的密切关系,让我再次想起散文家苇岸所言:“那吃草的亦被草吃,那吃羊的亦进羊的腹里。”世间的每一个角落,都诞生着哲学。
这些物事,年复一年地在平原上发生着,看起来没什么可以大书特书的。
年少时,去梅村小学的上学路上,每天会途经两次孔庙,那时候不晓得孔庙与孔子有关。印象中,孔庙因一个特殊的年代而十分破败,只剩下大致的框架,里面堆满了乡邻们捆好的柴草。我的外婆不能人家谱,她的兄弟们好像是孔子的75世孙。每个少年的身后都有一双外婆的眼睛,不识字的外婆却有菩萨般的好心肠,她在我年幼时就递给我一种品质:善良。外婆一直活在灶膛前,从未停下烧柴火的温暖样子。
爷爷生前是一个好木匠,他用屋前屋后的树们,打制过许许多多精致的家什。刨下的木花在灶膛里烧得特别旺,锯下的木屑打扫好装进蛇皮袋,冬天能派上用场。挂满冰凌的教室里,一个孩子搓着冻红的小手,将双脚架在脚炉上。脚炉里底下铺了一层木屑,中间铺了一层淬满火星的稻草灰,上面再铺一层木屑,可以暖脚,课间休息还能烤点零食吃。当我写下“脚炉里那块饼干/夹了通红的心/几颗在蹦的老蚕豆/如缀在上面的芝麻”这样几句,日子又被拉回。我拎了脚炉回家,把里面冷却了的草木灰倒人羊圈。遗憾的是,我一点未能继承他的手艺,可以透过一棵树看到它内里的木纹。
小雪与大雪间,雪一粒未落,两位亲人再也见不到今年的雪了。
一米五几的奶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只剩下四五斤的样子,装进了那只小巧的檀木盒子。爸爸是长子,患了阿尔兹海默症,那盒子只能由我这个长孙帮他捧了。一米八几的岳父,饱读诗书与报纸的头版新闻,只剩下六七斤的样子,装进了那只小巧的楠木盒子。他也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生有二女,那盒子还是只能由我这个长婿捧了。
我一直觉得他们虽说活得苟延残喘,大概还能陪我一段时光。最后,岳父留给了我好些没有喝完的老酒,奶奶留给我好些认识却喊不出名字的野花野草。我永远忘不了奶奶最后张大嘴巴的样子,弥留之际,隔壁房间的姑姑在酣睡中,没有人和她道别,三个儿子和—个女儿她想喊谁的名字呢?脑海中有没有闪过我这唯一的孙子?《星际穿越》里有句台词:“知道人死前看到的最后一幅画面是什么吗?是孩子,孩子的脸,在死亡的瞬间,你会完全下意识地挣扎求生,放不下它。”我们没有死过,死过的人无法告诉我们,所以这台词不是答案,只是猜想。
那是曾经不用去远方看油菜花的日子,大雁守时地从头顶飞过,梅村小学门口那座老戏楼上一出不知名的戏里—条水袖像是拂到了脸上。每年收割完庄稼,乡亲们会把剩下的裸露在地面的作物根茬烧为灰烬,它们经过雨水渗入泥里。我把这看作一种反哺,因为这种好的循环,平原上的温情生生不息。这里生长我一直在写的东西,我写了很多年了,还没写完,这片小小的故土,足以让我用汉语叙述的方式为它匍匐一生。
摇篮曲
摇篮曲不光是那些哄宝宝入睡的歌谣吧?五六岁、七八岁的童谣也是。
1945年,在南半球安第斯山脉西麓的智利,五十七歲的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给诗集《柔情》写后记时说道,“摇篮曲其实是第二种母奶”,她一直断断续续地写一些摇篮曲,是想成为能哄自己入睡的母亲。她说,最早的夏娃们先是把孩子抱在怀里或放在摇篮里摇晃,后来发现来回摇晃的动作中有了柔和的声音伴随,更能使孩子入睡,不过那时的声音只限于闭住嘴唇的哼哼。
1908年左右,在北半球太平洋西岸中国宣统年间的浙江嵊县,两三岁时的胡兰成(1906-1981)开始学语,母亲抱他看星,教他念:“一颗星,葛伦登,两颗星,嫁油瓶,油瓶漏,好炒豆,豆花香,嫁辣酱,辣酱辣,嫁水獭,水獭尾巴乌,嫁鹁鸪,鹁鸪耳朵聋,嫁裁缝,裁缝手脚慢,嫁只雁,雁会飞,嫁蜉蚁,蜉蚁会爬墙……”接下来,因为母亲要骂四哥一句“还不楼窗口去收衣裳,露水汤汤了”而中断了。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说她尊重儿童们的记忆,远超过一切,超过她的荷马、莎士比亚、卡尔德隆或者鲁文·达里奥。她的记忆或许来自哄孩子睡觉的“啊哦”声最终使自己也睡着了……
而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对儿歌的经验是,“我的母亲不会唱歌,而童谣本来就是念念的,单是念亦可以这样好听,就靠汉文章独有的字字音韵俱足。”我相信,他母亲哄他睡觉时就这样念着念着自己也睡着了……
这摇篮曲隔了七十多年的时光,从浙东新嵊盆地袅袅飘来,飘到苏南平原上的武进,我两三岁,妈妈也抱着我看星,教我念:“天上星,地下钉,叮叮当当挂油瓶,油瓶漏,种赤豆,赤豆勿开花,外甥绣球花……”是吗不是我记错吧,不会的。胡兰成听到的是“油瓶漏,好炒豆”,我听到的则是“油瓶漏,种赤豆”,一样的是两位相隔七十年的母亲都用着方言。好炒豆也好,种赤豆也罢,接下来扯的逻辑大概会笑疼肚子了。
再往东南,又一个粤地孩子的嗓音:“月光光,照地堂,年三十晚摘槟榔,槟榔香,摘子姜……”大年夜的月亮啊,只有孩子敢唱,我也在用吴方言回应他“亮月月,桫椤树,知了看家啼又啼……”。
我听见了一种对话,这些有时听起来不知所云的摇篮曲或童谣中,夹杂着乡间动植物温和的影子,以至几十年后我怀想那些歌谣,总有一种声音在其间丝丝人扣,那就是布谷始终乐此不疲地叫着,事无巨细地看护着东部中国的农业。古老的风在吹拂大地,怀抱我们的双手是妈妈们用蛤蜊油涂过皴裂的指头、再用橡皮膏绑好的双手,哄我们入睡时,她们念着念着也睡着了……因为我记得,清楚记得,好多次从松垮的怀里醒来时,妈妈疲惫地睡着了,而我张望几下又继续睡去。有人说摇篮曲是妈妈们劳碌一天后轻轻哼唱可以哄宝宝早点入睡后自己也能早点睡,有钱人家的奶妈、保姆是哼不出民间摇篮曲的韵味的。
“萤火虫虫夜夜红,阿公担水卖胡葱……”又一首摇篮曲念起了起句,昆虫和谷物们依然住在童谣中。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继续说,摇篮曲可说是母亲白天黑夜对自己的心灵,对孩子,以及对白天看得到、晚上听得见的大地的对话。我生活的乡间还有摇篮曲吗昔日的鱼米之乡已看不见麦芒与稻穗,人们吃着东北运来的大米。像我这样远离出生地的孩子已经到了中年,那里几乎只剩下没有孩子可哄的老人了。
想起多年前的一幕,五十几岁的叔叔要去动手术,他含着泪对七十多岁的奶奶哽咽:妈妈,我怕。奶奶说:你个小佬,怕什么呢,妈妈陪你的。奶奶伸出细瘦的胳膊,搂着叔叔,轻拍他的背,哼起了熟悉的调子,具体哪一首童谣,我确实忘记了。轻轻拍着,轻轻哼着,稍一会儿,叔叔就安静睡着了。我想,这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叔叔没有生病的话,可能再也不会有机会躺在奶奶怀里睡着,没事的话,一个五十几岁的人也想不出来去撒这样的娇了,他不怕我们笑话吗?可那次,谁都没笑。我的眉头从紧皱到舒展开来,嘴角微微一抿。
快有三十几年了吧,没有妈妈搂着,听她哼摇篮曲了。伴随我的,有时是弗朗茨·舒伯特(1797-1828)的,有时是弗里德里克-弗朗索瓦·肖邦(1810-1849)的,有时是约翰奈斯·勃拉姆斯(1833-1897)的,他们不是母亲,却都有摇篮曲,哄睡了无数不同国度、不同年月的大人与孩子。
我试图寻找妈妈给我哼过的第一首摇篮曲,或许她也忘记了,我肯定已记不得了。但似乎有一种不确定的声音就是那个旋律,我一直找不到又仿佛在身边。我隔着肚皮,妈妈的羊水是我未出世前的大海。去大海边吧,也许那里有声音可以让我们安然入睡。
长河
我三五岁时,奶奶就一本正经地说,不可以做坏事,做坏事的人会被雷劈到的。有时挺感激老人们那些唬人的谎话,自幼就约束了孩子的举止。她口中的雷说的是闪电,她现在还不知道闪电是雷。所以我从小就害怕闪电,谁没干过一两件诸如摘瓜偷枣之类的出格事呢?到四十岁了依然害怕,虽然长大了没干过什么坏事,但我怕闪电认识我小时候的那张脸。若是夜里打雷,我会拧开灯,拉上窗帘,这样就只闻其声看不见它的怒样了。
长大了除了闪电,我又怕上了一样东西——X光片。灰底上透白部分就像闪电,就像暗中伸出的野兽的白色獠牙。我奶奶不干坏事,因此她不怕闪电,她怕的是X光片。我起码陪她住过四次医院,都是年纪大了一不留神摔断了胳膊大腿,每次我去取片子時,也假装捏起来对着日光瞧几下,看看肉体中的轮廓有了什么明显变化。
从闪电到X光片,两种害怕几近三十多年了。这些年月就装在一只手表里,那手表我们这一代人共同拥有过,而且是同一个牌子。
于是看见了在手腕上画表的那个男孩。时间真在“嘀嗒”撒腿跑呢。
这声音分明一直在响,从每一个昨夜响到每一个今晨。
我去学校门口接孩子,每一声“爸爸”听起来都那么像。我注意到孩子也在手腕上画了只表。样子和我小时候画的差不多,时间和我的表一样精确。我等孩子的手慢慢塞进我的手里。
就这样,我从一个有人愿意吃我剩饭剩菜的人,变成了不嫌弃他用过的筷子和吃剩的面汤的人。
我在作文里写爸爸,我也在他的作文里当爸爸了。
时光荏苒,我越来越喜欢多年前写的一首诗《三代人》:“有一年,爸爸左手/扶着生病的爷爷/右手拉着我/而立之年的爸爸/多像坚实的扁担/我们去麦地旁看望祖先/在乡间的小路上/我有野花和菜粉蝶的好心情/终有一年/我走在了中间/像那支扁担一样/在那条乡间小路上/走了若干年/直到我也站在了左边//阳光那么光荣地跟随一个家族/简单地走着/走啊,走啊,一直走下去/只是简单去看看爸爸和爷爷”。
走啊走啊,我的爸爸已做了爷爷,走到了另一首诗面前:“秋分深处/有三双眼睛:/一个老花镜/一个近视镜/一个望远镜”。
一段时日以来,我写着写着句子,就会用到“牙口”这个词语。原来是下意识里的事。我以为牙口等同于牙齿的意思,实际上它一指牲口的年龄,二指老年龄牙齿的咀嚼能力,看到第二种精准的释义,内心竞有点悲凉起来。
差不多在孩子第一颗乳牙脱落的时候,我掉了第一颗恒牙。我俩像做功课似的,非常认真地把牙齿收集在同一个储蓄盒里。我记得当时,孩子很不情愿我那浊迹斑斑的老黄牙与他晶莹的小乳牙摆在同一个屋子。
听说在国外,拔颗牙也是一次重要的手术,我终于到了人生第一次动手术的年龄,且一次拔了六颗牙,相当于动了六次手术。我有保留脱落的牙齿的习惯,觉得把妈妈给我的东西收藏齐全。当我看着那些血淋淋的不忍目睹的牙齿、露出不舍的神情时,医生朋友问我,要不洗一洗给你带回去?我果断地摇了摇头。
我弄丢了它们,身体的一些部分再也回不来。
咀嚼是动物们十分美好的事,食草的、食肉的,它们都靠咀嚼成长、衰老,其中的一种动物高大起来,学会了咬文嚼字,虽说读书用不了牙齿,却也会令我多少有点儿失落。门牙没了,平舌音与卷舌音的清脆也离我远去,而我那孩子正在口齿伶俐地背诵唐诗。
2017年,我给《钟山》写稿子写了篇《牙齿》,因为牙齿一下子糟糕起来,写得很是纠结。那时,我已掉了两颗磨牙,还有好几颗也已松动。时隔三年,写这篇《长河》时,我看完牙医捂了腮帮回来,约好下周继续拔牙。等三个月后牙龈生长恢复,再拍X光片视牙槽骨的条件允许,要么种植牙齿,要么装活动假牙。反正都不是真的,我的假牙岁月提前来了。
看着那些婴儿笑起来,露出光溜溜的牙床,然后淌着口水把自己的舌头吮吸得津津有味,我就想着体验那种舔牙床的感觉,可惜有牙齿的时候怎么也舔不到牙床。而今可以舔到牙床了,那感觉却不是多美妙,想想半生有点滑稽,甚至百感交集。舔的时候,一不留神口水溢了出来,我本能地伸出舌头卷刮了回去,我比婴儿多了一个本领是,会舔回自己的口水了。从口水到口水,也是一条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