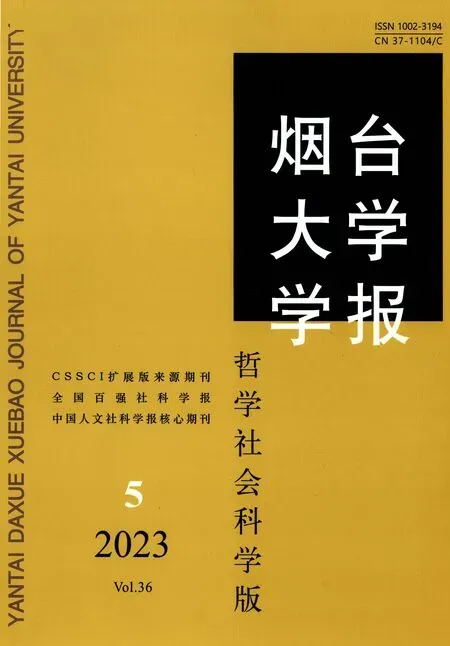回到自在的差异
——德勒兹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三重批判
2024-01-03韩志伟张翘楚
韩志伟,张翘楚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1)
正如M·怀特所说的那样,“20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显赫的19世纪的德国教授的观点开始的”,(1)M·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杜任之主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版,第7页。这里所说的教授就是黑格尔。作为二十世纪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德勒兹也是从批判黑格尔开始的,但他对黑格尔的批判有其独特之处。他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外部的现实经验的差异被概念表象为自我意识的内部差异,再经由辩证法的否定运动在绝对同一之物中被调和。差异仅仅被理解为辩证的、思辨的差异,即绝对精神内部的自相矛盾,而这种自相矛盾又随着绝对精神的自我回归得到最终解决。而由于黑格尔这一总体性的综合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修复对立的能力,真正意义上的反黑格尔主义和反辩证法极为困难,因为一种成为“对黑格尔而言的他者”(an “other” to Hegel)的尝试极有可能落回为“黑格尔之中的他者”(an “other” within Hegel)。(2)Michael Hardt, Gilles Deleuze: An Apprenticeship in Philoso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xi.针对这一困难,德勒兹的方案更彻底地摆脱了在黑格尔的地基上反对黑格尔及其辩证法时所遇到的问题。正如迈克尔·哈特所指出的那样,德勒兹并非后黑格尔主义的,而是彻底离开了黑格尔并尝试为思想建立起新的、替代性的领域。这一尝试的出发点便是摆脱了同一性之束缚的自在的差异,即不是在矛盾与否定的意义上被理解的差异,而是从根本肯定的意义上去理解的差异。
一、自在的差异的出场
影响德勒兹整个哲学计划倾向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如何思考自在的差异本身而又避免落入一种同一性哲学和表象(representation)之中。就德勒兹个人而言,他之所以将矛头指向黑格尔,是因为他将黑格尔的整个理念论体系视为表象体系的巅峰。当然,黑格尔给出的这一无所不包的表象体系并非一蹴而就的,甚至可以说,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表象体系逐步发展的历史。在德勒兹看来,尽管表象体系的每一次发展都试图将存在差异的事物更和谐地纳入其中,但实际上只是使差异服从于更高的同一性的尝试,因而一次又一次地使自在的差异溜走。
德勒兹认为,以往哲学史对差异的把握都是表象主义的,自在的差异在其中被扭曲为表象的差异,被纳入某一层次的同一性之中,而无法实现自身的出场。在古典时期,自在的差异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样,服从于一种实在与概念之间不自觉的同一性;到了近代,尽管康德通过对现象与物自体的划分自觉地指出了认识主体与客观实体间的本质差异,但最终仍乞灵于一种合目的性意义上的同一性,这反而为黑格尔进一步的综合提供了条件;黑格尔通过既是主体又是实体的绝对精神的自身运动,使诸差异服从于一种最高程度的自在自为的同一性。亚里士多德用种差来把握事物间的差异,他认为种差是事物间最完满的差异和距离,是事物之间对立统一的中介。差异大于种差,事物的本质或属就改变了,事物之间就不是相互区别,而是完全相异;差异小于种差,事物之间就无法承载对立形式,它们就成为不可分者。对此,德勒兹指出,亚里士多德的种差仅仅是以同一性为前提、在概念中相互区分的差异,而并非自在的差异本身。用于感知这种差异的是一种概念的眼光,是“希腊人折中的眼睛”;(3)吉尔·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安靖、张子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4页。把握这种差异的方式属于一种有限的表象方式。其之所以有限,是因为差异被限制在对事物大小进行外在划界的种差的层面上,这种大与小的界定歪曲了旨在使差异显现自身的遴选。在差异之遴选中,事物只要达至其所能的极限即为最大,事物的大与小摆脱了本质与表现以及事物间的相对关系,因而差异不再只存在于关系之中,而能够获得自身恰切的概念。而其之所以是表象,则因为此差异总是相对于一种潜在的同一性而言的,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差异总是能够在行使中介功能时达到某种同一性的层级,并且这些层级间又彼此连续,最终形成一个关于世界的树型表象结构。德勒兹认为,亚里士多德式的种差表象混淆了自在差异的恰切概念与概念化的差异,从而也将表象结构误认为是事物本身的结构。从自在的差异的视角出发,亚里士多德对事物的把握不自觉地预设了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在之间的同一性,因此他自认为是差异之圆满时刻的种差,只是恰好能够进入概念之同一性结构中的对差异的表象;他亦自认为呈现出的整个世界的结构也并不是事物本身的结构,而只是能被纳入知识体系、能够填充进表象结构中的内容。
当然,事物本身的结构与表象结构之间的区分,借助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才被揭示出来,一种不自觉的实在论的表象主义才转化为一种自觉的认识论的表象主义。正如汤姆·洛克摩尔指出的那样,古典式的理念论与近代式的理念论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区分了实在本身与对实在的表象。(4)Tom Rockmore, Kant and Ideal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40-41.德勒兹认为,在近代,正是康德最先表明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古典式理解的问题在于其不自觉地预设了客体必然服从于主体的同一性原则,正是康德自觉地坚持了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本质差异,即主客体之间的二元性,从而也为主体不同的认识能力划定了各自的界限。在德勒兹看来,康德坚持诸认识能力间的界限的意义在于“它们的高级形式从不会把它们从它们的人类限度中抽离出来,也不会消除它们在本性上的差异”。(5)吉尔·德勒兹:《康德的批判哲学》,夏莹、牛子牛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5-96、22页。这种划界既避免了能力自下而上的僭越,也避免了能力自上而下被“拔高”。更重要的是,原本由界限表明的异质性的差异不会通过被纳入更高层级而转变为只是在程度或量上有所不同的同质性差异,或者作为同一之物的总体运动中的差异时刻。尽管如此,德勒兹仍指出,康德虽然自觉地认识到实体与对实体的表象之间存在不可弥合的鸿沟,但这一鸿沟只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被言明,现象的差异仍然是表象的差异,而自在的差异始终作为物自体被悬置。如此一来,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核心不过在于“用客体必然服从于主体的原则来替代主客体之间的和谐(最终的一致)的观念”,(6)吉尔·德勒兹:《康德的批判哲学》,夏莹、牛子牛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5-96、22页。从而指出知性的立法职能。然而,知性的立法只能够为现象提供一种形式上的原则,其仍然无法统辖现象在质料方面的差异与多样性,只有理性能够以合目的性的方式重新提供一种和谐。因此,差异要么作为自在的差异被悬置在认知职能的彼岸,现象的杂多性与物自体的普遍性之间的差异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要么作为现象的差异服从于具有更高同一性的认知职能,这不过是以主体的诸认知职能间的同一性取代了主客体之间的同一性。在德勒兹看来,康德对现象与物自体的区分呈现了一个直接向自在的差异敞开、拒斥以概念为中介进行调和的短暂时刻,但无论是康德本人还是其后继者黑格尔,都没有推进这一短暂的环节。康德最终还是以共通感保障了已然被划分的诸职能间的同一性,以合目的性保证了现象之杂多与物自体之唯一间的同一性。黑格尔则更是以绝对精神所具有的无所不包的同一性,在表象体系内部彻底解决了康德式有限知性表象的二元论问题及其模棱两可的态度,成为同一性哲学与表象体系的集大成者。
如前所述,德勒兹指认康德哲学中有过一个自在的差异的短暂出场,只不过康德本人没有继续推进这一差异的立场,也没有接受两个领域间的本质差异所揭示的表象失效的事实,而是延续了以同一性和表象调和差异的立场。对此,同为康德后继者的黑格尔和德勒兹在不同的方向上进行推进,只不过这同一个问题被德勒兹把握为有限表象,而被黑格尔把握为知性思维。(7)Henry Somers-Hall,Hegel, Deleuze and the Critique of Representation: Dialectics of Negation and Differen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2, p.3.黑格尔仍然坚持同一性与表象的效力,因而他只是将康德式表象主义的问题把握为知性思维的有限性,他认为,只要以具有更高统摄力的同一性去突破这一界限,差异就能得到解决。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坚持在诸职能间进行划界的立场是有限的知性的立场,“就思维作为知性[理智]来说,它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彼此的差别。以与对方相对立。知性式的思维将每一有限的抽象概念当作本身自存或存在着的东西”。(8)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版,第173页。知性表象将概念作为既有的、固定的和永恒的东西,因而无法很好地解释一与多、多样性与总体性等关系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突破有限的知性表象方式,进入到一种更宽泛的表象之中,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环节。在有限的知性表象中,概念被视为既定的,界限被视为限制,因此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分界也是绝对的,无限是对有限的超越。然而,当我们这样去理解无限时,无限本身又被限定在有限之外,它总是有限的对立面,受限于对立结构,因而其仍然是有限的。对此,黑格尔指出,无限不是向前一步“超越”有限,而是一种向后一步的“回溯”,无限本身正是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循环往复,是有限不断在无限之中生成和消失的运动过程,有限与无限在其中仍然对立,但二者都被视为同一过程的不同环节。康德坚持知性有限性的界限,“认为只有知性才能成就真理,因而是站在总体的知性立场上反思知性,因而反思出的是知性的界限。黑格尔则认为理性能够成就真理,因而他是站在理性的立场上反思知性,不仅反思出了知性的界限,同时超越了知性界限”。(9)王天成:《黑格尔知性理论概观》,《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3期。从更高的同一性立场出发,诸有限界限之间的差异被推进至对立状态,并进一步发展为矛盾,以至于它们最终成为概念总体内部的自身矛盾,从而将对立或相反的诸差异纳入最高的同一过程。
既然黑格尔已经给出了一种针对表象问题的诊断和解决,德勒兹为何仍将黑格尔理念论视为一种表象主义并极力反对呢?这是因为,在德勒兹看来,康德式的有限表象已经表明表象对差异的有限性,黑格尔并没有将康德短暂地揭示出来的差异立场进行推进,而只是推进了表象体系的最终完成。对黑格尔而言,一切都是那一个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自我中介、自我克服和自我展开,差异、对立与矛盾是精神自身回归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和中介。对德勒兹而言,无论黑格尔如何鼓吹绝对精神中的运动、发展与超越,该过程也不过是绝对精神这一唯一的同一之物自身的变化,其所揭示的并非自在差异的真实运动,而是虚假、抽象的概念运动。尽管黑格尔以思辨思维超越了知性思维,但这仅仅是从有限表象进入了无限表象,并没有超出表象这一平面本身而进入差异化存在的深度之中,也没有将自在的差异从表象的同一性中解放出来。因此问题不在于从有限表象推进到无限表象,而是摒弃有限的表象,使自在的差异出场。
因此,德勒兹指出,哲学需要新的表达方式,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式有限的实体论的表象或康德式有限的认识论的表象,还是黑格尔式绝对的无限表象,它们都错失了真实的、自在的差异及其运动。仅仅从有限表象推进到无限表象是不够的,因为用一种关于运动的表象代替另一种关于运动的表象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放弃表象机制,放弃静观中的运动,放弃中介,直接面对真实的运动。德勒兹将这种新的表达方式概括为理念的戏剧化,但这是一种未来的戏剧,它是直接遭遇自在差异的新的实践方式。在这里,自在的差异呈现为先于主体的经验之流,先于角色、面具和观众而充盈于舞台空间中。它不是再现(re-presentation)某一场景,也不是给角色带上一个又一个面具,否则它就又是表象的戏剧了;而由于表象始终试图以同一性管理差异,所以从表象的眼光看待世界时,这一舞台上的诸差异总是无法捕获的虚空,这一出戏剧总是无意义的,因而只能用一个又一个的概念作为面具和工具将其纳入可被理解的表象之中。但对德勒兹而言,我们本应当从康德那里学到的教训是,由于自在的差异是超越我们的表象能力的,因此它们只能在表象中被理解为虚空,表象只是自欺欺人地遮盖了它们,自在的差异总是从中逃逸。只有掀开表象这张巨大的幕布,特别是在黑格尔那里达到无限大的幕布,自在的差异才能如其所是地登台亮相。
二、自在的差异的逃逸
对德勒兹而言,西方哲学传统中经由黑格尔通过辩证法达成的最高程度的同一哲学和表象体系的问题就在于对差异的态度,即总是试图将差异纳入一个统一体之中,以这一体系的同一性外在地否定和干涉自在的差异本身的状态。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将差异、对立和矛盾都视为最终会在绝对精神中被否定、被扬弃和被调和的东西。德勒兹则认为,要真正使自在的差异现身,不仅要掀开表象对于自在的差异的遮蔽,而且还要进一步使自在的差异从同一性的外部否定和中心化管理之下逃逸出去,肯定差异自身的差异化力量,差异运动的现实并非黑格尔辩证法所呈现的向心圆圈运动,而是如尼采以永恒轮回所揭示的那般去中心化的逃逸运动。
差异的逃逸运动首先表明诸差异并非以定居分布的方式存在于一个预设的统一体之中,而是其以游牧分布的方式将自身组织为一个自在的“繁复体”(multiplicity)。在传统哲学的语境下,无论是亚里士多德通过属加种差所呈现的整体结构,还是康德通过知性范畴编织的认知体系,抑或黑格尔通过辩证法达到的绝对精神,它们对差异的处理总是遵循着归纳和分类的思路。在这其中,差异以一个预先给定的整体或统一体或同一之物为前提,一切差异、限制、对立和矛盾都聚集在这个整体之中,差异表现为对同一性的分割。但由于整体的同一性被预设在差异产生之前,差异相对于同一之物而言是派生的,就像在黑格尔那里差异、对立和矛盾被视为同一之物自身发展的必要环节一样。因此,无论差异如何对同一性进行分割和阻碍,其最终仍然能够被丝毫不差地拼装起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的辩证法所表现出来的只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现有经验在哲学上的分解和恢复”。(1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00页。自在的差异作为活生生的现实经验,在绝对精神自身的发展中被表象并分解为数量和程度不同的差异、限制、对立和矛盾,它们都是相对于绝对精神这一更高深的同一之物而言的,并最终通过辩证法的否定运动回归到绝对精神自身之中。
然而,在德勒兹看来,作为规定的限制和对立确实是在一个更为深邃的元素之中显现出来的,但这样一个元素并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一个“繁复体”。在繁复体中,自在的差异处于自由而未经驯服的麇集状态,诸差异呈现出如蚁群般密密麻麻的攒动感。“麋集”指移动中的一大群,这首先便表明它是一个动态的、各自为政的开放空间。就差异在空间中的分布而言,统一体与繁复体分别代表了德勒兹所区分的两种差异的分布状态:定居分布与游牧分布。在定居分布中,差异被设想为派生自对同一性的分割,一个事物越是接近或符合被视为基底的同一性,它就越是被分配到更高的等级;黑格尔之所以主张将差异推进至矛盾,是因为在其辩证法中,诸差异刚刚离开空洞直接的同一性,而距离自在自为的同一性又太远,但矛盾与同一性则仅有一步之遥。这同时也意味着定居分布中包含了一种中心—边缘的空间隐喻,从中心到边缘,等级依次降低,而远过边缘或“越界”则意味着本性的改变,被视为混乱的、恶的,事物的好坏由它离其中心的距离远近来衡量。与此相反,德勒兹指出,自在的差异有其自身的游牧分布方式,即一种事物在开放空间中进行遍布和填充的分派方式。在开放空间中,没有任何界限、归属,差异不需要服从于任何本质、同一之物,而是可以在开放空间中尽其所能,直至其强度极限;差异在其中不是被统一的要求聚集在一起,而是在展现自身强度的动态过程中,展现为一种麋集的繁复体,一种自在的多。因此事物必定会冲破统一体之定居分布的界限,冲破中心—边缘的空间结构,表现为一种“僭越”或“谵妄”。德勒兹进一步指出,这种冲破并不是中心—边缘框架下远近距离的突破,而是强度意义上的突破和跳跃,强度的极限也不同于在定居分布中作为法则的限制和对立,而是差异自身的差异化强力。此时限制和对立不再作为边界,不再作为有限的和否定性的,而是事物由内而外的强力扩张和自我展现、自我肯定的结果,界限因而不是既定的,而是生成的。在黑格尔统一体式的定居分布中,差异向绝对精神的回归被视为理性的、善的,但自在的差异恰恰在其中被裁剪和扭曲了,它要求从同一性强加其上的定居分布中逃逸出来。自在差异的麋集虽然从统一体的视角看来是混乱和恶的僭越,呈现为一种参差不齐的杂多,但就诸差异在其中都能够达到自身存在的强度极限而言,差异的繁复体恰恰能使诸差异在其中触碰到一种相等性。
差异的逃逸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同一性自上而下的外部干涉,就是要坚持自在的差异的自我判决。德勒兹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差异、限制、对立和矛盾处于以同一性为预设基底的语境下,它们往往被视为否定因素与通往同一性的阻碍,需要被同一性管理、克服和超越,被同一性否定。然而,从自在的差异的立场来看,差异才是那个根本的肯定的东西,一切限制、对立和规定只有在差异的深度空间中才得以显现。差异才是一切同一性在其中不断涌现和消逝的基底,而非派生的。同一性与差异的关系在自在的差异之逃逸运动中完全被颠倒过来。“差异有自己的判决性实验”,(11)吉尔·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安靖、张子岳译,第95页。也就是说,差异本身有能力去判定如何行动,而无需听从它以外的和强加给它的同一性的指引,并且它会证明这样的同一性仅仅是一种虚假的和解。德勒兹用三个维度间的关系对比了同一性之外部干涉下的限制与对立同差异之自我判决下的差异空间。他指出,限制是一维的,它是一条只有长度和一个方向的线,这主要是说莱布尼茨关于造物之自然限制的观点。诸差异的碰撞、不和表现为它们自身的限制以及它们共同作为上帝造物的均等化。对立则表现了具有长度和宽度的二维平面,事物通过一分为二的方式被定义,事物的特质都被极化。在对立中,精细的差异被粗糙地对待,简单地归入到一分为二的阵营中。不仅如此,即便对立的两极在综合中能够被归入一个同一物中,这也是因为黑格尔辩证法在预设好的同一之物中区分出的对立斗争本就是虚假的。对立思维始终运行在二维平面,所谓的正反综合不过是虚构了一个折叠动作,也就同时虚构了一个三维空间。在自在差异的逃逸运动中,确实有一个三维的空间,但它不是被限制和对立分割的,而是事物的原初深度和内在的强度差异的空间。正因如此,德勒兹批评黑格尔的整个精神现象学制造了虚假的运动,并对差异、肯定和否定的关系进行了颠倒,其现象学预先设定了同一之物,将差异始终作为否定之物强行引向同一性,使差异失去自身的根据而以同一性之下的对立为前提,差异始终戴着镣铐跳舞。精神现象学对差异的表象本质上是代表差异说话,但作为特异之物的差异根本拒绝被绝对精神这一最高的同一之物代表,不愿做在同一之物自我生成过程中的牺牲品,它们始终自在地存在着。
自在的差异立场应当拒斥这样的代表与牺牲,因为这总是涉及谁来代表、依据什么标准来决定的问题,在诸差异间总要从外部找到一个“调解员”或“治安官”。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则充当着这样的角色,它将一切差异、对立和矛盾通过辩证法的操作和解于自身之中,存在及其否定本身被设定共在于同一之物中。干涉与调节从辩证法的开端就开始了,直接性被视为无规定和无内容的“无”,直接性存在虽然是肯定,但其内在始终包含内容上的虚空。归根结底,同尼采一样,德勒兹亦认为,无论是黑格尔还是整个传统西方哲学,其共性在于试图通过设定一个“优美灵魂”,来干涉现实生活中的差异、斗争和苦难,通过在优美灵魂中将它们进行否定、调节和超越,假装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在实际上,这种做法只是通过否定感性生活、否定现实世界,在虚幻的和谐完满中试图将这些不和谐的东西合理化。但在真正的差异哲学看来,这些差异、特异性不需要被理解、被合理化与被表象。换言之,自在的差异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干涉,它们在同一性看来的不可理解性、荒谬性与不合理性,恰恰是自在的差异对自身差异力量的判定和决断。
因此,差异的真实运动并不是黑格尔辩证法所呈现出的围绕绝对精神这一中心所做的向心圆圈运动,而应当是一种去中心化的逃逸运动,德勒兹将尼采的永恒回归视为这种运动的典范和对黑格尔式圆圈运动的有力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无限圆圈始终是围绕一个中心的向心运动,一次次的否定、剥除和蜕变都是向那个唯一中心的复归;而永恒轮回则是离心运动,它总是不断将那些试图管理差异的表象和秩序甩出去,它是对同一物的无限逃逸。黑格尔式的绝对体系仍诉诸一种互补性,即诉诸无限的矛盾运动,并且这一运动实际上受控于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这其中必然有同一性与差异、建立与颠覆、肯定与否定的辩证关系。特别是在黑格尔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阐述中,在世界精神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能够作为其当前阶段代表形式的统一体,如国家和民族复兴起来,又随着另一个阶段的兴起而覆灭,后继者总是作为对前任者的否定而出现。而在尼采的永恒轮回中,差异的力量也是在不断地进行着破坏,那么二者有什么区别呢?德勒兹指出,前者是政治家的破坏方式,而后者是诗人的破坏方式,二者分别代表两种对肯定与否定间关系的看法。
尼采的永恒轮回并不认为差异是需要被否定和调解的东西,差异是自身具有肯定性的存在。在永恒轮回中不断复现的正是这些差异,它们永远不会委身于某个统一体,而一旦有某种秩序或表象试图将它们收编或摆弄,差异必然会将之驱逐。换言之,尼采的永恒轮回之所以进行破坏和否定,是为了肯定差异、无序与混沌,他向否定差异的表象说“不”,是为了向差异说“是”。而黑格尔辩证法则通过向不同者、混乱与差异说“不”,是为了向相同、同一、超越、完满说“是”。也就是说,政治家式的否定,不过是用一种同一性取代了另一种同一性,其虽然给人们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烦恼的希望,但却是以否定现实生活的实际多样性为代价的。在黑格尔辩证法对肯定与否定间关系的构想中,否定及否定之物被视为运动的动力,肯定被视为否定的影子和伴随物,只是从存贮于同一物中的全部否定之物中抽取出的部分,是“无中生有”。因此,肯定相对于否定之物而言就显得是不完满的、偶然的和有限的。这体现出同一之物的虚假运动对于自在差异的无力,“哲学并没有真正的开端,或者更确切地说,真正的哲学开端——亦即差异——本身已然是重复……圆圈的形象表明哲学不仅没有能力真正地开始,也没有能力真实地重复”。(12)吉尔·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安靖、张子岳译,第227页。与此相反,在尼采指出的另一种构想中,肯定才是起作用的强力,永恒轮回的圆圈肯定了差异和距离。也就是说,差异、分裂等在前一种构想中需要被否定的东西,在后一种构想中恰恰是肯定之物。否定不再是源动力,而只是产生于两种肯定之间的结果,是如影随形的东西。两种肯定可以理解为要求永恒回归的权力意志对存在的双重肯定:第一重肯定是差异和生成,第二重作为对差异与生成的肯定是存在。在差异就是存在的意义上,双重肯定是同时发生的,首先差异、混沌、感性事物和多样性本身就是肯定之物,它们同时也是被肯定的东西,即存在就是这样的东西。正是因为尼采的永恒轮回肯定了自在的差异,揭示出自在差异的逃逸运动,所以德勒兹才借以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无限圆圈运动。后者通过将差异封闭于向心的复归,遮蔽了差异真实的逃逸运动,同时也遮蔽了差异的现实遭遇。
三、遭遇自在的差异
德勒兹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以往哲学史的解读之上的,对德勒兹而言,无论是使自在的差异无法出场的表象主义,还是遮蔽了自在的差异之逃逸的同一性哲学,归根结底源于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总是试图确立人类主体作为理性存在者的特殊地位和能动性,而不愿承认人类主体在理性能力上的有限性和被动性。理性的、普遍的和纯粹的世界被视为真实的原型,理性的普遍性被奉为圭臬;而感性的、特异的和杂多的世界则被视为虚假的拟像,感性的杂多与流变在理性的标准下被拒斥和贬低。但实际上,在自在的差异面前,理性主义诉诸表象和同一性想要将其纳入一种普遍和绝对的真理体系的尝试一次次宣告失败。而如果想要真正遭遇自在的差异,就必须对理性主义传统进行颠倒和瓦解。
德勒兹指出,在表象体系破产之后,现代哲学的任务就是重新向自在的差异敞开,这首先要求对柏拉图主义进行颠转。如果将颠转柏拉图主义仅放在柏拉图的语境中,那么它就意味着“否认原初之物对于复制品的优先地位,意味着拒斥原型相对于影像的优先地位,意味着赞美拟像与映像的主宰”。(13)吉尔·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安靖、张子岳译,第123-124页。正如怀特海所指出的那样,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无非是对柏拉图主义的注解,黑格尔也并不例外,他甚至认为:“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1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3页。黑格尔将柏拉图主义所代表的古希腊精神视为调和与同一性的典范,特别是在经历了康德进行的二元划分之后,黑格尔更加感受到柏拉图主义这一古希腊的精神家园对他的呼唤。他继承了柏拉图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思想,并从中提出自己的辩证法理论的雏形,其表现为精神从低级到高级的自我提升运动,各个环节不断克服自身的有限性与特殊性,最终在无限普遍的绝对精神中得到升华。用德勒兹的术语来说,在黑格尔辩证法中,自在的差异被视为未经思维的简单同一,随着精神的发展,自在的差异发展到能被表象把握的自为的差异、对立和矛盾,自在的简单同一被否定掉;随后,这种自为的差异再次被绝对精神这一最高的同一性否定,此时同一性就是自在自为的。绝对精神在双重否定中达到了绝对肯定,对事物的认识达到了自在自为的绝对知识。
在德勒兹看来,黑格尔辩证法对于自在差异的处理充斥着柏拉图主义中原型与拟像的隐喻,其自认为通过不断扬弃差异达到的纯粹肯定的绝对知识仅仅是“肯定的幽灵”,其仅仅与表象的差异打交道,而没有真正遭遇自在的差异。因此,其不仅是同一之物通过否定运动而进行的无限回归,同时也是有限的、特殊的事物朝向无限的、普遍的事物的永恒超越。否定是运动的动力和源泉,肯定是否定的结果、副现象、影子或拟像,并且即便在肯定之中,否定之物也早早被存贮其中。在这种构想中,作为现实的、感性的、直接性的东西的肯定,只是最粗糙的、没有自身根据的、不完善的东西,它之所以不完善,是因为它始终被置于与一个完美的同一物的参照中,它只是否定之物在其中潜在、暂存的替代物或躯壳,或对否定之物的模仿、分有。否定之物之于柏拉图是理念,之于基督教是上帝,之于黑格尔是绝对精神,其他一切事物在它面前都是要被否定掉的。在它能够否定其他一切事物的意义上,它具有最高权力,是否定的东西和进行否定的东西。德勒兹指出,从古希腊到现代的哲学,逐渐发展出一套审判(Judgement)体系,而这正是柏拉图主义带给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份“有毒的礼物”,即把一种审判程序引入哲学。理念固然能够制造差异,但这一点更重要的前提在于,理念能够进行审判,它同时也是审判的标准。一切追求者、声称者在理念的审判面前都被强加了一种自证的义务,但是他们越是试图得到肯定的证明,就越是得到否定的反馈。在黑格尔辩证法中,我们根本无法遭遇自在的差异,因为它在开端处就被一种简单的同一性所否定,当我们再次遭遇差异时,差异已经是表象的差异了,它要继续被作为原型的绝对同一性所否定。而在颠转柏拉图主义的语境下,唯一真实的原型只能是自在的差异,表象的差异以及将其调和的同一性都是自在的差异在主体心灵中留下的拟像和影子。这就意味着,原本作为拟像和影子的表象和同一性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在以往的哲学传统中被提升至原型的高度,都是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在起作用。德勒兹指出,“神圣实体的独特性与同一性是为一且同一的自我的唯一保障,而且只要人们还保留着自我,上帝就同样被保留着”。(15)吉尔·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安靖、张子岳译,第108页。这样一来,只是翻转原型和拟像的关系,并不足以颠转柏拉图主义与黑格尔哲学,关键还在于消解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主体。
对德勒兹而言,自在的差异起初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遭遇的对象,因此遭遇自在的差异首先意味着消解以往作为能动认识者的理性主体,指出在能动地认识自在的差异之前,我们首先是作为被动综合的主体存在的。这种被动综合虽然是在主体的心灵中发生,但其本身并非心灵的创造,而只是有重量的内在的质的差异在心灵中造成的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灵的反应。换言之,德勒兹在此并没有预设一个能够进行综合的先验主体,而只有一个因在想象中缩合了重复而产生差异的心灵,自我在此就是这种被动综合。德勒兹并不否认记忆与知觉对于感觉印象的主动再现过程,但他强调主动的主体并不是认识的开端,在主体的能动综合起作用之前,必须先有无意识的被动综合为其搭建起一个平面,主体及其理性都是这一被动综合的结果。
柏拉图主义的一个基本预设就是作为被思维者的客体与作为思维者的主体之间的同一,虽然在这一时期认识外部存在的客观真理被当作思维的目的,但实际上这是不自觉地将主体自我的思维当作最高的存在。到了笛卡尔那里,主体则发展为不可怀疑的我思的自我,他将自我视为一个本性为思考的实体。笛卡尔的“哥白尼式革命”在于,将自我视为第一性的,而一切可感物都是在我思自我的基础上才得以可能。对此,黑格尔称赞笛卡尔“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多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1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9页。在论及自身的哲学体系时,黑格尔指出,“哲学就表明自己是一个返回自身的圆圈,这圆圈决没有其他科学意义上的开端,因而哲学的开端仅仅与决意作哲学思维的主体有关”。(17)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版,第48-49页。也就是说,同其之前的哲学家一样,黑格尔给出的关于思想的图像同样预设了一个进行能动认识的主体作为条件。不仅如此,黑格尔还要解决康德的主客二元划分所造成的主体与实体间的分裂,他要在自觉的意义上将实体重新恢复至主体的高度,“不仅把真相理解和表述为一个实体,而且同样也理解和表述为一个主体”。(18)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正如德勒兹指出笛卡尔的我思之所以能够作为开端是由于我思已然隐含地预设了一个经验自我一样,他也指出,黑格尔能够从一个主体假定的特殊对象开始是由于“将其所有的前提都指向了经验的、感性的、具体的存在。这种态度旨在拒斥种种客观前提,但却以允许同样多的主观前提为条件(况且,它们可能只是不同形式下的同一种东西),它依然乞灵于海德格尔所持有的一种先于存在论的存在领会”。(19)吉尔·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安靖、张子岳译,第227、134、244-245页。
然而,对德勒兹而言,纵观哲学史,正是黑格尔着力进行调和的康德式分裂指出了一种消解我思的自我的可能性,因为康德承认自我在直观层面上只是一种被动的接受性。康德指出:“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心灵在以某种方式受到刺激时接受表象的这种感受性称为感性的话,那么与此相反,自己产生表象的能力,或者知识的自发性,就是知性。我们的本性导致直观永远只能是感性的,也就是说,只包含我们被对象刺激的方式。”(20)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典藏本)》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这样一来,在能动的我思自我自发地进行表象之前,自我在遭遇自在的差异时,是被动接受性的,德勒兹将这一过程称为被动综合。被动综合的这种结构并不是向上的主动建构,而是在感性和知觉之下更为基础的结构。我们之所以有感性和知觉,是源于有一种“我们所是的原初感性。我们是由被缩合的水、土、光、气组成的——不只是在认知它们或表象它们之前,而且还是在感觉到它们之前”。(21)吉尔·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安靖、张子岳译,第227、134、244-245页。原初感性意味着在能够说宏观层面上的“我”以及我的感性和知觉之前,就已经有无数微观的、差异的“我”了,这些微观的差异元素在差异的条件下进行缩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差异瞬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正的感性物恰恰不是认识、反思、表象这些更高级的能力的对象,而是被动主体遭遇的对象,“被遭遇的对象使感性真正在感官中诞生了”,它不是感性存在者,而是感性物之存在。它“使灵魂动荡翻腾……也就是说,它要强迫灵魂提出一个问题”。(22)吉尔·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安靖、张子岳译,第227、134、244-245页。换言之,真正的感性物就是自在的差异。
在颠倒了拟像与原型的关系、被动综合与主动综合的关系之后,一种面对自在的差异的态度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即从拒斥感性流变、追求理性统一到直接遭遇自在的差异,肯定其差异化力量对于一切同一性的破除。以往的哲学家拒斥变化和追求永恒,他们总是从非历史的和永恒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对一切变化因素的层层剔除和剥离,事物的本质才能得到把握和呈现。只有一个事物经过不断蒸发,被制作成“概念木乃伊”,它才是可靠的和真实的。哲学家们总是带着虔敬的心情和意图来从事这项工作,他们认为自己是在赋予事物以永恒性和确定性,使其免受流变的侵袭。这样一种探寻目的显然在现实研究中无法直接得到满足,因为变化随处可见,但这并没能阻止哲学家们继续相信“存在者不变化,变化者不存在”(23)尼采:《偶像的黄昏》,李超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9、20页。这一信条,即便肉眼可见的现实与他们的信念相悖,他们也相信永恒不变的存在者。然而,当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获得存在者时,他们没有质疑上述信条,没有质疑他们寻找变动不居的永恒存在者这一行为本身,而是转而探究其为何被隐瞒,探究自己如何被欺骗。最终,这些哲学家们找到感性和感官作为“始作俑者”,他们认为感官和感性对他们隐瞒了真实世界,因而它们是极不道德的,它们所呈现出的一切流变都是为了欺骗和蒙蔽人们以使其无法抵达真实世界。由此,道德就应当力图摆脱感性和感官,质疑并剔除直接呈现于感官面前的东西,它们不是别的,只是谎言。生成观念和历史感也出于同样的理由遭到唾弃,既然存在者不变化,是永恒的,那么它的生成和历史也就无从谈起。然而,在德勒兹眼中,死亡、消退、生成和增长等变化恰恰是事物的生命所在,哲学家们的上述工作是对活生生的事物的扼杀。正如最先将自身任务确定为颠转柏拉图主义的尼采所指出的那样,感官“根本就不撒谎”,(24)尼采:《偶像的黄昏》,李超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9、20页。它们始终如其所是地呈现着,正是人们借助感官证词所进行的加工和伪造才产生了谎言。感官本就呈现着生成、衰退等各种变化,呈现出多样性,只有当人们想从中制造出不变的永恒性时,才会拒斥感官证词。谎言和伪造的真正根源是“理性”,它始终追求永恒的、统一的、绝对的和普遍的东西,因而它一方面拒斥感官的变化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则不管不顾地进行虚构。在以往的哲学家们看来,剔除了感性感官变化的世界,一个纯粹概念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而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感官世界则是虚假的。相反,尼采则指出,只有唯一的一个世界,那就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运动着的世界,即所谓的“虚假的”世界;而哲学家们口中那个“真实的世界”,不过是理性用谎言虚构出来的。这种颠倒来自于他们对生成和历史感的痛恨,换句话说,这也来自他们对统一性、普遍性和永恒性的追求,以及对感性、差异、流变的拒斥。在德勒兹看来,遭遇自在的差异时唯一真实的情况是,被动主体在与经验之流的遭遇中,“直接在感性物中领会那只能被感觉的东西,领会那感性物之存在本身——差异、潜势者之差异、作为质的杂多之理由的强度差异”。(25)吉尔·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安靖、张子岳译,第106页。只有这样,感性物之科学才达到其高级形式,感性论才成为向自在差异真正敞开的肯定无疑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