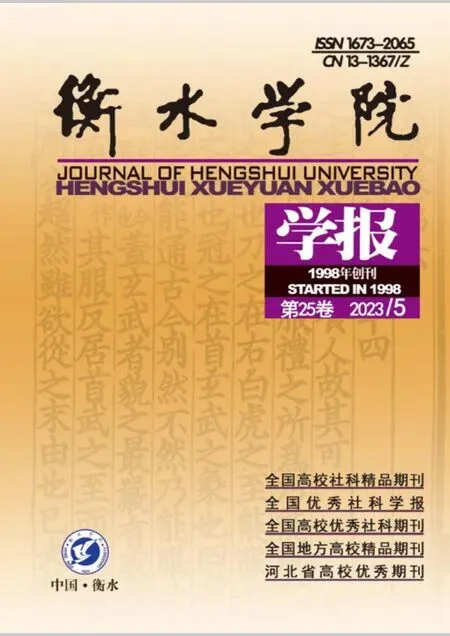董仲舒的《孝经》学
2024-01-02刘增光
刘 增 光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董仲舒为西汉最有影响之大儒,班固《汉书·五行志》评价其“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而《汉书》本传篇末载推尊《左传》的刘歆评价董仲舒“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至东汉王充虽批判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但《论衡·超奇》仍谓“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近人李源澄谓:“周末以来,政治学术皆有由分而合之趋势,政治上产生汉武帝,学术上产生董仲舒。董仲舒之学术,实与武帝之政统相应,武帝完成大一统之政统,仲舒„„造成‘天不变,道亦不变’之学统,在思想上影响之大,与武帝之在政治上相等。”[1]就董仲舒建立西汉之学统而言,足见其思想在两汉之世的深刻影响。据此就《孝经》学之发展而言,董仲舒并未注解过《孝经》,但是《春秋繁露》中却可以看到董仲舒屡屡援引《孝经》。不夸张地说,在《春秋》之外,《孝经》俨然成为董仲舒思想理论建构借以展开的重要文本。以至于清人王仁俊在《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中将董仲舒有关《孝经》之说辑为《孝经董氏义》,发明董仲舒之《孝经》学。清末章太炎、曹元弼,以及民国时署名“世界不孝子”的《孝经救世》等均注意到了董仲舒《孝经》论说的精彩。更值得称道的是,清初康熙时人张叙撰述《孝经精义》,认为《孝经》“是故孔子以是传之曾子,曾子以是传之子思,子思以是传之孟子,孟子后,愚不知其谁传焉。董子述之天人策,盖得其传与”[2]。一改宋明理学家对董仲舒的评价,从道统论的层面肯定了董仲舒思想的传道地位。总体说来,董仲舒《孝经》论述的影响极为深广,在很多方面奠立了两汉《孝经》论述的基本主题和格调,欲究明汉代以降《孝经》学之发展,必然不能置董仲舒而不言。
一、尧舜之道与家天下的调和
董仲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3]219-221(以下只注篇名)一文堪称汉代儒者讨论政治最经典的文字,但以往对这段话的分析并未十分透彻,为了论述分析得方便,以下将此文分列三段:
尧舜何缘而得擅移天下哉?《孝经》之语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与父同礼也。今父有以重予子,子不敢擅予他人,人心皆然;则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犹子安敢擅以所重受于天者予他人也,天有不予尧舜渐夺之故,明为子道,则尧舜之不私传天下而擅移位也,无所疑也。
儒者以汤武为至圣大贤也,以为全道究义尽美者,故列之尧舜,谓之圣王,如法则之;今足下以汤武为不义,然则足下之所谓义者,何世之王也?曰:弗知。弗知者,以天下王为无义者耶?其有义者而足下不知耶?则答之以神农。应之曰:神农之为天子,与天地俱起乎?将有所伐乎?神农有所伐,可;汤武有所伐,独不可,何也?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诗云:‚殷士肤敏,祼将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无常予,无常夺也。故封泰山之上,禅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尧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夺也,今唯以汤武之伐桀纣为不义,则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说,将以七十二王为皆不义也。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宁能至汤武而然耶!
夫非汤武之伐桀纣者,亦将非秦之伐周,汉之伐秦,非徒不知天理,又不明人礼,礼,子为父隐恶,今使伐人者,而信不义,当为国讳之,岂宜如诽谤者,此所谓一言而再过者也。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纣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谓汤武弒?
这篇文字仍是在谈论汤武革命的问题。从汉初黄生与辕固生在汉景帝面前谈论汤武是革命还是放伐开始,对这一论题的关心可谓贯彻始终,至少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皆是如此。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在记载二人争论的最后不忘加上一句:“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①司马迁《史记·儒林传》第3122 页。黄开国指出,在汉景帝之后,儒者们并非完全不谈受命放杀,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以及齐诗的‚五际‛说。见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139-140 页。正说明了此问题之重要,应该说,这一问题直到董仲舒才予以解决。董仲舒的这一论述显系受到孟子影响。《孟子·万章上》载: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董仲舒以尧舜并未擅移天下作为概括,可谓十分精当。这就意味着,尧舜政权的转移并非个体之间的私相授受,而是“天人之际”的天与民共同选择的结果,是公天下,换言之,公天下并不是表面上的禅让传贤而已,更是天意的体现,后者才是根本,前者仅是表象。同样,在董仲舒看来,夏商周三代之政权转移虽然并非以禅让的形式,而是以讨伐的形式,汉之代秦亦如此。但是,他认为这仅仅是表面的不同,因为“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天理即是“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也即是说,不论是尧舜禅让还是汤武征诛,都是天理,是正义,并非篡逆②黄开国分析董仲舒的三统说,认为他‚刻意回避了历史的兴替是否需要革命的问题‛。见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第178 页。。这也意味着,夏、商、周每一代也是公天下,并非家天下。且董仲舒的论述有着其超越前儒之处,“神农之为天子,与天地俱起乎?将有所伐乎?”这句话意味着任何一个统治天下的天子都存在着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因为从根源上来说,作为“百神之大君”的“天”才是真正的主宰者,除却天之外,任何人包括天子在内都不可能是与天地俱生,故而也就不可能拥有根源或根本的合法性,此合法性也可称为形而上的合法性,类似西方哲人所言“自然正义”。
在此意义上,禅让或征诛便都是第二层级的问题,政权以禅让还是征诛形式转移均不是最本源的问题。“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禅让或征诛,是天之予夺的方式,正因为“天之无常予,无常夺”,所以禅让或征诛就有了根源上的必然性或曰合法性,符合自然正义。进而言之,神农亦有伐,七十二王亦有伐,此是由历史经验而来的合法性,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征诛的合法性,汤武放伐并非偶然发生的单个事件,此可称为“历史正义”。
而且,退一步讲,即使不是天理,那些非议汤武伐桀纣,非议秦之伐周、汉之伐秦的人,也是“不明人礼”,因为按照礼仪,子当为父隐恶,故即使汤武有伐人之恶,确实是不义之举,为臣子者亦当为国讳之,这是孔子之教与《春秋》之义,而不应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和非议。若如此,那就是不明天理亦不守人礼。此是就现实政治与礼制而言,故可称为“现实正义”。
可见,董仲舒的讨论逻辑十分严密,同时在天理自然、历史经验和现实政制中的君臣之礼三个方面,反驳了对于汉代秦而兴政治合法性的质疑,认为汉朝亦是承受天之命。反观孟子的论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可以说仅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天理自然,二是百姓之公意。这样说来,董仲舒的论述中看似并不包含百姓之公意的成分,其实不然,因为董仲舒也对《尚书》所言“天生民,立之君,立之师”表示认可,故他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但是,在董仲舒这里,天志其实已经代表了民意。同样,也可以说,“民意”被“天志”遮盖了。尤其是当董仲舒说“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时,就更是弱化了“民意”的权威性。在这一点上,必须指出的是,孟子“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论述中对民意的强调在董仲舒这里已然隐藏了,民和君有了等级之分。这当然会让我们想到董仲舒性三品的人性论以及他以“民”为“瞑”的说法[3]286。这都无疑从人性论上在百姓与“(圣)王”之间划出了等级。董仲舒在《符瑞》中强调孔子作《春秋》,“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其尊王思想是非常明确的,这就与孟子的汤武革命说不同,故有学者言:“革命说主张人人皆有推翻暴君的政治权利,改制说则承认君主一人的特权,将社会变革的政治权利交给在位的君主,„„这就取消了卑者、不在位者改变现实的权利,这是一种明显为君主集权作论证的理论,也是董仲舒改制说的要义所在,它为君主专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最有价值的经学理论。”[4]
回到正题,董仲舒之论代表了汉儒对于尧舜之道与汉道的调和。这一调和,也可以说是对“汉家尧后”的证明。就经典文献而言,董仲舒的这一证明是以《春秋》和《孝经》为主要根据。依《春秋》,王为“天王”,董仲舒以“天子”为顺承天意或天志、天心的天之子。故他引《孝经》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与父同礼也。今父有以重予子,子不敢擅予他人,人心皆然;则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3]219《深察名号》篇亦谓:“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为父,事天以孝道也。”[3]286这其实意味着,尧舜禅让、汤武征诛、汉代秦兴,都是“天与子”的表现。因为王者都是天之子,故所谓的传贤与传子都是“天与子”,也就皆为公天下,而非私天下或家天下。公羊学的“通三统说”则是进一步从理论上为传子非家天下做了侧翼论证。正如《白虎通》所言:“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后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统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谨敬谨让之至也。”[5]366
孟子说:“使其主祭,而百神享之。”此为本《尚书·尧典》的记载引申之。董仲舒“事天与父同礼”之说,当是按照《孝经·圣治章》“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引申之。在此意义上,董仲舒所说“孝”就不仅仅是事亲之孝,而更是事天之孝。若为事亲之孝则会落在“家”“家天下”的格局上,而当孝被提升至“事天”的层面上,那么自然就成了公天下、顺天命的格局。董仲舒赋予原本更具道德色彩的《孝经》以鲜明的政治化内容。
在论述政权转移合法性之外,董仲舒还对政权初建后是否改制做了解释,而其解释也离不开“孝”与“天志”。在董仲舒的论述中,公羊家所言“改正朔,易服色”,皆是顺应“天志”。董仲舒在《楚庄王第一》①《汉书·董仲舒传》中也记载董仲舒对策:‚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更何为哉!‛中说: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己,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徒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
正如他认为禅让与征诛皆合于天理天志一样,新王必改制亦是顺承天志的体现。故曰:“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②此处‚顺天志‛之说,近人李源澄谓董仲舒取墨家以为说。然而此亦显非纯然墨家之说,孔子已言‚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中庸》)。李源澄之说见氏著《西汉思想之发展》,载《李源澄著作集》第2 册(林庆彰、蒋秋华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 年)第470 页。但是并无易道之实,归根言之,人是无法改易天道的。在此,董仲舒对《论语》中孔子称赞尧舜的“无为而治”给予了自己的解释,“无为而治”的含义是指尧、舜等圣王皆尊奉天道而治天下,法天而行。董仲舒在《对策》中也注意到孔子对舜韶乐和武王武乐的不同评价,他认为这是“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汉书·董仲舒传》)。尧舜之垂拱无为和文武之日昃不暇食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均是遵循天道。
二、“为人者天”
《春秋繁露》中的《为人者天》[3]318-320一篇共五段话,但每段话末尾皆引《孝经》之文以作结,故此篇堪称解释《孝经》的传文,显得非常特别,也集中表达了董仲舒的孝治思想。先录其文如下,稍加按语,以便做进一步申释: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号也。为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时,而必忠其受也,则尧舜之治无以加,是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按:此为《孝经·卿大夫章》文)此之谓也。③李源澄认为:‚西汉儒者,贾谊、董仲舒、司马迁之徒,往往称引六艺及孔子撰述,皆不及《孝经》。故知《孝经》作于孔子之说,不可信据。‛见氏著《孝经出于阴阳家说》,载《李源澄著作集》第2 册第889 页。清末以来疑古之风流行,论者率多认为《孝经》为汉人伪作,李氏似亦受此影响。然观本节之论,即可知此说多存疑窦。董仲舒称引《孝经》之语,言‚故曰‛,显然即是将其放在经典权威的意义上。另外,贾谊《新书·大政》言:‚事君之道,不过于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长之道,不过于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长;„„慈民之道,不过于爱其子,故不肖者之爱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过于居家,故不肖者之居家也,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于父,则行之于君也;行之于兄,则行之于长矣;„„行之于子,则行之于民矣;行之于家,则行之于官矣。‛此段文字显系本于《孝经》‚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新书》所佚之《问孝》一篇很可能与《孝经》关系更为密切。
传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④清人有以《孝经》‚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诗句属下章《诸侯章》连读者,如张叙《孝经精义》和汪师韩《孝经约义》均如此认为,观董仲舒之说及东汉郑玄之说可知,清人的这一移改《孝经》的作法是很欠妥当的。(按:《孝经·天子章》末所引《诗》文)此之谓也。
传曰:政有三端:父子不亲,则致其爱慈;大臣不和,则敬顺其礼;百姓不安,则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按:《孝经·三才章》文)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义也;(按:《孝经·圣治章》文)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按:《孝经·感应章》文)此威势之不足独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传曰: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故君民者,贵孝弟而好礼义,重仁廉而轻财利,躬亲职此于上而万民听,生善于下矣。故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按:《孝经·三才章》文)此之谓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说目也,声音应对者,所以说耳也,好恶去就者,所以说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则目说矣;言理应对逊,则耳说矣;好仁厚而恶浅薄,就善人而远僻鄙,则心说矣。故曰:‚行思可乐,容止可观。‛(按:《孝经·圣治章》文)此之谓也。
第一段话陈说天为人之祖的道理,申发出人类天、天副人的天人相符思想,这正是上节所论事天与事父同礼的理论基础。苏舆认为北宋张载《西铭》“乾父坤母”之说即是本于此[3]318。其实《礼记·祭义》中即有“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6]1335之说。正因为人之血气、性情、好恶、德行皆是受命于天,故人之行为即当遵循天道。人知一己之身出于天,则为人君之道即“莫明省身之天”。其引《孝经》之语意义在此,“身之天”一词尤其能发明《孝经》“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精义。但需要指出的是,“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所指本是“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并非直接指涉天道,因此董仲舒的解释就相当于指出,先王之法言和德行本即是遵循了天道。另外,这段文字其实也是对《孝经·圣治章》“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解释,因为依董仲舒之意,身并不仅仅是属于自己的,也是属于作为人之祖的天,所谓“身之天,如天出之也”,也即是说,人之身出于天,为人者天。而这也正与《汉书·董仲舒传》中所载董仲舒言相符:“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段话的语式结构与《为人者天》如出一辙。另外,这段话也涉及董仲舒对“忠”的理解,为人主者“必忠其所受”,也就意味着君主应忠于天。
此下之第二、第三和第四段话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即是君主为政,要注重教化、德化,而不可依赖刑法威势,正如天道既有寒暑,又有春秋一样。他将致其爱慈、敬顺其礼、力其孝弟视为政治的三个主要内容,而不提刑罚。因而《孝经·五刑章》并不为其所取。可以看到第三、第四两段话的内容基本就是对应于《孝经·三才章》所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于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
最后一段话所言者为君子之言行举止,但君子实即为君者,《孝经》原文谓:“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虽得之,君子不贵也。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此处之“君子”显系君主。可以看到,这段话所说似乎正是对第一段话“为人主者,道莫明省身之天”的解释。
总而言之,《为人者天》一篇表现的是董仲舒的德政思想,其中包含了对于君主修身以治人的要求,体现的是德主刑辅的思想。具体来说,董仲舒尤其强调君主要“爱人”、要博爱,对儒家的仁政思想做了新的发展。《五行相胜》中即有“仁者爱人,义者尊老”[3]367的说法。《为人者天》援引《孝经》“先之以博爱”的说法,正与仁者爱人之说相应。那么孔子所作《春秋》的主旨又是什么呢?董仲舒的回答也是“爱人”。《竹林》中说:“《春秋》爱人。”[3]49正如《为人者天》主张君主不可依威势,《竹林》中亦言“《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3]48。又:《必仁且智》:“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3]257“何谓仁?仁者憯怛爱人。”[3]258《仁义法》[3]249具体解释《春秋》爱人之旨,这意味着《春秋》是孔子仁学思想灌注的作品。孔子曰仁,孟子扩之以仁义,故董仲舒之说仁义,正是对于孔孟的发展。他说:“《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于人,义之于我者,不可不察也,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处理的也正是孔子所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问题。“《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这就意味着,只有爱人才是真正的爱,仅仅爱己不是爱。王者正是要爱天下人,仁及四夷。“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独身者,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无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独身之爱是自寻危亡之爱。爱及四夷的王者就是圣人,他称这种爱为“博爱”,故他说:“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3]304可以推测,董仲舒以“爱人”为《春秋》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孝经》的影响,同时也正是对《春秋》与《孝经》相表里说的一种发明。
在汉儒对于秦亡的反思中,仁义不施成了非常普遍的结论。秦朝之以严刑峻法暴政治国遭到了汉儒的批判,董仲舒也对刑法之治做了反思。既然不能以法家所言法、术、势维持君主的权威,那么应当如何维持呢?答案是仁义。这正表现出,汉儒在对秦政的反思中,对政治权威的塑造有了更加清晰的意识,直接转向儒家的仁政思想以吸取资源。威来源于仁爱,正因此,君主作为天子,就应当仁爱天下人。且“仁爱”也正是天志。《王道通三》中言:“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逆顺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有而博,唯人道为可以参天。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3]329王者爱利天下正是顺应天命天志。
在此意义上,董仲舒对儒家仁说或仁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他以生长化育释仁,这可以说是宋明儒以生言仁的先导。当然,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当是最早的源头。第二,他重申了仁爱之他人向度,因为不论是孔子所说“己欲仁而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还是孟子仁义内在的“四端”说以及“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的“固有”说,都强调了仁与己身的相关性,就仁德的践履而言,仅仅强调己身有仁心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仁是要见之于行的。汉儒强调“仁,从人从二”,正是看到了仁是在社会关系中体现出来的。董仲舒吸收了孔孟的这一维度,如《必仁且智》中说:“何谓仁?仁者,憯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3]257其中既强调了仁者之心志,也强调了仁者之行事,正是人我兼顾。第三,董仲舒以仁为天志,通过人副天数来论证人性中的善恶、仁贪,这就为儒家的仁爱思想确立了形而上的根据。
有学者谓董仲舒的仁爱思想“扬弃爱亲中心主义,把仁人之爱向更多的人群延伸”[7]。这一论述有其道理,但并非全然合理,正如上文所言,董仲舒以博爱解释仁是受《孝经》影响,《孝经·天子章》言:“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三才章》言:“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所以要“先之以博爱”。也就是说,爱亲和博爱是统一的。此为董仲舒仁说的重要内容。
嘉兴和绍兴各有1处景观得到康、乾二帝的偏爱,烟雨楼在避暑山庄中仿建,兰亭在紫禁城、清漪园、圆明园、西苑和避暑山庄等多处皇家园林中仿建。
三、“五行者,五行也”:孝的形上化与移孝作忠
除却《为人者天》外,《春秋繁露》中的《五行对》一篇也可以视作《孝经》之传。这篇文字显示出,董仲舒对儒家五常观念的论述是以五行学说为基础。民国大儒宋育仁曾言:“董子《繁露》发明‘地之义’特深微,心知其意,而汉初注家未起,惜其未诠注本经。”[8]指出董仲舒所论重在《孝经·三才章》的“地之义”,其《五行对》[3]315文曰:
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对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此之谓也。‛王曰:‚善哉!天经既得闻之矣,愿闻地之义。‛对曰:‚地出云为雨,起气为风,风雨者,地之所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从天气者,故曰天风天雨也,莫曰地风地雨也;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非至有义,其庸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五声莫贵于宫,五味莫美于甘,五色莫盛于黄,此谓‘孝者,地之义也’。‛王曰:‚善哉!‛
这段话所包含的首要命题是:孝是天理、天行、天道、天经。天有五行,孝就是五行相生之理,正如,父生子、子养父一样。故天之五行就是人之五行,这就以五行相生的道理解释了《孝经》的“天之经”。而关于“地之义”,他的解释则是下事上、地事天,但《孝经》本文中天经和地义是并列的,并不包含董仲舒解释之意。之所以如此解释,正是为了将“下事上”的忠德包含进去。这相当于将“孝经”变成了“忠经”,其中包含了浓厚的尊君观念,尤其是考虑到这段文字是对河间献王的回答。严格说来,地不能等同于“土”,但在董仲舒这里,则着力强调地德就是土德,“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孝经》言:“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董仲舒之说本此。但他又自行添加了“忠”德。这样的说法在汉代并不鲜见,如刘向《说苑·臣术第二》中载:“子贡问孔子曰:‘赐为人下,而未知所以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为人下者,其犹土乎!种之则五谷生焉,掘之则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兽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为人下者,其犹土乎!’”为人下之道犹土,正是董仲舒忠臣之义取之土的意思。依此,《孝经》所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就变成了忠孝俱为天经地义。而且,不难体会到,在这一论证中,当董仲舒将“地”等同于“土”①《白虎通》卷四《五行》显然较董仲舒更进一步,认为‚地,土之别名也‛。见《白虎通疏证》第168 页。时,就已经降低了“地”相对于“天”的位置,而仅仅成为天之五行的一行②后来的儒者正是在这一点上发生纷繁复杂的争论。在祭祀五行之神和天地二者上冲突矛盾。。虽言天经地义,但是“天”更像是五行之德、忠孝之德的订立者,而地则是施行者。唯言“五行莫过于土”或土旺四季可以稍稍提高其位置。《五行之义》[3]321中亦有土为五行之主的论述: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火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为言也,犹五行欤?是故以得辞也。圣人知之,故多其爱而少严,厚养生而谨送终,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养,如火之乐木也;丧父,如水之克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谓有行人矣。五行之随,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数也。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若酸咸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气也,犹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职,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这段话完全将五行的相生关系视作父授子、子受父的相生关系。五行就指涉了孝子忠臣的五种行为:养之、藏之、养以阳、丧以阴、竭其忠。《孝经》说:“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在董仲舒看来,之所以“多其爱而少严”,正是因为教与政皆是遵循了天道,是五行生克之道的体现。正如他在回答河间献王时从论孝转及论忠,此处亦是循着移孝作忠的思路,故后半段内容主要落在臣子之忠上说,但董仲舒不是泛泛说所有臣民之忠,而是特别落实在官之大者——“相”上说,土为天官,相为人官,正如土为五行之主一样,相为人官之大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结合两篇文字来看,“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是故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董仲舒虽然是在以五行解释《孝经》“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但他解释的重心实则是在“地之义”,也即五行中的“土”。地事天就是臣事君、子事父。由此,子尽孝于父即是臣竭忠于君。既然《孝经》说:“至哉,孝之大也。”“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同理,自然可以说“忠之义不可以加矣”“圣人之行莫贵于忠”,这样一来,先秦儒家设想中的圣王也就变成了“圣相”,圣人只能是做臣,汉儒已默认或默然接受德与位之相分离。五行之主是土,人行的中心则归本于忠孝,犹如《孝经》开首所言“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根据董仲舒的思路,他对《孝经》所言“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义也”做了连贯的理解,意即:父子之道既是天性,也是君臣之义。概括言之,忠、孝皆是天性,皆是天经地义、五行授受的天道。
显然,在五行体系中是不能以天地分别对应阳和阴来论说的。而在阴阳系统中,则可谓地卑于天,正如《易传》所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这一点,在《阳尊阴卑》篇中就表露无遗:
下事上、地事天的说法再次出现。但这段话已经不在五行系统中来论证君臣关系,而是在阴阳系统中。地为天之合,即是《孝经》:“君臣之义也。”君臣以义合。《五行之义》中也说:“土者,天之股肱也。”臣子为君主之股肱。但是,在董仲舒以五行论述天经地义的框架中,君臣之义和父子之义是相同的。他正是通过这种论证弥合父子之亲和君臣之义二者间的差别。这段话中说:“《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正对应于《五行对》中所说:“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土者,火之子。„„不与火分功名。”董仲舒的这一说法,并非毫无根据,在汉人的著述中也并不鲜见。纬书、东汉的官方制典《白虎通》均采纳其说,如《春秋·元命苞》言:“土无位而道在,故大一不兴化,人主不任部职。地出云起雨,以合从天下,勤劳出于地,功名归于天。”此说很可能系本于董子。《白虎通》亦是如此②见《白虎通疏证》第168 页。《白虎通》中又说:‚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犹五味以甘为主。‛此亦是本于董仲舒,见《白虎通疏证》第171 页。。就经典文本根据来说,董仲舒“名一归于天”、善归于君、恶归于臣的“大忠”思想有着《春秋》学的论据,而另外则很可能与《礼记》有关。《坊记》[6]1407言:
子云:‚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不争。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怨益亡。《诗》云:‘尔卜尔筮,履无咎言。’‛子云:‚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君陈》曰:‘尔有嘉谋喜猷,入告尔君于内,女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于乎是惟良显哉!’子云:‚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在《坊记》的语境中,孔子是在谈论礼仪中人我彼此关系的相互性,由此䌷绎出君臣关系、亲子关系,但他强调的是“为己者”之道德主动性,并未将君主的权威绝对化,认为君主不会错。故第三句话所引《大誓》即为武王自认有罪之语。也就是说,这三句话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别抽出断章取义来理解。且孔子极为强调的是这样做的教化意义。在此意义上说,君主自身能做到“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对于天下民众来说,无疑有着更广泛深刻的教化意义。对此,结合《礼记·祭义》之说即可明了,后者谓:“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善则称人,过则称己,教不伐以尊贤也。”[6]1343此即明确说明,天子亦应“尊天”,以向天表明自己并不敢自专己志,强调了君主本身的敬慎戒惧之心。且天子本人也是应“善则称人,过则称己”。这样做,有“尊贤”的教化意义。
而唯一可以做绝对化原则看待的是一种特殊情况,《礼记·曲礼》言:
大夫士去国逾竟,为坛位乡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彻缘、鞮屦、素幂,乘髦马,不蚤鬋,不祭食,不说人以无罪,妇人不当御,三月而复服。
这段话是就臣子去国而言,有其特殊语境。孔颖达《正义》即指出:“不说人以无罪者,善则称君,过则称己。今虽放逐,犹不得乡人自说道己无罪而君恶,故见放退也。”[6]116遗憾的是,虽然汉儒将《坊记》这段文字视为理解事君之道的典范文本,但却是将《坊记》中的第二句话单独抽出,以论证臣忠于君。董仲舒就说:“是臣子之不为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3]279他们忽视了其中的“善则称人,过则称己”正是儒家忠恕之道、反求诸己精神的一种体现。而在汉儒三纲的观念中,《坊记》这一说法的具体语境被抽离掉了,变成了父为子纲、君为臣纲,故董仲舒强调“阴兼于阳”“子之功兼于父”。
同样可以看到的是,西汉前期的《韩诗外传》卷三[9]与《说苑·君道》都记载了这样一段话: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由此险也。以其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诗曰:‚载色载笑,匪怒伊教。‛舜之谓也。问曰:‚然则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请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臣下之义也。假使禹为君,舜为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谓达乎为人臣之大体也。‛
《白虎通》卷四《五行》中亦以阴阳论君臣,说:
善称君、过称己何法?法阴阳共叙共生,阳名生,阴名煞。臣有功归于君何法?法归明于日也。[5]195
事实上,通过公羊学对于《春秋》微言大义的发挥,“为尊者讳”就成了孔子本人之意,并将其与《论语》中的相关文本结合起来。《白虎通·谏诤》篇中就说臣子谏诤君上当隐恶扬美:“所以为君隐恶何?君至尊,故设辅弼、置谏官,本不当有遗失。故《论语》曰:‘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此为君隐也。„„诸侯臣对天子,亦为隐乎?然。本诸侯之臣,今来者,为聘问天子无恙,非为告君之恶来也。故《孝经》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治,能相亲也。’”[5]239郑玄注《孝经·事君章》“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正是本《坊记》此文,说:“善则称君。„„过则称己。”[10]但郑玄强调:匡正君主之行为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依董仲舒之意,天子要顺承天,天子顺承天即是忠,即是孝。天是百神之大君,人君法天即是忠于君。但以天抑君这一维度仍然显得太弱。
《立元神》一篇体现出了董仲舒以孝为本、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而亦是本于对《孝经·三才章》“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的理解。其文曰:
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豪厘,驷不及追。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君人者,国之本也,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崇本则君化若神,不崇本则君无以兼人,无以兼人,虽峻刑重诛,而民不从,是所谓驱国而弃之者也,患庸甚焉!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则民如麋鹿,各从其欲,家自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虽有城郭,名曰虚邑。如此,其君河块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丧而自亡,是谓自然之罚,自然之罚至,裹袭石室,分障险阻,犹不能逃之也。
明主贤君,必于其信,是故肃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祢,举显孝悌,表异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谷,开辟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让,明以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则民如子弟,不敢自专,邦如父母,不待恩而爱,不须严而使,虽野居露宿,厚于宫室,如是者,其君安河而卧,莫之助而自强,莫之绥而自安,是谓自然之赏。自然之赏至,虽退让委国而去,百姓襁负其子,随而君之,君亦不得离也,故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是以圣贤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
此处以天、地、人三才为万物之本,但他所言作为本的“人”主要是指君而言,故谓“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君主正是制作礼乐者。但不论是天生、地养、人成,三者皆可贯之以“孝”。故他在论述“肃慎三本”时所述皆是本《孝经》言孝之义,奉天本是《孝经·圣治章》所言郊祀配天以祖配祭,奉地本则是脱胎于《孝经·庶人章》“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奉人本则涉及《孝经》多章内容,如《三才章》“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圣治章》“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广要道章》“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等等。而所言“自然之灾”“自然之赏”与《春秋》灾异说有关,也同样与《孝经·孝治章》所言“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相应。难怪有学者会认为此篇文字“即使视为《孝经传》也不过分”[11]。董仲舒实则是以公羊学的义理理解《孝经》,《春秋》开首言“元年春,王正月”,《玉英》解释说:“谓一元者,大始也。„„《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王道》篇亦言:“《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①此后,何休《公羊传解诂》解释‚王‛为‚人道之始‛。见《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0 页。。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制作礼乐的王是人道政教之始,所谓“国之元”,故“王正”、王之崇本即至关紧要,这就是对君主本身的严格要求。就《春秋》与《孝经》之关联而言,董仲舒将《春秋》的“一元”演绎为天地人“三本”,后世公羊学的《春秋》“五始”说正是在此三本说基础上的进一步演化。因此《立元神》不仅可视为《孝经》之传,也同样是《春秋》之传。《春秋》贵元,而《孝经》重本,董仲舒概之以“崇本”“谨本详始”,将《春秋》以“元”为始与《孝经》“夫孝,德之本”“其所因者本也”相结合,充分阐发了治国以孝为本的理念。其阐发也正与西汉政治有关,汉制使天下诵《孝经》,而正如清人苏舆所指出的,董仲舒言“举显孝悌,表异孝行”正是西汉表彰孝悌力田制度的体现[3]169。
而不得不指出的一点是,董仲舒的这一“君本”说,未免会使得孔孟以来的仁民、民本思想变得黯淡不彰。虽然他曾偶尔谈到人君“必忠其所受”——君主忠于天,但在其五行理论中又完全不提这一点。以他为代表的汉儒如此拔高“忠”德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正违背了《孝经》②故有学者以董仲舒为例,指出:‚儒家孝论在秦汉时代已经面目全非。‛见曾振宇《以天论孝:董仲舒孝论发微》(《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10 年第2 期)。。《孝经》本以“中于事君”为孝之一节。“终于立身”“立身行道”才是孝的最高境界。《孝经》固然有忠、孝并提之言,如《士章》:“以孝事君则忠。”《广扬名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但这正显示出:孝可以包含忠,孝才是最本源的,不宜将忠提升到孝的高度。《孝经》仅言:“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从未说忠是圣人之所贵。且根据《孝经·士章》“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之说,事君之忠仅仅是资取事父之敬。故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显然不能等同。“以孝事君则忠”的意思是说,人之入仕事君,是出于安亲孝亲之心,是为了安亲养亲,若是为了贪荣富贵,则非忠。只有在此意义上才能说孝是“德之本”。董仲舒、《白虎通》之说以五行理论贯通忠、孝,此点问题不大,但是将忠与孝等同,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等同,则隐含很大问题,流弊无穷;据阴阳理论而以尊卑解君臣,将臣事君之敬绝对化,这也忽视了父子关系不仅有敬还有爱,也忽视了君臣以义合、不合则去的道理。而从根本上说,《孝经》言治天下的明王本身必须率先行孝,“先之以博爱”“先之以敬让”等,故君臣关系、父子关系的爱敬都是相互的,并非仅要求下对上的爱敬。董仲舒对“忠”的提升,对阳尊阴卑、君善臣恶的强调,犹如天平偏向了一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为孝奠立了天人之际的宇宙论根据,但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孝的真义。而且在对忠的论述中强调君尊臣卑,实则无形中取消了革命、放伐的合理性。当然,换个角度看,则可说董仲舒之论包含了维护汉朝政治稳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