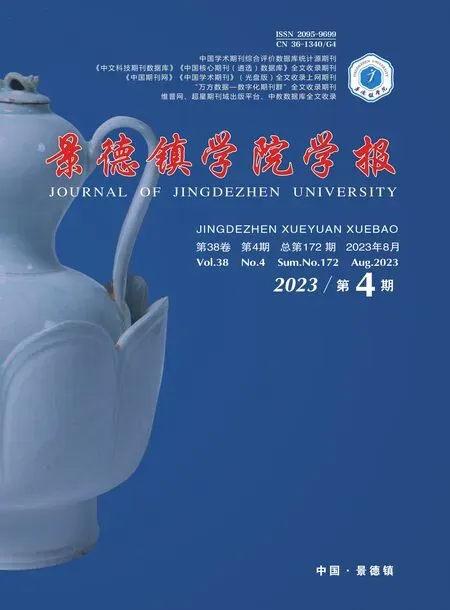唐代敦煌壁画中飞天形象的审美意象研究
2024-01-02谭彬清
谭彬清
(1.澳门科技大学 人文艺术学院, 澳门 999078;2.景德镇学院 陶瓷美术与设计艺术学院, 江西 景德镇 333400)
一、飞天形象概述
“飞天”一词在西晋竺法翻译的《普曜经》和隋代阇那崛多翻译的 《佛本行经》 中被记载为“天人”和“诸天众”,而最早的汉语“飞天”见于北魏杨炫之撰写的《洛阳伽蓝记》,其描述一幅金像辇的场景并提到了“飞天伎乐”的形象:“有金像辇,去地三尺,施宝盖,四面垂金铃七宝珠,飞天伎乐,望之云表”。 佛教造型艺术中的飞天形象源于古老印度神话, 在汉译佛经中专指天宫中的供养天人和礼佛、舞乐的天人,每当佛讲经说法时与佛最后涅槃时他们都凌空飞舞,奏乐散花。 其形象于公元1 世纪前后随佛教传入中国,经由朝代不断地发展演变,飞天形象逐渐成了中国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 表现了佛教信仰中的神秘和灵性, 最终在敦煌石窟壁画中趋于成熟。 敦煌石窟是中国著名的古代艺术宝库之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境内,其主要包括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五个庙石窟等一系列洞窟群, 其中莫高窟是敦煌石窟的主体,也是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被誉为“东方艺术宝库”。 常书鸿先生和李承仙先生都是中国著名的艺术史学家, 他们曾将敦煌誉为中国飞天图像荟萃之地, 强调了敦煌石窟在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据统计,仅莫高窟就有270 多个洞窟里绘有飞天, 数量多达4500 多身,加上其余石窟,飞天总数达6000 多身,因此敦煌石窟可谓飞天的故乡。[1]
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开窟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个朝代,时间跨度长达一千余年(4—14 世纪)。对于敦煌飞天的分期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学界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其中,较为主流的观点主要有两种。 一种观点认为,北朝的四个朝代为飞天的成长期,隋与初、盛唐为飞天的鼎盛时期,中唐开始则为衰落期。 这种观点主要是从敦煌石窟中的飞天形象数量和质量的变化来判断的,学界认为北朝时期的飞天形象数量较少, 质量较低; 隋唐时期飞天形象数量较多, 质量也较高;而到了中唐时期,飞天形象数量和质量都开始下降,标志着敦煌飞天进入了衰落期。 另一种观点则以敦煌飞天造型的演变、 时代特征以及技法特点将其划分为早、中、盛、晚四个时期。 早期北凉、北魏、西魏为模仿萌发期;中期的北周至隋为转型创意期, 此时飞天形象开始出现多样化的造型和装饰, 表现出一定的创意和艺术特点;唐、五代为鼎盛期,此时敦煌飞天的形象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一个高峰, 表现出丰富多彩、雕工精细等特点;宋、西夏、元为程式化衰落期, 此时敦煌飞天的形象逐渐失去了创意和艺术特点,呈现出程式化和重复的状态。 虽未有定论,但显然飞天艺术顶峰在于唐朝,无论外观造型的塑造,还是内在精神的传达,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唐代敦煌壁画飞天形象的审美意蕴
唐代是中国佛教艺术中的集大成时期,在20 位皇帝中,除武宗李炎(公元841 年—846 年)外,大多积极扶持佛教,并利用佛教与儒教、道教共同维持统治。 在佛教大兴的氛围下,僧侣、商贾等往来交流频繁,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中原文化对敦煌地区的影响与日俱增, 雄踞世界的大唐帝国亦是中国化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 敦煌莫高窟现存唐代洞窟236 个,占南区全部洞窟的将近一半。 敦煌的唐代分期,以吐蕃占领该地区来划分,分为前后两期。 唐前期,即公元7 世纪至8 世纪初, 是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 这一时期国家蒸蒸日上,敦煌地区的文化和艺术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石窟壁画绚烂华彩,风格清新爽朗,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唐后期,吐蕃占领敦煌,由于吐蕃人也笃信佛教,加之唐代文化根深蒂固,因此艺术风格一脉相承,变化不大。 晚唐至五代,敦煌艺术进入了成熟、定型,并逐渐趋于程式化的时期。[2]
(一)初唐时期的喜悦与活力
唐前期国力强盛,对西域地区的控制力度加强,敦煌地区也直接受到唐王朝的统治。 这种政治背景为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敦煌壁画呈现出一种姿态新奇, 充满律动的活力, 表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些壁画作品在构图上注重对称、平衡的原则,色彩鲜艳、明快,形象逼真、生动,呈现出一种充满生命力和活力的艺术形态。 唐代壁画一改北魏以来的印度画风, 转变为成熟的中国式佛教艺术, 唐时期敦煌壁画一般不再以故事画为唯一重点, 画家强调安静祥和的画面以传达宗教给人的喜悦和幸福,增加了以“净土”为描绘对象的绘画。 画家想象中的“净土”大概像皇帝住的宫殿, 原来的印度宗教画经由画家改变更像是唐代宫廷写实绘画, 展现了佛教庄严壮阔的盛景, 穿梭于其中的飞天形象不似印度西域风格的“V”字形态,体态轻盈优美,甚至逐渐呈现青春少女形象,充满生机与活力。 莫高窟第321 窟著名的双飞天样式,两组飞天俯冲向下利用腰身头部的转折体现强烈的张力与动感,脸部丰盈飘带细腻,长裙裹足,尽管脸部晕染已氧化变色,但仍能读出画家表现的喜悦之情,飞舞在菩提树间华贵且祥和, 完全能体现初唐时期充满活力的精神面貌。
(二)盛唐时期的自由与优美
盛唐时期由于国力极强,经济繁荣,文化艺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艺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时期的飞天更具活力与气势,这些飞天形象造型更加精细、雕工更加精湛,色彩更加鲜艳、明快,飞天形象的姿态也更加自由、优美,展现出一种轻盈、灵动、高雅的艺术风格。 几乎成为敦煌飞天代表的莫高窟第320 窟的双飞天形象出现了戏剧性的对比画面,四身飞天间不仅自身姿态优美,且相互间有了互动的关系, 似乎有了前后相互追逐嬉戏的动态之感,配上身边向上涌动的祥云,自然呈现向上漂浮的升腾感, 展示了盛唐时期全盛的精神面貌。
(三)晚唐时期的忧郁与清冷
唐后期外族入侵,这一时期敦煌壁画似乎不复前期热闹景象, 包括飞天在内全景幽静、恬淡。 吐蕃时期的飞天形象虽在艺术风格与唐前期呈继承关系, 是表现现实生活的风俗主题的绘画样式, 但就飞天人物形象来看体貌更加丰满雍容,佩戴头饰,气质更加富态,如莫高窟第158 窟西壁的持璎珞飞天,表情忧郁行动缓慢气氛凝重,衬托出《涅槃经变》中的哀悼之情,这与盛唐时期莫高窟第172 窟西壁的龛内飞天形成鲜明对比。 晚唐归义军时期飞天形式较为统一,不再具有唐初期活力富贵的大气氛围, 人物形态又变得消瘦,动态转折舒缓,如晚唐161 窟中的四身法会伎乐飞天, 各自手持乐器, 神态悠然,色彩不复前期明艳转为清冷,仿佛映衬出晚唐时期的萧瑟与国力甚微的景象。
三、 唐代敦煌壁画中飞天形象的表现特点
“意象”这个概念最早由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学家所提出, 意指艺术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意境或象征。 意象不仅是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也是艺术家情感和思想的表达,是艺术作品与自然界、社会、文化等多种元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艺术创造中,艺术家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和理解, 以及对人类生活和文化的感悟,创造出具有独特意境和象征的艺术作品,从而丰富了人类的文化遗产和审美体验。 题材就是客观之“物象”,在敦煌壁画中飞天形象本身就具有意象色彩, 敦煌开窟以来飞天就具有符号化特点。 按照佛经所示,飞天在佛教中具有三项主要职能,分别是礼拜供佛、散花施香和歌舞伎乐, 这些职能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艺术中不仅象征着佛教信仰的重要内容, 也反映出了当时唐代文化和社会的特点, 成为中国佛教艺术中的重要代表之一。 根据这三项职能,古代匠师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把一个本无情可言的题材表现得丰富多彩、婀娜多姿,并逐渐形成近乎完美的艺术表现形式。[3]
(一)动静结合的构图
在中国绘画中,构图也被称为“章法”或是“经营位置”,它是绘画创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构图的经营位置,指的是在绘画创作中,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和画面位置的妥善安排, 达到表现作者创作意图的目的。 在敦煌壁画中,由于其装饰性特点的影响, 画面事物的安排也显得尤为重要。 在飞天形象的构图中,敦煌壁画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形成了一些常见的构图形式,包括连续式、对称式、零散式等[4]。 连续式构图是指一组飞天形象依次排列在画面中, 形成一种连续、流畅的感觉,这种构图形式常常被用于表现飞天形象的舞蹈和歌唱等活动,形象生动、自然。 对称式构图是指将飞天形象以中心点为对称轴,左右对称地排列在画面中,这种构图形式强调对称美和平衡感, 常常被用于表现宗教仪式中的飞天形象,形象庄重、肃穆。 零散式构图是指将飞天形象散布在画面中,形成一种自由、松散的感觉, 这种构图形式常常被用于表现飞天形象的舞蹈和飞翔状态,形象灵动、自由。 无论是哪种构图形式, 都需要考虑形象的位置和大小,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从而达到画面的平衡与和谐。 在敦煌壁画中,关于飞天的构图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创新性, 这些构图形式不仅表现了飞天形象的动态美和静态美, 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和艺术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从敦煌壁画的传达意义上, 飞天构图本身能很好体现作者意象,如莫高窟第217 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为传达净土思想和十六种观想方法,连续式穿楼而过的飞天极具特色。 “净土”中的楼阁宫殿完全是唐代宫廷的规模, 飞天也连续性地在其中穿行, 从一扇窗户穿进去另一扇窗户飞出来,飘带还留在楼阁中,像是塑造出慢镜头的剧情模拟出飞天的飞行轨迹。 通过画家异乎寻常地安排和组合,其构图具有动感活泼特征,将凝固的空间绘制出飞天们曳然飞过的动态场面,仿佛华丽的净土中充满幸福与欢乐。
(二)极富变化的线条
潘天寿曾说:“吾国绘画以线为基础”,线条是中国画独有的绘画语言, 具有其独立审美价值和独特的象征意义。[5]线描发展到唐代,进入登峰造极的鼎盛期,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表现程式:“兰叶描”“莼菜条”“春蚕吐丝”等等,唐代画家吴道子以极富节奏变化的线条表现人文、描绘出唐人宽衣博带、 迎风飘举的圆转动势,将“白画”推向了巅峰。[6]“吴带当风”强调着线条的流畅、自然和笔墨的轻重疾徐,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唐代绘画中, 也反映在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中。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常常被描绘成轻盈飘逸、韵律感强的形象,这种风格与吴道子的画风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 飞天形象的线条流畅、自然,笔墨轻重疾徐,这些特点都与吴道子画风的特点一致。 同时,飞天形象的飘带迎风飞舞,也表现出一种动感和生气勃勃的气息,与吴道子强调的抑扬顿挫、 气势磅礴的笔墨风格相契合。 除了吴道子,唐代还有其他著名画家,比如周昉、阎立本等,他们也对唐代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昉创造了 “吴家样”“水月观音体”等画风,注重形象的流畅和生动,使得唐代绘画在表现力上更加丰富和多样化。 阎立本则善于通过细腻的线条和色彩表现人物的情感和特征, 他的画作中经常出现丰颊曲眉的侍女形象,形象生动、自然。 在唐代绘画中,人物形象的造型和晕染添色都非常重要, 唐代画家善于运用线条和色彩表现人物的特征和情感。 在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中, 也能够看到唐代画家善用线条造型再晕染添色的技巧。 飞天形象的线条流畅、自然,笔墨轻重疾徐,往往采用晕染添色的技巧表现出形象的层次感和立体感,使得形象更加生动和立体。 莫高窟第39 窟献花飞天线描流畅有力,用色绚丽多彩,层层叠染,加金线提神,极富装饰性,舞动的飞天蕴含着生命意象的线条,同样也蕴含了对于生命的观照。总的来说,唐代绘画中的各种画风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风格,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共同推动了唐代绘画的发展和创新。 在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中,可以看到吴道子画风的影响,也能够感受到唐代绘画中其他画家的影响和创新,这些都为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和创新奠定了基础。
(三)仕女画的艺术形态
艺术审美意象的产生与创作者主观的 “意”密不可分, 其与艺术创作的目的和艺术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艺术中,主观的“意”往往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和构图来表现的,从而达到表现作者创作意图的目的。 在初唐时期, 高僧道宣就对佛教造像的审美意象进行过探讨,他认为:“造像梵相,宋齐间皆厚唇鼻隆,目长颐丰,挺然丈夫之相。 自唐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貌,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 ”这些变化反映了唐代社会和文化的变革, 艺术审美意象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在唐代的审美观念中,宫廷女性的审美标准逐渐影响了佛教造像的审美意象,使得佛教造像的形象更加婀娜多姿、柔美细腻。 这种审美观念的变化也反映在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中, 使得飞天形象的审美意象更加多样化。 如此,唐时期飞天出现更为经典的“周样式”, 这些美丽的飞天不再是印度佛经中的神,而是人间的美丽女子。[7]唐代敦煌飞天形象所呈现出的美感趋向人物画尤其仕女画的审美趣味,显示出更多的女性化特征。 盛唐时期莫高窟第39 窟的献花飞天丰肌秀骨, 珠光宝气,一手持莲花花盘,一手拈牡丹花蕾,飞身而降,表明盛唐飞天图像已进入工笔仕女画范畴。 榆林窟第15 窟前室顶的凤首琴伎乐飞天上身半裸,体态丰满,以缓慢的“U”形转折庄重专注地弹奏凤首箜篌,飘带翻卷。 若初唐时飞天显示出青春少女的天真稚气, 那么中唐时期的这身飞天就显示出一种成熟的雍容典雅之美。 这类“丰颐典丽,雍容自若”的风格,也是唐代社会审美情趣、审美情感的反映。
四、结语
印度飞天侧重于宗教功能的实现,其身形健硕,动作僵硬,具有明显的印度审美特征;而敦煌飞天则更加注重美学表现和艺术呈现, 从身形、衣着到整体形象、气韵都散发着中国审美的韵味。 画家通过主观审美观照巧思其身姿及服装,由最初西域模式的飞天画法将粗犷、稚拙的状态发展为中原式飞天甚至出现中国神话及道教中所谓的“飞仙”“羽人”的形态,唐代敦煌壁画中曼舞在空中的似乎已是宫廷侍女。 原印度石窟寺艺术里飞天持乐器的形象非常少, 而伎乐飞天在敦煌石窟里已成为主题; 原先印度飞天的动作姿态都出自南亚一带的舞蹈, 而敦煌乃至中原的飞天,从舞姿、服饰等特点看,则受到当时中国舞蹈的影响。 从中可见,在敦煌壁画中, 飞天形象的表现是非常注重主体与客体的和谐结合,同时也以客体为出发点。 这种表现方式反映了中国古代艺术中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审美观念, 也反映了佛教中讲究 “物我两忘”的精神。 在唐代时期,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期, 艺术审美意识也经历了大幅度的变化和发展。 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将佛教中的菩萨形象与宫廷女性的审美意识相结合,形成了“菩萨即宫娥”的审美观念。 这种审美观念将佛教的精神内涵与当时社会的审美要求相融合, 使得艺术审美意象得到了更加广泛地发挥和表现。 在敦煌壁画中,这种“菩萨即宫娥”的审美观念影响着飞天形象的表现方式和审美意象的发挥。 在壁画中,飞天形象常常被描绘成容貌秀美、仪态婀娜的形象,与当时的宫廷女性审美标准相符合。 同时,飞天形象也通常穿着华丽的服饰,配饰着珠宝首饰,表现出一种高贵、华丽的气质,与唐代宫廷文化的审美要求相契合。这种审美观念的影响, 使得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审美内涵和情感表达。飞天形象不仅是佛教信仰中的重要形象, 也成了当时社会审美意识的重要代表, 反映了唐代社会和文化的多元性和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