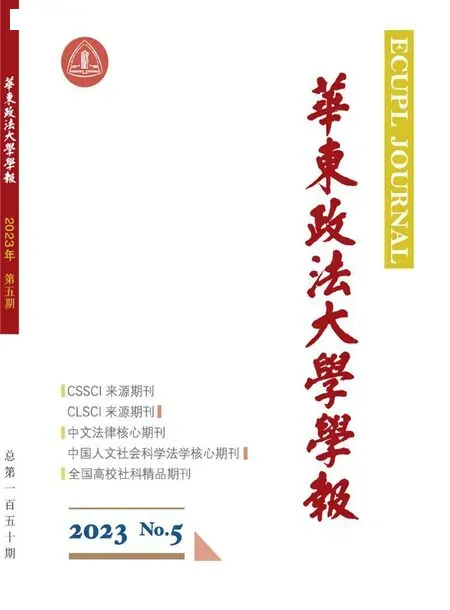国际体育仲裁中的规则之治与权利保障
2023-12-30冯硕
冯 硕
目 次
一、国际体育仲裁规则之治与权利保障的裁量:以孙杨案导入
二、国际体育仲裁规则之治与权利保障的失衡
三、国际体育仲裁规则之治与权利保障的协调
四、结语
2020 年2 月28 日,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以下简称“CAS”)针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孙杨和国际游泳联合会案”(以下简称“孙杨案”)作出对孙杨禁赛8 年的裁决,〔1〕See World Anti-Doping Agency v.Sun Yang &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 CAS 2019/A/6148, Arbitral Award, 28 February 2020, para.382.令国内民众再度对国际体育仲裁予以关注。2020 年12 月24 日,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以仲裁员存在偏见等理由撤销裁决,发回CAS 重审,并要求原审仲裁员不得参与重审。〔2〕See Request by Sun Yang for Revision of Arbitral Award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Approved, Swiss Federal Supreme Court, https://www.bger.ch/files/live/sites/bger/files/pdf/en/4a_0318_2020_yyyy_mm_dd_T_e_08_43_21.pdf, accessed August 13, 2023.2021 年6 月22 日,CAS 将原处罚缩减至4 年3 个月。〔3〕See World Anti-doping Agency v.Sun Yang and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 CAS 2019/A/6148, Arbitral Award, 22 June 2021.尽管改判纠正了原裁决的失当,但这种因歧视等原因的改判也凸显了CAS 仲裁对运动员权利保障的缺失。
国际体育仲裁作为维护国际体育竞技公平并解决国际体育争议的首要方式,既强调对运动员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强调对暴力、兴奋剂等不公平行为的禁止。〔4〕参见黄世席:《国际体育争议解决机制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32 页。因而,反兴奋剂争议始终是包括CAS在内的相关国际体育仲裁机构所关注的重点。在CAS 反兴奋剂仲裁中,曾经有众多运动员举起保障权利的大旗为自己辩护,但鲜有成功。究其原因,现实生活中的理由千变万化,如果任由运动员以自己的理解解释规则,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以下简称“WADA”)就难以顺利地对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情况进行检查,《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orld Anti-Doping Code)和CAS 所追求的国际反兴奋剂的规则之治就荡然无存。从更大的视角看,作为一种国际司法活动,国际体育仲裁的重要议题便是寻求规则之治与权利保障的协调。但由于权利的抽象性和规则的不周延性,国际体育仲裁会在维护规则的过程中侵蚀权利。
本文以孙杨案导入,通过个案分析厘清技术层面的得失,探求仲裁庭对规则和权利的裁量倾向,进而从整个国际体育仲裁制度的角度探讨规则与权利的平衡,明确其在规则权威导向下可能影响权利保障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厘清规则之治与权利保障的关系,探寻如何实现国际体育仲裁中规则之治与权利保障的协调,以期维护国际体育仲裁的制度价值。
一、国际体育仲裁规则之治与权利保障的裁量:以孙杨案导入
“孙杨作为世界顶级运动员,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体育成就,但这并不是他凌驾于法律与程序之上的理由。就像这些规则平等适用于所有运动员一样,孙杨亦必遵守之。”〔5〕World Anti-Doping Agency v.Sun Yang &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 CAS 2019/A/6148, Arbitral Award, 28 February 2020, para.358.仲裁庭的裁决既宣告了孙杨的败诉,也指出了对孙杨案裁判的内在逻辑与价值考量。
(一)孙杨案的案情与焦点
2018 年9 月4 日,受国际游泳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 Association,以下简称“国际泳联”)委托,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International Doping Tests and Management,以下简称“IDTM”)对孙杨进行赛外兴奋剂血检与尿检。参与此次采样的共有三人,分别是一名兴奋剂检查官(Doping Control O☆cer,以下简称“DCO”)、一名血液采集助理(Blood Collection Assistant,以下简称“BCA”)和一名兴奋剂检查助理(Doping Control Assistant,以下简称“DCA”)。DCO 与孙杨在之前的检查中认识,并出示了IDTM 签发的身份证明,以及一份国际泳联给IDTM 的通用授权书,DCA 出示了身份证,BCA 出示了护士专业技术资格证。
采样过程中,孙杨签署了兴奋剂检测表接受采血,血样被密封在玻璃容器并储存在储物箱中。但孙杨发现DCA 偷拍而怀疑其身份,要求重新审查其相关证件。在采样人员无法进一步提供证件的情况下,孙杨对其资质提出异议。之后,孙杨及其母亲与相关管理者取得联系,相关人员告知孙杨因DCO 证件不合规,已收集的血样不能被带走。采样人员警告孙杨如果收回血样会违反规则并需承担严重后果,但在孙杨压力下采样人员还是将血样交给孙杨。当DCO 告知孙杨IDTM 任何材料都不能遗留在现场时,孙杨指示并协助相关人员打破一个存血容器,其中的血瓶完好无损地被孙杨取回,导致该血样未能按规定送至WADA。此后,孙杨又撕毁了已签署的兴奋剂检测表。
事发后,WADA 向国际泳联报告了相关情况,国际泳联认为采样人员在得到授权的情况下进行检查符合规定,孙杨拒绝提供尿样并打碎血样容器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泳联兴奋剂管制规则》(FINA Doping Control Rules)第2.3 条和第2.5 条,应承担后果。2018 年11 月19 日,国际泳联兴奋剂仲裁庭(FINA Doping Panel,以下简称“国际泳联仲裁庭”)在瑞士洛桑就该处罚举行听证会,次年1 月国际泳联仲裁庭裁决认为IDTM 派出的工作人员中有两位缺乏《国际检测与调查标准》(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Testing and Investigations,以下简称“ISTI”)中规定的样本采集人员必备的授权,当晚的采样工作是在不恰当的基础上开始的,故抽取的血样并非ISTI 规定的“样本”,IDTM 代表国际泳联进行的检测行为无效。因此裁定撤销了国际泳联的处罚,但同时也警告孙杨其行为存在风险。〔6〕See FINA v.Sun Yang & China Swimming Association, FINA Doping Panel 01/2019, Arbitral Award, 3 January 2019, paras.6.54-6.58.
针对国际泳联仲裁庭的裁决,WADA 表示了强烈不满并向CAS 提起仲裁。WADA 认为孙杨未按规定提供尿样、擅自收回已采集的血样并参与打碎血样容器、撕毁已签署的检测表并撤回同意采血的意思表示等行为违反《国际泳联兴奋剂管制规则》第2.5 条“篡改或企图篡改兴奋剂管制的任何部分”和第2.3 条“逃避、拒绝或未能提交样本收集”。鉴于此系再犯,故申请CAS 对孙杨处以禁赛2~8 年的处罚。孙杨和国际泳联除了在程序上就管辖权提出异议外,在实体上认为由于采样人员并未按ISTI 规定进行适当通知并获得授权,不构成合法采样,故孙杨未违反《国际泳联兴奋剂管制规则》,不应受到处罚。同时采样人员存在对孙杨隐私权等基本权利的侵犯,即使相关行为过当,WADA 建议的处罚也有违比例原则,应酌情减免。〔7〕See World Anti-Doping Agency v.Sun Yang &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 CAS 2019/A/6148, Arbitral Award, 28 February 2020, paras.128-133.
通观CAS 裁决书,仲裁庭将目光集中于孙杨的行为定性和处罚程度两方面。在对孙杨行为定性上,仲裁庭着重考察IDTM 的采样是否符合ISTI 和孙杨是否有正当理由不遵守相关程序。双方的争议焦点是:(1)IDTM 的检查官是否具备ISTI 规定的采样资质;(2)孙杨可否以采样人员资质不符为由直接拒绝接受采样;(3)孙杨的拒检等行为是否违反了《国际泳联兴奋剂管制规则》第2.3条和第2.5条。WADA 想要胜诉有两条路径:(1)论证采样人员符合ISTI,孙杨抗检违法;(2)说明即使采样人员不符合ISTI,孙杨也无权拒绝检查并构成干扰检查。而孙杨想要胜诉只有一条路径,即在论证采样人员不符合ISTI 系非法采样的前提下,说明其有权直接拒绝检查。
(二)孙杨案的规则解释:采样的合法性分析
对采样人员资格的认定关键在于规则的解释,ISTI 第5.3.3 条规定,样品采集人员应具有样品采集机构提供的官方文件,如检测机构的授权书,以证明其有权对运动员采集样品。DCO 还应携带补充身份证明(例如样本收集机构的身份证明、驾驶执照、健康证、护照或类似的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明应载有姓名、照片和身份证件的有效期限。〔8〕参见梅傲、钱力:《世界反兴奋剂规则的争议、反思及其完善——以“孙杨案”为角度》,载《国际法研究》2020 年第4 期,第56 页。
根据国际泳联仲裁庭确定的事实,案发时采样人员分别出示了国际泳联出具给IDTM 的通用授权书(其中并未写明DCO 和受检运动员姓名)、DCO 的IDTM 身份证明及个人身份证件;BCA 的护士资格证和DCA 的身份证四份文件。
孙杨方认为:(1)采样人员不应只出示国际泳联向IDTM 提供的通用授权书,而应出示针对孙杨此次检查的特别授权书;(2)根据WADA 官方颁布的《ISTI 血样采集指南》(ISTI Blood Sample Collection Guidelines,以下简称《指南》)第2.5 条规定“每位采样人员应当接受培训并获得授权以实施其各自分配的职能”,〔9〕WADA 颁布的ISTI 血样和尿样的采集指南对采样人的要求作出了完全一致的规定,英文原文为:These individuals must be trained and authorized for their assigned responsibilities.仅DCO 获得授权的采样不合规;(3)根据中国的反兴奋剂实践和相关法律,每位采样人员须具备相应授权和中国反兴奋剂中心颁发的身份文件,本案中BCA 所提供的护士证明材料并不符合上述规定且异地执业违规。
WADA 认为:(1)采样人员作为一个整体,国际泳联只需向IDTM 出具一份通用授权书,无须标明采样人员和运动员的姓名;(2)ISTI 未对DCO 以外的人员作额外要求,即使《指南》倡导每位采样员应获授权,但WADA 通过《指南》起草者的证言证明,《指南》只是对“最佳实践”的建议,而非与ISTI具备同等效力的强制规定,故采样人员适格;(3)针对中国的国内法规定和实践惯例,WADA 认为本案涉及国际泳联对运动员的检查,CAS 只需审查采样行为是否符合ISTI 即可,不必考虑中国的规定。
尽管仲裁庭选择支持WADA,客观上仍需对其中的规则解释予以分析。下文将通过分析双方在采样合法性问题上的争议和仲裁庭的裁决,厘清争议焦点并探明孙杨方的败诉原因。
ISTI 第1 条明确指出:“ISTI 的起草也充分考虑尊重人权、比例原则和其他适用法律的原则,应据此解释和适用之。”故在对规则的解释倾向上应以尊重人权和比例原则为基本导向。
针对授权方式,仲裁庭首先接受了孙杨方对通用授权书和特别授权书的分类,并明确DCO 已出示了前者。ISTI 第5.3.3 条仅列举了通用授权书(原文为“检测机构授权书”),没有强制要求提供特别授权书。实践中,根据IDTM 提供的180 份检查案例,采样人员都只出示通用授权书。孙杨在之前经历过多次类似的检查,也未反对此做法。因此,无论是ISTI 的规定还是实践案例,孙杨方的抗辩都力度不足,尤其孙杨在之前类似检查中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这一抗辩更难成立。
针对授权对象,从ISTI 第5.3.3 条的文义出发,该条规定的采样人员们(their)应证明其获得授权。在集体授权还是单独授权的问题上,ISTI 的《指南》虽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孙杨方认为《指南》规定的“these individuals”强调的是每个人,但WADA 请出《指南》起草者作证,表示所有人都授权是“最佳实践”,现实中多难以实现。仲裁庭接受了后者的观点,认为“their”仅指所有涉及的样本收集人员,而非小组的每个成员,如果起草者有别的意图可以用更明确的语言表达,故孙杨方的理解有偏差。〔10〕See World Anti-Doping Agency v.Sun Yang &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 CAS 2019/A/6148, Arbitral Award, 28 February 2020, paras.247-253.仲裁庭在该问题上过度倚重《指南》起草者欠妥。WADA 作为《指南》制定者,尽管能证明规则的规定意向,但法律解释应同时考虑立法者的规定意向及其具体的规范意图,而非完全忽略后者,如此才能确定法律在法秩序上的标准意义。〔11〕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199 页。起草者认为三人都获授权是“最佳状态”更是其所追求的,《指南》的示范性也的确令运动员信赖并希望三人都授权,在追求合法性上二者是一致的。尤其面对WADA 在本案中的利益,规则解释应更多考虑孙杨的理解,至少该授权存在瑕疵,孙杨的行为具有合理性。
针对采样人员资格,仲裁庭分析了三名采样人员的资格,并认为均符合ISTI 的规定。但仲裁庭在BCA 违反中国国内法异地执业上的分析有待商榷。根据中国法,BCA 应具备国家认可的采血资质并获得资格证,反兴奋剂中心每年需对其进行资格认证。〔12〕参见韩勇:《世界反兴奋机构诉孙杨案法律解读》,载《体育与科学》2020 年第1 期,第6 页。BCA 的护士异地执业的确不符合中国法,本案作为国际案件虽应优先适用ISTI,但中国法更严格的标准实际上是为了规范采样人员行为以保障运动员权利,符合ISTI 第1 条的宗旨。在国际法上,国内法采用符合国际法宗旨的更高标准也多被允许。另外,ISTI 的执行要依靠各国国内从业人员,如果仅要求符合ISTI 的低标准而容许其违反国内法的高标准,既存在稀释各国主权的嫌疑,在客观上也难以实现。
因此,在采样合法性上,仲裁庭的裁决适当,且孙杨方在规则解释上确有瑕疵。但在授权对象和采样人员资格的认定上,仲裁庭未能全面分析和考量规则意旨,也未贯彻ISTI 人权保护理念,该采样至少存在程序问题,孙杨的行为和诉求也具有合理性。
(三)孙杨案的权利悲情:拒检行为的定性
如果说仲裁庭的不利裁决主要因孙杨方对规则理解和解释的偏差,那么最终判定孙杨“故意或尝试干扰兴奋剂检测”更多是仲裁庭在利益平衡下对孙杨个人权利的牺牲,折射出规则之治下的权利悲情。
根据孙杨所言,当晚对采样人员产生怀疑并采取相关行为,起因是DCA 私自对他拍照。在仲裁庭的调查中,案发时的录像和DCA 的证词都证实了这一事实,故仲裁庭认为该行为是不适当且不专业的。但在认定该行为失范的前提下,仲裁庭却认为这并不足以让孙杨中止整个采样工作,尤其在BCA 没有任何失范行为且采血已经结束后,孙杨取回血样、打碎容器、撕毁表格等行为都是不妥的。其认为正确的方式应是允许DCO 带走血样,并在当时(或嗣后)通过其他途径维权。在明确该观点后,仲裁庭进一步确认了DCO 曾对孙杨的行为作出警告并强调了可能的后果,证明其履行了法定职责。在DCO 的警告下,孙杨依旧选择收回并打碎血样容器,最终导致采血失败。
明确客观上是孙杨的行为导致采样失败后,仲裁庭将目光聚焦于《国际泳联兴奋剂管制规则》第2.5 条“篡改或企图篡改兴奋剂管制的任何部分”主观故意的认定。尽管WADA 认为孙杨违反了第2.3 条和第2.5 条,但仲裁庭采用举重以明轻的方式优先考察第2.5 条。〔13〕See World Anti-Doping Agency v.Sun Yang &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 CAS 2019/A/6148, Arbitral Award, 28 February 2020, para.191.在主观认定上,仲裁庭认为DCO 的提醒已经让孙杨知晓相关行为的后果,此时孙杨依旧选择毁掉血样容器并撕毁检测表带有明显的故意。尽管孙杨在听证中曾试图以“团队成员的要求”进行抗辩,但CAS 以往的判例中也强调反兴奋剂制度以运动员的个人责任为基础。如果任由运动员将责任推给团队,那么反兴奋剂执法便失去意义并会造成更大的不公。〔14〕See World Anti-Doping Agency v.Norjaimah Haiiszah Jamaludin, Nurul Sarah Abdul Kadir, Mohamad Noor Imran Hadi, Siti Zubaidah Adabi, Siti Fatimah Mohamad, Yee Yi Ling, Harun Rasheed & Malaysia Athletic Federation, CAS 2012/A/2791, Arbitral Award,24 May 2013, paras.8.1.5-8.1.6.因此,孙杨的确存在主观故意并违反了《国际泳联兴奋剂管制规则》第2.5 条。
孙杨的拒检是由于采样人员对孙杨隐私权等个人权利的侵犯,该行为也可理解为基于采样人员行为失范在先的一种自保行为。对此,仲裁员菲利普·桑德斯(Phillippe Sands)曾在听证时问孙杨一方,如果仲裁庭支持孙杨因对采样人员的质疑直接拒绝采样,是否会打开“轻浮之诉”的大门?作为仲裁庭,是否要考虑裁决对公共利益的影响?实际上,仲裁员的问题传达了两层意思:(1)仲裁庭不支持孙杨的原因主要是防止“轻浮之诉”的出现并影响反兴奋剂秩序,除非孙杨方能够阐明不会产生该情况;(2)在解决第一个问题时,仲裁庭似乎不应只局限于对反兴奋剂秩序的维护,或许也应考虑其对全社会的影响,这便直指对孙杨隐私权和知情权等基本人权的保护。孙杨的抗辩虽援引《瑞士民法典》第27条和第28 条,强调体育组织不得任意侵犯隐私权等人格权。但孙杨的律师并未沿着这一思路进行阐述,反倒是国际泳联的律师提到WADA 存在侵犯人权的情况。这无疑是一种对孙杨基本权利的牺牲,是权利未被保障的悲哀。恰因CAS 对孙杨个人权利保障的缺失,令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在关于裁决撤销审查中进一步重视了相关问题,力图维护运动员基本权利。
二、国际体育仲裁规则之治与权利保障的失衡
孙杨案反映了CAS 在国际体育规则与运动员个人权利保障之间的权衡与决断,这种为规则之治牺牲个人权利的情况在CAS 的历史上并非个案。因此,我们应超越个案从更为全局的视角审视CAS的裁判倾向,这既需要追溯国际体育仲裁的价值追求,更需要挖掘其背后的原因。
(一)规则之治与权利保障的平衡现状
长期以来,与反兴奋剂有关的体育仲裁是CAS 的核心业务,以至于CAS 专门设立反兴奋剂法庭并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以下简称“国际奥委会”)等机构的授权下解决争议。近年来,CAS 处理了众多反兴奋剂争议,并通过诸多案例捍卫国际体育规则。
2018 年,俄罗斯因涉嫌兴奋剂违规,被国际奥委会暂停提名运动员参加平昌冬奥会的资格,并通过筛选机制选择符合要求的俄罗斯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参赛。2018 年2 月7 日,多名未获资格的俄罗斯运动员对国际奥委会提起上诉,请求推翻拒绝邀请他们参加平昌冬奥会的决定。该案中运动员认为其并无兴奋剂违规行为,国际奥委会的做法是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歧视并侵犯其基本权利。但仲裁庭认为,这种看似不公平的处罚是因俄罗斯涉嫌官方实施集体兴奋剂违规操作造成。〔15〕See Victor Ahn et al.v.IOC, CAS ad hoc Division OG 18/02, Arbitral Award, 9 February 2018, para.7.19.并且CAS早已指出,为维护体育运动廉洁性,国家联合会有责任对管辖的运动员实施反兴奋剂教育,故“连坐”是合法的。〔16〕See Bulgarian Weightlifting Federation v.International Weightlifting Federation, CAS 2015/A/4319, Arbitral Award, 15 February 2016, paras.80-84.客观而言,国际奥委会的做法可能侵犯了不存在兴奋剂违规的俄罗斯运动员的权利,CAS 的这种“司法谦抑”也确乎欠妥。〔17〕See Antoine Duval, “Getting to the Games: The Olympic Selection Drama(s)at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16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Journal 52, 65-66 (2016).但面对反兴奋剂这一“天条”时,CAS 也不得不退缩,或许让权并非其本意,但不敢夺权却是它基于制度框架的现实选择。
根据CAS 仲裁规则,CAS 仲裁的仲裁地均为瑞士洛桑。《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采仲裁地标准,即凡是仲裁地为瑞士的裁决,瑞士联邦法院均可行使撤销权,成为能够撤销CAS 裁决的唯一机构。〔18〕参见高薇:《论司法对国际体育仲裁的干预》,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 年第6 期,第176 页。包括孙杨在内的运动员在不服CAS 裁决时,多会向瑞士联邦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依瑞士法,可撤销裁决的法定理由主要为仲裁庭组成不当、仲裁庭无管辖权、仲裁裁决超裁或裁决违反公共政策等。〔19〕参见熊瑛子:《国际体育仲裁司法审查之法理剖析》,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9 年第3 期,第8-9 页。
除瑞士国内救济途径外,因体育仲裁多涉及运动员人权,故运动员可援引《欧洲人权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向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以下简称“ECHR”)请求救济,最为著名的便是德国速滑运动员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Claudia Peschstein)启动的程序。2009 年,国际滑冰联盟(International Skating Union,以下简称“国际滑联”)认定佩希施泰因兴奋剂违规并予以禁赛,之后运动员经历CAS 和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定程序均以败诉收场。最终,运动员向ECHR 起诉并认为:(1)CAS 因受到国际奥委会与国际滑联影响,未坚持独立公正;(2)CAS 与瑞士联邦最高法院都未公开审理,侵犯人权;(3)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对CAS 裁决仅进行了最低限度的程序性审查,未矫正裁决错误。〔20〕See Mutu and Pechstein v.Switzerland, Applications Nos.40575/10 and 67474/10, Judgement, 2 October 2018, paras.52-53.最终ECHR 仅支持了第二项请求,仍在维护CAS 的司法权威。
尽管该案在实体上并未撤销对佩希施泰因的处罚,但却暴露了CAS 在运动员人权保护上的缺陷并推动了改革。首先,在管辖权上,佩希施泰因通过国际途径争取救济的同时,也在德国展开诉讼。德国慕尼黑高等法院认为,国际滑联将接受CAS 仲裁条款作为运动员参赛的前提条件属滥用垄断地位,故仲裁条款无效。尽管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该结论,但也暴露出CAS 在管辖权上缺乏对运动员意思自治的尊重。〔21〕参见向会英:《体育自治与国家法治的互动——兼评Pechstein 案和FIFA 受贿案对体育自治的影响》,载《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6 年第4 期,第46-48 页。其次,在CAS 独立性和公正性上,案发时CAS 的仲裁员均直接或间接由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提名,封闭的仲裁员名册很难找到独立仲裁员,故裁决深受国际体育组织的影响,这在ECHR 审理的案件中也获得少数法官认同。在CAS 对该案处理的过程中也日渐发现该问题,故在2016 年新版规则中改变了仲裁员配额方式,扩充了独立仲裁员数量,但提名方式上仍倚重各体育联合会,中立性改革仍显不足。〔22〕参见郭树理:《运动员诉权保障与〈欧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法院佩希施泰因案件述评》,载《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9 年第9 期,第59 页。再次,在仲裁公开上,诚如ECHR 判决所强调的,诉讼程序的公开性既是维护人权和司法公信的应有之义,也关系到人们对司法的信仰。〔23〕See Mutu And Pechstein v.Switzerland, Applications Nos.40575/10 and 67474/10, Judgement, 2 October 2018, paras.178-179.2018 年ECHR 作出判决后,CAS 正式明确在运动员申请后相关程序都应公开,这才有了孙杨的公开听证。2022 年6 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针对佩希施泰因的上诉作出判决,并在程序公开和强制仲裁条款效力两方面支持了运动员的诉请,最终发回慕尼黑高等法院重审。〔24〕Vgl.BVerfG, Beschluss der 2, 1 BvR 2103/16 (Juni 3, 2022), paras.46-54.
CAS 长期的实践都在维护规则之治和保障权利中选择了前者,尤其在反兴奋剂上更凸显宁肯牺牲运动员权利也要维护规则的态度。尽管牺牲运动员权利的行径遭到了多方批评且CAS 也进行了改革,但改革的力度似乎隔靴搔痒,显露出一种消极的态度,究其原因或许还要回归到国际体育仲裁的价值追求。
(二)国际体育仲裁的规则权威导向
规则之下我们仍要聚焦国际体育仲裁的裁判倾向,这也深受国际体育组织的影响。在众多国际体育组织中,国际奥委会处于核心地位,它的自我定位代表了国际体育组织的普遍意愿。《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体育组织承认运动是在社会框架内进行的,因此应保持政治中立。它们有自治的权利和义务,包括自由地建立和控制体育规则,决定其组织结构和治理,享有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选举权利,并有责任确保良好治理的原则得到实施。”自治成为体育组织的追求,它们希望在不受任何外部干扰的情况下独立运作,包括司法在内的外部介入也常受到体育组织的抵触。〔25〕See Ian S.Blackshaw,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An Introductory Guide, T.M.C.Asser Press, 2017, p.22.因此,国际体育组织始终在追求独立之下的自治,其体系内部的司法活动等相关组织行为都强调对自身权威的维护。想避免司法的外部干预就需设立相应的内部争议解决机制,以CAS 为代表的国际体育仲裁机制应运而生。由于国际体育仲裁与国际商事仲裁相似,故在研究范式上常常混同,实则不然。
CAS 等国际体育仲裁机构虽会处理与体育有关的商事争议,但多数是与孙杨案相似的纪律处罚上诉仲裁。此种仲裁不同于商事仲裁处理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法争议,而是一种为维护规则和秩序的纪律仲裁。〔26〕See Johan Lindholm,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and Its Jurisprudence: An Empirical Inquiry into Lex Sportiva, T.M.C.Asser Press, 2019, p.289.
首先,国际体育仲裁的主体不平等。不同于解决平等私主体争议的商事仲裁,国际体育仲裁的对垒双方多是运动员与国际体育组织。尤其在纪律仲裁中,运动员是在被体育组织判定违反规则并施以处罚时提出仲裁,更处在不利地位。〔27〕See Antonio Rigozzi, “Challenging Awards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217, 241(2010).通常而言,仲裁作为一种第三方争议解决机制,需要在程序推进中力图实现当事方的地位平等。但与以反兴奋剂处罚为代表的体育纪律处罚相关的体育仲裁是在维护国际体育规则和秩序,运动员实际上难以获得与体育组织真正平等的地位。诚如菲利普·桑德斯在孙杨案中指出的,除非存在明显的侵犯人权,否则仲裁庭必须对体育活动的公平性进行充分考量。故在佩希施泰因案中,即使存在程序瑕疵,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和ECHR 也都充分尊重了体育组织为维护规则而做出的处罚。
其次,国际体育仲裁弱意定强法定。意思自治作为商事仲裁的制度基石,其在管辖、法律适用、程序推进和裁决执行方面都倚重当事人的合意。尽管在商事仲裁的发展中,意思自治也在与国家法秩序的博弈中得以归顺,但意定性依旧是商事仲裁的核心特征。〔28〕参见冯硕:《仲裁的数据化与中国应对》,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23 年第4 期,第106 页。在国际体育仲裁中,争议方尤其是运动员多不具有选择的权利。无论是国际奥委会还是其他体育组织,在运动员报名参赛时就被要求接受相关规则拟定的“法定”争议解决条款,否则便失去参赛资格,运动员也只能被动接受。〔29〕See Gabrielle Kaufmann-Kohler & Blaise Stucki ed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 Switzerland,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4,p.137.这反映出国际体育规则的强制性,凸显国际体育组织为维护其权威而对运动员的控制。
因此,基于对自治权的追求,国际体育组织在百余年来的管理与运行中始终强调对国际体育规则的维护。作为国际体育组织的有机组成,以CAS 为代表的体育仲裁机构也在司法活动中形成与商事仲裁不同的价值取向。由于对规则权威的维护,国际体育仲裁庭的权力来自国际体育规则的授予,故法定性强于意定性。其往往将运动员置于弱势地位,运动员也多基于对参赛利益的追求而选择接受。
(三)国际体育仲裁的权利保障缺失
作为国际体育规则的解释机构,CAS 要坚守规则的基本意旨。ECHR 对国际体育仲裁的介入,凸显国际体育规则对《公约》规定的基本权利保障缺失。尤其在以反兴奋剂仲裁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体育仲裁中,对公平审判权、隐私权和不受歧视权的忽视已造成诸多问题。
在公平审判权保护上,《公约》第6 条强调公民接受公开公正审判的重要性,国际体育仲裁的强制管辖、CAS 的独立公正和不公开听审等问题与之产生龃龉,并在佩希施泰因案等案件中被ECHR批评。但上述问题主要聚焦于程序层面,在实体上反兴奋剂仲裁的有罪推定倾向才是对个人权利的深层伤害。体育仲裁作为对运动员生涯作出“刑罚”的司法活动,秉持无罪推定理念才能保障运动员权利。尽管CAS 在相关判例中强调无罪推定,但实践中似乎又很难实现。例如,在举证责任上,相关规则都要求主管当局承担兴奋剂违规的举证责任,运动员在质证过程中几乎没有抵挡能力。究其原因,在兴奋剂检测中样本自离开运动员后便被WADA 控制,运动员无从介入也就难以取证。此外,WADA 的许多指控往往根据一种看似“科学”的推测,故实践中运动员会认为以间接证据论证兴奋剂违规有违无罪推定。另外,在证明标准上,体育组织内部的处罚多基于听证小组的“满意程度”而非“排除合理怀疑”,导致作出的处罚并不能全面保障运动员权利。〔30〕See Despina Mavromati, “Indirect Detection Methods for Doping from a Perspective: The Case of the Athlete Biological Passport”, 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olicy and Politics 241, 256-258 (2014).
在隐私权保护上,《公约》第8 条强调公共当局除以国家安全、公共健康及其他公共利益为由外,不得干涉公民及其家庭的隐私权和通信权。在WADA 主导的兴奋剂测试中,均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运动员的上述权利。例如,WADA 的赛外检查有时会干扰运动员的日常生活,故欧洲人权委员会在承认赛外检查必要性的同时,也强调检查不应无理干扰运动员的私生活。〔31〕See Council of Europe (1989)Explanatory Report to the Anti-Doping Convention, (19 September 1989), http://www.worldlii.org/int/other/COETSER/1989/6.html.但在WADA 检查权不受约束的前提下,这种带有追踪性质的检查多会对运动员产生困扰,并被视为对运动员私生活的限制。〔32〕See James Halt, “Where is the Privacy in WADA’s ‘Whereabouts’Rule?”, 20 Marquette Sports Law Review 267, 269-233(2009).在飞行检查(Unannounced Inspection)〔33〕在反兴奋剂执法中的飞行检查,主要指跟踪检查的一种形式,通常兴奋剂检测机构在事先不通知被检查运动员的情况下临时作出决定并联系运动员即刻进行现场检查。中,相关人员必然会与运动员产生直接接触,如何保证该过程不会侵犯隐私也令人担忧。尽管从CAS 到ECHR,相关的案例都尽量保持对WADA 的支持,但也或多或少地指出检查在可接受性和权利保障上存在缺憾,〔34〕See Bart van der Sloot, Mara Paun & Ronald Leenes, Athletes’Human Rights And The Fight Against Doping: A Study of The European Legal Framework, T.M.C.Asser Press, 2020, pp.204-207.这也在孙杨案中有所暴露。
在不受歧视权保护上,《公约》第14 条指出其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不得因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或社会出身、与少数民族的联系、财产、出生或其他地位等任何理由而受到歧视。在非歧视问题上,性别歧视居于首位。随着时代的发展,简单以男女为界限划分性别似乎正在成为历史,故现行体育规则的性别分类可能会对变性人、跨性人造成歧视。例如,2009 年柏林田径世锦赛女子800 米冠军卡斯特尔·塞门亚(Caster Semenya)因雄性激素过多症被判定为非100%的女性,遭受巨大质疑。国际田联更规定如果女运动员的睾丸激素超过10 nmol/L 就不能参加比赛,除非其能证明激素未带来优势。对此,运动员向CAS 提起仲裁,要求国际田联撤销该性别分类政策,但最终CAS 驳回了该诉请。我们可以理解国际体育组织为比赛的公平性和规则的可执行性而不得不如此规定,但此举也剥夺了在性别上有特殊情况的人群参与体育竞技的权利,可能背离国际体育精神和宗旨。因此,2023 年ECHR 判决认为强制要求降低体内睾酮水平才能继续参赛是对她的歧视,〔35〕See Semenya v.Switzerland, ECHR 10934/21, Judgment, 11 June 2023.保障了运动员的人权。
在《公约》的人权保护视域下,国际体育规则的确在个人权利保障上存在问题。这种缺失寓于规则中,因而左右了国际体育仲裁的实践。对此,国际体育组织选择通过规则的完善强化对运动员权利的保障。2019 年WADA 颁布的《反兴奋剂运动员权利法案》便通过法定权利与建议性权利两种模式,包括原则性权利、实体性权利、程序性权利和兜底性条款共计17 项权利内容,对运动员在反兴奋剂过程中的权利展开了全面保护。〔36〕参见徐翔:《WADA〈反兴奋剂运动员权利法案〉的解读与启示——基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孙杨案的思考》,载《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0 年第4 期,第61 页。2021年版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修改和完善了兴奋剂违规的认定、罚则、救济与执行,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强化对运动员合法权益的保护,充分体现了兴奋剂违规处罚的相称性,以保障运动员的合法权益。〔37〕参见徐伟康:《2021 年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ADC)的修改评述——基于与2015 年版WADC 条款的对比》,载《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0 年第4 期,第408 页。上述规则的革新也证明国际体育仲裁在运动员权利保障上亟须完善,规则完善后国际体育仲裁应如何实现规则之治与权利保障的协调关系到它的权威性。
三、国际体育仲裁规则之治与权利保障的协调
尽管国际体育仲裁的规则权威导向立足对自治权的追求,但对运动员权利保障的缺失也撼动了它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对此,需要从理论出发厘清规则之治与权利保障的关系,探寻国际体育仲裁规则之治的价值指向,明确权利保障的具体路径,在协调中维系国际体育仲裁的权威性。
(一)规则之治与权利保障中的利益考量
诚如菲利普·桑德斯在孙杨案中所言,CAS 是否应为了维护运动员个人权利而挑战国际体育组织反兴奋剂规则适用的统一性,进而撼动规则所维护的秩序。这将规则之治与权利保障的协调问题拉入具体案件的裁量,直接指向利益的衡量。
对利益的追求源自人之本能,权利则是在现代法治体系形塑中对利益的规范性表达,权利体系构建的根本指向在于维护各方之利益。〔38〕参见付子堂:《对利益问题的法律解释》,载《法学家》2001 年第2 期,第31-33 页。利益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满足社会成员主观需要的客体对象。一方面,利益是一种客体对象,表明利益来自客观的物质世界并不受人主观意识的左右。另一方面,利益应满足人的主观需要,能唤起人的利益兴趣和认识,促使人追求利益。但利益的客观有限和人追求利益的主观无限,会引发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冲突,需要一种规则定分止争。〔39〕参见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169 页。
规则往往由统一的最高主体制定并实施,构成了权力的生成与运作的过程。这令权力与权利对应性地内化于法治体系,使之在碰撞中锤炼规则的韧性并形塑法治的样态。从历史的维度考察,这种基于利益展开的权力与权利的互动,集中反映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与博弈中。在政治国家吞没市民社会的阶段,统治者依靠强权制定规则以维护其利益并形成相应的利益输送秩序。被统治者限于依靠人身依附性建立的等级社会中并无权利可言,彼时的规则之治是基于统治者利益以权力压制权利的治理方式。
随着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人文主义兴起,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逐渐分离。从身份向契约的社会形态转变,在打破社会等级的同时,实现了人的独立并催生了市民阶层的权利意识。一方面,市民社会的发展令多元利益格局逐步形成,市民阶层不同主体之间基于各自利益所产生的利益冲突愈发复杂,需要规则对横向的利益冲突作出协调。〔40〕参见马长山:《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载《法学研究》2001 年第3 期,第23-25 页。另一方面,以社会契约为基本模式的代议制政体开始出现,市民阶层通过让渡权利所选择的主权者成为纵向利益协调的权力主体,化身为维护市民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故在法治国家,规则之治既需要满足对平等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也需要协调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种权利的集合。
从权利的角度,规则对利益的协调构成了一种权利的处分,根植于权利的能动性。所谓能动性,是指规则给了权利主体在一定范围内为实现利益要求而表现意志、作出选择、从事一定活动的自由,包括在一定条件下转让或交换权利的自由。〔41〕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85 页。权利之所以可以处分,源于利益的主客观统一。一方面,客观性决定了利益会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动而变动,利益的常变也决定了权利的常变。另一方面,主观性允许利益主体基于需求对利益进行交易。利益作为满足利益主体需求的对象,主体在主观需求变化时可对所获利益进行处分。质言之,利益的客观常变为权利的处分提供可能,权利主体需求的能动使其通过主观意志实现对权利的处分。在明确权利为何可以处分的基础上,我们更需追问在现代法治社会究竟什么权利可以处分。权利作为经规则确认之利益,规则对权利的分类是现代法治社会所应普遍遵循的。现代法治国家往往将与人的生命、人格等利益相关的基本权利作为不可处分的权利,这便要求规则予以全面保障。
总之,无论是规则还是权利,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利益展开的,具有对立统一性。权利作为利益的规范性表达,镶嵌于整个规则体系中,伴随着主体对利益的追求而催动法治体系的运转。但利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必然会导致利益冲突,并以权利冲突的面貌呈现。面对冲突,规则应运而生并发挥利益协调的功能以期定分止争。在利益协调的过程中,由于规则制定与执行主体是经被协调主体权利让渡而产生的,故前者所制定的规则应满足后者的诉求并保障其权利。一方面,在法治的体系中应明确基本权利之范畴并强调严格保障。另一方面,利益的协调更要从整体出发兼顾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以维系整个体系中利益分配和流转秩序的稳定,构成国际体育仲裁平衡规则之治和权利保障的法理基础。
(二)国际体育仲裁的规则之治应以权利为底色
国际体育仲裁通过实践所树立的规则权威导向,目的在于维护国际体育组织的自治权。尽管其侧重于维护体育组织的对外独立,但这种自治权仍要以权利为底色,规则的权威性建筑于对权利的尊重之上。
体育组织的自治权根本上仍来自契约性的权利让渡,任何运动员参与体育赛事或体育组织,前提便是认同相关体育规则并以意思自治的方式自愿参加。这种基于个人自由意志作出的权利让渡,彰显着私法契约之精神。当然,权利让渡赋予了包括体育仲裁在内相关体育组织权力,但这种权力仍沿着实现利益诉求的外在样态转化,不影响权力的内在属性并以权利为基础,权力的运行也会受到权利的价值与功能的指导和规制。〔42〕参见胡杰:《论权力的权利性》,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 年第2 期,第85 页。
作为维系体育组织自治权的重要依据,体育规则的制定也以权利尤其是运动员权利为底色。从契约的角度,体育规则构成一种格式化的契约,运动员在基于自由意志作出选择时会从利益出发审视整个规则。运动员愿意接受规则加入其中,关键在于规则能够保障大多数运动员的基本权利并满足其利益诉求。目前的国际体育规则尽管对外强调一种排他性,但对内依旧构成了多数运动员权利的最大公约数,其满足了多数人的利益并获得他们的认同,这种认同也加持了整个体系的稳固性进而促进自治。就自治权与个人权利关系而言,二者始终处在同一利益链条上。无论是权力间的关系、权利间的关系,抑或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本质上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利益的博弈。国际体育自治秩序的形成以权利为纽带,依靠的是体育参与者这一数量庞大的利益主体间团结一致。体育自治权与体育参与者的个人权利,正是在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的理念上得以协调。〔43〕参见李智、喻艳艳:《体育自治的导向:体育自治权的属性辨析》,载《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8 年第2 期,第31-34 页。
国际体育组织自治权的权利属性和体育规则的权利底色,决定了国际体育仲裁在推动规则之治的过程中也应坚持对参与方权利的尊重,并以此为基石展开对制度的完善和规则的解释。在仲裁协议的解释中,尽管国际体育仲裁始于格式化的仲裁条款,排除了其他争议解决方式介入,凸显强制性。但实质上仍体现意思自治的特点,指引着仲裁协议的解释。
在解释立场上,尽管法律的解释力求中立,但在规范与现实的穿梭中,法律的立场倾向往往决定了最终结果。〔44〕参见冯硕:《TikTok 被禁中的数据博弈与法律回应》,载《东方法学》2021 年第1 期,第88 页。在合同法上,CAS 仲裁协议属于一种格式合同,只有这种强制性有损于接受方的根本利益而伤害其最基本的道德和正义观念时,合同才可能归于无效。在仲裁法下,仲裁协议仍区别于一般的合同,在解释中倡导有效性优先。即当某一条款存在不同的解释结果时,使之有效的解释应当被优先采纳。当仲裁协议可以适用多种法律时,使之有效的法律居于优位并促成仲裁协议有效。〔45〕参见张春良:《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的合法性论证——CAS 仲裁条款的效力考察兼及对中国的启示》,载《体育与科学》2011 年第2 期,第24-25 页。故从合同法和仲裁法的理论出发,不能贸然否定CAS 仲裁协议的效力,而应本着倾向于认定仲裁协议有效的立场探寻解释的路径。
在解释路径上,体育仲裁协议的效力仍应考察其是否符合当事人真实意思。对真实意思的探求需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应根据具体境况考虑当事人的意志,即考虑当事人合理和正当的预期结果;二是应考虑当事人签署协议直至争议产生时的态度;三是应进行整体解释,综合考察仲裁协议在整个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46〕See Emmanuel Gaillard & John Savage eds., Fouchard, Gaillard, 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 pp.256-260.体育仲裁协议的强制性是参与体育赛事的运动员普遍了解的事实,是其参与比赛并实现自身利益的前提。仲裁协议基于当事人意志,包含运动员追求利益的目的。因《奥林匹克宪章》将一切与体育相关的争议交由CAS 仲裁,故该仲裁协议均可视作对宪章的延伸,对它的解释也应本着维护国际体育组织整体利益之目的。承认仲裁协议有效维护了体育组织的自治,这便是国际体育组织作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所以,体育仲裁协议仍体现运动员与相关体育组织的真实意思。
在解释效果上,条文的解释除探求文本及其背后的意图外,更要重视其产生的效果。仲裁的专业和高效是较之诉讼的优势,CAS 作为专业体育仲裁机构能够通过组织全球体育领域最专业的仲裁员实现争议的公正裁判,这是保障当事人尤其是运动员权利的底线。换言之,相较于行业以外的法官裁判,体育仲裁员更明白争议背后复杂的利益关系,更理解当事人的利益诉求与心酸苦楚,能在理性与感性的双重视角下作出妥当的裁决。另外,不同于商事仲裁,体育仲裁对效率的要求更高,尤其是重大赛事中的体育仲裁关系到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甚至是国家的利益。故CAS 强制管辖能防范管辖权上的推诿而直入争议核心,并依凭仲裁员的专业和权威快速作出裁决,这也是及时维护运动员权利的体现。〔47〕参见姜熙:《我国兴奋剂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研究——基于新修订〈体育法〉的思考》,载《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 年第8 期,第44-46 页。
所以,体育仲裁协议具有强制性似乎压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其仍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实现了体育组织自治与当事人权利处分的平衡,是一种对零散意思自治规则化的过程,具有契约属性并指导着程序的推进。
在仲裁程序推进中的权利保障上,一方面,要认识到体育仲裁不同于商事仲裁中当事人地位天然平等,运动员多处于弱势地位,故在程序的推进中,应倾斜性地保障运动员程序性权利,尤其在纪律仲裁中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的裁量等方面应给予运动员适当的保障。另一方面,基于国际体育仲裁的契约性,要明确运动员接受体育规则和仲裁实际是接受格式合同的过程,故在有关体育规则的解释和适用中,更应在规则的刚性标准下以保障运动员权利为目标作出有利于运动员的解释。〔48〕参见张俊等:《体育正义实践表达的四重维度——基于孙杨案的相关分析》,载《体育学刊》2020 年第5 期,第20-23 页。具言之,在涉及运动员基本人权方面,除关注体育规则本身外,更应关注有关人权保障的国际公约和国内法的规定,强调基本人权不可让渡且必须保护的立场,不应以所谓的权威和秩序忽视基本权利。在其他权利的处置上,仲裁庭更应考虑保护运动员职业生涯等多方面因素,朝着有利于运动员方向解释和适用规则,不应片面地以整体规则利益压制个人发展利益。
回归孙杨案中的规则解释与适用,在有关授权主体资格的认定上,既然《指南》强调每位采样人员都应获得授权,便不能简单以WADA 作为规则起草者所认为的“最佳实践”不具有强制性为由忽视孙杨主张的合理性。仲裁庭更应站在保障孙杨权利的立场上,作出有利于运动员的解释。这既是《指南》所倡导的满足多数运动员权利诉求的规定,也是保障运动员基本权利之必需。在采样人员资格的判定上,更应看到中国法为维护运动员权利所采用的高标准符合国际法意旨,在适用国际规则的同时也应兼顾国内法的可执行性。
(三)国际体育仲裁的权利保障应以规则为指引
国际体育仲裁规则之治的权利底色,侧重于从权利保障的角度指导仲裁中具体的规则解释与适用。国际体育仲裁除了具有维护国际体育规则统一和组织自治的作用外,更通过国际司法活动完善规则实现规则与权利的统一。故在体育仲裁的发展中,应关注当前规则对权利保障的缺失,借助体育仲裁的司法能动来弥补这一缺陷,从而将权利保障的理念内化于规则之中,沿着规则的指引保障权利。〔49〕参见陆宇峰:《“规则怀疑论”究竟怀疑什么?——法律神话揭秘者的秘密》,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 年第6 期,第70-71 页。同时,除了国际体育规则是国际体育仲裁的指引,有关国际法和国内法规则更从外部影响着国际体育仲裁。相关规则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强调了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应成为国际体育仲裁中不可或缺的法律渊源。
将权利保障理念内化于规则始终是国际体育规则制定与执行的重要方面,包括ISTI 在内的相关规则也都将保障人权置于首位并指引实践,但在国际体育组织追求自治的过程中,基于制度的惯性常常陷入对权威与秩序的追求,忘却了自治权的权利属性并凸显出权力化的趋势。这直接导致国际体育仲裁淡化了契约性底色,逐渐将自己视为一种具有最高裁判权的公权机构,并板起一副家父主义的面孔对争议作出独断的裁判。恰因这种定位偏移,令体育仲裁庭在解释和适用以权利保障为底色的规则时,往往仅就规则论规则而忽视其背后真意,导致规则的异化。
所以国际体育仲裁应贯彻寓于规则当中的权利保障理念,通过具体的解释与适用促进规则之治与权利保障的协调。在孙杨案中DCO 的授权方式上,尽管通用授权书在实践中已经成为惯例,但惯例并不意味着合法与合理。〔50〕参见宋阳、崔心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商事惯例适用问题研究》,载刘晓红主编:《“一带一路”法律研究》(第3 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52-55 页。当运动员接受一次严格的检查时,满足其知情权的,如果是一份缺乏必要内容的格式文件,那么运动员将很难信服该检查的合法性并保障自身权利。孙杨的这种抗辩尽管在技术层面存在困难,但在制度层面也具有合理性。仲裁庭或许更应从规则的本意出发,通过裁决接受这种诉求,使之成为相关规则的一部分,提醒WADA 在检查中严格遵照程序保障运动员权利,这也是国际体育仲裁推动体育规则完善的一种方式。
孙杨团队最终通过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撤销CAS 的8 年禁赛处罚,也反映出司法审查的重要性。从规则的角度看,这提醒国际体育仲裁虽要以体育规则作为主要的法律渊源,但并不意味其可以规避国际法和国内法的适用以及其他司法机构的介入。在权利保障上,包括《公约》在内的相关法律规则始终具有相对普遍的适用价值,指引着各类司法活动的进行。国际体育仲裁虽然可以基于自治性的初衷以国际体育规则为基准裁量案件,但因国际体育仲裁在国际法治体系中的特殊价值,更应兼顾国际法和国内法对相关问题的关注,通过自身规则和外部规则的共同指引作出裁决。这既可以保障运动员权利,也维护了裁决的合法性和可执行性,实现体育自治与国际法治和国内法治的协调。
四、结语
穿梭于规则与权利之间,孙杨案的裁决与撤销既显现出国际体育仲裁对规则之治的强调,也反映了权利保障缺失的悲情。长期以来,以CAS 为支柱的国际体育仲裁始终在维护规则和保障权利之间找寻平衡,逐渐显现出重规则而轻权利的倾向。虽然国际体育仲裁的规则权威导向来自国际体育组织对自治权的维护,但与之相伴的权利保障缺失也成为国际体育仲裁的内在缺陷,侵蚀了国际体育仲裁的公正性与权威性。
规则和权利都根植于利益而具有对立统一性。权利作为利益的规范性表达,镶嵌于整个规则体系。利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会导致利益的冲突,规则应运而生并发挥利益协调的功能以期定分止争。在利益协调中,既要在法治体系中明确基本权利之范畴并强调权利保障,也要在利益协调中兼顾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维系整个体系的利益分配和流转秩序的稳定。
因此,国际体育仲裁要明确规则之治应以权利为底色,强调国际体育组织自治权的权利属性。在仲裁协议和体育规则的解释中,明确保护运动员权利的解释倾向。同时,国际体育仲裁对权利的保障也要以规则为指引,既要强调通过仲裁判例填补现有规则的空白,贯彻权利保障理念;也应关注国际法和国内法在仲裁中的作用,实现体育自治与国际法治和国内法治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