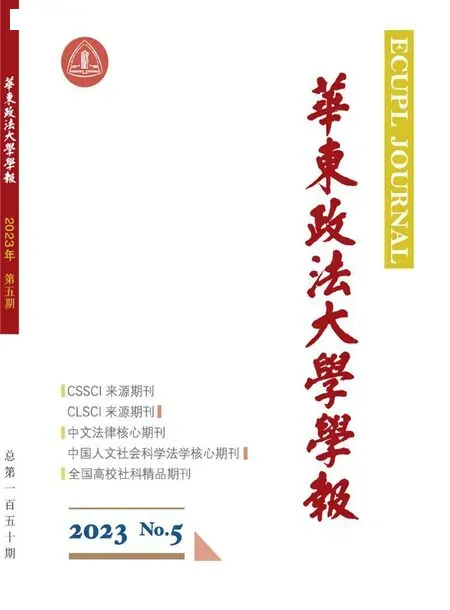技术、证据与信仰:清代地方疑案审断中的城隍庙祈梦析论
2023-12-30方潇
方 潇
目 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作为司法技术的“城隍庙祈梦”之构成因素解析
三、作为证据启示的“城隍庙祈梦”之司法效果分析
四、作为信仰支撑的“城隍庙祈梦”之历史价值分析
五、结语:证据神示、理性审判与神道司法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古代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城隍神信仰,自不待言,然而通过城隍庙祈梦以断疑案的做法,则主要流行于清代。不过,从发生学角度看,其在元明时期即有所萌芽和体现。〔1〕如元代至元年间都城的一桩疑难命案,主审官就疑似采用了城隍庙祈梦法。参见(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第2 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第793 页。因元代之前似未见类似记载,此案或可谓祈梦断狱之滥觞。又如明代成化年间,四川左参政黄绂即以祷城隍神祈梦的方式,发现并审断了一起僧人盗杀案。参见(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八十五,列传第七十三《黄绂》,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4897 页。在明代后期的一些小说中,此类祈梦断狱的描写始有所增多。清代各种文学作品中存在大量此类祈梦断案的描写。或有人会以为文学描写有诸多虚构成分在,不能代表现实。然而,文学往往源于生活,虽有艺术夸张或渲染,但也往往是现实的某种反映。事实上,除了诸多民间野史外,即使是官方文献也一本正经地记载着此种现象。〔2〕如后文提到的康熙年间广东巡抚朱徽荫破获的江洋大盗杀害舟客并剖腹沉尸之案。这种现象,即使在西方科学观念输入已久的光绪时代都时有发生,如《申报》就刊载过此类案件。〔3〕如光绪十六年四月十一日(1890 年5 月29 日)的《申报》第2 版记载一则题为《劫财害命》的案件新闻:安徽绩溪商人某甲经商外埠,三月初思归,结果回家途中与代肩人某乙在泾县黄梅岭被强盗所杀,后两人尸体被某丙发现并“赴泾县报验”。“包邑尊得信后,立即带同刑仵亲往验尸,验得确系被人杀毙,乃饬先行铁棺收殓,一面籖派干役四出缉拿。奈已及二旬,凶手仍无踪影。邑尊焦灼,特亲自斋戒薰沐,宿于城隍庙中祈梦,俾得明目达聪者之指示。无如连宿三夜,影响全无。”作为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标志,也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份报纸,《申报》对报道真实性十分重视,其创刊之日不仅将自己定性为“新闻纸”,还宣称“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4〕参见《本馆告白》,载《申报》同治壬申三月二十三日(1872 年4 月30 日),第1 版。《申报》对当时官员祈梦断案的报道,可视为不虚。不过,因这种祈梦断案之法,官方正规文献并不多载,今人怀疑其真实性也可理解。窃以为,官方文献并不多见,原因有三:一是此法过于神秘莫测,难以轻易把握,如官方宣扬,很可能影响地方官对案件公正司法的常态化追求,甚至有招致“不问苍生问鬼神”之讥;二是此法主要针对疑案而用,官方宣传可能导致官员对神道的滥用,从而妨害一般案件的正常司法;三是此法更多的是限于法官之个人经验,复制并非易事,难以上升为办案规律。但即便如此,在信仰城隍神的清代语境中,面临疑案山穷水尽之时,法官凭借此法仍时有发生。特别是被民间广泛传播更显神乎其神,反过来又推动了官员的效仿。可以说,揆诸诸种史料,司法官员在城隍庙祈梦,当是清代地方司法针对疑狱的一种现实常见做法。这个做法至少涉及这几个问题或范畴,即技术、证据与信仰。当某个案件陷入困境而一筹莫展之际,如何找到案件突破口,司法官就需借助某种技术手段,这个技术在清代往往是去城隍庙祈梦;如果祈到梦并又能得以有效解梦,那就既提供了疑案线索,又往往同时找到了证据进行定案;而通过这个司法技术去发现证据,又必然涉及对城隍神的信仰。事实上,在传统社会,技术、证据和信仰三者构成了地方司法解决疑狱的三大要素,此在清代尤为如此。
笔者注意到,虽然学术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城隍神信仰有很多著述,甚至也有一些专论城隍司法审判方面的成果,〔5〕此方面较早的专题研究当为日本学者增田福太郎的《台湾汉民族的司法神——城隍信仰的体系》(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99 年版)。国内法史界较具一定代表性的是范依畴的研究,如《世俗法律秩序缺憾的神祇弥补——古代中国城隍神信仰的法律史初释》(中国政法大学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民间司法公正观念的神话表述及其特征——明清文学中“城隍信仰”的法文化解读》(《法学》2013 年第1 期)、《城隍神“法司”角色及其对世俗法制缺憾的弥补》(《暨南学报》2013 年第9 期)。此外,赵娓妮、里赞的《城隍崇拜在清代知县司法中的影响》[《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6 期]专注于清代知县司法。近几年尚有几篇硕士论文进行了专题研究,如张洁玉的《城隍审判的类型化探析》(苏州大学2016 年硕士学位论文)、李雍的《中国古代的城隍“司法”——信仰、功能与社会秩序》(南京大学2017 年硕士学位论文)等。最近的研究有张成龙的《宋代司法符号中衙门、城隍庙及其互动的司法效果》[《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1 期]、张守东的《城隍神的构造原理:法律与宗教互动的古代中国经验》(《财经法学》2020 年第2 期)等。但遗憾的是目前似不见针对清代地方官员祈梦城隍庙进行司法断案的专门研究。这种祈梦城隍庙的司法做法,显然与一般性的城隍信仰以及城隍司法等现象有着差别且更为复杂。可以说,祈梦于城隍庙,除了是清代地方司法应对疑难案件以获取证据线索的一个重要技术外,还充分折射出司法审判与神道信仰的密切关系;当然也客观展现了司法取证与梦因心理机制的关系问题。因此,对清代地方疑狱审判中城隍庙祈梦现象进行针对性解析和研讨,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当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不仅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清代地方疑案司法运作的此种独特面相,而且有助于如何合理或客观地评价这种司法现象,并从中得到可能的启示。
二、作为司法技术的“城隍庙祈梦”之构成因素解析
(一)前提因素:疑案
清代较为流行的城隍庙祈梦,并不是司法官一遇案件就立刻尝试运用的一种司法技术,通常情况下是只有在疑案的前提下才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并非疑难案件,司法官通过自身的智慧和力量能够裁断的,就没有必要求助于城隍神,否则既体现了司法官员的无能,也表现出对神灵的滥用和不敬。只有当人本身的智慧用尽而案情依然不明,那此时求助于神灵,则既可体现出司法官员公正断案的尽责努力,又可显示出神灵的英明伟大。事实上,法的古体字“灋”中包含的那头“獬豸”独角兽,就是在作为人的法官(如皋陶)面对疑狱而智力枯竭之时,才展现其神奇的“以角触邪”的能力。〔6〕值得注意的是,独角兽能否真正以角触邪,与其独角朝向紧密相关。如果独角朝后甚至紧贴后脑头皮,则恐难完成触邪以实现正义。研究表明,獬豸独角朝向在明初即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之前历代塑像独角是直向前伸或至少向前倾,但明代开始遂全面朝后以至紧伏后脑,而其朝向变化则深藏玄机。参见方潇:《獬豸独角朝向关乎“权大”还是“法大”》,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11 月27 日,第 A07 版。可以说,神性独角兽的出场,喻示着求助神灵的前提——疑狱的存在。综观清代地方官员的城隍庙祈梦,几乎均为面对疑案“智力穷尽”时的兜底性技术选择。〔7〕当然,所谓的“智力穷尽”,当针对该司法官员的个人能力而言,以其主观努力为限,而非指向客观的人的智慧理应达到的程度。事实上,传统社会官员的断案智慧参差不齐,故在“智力穷尽”上亦各具特点。
(二)空间因素:城隍庙
司法官员祈梦于城隍神,当运作于特定的空间场所——城隍庙。城隍庙就是奉祀城隍神的庙宇,而这个城隍神也是当有塑像的。不过作为城池保护神,城隍受到祭祀,原无祠庙,也无塑像。南宋赵与时《宾退录》卷八:“州县城隍庙,莫详事始……芜湖城隍祠,建于吴赤乌二年。”〔8〕(宋)赵与时:《宾退录》,齐治平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103 页。《辞海》“城隍”条依此视芜湖城隍为“最早见于记载”的庙祠。〔9〕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第6 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87 页。芜湖城隍庙内供奉的城隍,乃汉初名将纪信,在楚汉之争中立下汗马功劳而战死,刘邦称帝后封为“匡侯”,并多处建祠纪念,后演变为城隍祠庙。〔10〕《嘉靖建阳县志》卷六《重建城隍庙记》:“城隍之祀,三代盛时未之有闻。至汉以纪侯初平江南有功,因祀之为城隍神。”载《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31 册),上海古籍书店1982 年重影印本,第65 页。又据南宋赵与时《宾退录》卷八,至宋供奉纪信的城隍庙很多,“神之姓名具者:镇江、庆元、宁国、太平、襄阳、兴元、复州、南安诸郡,华亭、芜湖两邑,皆谓纪信”。参见(宋)赵与时:《宾退录》,齐治平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104 页。可见城隍祠庙与塑像,当源于城隍由自然神向人鬼神的转变。唐宋以来,城隍庙的人鬼神祭祀愈益增多,去世的忠臣烈士纷纷进入祭祀行列。虽然明初朱元璋曾敕令以木主代替塑像,因此举未能考虑民间信仰传统,从而至明中后期各地出现重塑神像的高潮,但因明初二次城隍改制〔11〕第一次是洪武二年,敕令“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在历代所祀基础上重新封爵,京城、府、州、县城隍相应被封为王、公、侯、伯。第二次是洪武三年,诏令又革去了城隍封号,而只以某府、某州、某县城隍神称之。第二次可谓是对第一次的某种否定,其原因是朝廷内部儒教“理念派”压倒道教“惯习派”的结果。但两次改制的共同点均是将城隍全面上升到国家正祀地位,并在全国铺开。均强化城隍祭祀的国家正祀地位,从而使得城隍庙遍设天下各府州县甚至乡镇。〔12〕城隍庙的建制,其样式需按照州府衙门的款式而建造。清承明制,其城隍庙祀亦一应承袭,甚至更有发展。清代地方官员为断疑狱,特别是想达到成功,就必须来到这个神圣的空间场所,面对栩栩如生的神像进行祈祷,才有可能得到城隍爷的托梦。
(三)时间因素:夜晚
去城隍庙祈梦,有其特定的时间条件,即必在夜晚。为何选取夜晚?此与中国古人对夜晚的特定认识有关。按阴阳观念,白天属阳,夜晚属阴,生人属阳,人鬼属阴。故人鬼及人鬼之神惟有夜出,白日难见,此乃阴阳相隔之因。所谓人在白天活动,鬼灵在夜晚出没。〔13〕当然此亦非绝对。古人认为,在某种特定时空环境中,除了在夜晚容易碰到鬼外,人与鬼亦可在白天有所交集,即所谓“白日见鬼”。自唐宋以降,由于城隍的人鬼神化,故城隍神的显灵和出场,也基本在夜晚发生。正因如此,官员为断狱去城隍庙祈梦,必选择夜晚,才有可能与神灵交流,以便梦中得到神示。此外,选择夜晚祈梦,也是与古人对梦之认识有关。一般认为,梦是梦者灵魂外游与鬼神进行交往的产物,甚至就是梦者被动地接受鬼神的启示。〔14〕参见姚伟钧:《神秘的占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7-9 页。古人的生活秩序在时间上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做梦也基本发生在夜晚睡眠之时,而“白日做梦”往往被视为不可能发生之事。因此,选择夜晚祈梦城隍神,恰恰符合人鬼幽明两界的作息时间及其交集。〔15〕少数文学描写也见有白日做梦得到神示者,但似均体现为被动托梦,而非主动祈梦。
(四)身体因素:熏沐斋戒
司法官员欲祈梦城隍神,并非说去就去,而是必须先对自己的身体有个认真的打理。这个打理,就是熏沐斋戒。熏沐是将自己身体洗干净,也即沐浴更衣,并用香料涂身;斋戒是不吃荤〔16〕不能简单将“吃荤”与“吃肉”混同。实际上,道佛戒律中的戒荤,主要指向大蒜、葱、韭菜等一些气味浓烈、富于刺激的东西,为教徒所禁食。民间社会则将荤扩大至肉,甚至认为吃荤就是吃肉。不饮酒只吃素,并戒除身体的一切游乐欲望。这些当源于古人对鬼神的认识。古人认为,祭祀和祈祷鬼神,必须对鬼神持有虔诚的信仰和尊敬。信仰体现在内心,而尊敬则体现在外在的身体状态。古人认为,鬼神尤其那些正直的鬼神均为洁身自好者,甚至个个都是洁癖,它们厌恶肮脏,讨厌刺激腐败等难闻气味而惟喜好香味。〔17〕像传统休妻制度“七去”中的“恶疾去”,固是源于患病妻子的“不可与共粢盛”,同时也是因为祖先神灵的洁癖所致。祈祷或祭祀者熏沐斋戒,不仅使身体达到鬼神满意、接受的状态,还可使身体之精气神达至洁净专一,从而便于与鬼神进行有效交流。对神灵如此身体上的投其所好,正是对其尊敬的具体表现。作为大都由忠臣烈士充任的城隍,由其自身素质决定,其要求自然会更加严格。
(五)仪礼因素:焚香、跪拜、焚祝
司法官去城隍庙祈梦,除身体熏沐斋戒外,还必须在城隍神像前完成一系列祭祀仪礼。此可谓是祈梦的核心所在。焚香可谓是祈梦仪礼中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其目的除了除秽净气外,更在于使得香气达于空中,弥漫神庙空间,从而吸引和迎请神灵,供其品闻与歆飨,即所谓“香者,以通感为用,隔氛去秽”〔18〕《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七十一《镇十方香华》,载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35册),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428页。。焚香之后,官员即可竭诚祈祷,一般为心头默念,亦可写在纸上念出,祷词内容即为某案而来,请求城隍神相助云云。祷毕后,还需将祷词以文书方式焚化,其用意即将该祝文送达阴界,以便城隍神及时收悉。由于城隍等级对应于阳间官阶,故文书有不同称呼。向本地同级别城隍送达,用辞为“牒”;向低级别城隍送达,用辞为“檄”。〔19〕史料似未见向上级别城隍神进行焚文送达的情况。实际上,在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此种情况亦不大可能发生。《清稗类钞》“迷信类”即载有一则“官与城隍神较品秩”的有趣记载。参见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4780 页。官场如此,神也一样。除焚香、焚祝文外,虽然史料似未见祈梦官员向城隍行献爵与跪拜之礼,但据明清官员上任时祭拜城隍之仪,〔20〕如清代张鉴瀛《宦乡要则》卷二《赴任》:“献爵读祝,皆行跪礼。”参见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9 册),黄山书社1997 年版,第120 页。一个虔诚的祈梦官员亦当会行此大礼。至于献牲之礼,则主要体现在城隍祭厉活动中,〔21〕据《大明会典》卷九十四《群祀四·有司祀典下·祭厉·仪注》,祭厉时以本处城隍主祭,如为州县城隍,祭物用羊一、豕一;如为府城隍,祭物用羊二、豕二。参见《续修四库全书》(第79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634-635 页。笔者接触之史料似未见祈梦断狱者有此类献礼。在所有这些仪礼中,祈梦官员须拥有高度的虔诚之心贯穿始终。
(六)行为因素:夜宿城隍庙
可以说,夜宿城隍庙是官员祈梦的关键所在。经过前面一系列准备和仪式,现在该到了请求城隍托梦的时候了,但夜宿何处进入梦乡则较有讲究。为表达虔诚,祈梦官员一般均将夜宿城隍庙作为最佳选择。某种意义上,城隍庙就是城隍神的受祭家园,在城隍庙中夜宿祈梦,不仅可让城隍“足不出户”以示礼敬,而且在这种神圣空间更易做梦得到神启。虽然也有公案小说描写官员祈梦不夜宿城隍庙的情况,但并不发生于清代,并且可能有其他某种意义的表达。〔22〕如《包公传》第67 回“决袁仆而释杨氏”:“(包拯)次日斋戒祷于城隍司云:‘今有杨氏疑狱,连年不决,其有冤情,当以梦应我,为之明理。’祷罢回衙。是夜拯秉烛于寝室,未及二更,一阵风过,吹得烛影不明。拯作睡非睡,起身视之,仿佛见窗外有一黑猿在立。”(明)安遇时:《包公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年版,第257-258 页。笔者以为,包拯不夜宿城隍庙而祈梦成功,当是小说家突出包公高大形象所致。值得一提的是,为断狱祈梦而夜宿城隍庙,一般当然由主事官员本人亲力亲为,但也偶有命家丁、捕役或他人而为者。〔23〕如清毛祥麟撰《墨余录》卷十五《鲍老国》载:“会匪未乱之先,邑小东门外,沿濠负郭,……一日,濠边忽有一肢解尸,经官案验,而凶无从得。邑宰某,饬家丁祈梦于城隍神,梦神以木鱼袱包各一示意。”(清)毛祥麟:《墨余录》,毕万忱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238 页。
三、作为证据启示的“城隍庙祈梦”之司法效果分析
(一)如何解梦是司法效果成败的关键
司法官员夜宿城隍庙,其目的当然是期望城隍托梦给他,提供解决疑案的证据线索。但若果真祈梦成功,则如何解梦,将梦境神启转化为有效的证据线索并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因为史料表明,虽然“直梦”在古人多有发生,但就祈梦断狱方面而言,除极少数梦境会直截明白地指示出疑案证据外,绝大多数描写或记载则是间接乃至非常隐晦的情况。因此,如何正确解梦而领会神启,则是城隍庙祈梦断狱此类案件中决定司法成败的关键。
如何解梦实涉及中国古代的占梦文化。古人认为梦是“魂交”“魂行”的产物,预示着命运的吉凶和走向,早在周代就有专门的占梦官,并有了初步的占梦理论。《周礼·春官》云:“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曰思梦,四曰寤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可见占梦是观察国家吉凶、决定国家大事的一个重要手段,到了后世因社会广泛需求才演变成官民共享的迷信大餐。王符《潜夫论·梦列》曾把梦分为十类:“凡梦: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时、有反、有病、有性。”梦的繁杂使得占梦方法也显繁杂,不过归纳起来可分为“直解”“转释”和“反说”三类。“直解”与“反说”相对容易,“转释”则较复杂,视梦境不同而又有象征法、解字法、连类法、类比法、破译法、谐音法等之分。在司法官所祈之梦中,直接指引证据线索的“直梦”极少,一般均需要进行“转释”方有可能得到神启答案。如此,就需要解梦者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乃至术数知识。清代时期的司法官员,虽因八股取士而对法律不甚擅长,但四书五经的熏陶也令其有某种自信,故大都为自占其梦。当然,自己百思不得其解而求助他人(如上级、下级、幕僚乃至内室等)也不少见。不过,无论是自解还是他解,如果解梦方向错误,城隍的神启就起不到释疑的作用,有时甚至带来冤案的发生。可见,在此种断狱模式中,解梦成为关键并非虚言,如下例。
(二)祈梦断狱成功者举例分析
清代地方司官祈梦断狱成功的典型代表,当为蒲松龄笔下的“老龙船户”案。
朱公徽荫,总制粤东时,往来商旅,多告无头冤状。往往千里行人,死不见尸,甚至数客同游,全绝音信,积案累累,莫可究诘。初告,有司尚欲发牒行缉;迨投状既多,遂竟置而不问。公莅任,稽旧案,状中称死者不下百余,其千里无主者,更不知其几何。公骇异惨怛,筹思废寝。遍访僚属,迄少方略。于是洁诚熏沐,致檄于城隍之神。已而变食斋寝,恍惚中见一官僚,搢笏而入。问:“何官?”答曰:“城隍刘某。”“将何言?”曰:“鬓边垂雪,天际生云,水中漂木,壁上安门。”言已而退。
既醒,隐谜不解。辗转终宵,忽悟曰:“垂雪者,老也;生云者,龙也;水上木为船;壁上门为户。合之非‘老龙船户’耶!”盖省之东北,曰小岭,曰蓝关,源自老龙津以达南海,岭外巨商,每由此入粤。公早遣武弁,密授机谋,捉老龙津驾舟者,次第擒获五十余名,皆不械而服。盖寇以舟渡为名,赚客登舟,或投蒙药,或烧闷香,致诸客沉迷不醒;而后剖腹纳石,以沉于水。冤惨极矣!自昭雪后,遐迩欢腾,谣涌咸集焉。〔24〕(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十六《老龙船户》,俞驾征等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第576 页。
在此案中,针对大批商旅失踪疑案,朱巡抚虽“筹思废寝”“遍访僚属”,但也无头绪,无奈之下向当地城隍神祈梦。文中“变食斋寝,恍惚中见一官僚,搢笏而入”云云,即意谓夜宿城隍庙祈梦成功。因朱徽荫官巡抚,粤东城隍级别为低,故用词“檄”,城隍刘某亦“搢笏”见退。如何解释城隍“鬓边垂雪,天际生云,水中漂木,壁上安门”之梦语,就成为关键。经“辗转终宵”,朱巡抚终通过解字法正确解梦,从而破获审断该起大案,昭雪冤魂。
关于《聊斋志异》,因其多为离奇神鬼狐仙故事,人多以为蒲氏虚构。其实不尽然,有些故事实有其现实之本。就上述“老龙船户”案而言,实源于朱徽荫抚粤时之真实案件。在当时朝廷予以表彰宣传的《各省士民公启》中有云:“巡抚广东朱大人,于丁卯仲冬,朝廷特简抚粤……乃公特虑粤东江滨海港,为害最深,船贼以驾船渡载为名,肆行谋劫:或烧闷香,或下蒙汗药,满船客商,眼睁不能言,手软不能动;被贼勒其咽喉,缚其手中,刳肠纳石,沉尸于水;即閤船多人,无一脱者,赀财行李俱被卷掠。踪迹诡秘,人不得知,亦无从查察。伤哉无辜,而罹此祸!……即告发,亦无影响物色。公阅案卷,食不下咽,寝不安枕,昼夜筹策,乃焚香告天,于十月望日,诚心斋洁,复移牒城隍。神鉴公忠诚,随示梦于公,始知凶恶者即‘老龙船户’也。臬司沈公,捐赀悬赏,多方购兵,共获凶党五十余名,俱不刑自认。其非公视民如伤之心,所以感格至此乎!”〔25〕朱一玄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322 页。此布告虽未记蒲氏笔下那种城隍梦语及如何解梦之情节,但城隍直接将“老龙船户”示梦于朱公似也不大可能,可推蒲氏之解梦深描恐非虚言。
另一个较为典型的成功案例,或为清人许奉恩《里乘》中的一个谋杀亲夫案:
倪公春岩廷谟,由进士出宰吾皖潜山县。廉明公正,四民爱戴,皆呼之曰“倪青天”。公尝于冬月有事至乡,忽有蝇成群飞缭舆前,左右挥之不去。意时方苦寒,那得有此?得勿冤鬼作祟耶?因默祝如有冤屈,蝇当导我为之伸冤。祝毕,蝇果群飞前导,不里许,路过一山,旋风骤起,将群蝇卷入山中。公急命停舆,自徒行入山迹之,步上山凹,见一坟新筑,湿土未燥,群蝇栖集其上,心益惊异。比呼亭长问,知为前村某甲新冢……乃命舆径至甲家,直升其堂,召其妻出见问话……公心终不释,乃执意开墓启棺检验,以决其疑……甲尸以天寒丝毫未曾腐坏。伍伯承公意旨,由首而足,由腹而背,细意检验,竟无微伤,惟骨瘦如柴,确系病瘵而死。公无奈何,只得仍命盖棺封墓……公已具文上请,复自踵谒大府,面陈梗概……公请展限三月,当密加访察,如真不得确耗,甘罪无悔。大府许之。公旋任,路经城隍庙,式舆默祝,祈神示梦。夜果梦城隍神遣人赠万年青草一盆,惊寤,不解所谓。〔26〕(清)许奉恩:《里乘》卷八《倪公春岩》,文益人等点校,齐鲁书社1988 年版,第270-272 页。
倪县令为解城隍所托之梦,百思不得其解,遂打扮成卜人下乡访察。一日在河滨向一形似壮年的垂钓渔人问路而与其相识。在交谈中得知该渔人姓万,实已六十四岁,里党因其“不形老态”,故都叫他“万年轻”。县令闻“万年轻”三字,顿忆前梦,因而言语相诱相激,渔人终将其所知之秘情告知。原来渔人有赌习,一次大输,遂夜去某甲家偷窃,在伏窗潜窥中骇然发现甲妻与另一男子共同用蛇入肛门方式杀死卧床之甲。最终倪县令以此线索审断此案,“遐迩闻之,无不称快”。在解梦过程中,因城隍托梦中的草盆“万年青”与渔人姓名“万年轻”音同,县令因而用谐音法解梦,顺藤摸瓜,从而成功获得证据线索。作者借“里乘子”之名评价说:“公自筮仕吾皖,历宰剧邑,所断奇狱甚多,皖人至今犹津津乐道之。其最著者,莫如某甲之狱。好事者已谱入传奇,播之管弦矣。”〔27〕(清)许奉恩:《里乘》卷八《倪公春岩》,文益人等点校,齐鲁书社1988 年版,第274 页。按此说法,此案可为不虚。〔28〕按:《里乘》虽为小说作品而固然有虚构成分在,但作为一部“以备劝惩”之作,作者尽量将亲历、亲见、亲闻之事“实事求是”,以避免小说家言的四种流弊(序三,第3 页);而在作者“说例”中尤强调“是书多系实事”(第11 页)。
清代还有其他诸多祈梦城隍神成功断案的记载。如《清稗类钞》记,康熙时某布商“失橐金三百两”,时上海县令为任待庵,虽平素善谳,却对此案一筹莫展。“因诣城隍庙祷之,请神以实告,乃留捕之随往者,使待命于神寝宫。入夜,捕梦寝官有幼妇出,右手抱细女,左手挈衣与之,及接视,则裙襕也。”任县令经对此梦再三研析,终得“裴爱”之义,“遂收裴,拷之得实”。〔29〕(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七册《明智类·任待庵悟盗金者为裴爱》,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3333 页。又如《青楼梦》记余杭县令金挹香讯鞫王小梧谋害蒋氏子案,“形迹无稽”,“踌躇良久,忽然想着了本县城隍十分灵感,何不今夕往祈一梦,或可明白,以结其案”。于是“斋戒沐裕,到了二更时分……向城隍庙而来”。“挹香拈了香,暗暗的通诚一番,然后就寝。到了三更,梦见六个人手中都捧着牙笏,在那里朝拜灶君。俄而六人席地坐下,在那里诵读灶经。”经夫人点拨,解梦为“陆笏君下毒”,于是令差役拿获陆笏君到案。差役最终偶然在一酒肆中拿获一名为“陆笏臣”的人,审问之下,案情大白。〔30〕(清)俞达:《青楼梦》第53 至54 回,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第200-203 页。又如《施公案》记阜宁县令颜继祖审杨大富中毒暴毙一案,穷究无奈下只好去“宿庙求神”,“用过晚膳,便斋戒沐浴更衣,带了一个书僮……直往本邑城隍庙而去。入庙以后,焚香点烛祷告一番。然后就命书僮将铺盖在大殿上打开……书僮去后,颜县令即就大殿旁侧睡下,以觇梦示”。当夜城隍托梦一首七绝:“紫荆花下碧栏边,正是江南春暮天。有酒一樽鱼一尾,陶然醉卧便神仙。”颜县令不解此梦,遂公文请示施公,施公偶看医书,方得诗解,原是“荆芥花与鲫鱼同食毒毙”之隐义,最后才公正顺利结案。〔31〕(清)佚名:《施公案全传》第315-321 回,延边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133-1155 页。再如《申报》载邗江小白大被刺殒命一案,因尸亲日日至甘泉县署号泣,县令朱明府亦急欲破案,“屡宿邑庙(即城隍庙)祈梦,夜间更私服微行,细访一切。一夜独宿庙内,梦中恍惚闻人言‘弓匠王干’四字。次日侵晓,即另签健快,指各密拿。该快误拿地棍王淦到案,鞫之,坚不肯承。明府忆梦中有弓匠之说,因又派差再访,果于教场大瓦砾堆前弓箭店内,获得王干其人者。两将伊扭住一问,即吐实,云与小白大争风仇杀”。〔32〕《申报》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三日(1884 年7 月15 日),第2 版,“破家彚志”栏目。
(三)祈梦断狱失败者举例分析
不过,祈梦断狱并非都能成功,也有一些失败的案例。这些失败,从史料来看,有的是对城隍所托之梦终不能解,因而对最终断狱没有产生实质价值;也有的是不能正确解梦,解梦方向和内容错误,使得案件越审就越进入死胡同。
袁枚《子不语》中就记载一则司法官员不能解梦而无益于断狱的事例:
四川茂州富户张姓者,老年生一儿,甚爱之,每出游,必盛为妆饰。年八岁,出观赛会,竟不返。遍寻至某溪中,已被杀矣,裸身卧水,衣饰尽剥去。张鸣于官,凶手不得。刺史叶公,身宿城隍庙求梦。夜梦城隍神开门迎叶,置酒宴之。几上豆腐一碗,架竹箸其上,旁无余物,终席无一言。叶醒后解之,不得其故。后捕快见人持金锁入典铺者,获而讯之,赃证悉合。其人姓符,方知竹架腐上成一“符”字。〔33〕(清)袁枚:《子不语》卷十八《豆腐架箸》,崔国光校点,齐鲁书社2004 年版,第341 页。今人常以为《子不语》仅为志怪小说而视为虚构,此实为表象之误读。实际上,其记载的奇闻异事,还是有许多可信之处,甚至部分内容就是客观事物或现象的直白叙事;即使看似荒诞的鬼神故事,也多是对现实生活中真实原型的虚构和夸张。此主要得因于其材料来源有诸多可信之处。研究表明,《子不语》故事来源有四:一是“得之传闻,名言其亲朋好友所述”;二是“袁枚的亲身和经历目睹”;三是“得自官方的公文邸抄”;四是“来自文献史料和前人著述”。参见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290 页。
叶刺史虽身宿城隍庙求梦成功,但对城隍所托之梦“豆腐架箸”终不得解。后来还是通过捕快智慧抓获凶手,从而审断此案。虽然“其人姓符,方知竹架腐上,成一‘符’字”而梦解确认神助无误,却也是马后炮或事后诸葛,于该案最终审断没有本质关联,实为失败。
不过上述杀人案,幸亏叶刺史梦不得解,如果胡乱解梦,说不准不但真凶难获,而且很可能冤及无辜。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曾转述其“从伯灿臣公”讲的一个案件,就反映了官员错误解梦后的严重失败恶果:
曩有县令,遇杀人狱不能决,蔓延日众。乃祈梦城隍祠。梦神引一鬼,首戴磁盎,盎中种竹十余竿,青翠可爱。觉而检案中有姓祝者,祝竹音同,意必是也。穷治亦无迹。又检案中有名节者,私念曰:“竹有节,必是也。”穷治亦无迹。然二人者九死一生矣。计无复之,乃以疑狱上,请别缉杀人者,卒亦不得。〔34〕(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四《滦阳消夏录(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64-65 页。今人常将《阅微草堂笔记》视为虚构之志怪小说集,也是误读。已有研究表明:“如果我们沿着乾嘉学术的脉络和立场,从纪昀对‘子部小说家类’的认识与判断角度来看,《阅微草堂笔记》就不是一部文学虚构性的小说,而是传统学术体系中的子部之学。”参见王昕:《论乾嘉学风与志怪“小说”——以〈阅微草堂笔记〉为线索》,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5 期。
纪昀生活的时代已距清立国百年,所谓“曩有县令”,按其语境,不应久远,而当发生在纪昀之前的某个清代时空。该县令遇杀人疑狱,无法审断之下只得向城隍庙祈梦。显然县令先用的是占梦中的谐音法,据梦象竹,而推测是案中姓“祝”之人。失败之下,接着又用连类法,因为竹子有节,推测是案中名“节”之人,再次失败。看来该县令解梦已是山穷水尽,最后以疑狱上报。只是可怜那两个被误解怀疑的人,在经历种种刑讯逼供后已是九死一生了。正因如此,纪昀对此种祈梦断狱进行了全面否定。纪昀的观点后将详论,此处不述。
当然,司法官员去城隍庙祈梦,并非必然就能祈到梦,宿而无梦者也有发生。如光绪十六年(1890年),安徽商人某甲回家路上与代肩人某乙一起被杀,泾县县令包某缉拿凶手二旬无果,十分焦灼,“特亲自斋戒薰沐,宿于城隍庙中祈梦,俾得明目达聪者之指示,无如连宿三夜,影响全无”。〔35〕《申报》光绪十六年四月十一日(1890 年5 月29 日),第2 版,《劫财害命》。包县令去城隍庙连宿三夜,可见其诚意颇深,然而并没有祈得一梦,可谓非常失败。又如光绪十九年(1893 年),常熟徐庄钱润甫之妻及佣妇被劫财杀害一案,县令朱大令“勘验饬缉”,先是将疑犯钱侄福森拘捕,然“叠次刑讯,坚不认承”。于是,“善以神道设教”的朱县令“虔诣城隍庙拈香祈梦”,然“毫无应验”;又“于深夜设案庙中大殿,与城隍神并坐讯鞫福森”,福森仍“一味叫屈”,还是无法审明。〔36〕《申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1896 年4 月29 日),第2 版,《案有端倪》。
(四)诈梦断狱的司法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祈梦断狱的司法流行风中,有意思地出现了司法官诈梦断狱的现象,此可归入“用谲”之类。这种现象的动因,当是建基在当事人及民众对祈梦本身的某种迷信上。当然,诈梦断狱也纷呈复杂,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员的确曾赴城隍庙祈过梦,惜未能祈到,但在判案时则诈称祈梦成功,神启如何;另一类是官员并未祈梦城隍庙,为图审案便捷顺利或某种目的,故意在堂审时诈称城隍托梦。这两类诈梦断狱,往往会体现出不同的司法效果。
第一类诈梦断狱的案件代表,当可推张静山断一争坟案。许奉恩《里乘》卷八载:
滇南张公静山观察其仁……道光乙巳夏,以蓬州牧特擢新安太守。甫下车,有两姓争坟互控者。稽核旧牍,自嘉庆甲戌年兴讼,至是已三十余年矣。公诧问书吏:“何迟久不能判断?”书吏对谓:“此案每新太守莅任,例来互控,缘两姓俱无契据,无从剖决,只合置之不理。”公叱曰:“天下岂有三十余年不结之案!”立命传谕两姓,五日后登山验看,听候判断。翌日,公沐浴斋戒,祈祷城隍,夜宿庙中,求神示梦。五日后,亲自登山讯断。两姓俱至,一姓系望族,其人纳资以郡丞候选……一姓系老诸生……公大声谕之曰:“汝两姓为祖兴讼,历久不懈,孝思可嘉。惟闻自经具控,彼此阻祭,为汝祖者,毋乃馁而实甚,汝心安乎?”两姓皆伏地稽颡,唯唯请罪。公笑曰:“吾稽旧牍,见汝两姓各执一说,皆近情理,所恨两无契据耳……非求神示梦,究不能决。昨特沐浴斋戒,祷宿城隍庙中,果见神传冢中人至,自称为某某之祖,被某某诬控,求我判断,我已许之矣……”……于是阄拈,老诸生居先,郡丞次之。老诸生乃勉整敝冠,次且走伏墓前,草草三叩首毕,起身干哭,颜色忸怩,口中喃喃,不解所谓。公笑谓郡丞曰:“渠已别墓,次当轮至汝矣。”郡丞闻言,涕泪泫然,乃侧身伏拜墓前,大声泣曰:“子孙为祖宗兴讼多年,不辞劳苦。今郡伯祷神得梦,一言判断,究不知真伪,可否不谬,倘所梦不实,为子孙者,此后不能与祭矣!兴念及此,能勿悲乎!”言毕,痛哭卧地,晕不能兴……公笑谓众曰:“观两人别墓情形,真伪是非,汝众人当其喻之,尚待吾明白宣示乎?”……因共赞郡丞为真孝子,而不直老诸生……公谓老诸生:“汝别墓情形,众目共见,抚心自问,尚有何说?”老诸生汗流满面,自称知罪……公乃亲笔书判,令两姓画押。三十余年难了葛藤,一旦斩绝,众口称快。〔37〕(清)许奉恩:《里乘》卷八《张静山观察折狱》,文益人等点校,齐鲁书社1988 年版,第277-279 页。
在这一案件中,可见张太守为解疑案而的确夜宿城隍庙祈梦了。不过,张太守果真如审案时自言已得到城隍托梦吗?实质不然。当年秋天,张主持郡试,延请作者(许奉恩)校对试卷,在酒席间得知此案而“叩公祈梦城隍,究竟果得梦兆否”时,张笑着说:“此姑妄言之耳。吾思两姓既无契据,只合令其别墓,以察其情形,果系真子孙,自有缠绵难舍之状;否则出于勉强,仓猝间难以掩著矣。大抵人即无良,于稠人广众之前,断未有甘心厚颜而真忍以他人之祖为祖者,天良未尽梏亡,只在此刻,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也。吾悬揣此情,姑托言神梦以微察之,不谓果以此而竟决是非真伪也。”〔38〕(清)许奉恩:《里乘》卷八《张静山观察折狱》,文益人等点校,齐鲁书社1988 年版,第279 页。可见,张静山虽有祈梦之举,却无祈梦之实。但因其审案时做得天衣无缝,更能揣度人情,诈梦断案竟获奇效!
第二类诈梦断狱的典型代表,或可推《施公案》中施公堂审王开槐被杀一案:
施公随即恭坐大堂,悉心复讯。先问王李氏道:“本部堂昨已住邑庙求神示梦,已蒙城隍神明示清楚:尔丈夫王开槐,与尔女秀珍,实系尔与武生同谋,一并毒死。尔尚有何言抵赖?可从实招来!”只见李氏说道:“大人明鉴,小妇人丈夫,实系暴病身亡,委无谋害情事……若果真是谋害死的,难道县大老爷与小妇人也有什么奸情,有伤反说无伤,有心袒护吗?”施公听说,大怒……差役答应,随将王李氏拖翻在地,将夹棍在腿上夹起……只见李氏大声哭道:“小妇人实被冤枉!”施公便命松了……〔39〕(清)佚名:《施公案全传》第211 回,延边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754 页。
到次日,将那个著名老仵作金标叫来,望他说道:“本部堂昨夜梦城隍神示兆,说王开槐实是中伤致命。尔亦明知其情,有意蒙混。本部堂定将尔照知情不报,得贿卖放例,加一等从重治罪。”那金标正欲辩白,施公不由他分说,忙喝道:“毋许多言,速速前去!若三日验出,本部堂重重有赏。”金标不敢再说,且先行回去……〔40〕(清)佚名:《施公案全传》第212 回,延边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756 页。
上述两则材料中,第一则施公明确自述昨已夜宿城隍庙求神示梦,第二则施公自述虽未明确,但很可能是作者为文字修辞避免重复故而行文简洁处理,且照上下文逻辑看也应一致。这就是说,无论对王李氏还是对老仵作,施公均信誓旦旦强调其已夜宿城隍庙祈梦并得神示。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呢?虽然施公之前曾因他案赴城隍庙祈过梦,但在此案上则根本未有此为,实为诈梦。其结果是均未起到任何作用,甚至第二则材料还反映了施公诈梦的某种心虚。按中国古人对神的虔诚信仰看,此类诈梦或许已构成对神灵的亵渎,又怎可对被诈者产生作用呢?实际上,除了此种声称已赴城隍庙求梦诈审外,《施公案》还有种仅诈城隍神托梦的情景:“彼此商议许久,那幕友道:‘据我看来,必得先将那少妇提案,就硬说是她丈夫吴其仁的阴魂,在城隍庙前控诉尔谋死亲夫,城隍神托梦,请本县审断,先诈一诈她,看她如何情形,再作商议。’……山阳县把惊堂木一拍,大声喝道:‘好大胆的淫妇,尔敢谋害亲夫!本县奉城隍神托梦,说尔亲夫在城隍神前,告尔谋害身死,饬令本县提尔到堂,彻底根究,代尔亲夫申雪……若不从实将奸夫招出,本县定用严刑拷你!’”〔41〕(清)佚名:《施公案全传》第243 回,延边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867-868 页。此种诈梦最终效果如何?虽然以严刑恐吓,结果不仅被吴何氏识破“谬言神来托梦”,而且还将山阳县驳得哑口无言。看来没有任何城隍祭祀的纯粹诈梦,其司法效果似全面失败。
四、作为信仰支撑的“城隍庙祈梦”之历史价值分析
(一)祈梦本身与内容纯属巧合还是有某种可能乃至必然?
笔者检阅史料发现,清代地方官员遇上疑案而去城隍庙夜宿祈梦,祈到梦或被托梦的机率相对较大,似只有少数才无功而返;同样,所祈之梦的内容也往往对案件的关键证据或线索有指引或暗示意义,无意义的梦境也基本不见。当然,如此面貌当很可能有书写者描述上的局限,比如有些无效祈梦被有意漏网,或者有些祈梦是夸张甚至虚构或附会。但须承认的是,清代地方官赴城隍庙祈梦以断疑案,的确是清代地方司法的一个特色,而并非仅是诉诸文学作品对现实司法腐败无能的想象救济和精神弥补。〔42〕如范依畴就认为,城隍神话的法律文化价值,就在于世俗法律秩序的缺憾需要宗教神话式的精神弥补。参见范依畴:《城隍神“法司”角色及其对世俗法制缺憾的弥补》,载《暨南学报》2013 年第9 期。笔者认为,此论对城隍亲自执法与司法之神话而言当然对,但对于祈梦城隍庙而言则不太适合。如果祈梦总是无效,官员祷神城隍庙也就没有了积极性或市场,更不可能作为司法经验而被模仿,同时民间传播也就没有了动力。因此可见,无论祈梦断狱现象记载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局限性,它就在那里。那么问题是:祈梦本身及其内容,到底是纯属巧合,还是有其一定的可能乃至必然呢?笔者认为,虽不排除其有一定的巧合或偶然,但某种程度的必然性也可能往往存在。此可从官员那种浓厚的城隍信仰,以及在此基础上“梦的发生机理”得到一定解析。
信仰总会影响乃至决定人的思想和行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浓厚的鬼神信仰,除极少数无神论之“另类”外,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一能免,而城隍信仰正是传统鬼神信仰中极重要的一环。自宋代某些城隍被列为国家正祀,〔43〕唐代李阳冰曾在《缙云县城隍神记》中说:“城隍神祀典无之,吴越有之,风俗水旱疾疫必祷焉。”任继愈主编:《中华传世文选·唐文粹》,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740 页。可见,在唐代的礼典中是没有祭祀城隍神的明文规定的。宋代则为之一变,宋人赵与时说:“今其祀几遍天下,朝家或锡庙额,或颁封爵。”(宋)赵与时:《宾退录》,齐治平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103 页。特别是经明初朱元璋两次城隍改制后以至于清,城隍信仰及其祭祀已全面纳入国家祀典体系,并成为国家管控民间社会和信仰的主导,城隍的职责也从地方保护神扩展到地方冥界主管和法司。朱元璋曾亲撰“祭厉”活动的《祭文》作为规范性摹本发布全国,其内容充分体现了朱元璋欲利用城隍“鉴察善恶”以达治民治官的目的。〔44〕其中有云:“仍命本处城隍以主此祭……凡我一府境内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亲者;有奸盗诈伪、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压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损贫户者,似此顽恶奸邪不良之徒,神必报于城隍,发露其事,使遭官府。轻则笞决杖断,不得号为良民;重则徒流绞斩,不得生还乡里。若事未发露,必遭阴谴,使举家并染瘟疫,六畜田蚕不利。如有孝顺父母、和睦亲族、畏惧官府、遵守礼法、不作非为、良善正直之人,神必达之城隍阴加护佑,使其家道安和、农事顺序,父母妻子保守乡里。我等阖府官吏等,如有上欺朝廷、下枉良善、贪财作弊、蠹政害民者,灵必无私,一体昭报。如此,则鬼神有鉴察之明、官府非谄谀之祭。”参见《大明会典》卷九十四《群祀四·有司祀典下·祭厉·祭文》,载《续修四库全书》(第79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635-636 页。为强化监察官吏,突出神道设教,明代开始要求地方官上任时,必须先赴该地城隍庙斋宿、拜祭和宣誓,〔45〕明人叶盛《水东日记》卷三十《城隍神》载:“(洪武)四年,特敕郡邑里社各设无祀鬼神坛,以城隍神主祭,鉴察善恶。未几,复降仪注,新官赴任,必先谒神与誓,期在阴阳表里,以安下民。”(明)叶盛:《水东日记》,魏中平点校,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297 页。并且每月朔望还须率僚属前往上香谒礼。清代则继承明代关于城隍“鉴察善恶”思想,并对官员赴任与在任致祭城隍制度予以完全沿袭,〔46〕如《福惠全书》卷二《蒞任部·入境》:“于上任前一日或前三日至城隍庙斋宿,谓之‘宿三’。”《蒞任部·斋宿》:“斋宿例于城隍庙。……先一日,预拟誓文,端楷书就,授礼生。俟谒神时,礼生展读焚化。”(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周保明点校,广陵书社2018 年版,第28-29 页。实际上,清代很多官箴书均明确并详细记载了新官赴任这一重要的仪制和程序。甚至为汉化统治需要进行强化,如还形成了离任也需拜辞城隍的惯例,以表对城隍的礼敬。〔47〕如清人张泰交《受祜堂集》卷二《为邑上·离任辞城隍神》有云:“职今去矣……但回念受事之初,焚香告神,誓词历历,有如昨日。今去矣,敢一梘缕,以复神命……初誓之词,曷敢忘之?……职志毕矣,惟神有灵……兹束装就道,一叩神前,以白初终,以当辞别。”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第5 册),三晋出版社2010 年版,第94-95 页。因此,在鬼神信仰的大环境下,在国家强化正祀的气氛下,尤其在官员赴任、在任乃至离任的频频祭祀中,城隍信仰不仅成为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更是成为官员理政治民的精神支撑和解决疑案的最终路径依赖。
对梦的理解,虽然古代也有像王充之类唯物思想家的批判,但“魂行”观念却一直大行其道,流行迄清末甚至民国。人们普遍认为,梦是睡眠者游魂与外在神灵的交往产物和表现,而梦境则往往兆示出命运或事件的祸福吉凶和未来走向。清代地方官员(包括捕快等)因笃信城隍神灵及其司法力量,当遇上疑案而一筹莫展之际,向城隍神求助托梦也就理所当然,而斋戒夜宿祠庙以礼敬城隍,就是求得托梦的最佳选择。应该承认,此种方式的祈梦实践当多多少少有所收获,否则就不会流行,史料再有水分也可侧面反映。此种方式的祈梦成功事例,又必进一步推动这种方式,并强化了各类司法人员那种惟有对城隍神灵充满礼敬才能得到神灵示梦的观念。〔48〕如光绪八年十月十三日(1882 年11 月23 日)的《申报》第3 版记载一则题为《差役祈梦》的新闻:某姚姓家婢女在沪北静安寺附近伤毙,知县饬捕役柴樛访拿。“该役毫无头绪,殊难捕风捉影,随商之十二铺地甲,于前夜同至城隍神前,焚香点烛乞梦指迷。睡至夜半,毫无动静,因复燃香烛跪祷,再睡,俄而已入南柯郡矣。然梦境迷离,二人又各不相类。及黎明焚香虔祷,求得谶诗,有‘寻人须在水道中’之语。闻该捕役前因姜衍泽药铺盗案急难破获,曾祈梦而效,故此番复求神助耳。”
不过,这种必有神灵参与其中的祈梦观念、行为和结果,虽然在清代地方官的观念世界里被视为“真理”,但客观而论,则未必不能以“反神灵”的梦理论进行某种“科学”色彩的解释。人们或以为“反神灵”的梦理论只是近现代科学的产物,典型如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但事实上从医学角度看,此论在中国古代社会至迟在西汉就已出现。如最迟成书于西汉的中国医祖经典《黄帝内经》,其在否定鬼神的基础上,〔49〕《素问·五藏别论篇》:“凡治病……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素问·宝命全形论篇》:“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道无鬼神,独来独往。”对梦进行了生理病理上的分析。〔50〕《黄帝内经》从生理病理上释梦,主要体现在《素问·脉要精微论篇》《素问·方衰盛论篇》与《灵枢·淫邪发梦》三篇中。《灵枢·淫邪发梦》云:“正邪从外袭内,……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所谓“正邪”,即指能够刺激身心正常活动的各种因素,如情志欲望、劳逸等。〔51〕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注:“凡阴阳劳逸之感于外,声色嗜欲之动于内,但有干于身心者,皆谓之正邪。”(明)张景岳:《类经》卷十八《疾病类》,载李志庸主编:《张景岳医学全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 年版,第336 页。可见《黄帝内经》将梦视为心神受到情志等因素的刺激而在睡眠状态下导致的一种“魂魄飞扬”,与阴阳盛衰及营卫运行有关,是人体生理或病理的表现形式。至东汉,从精神层面“反神灵”的梦理论更为突出,并首先出现在个人思想中。王充可谓是最早对神秘占梦术进行批判的思想家,他深受《黄帝内经》的影响,有着丰富的医学思想,〔52〕参见郭洪涛:《论王充的医学思想》,载《中医文献杂志》2003 年第2 期。不仅以“精神依倚形体”的观点批驳“魂行”说,而且还从生理病理特别是心理方面,去解释梦产生的原因及梦中遇见鬼神的问题。这个心理方面,就是“精念存想”。所谓“精念”就是精神上的一种思念,“存想”就是总会神经质或专注地想着某个东西。王充认为,“精念存想”必定会有所外泄,如白天可能“活见鬼”,晚上睡觉就会梦见白天总是想着的那个东西,如果白天总害怕,晚上还会梦到鬼。〔53〕《论衡·订鬼篇》:“夫精念存想,或泄于目,或泄于口,或泄于耳。泄于目,目见其形;泄于耳,耳闻其声;泄于口,口言其事。昼日则鬼见,暮卧则梦闻。独卧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惧,则梦见夫人据按其身哭矣。”(汉)王充:《论衡》,陈蒲清点校,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88 页。东汉另一位进步思想家王符,也受到《黄帝内经》的影响,对梦相迷信进行批判,并从精神心理因素对梦因进行一定揭示。他将梦分成十类,其中“精梦”和“想梦”虽名有异称,但可谓都是“昼有所思,夜梦其事”的结果。〔54〕《潜夫论·梦列》:“孔子生于乱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梦之。此谓意精之梦也。人有所思,即梦其到;有忧,即梦其事。此谓记想之梦也。”“凝念注神,谓之精;昼有所思,夜梦其事……谓之想。”(汉)王符著,张觉校注:《潜夫论校注》,岳麓书社2008 年版,第363、367 页。可见,以《黄帝内经》为医学源头,以王充和王符为代表的基于情志心理因素的梦因解说,其实就是受过科学熏陶的现代人常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与弗洛伊德关于“梦是对欲望的满足”的释梦理论,〔55〕[奥]弗洛伊德:《释梦》,孙名之译,商务印书馆2002 版,第119-129 页。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欲望在梦中的表现,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有时则以相反的形式出现。虽然现代心理学、脑医学等进一步深化了梦的机理,但在核心理论上仍未超越弗洛伊德。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差别。〔56〕参见梁绮婷等:《〈黄帝内经〉释梦与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理论融汇》,载《光明中医》2013 年第9 期;Ho Kan Au & Zhang-Jin Zhang:《传统中医解梦与弗洛伊德释梦之异同及其临床意义》,载《世界睡眠医学杂志》2018 年第1 期。人的“精念存想”或“昼有所思”不就是一种“欲望”吗?
回到清代地方官夜宿城隍庙祈梦这个话题上,实质就是官员在执着情志刺激下“精念存想”和“昼有所思”而产生的“潜意识”活动结果。赴城隍庙祈梦断狱,往往是司法官员智力枯竭下的不得已选择。在夜宿庙祈梦之前,可以想见,为获得证据线索,他研鞫案情而“精念存想”不知凡几。而赴城隍庙求神示梦,是出于对城隍神灵及其巨大法力的虔诚信仰,更是加强了对城隍托梦及内容的渴望,再加上那一套焚香祷告仪式,关键当夜就睡在城隍神像旁边,那种“精念存想”的“欲望”实已达到一种极致状态。因此,从梦的精神心理机制看,官员祈到梦或得城隍托梦的概率,无疑是较高的,从而具有一定甚至较大的必然性。就梦境具体内容而言,其能够对疑案的证据或线索具有指引或隐示意义,既有巧合性也有必然性。司法官对疑案往往有过长期思考和研判,是久审不决情况下才去寻求城隍托梦。因此,梦境内容当不排除司法官之前曾长期思考与研判而形成的某种潜在推理因素或信息。这些因素或信息,司法官之前很可能有所触及,只不过因为零碎或念头闪过未能有效捕捉等,而难以形成一定的证据线索,但是却都在官员的“潜意识”里贮存起来,而在他虔诚地夜宿城隍庙祈梦之时,那些潜伏的因素或信息就很可能被激活,并成为一种向城隍诉求的欲望,最终借助城隍托梦的方式在梦境中得以体现。可见,无论是祈梦本身还是内容,无论是“精念存想”还是潜在意识,在发生机理上其实都是如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梦是欲望的满足”,具有发生上的某种客观现实性。
而更重要的是,虽然清代官员笃信他们祈梦是源于城隍所托及神启,不知其实另一种“反神灵”的释梦理论更能科学合理地解释,但事实不管怎样,我们无法全面否定祈梦断狱的某种有效性甚至必然性。诚如台湾著名文化学者王溢嘉所言:“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在梦中获得破案线索的情节,并非‘纯属捏造’,因为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它其实就是我们在梦中所显现的‘潜意识智慧’。荣格认为,梦是潜意识的活动,而潜意识比意识具有更宽广的视野,常能为我们褊狭的意识(也就是白天的想法)带来‘补偿’或‘启示’。”〔57〕王溢嘉:《中国文化里的魂魄密码》,新星出版社2012 年版,第127 页。无疑,这一说法较为契合人类的精神心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二)如何看待纪昀对祈梦断案的否定性评价?
虽然对祈梦、占梦之类,中国古人早就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是就针对官员夜宿城隍庙祈梦断狱之事,似只有纪昀进行过否定性评价,而其他无见。这种否定性评价见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之《滦阳消夏录(四)》中。纪昀在记述某县令因杀人疑案而祈梦城隍庙,根据谐音、连类法对梦“竹”进行解读仍无法成功断狱,却导致两个无辜者九死一生的故事后,〔58〕具体内容请参见前第34 注之正文引文。愤愤不平,从而道出了如下的话语评价:
夫疑狱,虚心研鞫,或可得真情。祷神祈梦之说,不过慑伏愚民,绐之吐实耳。若以梦寐之恍惚,加以射覆之揣测,据为信谳,鲜不谬矣。古来祈梦断狱之事,余谓皆事后之附会也。
读着这样的话语,我们似乎看到纪昀拍案而起而义愤填膺的样子和表情。的确,纪昀虽然机敏圆滑,但为人正直,这样的文字正是一种反映。可以肯定,对于纪昀做出的这段评价,想必只要受过基本科学教育的现代人阅读之后均会为之点赞,并对这种出现在神灵弥漫时代的先锋思想敬佩不已。笔者也同样拍手叫好,击节称赞。不过,随着对清代祈梦断狱现象的深入认识,对纪昀这种全盘否定性评价始有一种保留态度。笔者认为,纪昀的评价虽有可取之处,但总体上似缺少对祈梦断狱现象的全面认知,并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体现了他在断狱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的严重不足。
纪昀评价的可取之处,在于“夫疑狱,虚心研鞫,或可得真情”一句。的确,虚心研鞫,历来是疑案得以公正司法的必备条件,此自不可疑。但是虚心研鞫,并不见得就一定能获得真相,纪昀“或可得真情”也算实话实说。纪昀的评价除了这点外,其他话语均经不起推敲。首先,官员祷神祈梦,并非“不过慑伏愚民,绐之吐实耳”这样简单。清代地方官员的城隍庙祈梦,可谓是官员在城隍信仰下的一种极虔诚的行为,其沐浴、其熏香、其斋戒、其焚香、其跪拜、其祷告、其夜宿,哪一件不做得认认真真、规规矩矩?如果说真有“慑伏愚民,绐之吐实”之类,那只能是那些纯粹的诈梦诈审而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祈梦断狱。那种纯粹的诈梦诈审,的确会时有发生,严格意义上看体现了对城隍神灵的亵渎,也反映了司法官员的懒政,从而为真正追求公正而极负责任的官员所不齿。纪昀以这种诈梦诈审现象来评判祈梦断狱,实大失偏颇。其次,将祈梦断狱简单误读为“以梦寐之恍惚,加以射覆之揣测,据为信谳”。如果祈梦断狱果真如此,那“鲜不谬矣”肯定对,但问题是真正的祈梦断狱并非如此。正如前述,梦境对案件证据线索往往有一定的指引或隐示意义,因此祈梦断狱的关键主要在解梦。而解梦绝不等同于“射覆之揣测”。“射覆”是古时一种猜物的游戏,〔59〕具体指用瓯、盂等器具覆盖某一物件,让人猜测里面是何物。《汉书·东方朔传》:“上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赞曰:‘臣尝受易,请射之。’”颜师古注:“数家,术数之家也。于覆器之下而置诸物,令闇射之,故云射覆。”(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五,传第三十五《东方朔》,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2843 页。它需要一定的易占知识作为基础,但仍是一种带表演性的、集卦术与趣味于一体的预测方法或游戏。远不能与对有启示意义的梦进行解析的行为相提并论。如果无法解梦或解梦无效,疑狱都不可能解决。一个具有公正心而又负责任的官员,是不会轻易将某种梦解作为“信谳”的。即使那位对梦竹进行“祝”“节”解读的官员,虽然对无辜者进行穷究,但毕竟没有将此“据为信谳”,而是以疑案上请。可见这位官员虽然有些可恶,但毕竟还是遵循了基本的祈梦断狱原则,没有酿造冤案。最后,纪昀将古来祈梦断狱之事,统统认为“皆事后之附会”,显得有些武断,有以偏概全之虞。应当承认,为神道设教计,事后附会肯定存在,但祈梦断狱之成功者也有事实。像蒲松龄笔下的《老龙船户》就有真实之本,《申报》记载的祈梦案例也具有较高可信度。实际上,据前述按梦的精神心理机制分析,祈梦断狱的有效性其实是有一定客观存在的。纪昀仅因此案未能成功审断,就以所有祈梦断狱之事均为事后附会,实有厚诬之嫌。
今人初看纪昀对祈梦断狱的否定性评价,想必都会以为纪昀是个无神论者而为之赞叹,却不知事实上并非如此。虽然纪昀为旷世高才,领纂四库全书,但其实依然未能免俗于那个时代的鬼神观念,《阅微草堂笔记》中就可多见。如描写某学官之妻秋祀夜梦数十妇女进入节孝祠,其中所识两位贫妇并未得到旌表,但“鬼神愍其荼苦,虽祠不设位,亦招之来飨”,纪昀以“信忠孝节义,感天地动鬼神矣”进行感慨。〔60〕(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槐西杂志(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229-230 页。又如描写静海一人梦己妇被劫,噩醒后不自知其梦而携梃出门追赶,却巧遇他妇被劫而奋力相救之事,纪昀以“此则鬼神或使之,又不以梦论矣”进行评论。〔61〕(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槐西杂志(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323 页。尤其还描写自己外祖父殁时厚葬而后遭盗墓而捕获不得时“诸舅同梦外祖曰”事,纪昀评之以“梦语不诬矣”。〔62〕(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384-385 页。可见,同是鬼神之事,纪昀却有着矛盾性或选择性的态度,不相信断狱之城隍托梦,但相信自己外祖父托梦。〔63〕其实纪昀对梦亦有深刻认识,他将梦分为“意识所造”“气机所感”“意想岐出”“气机旁召”四类,其中“意识所造”乃“念所专注,凝神生象”所致,“气机旁召”则涉及鬼神托梦。参见(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滦阳续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516-517 页。此或与纪昀对自己断狱有着曾经的“痛”有关。《清史稿·曹文埴传》载乾隆年间,时任左都御史的纪昀曾受命重新勘验军机章京员外郎海升殴杀妻案,纪昀却“仍以自缢具狱”,后因真相大白而被“下吏议”,受到弹劾。〔64〕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 年版,第10784 页。可以说,此案为其司法生涯一大败笔,也最终引来乾隆如此谕旨予以惩戒:“此案纪昀本系腐儒,于刑名素非谙习,且目系短视,未能详悉检验。其平日校勘各书,尚属认真,姑从宽改为革职留任。”〔6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2 册),档案出版社1991 年版,第585 页。此虽为从宽处理,但此种受辱之痛,无疑给纪昀以深刻教训——断狱须慎之又慎。而前述某县令祈梦断狱的失败,或恰好给他提供了全面否定的机会。如此看来,纪昀对祈梦断狱的全盘否定有其特定原因,当不足据信。故,虽然纪昀倡导虚心研鞫当值得充分肯定,但祈梦断狱的一定技术价值,在清代司法语境中也不宜就此被完全否定。
(三)祈梦断狱反映了司法官对公正司法的积极追求和探索
今人对清代流行的城隍庙祈梦断狱大都会投以鄙夷的眼光,因为在现代科学看来,鬼神是不存在的,将案件交给不存在的鬼神让其示梦解决,真是太荒谬、太愚昧了!然而,如果我们放下科学姿态,回到历史现场,站在清代那个流行城隍信仰的语境中再去观察,我们或许就会有着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理解之同情”(也可谓“同情之理解”)。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说:“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66〕陈寅恪:《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载《陈寅恪先生全集》,台湾地区里仁书局1979 年版,第1361 页。此义与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篇同感:“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67〕章学诚:《文史通义》,罗炳良译注,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391 页。陈、章之论均表达了今人对古人思想学说如何评价应有的学术态度。当然,此处“理解之同情”并非就要肯定或赞同,而是“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古代语境中官员的这种做法。其实这也就是一种“历史语境论”的评价姿态。不过笔者在此想强调的是,历史语境论只是提供一种“理解之同情”的直观平台,并不能提供历史事物背后隐藏的意义或价值,它需要我们在同情理解基础上进一步去发现和揭示。清代地方官夜宿城隍庙祈梦以欲断疑案的做法,实反映了中国古人面对疑案时对公正司法进行积极追求和探索的某种传统。当然,这种传统背后的支撑或推力,则是浓厚的神灵信仰也即城隍信仰。
中国古代司法官人为制造冤狱的事例,可谓史不绝书,反映了司法史上腐败以及黑暗的一面。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古人对司法公正积极追求和探索的一面。就清代司法官而言,当遭遇疑狱,如果抛开其典型的腐败及黑暗不论,仅从常态的角度出发,他也可能出于自负傲慢、政绩挂帅、破案压力等原因,在证据不足情况下结案,从而将疑案办成冤案。但是我们发现,大凡最后欲通过夜宿城隍庙祈梦方式断案的司法官,往往是重视证据、追求公正、办案谨慎的官员。当面对疑狱,他们努力调查案情、研析线索,而当一切努力仍无法掌握证据之时,并非昧着良心定案,而是以一种百倍虔诚的系列仪礼去夜宿城隍庙求梦神示。毋庸置疑,这多少折射出祈梦官员对公正司法的追求,也体现出他对城隍神灵的信仰。而在这种司法技术下,有些祈梦断狱就得到成功审断;而即使祈梦或解梦失败,也不会强行枉法裁判,因为“举头三尺有神明”,鉴察善恶的城隍神正在暗中时刻监督着他。
实际上,为断疑案以求公正,清代地方官夜宿城隍庙请求神灵帮助的司法技术并非突然如此,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先秦时期齐庄君求助社神,用神灵附体之羊,审断手下二臣长达三年的疑案的记载,〔68〕《墨子·明鬼下》:“昔者,齐庄君之臣有所谓王里国、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齐君由谦杀之,恐不辜;犹谦释之,恐失有罪。乃使二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二子许诺。于是泏洫,羊而漉其血。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槀之,殪之盟所。”《墨子》,李小龙译注,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120 页。正表明了求助神灵的积极目的和价值——力求最终的司法公正。当然,从观念源头看,为求公正而不枉法裁判者可为尧时大法官皋陶。传说他虽断案英明,但当遇到令其也一筹莫展的疑案时,他就会唤出那头上天派送的独角神兽,用那只象征正义锋芒的独角触碰“不直”者,从而实现公正司法。由此可见,独角神兽进入古代司法领域,从“历史语境论”看,当是古人积极追求公正目标的创造和期待,而并非如现代有人轻率评价的“愚昧司法”。像法的古体字“灋”,即体现了古人在神灵信仰(獬豸神兽)的精神支撑下,对司法公平正义的期望,特别是对公平正义的积极和执着追求。〔69〕今天许多法院大门口摆放着金属铸造或石雕的獬豸独角兽,虽然已被剥离了神性,但由神性引发出来的正义精神及其象征则保留了下来。依此,就古代司法官而言,当遇上疑案智力枯竭难以断案之时,也千万不能灰心、气馁,更不能“葫芦僧断葫芦案”,而是可求神助,从而最终实现公正。清代官员夜宿城隍庙的祈梦断案,只不过是在上述传统神助观念上的进一步探索和精致化建构。清代之前如元明虽有所初显,但至清代才得以精致化并趋向蔚为大观。某种意义看,这实是清代司法官为追求公正而解决疑案的某种终极努力,而其背后的推力,则是官员对城隍神灵那种超越历代的空前信仰和崇敬。〔70〕史料显示,清代以前地方官常常会因灾害而约定将对城隍进行责罚威胁。但在清代已不再见,即使有所不敬也是用词客气。如蓝鼎元《祈年告城隍文》:“……礼教政刑,某之责任,废而不修,则令为失职。水旱疾疫,神当驱除,岁比不登,则神为失职。……请以今年今日为始,风雨调顺,螟蝗不生,冬稔大有,百室盈宁,俾我民得籍神庥,神亦永享明禋于勿替。不然久荒之后,难再洊饥,今冬弗稔,将靡孑遗。旱干水溢,变置坛壝之忧,吾不能为尊神保也。神其鉴兹,慰我民望。谨告。”(清)蓝鼎元:《鹿洲全集》,蒋炳剑等点校,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335 页。
(四)祈梦断狱典型体现了“人神共治”以建构社会秩序的目标价值
传统中国社会秩序,可谓有两套体系加以维系:一套是社会行政体系,以实际的政法运作,通过大大小小的官吏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一套是象征体系,以形形色色的神灵信仰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二者一阳一阴、一外一内,将广大社会成员纳入既定的社会秩序中。自唐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城隍成了神灵象征体系中极重要的一环。它不仅成为地方城池的管理守护神,还是当地冥界的主管和法司,特别是它还能在阴间对阳间的官民进行善恶是非的鉴察和奖惩。因此,阴阳相隔只是相对而言,城隍以其鉴察善恶的功能将两者打通,对于阳世而言,也就不仅有世俗的官方力量管治社会,还有以城隍为核心的神灵力量进行有力配合。可见,在城隍信仰可谓“盛世”的清代,“人神共治”就成了地方建构有效社会秩序的重要模式。
清代地方官赴任向城隍致祭宣誓时的誓文,均强烈体现了这种“人神共治”的理念。不过随着城隍信仰的强化,这种理念有稍许变化。清初除主动请求城隍监察外,还往往向城隍明确职责之分乃至相互监督。如戴兆佳于康熙年间任浙江天台县令期间,就论及城隍的一系列职责,如城隍失职,则“必将奉圣天子声灵,为神致讨,为民请命,无所依回瞻顾也”,并强调“阴阳同理,均当父母为心;祸福无门,惟在公私一念”。〔71〕(清)戴兆佳:《天台治略》卷九《到任告城隍文》,载《官箴书集成》(第4 册),黄山书社1997 年版,第207 页。这或可谓一种“平等”意义上的“人神共治”。然而清中后期,到任告城隍誓文似只见官员主动请求城隍的全面监察了。如嘉道年间刘衡赴任知县的誓文〔72〕誓文为:“维神聪明,维神正直,以佑我民,以福我国。惟小子衡,自慨凉德,今来作宰,行不敢墨。除沿用旧章之不病民者,未便遽革。此外一切词讼案件,倘敢受百姓一文,维神其殛。吃百姓一饭,维神其殛。故纵书差索扰,维神其殛。或遇事不肯尽心,任其延宕,以致拖累,维神其殛。敬陈誓文,用表我心,用尽我职。神鉴昭昭,尚其来格。敢告!”(清)刘衡:《庸吏庸言·到任谒城隍神誓》,载《官箴书集成》(第6 册),黄山书社1997 年版,第176 页。不仅请求城隍对自己,还请求对手下差役的索扰行为进行严格监察。〔73〕当然,除请求城隍神监察外,刘衡对差役更有其针对性的管控措施。参见邓建鹏:《清代知县对差役的管控与成效——以循吏刘衡的论说和实践为视角》,载《当代法学》2022 年第2 期。但不管怎样,充分运用城隍,将“牧宰职明”与“城隍职幽”进行贯通和整合,是清代地方治理的重要法宝。无疑,在全面信仰城隍的环境中,这种“人神共治”不仅弥补了世俗力量的不足,还管控了民众的精神,从而达到一个令统治者满意的社会秩序。清代地方官夜宿城隍庙的祈梦断狱,正十分典型地体现了“人神共治”的目标价值。
一般而言,地方官治理一方,最怕遇上疑狱。因为疑狱一旦处理不好,就会酿成冤狱,进而触发民变危及仕途;如长期拖延,同样激发矛盾。因此,当遇上疑狱,除官员自身司法腐败或黑暗外,大都会谨慎对待、仔细研鞫。但正如前述,有些疑案对司法官来说可谓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此时求助于神灵,恰恰是期望“柳暗花明又一村”,而夜宿城隍庙求神示梦,则是一个最为虔诚、最具系统的技术手段。它与其他具有城隍因素的断案有较大不同。比如清代常见有司法官将疑案拉到城隍庙去审,这种方式主要是凭借当事人心理恐惧的外在表现。〔74〕如“幽魂对质案”与“刘开扬案”即是典型。分别参见(清)蓝鼎元:《鹿洲公案》,群众出版社1985 年版,第44-47 页;(清)汪辉祖:《学治臆说》,载《官箴书集成》(第5 册),黄山书社1997 年版,第280-281 页。如果当事人的内心足够强大,则此法无效,其被动性是很明显的。而祈梦断狱中,司法官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自我行动,无须受制于当事人的主观因素。正如前述,无论是祈梦本身还是祈梦内容,因常常有其效果,因而在古人看来,无疑都是神灵显灵而启示证据、参与案件的结果。这种体现在疑案上的人神配合,当是一种典型的“人神共治”。虽然其他城隍因素的裁判也体现某种程度的共宰一邑,但远不如夜宿城隍庙祈梦之典型,因为毕竟有一套完整的系列礼仪,而不是碎片化或一般性的祷告或空间借助。
五、结语:证据神示、理性审判与神道司法
当遭遇疑案,“山穷水尽”之下,清代地方官只好祭出兜底性司法技术:经熏沐斋戒,赶赴当地城隍庙,焚香祭拜祷告之后,便夜宿祭案旁边,静候城隍托梦。这一套程序和仪礼,是何等的虔诚和肃穆?如果将清代地方官祈梦的整个过程全程真实拍下,我们或除了可笑之外就是感动!为了解决疑案,司法官可谓做了最后的努力。无疑,这种祈梦断狱的核心所在,就是为获得证据。然而,这种证据却来自梦,确切讲来自城隍托梦,可谓是神示证据。显然,这种为证据神示而来的祈梦,绝非传统民间那种一般性祈梦。传统民间为科考、升迁、治病、经商、求子等等都有向神灵祈梦,以预知和应对个人命运的吉凶祸福。为断狱而来的祈梦,除仅向城隍祈祷外,与民间祈梦的关键区别在于获得证据神示。这个神示的证据将会对疑案当事人产生重大影响,甚至生死攸关。因此,我们不仅看到清代地方官祈梦的独特性,更可注意到其中证据神示的重大意义。
然而,证据神示是否就意味着祈梦断狱就是一种现代人目为“非理性”的“神判”呢?非也!关于历史上的神判,诚如费孝通所说,“是人们在不能利用自己的智力来搜索犯罪证据或迫使嫌疑犯吐露实情时,不得不仰赖于神的一种方法”;〔75〕费孝通:《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第288 页。研究中世纪神判的英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巴特莱特也说,“神判是在常规司法程序无法运用的情况下,适用于疑难案件的一种证明形式”。〔76〕[英]罗伯特·巴特莱特:《中世纪神判》,徐昕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202 页。可见神判与祈梦断狱一样,都是针对疑案而运作,不过两者却在本质上存在重大差别。可以说,由所谓的神灵直接作出裁判,是神判的本质共性。前述皋陶遇上难解疑案而用“独角兽”,以及齐庄君无奈下用“神羊”断案,虽然理念上都体现出对司法公正的追求,但两者其实都是典型的神判。〔77〕关于中国古代的獬豸神判,陈灵海从观念构造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其提出的制度性神判与观念性神判的区分很有价值。参见陈灵海:《中国古代獬豸神判的观念构造(上)》,载《学术月刊》2013 年第4 期。不过,其对先秦文献唯一记载神判过程的“王里国中里徼案”并非神判而只是神鬼故事的分析,笔者不敢苟同。实际上,从整个案例记载来看,“羊起而触之,折其脚”正是“盟誓神判”的体现。中里徼被“羊触折脚”,恰恰表明神判之证据神示从而判定其有罪过;正基于这种神判,神社的主祭官根据羊(实为时人眼中神灵附体的神羊)的有罪判断杀死了中里徼。还有中外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那些所谓热铁判、沸水判、冷水判、宣誓判、抽签判、圣餐判、吞食判等乃至司法决斗,均为由神灵直接作出裁判的神判范畴。那祈梦断狱为何不同于神判呢?是因为祈梦断狱的最终裁判者,不是“神”而是“人”,是该疑案的主审官员。城隍托梦所示之证据往往只是隐藏在梦境中,或谓只是种暗隐的线索,它需要对其解梦才有可能有所发现。因此“人”的解梦就成为关键。显然,人如何有效解梦,则明显是个“理性”运作的问题,或至少不排除“理性”因素的存在。〔78〕清代所见此方面史料已充分证明,解梦涉及很多术数知识和智慧。当然,实践中可能也存在胡乱解梦的非理性情形,但应当极少,因为一个经过虔诚而繁琐仪礼去城隍庙夜宿祈梦的官员,不会轻易如此作为。况且正如前述,按“梦的精神分析”理论(如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这种祈梦本身及内容还往往真有暗藏玄机。但问题的关键还不仅于此,还在于解梦获得的神启证据并非就是“不证自明”,而是还必须进行“验证”才能采信。如当事人就是不招,又难以通过其他方式佐证,这种所谓的神示证据就会被置弃。前述某官员梦“竹”而以“祝”“节”鞫讯失败后,只有放弃他所解的神示证据而将该案上请,就是神示证据没有通过验证的一个范例。毋庸置疑,对神示证据的验证,更体现出理性色彩。因此,赴城隍庙祈梦断案,虽然其中弥漫着神灵因素,但关键之处往往还是有司法官的理性把握,从而体现出某种程度的理性审判。这点尤需值得注意。
不过,无论祈梦断狱有多少理性审判的因素存在,它毕竟是一种对城隍神灵进行虔诚信仰下的司法,因此从本质看仍是一种“神道司法”。司法官对梦的“心理机制”可能一无所知,但对梦的“神道机制”却充满期待和坚信。《官场现行记》第46 回记钦差童子良的话:“神道自有的。我们老太爷从前在山西做知县,凡是出了疑难命盗案件,自己弄得没有法子想,总是去求城隍老爷帮忙。洗过澡,换过新衣服,吃的是净素,住在城隍庙里,城隍老爷就托梦给他,或是强盗,或是凶犯,依着方向去找,回回都找到的。后来老太爷升天之后,老太太还做梦,说是老太爷也做了那一县的城隍了。神道的确是有的,不可不相信。”此段话不仅将清代地方官遇疑案而赴城隍庙祈梦活灵活现地描述出来,而且证明了神道的存在。钦差观念如此,地方官更是如此。如此神道司法,实涉及司法与信仰两者的关系及其意义问题。如果司法进程拒绝神灵因素的介入,我们今天或可凭科学手段以获取证据,而在古代则很可能会因此导致“疑案”遥遥无期或草率结案。因此,以城隍为核心的神灵信仰进入“疑案”的司法流程,在传统中国尤其清代,可谓意义重大。〔79〕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现代诸多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西方国家中,在诉讼中依然存在证人必须向上帝宣誓以表不作伪证的程序规则。依此来看,在这些国家,神灵信仰仍然在司法迈向公正的流程中留有一席之地。虽然西方的上帝与中国传统的鬼神有诸多不同之处,但作为超自然力量的神灵则是其共同本质。
当然,清代祈梦断狱,体现的不只是司法官也是全民的城隍信仰。从地方官治理看,这种神道司法正可实现人神共治,体现神道设教。而于城隍的神道设教,从清代的历史语境看,恐怕不能被简单指责为一种“愚民”政策,因为除官僚阶层其实也普遍相信城隍神灵外,〔80〕当然不排除可能有少数官员不相信城隍而又利用城隍的情况,如蓝鼎元审“幽魂对质案”。它还充分接洽着大众对此的知识信仰。〔81〕可以说,传统中国民众普遍的神灵信仰,经常被司法官作为断案之用,种种案例集多有载见。有论者通过对《折狱龟鉴》中“摸钟辨盗”案的信息经济学(博弈模型)分析,揭示了知县陈述古之所以“用谲”成功,关键在于知县能在对民间普遍神灵信仰大体准确估计的基础上确定窃贼的信念,进而诱使窃贼暴露自己的私人信息(参见吴元元:《神灵信仰、信息甄别与古代清官断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6 期)。当然,此主要是针对司法官“用谲”类的分析,实际上建立在民众神灵信仰基础上的断案情形十分复杂,远非“用谲”类所能涵盖。特别是在明清时代,由于央地官方的推动和强化,城隍神的信仰相较其他时代的神灵信仰则更为普遍和浓厚。就祈梦断狱而言,即便到了科学尚属昌明的民国,也仍似见有官员夜宿城隍的身影;〔82〕如《真报》于1947 年11 月9 日第2 版刊登署名“金恶”并题为《祈梦破案》的一则案例:“吾友张生,宰浙江宣平县。一日乡长来报,谓一农家夫妇子女五人,悉遭杀。……时极,乃令下属三日内破案。四处捕惨,苦无踪影,经日二月,仍不得凶犯。张忧甚,遂仿包孝肃所为,斋戒沐浴,祈梦于县城隍庙。是夜,作二梦。梦行故乡柳堤中,遇其老师汪先生父子,联袂而来,点头不暇相语;一梦行行湘潭至衡山驿道,俗名南山大路者。明日起,不自解,复询诸僚属,亦不能答。夜秉烛偶检盗匪黑名单,得二人,一曰柳连单,一曰蓝大路。张悟曰:‘必此二人矣?’立令侦骑重往捕。柳遁去,获蓝,一讯即白。张问蓝与死那结何仇恨,蓝答系十年前与柳同为匪,被死者报官,入狱经年始出,今报昔仇,乃斩草除根,戮其全家。隔日,蓝弃市,邑人称快,犹不知宰官有此一段神秘故事。”此处弃市实即斩首。斩首虽在清末法制改革中得以废除(绞刑为死刑唯一方式),但民国建立,斩首作为法外死刑方式又在司法中不时被运用。而社会媒体在关于祈梦或造梦的新书广告中,亦一直突出渲染以往良吏祈梦城隍以断疑案的成功以招揽顾客。〔83〕如1925 年12 月27 日的《申报》第12 版的新书出版广告:“《祈梦秘书》,一名《造梦术》(仿古精装,一册特价五角六分,函购寄费五分)。从前良吏,每遇疑难不决之奇案,往往祈梦于邑庙神前,而得平反冤狱,水落石出。惜此祈梦之术,世少流传,间有一二抄本,亦不肯轻以示人,本书兹以重价购得真本,公诸当世。”此后,该报于1926 年3 月9 日、3 月22 日、3 月24 日、3 月26 日、4月18 日、4 月20 日等日不断重复刊登该广告。此种在民国官场与民间都有所反映的遗风和心态,可进一步折射出清代地方官祈梦断狱的一定流行,以及“神道司法”观念的官民共振。也正因为传统社会相信并敬畏神灵的存在和力量,古代许多具有神秘性的司法技艺,在现代一般科学视野下自然纯属愚昧透顶,但在传统中国却为解决诸多法律疑难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从而圆满地解决了疑案,达到了传统社会所认可和追求的公平正义。〔84〕除却本文所论祈梦城隍庙外,还有其他诸多神秘性司法技术以应对疑案。比如“滴血(骨)认亲”,显然极不符合现代科学,但因为古人相信它,相信其背后建立在诸如“血食”“血亲”等基础上对血液的神性认知,故常常关键性地解决了诸多司法难题。可以说,传统社会虽然没有近代以来兴起的科学观念进行指导,但古人似并没有因此而全部生活在困顿混乱之中,而是用他们那时共有的法律观念、知识和信仰,维持着秩序、解决着纠纷,建构属于他们心目中的和谐社会。从这个方面看,传统中国的法律之学,当然远非现代人对现代法学予以界定的一种“科学”,而是如何有效解决种种法律问题的一门“艺术”。基于清人普遍而浓厚的城隍信仰,“祈梦断狱”作为时人解决“疑案”的一种司法技艺,或可值得“理解之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