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越民族的无间道
2023-12-26叶远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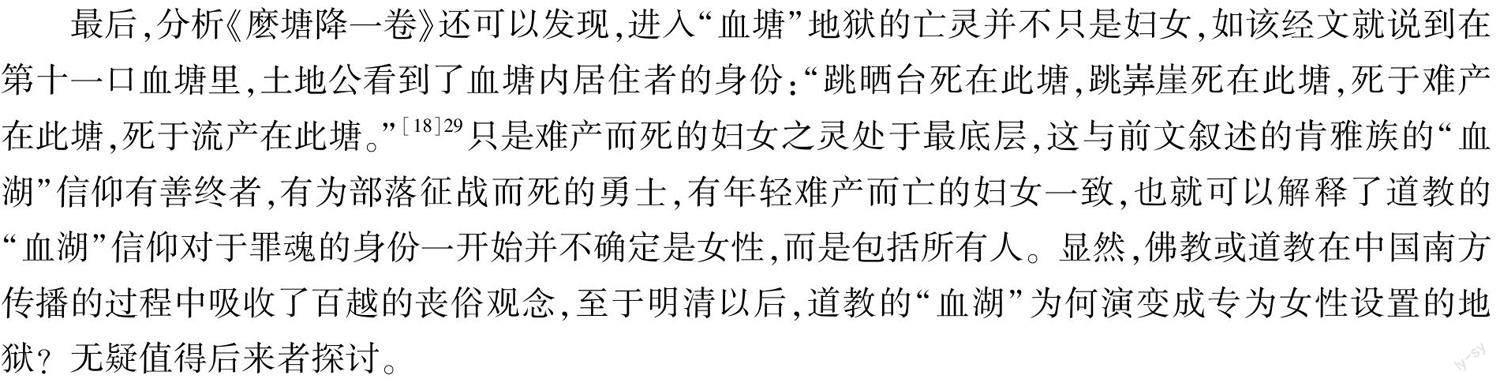
【摘 要】“血湖”是中国道教专为女性亡灵设置的一处地狱,道教认为女性因为月经或生产恶露流出的血造成污染导致死后亡灵堕入“血湖”,在丧葬时需举行“破血湖”仪式将灵魂拯救。以往研究几乎全部认同道教的这一观念来源于佛教,本文对此提出质疑,通过观察中国南方各地区的“破血湖”科仪,归纳其共同点,结合壮侗语民族的丧葬民族志资料与环南中国海区域出土的考古资料、神话传说对其源头进行挖掘,结果表明,道教的“血湖”信仰来源于百越民族的丧俗观念,借此说明少数民族视角对中国宗教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关键词】百越;丧俗观念;血湖信仰;道教
【作 者】叶远飘,广东医科大学生命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博士。广东东莞,523808。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3)05-0104-0008
一、血湖研究現状及其留下的困惑
“血湖”是中国道教专为死亡妇女的灵魂设置的一处地狱,在道教有关“血湖”的经文记载中,认为女性因月经或生产流血造成污染而带有“原罪”,导致死亡后灵魂堕入“血湖”地狱,痛苦万分,因此对于女性的丧事超荐活动需要举行“破血湖”科仪,目的是将这些灵魂从“血湖”地狱拯救出来。该信仰目前主要流行于中国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向东跨越日本,向南远达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尽管很早就流行而且影响广泛,但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起步却很晚,相关成果也不多。
1965年,法国汉学家苏远鸣在日本发表《〈血盆经〉资料研究》一文,开启了血湖信仰的科学考察。苏氏以其出色的文献考证功力论述了“血湖”观念的由来,认为道教的“血湖”说成形时间在南宋嘉定癸未年(1223),以道经《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首次出现“血湖”为标志;但“血湖”说的源头是佛教的“血盆”说,虽然在目前可考的文献中,直到南宋绍熙甲寅年(1194)的《如如居士三教大全语录》才有“血盆”的记录,但是,佛教的“血盆”观念大约在公元286至315年,竺法护翻译《盂兰盆经》时就已经萌芽,“血盆”信仰正是依托佛教《盂兰盆经》中的“目连救母”故事传播的。[1]78~116苏远鸣是血湖信仰研究的开拓者,这个观点具有奠基性的地位,在其文章发表的第2年,日本学者泽田瑞穗给予高度认同。[2]40此后韩国学者宋尧厚也给予积极附和。[3]已有研究基于佛教、道教经典对血湖信仰进行的思想史考察,为学术界理解血湖信仰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参考。不过,正如杨德睿所指出的一样,如果说道教的“血湖”观念出自佛教的“血盆”观,至少有两点困惑无法解释:
一是唐代以后,“地藏菩萨率领十殿阎罗统御大小诸地狱”这套说辞已经相当普及而且趋于巩固,“血湖”说为何胆敢不依托佛道两教既成的通说,凭借着极为单薄的内容新出一格?二是佛教“目连救母”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深入人心,而依托这个故事传播的佛教“血盆”观念为何没有大面积传播开来,目前除了留下一部不足500字的“伪经”(《目连正教血盆经》)以外基本销声匿迹,反而是道教的“血湖”说一枝独大?[4]200
更重要的是,翻遍《大正藏》的佛经,也没有发现佛教有类似观念,印度佛教也找不到这样的观念。如此看来,似乎有理由相信,“血湖”的源头不在佛教的“血盆”观念,与“目连救母”故事的关联也不大,其中最有力的一个证据是《目连正教血盆经》已被证明为“伪经”。既然是“伪经”,就说明是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吸收了中国文化元素形成的,因此,佛教所吸收的那部分元素才是“血湖”的源头。那么,如何对“血湖”源头进行挖掘呢?实际上,血湖信仰传播依托的是“破血湖”的科仪,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丧葬实践,涉及到的是“正统动作”与“正确信仰”的关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多元而且历史悠久的国度,人们的信仰是杂糅的,也是易变的,但丧葬动作的传承却是相对稳固的,正如华琛所言:“中国所有与死亡有关的礼仪,只是暗示着生者和死者之间仿佛存在着一种连续不断的关系。至于参与丧礼的人是否相信灵魂真的存在、是否相信祭献会对亡者有用,那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丧礼必须要按照公众认可的程序进行。”[5]105故而,本文首先从“破血湖”科仪入手,通过归纳各地宗教实践个案的相同点以推断这项仪式的底层信仰,继而在文化整体观的关照下通过大量的民族志、宗教文本与神话学资料对其源头进行挖掘。
二、中国南方多民族的“破血湖”科仪
2014年,笔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参观过一场“破血湖”科仪,这场仪式所超荐的对象是一名68岁的老奶奶,毛南族。仪式的道场设置在丧家堂屋的大院,仪式开始前,道公用丧家的米在院子的地上画一个法坛,经过念咒以后,布置一张祭台,挂上许多神灵的画像,摆上香烛纸火,又在距离法坛正前方12米的地方摆一张八仙桌,桌子底下放一块红布,上绣有图案,图案中心是一顶道士的帽子,帽子上面挂着葫芦和宝剑,天空有星星和月亮,帽子底下写着“血湖池”三个金黄色大字,由一圆形小湖围起来,小湖还绣有水波纹,栩栩如生,“血湖池”中心放一大碗红糖水,碗的旁边还有一艘装着死者灵魂牌位的小木船。整个仪式在漆黑的夜里举行,伴随着几盏在风中摇曳的微弱灯光,道公们念着咒语,几个女人时断时续的抽泣声以及铃铛声交替传遍漆黑的夜空,让人背脊发凉。“破血湖”时道公的表演可谓“步步惊心”——手握木剑在空中挥舞,摆出一副斩怪除魔的样子,然后带领死者家属反复围绕着八仙桌转圈,扮演寻人的动作,再折回堂屋唱跳,最后一路“过关斩将”来到了堂屋外面的桌子跟前,突然大喝一声把桌子掀翻,家属们从四面八方围过来,喝红糖水,掀木船,取灵牌,整个仪式带给人极大的感官效果。2015年,笔者在海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又观看了一场“破血湖”科仪,过程与广西的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它的“血湖”不以绣图案的红布呈现,而是用泥土堆了一个直径和深度大约30厘米的坑,里面灌上水,放一只装着死者灵魂的纸船。从道具来看,比起2014年的那一场似乎更原始一些。其实,各地关于道教“破血湖”科仪的宗教实践都差不多,为了更清晰地概括这项仪式的共同点,笔者不厌其烦地再举两例,以下个案是一名网友在网络上对其奶奶葬礼的描述:
奶奶安静地躺在门板上,门板一侧的地面上,平铺着一张红纸,上面用米粒排列了四个大字:血盆地狱。父亲、伯伯和姑姑等人,每次两个人,轮流牵着一只纸船,在道婆的歌唱声中,围着奶奶绕圈圈,绕一轮,喝一杯红糖水。我们几个小辈的,就坐在一边听那两个道婆唱,从奶奶的出世、做姑娘、嫁人、生子一直唱到她的离世。那时候,真是不明白,过地狱为什么还要喝红糖水?后来一些偶然的机会,看了胡兰成的《今生今世》,看了电子版的《金瓶梅》,才开始有些许明白,原来过血盆地狱,是专门为女人做的法事。[6]
陆冉在《多民族视域下的〈血湖宝卷〉研究》一文也叙述了土家族的“破血湖”科仪:
土家族丧葬仪式中的“破血湖”仪式,是在室外进行的。道师在灵堂附近设方桌象征灵山,再在方桌下挖渠引水,设置东西南北中五方血湖地狱。通过在灵山和各方地狱间来回奔走,重现目连灵山求宝,地狱救母的情境。在此之后,还有挂灯科,破五方池,喝血水(红糖水)等仪式内容。当五方池地狱中的血水全部流尽,道师会把立在五方池地狱狱角的瓦片打碎,把装着亡者灵牌的小船打翻,至此,“破血湖”仪式才算基本完成。[7]31
仪式是信仰的内容,信仰是仪式的表现。如果说道教的“血湖”观念是吸收了其他观念而非自身创造的,那么这种信仰就必定显示出类似考古学的文化层关系,即道教在表层,而表层之下的底层是其源头,而多层信仰也必然反映在仪式当中。通过对系列“破血湖”科仪的宗教实践之观察,不难发现“破血湖”科仪与道教其他仪式所使用的道具有明显的区别——即红糖水和船型模具。而这两样道具本身不是道教的专属,但它们却是“破血湖”科仪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同意华琛的观点——人们在丧葬中遵守符合传统的正统动作,那么便有理由推断,红糖水与船型模具必定隐藏着更古老的信仰。
首先来看“红糖水”,根据道公的說法,红糖水就是女性排出的月经在地狱形成的“血湖”,而亡灵深浸在湖水之中,说明这个阴间在水底。关于这一点,在道教的正统经典《元始天尊济度血湖真经》已有描绘:
“血湖地狱地处东北壬癸之地,是属于北阴酆都罗山诸地狱中的一狱,具体位于北阴酆都罗山的海底,内有四小狱,即血池、血盆、血山、血海,四狱相通。”[8]37
也正因为这个阴间处于水底,亡灵在没有襄灾成仙之前,不具有特别的法力,所以需要搭船,这就是在大多地区“破血湖”科仪为什么使用“船”的信仰逻辑。等家属们把红糖水喝尽了(家属喝红糖水表示替亡灵赎罪),也就意味着血湖的水干了,灵魂便可升天成仙,也就不需要船了(把船打翻实际上象征着灵魂得以脱离阴间水底前往极乐世界)。事实上,这种人死亡以后灵魂在阴间搭船的观念并非仅仅获得道教的认可,前述《目连正教血盆经》中也有相关记载,该经卷在叙述目连前往地狱救母时与狱主的一段对话:
目连悲哀,遂问狱主:“将何报答产生阿娘之恩,出离血盆池地狱?”狱主答师言:“惟有小心孝顺,男女敬重三宝,更为阿娘持血盆斋三年,仍结血盆胜会,请僧转诵此经一藏,满日忏散,便有般若船载过奈河江岸,看见血盆池中有五朵莲华出现,罪人欢喜,心生惭愧,便得超生佛地。”[9]
“般若船”是佛学术语,指的是“度越生死海,达于菩提彼岸之船筏”。不过在汉人原本的冥府观念中,灵魂过奈河并不需要搭船,因为奈河有桥,即奈何桥,换言之,在汉人的丧俗观念中,灵魂过奈河依靠双腿走路。这一点,恐怕杨德睿先生也意识到了,因此他说血盆经宣传的观念与汉文化格格不入。[4]202既然如此,能否换一个角度,将关注点转向少数民族呢?尽管佛教与道教对于将灵魂从血盆(血湖)地狱拯救出来的手段不同,但两者都保留了“船”的观念,体现出该信仰具有浓厚的“水”文化象征,而武清旸基于南宋到明清的道教文献研究还进一步证实了血湖地狱中的罪魂身份大致经历了南宋时期到明清时期的“不分男女——产死妇女——一切妇女”的演变。[10]也就是说,在道教最早关于“血湖”记载的文献当中,堕入此处的亡灵是没有男女性别之分的。这样一来,我们将信仰的上层剖离,血湖信仰的底层就展现出来了:即人(无性别区分)死以后亡灵(搭船)到一个水底世界。结合该信仰流行的区域——主要在“长江流域以南”这一点来看,古代能够表现这种信仰的最醒目葬式无疑是百越民族实行的“船棺葬”,尽管目前学术界关于“船棺葬”的研究还没有揭示出这一点。
三、环南中国海区域的“血湖”传奇
根据《汉书》的记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11]1669可知从今江苏南部沿着东南沿海的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及越南北部这一长达七八千里的半月圈是百越最集中的地方。百越长期生活在河流纵贯、湖泊密布的泽国水乡,水行而山处,擅长驾舟的本领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浙江河姆渡与良渚文化出土划舟与木桨就可见一斑。[12]先秦文献对此也有诸多记载,如《淮南子·齐俗训》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原道训》云:“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然而,百越文化的流布并不局限于中国境内,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和语言学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已经证实,遍及两大洋的南岛居民,直接源于中国大陆的百越民族。[13]包括本尼迪克特、克鲁伯、徐松石、林惠祥和凌纯声等在内的多位学者都赞同“中国南方——婆罗洲——中南半岛”是一个有机的文化整体:“在中国长江以南到东南亚的半岛和岛屿这一广阔地带的任一人群中,存在着铜鼓、龙船、猎头、人祭等50项相同的文化要素。”[14]395这一事实提醒我们需要用更广阔的视野去搜索百越民族的血湖信仰。就目前笔者所能接触到的民族志资料,血湖信仰在婆罗洲肯雅族中非常普遍,出生于婆罗洲的台湾作家李永平在其作品中曾以“主位”(emic)视角描绘如下:
肯雅族有个非常古老至今族人们仍然深信不疑的传说……大河尽头的圣山峇都帝坂,山麓有五个大湖,专供往生者的灵魂居住:善终者,死后前往位于中央的“阿波拉甘”定居,过着和生前同样衣食不缺、无灾无病的平静生活;为部落征战壮烈阵亡者,英灵骁骁乘风飘向西边的“巴望达哈”,血水之湖,那儿有众多来自全婆罗洲,死于难产的年轻妇女,任他挑选为妻,从此过着安逸富足的日子;溺水死亡者,进入南方“巴里玛迭伊”,冥河下的一座地底湖。[15]222
这段话明确提到了“血水之湖”,而且指出它是一座地底湖,是死于难产的年轻妇女的灵魂所居之地,与道教文献的记载竟完全吻合。书中还说除了五大湖之外,还有几十个零星的小湖,让世间人人死后各有其所。然而,婆罗洲的肯雅族至今信仰的依然是原始多神崇拜,并不信仰道教,也不信仰佛教。那么,这些亡灵是如何去“血湖”的呢?文章继续讲道:
“河北岸死亡荫谷的“巴望达哈普帖(白血湖),专门收容那近来渐增多、每逢月圆之日便搭乘无人驾驶的空舟,或孑然一身,或成群结伙,朝向峇都帝坂溯流而上的异国魂灵。”[15]223
上述文字清晰说明了这些亡魂前往“血湖”的方式是“搭船”,关于百越民族死后搭船去湖底的考古学证据是两汉到唐宋期间中国南方至东南亚大面积出土的铜鼓,铜鼓的主人是中国南方的壮侗语民族,关于铜鼓的核心功能,张经纬通过归纳10个分布于中国西南、包括一些中国与东南亚跨境民族(壮、苗、傣、彝等)、甚至还有境外民族的民族志资料,发现他们使用铜鼓的方式,80%都体现在“送葬”过程中。[16]说明尽管铜鼓的功能可能有很多,但它的核心就是用于丧葬。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用于丧葬的铜鼓鼓身都普遍刻有龙舟纹饰,其文化内涵正如俄裔法国学者V.戈鹭波所言,它们反映了同样使用铜鼓送葬的达雅克人的民间传说——它们被称为“黄金船”,使命就是把亡灵运到云湖中央的“天堂之岛”。[17]254值得注意的是,与“血湖”类似的观念在壮侗语民族世世代代流传的民间史诗中也有发现,如壮族的传世文献《麽经》就有“血塘”“红塘”或者“血潭”的说法,根据《麽经》的讲述,“塘降”是壮族社会用来指民间因为难产而死的女性的亡魂居住之地,又称为“血塘”“红塘”,如《麽经》的《麽塘降一卷》就叙述了壮族始祖母姆六甲生了9个女儿,8个女儿都已经出嫁成家,而小女儿因被冤怪缠身,与情人私通怀孕后被逼投河身亡,成了“血塘王”的故事:
“死后去做血塘王/天上要过十二关/下地要过十二坎/造出血塘在高处/仙女相随在身旁/妻子独自去泉口/妻子独自去塘口/去到血塘过三天/去到血塘过五天/住在血塘不自在/住在高塘烦闷多/愿回凡居做情人/乘一片黑云上来,过星星旁边上来,飞过微光渺渺处,穿过十二孔圆洞,走过前人的老路,水深地方不要去,来到父亲深渡口,来到河口交汇地,该碰上的碰不上,该相遇的不相遇,偏偏遇见红塘婆,偏偏遇见血塘女,转头过来我们说,转身过来我们讲,人在世间成巫婆,人在世间也烦闷,和我一同上天堂,来做天堂血塘人。[18]159~165
壮族民间还认为,因难产死亡妇女的灵魂被阎罗王扣在“塘降”变成离宗的野鬼,有的虽自得其乐,但不能享人间香火,故不时给阳间兴灾作难,其家人须请布麽来做破塘法事,诵唱将其灵魂解救归宗。[18]151《麽经》中的《破麽塘》还详细叙述了布麽前往血塘拯救亡女灵魂的过程。由此可见,壮族“血塘”的文化内涵与道教“血湖”、佛教的“血盆”文化内涵完全一致,三者具有共同的源头。
四、百越民族创造的彼岸世界
虽然目前我们还不清楚“血塘”观念具体产生的时间,但是判断“血塘”是壮侗语民族原生性创造的彼岸世界是没有疑问的,道理在于:
首选,在壮族社会,麽经只供布麽为死者超度亡魂使用,其他宗教包括道教、佛教职业者都不使用。虽然壮族社会的宗教呈现出多元特征,各种宗教也不可避免出现相互借鉴、吸收对方的内容,但是从人们对宗教职业者的称呼来判断何种宗教属于原生型宗教并非难事,总体而言:“巫”属于准宗教性质;“道”“僧”属于外来宗教,“师”受汉族道教影响较深,是壮族再生型的民间宗教,而只有“麽教”才是植根于壮族本土的原生态的民间宗教。[19]在麽公们看来,《麽经》都是壮族开天劈地的人文始祖布洛陀创造的,所以大家叫这些经书为“麽经布洛陀”,它由古方块壮字抄写,从时间来看,最早的《麽经》成文于唐代,但大规模的《麽经》出现时间是在明代以后,不过这里有一个逻辑需要注意,明代才产生的书面文不等于此观念在明代才出现。因为《麽经》是由口头传承到不断加工、编纂汇集、最终成型而化为文本的产物,体现了壮族的历史性记忆。[20]具体到《破麽塘》《麽塘降一卷》两篇经文来看,没有任何道教、佛教的术语或思想,反而凸显的是壮族的本土文化意涵,例如经文通篇所写的“山歌相逗来传情”“山歌相情意绵绵”等等,表达了非常朴素的壮族人文思想,与我们看到的壮族民风也颇符合。正如梁庭望先生所言:“麽经虽为宗教经书,但内容却是远古神话,只是在一些地方加入了宗教意识,比较完整地保存了神话传说和古老习俗。”[21]可以说,《麽经》是壮族原生态文化的集中展示。
其次,作为一份超度亡灵的经卷,阴间观念无疑属于最核心的位置,麽经所宣扬的“血塘”位于12层水底——“水过腰身流嗦嗦,水淹脖子响哗哗”,这与后世佛教道教所说的18层地狱明显对不上,麽经宣扬的“血塘”观念也非常独特,是佛教或道教不具备的——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亡魂前往“血塘”的过程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先到达第一泉,再到第二泉……一直到达第十二泉,再到第一塘,第二塘……一直到达第十二塘。“血塘”的空间结构为:它处在天界,到达那地方要经过太阳与月亮所在的地方,它由十二个泉与十二个塘组成,“血塘”在最顶端。[22]119暗示了《麽经》所创造出来的阴间世界是阳间世界的逆向反映,关于这一点,中国南方至东南亚出土的时间为两汉到唐朝的铜鼓图案也可以印证——铜鼓表面所有连续的图案,包括鼓胸部位的船纹,鼓面旋转飞翔的鹭鸟、连续的舞蹈羽人,甚至是鼓面上立体的蛙饰和其他动物、人物图案都是从左向右运动的,就是说和太阳每天的运动方向相反,说明在天国的一切事物正好和尘世相反。[23]7实际上,有关阴间的世界与阳间的世界是相反的,类似传说至今在中国南方地区乃至东南亚地区的民间中仍然大面积流行。正如杨德睿所说的那样,“地藏菩萨率领十殿阎罗统御大小诸地狱”这套地狱说辞在唐代以后就已经相当普及而且趋于巩固,而明代以后,此时佛道的地狱观念比起唐代更为普及,《破麽塘》和《麽塘降一卷》如果借鉴佛经、道经,没有理由在这时候仍然宣扬12层地狱观念。恰恰相反,在“地藏菩萨率领十殿阎罗统御大小诸地狱”的说辞已经相当普及的情况下佛经、道经别出一格,抛弃已有说辞而宣扬“血盆”“血湖”观念,是佛教、道教在民族民间化道路上借鉴百越民族阴间观念导致的结果。对此,我们仍然可以提供有力的旁证,即所谓12层地狱观念至今在壮侗语民族的丧葬实践中仍然有仪式上的反映,例如与壮族同源异流的布依族在举行丧葬活动的时候,布摩就需要敲铜鼓,而且需要连续敲12响,按照布依族民间的说法,人死以后灵魂前往天堂要经过12道关口,敲12响铜鼓意味着铜鼓能将死者的灵魂平安送到天堂。这与我们在前文所看到的毛南族在进行“破血湖”仪式时把“血湖池”设置在距堂屋门前12米的地方具有相同逻辑。林安宁的研究也指出:“若以《民间文学母题索引》的母题去归类,《麽经》中的‘血塘很难放到某一个相应的母题之中。它似乎可以放到‘天堂是一個极乐的世界中……然而,《麽经》的叙述让我们得知,将‘血塘这一母题归入‘天堂是一个极乐的世界有不妥之处,因为‘血塘里的生活也有难以启齿之处……由此也更能体现出‘血塘这一母题的独特之处。”[22]119
五、壮侗语民族原始丧葬的民族志
自秦朝统一中国以后,百越与南下的北方移民不断交融,特别是唐宋随着中央王朝对南方的大规模开发,民族融合空前,大多数百越人融入汉族,没有融入汉族的百越人即演变为今天华南地区的壮侗语民族,如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族、毛南族、水族和黎族等,他们是百越文化最直接的继承者。这些民族皆有血湖的相关信仰,虽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一古老的信仰已被层层遮蔽,但通过对该群体丧祭民族志的神话学分析,仍然体现出血湖信仰的痕迹。这些材料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亡灵需要搭船,一类是亡灵不需要搭船,但表达的观念都是祖先来自水里,死亡以后要回到水底。
我们来看第一类。首先是水族。人死以后亡灵搭船前往阴间水底在丧葬文化的器物层面上表现最明显的莫过于水族,在今天贵州三都、荔波地区水族的丧葬仪式中,“许多人家要为死者作一纸船,把死者衣裳的领、袖或边、角放入船里,意为放亡灵进船,然后拿到河沟边去烧化,再把灰烬撒入水中,目送纸船的灰烬顺流而下,意为死者落叶归根,百年之后仍要回老家,因为其祖先是坐船来的,死者也要坐船回去,只有这样,才能返抵老家”[24]187。其次是布依族。布依族的丧葬仪式虽然不像水族那样频繁出现纸船,但是布依族的民间传说却认为用于丧葬的铜鼓可以变船,由铜鼓变成的船还具有上天下海的功能,它们能够搭载死者的亡灵下到12层的水底世界,也能飞上12层的天堂。例如在布依族民间流行的《铜鼓的传说》中就讲述了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古杰与龙王女儿相恋后,两人坐着铜鼓入海上天——铜鼓“变成一只船,他俩坐在船上划着,越过刀山火海,跨过十二层海域,终于又回到了人间”[25]121。最后是侗族。侗族的丧葬仪式同样没有船,但是亡灵死后搭船前往血湖的观念却在本民族司祭给亡灵唱的祖源歌当中体现出来,侗族的祖源歌表达了亡灵祖先是通过划船到达今天的居住地的,又劝勉亡灵按照来时的路线往回走,以便和祖先团聚。如流行于贵州黎平、榕江一带的侗族在丧葬仪式中唱《古邦祖公落寨歌》,其中讲叙到祖先的来源时就说:“我们祖宗原是木究发,那里就是我们的老家……逆水而上把船划,祖公落脚演究孖。”[26]88在劝勉亡灵回去的时候又说:“男的上山砍树造船,女的在家收拾行装。”
再看第二类。首先是黎族,在黎族的神话传说中,认为自己的祖先是蛇,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黎族还保留有“纹面”习俗,其刻的花纹“有斜形纹素,横形纹素,圆形纹素及缀音符号等四类……甚似象征龙蛇一类水族形状。”[27]至于“纹面”的原因,从黎族的主位视角来看,正如明代顾岕在《海槎余录》中说的:“黎俗男女周岁即文其身,自云,不然,则上世祖宗不认其为子孙也。”[28]385由于黎族的“纹面”与死后认祖密切相关,因此近年来政府禁止纹面以后,黎族在丧葬中需要用火碳在死者的脸部象征性画纹,正是相信自己的祖先属于龙蛇一类的水族,本身就生活在水中。也就是说,自己的祖先从水里来,因此人死后亡灵到水里去,不需要搭船。其次是壮族,除了上文《麽塘降一卷》所叙述的“血塘”表明其阴间在水底以外,其丧葬习俗也有相同的反映,例如人死以后家属要到河里沐浴哭泣,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曾这样描述壮族,称“人始死……邕州溪峒,则男女群浴于川,号泣而归。”壮族到今天还保留二次葬,壮族民间称之为“洗骨葬”,即用水把骨头洗净安葬,实际上暗示了死者的灵魂在水里。最后是傣族。傣族的各种仪式活动都离不开水,全国闻名的“泼水节”就是傣族的全民节日,傣族今天的丧祭仪式仍然保留独特的“滴水”仪式,即把食品供奉给祖先的时候要往贡品“滴水”,傣族人说只有这样祖先才能够吃到贡品。根据傣族的民间传说,以前有个大富翁死了孩子,家长把他埋在河的对岸,每天差佣人按时送饭供奉,但死者都吃不到,直到有一天下大雨,佣人过不了河,不小心使饭掉到了河里,死者晚上才托梦给他的父母说吃到饭了,于是,傣族就在供奉给祖先的贡品中“滴水”,这一行为实际上暗示了死者的灵魂在水里。
人类学的研究重视整体观,它的核心概念是“文化”,在人类学家看来,文化是由许多要素构成的,但诸多要素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彼此依存构成一个整体,对于一种文化的探源,需要立足于逻辑勾勒其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如此便能正本清源。
六、余 论
毋庸置疑,“血湖”信仰的源头在百越民族的丧俗观念,我们也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佛、道两教同样吸收这种观念以后前者没有大面积传播,而后者却成为一枝独秀的现象了。从宗教实践的角度看,我国三大民族走廊的主流宗教以西北走廊的伊斯兰教,藏彝走廊的藏传佛教与南岭走廊的道教呈现。也就是说,至今南方少数民族信仰的主流宗教是道教而非佛教,说明比起佛教,道教的教义教理与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更兼融。那么,道教大规模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以后吸收这些观念然后再传到汉族地区就是合理的推断。
行文至此,已经可以为本文画下句号。然而,笔者更希望借此机会向学术界呼吁:对于中国的宗教研究,应重视少数民族的视角。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历史上,中国的宗教市场从来就没有发展出排它性宗教,特别是中国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历史以来就与多民族的文化形成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但是限于“民族”的分类,许多研究有意无意把宗教与少数民族宗教进行切割。例如,我国宗教学的一级学科设置当中就有二级学科“少数民族宗教”,但是不少研究在潜意识中却认为“少数民族宗教”关注的对象是“少数民族”的“宗教”,即以少数民族为单位对宗教进行界定,但是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而言,要从界限上对某一个少数民族的宗教做一个清晰的区分显然困难重重,而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对于推动今后的宗教研究具有積极意义,这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法]苏远鸣.《血盆经》资料研究[C]//法国汉学(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
[2][日]泽田瑞穗.大日本续藏经:第1辑[M].东京:大藏出版社,1966.
[3][韩]宋尧厚.论《血盆经》在中国的发展[J].刘晨,译.世界宗教文化,2011(3).
[4]杨德睿.“血湖”研究刍议[C]//宗教人类学(第六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5]华琛.中国丧葬仪式的结构:基本形态、仪式次序、动作的首要性[J].湛蔚晞,译.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2).
[6]浅谈民间丧事中的“血盆”[DB/OL].(2020-10-09)[2023-09-02].https://www.zhmu.com/news/binzang3547.html.
[7]陆冉.多民族视域下的《血湖宝卷》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9.
[8]道藏:第2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9]大乘诸品经咒[Z].康熙三十九年(1700).柏林: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
[10]武清旸.道教“血湖地狱”罪魂身份的演变论析[J].云南社会科学,2016(6).
[11]〔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8(1).
[13]范若兰.“三重嵌套”:南海文化圈宗教流变特征及影响[J].东南亚研究,2021(3).
[14]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M].中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
[15]李永平.大河尽头: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16]张经纬.铜鼓文化与华南信仰体系探源[J].艺术探索,2016(4).
[17][俄]V.戈鹭波:东京和安南北部的青铜时代[C]//民族考古译文集.刘雪红,等,译.昆明:云南省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印,内部资料,1985.
[18]黄明标.壮族麽经布洛陀遗本影印译注[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
[19]黄桂秋.壮族民间麽教与布洛陀文化[J].广西民族研究,2003(3).
[20]李小文.壮族麽经布洛陀文本产生的年代及其“当代情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21]梁庭望.古壮字结出的硕果:对《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的初步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5(1).
[22]林安宁.壮族《麽经》神话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2.
[23]罗伯特·海涅·革尔登.后印度最古金属鼓的来历及意义[C]//铜鼓资料选译(五).席德茂,译.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1983.
[24]何积全.水族民俗探幽[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5]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民间故事选[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
[26]杨国仁.侗族祖先哪里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27]罗香林.海南岛黎人源出越族考[J].青年中国季刊,1939(1).
[28]〔唐〕段成式,〔元〕汪大渊,〔宋〕赵适汝,〔明〕顾岕.酉阳杂俎·岛夷志略·诸蕃志·海槎余录[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
INFERNAL AFFAIRS OF BAIYUE:Textual Research for Origin of Blood Lake Belief of Taoism
Ye Yuanpiao
Abstract:The Blood Lake is a hell specially set up for departed souls of women by Taoism,who believes that women's departed souls fall into the Blood Lake after their death because of blood pollution caused by menstruation or delivery lochia,so that a ceremony of “breaking the Blood Lake” should be held during funeral to save their souls. Almost all previous researches agree that this opinion of Taoism comes from Buddhism,but the article questions about it. The author observes the ceremony rites of Breaking Blood Lake in south China and summarizes their common points,as well as excavates their origins in combination of materials about funeral ethnography of Zhuang and Dong-speaking ethnic groups,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unearthed in the area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myths. Finally,it turns out that the Blood Lake belief of Taoism originates from the concept of funeral customs of Baiyue ethnic group,which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the ethnic minority perspective to the religious research in China.
Keywords:Baiyue;Funeral customs and concept;Blood Lake Belief;Taoism
〔責任编辑:黄润柏〕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项目“岭南‘珠玑巷传说的人类学研究”(GD23YDXZSH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