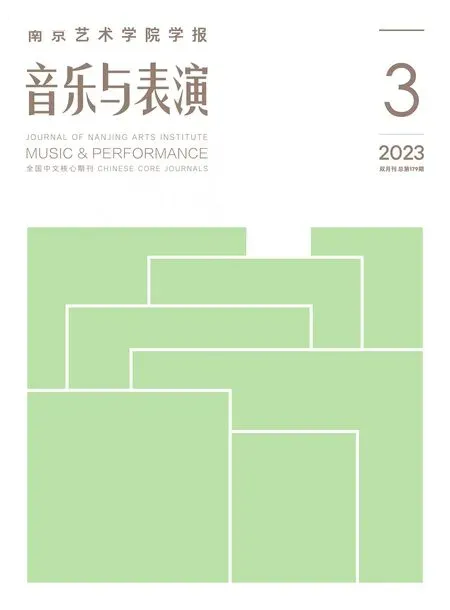儿童视角、儿童心理与儿童立场
—— 冯俐儿童剧编创理念简析
2023-12-23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北京100006
于 凉(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北京 100006)
“儿童剧”是唯一一个以观众群体命名的戏剧形式,其主要受众便是儿童。近年来,随着观剧年龄分级制度的实施,儿童剧适宜的观剧年龄有了更细致的划分,反映出儿童剧工作者对于不同年龄段儿童心理成长、精神需求的精准把握。同时,也更加注重不同年龄段儿童对外界的认知和理解。另外,儿童剧的表现内容也不再是透过成人视角俯视儿童的“大猫叫叫、小狗跳跳”,是“放下身段”正视未成年人的成长规律,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的“蔬菜水果”。
在诸多优秀儿童剧作品中,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冯俐编剧的《山羊不吃天堂草》《木又寸》等作品引起了业界的极大关注。这些作品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充满童趣的文本语言,在故事情节中融入儿童成长所经历的苦难教育和挫折教育,正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苦难”与挫折,打破了儿童剧原有的“童话式”结局和刻意营造的美好假象,引发了深层次的思考。
冯俐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现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从小就热爱写作的她,经过5 年的戏剧文学专业学习后,坚定地走上了编剧这条道路,曾创作多部电影、电视剧、情景剧、舞台剧、广播剧的剧本。2014 年进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后,她将目光聚焦到儿童剧创作上。她编写的《山羊不吃天堂草》《木又寸》《小蝴蝶的妈妈在哪里?》等多部优秀儿童剧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舞台上悉数亮相,并获得曹禺剧本奖、布加勒斯特国际动画戏剧节“最佳当代戏剧剧本奖”等荣誉。这些剧目不仅以生动的戏剧情节和巧妙的舞台呈现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其所体现的主题思想与编剧理念也引发观众共情,启迪心灵。本文从儿童剧的编创视角、文字语言以及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教育方法出发,分析、评述冯俐在儿童剧创作上的特性与追求。
一、以儿童视角聚焦成长认知
儿童剧的受众群体主要是儿童,这里所说的“儿童”指广义上的儿童,即0—18 岁的未成年人。儿童剧创作的第一要义,是符合当代儿童的欣赏需求和精神追求,让儿童能够根据剧情发展、戏剧行动与剧中人产生共鸣,获得心灵上的净化和精神上的洗礼。
“儿童自己演的是儿童剧,成年人、专业艺术家演的也可以是儿童剧。由谁扮演,不能决定戏剧的性质。决定性质的特征,取决于服务对象和适合于它的服务对象的题材、体裁、风格、样式。”[1]可见,儿童剧的创作必须立足于儿童视角来认知外界、看待问题,并根据儿童的理解能力引导他们对事物的判断,从而让儿童理解剧中的人物角色和故事情节,产生内心共鸣与情感接纳。
(一)儿童成长中的自我认知
自我认知指个体对自我的觉察,或者说自我意识的形成来源于个体对外界环境刺激后,经由记忆和思想产生的反应。因此,在形成记忆前,个体对自我认知相对匮乏。如果说记忆是一切思想的基础,那么自我认知就是个人基于思想之上对于环境的反应。绝大多数儿童所处的成长环境,比成人要相对简单,儿童对于反馈外界环境的自我认知也相对单纯,在儿童剧创作中,应遵循儿童自我认知的发展规律。
比如,《小萤火虫跟宝宝一样……》采用“互文式”的戏剧结构,编剧将萤火虫母子的故事和小女孩西子的故事有机结合。由于母亲工作繁忙暂住外婆家的西子,每天都非常想念母亲,希望母亲早日接她回家。外婆为了安慰西子,为她捕捉了一只萤火虫,但她们捉走的却是一只萤火虫妈妈。失去妈妈的小萤火虫,奋不顾身地踏上了拯救妈妈的艰难旅程,为了撞破关着妈妈的玻璃瓶头破血流,为了追上载着妈妈的汽车筋疲力尽。最终在小萤火虫的不懈努力下,西子幡然领悟,萤火虫妈妈终于重回大自然与孩子团聚。
两个故事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织——萤火虫母子被迫分离,是外婆为了安慰想念母亲的西子无意造成的。合理把握儿童剧剧本内容,有助于使剧本与舞台呈现完美贴合。“合理把握”是指“叙述者究竟是采用自己的眼光来叙事,还是采用人物的眼光来叙事”。[2]冯俐的儿童剧创作就极注重对剧本内容的合理把握。在《小萤火虫跟宝宝一样……》中,编剧借助西子的儿童视角,让观众感受到孩子与亲人分离时的伤心难受,也对萤火虫母子的遭遇产生情感共鸣,最后认识到“尊重每一个生命”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生哲理。编剧正是遵循儿童成长规律,站在儿童视角观察生活,以“润物细无声”的创作手法,使儿童潜移默化地习得做人的道理。
(二)儿童成长中的亲子关系认知
亲子关系指儿童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等直系血亲之间的人际关系,也可理解为家庭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利于家庭和谐稳定与儿童健康成长,许多文艺作品以此为题材,塑造出朴实高尚的父母亲形象。
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毋庸置疑,子女对父母的依赖更是一种本能反应。此外,我们还应关注儿童对于“爱”——亲子关系的不同认知。儿童时期,人需要被照顾、被保护以及被肯定,这些呵护最初由父母给予。在儿童剧《小蝴蝶的妈妈在哪里?》中,编剧参照蝴蝶、飞蛾以及萤火虫等节肢类动物的特性(雌性产卵后死去,幼虫从未见过自己的母亲),将昆虫赋予了人类情感,塑造出“蝶儿”找妈妈的故事。戏剧高潮处以父母温暖的怀抱抚平孩子受伤的心,不仅表达了母爱的无私与伟大,也表现了孩子对父母的无尽依恋。这些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情感,通过编剧巧妙的构思使观众得到情感慰藉和心灵滋养。
亲子关系不囿于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还包括兄弟姐妹间的感情。随着我国二孩政策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养育两个孩子。儿童剧《萤火虫姐弟历险记》描写了一对萤火虫姐弟因栖息地遭受污染和破坏,不得已展开了一段颠沛流离的冒险事迹。这对萤火虫姐弟的关系,融入了编剧对二孩家庭情感问题的思考。萤火虫姐弟间的关系变化,意在表现兄妹并不是争夺父母呵护的对手,而是相互为伴的亲人,是成长道路上的盟友,彼此间要懂得相互分享、互相帮助。编剧期冀二孩家庭可以以矛盾冲突为突破口,让兄妹共同经历“磨难”再从“磨难”中走出,携手同行。
(三)儿童成长中的社会关系认知
除自我认知和家庭认知外,社会关系的认知在儿童成长阶段也十分重要。社会关系的认知指人(他人和自我)、人际关系、社会群体、社会角色、社会规范和社会生活事件的认知,以及对社会行为的理解和推断。大体可归为两方面认知:一方面是对他人内在心理过程或特征的认知,如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等;另一方面是对他人外在社会行为、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的认知,如友谊、道德、法律制度等。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对他人的社会认知主要从外形特征、心理状态理解以及在集体中的地位了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艺术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艺术家对生活的感悟与思考,是经过艺术提炼具有一定思想性、教育性的创作。儿童剧也不例外,它集观赏性、艺术性、教育性于一身。可以说,一部优秀的儿童剧是儿童心中多彩的画卷,是帮助儿童发现世界之美的眼睛,也是引导儿童认识大千世界的窗口。因此,相较于其他艺术作品,尤其在对社会关系认知的思想传达中,儿童剧要特别注意传达的方式与儿童受众群的理解力。只有通过儿童的视角观察生活,才可能更有效地传递作品的思想。
如《山羊不吃天堂草》,编剧借主人公明子之口说:“如果父亲知道我们这么做,一定会痛骂我的。”这不禁令观众思考,在生活中遇到不公平时,我们究竟该以德报怨,还是以眼还眼?其实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这个故事是想让儿童体会生活远没有想象的那样美好,面对未知的世界,我们要勇于探索,更要学会保护自己。
又如,在以环保为主题的《木又寸》中,编剧摒弃说教的口吻和空喊环保口号的窠臼,以一棵银杏树的遭遇展现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首先,银杏树小姐姐的人物设定,符合儿童奇思妙想的天性。其次,从银杏树的视角理解人类感到幸福的美食和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在植物的眼中究竟是怎样一种酷刑。最后,一边呈现便捷生活、富足物质和发达科技,另一边渲染漫天黄沙、污染河流和刺鼻空气,难道人类文明的进步就必然带来生态环境的恶化吗?银杏树的遭遇,使儿童打开了原本相对固有的社会认知,反思我们对于保护环境可以做出哪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儿童戏剧更需要文学精神的观照,因为孩子比成人更需要被触摸到内心,更需要通过形象和情感的方式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这些年,我笔下的主角无论是树还是昆虫,写的都不仅仅是故事,而是人的情感和精神。”[3]这不仅是剧作家冯俐的心灵独白,也是为儿童剧的编创指明的方向。创作儿童剧,既需要通过儿童的视角来拓展儿童对于社会外界的认知,也需要通过文学精神来关照儿童的内心世界,并以此对人性展开思考,对人类所处的境遇与选择产生共鸣,进而理解人类的情感与精神。
二、以儿童心理组织戏剧要素
儿童对于语言的表达和理解与成人有很大差异。在表达方面,成人形容事物的大小、长短会以计量单位表述,儿童则会附加肢体语言,年龄稍大的儿童还会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例如,这根绳子有我家客厅到卧室那么长,这个碗和爸爸的手掌一样大,等等。在语言理解方面,对成人说“观察、思考、行动”,他们能立刻理解指令并做出相应行为。但是儿童,尤其是学龄前儿童,他们听到诸如此类的描述会一脸茫然。若换成“看一看、想一想、做一做”,再加上辅助动作,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告诫儿童“不要玩火,否则手会被烫伤”,他们可能不理解“火”的危险与“烫伤”的感受。换成“不要玩火,不然手指会痛”,再配合摸着手指做出愁眉苦脸的表情,儿童可以通过表情判断,接收“火会造成危险”的信息。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儿童的词汇量不如成人丰富,对语言的理解也无法仅用语言形容,需要通过听觉、视觉、触觉等全方位的感知来接受和传递信息。
儿童剧的创排同样要遵循上述规律。儿童剧的规定情境刻画、角色形象塑造,以及戏剧冲突的发展激化等,都需要灵活运用儿童语言的特点。杨锋曾从儿童剧语言的儿童情趣、动作感与富有色彩三方面进行过深入探讨,他认为少年儿童处于成长阶段,好奇心强,求知欲盛,又具有好动性、模仿性,儿童剧要表现出富有儿童情趣的个性化语言、富有诗意的色彩化语言,还需具有强烈夸张的动作性语言,并强调儿童动作不是游离于语言外的附加物,是由戏剧引起,辅助语言表达的手段。[4]
(一)规定情境要适应儿童联想
规定情境指剧作家为角色规定的具体环境和实际情况,以及艺术家在二度创作中对表演所做的内容补充。通俗来讲,是戏剧中的时间、地点、事件,以及上场任务和历史背景。认清了规定情境,演员可以迅速调整表演状态,使表演更具真实性和感染力。对儿童剧来说,以符合儿童的联想视角融入规定情境,可以让儿童产生强烈的代入感,更加沉浸于剧情发展和人物表演中。
《小萤火虫跟宝宝一样……》运用表现主义戏剧的歌队形式,重要场景的规定情境通过歌队演员以身代景展现。比如,萤火虫妈妈被宝宝关进玻璃瓶,规定情境是压抑、禁闭的环境。编剧提示可以运用冷色调灯光,营造出冷漠、凄凉的舞台氛围;演员面色冷峻、步伐沉重地围绕在萤火虫妈妈身边,并阻挠萤火虫妈妈冲破玻璃瓶,也有助于表现这一规定情境。歌队演员表现出粗暴、隔绝的情感状态,则衬托出萤火虫妈妈在玻璃瓶中的渺小与无助。
规定情境的营造和刻画暗合了儿童联想的特点,儿童的感性认知远比理性认知敏锐。编剧将一场看似只有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表现孤独、凄凉的段落,借助众多歌队演员的形式呈现,使规定情境充实饱满,也使儿童在情感上共情萤火虫妈妈的凄惨境遇,继而在潜意识里埋下了同理心的种子。
因此,将符合儿童心智的联想手段融入儿童剧规定情境的营造中,是为儿童内心世界与儿童剧之间建立起情感桥梁的重要一环。它既能抓住儿童的注意力,使其专注于情节发展和人物遭遇,也能激起儿童的情感共鸣,使其心随戏动,入戏而思、出戏而悟。
(二)形象塑造要具有儿童情态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戏剧表演中的重中之重,它是剧作家与观众沟通思想的桥梁,是导演展现戏剧情节的抓手,还是演员塑造角色的表演依据。鲜活的人物形象可以令人记忆犹新,如《马兰花》中勤劳善良的小兰、阴险狠毒的老猫,《十二个月》中刁蛮任性的小女王、自私恶毒的继母等。正是鲜活的人物形象,配以动人的故事情节,才使这些作品经久不衰、传为经典。儿童剧的角色塑造,需要遵循儿童的情态特点。丰富的肢体语言与风趣形象的台词语言,可以拉近观演关系,激发儿童兴趣,令观众对角色形象产生深刻记忆。
儿童剧《木又寸》,编剧以拟人的手法塑造了一位烫着波浪卷发、腰身粗圆,喜欢与身边树拉家常,对新事物充满好奇的柳树大姐形象。这一形象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小区居委会里带着红袖箍的大妈们——她们平时三五成群地聚在树荫下,说东家长,拉西家短,叉着腰指点着辖区内的“江山”。演员在塑造柳树大姐时,同样将儿童关注的情态动作融入角色塑造——复刻大妈们的大嗓门、叉着腰指点江山的样子,以及摆弄柳条般的头发等典型动作,让柳树大姐的形象有了更加准确的定位。
儿童剧《小萤火虫跟宝宝一样……》,编剧把叶子比作野花的妈妈、泥土比作野花的外婆,宝宝之所以选择不摘花就是害怕野花离开了母亲。编剧巧妙地运用小花、叶子和泥土的关系,再赋予生动童趣的情态语言,让观众理解万物间的联系与情感。对比西子私藏萤火虫的行为,这表现了小主人公的成长与对待事物态度的变化,她学会了站在他人角度思考问题,建立同理心,也为放飞萤火虫的剧情发展作了必要铺垫。符合角色形象的儿童化语言有助于突出人物特点、展现人物性格、顺应人物成长,也能让观众更好地理解角色,并与之产生共鸣,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三)戏剧冲突要符合儿童性格
戏剧是反映生活,表现“人”的艺术。生活中面对不同的人物、事件和环境,都会产生相应的认识和态度,从而决定思想,产生行动。不同的思想会有不同的行动,不同的行动便有可能引发矛盾冲突。矛盾冲突有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环境之间的,还有人与自身内在精神之间的。一出好戏需要与主题契合的题材和结构,扣人心弦的情节,性格鲜明的人物和台词。强烈的戏剧冲突是构建戏剧情境、展现人物性格、反映生活本质、揭示作品主题的重要手段。同样,儿童剧作品也需要戏剧冲突,但切勿表现浓重的成人色彩,也不能简单地定义为“‘哄’孩子们‘玩’的‘儿戏’”[5],以免使人物形象和情节事件荒诞,影响观众的审美观赏。
在《山羊不吃天堂草》中,编剧考虑到青春期少年的敏感与柔软,构思了城里人的刻薄、同行间的竞争、家中债务压力等极端场景,让主人公明子饱受打击。层层递进的重压剧情下,明子的好友紫薇为治疗腿疾,决定和发小徐达前往美国。好友的离别,令本就心情低落的明子更加难过。徐达将他比作“护工”,让他把紫薇亲手做的复健车“卖了换钱”,并额外支付工钱“用钱再买些羊”等一系列看似明理却不近人情的话语,深深刺痛着明子的心。青春期的少年自尊心强烈,当他们遭受误解、秘密被公之于众后,他们内心羞愧、愤怒。这些符合青春期少年心理特征的描写,使明子的人物内涵饱满,也为此后人物情绪的爆发和矛盾冲突的激化奠定了坚实的心理依据。
三、以儿童立场实施教育理念
在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的教育理念也从“关注学科”向“关注人”转变。提升儿童的综合素质,使其具有健全的人格、乐观的性格、开阔的胸襟,以及求知的精神,成为当今教育的重点,也成为儿童剧编创的重要原则。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戏剧是培养人们合作精神的极有效的途径,而从审美的角度看,它也充分体现了情感的共享功能。”[6]一部优秀的儿童剧甚至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为他们打开认知世界的窗口,树立崇尚正直的榜样。欧阳逸冰曾总结,一部杰出儿童剧的魅力就在于让儿童终身咀嚼不尽,因为那是渐次加深的审美过程、长期回环往复的体验、人生不同时期记忆的数度重解。[7]将优秀的主题思想更有效地传达给儿童,使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行在事里,需要剧作家具备优秀的编创能力,深谙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将适用于儿童的教育方法巧妙地编织在故事中。
(一)“启发性”教育理念中的角色成长
为了迎合儿童的理解趣味,部分儿童剧作品故事情节简单化、人物性格单一化、角色造型脸谱化,且台词语言中充斥着说教意味,即便与观众展开交流互动,也是以对错衡量的判断题。这类剧目缺乏对人物内在动机的剖析,更缺乏对人物弧光的延伸,所传达的思想流于表面。
为避免这些问题,冯俐在剧目编创中采用了启发性的教育方法,让戏剧情节和人物角色更加贴近儿童生活,触动儿童内心。启发性的教育方法是将剧中的主题思想与角色的成长经历相结合,依靠角色性格的成长变化推进故事发展,用抽丝剥茧的方式带领观众一步步揭晓答案。这种方式能够让观众获得强烈的代入感,强化情感体验,从而与角色共同感悟剧中所传达的主题思想。
在《山羊不吃天堂草》中,编剧就融入了启发性的教育方法,引发观众对“山羊为什么不吃天堂草”的思考,让观众跟随剧情的发展窥视主人公明子的生活并探索答案。观众看到了明子替父还债进城打工的窘况,看到了明子拒绝师傅怂恿偷木料的坚持,看到了明子为紫薇打造复健车的纯真,也看到了明子因赌博萌生携款潜逃的内心挣扎。这一切都牵动着观众的心,观众与主人公一同探索、经历,最后领悟“非己之利,纤毫勿占;非己之益,分寸不取”的道理。
(二)“直观性”教育理念中的“共情”培育
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指出:“四到七岁的儿童还不知道怎样为他们所用的概念下定义……还不能用语言表达他的思想而仍然处于行动和操作的境地。”[8]换言之,儿童剧需要通过建立具象认知来表达抽象概念。直观性教育就是通过实物直观、模像直观和言语直观等手段,让儿童对所学事物或学习过程形成清晰表象,由此获得感性认识并丰富直接经验。
儿童剧《木又寸》,开场展现了一幅山林狼藉,小动物们流离失所,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衰败景象。编剧借用山鹰独白,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动物们的慌乱,其中台词写道:
大家都在逃,鸟、松鼠、兔子,晚一步就完了!哦,啄木鸟被人用弹弓打下来了,它的孩子们就随着倒下的树,被摔成了肉酱!河里漂满了大树的尸体!他们把好好的树都砍死,然后丢到河里,这到底是为什么?你们听到了吗?你们听到了吗?这是电锯。现在他们拿来了电锯!一个电锯比十个斧头还可怕!只要往你腰上一放,马上你就两截儿了!①所引台词根据编剧冯俐提供剧本。
直观、形象的台词,可以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动植物恐惧、害怕的情态,并从心理和情感上与角色共情,引导观众对人类乱砍滥伐的行为反思与自省。同样,在《小蝴蝶的妈妈在哪里?》中,编剧也融入了直观性的教育理念,解读了蚕进化成虫的过程。通过画着蚕的生命周期图的微黄叶子、四件大小不同的蜕下的皮,以及蚕蛹的图片等道具,再配以蚕宝宝们生动有趣的讲解,演示了蚕的一生。编剧运用模像直观和言语直观的手段,将事物的模拟形象配合形象化的言语,多角度强化感官知觉,加深观众对内容的认知和理解。
(三)“科教统一性”教育理念的知识科普
大自然、小动物是儿童剧中经常出现的元素。大自然是儿童的教科书、游乐场,也是儿童的良师益友。在大自然的广阔天地里,孩子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玩耍、探索,感知大自然有助于启发孩子的好奇心,锻炼注意力,激发儿童的创造性思维,培养情商。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对儿童成长有着极高的教育价值,为他们探索未知世界提供了无穷的源泉。小动物能给儿童带来温暖和安慰,对他们心理的健康和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研究显示,经常接触小动物的儿童具有较高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懂得爱与关心。接触小动物越多,儿童的社交能力越强。当儿童和小动物嬉戏时,内心的兴奋和开心是任何动画片或电子游戏替代不了的。因此,创作以自然生态为主题的儿童剧,对于儿童探索自然、了解自然、亲近自然具有正面导向。
冯俐的儿童剧作品有许多与大自然、小动物有关的设定,这不仅反映出她对自然生态的热爱与关注,也体现了她对儿童天性喜好的了解和熟知。这些作品不乏保护生态、爱护自然的教育理念,兼具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将自然的生态规律、物种特性等知识,通过儿童剧的形式向孩子普及,体现了“科教统一性”的教育理念。
比如在《萤火虫姐弟历险记》中,我们看到了萤火虫姐弟的精彩历险,小哲、曼曼与科学家们为改善生态环境做出的努力,还学到了“环境指标性生物”一词,了解到萤火虫的出现能够反映我们所处环境的污染指数。在《小蝴蝶的妈妈在哪里?》中,我们看到了蝶儿神奇的一生,也了解到像蝴蝶、飞蛾这类雌性昆虫在产卵后只能存活两至三天,还有的雌性昆虫会因为产卵导致体内脂肪耗尽,无法活过一个晚上的自然规律。在《木又寸》中,我们看到了一棵银杏树的经历和变迁,看到了人类对于自然开发和生态破坏的毫无节制,也了解到柳树会因杂交失去散播柳絮传播种子的能力,以及蝉一生要蜕五次壳——其中四次在地下进行,最后一次才会钻出土壤、爬到树上、蜕去干枯的浅黄色的壳,变成成虫。
结 语
如果说大部分儿童剧作家在作品里表现的是顺应成长,以乐观积极的心态面对挫折、克服磨难,冯俐更愿意表现的是认识苦难、接受苦难、理解苦难,再勇敢向前。她笔下的主人公通常都具有一颗善于发现问题的好奇心,这也成为指引主人公成长道路的灯塔。
通过分析《山羊不吃天堂草》《木又寸》《小萤火虫跟宝宝一样……》《萤火虫姐弟历险记》等儿童剧作品,我们注意到正是冯俐对儿童身心发展的精准把握和正向引导以及对儿童成长的殷切期望和细致关怀,才得以梳理出一套适应各年龄段儿童成长的戏剧理念。即透过儿童视角聚焦成长认知,展现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认知形成和影响因素,有助于儿童教育过程中的正确认识和积极引导;运用儿童心理组织戏剧要素,让作品内容贴近儿童内心,给予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立足儿童立场实施教育理念,使儿童更容易接纳作品所传达的思想。
总体而言,冯俐编创的作品没有自上而下的强加和审视,只有俯身于儿童身旁的倾听和交谈;没有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只有亲近儿童的童心童趣、童言童语。她编创的文本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还兼具广博的知识性和贴心的教育性,让儿童在观剧的过程中,为他们的童年添上一抹来自戏剧的启悟,也为他们的健康成长铺上一块攀升的台阶。